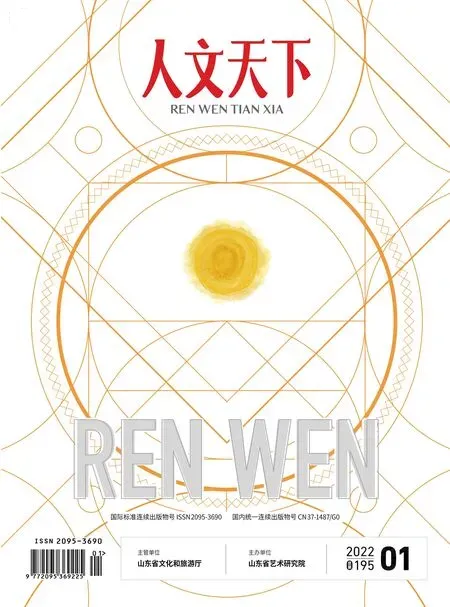精雄老丑贵传神
——石涛的书法及启示
■ 张 彪
明末清初,是汉族士人群体中“天崩地解”的时代,其思想情感与生活状态承受了较为沉重的痛苦与磨难。相比于元朝“九儒十丐”民族政策下汉族知识分子大量投身于杂剧、散曲等文艺创作的现象,身处家国之变且笼于“文字狱”等高压政策下的明末士人,他们要么组织反抗以身殉明,要么遁入空门苟全性命,要么潜心学术将毕生精力放在金石考据或远离政治的文艺活动中。处于这一时代剧变中的石涛(1642—1707),便选择了遁入空门。石涛原姓朱,名若极,除法名原济、别号石涛外,尚有苦瓜和尚、大涤子、小乘客等多种别号,与八大山人(朱耷)、渐江(弘仁)、髡残(石溪)并称“清初四僧”。清代李驎在《大涤子传》中写道:“大涤子者,原济其名,字石涛,出自靖江王守谦之后。”作为朱明宗室,明亡后,幼年石涛出家为僧,一生漂泊不定,鬻艺为生,晚年定居扬州。
一、石涛的书学思想及面貌呈现
石涛一生,以丹青显,历代学者也多将其列入画家的行列,绝少提及其书名、书法。个中原因,除却石涛画名大盛、传世作品多为画作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可能就是其独立书法作品存世较少且多以题画的形式留存。但不可否认的是,零星传世的书法作品,同样奠定了石涛在书法史上的地位。
由李驎的《大涤子传》可知,石涛学书,与时风相谐,取法广泛。从其传世作品来看,他的书法面貌较多,可以说是五体兼备,且不同书体之间相互杂糅,同一书体之中又显现出不同的风格取向。如其篆书,既有玉箸篆的样貌,亦不乏两汉篆书金文的风骨,且在其隶书作品中,又时有篆书结字糅入;至于其楷书作品,则时见出自钟繇的古拙、潇散之作与取法倪瓒的瘦硬、挺拔之作。下文将结合石涛具体的书法作品,对其书学思想及书法风格展开讨论。
(一)刀笔相参——篆书
白谦慎在《傅山的世界》中提及,明末清初是一个弥漫着怀旧气氛的时代,文艺界中尚“奇”、尚“古”的风气同样蔓延到了书法领域。对“奇”和“古”的追求,自然地使书法家将主要取法对象放在了三代、秦汉的金石文字之中,而石涛“上溯晋魏,以至秦汉,与古为徒”,正是彼时书学取法的一个缩影。
石涛的篆书作品传世不多,笔者目力所及,仅有两件。一件是其所题“淮扬洁秋之图”六字,另一件是他在《清湘书画稿》其六中所题“老树空山一坐四十小劫”十字(见图1)。前者是典型的秦汉小篆面貌,虽仅有六字,却显示了石涛扎实的学古功底和灵活的创作运用,在圆转流畅的线条中,尽显书法用笔的“婉而通”。后者则是取法汉代金文篆书而来,属于篆隶掺杂程度较高的一种“篆书”。汉代金文中的篆书作品,多仅存篆书结字,用笔则完全是化转为折的隶书法度,石涛的这件作品取法于此,以畅快的用笔,将肃穆的结字表现出来,兼顾了结字中的“刀”意,与墨迹中的“笔”意,刀笔相参,气韵别具。

图1 石涛《清湘书画稿》题字
石涛在《赠高凤冈诗札》中录有自作诗一首:“书画图章本一体,精雄老丑贵传神。秦汉相形新出古,近人作意古从新。灵幻只教逼造化,急就草创留天真。……”在诗中,石涛阐述了其对于书法、绘画、篆刻的审美追求,结合彼时文人参与到篆刻创作中这一史实,我们或许还可以解读出,其在篆书取法中,所追求的“老丑”与“天真”,似乎与篆刻尤其传世古印锈蚀斑驳的美学特征有着不可分割的因果关系。鉴于石涛所处时代的文人多自篆自刻印章的史实,笔者大胆假设,对篆刻有着明确审美追求的石涛,可能也参与到了篆刻创作之中,其自用印中,当不乏自篆自刻的作品,如此则又多了一项研究石涛篆书的资料。
(二)与时颉颃——隶书
明清鼎革之际,士人寒噤,“访碑”活跃,随着金石学的复兴,书法界出现了诸多如王时敏(1592—1680)、郑簠(1622—1693)、朱彝尊(1629—1709)、万经(1659—1741)和傅山等一批擅于隶书的书家,处于此种文化环境下的石涛自然也对隶书有所造诣,并取得了独到的成就。
石涛的隶书,用笔生动活泼,结字聚散生姿,章法参差错落,一任自然,气息接近同时期的郑簠、傅山等人的作品。石涛非专业书家,在规矩、法度中与郑、傅相比有所不逮,但其胜在天真,这应与其隶书作品多作题画、出之于无意有关。而郑、傅虽专擅于书,但作书时难免刻意为书,为法所缚。清代秦祖永在《桐阴画论》中说石涛的隶书“大江之南,无出石师右者”,看中的当是其笔下的天真,石涛隶书在当时之影响可见一斑。
认知科学家泽农·派利夏恩(Zenon W. Pylyshyn)进一步指出,认知就是一种计算。[1]他认为,认知有机体能以自己的行为方式对自己的心理活动进行表征,而后对这些表征进行操作——展示出某种认知行为,这与电子计算机的工作原理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因此,把认知有机体的认知行为看作是一种计算行为是可行的。简言之,认知就是计算。另一位认知科学家萨迦德(Thagard P.),以更为简洁凝练的语言把认知即计算概括为“计算-表征的认知理解模式”简称CRUM)。[2]
具体来说,石涛的隶书可分为古拙与清雅两种基本风格。
《山水图》十二帧其二、其三、其四、其七、其八、其十一之上的题字,当为石涛隶书中古拙风格的代表之作。其笔较为沉实率意,章法错落有致,结字则独守扁方,且多以隶笔运篆书结字,奇古可爱。如第三帧中“秋老树叶脱,林深人自闲”的“深”字(见图2),即由篆书隶定而来。

图2 石涛《山水图》题字
《唐人诗意图册》中的题诗与《爱莲图》中的题字(见图3)可以看作是石涛隶书中清雅风格的代表。其用笔轻盈,提、按动作明显,雁尾表现精到,章法中规中矩,与《曹全碑》如出一辙。

图3 石涛《爱莲图》题字
除此之外,石涛的隶书中尚有一种兼带行草笔意的面貌。这类隶书于静穆中现潇洒之相,堪为石涛隶书中的精品。
石涛所处的时代,隶书创作多以周亮工(1612—1672)、朱彝尊、万经等书家的清雅风格为主,而如郑簠、傅山及石涛般对隶书稍加写意的书家,则为数不多。个中原因,杨守敬在《平碑记》中解释到“分书之有《曹全》,犹真行之有赵、董”,可见,清初的书家是在帖学审美的基础上来选择相应的汉碑作为取法范本,或干脆用帖学的标准去表现不同风格的隶书。在此氛围下,石涛等人能不囿时风,去表现隶书的古拙,这不仅是冲破藩篱的勇气,更是对艺术强烈敏感力的体现,此正如石涛所说“精雄老丑贵传神”。
(三)不主故常——楷书
石涛的楷书主要以小楷的面貌呈现,取法则集中于钟繇及倪瓒。
《西园雅集图》和《搜尽奇峰打草稿图》后的跋文是石涛取法钟繇小楷的代表作。前者中规中矩,从用笔、结字到谋篇布局,均恪守魏晋法度,用笔多钝入钝出,笔画厚实圆润,字形略扁而多存隶意;而后者则在此基础上融入了些许行书笔意,于笔画连带中更见活泼。
《黄山游踪》册页中散见的题字为规模倪瓒的小楷而来,而《人马图》与《古木垂荫图》中的大篇幅题字,则集中表现出石涛对倪瓒小楷的取法与发挥。相较于对钟繇的取法,石涛对倪瓒小楷的取法多了几分自我发挥的成分。石涛说:“倪高士画如浪沙溪石,随转随注,出乎自然,而一段空灵清润之气,冷冷逼人。后世徒摹其枯索寒俭处,此画之所以无远神也。”倪瓒山水多用干笔淡墨,画上题字也多用此法,石涛在取法倪瓒时,为了破除干笔淡墨所致的“枯索寒俭”,多用湿笔、重墨甚至以涨墨来进行发挥。依此题画,不仅避免了倪瓒的“寒俭”,也与其水墨淋漓的画风相表里。此外,石涛在取法倪瓒的小楷创作中,也时常掺有行草笔意,时有一篇之中,楷书起首,渐次牵丝映带增多,最后则演变为行草书收尾,这是石涛书法中常见的一种现象,其书法的自由、不羁与其画家的身份正相表里,同时也流露出石涛在书写时的情绪、节奏变化,具备强烈的即兴色彩。
(四)自有我在——行草书
李驎在《大涤子传》中提到石涛“于东坡丑字法有所悟”,可以想见石涛对苏轼的书法是下过一番苦功的。苏字对他的影响在《客三槐堂诗页》和《赠翁山诗札》中体现得较为明显。而石涛最常见也最成熟的行草书面貌,是与时代书风密切相连的。石涛说“笔墨当随时代,犹诗文风气所转”,其书学思想接近同时代的王铎(1592—1652)、傅山,尤其是与傅山同样对“丑”的认同及在表现技法中对于水、墨的运用,令石涛的行草书法在沉浸于时风中时,更为接近王铎、傅山两家。但是,能够说出“纵有时触着某家,是某家就我,非我故为某家也。天然授之也”的石涛,在取法时风之时自有其独立性所在。
石涛对时风的追求,是在保留自我的前提下展开的。石涛说,“我之为我,自有我在”,“我自发我之肺腑,揭我之须眉”,故而他的行草书法虽然接近苏轼、王铎和傅山等人,却始终有“我”的存在。
石涛的行草书,不仅受古今书家的行草作品影响,他对隶书、楷书的学习,也影响到其行草书的创作。石涛将苏轼的扁方茂密及王铎、傅山等人的开张跌宕,与其隶书左右开张、波挑分明的意趣相结合,形成一种富有金石趣味、古拙朴茂的行草书面貌,其意近于王献之的“破体”,其迹则自出机杼,这在其《山水图》十二帧其一、其五、其六、其九、其十、其十二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二、石涛书法的启示
(一)理论的引导
赵孟頫题《秀石疏林图》:“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应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赵孟頫所说的“同”,除字面中的“同”之外,更是法理上的“同”,而除“同”之外,此诗中最重要的当属“会”字,不是会与不会的“会”,而是会心的“会”。
石涛对“同”与“会”的理解较为深刻,因而也才有“画法关通书法津,苍苍莽莽率天真”这样的诗句。所以笔者认为,《石涛画语录》不能单纯地当作画论来读,其中所提到的理论与主张,同样也在他的书法作品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石涛画语录·氤氲章第七》中提到,“得笔墨之会,解氤氲之分,作辟混沌手”,堪作汉人所谓“笔迹者界也”的另一种表述,也即“笔墨”所形成的“笔迹”,是在纸上去“界”,去“辟”,去分割空间。分割空间,在当代书画理论中比较流行,但早在汉代,便已提出这一观点,经过石涛,发展到现在,只不过变了说法,其内在精神还是一致的。
石涛善于师古,又善于化古,他在《石涛画语录·变化章第三》中说:“我于古何师而不化之有。”在本章中又说,“我之为我,自有我在。古之须眉,不能生在我之面目;古之肺腑,不能安入我之腹肠。我自发我之肺腑,揭我之须眉”。这句体现了石涛的独立创作观,即“有我”,但在时刻强调“我”时,也不排斥外界、时人的影响。只不过他将这种影响看作“是某家就我也,非我故为某家也。天然授之也”。然而,他这种“天然授之”的理论与徐渭的“从来不见梅花谱,信笔拈来自有神”的思想不谋而合。这是一种自负,更是一种传承,正如清代金农的漆书,与汉代简牍“诏书”二字如出一辙。艺术中,需要自负,更需要传承,但这必须建立在师古能化的基础之上。
除了在《石涛画语录》中表达了石涛的书学理论与主张之外,在其诗文之中,也零星存在着一些关于书法的主张。前文所述石涛的几首题画诗句即是如此。其中“精雄老丑贵传神”一句,尤为重要,几乎包涵了石涛全部的书学思想与创作主张。
在帖学盛行、董其昌“秀媚”书风大行其道的时代,石涛提出“精雄老丑”的书学主张,体现着一位艺术家对于艺术的敏感与敏锐,这从他对汉隶、对苏轼“丑书”的认同与学习中便可得到印证。石涛书法的“丑”,体现在他“支离残腊倍精神”的隶书之中,体现在他“精雄老丑贵传神”的行草书之中,更体现在他“珍重一身浑是玉”的自负与无奈之中。其所处时代的书家对“丑”的追求,最初不免带有民族情结,但最终上升为艺术追求,这种对“丑”的追求,当作后来“碑学”审美的滥觞,当无不妥。
而石涛所说的“传神”,则是其书学思想的另一层面。“神”与“形”相对而存在,石涛不贵“形”而贵“传神”,体现了他在书法取法中的侧重。刘熙载《艺概》中所说“学书通于学仙,炼神最上,炼气次之,炼形又次之”与石涛所说相合。而至于这里的“神”,是我“神”是他“神”?从石涛“我于古何师而不化之有”的说法中可得窥见,其是从他“神”中化出我“神”,即入古出新,自有我在。
石涛的书学理论与主张及对我们的启示,大致可以总结为以下五点:其一,书画相生,这不仅是形式上的相生,更是法理上的相生;其二,“精雄老丑”,石涛对“雄”与“丑”的追求,说到底是对“古”对“拙”的追求;其三,师古能化,石涛在学古时,始终怀着“我”去学古,这必然令其不囿于古,能破古之藩篱而出己之新意但又合乎古法;其四,“传神”,石涛所说的传神,是说学古当“师其心而不师其迹”,从而形成自己的面貌;其五,对时代的关注,石涛在其理论中未曾直接谈到对时风的学习,但在其作品中却体现出了浓厚的风气,这使其在学古的基础上又能够找到出新的方向,也使自己不至于因过于“入古”而遭到时人的不理解,这对于一个以书画自给的人来说是极为重要的。
(二)作品的提示
石涛书法的具体面貌,前文已详加论述,这里所谈到的作品,主要指书法的章法、形式。石涛的书法多作题画之用,加以其书法面貌众多,题画时往往一题再题,因而也就形成了独特的章法与形式。
石涛题画书法的章法、形式众多,除了一种书体一题到底的形式之外,尚有其他几种形式。一种章法是标题、诗文作一种书体,年月及名款又是一种书体。这类作品如《淮扬洁秋图》上的题字,标题作篆书,其余则用行楷书;又有《溪阁图》上的题字,题诗部分作隶书,年月名号款则作行草书,这一类章法是画家题画的一种常见形式,相对普遍。另一种章法是在同一件作品中,用不同书体、不同字径题写相当字数、不同段落的诗文。这类章法接近于古人的题跋作品,不同书家的不同书作聚于一处,形式虽古已有之,但是克服时间与空间的障碍而出自一人之手,且摆脱手卷的形式,在同一时间、空间中将这一形式展示出来,在当时则较为新颖,这也不排除石涛主动做形式的可能性。如《巢湖图》上方所题三段文字,有两段用隶书写成,一段用行书写成,而两段隶书风格也大相径庭。这种章法的形成,可能是作者画毕之后,即时加题诗文,事后兴之所至,再题一段,或者友人索画,要求加题……至于这种章法是怎么来的,在此不作探讨,但就这种章法、形式本身,可进行一番研究、学习。
结合前文所说石涛传世书法的面貌及章法形式,笔者认为有如下四点颇具启示意义:其一,书体糅合,隶书多篆意则高古,楷书多隶意则高古,行草书多篆隶意则朴茂雄浑,隶、楷书多行草意则活泼潇洒,在石涛的书作中,多有这样的糅合,这也是石涛书法高古、活泼的关键之所在;其二,即兴,石涛多在同一段题款书法中,由楷书过度到行书乃至草书,这不仅不会让人感到突兀,反而给人以极强的书写、时空推移之感;其三,重水墨,石涛题画书法多有涨墨及墨色浓淡变化出现,这在明代以前多被看作是败笔,而在石涛所处时代,却成了一种时尚,一件书法作品所包含的丰富信息,不仅在于字形结构、风神气骨等方面,也存在于诸种矛盾的对比之中;其四,章法及表现形式的多样,石涛多将各种书体集于一纸之上而形成一件作品,这种形式既存古朴又颇具新意,在当今注重形式的书法创作当中,可资借鉴。
结语
石涛作为画家,在书法方面的造诣,放在古代来看并不稀奇。石涛学书比学画要早,但他最终是从画家的角度看待书法,所以他对书法的理解,与其他书家的理解不尽相同。石涛重视对不同书体的把握,敢于打破书体的界限,大胆地将水墨画法运用到书法之中,善于用水,在书法的布局及形式构成上自出机杼,以“有我”的态度学习古人的书法,外师“古人”,中得“心源”,最终成就其注重形式、朴茂雄浑、灵活多变的书法风格。
自古以来的画家,无不善于临池之道且传统功夫深厚,从“四僧”到“扬州八怪”,从“海派”的赵之谦、吴昌硕到近现代的齐白石、黄宾虹等前辈书画家,无不在书法方面有着精深的造诣。但在当下,画家的书法多不通笔法,传统根基不扎实,因而,石涛书法在当下的启示,不仅仅对于书法家而言十分有益,对于画家来说同样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