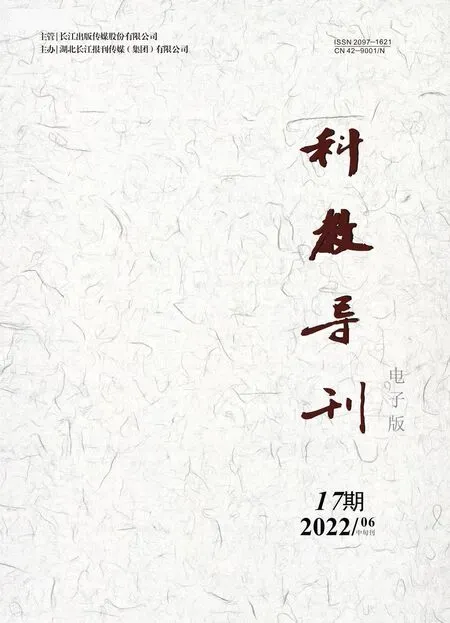“好感传播”视角下的新闻实践:观念与路径
凌 姝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湖北总站,湖北 武汉 430000)
在传播学领域的经典著作《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中,传播学学科的奠基人之一哈罗德·拉斯韦尔曾经对宣传作出自己的定义──宣传仅指通过重要的符号,或者更具体一点但欠准确地说,就是通过故事、流言、报道、图片以及社会传播的其他方式,控制意见。宣传关注的是通过直接操纵社会暗示,而不是通过改变环境中或有机体中的其他条件,控制舆论和态度。
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国内舆论环境中,“意见场”“舆论场”的形成也在不断地冲击着新闻实践领域的新闻生产环节、新闻价值评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2年工作会议提出要遵循国际新闻传播规律,持续深化“好感传播”,引导国际社会更加深刻感悟新时代中国的可信、可爱、可敬,“好感传播”成为近年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相关工作会议中频频亮相。
“好感传播”概念的提出,折射着主流媒体宣传观念的变化,也为新时代背景下的新闻实践提供了可借鉴的传播路径。本文试图从概念的提出、观念的达成路径两方面探究“好感传播”视角下的新闻实践。需要指出的是,“好感传播”在作为概念被提出时,其语境更多指向国际传播领域,但本文论述的侧重点为宣传观念转变后的新闻实践,并未将讨论范围局限于国际传播领域。
1 好感传播:概念的提出
1.1 宣传观念之变
近十年来,乃至更长的时间坐标轴中,数字化浪潮的席卷而来成为国内外传播环境的核心变量之一,深刻地影响着新闻实践的方方面面。“新闻是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在新的传播环境中不得不面临诸多审视:谁来对新近发生的事实进行报道?报道之后如何传播?哪些新近发生的事实是需要被报道的?
问题的提出背后,实际是数字化浪潮对传统媒体新闻实践方式的冲击带来的传播环境变化。在具体展开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不妨先回顾面临数字化冲击之前,中国的传统主流媒体面对的传播环境及持有的宣传观念曾处的历史坐标。刘海龙曾详细回溯了中国宣传观念的产生、中国共产党宣传观念的建立以及1949年之后中国宣传观念的变迁等问题,本文借由既有观点及论据梳理相关情况。[1]
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传统媒体深受一体化宣传观念的影响,将新闻实践纳入组织体系看待,与这种观念相伴生的便是宣传的组织化,通过建立群众宣传网络,将宣传渗透到公民的日常生活中,这既表现在吸引群众参与,建立通讯员网络,也表现在新闻工作者深入群众。而在宣传的内容方面,“党的喉舌”可以形象准确的概括主体内容,发表符合党中央精神的相关报道。例如直至今日也在沿用的“典型报道”,通过报道各行各业符合中央精神的优秀分子,“经过他们去鼓励与团结广大群众”。总而言之,一体化的宣传观念更多体现为自上而下的统一的、单向的传播。
自90年代开始,传统主流媒体开始走向市场,媒体的市场化开始对中国的媒介场域产生影响,中国媒介场的三个关键资本开始了复杂的互动关系,即代表党对于媒体正当性的认可程度的政治资本、代表媒体在市场上获取经济利益的能力的经济资本还有代表媒体所体现的文化水准和专业能力,大部分媒体都在寻找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之间的平衡位置,文化资本则逐渐成为衡量媒体质量的标准。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传统主流媒体新闻实践所秉持的宣传观念,大体呈现为在不动摇媒体管理体制的前提下,通过宣传内容中的“语态变革”,提升媒体的制作水准。有学者指出,通过诠释与构建,传统的宣传话语与市场经济乃至新闻专业主义话语勾连在一起,例如将舆论监督与反腐倡廉相联系,将媒体在市场上的表现作为衡量媒体舆论应道的能力,用新闻表现手段和技术升级来代替新闻内容的革新,客观上也起到了自上而下的启蒙作用,培养了公众的权利意识。
进入21世纪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市民社会的力量逐步强大。反映民众生活的“民生新闻”在传统主流媒体平台上大行其道,其报道内容大多以普通社会公众以及普通消费者的权利为诉求,通过报道具体而微的民生事务,来弥合政府与公民间的问题,在具体问题的解决中,强化政府“为人民服务”的形象。
通过上述回顾,我们不难看出在数字化浪潮来袭之前,传统主流媒体正处在宣传观念的转型阶段。这种转型更多地体现在新闻实践中的表现手段升级,但却未有效解决在新的传播环境中传统主流媒体的宣传效果趋弱的难点,换言之,随着社会的发展,曾经渗透到公民日常生活中的组织化的宣传体系日渐式微,曾经垄断信息来源的传统主流媒体自身也面对着分众化、专业化的媒体内容的冲击。在这样暧昧不明的转型阶段,数字化浪潮席卷而来。
1.2 何谓今日之新闻
回到我们最初提出的问题──谁来对新近发生的事实进行报道?报道之后如何传播?哪些新近发生的事实是需要被报道的?对于经典的“新闻是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这个定义,在数字化浪潮之下,我们至少需要审视三个明显的变化,即传播主体的变化、传播方式的变化、传播内容的变化。需要说明的是,在数字化浪潮的影响下,曾经以宣传主体意志为主的单向传播向传播者与受众的双向互动转型,为了在问题的讨论中更直观地传达这种区别,笔者将前文所述的宣传主体、方式、内容表述为传播主体、方式、内容。但这里所提及的传播所指代的依旧是有明确的宣传意图、塑造受众认知方式或者对现实认识的传播行为。
从传播主体来看,由于技术平台的赋能,全民参与新闻实践成为可能,这也使得当前的新闻生态中既包含由传统主流媒体进行的新闻实践,也包含着自媒体以及个人偶然参与的新闻实践。有研究者将这样的传播主体描述“由职业新闻生产者构成的作为社会守望者的新闻业,又包含由无数个题、组织乃至机器共同构成的泛新闻生态系统”。[2]
从传播形式来看,社交媒体的平台传播成为传统主流媒体自身渠道外,新闻实践内容的重要传播平台。社交媒体平台对于单向传播模式的介入,使得新闻实践的传播形式变为以人为媒的社交分发与基于算法的智能分发的混同,可以说社交传播与算法分发共同影响者新闻内容的流动。这样的传播形式,不可避免地将本来更具公共性信息的新闻实践内容与受众本身的形象塑造、社交关系维护等私人需求混杂在一起。有学者指出,面对这样的传播网络,新闻实践也应当被放在网络化、关系化的视野中审视。[3]
从传播内容来看,多主体、去中心的传播让“哪些新近发生的事实是需要被报道的”的标准成为一种动态中多主体不断博弈才能得出的结论,相较于此前由处在传播权力中心的传统主流媒体依据党的组织工作要求确定传播内容,抑或是90年代以来,传统主流媒体在政治资本、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间寻求动态平衡确定传播内容,如今的传播内容不得不更加注重受众的话语权。
由此可见,传统主流媒体在全新的传播环境中,亟待重新定义自己的角色与位置,以适应需求的新闻实践来完成自身承载的宣传使命。当然,数字化浪潮带来的变化不仅仅发生在国内的新闻实践领域,同样也发生在国外的新闻实践领域,篇幅所限,我们不具体展开相关论述,但显而易见的是,两者在传播主体、传播方式与传播内容方面的变化异曲同工。“好感传播”的宣传观念正是在如此的国际国内传播环境之中应运而生。
1.3 何谓“好感传播”
如何理解“好感传播”?我们可以从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与使命、传统主流媒体所面临的传播环境与传播方式两个层面来回答这个问题。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党的新闻舆论媒体的所有工作,都要体现党的意志、反映党的主张,维护党中央权威、维护党的团结,做到爱党、护党、为党。”
同时,社会化媒体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模式,有学者形象的将用户的关系网络比喻为信息传播的新基础设施,而在这样的信息传播网络中,每个传播个体都能成为传播主体,每个个体也成为兼具信息生产、传播与消费的节点。[4]在这样的信息传播模式主导的传播环境中,传统主流媒体反而容易受困于以往的传播观念与新闻实践带来的路径依赖,例如在各个主流媒体运营的微信公众号中,偏重于信息生产、传播,却往往忽略网络社群的持续运营,在内容的选择中,往往更凸显自身的权威性或者专业性,却忽略了内容是否具有社交传播力。
笔者认为“好感传播”概念的提出,生动形象的折射出了传统主流媒体的宣传观念的变化所在。一方面,传统主流媒体的新闻实践更注重社交传播力,将自己视为信息传播网络的节点,赢得其他节点的好感,达成新闻内容的传播效应最大化。也就是说新闻实践中选择的传播内容是否具有社交价值、有助于其他的传播节点提升社交形象、向更多的传播节点传导,成了与传统宣传观念的补充标准。
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理解,借由这样的新闻实践,传统主流媒体试图在信息传播网络中塑造一个“好感”形象,相较于新的传播方式下的其他节点与传统的传播方式下的天然权威性,如今的传统主流媒体需要提供更加可信、充分、专业的信息,以此来赢得更多的受众,才能有路径达成自己的宣传意图。
2 好感传播:观念的达成
正是基于宣传观念的变化,传统主流媒体的新闻实践也随之发生了许多改变,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改变中的部分新闻实践不再仅仅是技术性的修补,单纯的改变新闻的话语方式,而是面对新的传播环境重新寻找自己的角色与位置。接下来,笔者将从传统主流媒体在近几年来针对传播主体与传播内容所进行的部分新闻实践中明显的特点展开论述,一窥其中变化。
2.1 传播主体:个体身份走到台前
在当前的信息传播网络中,作为传播节点的主流媒体也被放置到网络化、关系化的视野里看待,越来越多的传统主流媒体将个体身份推向台前。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联播》推出的“主播说联播”,以新媒体短视频新闻述评的方式,或提炼或解读当天的《新闻联播》内容,以“主播说”的形式消解传统电视新闻报道的距离感。[6]同样在重大的时政报道领域,新华社在2020年在哔哩哔哩平台开设“小羊在鲜花舍”账号,通过美女记者张扬的vlog将众多时政主题报道以个性化的方式进行了报道,通过展现新闻生产背后的故事来进行新闻实践,收获好感。截至目前,“小羊在鲜花舍”在哔哩哔哩平台已累计近50万关注粉丝。
在对外传播领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更是提出打造国际传播的多语种网红工作室,围绕时政、文化等不同主体推出新媒体产品,截至目前,阿拉伯语、英语、日语等多个网红工作室成效明显,其中由五位女网红组成的“一千零一日工作室”与近百家海外主流媒体连线采访。
实际上,从新闻生产流程来看,这些看似个体化的表达背后往往是相应的媒介机构充分调动传统媒体资源完成的,但以个体身份走到台前代言确实适应了当前的信息传播环境,将传统媒体的优势资源与传播节点的个体化表达有机结合,在新的传播环境中寻找自身定位。
2.2 传播内容:主流媒体“好感形象”的构建
相较于传播主体的变化,传播内容的变化则复杂得多。笔者认为,“好感传播”的传播观念折射的不仅仅是传统主流媒体对传播内容的社交传播力指标的愈发重视,更有其通过新闻实践建构起受众心中传统主流媒体“好感形象”的自身需求。
在不同类型的新闻实践中,这种“好感形象”的建构对具体的新闻生产提出的要求也不尽相同。例如在云南野象群集体北迁并返回的“一路象北”报道中,海内外多家媒体自2020年3月至2021年9月持续关注,全面立体地展现了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成果,但传统主流媒体对这一主题进行报道时,却选用了更注重欣赏性、娱乐性与受众消费价值的报道框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社都从不同角度报道象群迁徙途中的温馨场景或者趣味故事,农民捐出玉米、路边摆好的堆堆绿叶等待野象到来、误饮酒水的野象、暂时离群的小象等等,当这些更具社交传播力的内容吸引足够多的受众关注时,再对其背后蕴含的生态文明建设成果解读分析。[6]
而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道中,新闻实践中的公共属性增强,在芜杂的信息传播环境中,对新闻信息进行广泛收集、深度挖掘整合,或者是对新闻事件的背景走向进行分析预测,都是建立主流媒体专业性“好感形象”的路径。
总而言之,传统主流媒体已经在尝试突破自身,在不完全依靠体制性壁垒自我保护时,从社会化媒体的传播内容中去粗取精,同时依靠自身的专业性在更多的渠道中构建“好感形象”,再度赢取受众的注意力与信任感。
3 结语
在全新的传播环境中,传统主流媒体正尝试以适应需求的新闻实践来完成自身承载的宣传使命。无论是将传统媒体的优势资源与传播节点的个体化表达有机结合,还是依靠自身的专业性在更多的渠道中构建“好感形象”,都可以从“好感传播”的概念提出与实践路径中一窥变化。
本文从纵向的历史流变与横向的传播环境两方面对“好感传播”这一宣传观念的变化进行了详尽的展开,但涉及问题核心的新闻实践部分的论述反而相对有限,只是简单的总结了传播主体、传播内容的部分变化特点。
新闻实践的变化,不仅仅关涉到传统主流媒体的文本变化、话语方式变化,还涉及新闻生产社会学层面的相关议题,这其中既包括实际的新闻生产的流程问题、新闻从业者对新的宣传观念的认知与执行,还包括不同的传统主流媒体所掌握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本的动态博弈对新闻实践的影响等等庞杂却具体的问题,受研究可行性及篇幅限制,难以展开具体论述,有待学界、业界共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