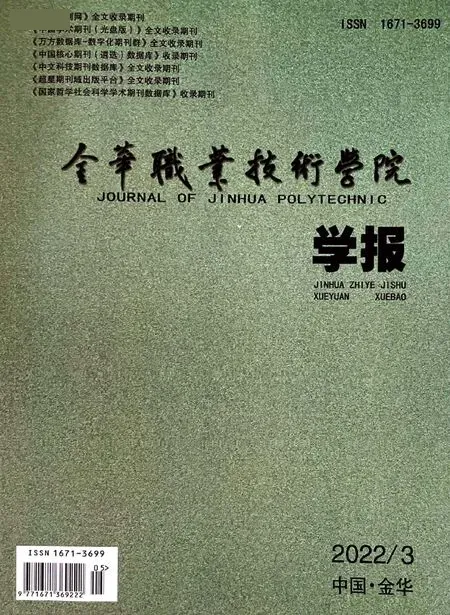李汉荣的多元“乡愁”书写
——以散文集《家园与乡愁》为例
罗维超
(陕西理工大学,陕西 汉中 723001)
思乡是古往今来为文人所喜欢的写作主题,乡愁更是文学领域中一个恒久的创作母题。但是,思乡与乡愁并不能简单地划上等号,因为乡愁并非是简单地表达思念故土之情,其饱含的意蕴是多元并存的,只有将这种单纯的思乡情感转化为意蕴多元的乡愁书写,才能为乡愁叙事提供更多的可能向度,从而丰富乡愁母题的内涵。作为生于陕南、长于陕南的地道陕南人,李汉荣对家乡的眷恋之情可谓深刻,而更可贵的是他将这种眷恋之情进行过滤转化后,转变为兼具小我情感与大我社会、传统文化与当代批判的具有丰富内涵意蕴的多元乡愁。在李汉荣一系列表达乡愁情结的作品中,《家园与乡愁》算得上是“乡愁”情结最为浓烈的一部作品。但是,除了记者丁纯曾在一篇题为《何人不起故园情》[1]的文章中以读后感形式提到了李汉荣的思乡之情,专门解读李汉荣散文集《家园与乡愁》的研究文献并不多。
李汉荣在《家园与乡愁》中有对故土的回望式怀旧、有对传统文化的审美式眷恋以及对精神家园的批判式重建,作品中不断嬗变与叠加的多元乡愁书写,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萦绕在李汉荣内心的乡愁情感及其背后的理性反思,读者更好地理解李汉荣的作品,同时丰富乡愁文学叙事的内涵。
一、故土之乡愁——回望式的怀旧
每个人的一生,总有一块生于斯、长于斯,最终也将葬于斯的土地,那里有自己的亲朋好友,也是自己成长的“根”。“中国有着祖先崇拜这种农耕文化审美传统”[2],因此中国人素来有着更为浓烈的怀旧情感,这正是最为具体、最贴近原本意义的传统乡愁。在这种传统乡愁中,回望式怀旧最先指向的便是对故乡的人、事、物的眷恋。
首先,在全书第一辑《故乡的植物》中,李汉荣描写了三十多种记忆中生长在故土的植物:有的是作者独自在郊外田野游逛时偶遇的野花芳草,有的是记忆中为“我们”健康成长立下汗马功劳的散发着阵阵药香的草药,有的是在“我们”心情烦闷时向“我们”讲授大地哲学的无言蔬菜,还有寓意着珍贵友谊的四季豆,寄寓舍得和生机深意的爷爷的柳木拐杖……李汉荣的细致描写不仅让原先陕南地区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生态资源在作品中得到充分展现,而且让读者不自觉地将作品中的陕南与现今的陕南作对比,感叹时空飞逝的同时,又被李汉荣带入到怀念故土的乡愁之中。在文章的后两辑中,驮着“我”渡过童年但最终成为“碎片”的“老黑”,伴“我”往返于学校却因误食农药死去的“小白”,失去生命前留下最后一只蛋给我的白母鸡,以及独属于母亲的农家坡,收藏着“我”许多好东西的五眼泉等,这些都是李汉荣笔下不会说话的朋友,虽然彼此无法用言语交流,却让人觉得可亲、可敬。这不仅仅是因为它们具有奉献精神,更是因为它们的身上承载着李汉荣美好的却充满遗憾的童年回忆。“传统乡愁最显著的心理特点便是怀旧”[3],因此,从对故乡的动物、植物、熟悉场景的描绘之中,读者便可充分感受到李汉荣这份独特的乡愁书写。
其次,李汉荣的故土之乡愁还体现在对故乡往事的回忆和留恋之上。由柳木拐杖引发对爷爷教导之言的回忆,由四季豆引发对朋友和妻子的怀念,由黄家院子引发对老人当年教育狗并呵护“我”的回忆,以及由家里养的猪引发对爸爸卖小猪、猪妈妈养育猪宝宝等故事的回忆,这些都成为李汉荣对故乡往事的深刻回忆。在李汉荣对往事的种种回忆中,读者几乎看不见“丑”的部分,貌似李汉荣对过去的回忆进行了“过滤”,而“过滤”后的回忆似乎只剩下美好的部分。美国学者斯维特兰娜·博伊姆提出的“修复型怀旧”恰好能道出李汉荣这种“过滤式”回忆的特点。“修复型的怀旧强调返乡,尝试超历史地重建失去的家园”[4],是对过去回忆充满想象性、修复性的重建。因此,李汉荣回顾式的乡愁中尽管流露出感伤或遗憾的情感,但是总体上体现出一种积极的情感倾向。无法回去的过往,有美好,也有遗憾,正是因为那些对故乡往事的美好又满是遗憾的回忆,使得李汉荣对故土产生了浓浓的、无法割舍的眷恋,李汉荣的乡愁情结也自然而然地展现于其中。
最后,李汉荣的故土之乡愁还体现在对故乡亲朋的回忆和留念之上。在以往多数乡愁作品中,思念故乡和思念亲朋的伦理情怀经常是相结合的。学者方维保曾提道:“乡愁是一种伦理情怀。”[5]而李汉荣的《家园与乡愁》所流露出的显然也是这种伦理情怀,如《柳木拐杖》中对爷爷的回忆留恋、《房前屋后药草香》及《农家坡,农家婆》中对妈妈的回忆留恋、《父亲赶集卖小猪》中对父亲的回忆留恋等等,这些都表现出李汉荣的乡愁情结饱含着伦理情怀。另外,伦理情怀中除了独属亲人的留恋,还有对朋友、邻居的回忆,如《四季豆》中对朋友的回忆留恋、《黄家院子》中对和善亲邻的回忆留恋、《北瓜》中对生产队长的尊敬留恋。
总之,乡愁大多是由空间转换或者人与人之间离散而形成,而空间转换或者人与人之间离散又容易激发出人们对故乡的人、事、物的怀旧情绪。因此,李汉荣对故乡的人、事、物的怀念是其乡愁情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正是这一份单纯的回忆怀念构成了李汉荣多元乡愁书写的底色。
二、文化之乡愁——审美式的眷恋
文化之乡愁是人们对本国传统文化产生的审美式眷恋。与具体存在的故土相比,文化更多的属于精神范畴,是如空气一般的存在,因此人们对故土的依恋往往夹杂着一份对传统文化的眷恋。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性格形成和生活方式。而对传统文化的留恋及对其不胜今昔的悲悼与回望,历来是文学创作中一大重要题材。对于一出生便浸润于此种文化氛围中并熟读许多经典的李汉荣来说,他内心的乡愁已不自觉地超越了地域的界限,直指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黑格尔曾对现代社会做过这样的阐释:“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新时期的降生和过渡的时代。人的精神已经跟他旧日的生活与观念世界决裂,正使旧日的一切葬入于过去而着手进行他的自我改造。”[6]在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传统的精神已被视为落伍,甚至遭到人们的遗弃,而取而代之的是现实的功利主义,这显然是一种文化的“退化”,而这必然最终导向对文化的怀旧。于是,人们开始对传统进行回望,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李汉荣正是在书写自己的乡愁时充分体现出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地方风俗的回望。在回忆古路坝时,李汉荣曾提出这样的观点:风水是一种比科学含有更多的宇宙意识和心理暗示的综合考量的潜科学[7]250。例如,闻到葱的香气,作者联想到“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古老哲理[7]68;卧于南沙河林间松下,作者梦见了骑着骏马且挥手便是万卷华章的唐朝诗人;在原公镇闲走时,令他印象最深的是一幅幅带有传统文化意蕴和传统风俗气息的春联……在李汉荣的作品中,这些时不时出现的、展示出作者对传统文化回望的正是李汉荣浓厚的文化乡愁的最好体现。
董桥在《给后花园点灯》中曾写道:“没有文化乡愁的心井注定是一口枯井。”[8]在《乡愁的理念》中,董桥又指出乡愁“是对精致文化传统的留恋”[9]。而这种“精致文化传统”在笔者看来便是审美式的文化传统。在《家园与乡愁》中,有许多地方体现出李汉荣对古典审美传统的深情回眸,字里行间更是处处流露出中国古典诗词文化独特的精致美。例如,李汉荣在欣赏田埂上的野花芳草时进入的是《诗经》、陶渊明的诗、孟浩然的诗之中的恬淡意境;他在看到庄稼地里整齐的韭菜时想到的是杜甫的诗句,感叹的是韭菜“很整齐地长在地里,像一首首对仗工稳、韵律匀称的五律”[7]60,这些都包含中国古典诗歌独特的“建筑美”与“音乐美”;他在回忆自己童年在“连二三弯”采青、放牛、采野草时想到的是贾岛的诗句——“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7]226-227,用的是此诗句中朴实无华、化繁为简的白描手法。纵观全书,处处可以感受到中国古典诗词这种“精致”文化所留下的审美式浪漫气息,以及那份不同于浮躁喧嚣的现代社会的优雅安然。
然而,随着商品经济时代的到来,现实功利主义逐渐盛行,传统文化逐渐走向衰微,李汉荣对此深有感触。于是,他追慕着古代诗人的洒脱风度,胸怀对古典文化的依依之情,借植物表达自己“断然拒绝向非诗的生活方式投降,在僵硬的逻辑之外,依旧坚持着温婉的情思和纯真的古典品质”的生活态度[7]9。
但是,李汉荣笔下这份对文化传统的眷恋,也并不仅仅局限于个人的情感天地,咀嚼一己的悲欢,而是寄寓了大多数中国人对国家、对民族的情感。例如,李汉荣在《原公镇》中描写门前长者为“面容神态,大都淳朴谦和,庄重安恬,透出自然亲和的气息,和诗书礼仪长久熏陶涵养出的古雅气息”[7]244,若没有对文化传统的主观眷恋,相信村中长者无论在何种环境中都不会有李汉荣所描述的古雅气息。除此之外,在《柳木拐杖》中,“爷爷”借由柳木拐杖教导“我”要“能扔下就要舍得扔下”[7]23,而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奉行的“舍得”哲理。
总之,在李汉荣的作品中,无论是对传统文化中哲理或习俗的书写,还是对中国古典诗词中文化审美及传统伦理素养的留念,都体现出李汉荣避免文化向功利或虚无方向退化所做出的努力。
三、精神之乡愁——批判中的建构
到不了的地方叫远方,回不去的名字叫家乡。家乡之所以回不去,最重要的不在于空间上的距离,而在于内心的距离。对李汉荣而言,地理意义上的故土已不能成为他漂泊灵魂所需要的栖息地。因为他的乡愁已超越了时间和空间,超越了实指的故乡,上升为对精神家园这个乌托邦世界的探寻与建构。
那么精神家园又在哪里呢?随着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拜金主义”逐渐盛行,那些经不住物欲诱惑的人,其精神在萎缩,甚至沦为金钱、名誉、地位的奴隶。许多文人被无法与畸形世态苟同又无处归依的苦痛纠缠着,成为一群无家可归的流浪者,此时的他们仿佛达成了一个共识——人类的精神家园,在现代都市之外。既然人类的精神家园在用钢筋水泥筑成的都市之外,那么人们就自然而然地将寻求精神家园的目标指向了大自然。而属于这一时期的文人李汉荣先生所寻求的精神家园也不例外地存在于自然田园之中,他表示,美丽的河流很难看到了……连一些小河小溪也被污染[10]。由此可以看出,李汉荣“其实是把田园作为精神家园看待的,以此拯救身陷城市牢笼的我们”[11],并在对城市的批判中建构自然的精神家园。
“西方社会中,修复性反思以卢梭为代表,卢梭倡导回归自然并以此抗衡现代工业文明,重返本真的人性,从而使现代乡愁的理性反思揭开了序幕。”[3]在李汉荣创作的散文集中,这种回归自然、寻求精神家园的现代乡愁得到了充分体现。例如,在面对被化肥反复刺激的菠菜时,李汉荣认为“技术和商业篡改了大自然的初衷”[7]51。他通过对金钱教唆下贪婪的市场的批判以及对故乡朴素的、自然的、本分的蔬菜的怀念,透露出自己对回归自然田园的强烈渴望。在回忆家乡的“连二三弯”和“凤凰山”时,李汉荣更是认为,虽然人可以赋予大自然以名字,但大自然也并“不是人的什么物、家具、资源或征服对象”[7]227。李汉荣将饱含诗意的自然田园与非诗意的现代城市相对比,表达了自己对大自然的崇敬之情和对人类藐视自然的批判之意。在李汉荣笔下,自然田园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故乡,更是渴望在喧嚣城市获得救赎与解脱的精神意义上的家园。
除此之外,李汉荣寻求的精神家园还是如张承志在《夏台之恋》中所描述的夏台一般的“邻而不近,友而不狎”[12]的乌托邦世界。在那里,本真的人性得到重返,人与人、人与自然都能和睦相处,各种语言透露出纯真无邪,正如孔子所描述的是一个“大同”世界。在散文中,李汉荣通过对丝瓜和葫芦、张家和李家关系的对照描写,展现出人与人、家庭与家庭之间如植物相互缠绕那样相互关照与依赖的生存关系。在《想念小村》中,李汉荣塑造的小村人个个心地单纯、心肠柔软,他们脾气好、性子慢[7]261,表现出作者对人与自然和睦相处的强烈渴望;在《黄家院子》中,李汉荣描绘了老人呵护“我”、教育狗的场景[7]233,表现出作者对纯真人性及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向往。上述这些都寄寓着李汉荣心中对和谐的大同世界的向往。李汉荣通过对记忆中故乡的怀念,企图在批判中建构精神家园的渴望也就显而易见了。
四、结语
多元的乡愁书写是李汉荣创作的重要表现之一,无论是对故乡的回望式怀旧、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式眷恋,还是对精神家园的批判式重建,无疑都蕴含着李汉荣的情感投射与理性思考。虽然小小的乡愁对生活在快节奏时代的现代人而言或许微不足道,但是这种多元的乡愁书写所蕴含的是作者对传统文化的肯定与珍惜,这对文化泛娱乐化的浮躁社会无疑具有乌托邦般的精神抚慰作用。另外,在回望乡愁的过程中,作者所流露出的对城市现状的反思与批判,使单纯的乡愁得到了具有价值性的升华,这不仅在文学方面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乡愁文学叙事的内涵,而且在社会现实方面给大众起到了一定的警醒作用。
总之,李汉荣将质朴的原乡思念转化为多元的乡愁书写,在融入审美式的传统文化符号与内涵的同时,企图建构一个自然的乌托邦精神家园。同时,李汉荣在这一转化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文化乡愁与精神乡愁,在回应传统内涵的基础上反思了现代文化的状态,督促世人返躬内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