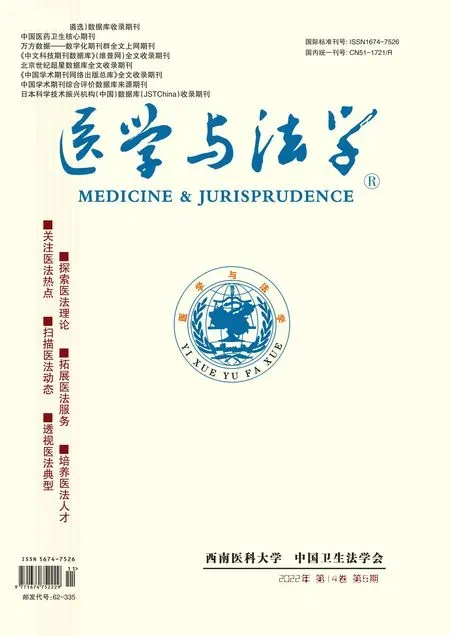我国刑法语境下“医疗行为”概念的再解释
方悦
一、问题缘起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对经济社会生活产生了一系列深远的影响。疫情发生后原本在刑法研究中备受“冷落”的危害公共卫生类犯罪进入各研究者视野,非法行医罪作为重要罪名之一,更多地被提及和讨论。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对于医疗领域的违法行为大多依赖行政法规进行规制,未形成专门的医疗刑法。因此,对非法行医罪展开研究对于规制涉医领域犯罪有重要意义。①
非法行医罪的法条表述较为简洁——“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非法行医,情节严重的”,但该条款并未提及核心构成要件要素之“医疗行为”的概念,这使本罪在面对现实中复杂多样并不断发展变化的医疗手段、诊疗技术所带来的各类问题时,颇有力不从心之感。可见明确医疗行为的内涵特征与判断标准,对其进行实质解释,对于解决类似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②、代购药物③、基因编辑④等行为是否适用本罪有重要意义。
二、现有学说评析
(一)我国现有学说评析
台湾地区的黄丁全教授在其《医事法》一书中对“医疗行为”作出定义,强调疾病诊治或某些医疗活动需要有治疗目的方可称之为“医疗行为”[1]。这可称为“诊疗目的说”。陈子平教授则将医疗行为与治疗行为进行了区分,认为治疗行为包含于医疗行为中,“治疗行为系属于以治疗为目的所为之侵袭病人身体之行为,即侵袭性的医疗行为,或可称为‘治疗行为’”,[2]其言下之意,即医疗行为包括具有侵袭性的治疗行为和非侵袭性的其他医疗行为。
大部分学者从医疗行为本身特征出发进行研究。[3]例如,有学者认为,医疗行为是改变医疗需求者的形态构造或机能、具有损伤性的医学过程,并且行为主体可以包含单位。[4]该观点认为医疗行为具有主体限定性,并将单位也作为医疗行为的主体进行讨论。但我国刑法中医疗行为的主体为“医务人员”“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否认了单位作为刑法中医疗行为主体的资格。张明楷教授主张“根据医学知识和技能从事诊断、治疗、医务护理工作”的行为,即医疗行为。[5]于佳佳博士则引入了日本的狭义“医疗行为”概念,强调“医疗行为”的危险性,并结合日本的判例展开对医疗行为的研究。[6]
总体而言,学者大多采用列举的方式意图扩张“医疗行为”概念的范围。然而,医疗技术的变化使“医疗行为”的内涵不断扩大;而列举法最大的问题,在于有违刑法的明确性要求。但过于宽泛的“医疗行为”概念,反而不利于公众健康行业的发展。综合比较各类学说及考虑我国立法的适配性,狭义“医疗行为”概念适用性更强。
(二)日本学说评析
日本《医师法》第一条规定了医疗行为的目的和主体,第十七条和第三十一条共同规定了对不具备医师执业资格者执行医师业务的处罚。⑤其“医疗行为”概念专指职业医师所进行的医疗活动。传统观点认为,以《医师法》为首的相关法律,是通过对从事医疗相关业务的人员进行卫生行政资格上的管制,间接地保持和增进国民的健康。[7]既然将医疗相关业务在保健卫生上的有用性作为资格制度正当化的基础,那么无资格行医的范围,由“医疗及保健指导”来限定,合乎逻辑。但是,无证行医不仅仅是侵犯医师职责,无证者行医在公共卫生上亦存在危险,仅以表示医师职责范围的“医疗及保健指导”的概念来定义“医疗行为”并作为其处罚依据,显然是不够的。于是日本学说和判例逐渐将实质性的危险性引入对医疗行为的判断,此后通过判例和学说,逐步形成了共识:“医疗行为”是指如果不由医生凭借知识和技术实施,则有可能在保健卫生方面产生危险的行为。[8]也就是说,其只把对健康卫生上有危害可能性的行为认定为医疗行为。该说被称为狭义的“医疗行为”,日本最高法院判例及日本厚生劳动省的行政解释亦采取该立场。
三、“业务行为危险说”的提倡
笔者认为,法益是一切犯罪构成要件的出发点,也是解释犯罪的指导思想。[9]判断行为是否属于非法行医罪的行为要件,要从本罪保护的法益出发,分析该行为是否危害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的生命安全与身体健康。“业务行为危险说”立足于医疗行为对人体的危险性,把握住了非法行医罪可罚性的实质根据:其一,对非法行医罪所禁止的医疗行为范围进行合理界定。例如,生活美容、针灸、按摩、洗牙、采耳等一些几乎没有危险性的医疗服务行业,可以排除出其在“医疗行为”概念的外延中;此外,一些并非出于诊疗目的但有刑法规制必要性的行为被纳入“医疗行为”范畴,比如摘取人体器官用以移植、采集血液用以输血、镶嵌假牙并拆卸等行为,其如果不是由医生凭借一定技术和设备实施,就可能对人体造成危险,因此应认定这些行为属医疗行为。[10]其二,该说避免了列举式的缺陷,兼具原则性与灵活性,能动态地适应医疗技术的发展。“列举的办法无法穷尽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只能在现有的社会背景中,‘暂时地’‘有限地’掌握法律材料”[11],故其既无法适应不断发展的医学技术,亦不利于保持刑法的稳定性。该说对“医疗行为”的界定把握住了核心特征,兼具限制性和开放性,使司法工作者在判断由无执业资格者实施的是否是法律所禁止的医疗行为时,可以进行合目的性的实质解释。
然而,该说并未对医疗行为的业务特征进行说明,故还应当结合非法行医罪客观构成要件中的行为要素来理解。根据现代汉语词典,“行”有“从事”的语义,故“行医”即从事医疗业务。禁止不具备医生执业资格的人“行医”,即是禁止除医生之外的人从事医生之业,这足以说明“业务”是本罪不成文的构成要件要素。在日本刑法中,非法行医是行为犯,在造成危害后果时,则构成业务过失致人重伤罪、业务过失致人死亡罪,因此其刑法中有“业务”之概念。然而我国立法上并没有“业务”概念,超法规的违法阻却事由“正当业务行为”亦只是学理上的概念,因此,应在非法行医罪的语境下对医疗行为的“业务”这一不成文的构成要件要素进行解释。
对于“业务”概念的界定,“三要件说”是日本的传统立场⑥,其包括:基于社会生活上的地位、反复持续性、对身体及生命存在危险的行为三个方面。[12]有学者对该三要件提出质疑,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基于社会生活上地位”标准并不明确,易将个人家庭生活中的事务也纳入业务行为的范围;二是“反复继续实施”无法处罚主观上欲反复实施但客观只实施一次的行为。[13]
针对第一个质疑。日本《刑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了业务失火罪,根据传统“三要件说”,反复、持续使用火的家庭主妇也是本罪的适格主体,这显然不太合理。故其诚如日本学者所言:“实际上,可以说这一要件几乎已失去了限定作用。”[14]对此,团藤重光等学者主张无须该要件。[15]例如,有学者提出了“社会需要说”[16],该说用“社会需要”取代了“社会生活的地位”,但实际上并未解决后者所面临的问题,甚至“社会需要”的判断标准更为模糊;同时,该说强调业务行为应具备合法性,又将业务活动限制得过于狭窄。
我国台湾地区有学者提出“排他性权利说”,认为业务应当源于社会或法令规定所赋予的权利,且该权利具有一定的排他性。[17]该说具有妥当性,一是避免了过于抽象的“社会地位”难以界定的问题;二是可以合理说明刑法对业务过失行为加重处罚的正当性根据,在于从业者比一般人具备更高的注意义务。比如上文所说业务失火罪的主体,就应当是具有防火职责的特定职业从业者,社会因其职业给予一定排他性权利,这些人就应当在对小心火灾方面给予特别注意,而家庭主妇等主体则欠缺这种排他性权利。
具体到本罪,医疗行业是知识与技术高度密集型的行业,又关切到国民的生命身体利益,因此国家对医疗从业人员规定了其所应具备的医学知识和医疗技术,并通过行政法规给予其独占地位,故医疗业务具有来自国家法令所给予的排他性。正是由于这种国家所赋予的排他性权利,使医师进行医疗活动时有一定的职业权威和能力优势,给人“可以治疗疾病”的职业印象,让就诊人放心地将身体法益交其作出处置。该说符合非法行医罪禁止“不具备医师资格”者进行医疗业务的立法意旨。
例如,我国传统的中医针灸行业,可分为两类行为主体,一种是专业的执业医师,经过专业学习取得专科以上学历后,经过国家统一考试取得执业资格,这些人可以在医疗机构从事医疗行为;另一种是只取得了由劳动部颁发的职业资格证书,只能进行保健类针灸行为的人员。这两者的技术要求和职业门槛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才有开展医疗针灸业务的权利,后者仅有由劳动部颁发的保健类针灸的权利。判断是医疗行为还是医疗保健行为,需要判断该具体行为所需技术复杂性是在何种业务权限范围内,如果保健类针灸人员进行了医疗针灸的业务,就有可能涉及非法行医中的医疗行为,需用由刑法进行规制。
针对第二个质疑。“反复继续实施”是针对客观事实还是主观的要求?实践中存在着行为人主观上想开展医疗业务,但只有一次行医的情况。对此,日本学者提出业务中“反复持续实施”更多地指向行为人主观的意思,即“只要具有反复继续实施的意思,即便实施了一次行为,也成为业务”[18]。显然这是对传统概念中“反复继续实施要件”的修正,将其放宽到主观有反复持续实施的意思即可。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司法实践均采此种观点。[19]如台湾地区对“医疗业务”的定义中有“职业上予以机会”的表述,即表明无须事实上多次反复,只要针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一次亦是医疗业务行为。⑦
笔者认为,应从保护公共卫生安全法益角度考虑,对“反复继续实施”作实质的理解。如果不具备执业医生资格的行为人主观上想要开展医疗业务,在其第一次进行医疗行为,给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造成了具体危险时,就符合非法行医罪的客观构成要件,因此即使只实施一次非法行医行为也可以构成非法行医罪。如果行为人只是偶然情况下实施了诊疗行为,或者偶尔为他人治病、提供医学建议和帮助,主观上缺乏反复、持续实施的意思,则不能认为开展了医疗业务,因为这种情形下行医行为仅仅针对特定的少数人,且对象或者行为的危险没有向不特定或者多数人蔓延的可能,危害范围、危害结果并没有不特定性,并未对公共卫生安全法益造成具体的危险。
立足于我国的刑法语境,非法行医罪“医疗行为”的概念可采取“业务行为危险说”,即在日本狭义的“医疗行为”概念之上,对业务这一不成文的构成要件要素进行明确——如果不是医师根据其医学专业知识与技能实施,可能对人体造成危险的业务行为。这种业务行为系基于国家法令而给予的排他性权利,是可以反复、继续实施的具有危险性的行为。
四、“业务行为危险说”的实践维度审视
(一)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的行为性质
实践中比较有争议的是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的行为性质。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随机抽取了2019年至2021年间以非法行医罪定罪的180起一审案件,其中违法进行胎儿性别鉴定被判处非法行医罪的案件有14起,占比7.8%。事实上,早在2005年就颁行的《刑法修正案(六)草案》第十五条中,就已经提出要增设为他人进行非医学胎儿性别鉴定犯罪⑧;虽然最后立法机关又将其删除,但可以看出对此类社会现象进行规制的制度需求。可见,对于实践中将非医学需要进行胎儿性别鉴定的行为纳入非法行医罪范畴的做法,学界目前尚未达成一致意见。⑨
日本基于其狭义“医疗行为”的概念,解决该类问题的方式是除行为对医疗对象造成直接危险之外,还将行为所造成的危险扩张解释为所谓“间接危险”和“消极危险”。[20]前者是指行为本身并无危险或危险性很小,但若实施不当将直接导致后续的错误治疗,间接地对法益主体的生命、健康造成危险;后者是指行为使患者失去得到正确治疗的机会,消极地造成危险。通过扩张“危险”的内涵,扩大医疗行为的范畴,但其扩张的前提是有“危险”的存在。⑩
有学者认为,“以性别筛选为目的的胎儿性别鉴定是一种危害公共卫生的行为,因为该行为事实上隐含着威胁孕妇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的因素。”[21]司法实务中,也有将该行为作为“其他严重的情形”入罪的判例。[11]之所以将鉴定行为与孕妇人身安全联系在一起,其逻辑在于胎儿性别鉴定行为可能与人工终止妊娠手术联系在一起,而选择终止妊娠手术的孕妇必然遭受身体伤害,因此鉴定行为给这部分孕妇的人身法益造成了危险。
鉴定行为本身并未给公共卫生安全造成风险,也没有给他人生命安全身体健康造成伤害的可能,笔者认为不应用刑事手段进行规制。其一,进行胎儿性别鉴定行为和终止妊娠并无必然的联系,在两个行为之中,介入了孕妇本人的意志和行为,且孕妇本人的行为已经阻断了鉴定行为与孕妇终止妊娠造成的伤害结果之间的因果联系,让鉴定者为选择终止妊娠的孕妇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违背了刑法罪责自负原则。其二,非医学需要进行胎儿性别鉴定的行为主体是否具有医生执业资格,对行为对象造成的影响并无区别。如果将不具备医生执业资格的人进行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的行为认定为非法行医罪,那具备医生执业资格的人实施该行为就不构成犯罪,反而造成了处罚上的漏洞。其三,非医学需要进行胎儿性别鉴定行为本身实际上并未对孕妇生命、身体健康侵害或者侵害危险,对该行为定罪就意味着本罪的可罚性依据是行为破坏了国家的生育管理秩序。然而,鉴定行为对人口生育规律产生的影响应当由行政管理法规调整,用刑法规制该行为,不啻于用刑法维护国家生育管理秩序。此外,我国的人口生育政策经历了从以“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为目标的计划生育政策,到逐步放开并鼓励生育的变化。[22]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下或许有必要禁止隐含导致孕妇实施堕胎手术可能的性别筛选行为,但在生育政策放开、国家鼓励生育的背景下,性别鉴定与孕妇实施堕胎手术联系已趋于弱化。
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行为并不算是一种医疗行为,因此不能用非法行医罪进行规制。
(二)基因编辑行为
2021年《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了非法植入基因编辑、克隆胚胎罪,而贺建奎案是直接推动基因编辑行为入罪的标志性案件。[12]在刑法未修改之前,对贺建奎基因编辑行为能否用刑事手段规制、用何罪名定性在刑法学界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最终法院以非法行医罪对其定罪处罚。
笔者认为,根据前文所提倡的“业务行为危险说”,贺建奎所实施的基因编辑行为,缺少业务行为的特征,其不以此为业,并反复、继续实施。此外,从行为对象来看,基因编辑行为也不会对“人体”造成危险,因为根据目前学理通说,胎儿从母体娩出时,其身体健康安全才能作为刑法所保护的对象,对基因编辑的行为,并未对“人体”造成危险,也未侵犯作为独立主体的胎儿生命健康权,事实上,其侵犯的是人类基因安全和生物安全以及生命伦理秩序,因此,该行为不是非法行医罪的“医疗行为”,诚如张明楷教授所言:“这一规定既是对‘基因编辑婴儿’案的类型化规定,大体上也是对基因编辑行为构成非法行医罪的间接否定。”
五、结论
我国刑法体系中,医疗行为的解释可借鉴日本狭义的医疗行为概念,并在其基础上对业务要素进行明确,即“如果不是由执业医生进行,有可能对人体造成危险的业务行为”,业务行为系基于国家法令给予的排他性权利,反复继续实施的具有危险性的行为。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基因编辑行为不是本罪中的医疗行为。
注释
①我国刑法中有关医疗的犯罪仅有第三百三十五条医疗事故罪、第三百三十六条非法行医罪和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了非法植入基因编辑、克隆胚胎罪,但笔者不赞成将其纳入医疗刑法范畴。
②实践中有大量此类案例,详见(2020)苏0391刑初203号刑事判决书、(2020)沪0120刑初874号刑事判决书、(2020)浙0109刑初645号刑事判决书、(2019)皖1522刑初609号刑事判决书、皖1524刑初34号刑事判决书。
③(2020)桂13刑终171号刑事判决书。
④参见王攀、肖思思等:《聚焦“基因编辑婴儿”案件》,载《人民日报》2019年12月31日第11版。
⑤《日本医师法》第一条规定:“医生应通过掌握医疗和保健指导,为改善和促进公共卫生作出贡献。”第十七条规定:“未取得医师资格,擅自执行医师业务者,处3年以下惩役或l00万日元以下罚金。第三十一条规定:“冒用医师或类似之名义者,处3年以下惩役或200万日元以下罚金。”
⑥根据日本最高裁判所的判例,业务是指“人基于社会生活上的地位反复持续地实施的行为,且这种行为具有对他人的生命、身体施加危害之虞”。
⑦在我国台湾地区,“凡职业上予以机会,为非特定多数人实施之医疗行为均为医疗业务。”详见黄丁全:《医事法新论》,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37页。
⑧刑法修正案(六)草案提出,在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条后将增加一条,作为第三百三十六条之一:“违反国家规定,为他人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导致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后果,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但由于对违规鉴定胎儿性别是否应运用刑罚手段打击存在较大分歧,为慎重起见,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审议时,删除了该规定。
⑨某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定罪量刑指导意见中,将“非医学需要鉴定胎儿性别三人次以上,并导致引产”和“因非医学需要鉴定胎儿性别受过行政处罚,又实施该行为”,认定构成非法行医罪,须追究刑事责任的意见。此文件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争议,有学者认为,因我国并没有将“非医学需要进行胎儿性别鉴定导致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的行为”作为刑事犯罪行为,一直都将其界定为“行政违法行为”予以行政处罚。将其作为刑事犯罪处理,严重混淆了行政违法和刑事违法界限。
⑩譬如,日本法院在一起判例中,将为隐形眼镜验光的行为认定为医疗行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不能立即说验光和戴上隐形眼镜本身可能危害健康,但如果戴上不适合患者眼睛的隐形眼镜,就会引起身体健康方面的危险。隐形眼镜处方系基于隐形眼镜的适配性的判断,是可能造成危害的行为,属于医疗行为。”
[11](2017)浙0603刑初78号刑事判决书。
[12]参见王攀、肖思思等:《聚焦“基因编辑婴儿”案件》,载《人民日报》2019年12月31日第11版。案情为:以贺建奎为首的医疗团队,违反国家有关规定,伪造审查资料,实施国家明令禁止的以生殖为目的的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活动,招募8对夫妇(艾滋病病毒抗体男方阳性、女方阴性)参与实验,策划他人顶替志愿者验血,指使个别从业人员违规在人类胚胎上进行基因编辑并植入母体,最终诞下婴儿3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