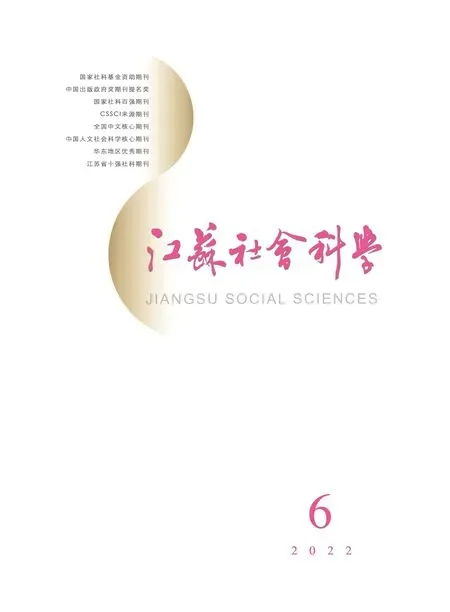“治出于二”与中国知识谱系的创建
陈 赟
内容提要 经-史-子的知识谱系是中国文明的创建,这一创建最早可以追溯到《庄子·天下》。《天下》从古之道术分化的视角理解中国知识谱系的起源,其核心是,从“治出于一”到“治出于二”的秩序转型导致了知识谱系从三代以上的浑然未分到三代以下经、史、子的分殊。古之道术的担纲主体是“治出于一”的帝王,他们是同时掌握精神(教化)和权力(政治)的神圣化统治者;但“治出于二”则意味着治教两大领域的分化,两大领域各有担纲主体。而在教化领域中出现的经史的分化以及子学(百家学或诸子学)的兴起,标志着经-史-子知识谱系的形成。经学或六艺学被视为古之道术的正宗嫡传,而子学作为方术,既是对道术的偏离,又可以上通道术。以经学为主体、以史学与子学为羽翼的中国知识谱系,既以经的主干性保证了中国学术精神的深层统一性,又向子、史开放而补充经学,从而形成经、史、子三者既分离又互补、既相异又相成的知识整体。
《天下》是今本《庄子》33篇的最后一篇,往往被视为揭明《庄子》全书宗旨的后序。是篇从古之道术(指内圣外王之道,尤其是其初始形态)的衍化所导致神、明、圣、王的分化开始,阐发方术(指囿于一偏而不能全面呈现道之整体的学术,具体指子学或百家学)兴起的根源,进而揭示古之道术向着旧法世传之史、六艺学、百家学三支的分化,是最早从义理上揭示经-史-子知识谱系创建的“大文本”,值得放在中国文明的大脉络里来解读。需要指出的是,经-史-子是中国知识谱系的核心,即便后世有了四部之学的说法,但集部本身作为知识分类并没有颠覆经-史-子的知识谱系,甚至它只是经-史-子知识谱系的一种衍生形式。严格意义上,在现代西方大学制度与知识谱系引入之前,经-史-子始终是中国的知识谱系的核心,并不存在与之并行的知识谱系。
本文试图从以下三个方面阐发中国知识谱系的创建问题:其一,在三代以上“治出于一”的宇宙论王国秩序中,教化与权力集中于王者一身,知识形态处在原初整体性的浑然未分状态,并没有经、史、子的分化。知识的分化以及知识谱系创建的社会前提,是“治出于二”的秩序格局。其二,在“治出于二”的格局下,统治与教化分离,诸子学或百家语出现,这就是“子学”。先王治理实践的王官学分化为经与史,经是孔子及其门人在新的格局下对先王经世实践的总结与提炼,而史是先王的经世实践之记录。子学则是新格局下由个体心智承载的开放性的学术思想。其三,古之道术经过“治出于一”到“治出于二”的分化[1]关于“治出于一”与“治出于二”的讨论,参见陈赟:《“治出于二”与先秦儒学的理路》,《哲学动态》2021年第1期。,不得不向个人意见敞开自身,由此而有“方术”的兴起。方术虽然是对古之道术的偏离,但又内蕴着通达道术的可能性——理解自身作为方术的局限,是开启通达道术的关键,这就给出了在经、史、子分化条件下中国学术统一的可能性。
一、“治出于一”与经史未分的原初知识形态
《庄子·天下》将自己所处的时代处境概括为“道术将为天下裂”,其本质是从三代以上“治出于一”到三代以下“治出于二”的秩序转型。正是这一转型导致了经、史、子浑然未分的西周王官学的解体,以及诸子学或百家语的兴起,后者被《天下》视为不见天地之全、古人之大体的“方术”。在《天下》看来,道术的分裂构成了方术兴起的前提,最典型的方术则是以私人著述形式出现的诸子学或百家学;而“古无私门之著述”[2]章学诚:《文史通义新编新注》,仓修良编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827页。,诸子学的出现伴随着经、史、子的分化。本来在宗周王官学中,学在官守,史以掌之,由此而有以“原史”为核心的学术形态。所谓“原史”,即由王者之官守(其主体是史官)所掌握的学术,其内容是王者治理天下的实践及其经验,它是不分科的,从后世经、史、子分化的视角来看,则是浑然一体的[3]西方文明以为哲学、宗教、哲学等,或者制作的科学、实践的科学、理论的科学,都是从神话中分化出来,故而神话是其原初的符号;而在中国,知识分化的源头则是由帝王史官所执掌的“原史”,之所以称为“原史”,是为了区别于“经-史-子”中的“史”。“原史”是未分的浑然的知识统一体,而“史”则与“经”“子”相对。参见陈赟:《“原史”:中国思想传统中的原初符号形式》,《船山学刊》2022年第6期。。胡应麟指出:“夏、商以前,经即史也。《尚书》《春秋》是已。至汉而人不任经矣,于是乎作史继之。魏晋其业浸微,而其书浸盛,史遂析而别于经,而经之名,禅于佛老矣。”[4]胡应麟:《经籍会通二》,《少室山房笔丛》卷二甲部,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16页,第16页。《尚书》与《春秋》即史即经,史外无经,经外无史。“《尚书》,经之史也;《春秋》,史之经也。”[5]胡应麟:《经籍会通二》,《少室山房笔丛》卷二甲部,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16页,第16页。刘因也指出:“古无经史之分,《诗》《书》《春秋》皆史也。因圣人删定笔削,立大经大典,即为经也。”[6]刘因:《叙学》,《静修先生文集》卷一,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5页。其实在郝经那里,已经可以看到这种观点:“古无经史之分。孔子定六经,而经之名始立,未始有史之分也,六经自有史耳。故《易》,即史之理也;《书》史之辞也;《诗》史之政也;《春秋》史之断也;《礼》《乐》经纬于其间矣,何有异哉?至马迁父子为《史记》,而经史始分矣。其后遂有经学、有史学,学者始二矣。”参见郝经:《经史》,《陵川集》第3册,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672页。经史原本浑然一体,由一而二的分化在汉代以后才出现,崔述说:“夫经史者,自汉以后分别而言之耳。三代以上所谓经者,即当日之史也。《尚书》,史也;《春秋》,史也。经与史恐未可分也。”[7]崔述:《崔东壁遗书》,《洙泗考信录》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96页。经史未分,构成了知识的原初形态,知识本身被视为整体,由于没有分类或分化,因而各个部分是浑然一体的。
经史一体与学在官守联系在一起,作为官守所记载的帝王之治迹,它们构成了孔子及其弟子未修的古六艺。古六艺记载三代以上宇宙论王国秩序中的帝王经世的事迹,这些帝王是宇宙论王国秩序之文明的担纲者,《天下》称之为“古之人”,“备”构成了其根本特征:“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庄子·天下》)古人之所以为“备”,正是由于他的双重代表身份:在人类社会的小宇宙,王者是大宇宙的代表,是天神的沟通者;而在天地万物的大宇宙中,王者则是人类社会的代表[1]关于宇宙论秩序的简要论述,参见埃里克·沃格林:《新政治科学》,段保良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58页。。王者以中介的方式垄断了通天权,作为“世界君主”,王者乃是“统治宇宙的唯一神在人间的类比”,由此而有“天上一神”与“地上一王”的紧凑对应关系[2]埃里克·沃格林:《以色列与启示》,《秩序与历史》卷一,霍伟岸、叶颖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81页,第130页,第130页,第131页,第135页。。王者是“人”,而不是“神”,然而又是“神”在“人”那里的显现。如此一来,一个宇宙论王国的秩序必然意味着以尊王为核心的礼法等级体系,而这个礼法秩序本质上又是宇宙秩序的类比物或相似物。宇宙论王国秩序紧密关联着的是一套以法老或王者为中心的礼法秩序,神在王者那里的显现并不因为他是一个人,而因为他是作为中介的王者,是人神之间的使者或双重代表。“一个社会是通过在一大群人中将制度融贯起来,并创立一个代表才能生存。因此,神不会随意在任何人身上显现自己,将其作为种类的代表;相反,他仅仅在统治者身上显现自己,使其作为社会的代表。我们可以说,在法老身上,具有神性的不是‘人’而是‘王’……在‘王朝’制度中,当每个法老作为神的儿子诞生时,都会同时存在具有神性的人(god-man)的观念,由于他所具有的资格条件,注定会接替法老的职位。”[3]埃里克·沃格林:《以色列与启示》,《秩序与历史》卷一,霍伟岸、叶颖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81页,第130页,第130页,第131页,第135页。在中国语境中,“治出于一”意味着王者垄断了通天权,既垄断了政治权力,又垄断了知识与教化,因而三代王者往往既是巫师,又是王者。至少,巫术构成其政治体系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王者或者自身是巫师,或者掌握了巫师集团。
关键的是,王者并不是以人之身份,而是作为社会的代表出现的。因此在他身上神之显现也扩展到整个社会中,整个社会都会分享王者的神性,其“神性辐射到整个社会,并将其改造成为神的民族”[4]埃里 克·沃格 林:《以 色列与启 示》,《秩序与历 史》卷一,霍伟岸、叶颖译,译林出 版社2010年版,第81页,第130页,第130页,第131页,第135页。。通过分享王者所显现之神性,整个社会的所有成员都完全融入社会,因而造就了一种以民族为单位的集体性生存样式,宇宙论王国秩序就与这样一种生存方式关联在一起。由于个人没有从社会成员的归属身份中独立,因此在其中生存的真理无法呈现为个体灵魂的真理,对存在的参与意味着以具体民族或社会为中心的集体性生存的参与。因此,宇宙论秩序中的神性并非对个体灵魂显现,而是对集体生存显现,它与尊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通过国王这一中介,宇宙的秩序辐射了整个社会”[5]埃里克·沃格林:《以色列与启示》,《秩序与历史》卷一,霍伟岸、叶颖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81页,第130页,第130页,第131页,第135页。。宇宙秩序与社会秩序被视为同质性的,“法老发散的社会秩序与神创世界的秩序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因为法老就体现了创造性神性本身。法老的秩序就是来自永恒的宇宙秩序之连续不断的更新和重新展现”[6]埃里克·沃格林:《以色列与启示》,《秩序与历史》卷一,霍伟岸、叶颖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81页,第130页,第130页,第131页,第135页。。在中国社会语境中,宗法正是一种将人归属到宗族集体主义生存中的方式[7]对宗法所体现的集体主义生存形式的理解,参见陈赟:《周礼与“家天下”的王制:以〈殷周制度论〉为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13—205页;对于这种集体主义生存形式与天命的关联,参见该书第206—285页。,即便是后人对三代之德的回溯,也都体现了这一点:要么是天命的政治德性,它源自天命,却为统治者所拥有,如西周前期《史墙盘》有“上帝降懿德”于文王的表述;要么是“周德”或“商德”这类表述所展现的族类品质,《国语·晋语》以“异姓则异德,异德则异类”“同姓则同德,同德则同心”清晰地展现了德性的集体主义品质。
有了对宇宙论王国秩序的如上理解,便不难理解《天下》何以说“古之人”的“备”:作为宇宙整体构成部分的神明、天地、万物、天下、百姓,都会通到帝王一人那里,其统治秩序表现为贯通宇宙整体的未分之“一”,这就是帝王本人可以“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的根本。这意味着,本末、数度、小大、精粗都以同质化方式融合进宇宙论秩序的体验中,“神”“明”“圣”“王”在三代以上“治出于一”的帝王那里并没有明确分化,而是浑然一体,那里并没有出现在王者秩序之外的另一种可以与之并行或不同的秩序或领域。
与此相应,古六艺作为帝王经世之迹,包含历代相传的治理经验与生存经验,并非某个有意志的作者根据其情志的创作或表达,而只是某种官守的“非作者化”行为的产物。章学诚云:“道不可以空铨,文不可以空著。三代以前未尝以道名教,而道无不存者,无空理也。三代以前未尝以文为著作,而文为后世不可及者,无空言也。盖自官师治教分,而文字始有私门之著述,于是文章学问,乃与官司掌故为分途,而立教者可得离法而言道体矣。《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虚行。’学者崇奉六经,以谓圣人立言以垂教,不知三代盛时,各守专官之掌故,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章也。”[1]章学诚:《文史通义新编新注》,仓修良编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70—271页,第270—271页。
但是随着礼坏乐崩,三代宇宙论王国秩序解体,也就出现了“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左传·昭公十七年》)的现象。这一现象伴随着“君师政教不合于一,于是人之学术,不尽出于官司之典守”的不可逆过程,此与“三代盛时,天下之学,无不以吏为师”[2]章学诚:《文史通义新编新注》,仓修良编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70—271页,第270—271页。形成了鲜明对照。的确,在三代秩序中,“岂独以君兼师而已,自冢宰、司徒、宗伯下至师氏、保氏、卿、大夫,何一非士之师表”[3]魏源:《默觚上·学篇九》,《古微堂内集》卷一,《魏源全集》第13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22页。,故而刘师培称:“周代之学术,即史官之学也,亦即官守师儒合一之学也。”[4]刘师培:《刘师培史学论著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9—14页。如果说“治出于一”对应于“三代以上,君师道一而礼乐为治法”,那么“治出于二”意味着“三代以下,君师道二而礼乐为虚文”[5]魏源:《默觚上·学篇九》,《古微堂内集》卷一,《魏源全集》第13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22页。宋代学者林曾以君师与宗师来分别表述君师合一的治教主体与君师分化以后的教化主体:“三代而上有君师,以任道统,固不待宗师之功;春秋以来无君师以任道统,不得不赖宗师之学。……三代而上,君师尊崇之功也;自贤圣之君不作,而正大之学无传。吾夫子虽不得其位,而所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极,为前圣继坠绪,其功又有贤于尧舜者。”参见林:《古今源流至论·前集》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5—16页。这意味着,“治出于二”的关键在于孔子的教统宗师地位的确立,也正是因此,更多的学者将“治出于二”与孔子联系起来:“三代而上,有王者作,而道行。三代而下,有孔孟继出,以道自任,而异端得以不炽。”参见佚名:《稽古伟议》,《群书会元截江网》卷三十五,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这一转型所导致的最大现实,就是伴随着统治权力与精神教化分离的治统与教统的分化,这就是“圣者尽伦”与“王者尽制”之区分,是圣人作为“天爵”而王者作为“人爵”的分离。与此相应的是精神生活可以独立于政治生活而有自己的领域和尺度,这就有了人的存在方式的选择问题,即所谓士人的出处、进退、隐显问题。一个人不必从事实际的政治,而是可以通过“与于斯文”的方式,构建教学共同体,在俗世政治社会之内开辟一方并不完全能由特定时代的政治社会所界定的超越性空间,这就使得知识本身可以不再如三代以上般无法脱离帝王治理天下的实践,而是以与具体政治社会实践拉开距离的方式对之加以反思。这就为知识谱系的创建提供了社会条件。
在这个意义上,孔子的有德而无位,尤其是孔子及其门人的述作六经,就构成一个标志性的文明论事件,它意味着不同于三代王者的新的价值尺度,通过这一尺度甚至可以批判王朝政治。如《孟子·滕文公下》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孔子作《春秋》与大禹治水、周公兼夷狄具有同样的意义。而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将孔子作《春秋》视为“以为天下仪表”的立法行动,可以起到“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的效果,这就意味着六经系统的创建作为教统确立的标识,终结了学术与权力都集中在王者手中的三代秩序,而开启了一个超出具体政治社会的精神领域;通过孔子所谓的“斯文”,千世以上之心与千世以下之心都可以凭着感触引发而相遇于这一精神宇宙,从而有了不同于现实政治领域的自我确证方式,也给出了统治者无法垄断的生存尺度与意义标准。自六经系统确立以后,即便秦汉唐宋明清的皇帝们可以掌握其当代的世俗权力,可以掌控他所在具体社会的士人,但具体社会的最高世俗权力无法跨越其社会与时代,而六经所提供的精神宇宙却可以内在于诸多具体社会而又不属于任何具体社会,这就是教统确立之后确立自身判断标准的文明论意义。至今仍有学者简单地以为,在六经系统确立以后的传统中国内,作为天子的皇帝仍然掌握精神与权力,与三代以上没有什么差异。如果这结论正确的话,那么,士大夫阶层就是以皇帝的意志作为标准与尺度来解释六经,而不是据六经来制约、批判皇权。这种简单化的观点没有进入传统中国的历史中,看不到士大夫阶层凭着作为大纲大经的六经与皇权之间的紧张,看不到治统与教统之间始终存在的结构性张力。
二、“治出于二”与经、史、子的分化
三代秩序解体之后,礼坏乐崩,而新的秩序又没有形成,《天下》如是刻画这个时代性处境:
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
三代秩序解体之后是全面的失序状态,未分之“一”分化之后,“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失去了统一性,于是,“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这就是人各为方的生存处境。展开在学术上,就是“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天下》以人的身体隐喻集体主义生存形式与宇宙秩序经验互嵌性秩序解体之后各个构成部分不再贯通,“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治出于二”意味着,古之道术分裂为以精神为主体的教化秩序和以政治为主体的统治秩序,但二者本身却不能连接为有机整体,这就是内圣外王之道的断裂。而且,即便是这两个领域各自内部的构成部分,也由于彼此支离而难以形成统一性。譬如在教化领域,首先是经、史、子的分化已经不可避免,其次是诸子之间各是其是、各非其所,难有共识。百家学的兴起源于三代王官学术解体后与“治出于二”格局相应的知识谱系的结构性变化;三代经史浑然一体的王官学解体,取而代之的是经-史-子知识谱系的确立。《天下》是最早揭示这一知识谱系确立的文本:
(1)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
(2)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
(3)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
按照以上的分解,与宇宙论王国秩序相应的经史一体的知识谱系解体之后,学术分为史、经、子三支。“世传之史是一项,史家所由传。此六经又是一项,士子所传”,“经史已属陈迹,至百家第据其散数以传,又道之微乎其微者也”[1]刘凤苞:《南华雪心编》,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780页。。蒙文通从《天下》看到了经-史-子这一中国古典知识谱系的起源:“周季之学,类别有三:旧史为一系,鲁人六艺为一系,诸子百家为一系。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夏有《连山》、殷有《归藏》,孔子谓宰予曰:‘五帝用记,三王用度。’此皆古代史迹之可考见者也。《吕氏春秋》说:‘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乃奔如商,殷内史向贽载其图法出亡之周。’是三代迭兴,图史不坠。史公谓:‘诸侯相兼,史记放绝,秦烧诗书,诸侯史记尤甚。’则列国又各有旧法世传之史,至秦而夷灭尽矣。孔子制作《春秋》,既求观于《周史记》,又求百二十国宝书,此尤列国之史,灿然具在之证。荀卿亦谓‘三代虽亡,治法犹存’。故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三古列国之书既存于世,则孔子之删定六经,实据旧史以为本,孰谓凡称先王之法言陈迹者,并诸子孔氏讬古之为乎!”[2]蒙文通:《经学择原》,《蒙文通全集》第1册,蒙默编,巴蜀书社2015年版,第236页,第238页。未经孔门修治的古六艺与存于官守的旧法世传之学,本属一体。“未定之六籍,亦犹齐、楚旧法世传之史耳,巫史优为之,删定之书,则大义微信,灿然明备,唯七十子之徒、邹鲁之士、搢绅先生能言之。”[3]蒙文通:《经学择原》,《蒙文通全集》第1册,蒙默编,巴蜀书社2015年版,第236页,第238页。如果说“六经皆史”传达了六经出于史的事实,那么,孔子及其门人对六艺的修治,所得的六经之学则为对古之道术的传承,出于史而自不同于史。
1.史学的创建 与“经”相对而言的“史”可以理解为后世史家所传承的史学,以记事为载道的方式,其核心以“通古今之变”的方式达成对天人之际的理解。三代旧法世传之史所记者为事,所明者乃古道术之数度,而未及义理。但数度与义理又不能完全分离,数度也是道术显现之一隅,“其明而在数度者”中的“其”当为“古之人”(三代以上的独享通天权的帝王)所体现的“古之道术”,古之道术在数度中亦有所显现,当然,有所显现同时关联着有所隐蔽。谭戒甫指出数度可以通达道术的一面,“数度有本末之分,即道术之著见者,故曰其明而在数度也”[1]谭戒甫:《〈庄子天下〉校释》,刘小枫主编:《经典与解释》第23辑《政治生活的限度与满足》,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216页,第216页。;吕惠卿则指出数度的局限,“古之道术所谓神,而数所不能计,度所不能度者,固不可以书言传”[2]吕惠卿:《庄子义集校》,汤君集校,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587页,第587页。。能以数度而对古之道术有所明者则为“旧法世传之史”。谭戒甫以为:“旧法者,如《墨子·节用中篇》称‘古者圣王制为节用之法、制为饮食之法、制为衣服之法、制为节葬之法’皆是。世传之史,如《史记·太史公自序》云:‘余所以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按故事(亦即旧法)世传当即古代史官所掌,迁乃述而整齐之;可知数度之明于后世者尚多矣。此在旧法世传之史者其一,似指春秋以前。”[3]谭 戒甫:《〈庄子 天下〉校释》,刘小枫 主编:《经典与 解释》第23辑《政治 生活的 限度与满 足》,华夏出版 社2008年版,第216页,第216页。旧法其实就是三代之治法,广而言之,涉及礼数、礼法、礼器、礼仪、礼节等,是生活世界中被体制化、机制化了的规范,虽然起源于既往生活的过去,但被世传之史者记述而得以为后人所明。三代之治法中即有三代之治道,是以治法中内藏治道,而史学所明者多在治法,所不明者则为治道,从史官所记载之三代之治法中探究三代之治道,则为孔门修治古六艺以成六经之取向。王夫之说:“法备于三王,道著于孔子。”[4]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一,《船山全书》第10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68页。史学所传者在三代之法,而即三代之法而上达三代之道,则在孔子及其六艺之学。三代之法虽然载籍犹在,然法之随时损益,不可复行于世,后世所可循者乃三代之道。孟子之学孔子,以为孔子贤于尧舜,司马迁称孔氏古文“正以示别于旧法世传之史、九流百氏之说,而表见其为孔氏一家之学也”[5]蒙文通:《经学择原》,《蒙文通全集》第1册,蒙默编,巴蜀书社2015年版,第239页。。
钟泰以为“旧以‘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十字作一句读者,误也”,正确的读法应是:“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在钟泰看来,“古者官师世守其业,《周官·考工》云:‘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是也,故曰‘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史’,史官。《周官·春官》:‘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国之治。掌法,以逆官府之治。掌则,以逆都鄙之治。凡辨法者考焉。’郑注:‘典则,亦法也。’是所谓史多有之也”[6]钟泰:《庄子发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759页。。尽管钟泰的理解与谭戒甫等有所不同,将世传之旧法与史官所传之法典区分开来,其意大致如吕惠卿所谓“明在数度者,有司出其法,国史记其迹”[7]吕惠卿:《庄子义集校》,汤君集校,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587页,第587页。;但史亦官师之一,甚至是官师之主体,一切官职之起源似皆可追溯于史官,在这个意义上,旧法世传与史在《天下》这里被列为一支,并非没有道理。
史之所载,乃帝王之治迹,而非其所以迹。《天运》谓:“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今子之言,犹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岂履哉?”作为帝王之治迹的古六艺,只是记载帝王在其时代情境下的治理方式,这一方式集中为因应当时社会历史情境的数与度,然而随着时间与形势的推移,昔日的数度岂能适合此后的形势?《天运》指出:“故夫三王五帝之礼义法度,不矜于同而矜于治。故譬三王五帝之礼义法度,其犹柤梨橘柚,其味相反而皆可于口。故礼义法度者,应时而变者也。今取猿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龁啮挽裂,尽去而后慊。观古今之异,犹猿狙之异乎周公也。”[1]“三王五帝”原作“三皇五帝”,兹依据钟泰《庄子发微》正之。数与度应时而变,因时而行,不得不随时变通,在古今之变的视域中,必须由作为帝王治迹的数度上升到具有原理性质的义和理。数与度是礼(规矩、规范)的更为具体的方面,具有可以操作性的维度,但由于礼随气运、时会、势变而不得不进行损益,因而数、度本身更具有随时而变的不稳定性质,能随时势变化而自身相对不变者,则是内在于数度中的义理。《天运》中记述,孔子“求之于度数五年”,遭到老子的批评。《荀子》论数度曰:“礼义法度者,是圣人之所生也”(《荀子·性恶》);“言治者予三王,三王既已定法度,制礼乐而传之”(《荀子·大略》)。数度与义理相须而行,然而史之所传,唯在数度。《荀子·君道》云:“不知法之义,而正法之数者,虽博,临事必乱。”《荀子·荣辱》云:“循法则、度量、刑辟、图籍,不知其义,谨守其数,慎不敢损益也。”《荀子》强调仅仅知数度而不知义理的问题。这里的“法则”“度量”“刑辟”“图籍”等正是《天下》所谓数度的具体内容,它正是史之所执掌。《礼记·郊特牲》云:“失其义,陈其数,祝史之事也。”史之所明在数度,而非义理,此即《庄子·天道》所谓的“末度”——“礼法度数刑名比详,治之末也”。此为史之限制。《马王堆帛书易传·要》云:“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向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2]于豪亮:《马王堆帛书〈周易〉释文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86页。这里托于孔子的话道出了巫史与六经的差别,孔门六经之学的核心在于德义,而巫史之学的核心在于数度。古者“官有世功,则有官族”(《左传·隐公八年》)[3]《汉书·艺文志》:“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故曰“世传之史”;而依据钱基博的论述,齐桓之时,世官已为禁令,故而《天下》谓之“旧法世传之史”[4]张丰乾编:《庄子天下注疏四种》,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第103页。。旧法世传的史学乃王官官守之学,其背景是宇宙论秩序中帝王之经世记录,在那里,由于原初宇宙体验的浑然一体同质,因而没有知识的分殊化。朱长青论及《天下》“古之人”时说:“典册掌于史官,无经学之异称,无经史之分称也。”[5]朱长青:《庄子解·天下》,《方山子文集》第21册《庄子纂要·天下》,学苑出版社2020年版,第867页。但在三代秩序解体之后,官司失其所守,昔日三代王者经世之学遂成旧法,赖史学以传其数度。广而言之,经史分化以后,史学以记事为主。人之行事之大者莫过于创制立法,以王者治理天下为中心的史学记载的便是王者创制立法以经济天下的实践。但史学的局限则在于对数度之义理不能尽显。
2.经学的创建 所谓经学即包括作为主体的六经以及解释六经的六艺学。六经被《天下》视为古之道术的嫡传,但并非全部,因为在“治出于二”的状况下,道在帝王一人之身的完全性视角已经不再可能:“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即孔子及其门人,多能承接《诗》《书》《礼》《乐》之学。《礼记·王制》云:“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西周以来已有《诗》《书》《礼》《乐》,孔子及其弟子修治之而为教材,使之经典化。值得注意的是,何以《天下》这里将六经列为单独的一支而不同于旧法传世之史?钟泰说:“特提《诗》《书》《礼》《乐》六经者,以别于世传之旧、史官之藏,盖经孔子删订之后,《诗》《书》已非昔时之《诗》《书》,《礼》《乐》亦非昔时之《礼》《乐》,故曰‘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明之’者,明其义,非仅陈其数也。”[6]钟泰:《庄子发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759页。作为古之道术之传者的六经与孔子关联在一起,而孔子又是圣者的符号化象征。对于旧法世传之史而言,其史学所载之道,乃三代以上帝王之治迹,故而其道术的主体本质上是作为宇宙论王国秩序的帝王——“古之人”,而六经的圣者人格符号乃是孔子,而不是“古之人”,因而二者有着本质的不同。六经与旧法世传之史,虽同为古之道术的两支,但二者有所不同:这里的旧法世传之史,由于已经不在三代王者的当世,因而其所记载者乃三代王者之旧法,史者于三代王者之道术所明者仅在数度,而不在义理;而孔门六经之学则出于史学而不同于史,所不同者在于即数度而明其义理,由法以见其道。在这个意义上,六经之学不能仅仅被视为六种典籍、六部经典,而应被看作以典籍承载道义,承载中华文明在历史中展开的精神。就六经之为典籍而言,则与史学无异,特道术之发见之具也。刘凤苞有谓:“古人大备者不可以言传,经史之载,世有掌故,治乱兴衰之理,反覆详明,皆古人之陈迹也。”[1]刘凤苞:《南华雪心编》,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783页。可以说,孔子及其后学对六经的修治,使得六经承载的是先王之道,但这是经由孔子整理的先王之道,因而六经的显性主体是三代以上的帝王,但隐性主体则是孔子。先王之道通过孔子的处理而进入六经,因而具有了超出其历史时代的普遍意义。王船山简明概括总结了六经中的两个主体问题:“法备于三王,道著于孔子。”[2]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一,《船山全书》第10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68页。如果说周公可以代表“治出于一”架构下的三王,而孔子是“治出于二”架构下作为文明担纲者的圣人的符号,那么经学本身的两大主体实质地对应着周、孔之道,后世经学中的古今差异,说到底关涉对周、孔关系的不同理解。而在孔子及其门人弟子整理传述的六经系统中,两个主体的关系非常值得思考。作为显性主体的是三代以上的帝王,作为帝王之统,不同于圣人之统;作为隐性主体的是孔子,它是圣人之统(教化之统)的化身。六经对隐显两大主体的处理方式,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但它本质上是以圣人之统消化帝王之统,即以圣人之统为枢纽,围绕着圣人之统的中心,将符合圣人之统的帝王纳入六经的叙事结构,这就有了圣帝、圣王观念[3]关于圣人之统与帝王之统及其复杂关系,参见陈赟:《从帝王之统到圣统:治教分立与孔子圣化》,庞朴主编:《儒林》第5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66—88页。。要知道,圣人观念的中心化是在孔门中奠定的,而就帝王之统自身而论,“圣”在其中并非中心的或主导的观念[4]关于圣人观念及其与明主、明君观念的区分性意识,参见顾颉刚:《“圣”“贤”观念和字义的演变》,《中国哲学》第1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80—96页;青山大介:《战国时代“明主”观念探析——以“圣人”的对比为切入点》,《东亚观念史集刊》2016年第11期;青山大介:《中国先秦“圣人”与“贤者”概念探析:以“预先性”和“创造性”的能力为线索》,《经学研究集刊》2015年第18期。,但在六经系统中,圣人之统作为隐性的尺度,影响制约着对帝王事迹的叙述与重构。这就是说,通过六经而呈现的帝王之统,是以圣人之统为尺度而裁剪构建的帝王之统。根据《太史公自序》,后来司马迁作《史记》也是师法孔子作《春秋》的历史编纂活动,《史记》并非以帝王或汉代的皇帝为尺度而是以代表圣人之统的孔子及其《春秋》为判断标准的。
《天下》对六经各自理念与意义的经典概括是:“《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六经被理解为一个整体,这个整体构成一种完整而有机的生活情境,这一生活情境滋养人的方方面面,其意义在于给出具体完整的“大写之人”。《天下》对六经的理解与《礼记·王制》中先王以诗书礼乐“造士”的理解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礼记·经解》对六经之教的理解是:“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诗》导志,而化人之性情为“温柔敦厚”;《书》以道事,深于《书》者能够疏通知远而不诬;《礼》以道行,深于《礼》者可以恭俭庄敬而不烦;《乐》以道和,深于《乐》者能够广博易良而不奢;《易》道阴阳,深于《易》者可以洁静精微而不贼;《春秋》道名分,深于《春秋》者可以属辞比事而不乱。《史记·滑稽列传》记载:“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而《礼记·经解》对六艺各自教化功能的揭示,也托名于孔子,或许正是在孔子那里才有了对六经以成人之学为取向的认识,《天下》无疑承接了这一取向。
在汉代可以进一步看到五经(《诗》《书》《礼》《易》《春秋》)与五常(仁、义、礼、智、信)的对应。对应的方式有两种。一是《汉书·艺文志》的对应方式:“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二是《白虎通·五经篇》的对应方式:“经,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经。《乐》仁,《书》义,《礼》礼,《易》智,《诗》信也。人情有五性,怀五常不能自成,是以圣人象天五常之道而明之,以教人成其德也。”[1]陈立:《白虎通疏证》,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447页,第447页。尽管二者中五常与五经的具体对应方式不同,但将五常与五经对应是一致的,不仅如此,这一观念有着更为深远的来源。《韩诗外传》引孟子之言曰:“常之为经,经有五,常亦有五。”[2]陈立:《白虎通疏证》,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447页,第447页。今本《孟子》中无此言,《韩诗外传》必有其本,其所引者当是孟子门人口传的没有录入《孟子》中的“教义”。五经之教,同本于人之源自天的五常之性,以成就人之为人之德,而由于五常相须而备,因此《五经》作为一个教化的体系,也是相须而有、并行不悖而又一以贯之的。王应麟在《困学纪闻》中评论《艺文志》与《白虎通》的上述二说时强调:“二说不同。然五经兼五常之道,不可分也。”[3]王应麟:《困学纪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076页。五经与五常的对应,可谓将对六经(五经)之教大义的理解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一言以蔽之,六经之学足以成人,使人安身立命,不仅解决秩序问题,而且解决生存意义问题。关于六经整体的隐性结构,《史记·匡衡传》说,“六经者,圣人所以统天地之心,……通人道之正”。这里面是一个天人之际的问题,在天人之际的视域中解决的是人的教养与成人问题。如何成为真正的人,这构成了秩序的根本问题。尤其是在“治出于二”的格局下,无论是政治秩序,还是教化秩序,都无法绕开这一问题。孔子删定的六经之所以不同于旧法世传之史,乃在于后者所解决的主要是秩序问题,没有将个体的成人问题作为归宿。相较而言,“三代以上”的秩序关联着的乃是宇宙论王国秩序中的宗法性集体生存样式,个人的内在精神领域并没有被凸显为秩序的主题。
3.子学的创建“治出于二”在更深刻层次上意味着道术在一个人、一个具体社会那里的完全性显现不再可能,而是散殊于不同个人、不同社会、不同时代,由此而有道术显现的局部性视角。人们不得不站在各自的视角参与道术,其对道术理解的自得之处与其独特视角相关,但也受限于其独特视角。子学之所以为子学,正在于生活于具体时代和特定社会的个人以其有限性视角只能获得对道术的不完全的理解,不全不备成为必然,任何人都不得不以“不该不遍”的“一曲之士”出现,故而他对道术的呈现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以他的意见的形式呈现。“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尽管或许可能得古之道术之“一偏”,所谓“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闻其风而悦之”(《庄子·天下》),但毕竟失去了会通(统之有宗,会之有元)的一体化能力。而所谓的“古之道术有在于是”与《汉书·艺文志》所谓的“出于某官,此其所长”一样,都表明“推之既极,遂欲以一端而概众事”,也与《孟子》所谓“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庄子·秋水》所谓“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荀子·解蔽》所谓“此数具者,皆道之一隅也。夫道者体常而尽变,一隅不足以举之。曲知之人,观于道之一隅,而未之能识也”等一样,都表达了对时代处境的同样认知[4]刘咸炘:《刘咸炘学术论集:哲学编》上册,黄曙辉编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1—52页。。这一处境的标志性事件就是诸子学或百家学的兴起,连诸子自己都以为百家学的兴起是精神危机的显现:《庄子·齐物论》对“儒墨之是非”的批判、《天下》对六家学说的检讨、《荀子》对十二子的批评等,都包含了对百家学兴起这一现象的负面认识。然而,诸子学作为分化了的子学,其正面意义在于,道术从三代以上的帝王的垄断中解放出来,道之散殊于百家的情况才成为可能,而子学的出现不仅意味着每一个人皆可与于道术,而且只有道术向每个人开放,它才成为面向整全的天下的道术;进一步地,每个人皆有其独特的不可替代的视角,而道术在这些复数的视角中有不同的显现,这才有道术展开的丰富性与具体性。由此,子学的出现并不能仅仅作为精神危机的表现,还应作为精神在天下向天下人展开的必由之路。
诸子学或百家学,是三代解体之后出现的新现象。后人以“百家争鸣”概括之,这一现象与古希腊出现的智者现象具有某种意义上的相似性。《天下》以“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刻画的智识处境,虽然在整体上与从经史一体的原初知识形态到经、史、子分化的知识形态相关,但在某种意义上,其所直接针对的就是百家学,毕竟,百家学的出现极大地加剧了道术的分裂。《天下》谓:“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道术的分裂一方面根源于原初宇宙秩序经验之分殊,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三代以上的“古之人”不再可能存在,而由视角性认识所界定的“一曲之士”成为人的本体论意义上的条件。
在此情况下,诸子学或百家学的出现成为必然。在《天下》所讨论的六家之学中,(1)墨翟、禽滑厘“为之太过”“已之太顺”,“才士”而已;(2)宋钘、尹文“为人太多”“自为太少”,其说天下不取,“上下见厌”;(3)彭蒙、田骈、慎到“弃知去己而缘不得已”,所道非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4)老聃、关尹“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谦下为表,以空虚不毁万物为实”,虽为“博大真人”,犹是一曲之方术;(5)庄子本人“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6)惠施之学,弱于德而强于物,多方而无术,不特道术所不居,即方术亦所不取也[1]林云铭:《庄子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64—365页。。自(1)至(3)以及(6)之学,因非己或非人而反天下、毁万物,而无以见天德,故为神明所不居;(4)(5)已可与天地神明为友,或不毁万物,或不敖倪于万物而与世俗处,然犹是道之一曲,所谓方术者也。六家之学虽有深浅之不同,而皆在子学(方术)之列。“天地自含其美,判之则伤;万物浑融其理,析之则离;古人统汇其全,察之则隘。三者皆分裂大道、囿于一偏者也。百家之学,竞逐末流,而内圣外王之道日以就湮。”[2]刘凤苞:《南华雪心编》,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783—784页。
从与“治出于一”相应作为原初学术符号形式的“原史”到伴随着“治出于二”的经、史、子的分化,中国的知识谱系得以创建,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然而,分化了的经、史、子各以其自身方式参与道术,如何能保证中国文明的历史性精神的统一性?这是经-史-子知识谱系必须回答的问题。
三、作为“方术”的“子学”何以通达“道术”
经、史、子三者虽然皆从“原史”中分化出来,但它们之间是何种关系?有着怎么样的结构呢?
庄子在《天下》中自列其学为六家子学之一,而将孔子及其六艺之学独为一支,以区别于子学,因而自苏轼以来,解者皆见《天下》尊经、宗孔之意。这本身已见对经、子不同地位的理解。而庄子之所以自列其学为百家学,是因为对“时”之体会。孔子并无私言,只是删定六经,存先王之道,如《礼记·中庸》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刘咸炘指出:“孔子之教,全守先王之法,故删定六艺,以授其徒,未尝别为一书。六艺之书,皆有官守。”[3]刘咸炘:《刘咸炘学术论集·哲学编》上册,黄曙辉编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7页。孔子从先王之法提炼先王之道,可谓即事而穷理,而未尝立理以限事,此与子学往往离事以发明义理有所不同,故其学即述而作,最能绍述先王之道而返本开新。“庄子知孔子为集大成之圣,业备天地之美”,不列孔子于诸子之列,“正所以涋尊孔子也”[4]胡文蔚:《南华真经合注吹影》,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351页。;而“自比于百家众技,不该不遍、一曲之士,而不敢与六经孔子之学相提较论”[1]顾如华:《读庄一吷》,《方山子文集》第21册《庄子纂要·天下》,学苑出版社2020年版,第980页。,“语道术则己亦非其伦,语方术则己实居其至,此庄子之所以自处也”[2]陆树芝:《庄子雪》,张京华点校,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83—384页。。庄子之所以自处于子学之殿,而不与孔子六经并列,是因为深知其所处的时势:“道至于孔子而后集大成,盖几千百年而一出。孔子之上,圣人之因时者,有不得已也;孔子之下,诸子之立家者,各是其是也。庄子之时,去圣已远,道德仁义,裂于杨、墨,无为清净,坠于田、彭,于是宋钘、尹文之徒,闻风而肆。庄子思欲复仲尼之道而非仲尼之时。”[3]褚伯秀:《庄子义海纂微》,张京华点校,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039页。庄子不得不以子学自处,正因为其有对古之道术分化的认知,他深刻意识到三代帝王秩序终结之后神、明、圣、王不得不分,因此才有将关尹、老聃同列子学的做法,此中内蕴这样的认识:“道非集大成之时,则虽博大真人,犹在一曲。”[4]褚伯秀:《庄子义海纂微》,张京华点校,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039页。因此,叙述关尹、老聃之学,仍以“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关尹、老聃闻其风而悦之”予以定位。庄子同样把自己列于六家之学,而“于老之外别树一帜”[5]李大防:《庄子王本集注》,方勇总编纂:《子藏·庄子卷》第138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版,第684页。,“其叙庄周一段,不与关、老同一道术,则庄子另是一种学问可知”[6]林云铭:《庄子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65页。与此相似,陶望龄《解庄·逍遥游》云:“庄子甚尊老,而其学与老异派。观末章所列道术,可见甚取列子,而不许以神圣,与己地步亦殊,观此可见。”参见陶望龄:《陶望龄全集》,李会富编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60页。。这意味着,庄子远超诸子,尤其是当庄子在“子”位而自知其为“子”时,已经向“子”之外的“史”与“经”开放了。这或许是在六艺学、旧法世传之史学与诸子学三支所建立的巨型文化意识宇宙中,庄子能以所处之一隅而连通道术之“一”的根本,即从方术中开启通达道术的可能性。
《天下》论及道术与方术时,包含了两个方面。其一是方术对道术的偏离。钟泰云:“全者谓之‘道术’,分者谓之‘方术’,故‘道术’无乎不在,乃至瓦甓尿溺皆不在道外。若方术,则下文所谓‘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者。既有方所,即不免拘执,始则‘各为其所欲’,终则‘以其有为不可加’。‘其有’者,其所得也。所得者一偏,而执偏以为全,是以自满,以为无所复加也。此一语已道尽各家之病。”[7]钟泰:《庄子发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756页,第756页。其二是道术在分化之后又不得不通过方术来不完全地表现自己。“若学虽一偏,而知止于其分,不自满溢,即方术亦何尝与道术相背哉!”[8]钟泰:《庄子发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756页,第756页。就此而言,“方术”本身就是“道术”之局于一方者。所以,《天下》在讨论六家之学时,以“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评价其中五家,即将方术视为道术的不完全展现,或者说,方术是道术的视角性显现,多多少少显现了道术的某些侧面。这些侧面是对道术的局限性表现,而通过这些局限性表现可认识到其局限性本身就是对道术的通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方术与道术并不是截然分离的,而是交织交融的,方术之所以值得认真对待,正在于它内蕴通达道术的可能性。而且对于作为有限者的人而言,他所有的观看都必然是视角性的,这就导致了方术在人这里的不可避免性,而从方术到道术的上升之路,其实就是对方术之为方术的局限性认识。
总而言之,由《天下》的以上讨论,可以看到,从“三代以上”到“三代以下”秩序范式的结构性变化,构成了庄子时代的根本处境,这是其秩序思考的背景与动力。《天下》并非孤例,林希逸看到,《天下》对时代问题的体验与《孟子·尽心下》有着相通之处:“庄子于末篇序言古今之学问,亦犹《孟子》之篇末‘闻知’‘见知’也。自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至于道术将为天下裂,分明是一个冒头。既总序了,方随家数言之,以其书自列于家数之中,而邹鲁之学乃铺述于总序之内,则此老之心,亦以其所著之书皆矫激一偏之言,未尝不知圣门为正也。”[9]林希逸:《庄子鬳斋口义校注》,周启成校注,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491页。《庄子》与《孟子》各以自己的方式表明了其学术的源流,而《天下》更是对三代终结之后的知识谱系有着独特的思考。
胡朴安正确地看到,内蕴在《天下》总论中的是从“古之人”所在的历史时刻——“政学未分时”到三代终结之后“政学分途”时的秩序变迁。孔门六艺乃至诸子的学术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三代以上政治的反思。“今之学术,皆出于古人之政治”,然而“古之学术,即今之政治,故曰:无乎不在也。皇王而降,纯漓不同,以时代之故,各有政治之异,致有学术之异”,“古之人其备乎者,非谓古人一身备于各种之学术,言今人各种学术皆备于古人各时代之政治”[1]胡朴安:《庄子章义》,《方山子文集》第21册《庄子纂要·天下》,学苑出版社2020年版,第989—990页,第990页。。胡朴安的以上见解无疑颇有洞见。的确,三代以上学术即政治,政治即学术,但三代以下政学分途,而学术始分经、史、子三支。但胡朴安未能注意神、明、圣、王与其所原出之“一”之异,而把神、明、圣、王等同于政学未分时的学术与政治,未能看到《天下》所列七种人,正是政学分途、治出于二以后的产物:天人、神人、至人的生存视野指向“方外”,而君子、百官与民则指向“方内”,唯有圣人才能贯通“方内”与“方外”,从而连接神与明、天与地。而“治出于二”正是人的自我确证可以分化为方外、方内的根源[2]关于方外与方内,参见陈赟:《方内如何可游——庄子哲学中的两种生存真理及其张力》,郑宗义主编:《中国哲学与文化》第20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版,第52—78页。。胡朴安看到了,治出于二以后,学术分为三支:“其明而在度数者,政也;其在于诗书礼乐者,学也;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吏也。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儒耶,此政学分途,吏儒异名也。志事行和阴阳名分,政治演而为学术也。诗书礼乐易春秋,学术讬之于文章也。”[3]胡朴安:《庄子章义》,《方山子文集》第21册《庄子纂要·天下》,学苑出版社2020年版,第989—990页,第990页。史本来的确是三代以上的王朝官守之学,然而在周秦之际,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史官抱图而出,遂为旧法世传之史。故史既为六艺之所出,又下开史学之一脉,而与经、子并列。学术知识谱系之分殊化,正与“道术将为天下裂”相为表里,而秩序之思不能不以此为出发点。《庄子》内七篇之中,《大宗师》言内圣,《应帝王》言外王,正见《庄子》秩序之思,在结构上足以相应于并囊括“内圣外王之道”。而三代终结之后的“政学分途”“治出于二”,则构成庄子秩序之思的基本背景与出发点,也是中国知识谱系创建的社会条件。
虽然《天下》给出了经相对于子、史的优先地位,但并没有给出经-史-子的结构。到了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以《易传》的“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来统合各自为方的不同子学,“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史记·太史公自序》)。到了《汉书·艺文志》,才有一种对经、史、子具有结构性意义的建筑术:一方面,子学内部“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另一方面,“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因而有可以整合的依据——“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这就将经作为中国学术这棵大树的根干,将子学作为其枝条,或者说,将经作为中华学术的大河,而将子学作为这条大河的支流。于是,会通的方式在于,“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汉书·艺文志》)。子学之间彼此互补,并且可以上通经学,经、子整合,以见大道。无论《庄子·天下》抑或《汉书·艺文志》,都没有讲史学,但经与子所载之道,并非道体自身,而是人的体道经验。道体自身无所谓历史,但体道经验本身即是历史的内容。在这个意义上,经、子之学都以自己的方式向史学开放,在古今之变的会通中,不同时代的不同心灵,以其独特的体道经验汇入历史意识的长河,从而以超出其时代与个人的方式向在历史中的生存者开放。这就是以经学为主体、以史学与子学为羽翼的中国知识谱系,它以经的主干性保证了中国学术精神的深层统一性,又向子、史开放而补充经学,从而形成经、史、子三者既分离又互补、既相异又相成的知识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