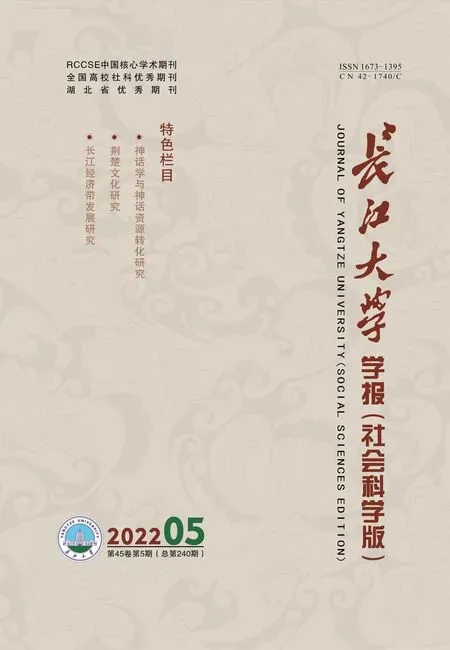与神诀别:人性的觉醒与自缚
——从四则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天地分离神话谈起
郑芩
(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871)
在璀璨的人类神话光谱中,“天地分离”母题在世界各地普遍存在。既有研究大多将天地分离置于创世神话的逻辑框架下进行阐释,为理解人类对宇宙万物起源的认知作出了有益探索。(1)相关成果如沼泽喜市《天地分离神话的文化历史背景》,收录于阿兰·邓迪斯编《西方神话学读本》,朝戈金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23~235页;尹荣芳《洪水神话的文化阐释》一书第六章节“天地分离神话”,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11~259页。笔者以为,解说客观世界的由来固然是天地分离神话的题中应有之义,但这些神话同时亦承载着人类对自我本性的定位与审视,并深刻影响、形塑了后世民众的某些观念认知与社会体制,具有深远的文化意义,对天地分离神话进行再探讨有一定的必要性。
相较于世界其他民族的神话研究现状而言,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文本向来较少受到学界观照,有鉴于此,本文拟从四则分别广泛流传于非洲中南部(M1)、中部(M2、M4)以及西部(M3)等地的神话谈起,以此为例,管窥天地分离这一标志性事件内蕴的人性觉醒历程,尝试以新材料为天地分离神话的解读提供新视角。
M1:赞比亚尼恩德人(Nyende)神话
古时,乌耶奴(Uyenu)的创造者与人类共同生活在一起。她只有一个乳房,一个男人把孩子带到乌耶奴喂养,婴儿觉得乳汁很甜美,就贪婪地把上帝口中的乳房拔了出来。上帝非常生气,于是远远地走开了。[1]
M2:尼日利亚比尼人(Bini)神话
一开始天空距离大地很近,人类无需耕种,只要割下天空的一块来吃就行。但人们常切下多于所需的量,把吃剩的扔到垃圾堆里,被天空予以警告。一天,一位贪婪的女人切下一大块天空,无法吃下后喊来全村人帮忙,依然无济于事,于是他们又把剩下的扔到垃圾堆里。上天真的发怒了,高离地面,人类再也够不到。从那时起,人们必须为生活而辛苦劳作。[2](P51)
M3:塞拉利昂曼代人(Mende)神话
上帝以前居住在岩洞里,他经常邀请动物到他的洞里做客,但不准碰他的食物。一天,母牛发现了一些美味食物,偷吃了几口,当场被上帝发现,被撵了出去。后来猴子和其他所有的动物,包括人也犯了过失,遭到了同样的命运。现在所有的动物都在到处寻找美味可口的食物,而上帝在天上监视着他们的行为举止。[3](P40)
M4:喀麦隆吉兹加人(Giziga)神话
从前,上帝和人类生活在一起,他离地很近,人类只能弯腰走动。需要食物时,人类伸手掰下一片天空来吃。有一天,一个首领的女儿不吃来自天堂的食物,而开始向地面寻找谷物。她制作了研钵和杵来捣碎谷物,每一次她举起杵都会碰到天空,她三次请求上天往高处退,不要妨碍她的工作。第三次后,上帝怒气冲冲地退到现在的位置。从那时起,人类直立行走,变成“吃小米的人”,但上帝不再解决人类纷争,由此引发人间战争。[1]
一、告别天堂:人类的无餍与抗争
斯蒂·汤普森(Stith Thompson)在《民间文学母题索引》一书中将“天地分离”母题大致归结为四类:天地混沌神话、原始洪水神话、巨蛋神话;世界父母神话;天被放逐神话;天堂神话。[4]不同于前三类神话中天与地分离之前世界总是黑暗混沌,以上述四则文本为代表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不少天地分离神话多属于天堂神话。
几乎所有人类文明都拥有各自的天堂(或曰乐园)想象,为众人所熟知的如希伯来神话《创世纪》中风光旖旎的“伊甸园”、苏美尔神话《恩基与宁胡尔萨格》里和平富饶的“迪尔蒙”,抑或是《山海经·大荒西经》中百兽“相群爰处”的“臷民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先民的记忆中,天地分离之前亦是人类的乐园阶段。所不同的是,其神话并未突出强调天堂的美妙环境,而主要从至上神与人类的亲密关系维度来建构乌托邦。这一时期,至上神与人类共同生活或频繁往来,并对人类施予家长式全方位的庇护,M1中神为婴孩供应甜美乳汁,M2与M4中人类唾手可将天空撕碎进食,至上神为人类无偿奉献所需之物,人类不稼不穑便可衣食无虞。然而,乐园时期固然优裕祥和,但在至上神的庇荫下,人类未觉生死、不分彼此,尚处于黑格尔所言“人性精神汩没于自然之中”的自在阶段[5](P57),一切生命活动以及自我与世界的关系均未成为人类意识的自觉对象。
好景不长,乐园的失落接踵而至。在上述四则神话文本中,由于人类的某些行为,至上神无一例外地逐渐疏远人类,从此神高居于天,人委身大地,最终神人、天地分离。相类于伊甸园中亚当夏娃对上帝所设禁令的违拗,从M1中婴儿戕害上帝口中的乳房,M2中女人肆意索取过量的食物,M3中人类不顾前车之鉴偷盗食物等情节可知,部分撒哈拉以南非洲神话亦将天与地的分离归咎于人类对神谕的违背。较之完全倚仗神的乐园阶段,对神的挑战毋庸置疑闪耀着理性的光芒,人类开始大胆质疑甚至违抗此前未加论辩的至上神的唯一合法性,这一举措宣示人类独立意志的萌芽。但同时,正如M2中人类将未吃完的食物直接扔进垃圾堆,M3中人类在美食诱惑前重蹈覆辙等细节所昭示的,对于至上神禁令的背叛,实则还指向人类对于贪欲的无节制,且尤其突显为口腹之欲的无餍。因而,神人、天地作别又兼具鲜明的对于人类享乐、犯忌、失约等弱点的惩戒与规训意味。
另有部分神话文本表示,天地分离乃出自人类的主观意愿。M4中首领女儿因直立行走与耕作受到妨碍而请求上帝远离大地,对乐园舒适圈的主动冲破以及对未知领域的果敢探索,展现出人类的能动性与创造性;但M4中“由此引发人间战争”的结局以及M2与M3中人类世代辛劳的下场,又暗示着对自我能动性膨胀可能招致灾祸的警惕。过度挑战自然带来的恶果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各阶段层出不穷。两百多年前,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以文学的方式告诫读者,不受限制的科学泛滥终将反噬人类自身;2021年一项科学调查统计,仅2019年一年内,现代工业带来的空气污染已造成非洲高达110万人口死亡。[6]神话中“人性的自缚”结局在现实中的轮番上演,印证了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所言:神话在最荒诞的幻想之中埋藏下“秩序”,且这种“秩序”将会以形式化了的“故事”的形式“一再于全世界重复出现”。[7](P192)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天堂型天地分离神话中,人类或因违逆神旨,或因主动抗争而与至上神分离,自天堂降落人间,从混沌无知迈向自我意识的觉醒。与此同时,对人性弱点的深刻反思亦随之俱来。一方面,人类的贪欲与自觉抗争一定意义上宣示着对至上神垄断权威的积极挑战;另一方面,对于贪欲与抗争不加节制地开发,将最终危及自身栖身的乐园,致使人类反而受困于自我的能动意志。
二、神人两隔:生死矛盾及中介者的显身
我们既知神话中天地未分之际,神人亲密无间;神人两隔后,人类与至上神的关系发生根本转变,退居大地的人类自我意识萌发,其结果主要显影于人类的“生之所依”与“死之所由”两大向度。
乐园时期,人类生存与繁衍全然依赖至上神供给,与神分离意味着人类开始自谋生路。观之其他民族神话,天地分离多与农事相关。苏美尔神话中“恩利尔从大地中取出土壤的种子,小心地把地和天分开……他发明了鹤嘴锄,‘日子’出现了,他引导劳作,支配命运”[8](P248);中国云南独龙族神话《创世纪》中紧随“天地分离”部分之后的亦是“种庄稼”[9](P187);佤族神话也讲述“天升高”后“粮食就种出来了”[10](P589)。撒哈拉以南非洲天地分离神话的结局同样与农业起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M2表示,从此“人们必须为了生活而辛苦劳作”;M3示意人类至今汲汲以求可口食物;M4更直观说明人类从此开始种植小米。进一步的,从M2中人类“仅需割下天空的一块来吃”以及M4中“人类伸手掰下一片天空来吃”蕴含的任意性可推想,乐园时期人类获取食物的方式,很可能意指先民曾靠游走四方、随机采撷来获取食材的采集经济阶段,人们幸运偶得的食物正犹如至上神对人的无偿恩赐。天地分离后,人类开始辛勤劳作,从事农业种植,M4中“研钵”与“杵”这些用于精耕细作的生产工具便是体现,而四则神话的主要流传地历史上均较早发展起发达的热带锄耕农业,在一定程度上辅证了这一猜想的合理性。或许可以认为,从神人和谐共生到神人两隔的情节推进背后,隐现的是先民对从采集经济向种植农业过渡的集体记忆。经由生产方式的更新,人类摆脱对至上神的依赖,将生存主动权掌握于自己手中,开启与天争胜的奋斗进程。
在此基础上再来探讨天地分离神话中屡次出现的与农业高度相关(如舂米、持杵)的女性形象时,也许便会有不同于惯常认知的新结论。曾有观点认为,“大部分非洲神话将得罪至上神的责任归咎于女人”[11],似乎旨在延续希伯来神话将破禁者夏娃设定为贪婪女性的立场,进而对原始妇女实施指控;但观之非洲各地流传的神话、谚语等民间文学,其中责备妇女的表述极少,而更多赞扬她们在创造生命及宗教祈祷中扮演的重要角色[12],丁卡人(Dinka)便虔心感恩“亵渎”神明的妇女,因为“她们发明了小米”[13](P53)。可见,妇女或许并非撒哈拉以南非洲神话意欲追责的对象;相反,她们在天地分离过程中承担的重要角色很可能恰是为了表明,女性是先民记忆中值得纪念的农业发明者,是人类创造力的早期践行者。
如果说农业起源是人类栖身的大地承载旺盛生命力的体现,那么土地同时亦是容纳生命走向终结的场所。M4的结局表明,人间由此引发招致死亡的战争,可知人类退居大地后,面临的另一根本变化即承受死亡。观之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死亡起源神话,有不少即连缀在天地分离神话之后讲述,且通常将天(神)与地(人)的分离作为故事讲述的默认逻辑前提:因神与人无法直接接触,神话中出现了一类在二者之间传递消息的角色——中介者。
延用弗雷泽(James George Frazer)的归类法,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大部分死亡起源神话属于“篡改消息型”[14](P25)。在阿散蒂人(Ashanti)的观念中,至上神离去后派山羊到人间传达永生的消息,但山羊路上耽误,再次派出的绵羊却传错话,从此人类必须接受死亡的归宿;塔蒂布须曼人(Tati Bushmen)、马萨尔瓦人(Masarwa)中亦广泛流传着近乎相同的神话,只是主角变成乌龟与兔子;班图部落(Bantu)的神话则通常安排变色龙充当永生信使,蜥蜴充当死亡信使[14](P20)。此外,撒哈拉以南非洲亦存在少量“蜕皮型”神话,如塞拉利昂科诺人(Kono)认为,“上帝送给人一捆新皮,但送皮的狗路上耽误了,于是皮被蛇偷走,由此蛇知道了换皮的方法得以永生,但人拥有了死亡”[3](P41)。无论各神话文本在具体细节处如何各放异彩,其共通之处在于,死亡的消息均无法在至上神与人类之间直接沟通,人类丧失对自我命运的第一知情权,仅能经由中介者的上传下达来被动接受。这些中介者无一例外均被设定为粗心或恶毒的动物,它们不仅作为信使,更被视为诱发死亡的“替罪羊”,人类将依靠主观能动性无法禳解的死亡恐惧转嫁到动物身上,通过贬低动物的合法地位来想象性满足自我在自然界中的优越感。故而至今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部分地区,人们碰到蜥蜴等动物时仍要将它杀死并说:“这就是那个丑陋的家伙,当初跑来说人要死的那个家伙!”[14](P31)
天地分离后,人类的自我认知困境在与至上神相关的生死两大向度间浮现:在生存之道上,人们能动地摆脱至上神笼罩,彰显出独立自主的创造能力;但在解释死亡之由来时,人类又将自我命运束手交由代神立言的中介者裁决,人类生生不息的无限创造性终受限于无可辩驳的死亡终点。
三、人际建设:等级秩序的神圣根基
伴随天地分离神话中至上神的隐退,中介者的存在不仅形塑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先民对于死亡的理解与言说,更内化为古代政治文化建设的既定前提,预设并事实上开启了人类与至上神沟通的更高层次条件。由此,人类的自我认知除表现在纵向的神人关系以外,还显影于横向的、共同栖居于大地上的同类之间,进而推动人类社会形态的嬗变与发展。
在中国古史传说中,经由颛顼“绝地天通”,民神杂糅的“家为巫史”时代结束,个人自由通神的权力旁落,由此催生重、黎这类专司此事的中介群体。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亦如是,在神人两隔的前提之下,为满足人类继续向神祈祷祝颂之需,祭司、通灵人、占卜师、巫医等神职人员应运而生。他们因掌握常人力所不能及的通神本领,在社会群体中脱颖而出,文字、天文、医疗等领域通常均由他们执掌。久之,人类在与同类共同生产生活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社会分工,开始意识到作为个体的自我以及自我与他者的区别。沟通神人的中介者身份被广泛认同为崇高权力的表征,成为统治阶级赖以进行权力建构的神圣资源,因而部落首领或国王通常将自我指认为最具权威的通神者。有时为进一步确立其作为中介者的合法性,统治者还会被赋予神灵血亲的神圣身份,以稳固其一神之下、万民之上的至尊地位。这一建构逻辑在世界多地文化史上均可寻得,《金枝》中载,“把王位称号和祭司职务合在一起,这在古意大利和古希腊是相当普遍的”,“古代中国的皇帝们也都主持公共祀典”[15](P16)。由此,人们对遥不可及的神灵的需求,实际转向了对作为神人沟通中介的现实统治者的崇拜。
但不同于中国上古神话中“绝地天通”事件发生后,历代文人墨客仍不断通过文学创作怀想失落的天堂,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先民而言,天地分离之后,至上神便与人类“形同陌路”,天上的乐园不再令人魂牵梦萦,地上的家园才是人们情之所系。在德兰士瓦北部洛维杜人(Lovedu of Transvaal)的神话中,至上神创造世界后就隐退了,人们现在不知道他的情况,也不再挂念他;斯威士人(Swazi)对至上神亦只有模糊印象,认为他“创造大地和人类,最后又降死亡于人类,但由于太遥远,显得和世人很生疏”。由于至上神的疏远,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人民转而关注与人们日常生活休戚相关的各类自然神与祖先神,例如奥瓦姆博人(Ovambo)便几乎不祭拜上帝卡伦噶(Kalunga),而更多寻求风暴神与祖先的庇佑,人们相信对他们的祈祷最终能够反映到至上神处。[3](P37~38)因而,尊奉统治者为与自然神、祖先神沟通的中介,将其塑造为神灵本身或其后裔,成为非洲社会分化程度较高地区的普遍宗教现象。加纳作家丹夸(J.B.Danquah)便曾坦言:“阿坎族(Akan)的上帝就是被神化的祖先,作为始祖,他理应受到崇拜,而这种崇拜就体现在现实的公众的领袖身上。”[16]类似的,约鲁巴人的雷神实则是奥约帝国(Oyo)的第四代首领,统治阶级将雷神崇拜强加于从属民族,以迫使其臣服于约鲁巴王室统治。[3](P71)
这种对统治者的敬畏溯及祖先(或自然)崇拜,又由对祖先(或自然)崇拜转向对其在俗世的中介代言人——统治者的膜拜之间的轮回,遂使人间统治者最终被神化为本氏族、本部落神圣不可侵犯的至高威权。追根溯底,正是天地分离神话隐含的文化逻辑赋予了社会权力以神圣的起源。神人两隔后出现的中介者形象扩展了人类认知自我的维度,神与人之间的纵向统摄关系向俗世统治者与被统治群体间的横向统属关系延伸,乐园时期均质无等差的人类群体衍生为内部等级分明、权力日益集中的社会实体。毋庸置疑,等级制、集权制的出现是人类迈向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统治权力的神圣化建构通过制造与推广全民共享的信仰认同,客观上还具有维系社会群体的纽带功能;但与此同时,统治者对中介者身份的霸占将导致神权、政权高度集中,悬殊的等级地位又将为人间永无休止的暴力纷争与深重的剥削压迫埋下伏笔。正如谭嗣同所言,“自绝地天通,唯天子始得祭天……民至此乃愚人膏肓,至不平等矣”[17](P89),M4结局亦表示“由此引发人间的战争”。退居大地后,人类群体内部的发展与建设长期在有序与失序、文明与野蛮、希望与绝望间迂回向前。
四、结论
为什么神灵总是显得遥不可及?为什么人类会饱受纷争与死亡之苦?本文以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广泛流传的四则文本为例,试图从中探寻人类文化心理层面的答案。天地分离神话告诉我们,与天堂的告别在宣示人类自我能动意识觉醒的同时,对人性的弱点与局限已有深刻反思,并于此后在纵向的神人关系以及横向的人际关系双重维度,奠定了人类将永远于觉醒与自缚间徘徊往复的原型发展模式。换言之,天地分离、与神作别具有终极意义上的二律背反性,与人性解放构成一体两面的,是人类为自身设下的永难翻案的沉重枷锁,并且这种矛盾困境不仅指向过去,更永恒地投向未来。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之旨在于以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文本为例,尝试为世界各民族神话中常见的“天地分离”母题提供一种新的阐释可能,但上述结论能否普遍适用于其他各民族神话,且盼专文加以进一步的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