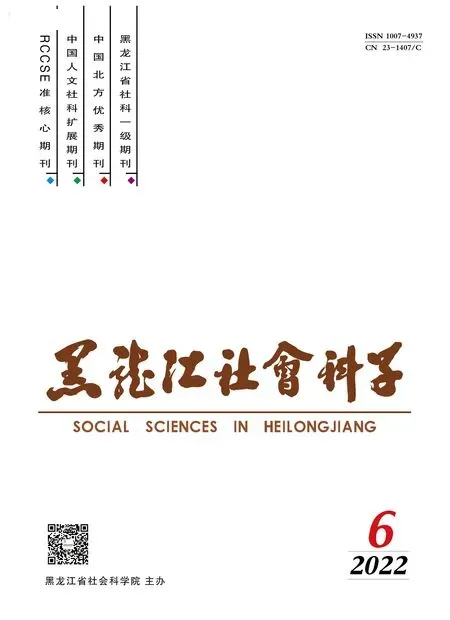唐代“河北故事”的文本起源、历史内涵及确立过程
——以韩愈《魏博节度观察使沂国公先庙碑铭》为线索
李 佳 哲
(河北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1)
“河北故事”是唐代藩镇研究领域的重要名词,学界对其内涵和形成过程已多有研究(笔者认为,“河北故事”“河北旧事”“河朔故事”“河朔旧事”“河朔旧风”“河朔事”等词在指代河北藩镇节帅更迭原则时具有相同的内涵,但其他表述均是由“河北故事”一词演化而来。因此在行文时,除了引用史料及前人论述外,全部使用“河北故事”一词)。其中樊文礼较早提出“河朔故事”的核心内涵在于藩镇节帅的世袭,而所谓藩镇节帅的世袭“既指诸节帅父子兄弟递相承袭,又指诸藩镇将士对节帅的自行拥立,而以后者尤见重要”[1]。张天虹对“河朔故事”的内涵进一步发覆,指出“河朔故事”至少包含三个方面的含义,即节度使之位的继承原则(世袭制)、相对独立的自治原则以及较为模糊的上下尊卑关系[2]。孟彦弘从唐廷对藩镇政策的角度描述了“河朔故事”确立及发展的过程,认为“河朔故事”是代宗为了结束安史之乱而采取的权宜之计,之后由于德宗、宪宗两朝对河北藩镇相继用兵的失败,使唐廷最终不得不接受“河朔故事”的事实[3]。对以上观点,冯金忠、李碧妍、仇鹿鸣等学者相继表示认可。
近来秦中亮注意到,史乘中关于薛嵩死后“(相卫)军吏欲用河北故事,胁平知留后务”的记载乃是后世史家的文本书写,并非“河朔故事”的真实起源,并指出“河朔故事”是“以唐廷认可河朔藩镇内部实行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世袭制为内核,又以节度使在藩镇内部一系列的人事安排来确保继承人顺利继位为外延”[4]。
可以说,学界对“河北故事”的研究在不断深化和拓展,但其未尽之处在于,现有研究多瞩目于“河北故事”在史实层面的形成与发展,而对其文本起源则鲜有关注,由此导致学者在探讨“河北故事”的内涵时往往表现出一种“不言自明”的状态:始终单方面强调“河北故事”对河北藩镇的作用,而忽视了其作为一种关系原则对唐朝中央政府的意义。有鉴于此,本文尝试以韩愈《魏博节度观察使沂国公先庙碑铭》为线索,从探究“河北故事”的文本起源入手,以揭示其完整内涵。同时,在梳理唐朝中央政府与河北藩镇关系演变的基础上,探究“河北故事”开启和确立的过程,以期能够拓宽唐后期中央政府与河北藩镇关系研究的视野。
一、从“故事”到“河北故事”
一般认为,“河北故事”“河朔故事”“河朔旧风”“河朔事”等词在指代河北藩镇节帅权力父子兄弟相继的更迭原则时具有相同的意义。如代宗大历年间,昭义节度使薛嵩去世,其子薛平“年十二,为磁州刺史,军吏欲用河北故事胁平知留后”(《旧唐书》卷124《薛嵩传》)[5]3526;宪宗元和年间,刘总继任幽州节度使之后,“愿述先志,且欲尽更河朔旧风”(《旧唐书》卷143《刘总传》)[5]3903;文宗太和年间,横海节度使李全略去世,其子李同捷“欲效河朔事,求代父任”(《旧唐书》卷142《王庭凑传》)[5]3887;昭宗乾宁二年(895),义武节度使王处存“卒于镇,三军以河朔故事推处存子郜为留后”(《新五代史》卷39《王处直传》)[6],均指河北藩镇在节度使更迭之际不受唐廷节制,自行择帅的行为。但不容忽视的是以上诸词均属于建构性文本,即均属于后世史家对既往史实的文本记录,而非当事人在历史发生时的现场表达。与此形成对比,“河北事”往往作为唐人现场表达的习惯性用词被运用于各种情境之中。如《资治通鉴》记载,德宗建中三年(782)唐廷出兵讨伐河北藩镇,马燧将兵与幽州节度使朱滔等对峙于魏州:“是夕,滔等堰永济渠入王莽故河,绝官军粮道及归路,水深三尺余。马燧惧,遣使卑辞谢滔,求与诸节度使归本道,奏天子,请以河北事委五郎处之”[7]7450;《新唐书》卷146《李吉甫传》记载,宪宗元和年间,魏博节度使田季安染疾病笃,于是身为宰相的李吉甫“请任薛平为义成节度使,以重兵控邢、洺,因图上河北险要所在,帝张于浴堂门壁,每议河北事,必指吉甫曰:‘朕日按图,信如卿料矣’”[8]4742。以上两则史料反映出无论是在唐廷与河北藩镇的双方交流中,还是在唐廷内部对河北藩镇事务的单方讨论中,均存在使用“河北事”一词的现象,而且其内涵则仅仅泛指与河北藩镇有关的普通事务,并非特指藩镇节帅权力更迭原则。
在辨析建构文本和现场表达区别的前提下,笔者从文本形成的角度对“河北故事”“河朔故事”“河朔旧风”“河朔事”等词的出现时间进行考证,发现“河北故事”最早出现于元和八年(813)韩愈为田弘正所写的家庙碑铭即《魏博节度观察使沂国公先庙碑铭》之中:
田季安卒,其子幼弱,用故事代父,人吏不附,迎弘正于其家,使领军事。弘正籍其军之众,与六州之人,还之朝廷,悉除河北故事,比诸州,故得用为帅[9]。
在上述碑文中,韩愈使用“故事”与“河北故事”两个词记录了魏博镇的政权更迭情况。其中所谓“故事”一般泛指普通事务既往的处理原则,它既非韩愈首创,也并非仅适用于河北藩镇,如:
杨炯《中书令汾阴公薛振行状》:“诏赠光禄大夫使持节都督秦成武渭四州诸军事秦州刺史,余如故……别降中使赐敛衣一袭、杂物百段,又诏陪葬乾陵,依故事也”[10]876;《唐大诏令集》卷2《中宗即位赦》:“业既惟新,事宜更始,可改大周为唐,社稷宗庙陵寝郊祀礼乐、行运、旗帜服色、天地等字、台阁官名、一事已上,并依永淳已前故事”[11];李翱《故东川节度使卢公传》:“李锜与国同族,其反逆不道,身既斩死,并杀其子,罪塞矣。若将追毁祖父坟墓,臣以为不可。淮安王有佐命之功,且国贞又死王事。汉诛霍禹,不毁霍光之坟,房遗爱伏诛,罪不追于元龄,此前代及圣朝之故事也。”[10]2863
虽然“故事”为唐代文本书写的一般用法,但“河北故事”却是韩愈根据“故事”的使用习惯创造出的用于指代魏博镇藩帅权力传递原则的用词。具体而言,从安史之乱结束到元和八年,魏博镇已经经历了五代节度使的更迭,分别为首任节度使田承嗣、田承嗣之侄田悦、田承嗣之子田绪、田绪之子田季安以及田承嗣堂侄田弘正。从五位节度使的上位方式来看,田承嗣因乱获位,田悦在田承嗣的安排下继任叔父帅位,田绪残杀田悦以夺大权,田季安与田弘正均为军士所推拥,其中无一人为唐廷正常任命,而且所有藩帅均出自田氏家族,由此形成了有别于唐朝其他地区地方长官的任命原则。同时,在藩帅产生方式上,魏博镇与成德镇、幽州镇存在着高度的一致性,因此碑文中所谓的“河北故事”便有了独特的文化内涵,成为指代河北藩镇节帅父子兄弟世袭相继的专有名词。
从“故事”到“河北故事”,是韩愈对安史之乱后河北藩镇统治状况的概括,这种概括本质上属于一种文本建构:它以唐代文本书写习惯(即史料中之“故事”)为基础,以河北藩镇节度使权力更迭原则(即史料中田弘正将帅自选与上秉朝命的继任方式)为核心,同时涉及河北藩镇军民超脱唐廷管辖的历史状况(即田弘正“籍其军之众,与六州之人,还之朝廷”的做法),以及由此产生的河北藩镇与唐廷之间的互动关系(即史料中“悉除河北故事,比诸州,故得用为帅”的结果)。可以说,“河北故事”较为全面、准确地概括了安史之乱后河北藩镇的统治状况及其与唐廷的关系,由此为后世史家记录河北藩镇的史事提供了一个经典文本。不过,由于“河北故事”的建构属性,导致它在后世的史学记录中受到不同时期用词惯例和个人书写习惯的影响,逐渐衍生出众多与此意思相同的名词,如“河朔故事”“河朔旧事”“河北旧事”“河朔旧风”等。但无论名词如何演变,如果我们遵照“河北故事”的文本属性,将其置于完整的记录文本当中便可发现,其内涵主要包含三方面的内容:一是河北藩镇节度使的自选原则,二是河北藩镇超脱唐廷管辖的独立状态,三是唐廷与河北藩镇围绕节帅更迭或独立状态产生的关系变动。对于前两个方面,学界已多有研究,也基本上取得了一定的共识,唯有第三点先辈学者似未曾论及,接下来本文将依据相应史料进行阐释。
为了全面掌握史料中“河北故事”一词的使用情况,笔者利用“文渊阁四库全书(原文及全文检索版)”对“河北故事”及其相关用词进行了全文检索,结果如下:河朔旧事(25条)、河北故事(23条)、河朔故事(11条)、河朔事体(5条)、河朔事(4条)、河朔旧风(2条)、河北旧事(2条)、河北事故(1条)。综合分析检索所得73条史料便可发现,在所有记录“河北故事”的文本中,除了记录河北藩镇政权变动的内容外,还会附带或者蕴含唐廷对相关事务的处理态度,如:
德宗贞元元年(785),幽州节度使刘怦去世,“军人习河朔旧事,请(刘)济代父帅,朝廷姑务便安,因而从之,累加检校兵部尚书”(《旧唐书》卷143《刘济传》)[5]3900;穆宗长庆年间,田布率魏博将士讨伐镇冀王庭凑,为将士逼行“河北旧事”,田布难从,乃抽刀自刺而死,“(史)宪诚闻布已死,乃谕其众,遵河北旧事。众悦,拥宪诚还魏,奉为留后。戊申,魏州奏布自杀。己酉,以宪诚为魏博节度使”[7]7929;穆宗长庆初年,刘总“欲尽更河朔旧风,长庆初,累疏求入觐,兼请分割所理之地,然后归朝……及疏上,穆宗且欲速得范阳,宰臣崔植、杜元颖又不为远大经略,但欲重弘靖所授,而未能省其使局,惟瀛、漠两州许置观察使,其他郡县悉命弘靖统之”(《旧唐书》卷143《刘总传》)[5]3903;武宗会昌年间,泽潞节度使刘从谏病逝,其子刘稹谋继帅位,“诸将乃诣监军崔士康邀说请如河朔故事……诏从素书敕稹护丧还东都,稹不奉诏。诏群臣议……有诏夺从谏、稹官,敕诸军进讨”[8]6016。
以上史料反映出,史书言及“河北故事”,并非仅仅着眼于河北藩镇内部政局的变动,也意在表达其与唐廷的态度和举措有着深刻的关系。“河北故事”的最终形成是河北藩镇与唐廷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在藩镇政局变动的过程中缺乏唐廷明确的态度,那么河北藩镇的政局便无法进入一个稳定的状态,也就无法出现“故事”的最终结局。因此,唐廷与河北藩镇的交流也应属于“河北故事”的重要内涵。
二、从“逆乱之地”到“许袭之藩”
对“河北故事”文本属性的把握,以及对其内涵应当包含唐廷与河北藩镇关系变动的揭示,可以说为探讨“河北故事”的形成提供了新的视角。接下来,本文将围绕河北藩镇与唐廷在安史之乱后不同历史时期表现出的不同政治追求和处事态度,来重新审视“河北故事”的形成过程。
(一)叛乱的延续:代宗、德宗两朝唐廷与河北藩镇的关系本质
代宗宝应二年(763),唐廷迫于“郡邑伤残,务在禁暴戢兵”(《旧唐书》卷141《田承嗣传》)[5]3837的压力,通过付授安史降将节度使的方式结束了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是时,李宝臣以成德节度使的身份统有恒、赵、深、定、易、冀六州之地,薛嵩以相卫节度使的身份领有相、卫、邢、洺、贝五州之地,田承嗣以魏博都防御使的身份领有魏、博、德、沧、瀛五州之地,李怀仙以幽州、卢龙节度使的身份领有幽、莫、妫、檀、蓟、平六州之地。虽然这样的划分确立起了乱后河北地区的统治秩序,但其本身并未蕴含太多的政治谋略,无论是对于唐廷,还是对于河北诸藩,都只是为了尽快甩掉战争包袱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在此局势下,唐廷和河北藩镇的关系表现出了强烈的变动、过渡色彩。清人王夫之对此曾有论曰:“讨贼易,平乱难;诱贼降己易,受贼之降难;能受降者,必其力足以歼贼,而姑容其归顺者也。威不足制,德不足怀,贼以降饵己,己以受降饵贼,方降之日,即其养余力以决起于一旦者也。”[12]唐廷在军事实力不足的情况下,将河北诸州付授安史降将的做法,其实并不是彻底平定了安史之乱,在此基础上确立的唐廷与河北藩镇的关系很大程度上仍可视作安史之乱的延续。河北藩镇一方,受封的安史降将曾随安史父子叛乱多年,见惯了叛乱中的僭越和悖逆,在性格上保持着强烈的反叛特性,由此在代、德两朝,河北藩镇虽然接受了分封,但依旧表现出极大的政治野心和极强的扩张性。归降之初,魏博节度使田承嗣“既得志,即计户口,重赋敛,厉兵缮甲,使老弱耕,壮者在军,不数年,有众十万”(《新唐书》卷210《田承嗣传》)[8]5924。于是在代宗大历八年(773)正月,趁相卫节度使薛嵩去世之机,“遣大将卢子期取洺州,杨光朝攻卫州……诱卫州刺史薛雄,雄不从,使盗杀之,尽屠其家”[7]7348,遂尽据相、卫、洺、磁、贝五州之地。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名位既高,自擅一方,专贮异志。妖人伪为谶语,言宝臣终有天位”(《旧唐书》卷142《李宝臣传》)[5]3868,并没有仅仅固守封土的打算。至建中之乱,河朔三镇更是联盟称王,“(朱)滔乃自称冀王,田悦称魏王,王武俊称赵王,仍请李纳称齐王。是日,滔等筑坛于军中,告天而受之。滔为盟主,称孤;武俊、悦、纳称寡人。所居堂曰殿,处分曰令,群下上书曰笺,妻曰妃,长子曰世子。各以其所治州为府,置留守兼元帅,以军政委之;又置东西曹,视门下、中书省;左右内史,视侍中、中书令;余官皆仿天朝而易其名”[7]7455。显然,这一时期河北藩镇僭越悖逆的行为已经远远超出了“河北故事”的内涵,河北藩帅的政治追求不仅仅是维持自身的割据地位或将藩镇已有土地传之子孙,而是不断地从野心和实力出发,延续着安史父子犯上作乱的政治意图。
鉴于河北藩镇的政治野心和僭越行为,代、德两朝中央政府对河北藩镇都采取了坚决的削弱和镇压政策。代宗广德元年(763)五月,“制分河北诸州:以幽、莫、妫、檀、平、蓟为幽州管;恒、定、赵、深、易为成德军管;相、贝、邢、洺为相州管;魏、博、德为魏州管;沧、棣、冀、瀛为青淄管;怀、卫、河阳为泽潞管”[7]7261,意图彻底解决河北藩镇的割据状况。大历八年,“委河东节度使薛兼训、成德军节度使李宝臣、幽州节度留后朱滔、昭义节度李承昭、淄青节度李正己、淮西节度李忠臣、永平军节度使李勉、汴宋节度田神玉等,掎角进军”(《旧唐书》卷141《田承嗣传》)[5]3840,对田承嗣进行讨伐,并成功夺取太行山东的邢、磁二州,形成地跨太行的昭义镇,实质性地改变了河北藩镇的力量格局(唐廷将邢、磁二州交由泽潞管辖,不仅可以从区位上对成德、魏博二镇形成威胁,而且还可以借助太行山陉道使之与泽潞产生联系,从而增强及提升二州的后方支持与战略地位。从更广阔的范围来看,邢、磁二州划归泽潞,也可使河北地区借泽潞“为洛阳两河之屏障,晋豫间交通孔道,南北向出太行可制洛阳、三河一带”[13]的区位与中原地区保持联系,而不至于被太行山和黄河从西、南两面锁死,成为完全封闭、与长安及洛阳隔绝的地理区域)。大历十四年五月,德宗即位,几乎同时,河北藩镇也进入节帅谢世的高峰。面对河北藩镇的政局变动,新即位的德宗先是以强硬的态度拒绝了河北藩镇关于继任的要求,然后又谋划了对拒不听命藩镇的讨伐战争,其最终意图便是要彻底解决安史之乱后出现的割据问题。对于建中年间的战争,成德节度使王武俊认为:“朝廷不欲使故人为节度使,魏博既下,必取恒冀,故分粮马以弱之”[7]7319;魏博节度使田悦派人游说朱滔时也说:“今上英武独断,有秦皇、汉武之才,诛夷豪杰,欲扫除河朔,不令子孙嗣袭……如马燧、抱真等破魏博后,朝廷必以儒德大臣镇之,则燕赵之危可跷足而待也。”(《旧唐书》卷141《田承嗣传》)[5]3843藩镇节帅的认识可谓是触及了德宗最深刻的政治意图。由此也可以看出这一阶段唐廷与河北藩镇的关系本质,即安史之乱虽已结束,但河北藩镇和唐廷均延续了安史之乱期间的政治态度。一方面,河北藩镇诸帅仍像安史父子一样,拥有极强的政治野心,他们将“父子兄弟相继,土地传之子孙”的追求附着于“开疆拓土、僭越称王”的行为当中,对唐廷的政治权威产生了严峻挑战;另一方面,唐廷对于河北藩镇的割据行为和世袭要求,则不断打压和驳回,期间虽有妥协和姑息,但也仅仅是因实力不足而采取的无奈之举,并非唐廷对藩镇割据行为的认可。
(二)“河北故事”:建中乱后唐廷与河北藩镇的相处之道
唐廷与河北藩镇关系的转变发生于建中平叛失败以后。建中四年,唐廷为了平定河北与淮西藩镇的叛乱,投入了尽可能多的兵力到前线战场,“时河东、泽潞、河阳、朔方四军屯魏县,神策、永平、宣武、淮南、浙西、荆南、江泗、沔鄂、湖南、黔中、剑南、岭南诸军环淮宁之境”[7]7465,但战局并没有朝着有利于唐廷的方向发展。同时,为了营救被李希烈围困的哥舒曜,唐廷继续征发泾原诸道兵奔赴淮西战场,结果泾原兵在经过长安时因供给不足发生叛乱,叛军进入长安,德宗仓皇出逃。此时闲居长安、郁郁不得志的前幽州节帅朱泚被奉为乱军之首,并于长安僭号称帝。之后,他一方面派军进攻奉天,另一方面派使者赴范阳,意图联合河北叛乱藩镇共同南下。在此危急形势下,德宗下诏罪己,称“悔过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辞不得不尽,洗刷疵垢,宣畅郁堙,使人人各得所欲”[7]7509,并明确表示“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等,咸以勋旧,各守藩维,朕抚驭乖方,致其疑惧;皆由上失其道而下罹其灾,朕实不君,人则何罪!宜并所管将吏等一切待之如初。朱滔虽缘朱泚连坐,路远必不同谋,念其旧勋,务在弘贷,如能效顺,亦与惟新”[7]7511。德宗在诏书中的言论实际上彻底否定了唐廷之前对待藩镇的政策,认可了河北藩镇割据擅权的现状。而作为对德宗下诏罪己的回应,王武俊、田悦、李纳、朱滔皆去王号,上表谢罪,表示尊重唐廷的政治权威。至此,唐廷意图彻底解决河北藩镇割据局面、河北藩镇不断挑战唐廷政治权威的关系模式结束,双方开启了“河北故事”模式下的相处之道。
在“河北故事”模式下,唐廷与河北藩镇的关系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双方从上一阶段的零和博弈演变为这一阶段的互认共存。首先,唐廷以河北藩镇尊重中央权威为前提,赋予了河北藩镇“自行择帅,将土地传之子孙”的权利。史载建中平叛失败后,“德宗中岁,每命节制,必令采访本军为其所归者”(《旧唐书》卷132《卢从史传》)[5]3652;“上不欲生代节度使,常自择行军司马以为储帅”[7]7696。可见唐廷开始以一种宽容、务实的态度对待河北藩镇节帅的更迭问题,因之贞元年间藩镇节帅的更迭局面才显得较为平和,没有引起太大的波澜。贞元元年,朱滔去世,幽州镇军人相继推举刘怦、刘济父子为帅;贞元十二年,田悦去世,魏博军人推其子田季安继任帅位;贞元十七年,王武俊去世,其子王士真袭位。对于这几次变动,朝廷均“姑务便安,因而从之”。其次,河北藩镇以享受自治权利为基础,承担起为唐廷内除叛乱、外御强敌的义务。早在建中之乱后期,魏博与成德二镇便与昭义镇联合,投入到阻止幽州朱滔南下的战争之中,最后迫使朱滔退回幽州,上表待罪。随后贞元十年,昭义节度使李抱真薨逝,其子李缄谋继帅位,秘不发丧,并遣人赴成德王武俊处寻求支持,结果为王武俊所怒斥:“吾与乃公厚善,欲同奖王室耳,岂与汝同恶邪!闻乃公已亡,乃敢不俟朝命而自立,又敢告我,况有求也”[7]7682,义正言辞地拒绝了李缄的请求。此外,幽州镇自朱滔获得唐廷的宽赦以后,由于区位的原因,成为唐廷捍蔽东北少数民族入侵的重要力量。史载德宗贞元十一年四月,“幽州奏破奚王啜利等六万余众”[7]7690;“奚数侵边,(刘)济击走之,穷追千余里,至青都山,斩首二万级。其后又掠檀、蓟北鄙,济率军会室韦,破之”(《新唐书》卷212《刘济传》)[8]5794。这一时期幽州镇可谓忠实、高效地履行了唐廷赋予的“押奚、契丹两蕃使”职责,对稳定大唐的东北边疆发挥了积极作用。
作为唐廷与河北藩镇互认共存关系原则的“河北故事”,自德宗朝开启,至穆宗长庆年间最终确立,其间经历了一个唐廷用兵河北、河北藩帅谋归唐廷、河北藩镇再叛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无论是唐廷一方出于宪宗个人的政治抱负,还是河北藩镇一方受到个别藩帅政治选择的影响,都曾导致“河北故事”出现过一些波折。宪宗“欲革河北诸镇世袭之弊”[7]7781,曾于元和四年、十一年两次用兵成德,但均无功而返,未能改变“河北故事”的基本原则。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可以看出,宪宗之所以有用兵河北的决心,一是征讨吴蜀胜利后政治自信高涨:“群臣见陛下西取蜀,东取吴,易于反掌,故谄谀躁竞之人争献策画,劝开河北,不为国家深谋远虑,陛下亦以前日成功之易而信其言”[7]7785;二是河北藩镇之间矛盾的刺激:“王承宗纵兵掠幽、沧、定,三镇皆苦之,争上表请讨王承宗。”[7]7843而二者中尤以后者因素为重,这一点可以从唐廷所派出的兵力构成清晰看出。但战争实际发生以后,各镇作战的态度和效果却远未达到唐廷的预期:“(李)师道令收棣州,至今竟未奉诏,至于表章词意,近者亦甚乖宜。(田)季安等心元不可测,与贼计会,各收一空县而已,相顾拱手便休……刘济大奸,过于群辈,外虽似顺,中不可知,有功无功,进退获利,初闻罢讨,或可有词,见雪恒州,必私怀喜。何则?于承宗本末之势同也。”[14]致使唐廷不仅无法取得对王承宗的胜利,更不能大范围改变“河北故事”的基本原则。
而河北藩镇作为另一角色,也曾出现过藩帅主动变革“河北故事”之举。宪宗元和七年,魏博节度使田弘正在田季安去世后被军士推举为帅,田弘正向军士提出的条件便是魏博从此“守天子法,以六州版籍请吏,勿犯副大使”(《旧唐书》卷141《田弘正传》)[5]3849,实现了魏博的归顺。元和十五年,成德节度使王承宗薨逝,诸将拥立王承宗之弟王承元为帅,承元拜泣不受,诸将固请不已,承元谓诸将曰:“诸公未忘先德,不以承元齿幼,欲使领事。承元欲效忠于国,以奉先志,诸公能从之乎?”诸将许诺,承元方于衙门都将所视事,并秘密上表请朝廷任命节帅。由于魏博与成德归顺,唐廷遂对两镇藩帅作出调整:“徙田弘正为成德节度使,以王承元为义成节度使……李愬为魏博节度使。”[7]7907受到魏博、成德两镇归顺的影响,幽州节度使刘总感到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因上疏愿奉朝请,且欲割所治为三:以幽、涿、营为一府,请张弘靖治之;瀛、莫为一府,卢士玫治之;平、蓟、妫、檀为一府,薛平治之。尽籍宿将荐诸朝”(《新唐书》卷212《刘总传》)[8]5976。由此唐廷实现了对河北三镇的重新控制,“河北故事”似乎不再行用。不过,田弘正、王承元、刘总对“河北故事”的变革,并不代表藩镇将帅士卒和诸州百姓对归顺唐廷的完全接受,因为这三人选择归顺唐廷多出于个人因素或私人利益。田弘正认为自己为帅乃是“白刃之下,谬见推崇”,其兄田融也认为他“卒不能自晦,取祸之道也”(《旧唐书》卷141《田弘正传》)[5]3849;王承元对将士也曾说过:“承元欲效忠于国,以奉先志……奉诏迟留,其罪大矣!前者李师道未败时,议赦其罪,时师道欲行,诸将止之,他日杀师道,亦诸将也!今公辈幸勿为师道之事,敢以拜请。”(《旧唐书》卷142《王承元传》)[5]3883可见,田弘正、王承元的归顺很大程度上是其个人的避祸之举。同样,刘总选择归顺唐廷也是其晚年的自安之策:“及吴元济、李师道平,承宗忧死,田弘正入镇州,总失支助,大恐,谋自安。”(《新唐书》卷212《刘总传》)[8]5975而且,三位节度使的归顺并没有为河北藩镇带来任何实际利益,反而使藩镇将士和诸州百姓受到了严厉的责骂,承担了不必要的负担。史载张弘靖坐镇幽州,“诏以钱百万缗赐将士,弘靖留其二十万缗充军府杂用,(韦)雍辈复裁刻军士粮赐,绳之以法,数以反虏诟责吏卒”[7]7914;田弘正“兄弟子侄在两都者数十人,竟为崇饰,日费约二十万,魏、镇州之财,皆辇属于道,河北将卒心不平之”(《旧唐书》卷141《田弘正传》)[5]3851-3852。由于上述行为使得藩镇将士、诸州百姓对节帅归顺唐廷的做法并不能真正接受,因此只要有机会便会有人企图作出改变,这也正是穆宗长庆年间河北藩镇复叛的重要原因。
史载长庆元年(821)七月甲寅,幽州监军使奏:“今月十日军乱,囚幽州节度使张弘靖别馆,害判官韦雍、张宗元、崔仲卿、郑郧,军人取朱滔子洄为留后”,而朱洄自以年老,令军人立其子克融为留后;长庆元年八月乙巳,镇州监军宋惟澄奏:“七月二十八日夜军乱,节度使田弘正并家属将佐三百余口并遇害,军人推衙将王庭凑为留后”;长庆二年正月“庚子,魏博兵自溃于南宫县。戊申,魏博牙将史宪诚夺师,田布伏剑而卒”(《旧唐书》卷16《穆宗纪》)[5]490-494。长庆叛乱,致使唐廷再次失去了对河北藩镇的控制。此后虽经年平叛,但结果仍归于失败,唐廷与河北藩镇的关系又回到了“河北故事”的框架之下。自此无论是唐廷还是河北藩镇,再也没有对“河北故事”这一关系原则作出实质性改变,“河北故事”作为唐廷与河北藩镇共同认可并自觉遵守的相处之道被沿袭下来。
综上所述,“河北故事”作为唐代藩镇研究不可跨越的话题,对它的认识应该从两个方面展开。首先,“河北故事”作为建构性文本在史料中的出现及发展脉络。准确来讲,其由韩愈创造,经历了一个从“故事”到“河北故事”的演化。此后则受到不同时期用词习惯和不同史家书写习惯的影响,逐渐衍生出诸如“河朔故事”“河朔旧事”“河朔旧风”之类意思相近的名词。而正因如此,当今学界惯用的“河朔故事”一词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河北故事”。其次,“河北故事”作为唐廷与河北藩镇间新的关系处理原则,开启的时间是在德宗建中平叛失败以后。它取代了之前从安史之乱延续下来的零和博弈的关系模式,使唐廷与河北藩镇开始以一种互认共存的方式相处。此后,经过宪宗、穆宗两朝的波动和调整,最终在穆宗长庆年间河北藩镇复叛之后确定下来,一直延续到唐末五代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