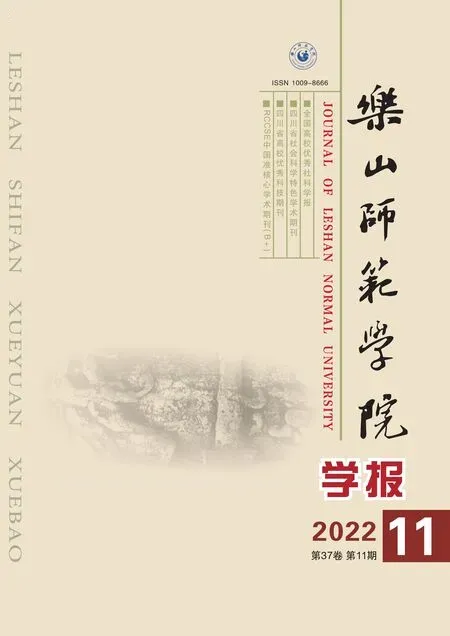“感通”的悲悯与达观
——论陈卓仙的悼亡诗
赵刘昆
(吉林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悼亡诗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已发展了2000余年,有着深厚的文学积淀和坚实的文化心理基础。自《诗经》以来,历朝历代皆有悼亡诗创作,且不乏名篇佳作,与之相对应的文学批评也蔚为大观。反观民国时期的悼亡诗创作,其取得的成就虽令人瞩目,但相应的理论批评却乏善可陈,尤其是像陈卓仙一类的女诗人的悼亡诗创作,成就虽大,却长期处于无人问津的遮蔽状态。因此把陈卓仙的悼亡诗置于整个悼亡诗的传统之中进行考察,重新审视其内在的文学价值和思想意蕴就显得格外重要。
一、性理的求索与实践:陈卓仙文化理想与文学观念的形成
唐迪风早期追随“五四”革命新潮,做过不少“出格”之事,至1920年前后,其思想“遽变”,转而信奉儒家性理之学。未入学门的陈卓仙于1905年与唐迪风结褵,她亲自见证、参与了唐迪风的思想转变,并在唐迪风的影响下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念和文学理念。
(一)唐迪风的思想文化观念及其“遽变”
唐迪风名烺,四川宜宾人,生于1886年5月17日,初字铁风,后改字迪风。他自幼被过继给三伯母抚养,却一直挂念日夜操劳的生母卢氏,事母至孝。1904年,唐迪风应童子试,为乡举末科秀才,后就学于成都叙属联中及法政专门学校。[1]193唐迪风曾任四川《国民公报》主笔,其时发为文章能够立论刚直、秉笔直书、历陈时弊。后来又与友人彭云生、蒙文通、吴芳吉等一起创办了敬业学院,唐被推为院长,教授国文、宋明理学及诸子课程。[1]191唐迪风生前仕途坎坷,文名不张,一直辗转于当地几所中学以及成都大学、四川大学、华西大学等处任教,生活一度拮据。他在蜀地的许多言行也颇有争议,面对“元年革命成,蜀之士不图建树,而竞禄”[2]7的情况,他“愤而有句:武士头颅文士笔,竟纷纷化作侯门狗,谁共我,醉醇酒”。[2]7也正因这些貌似出格的言论,他一度被混称为“唐风子”[3]11。但在那些知己们的眼中,唐迪风却是另外一种形象,“蜀中学问之正,未有过铁风者矣”、“直截透辟近象山,艰苦实践近二曲”、“信道笃而自知明”[2]12、“性情真挚坦易,语皆如肺肝中流出”[2]84等都是他们对唐迪风最为真实的评价。
唐迪风早年受五四新思潮的影响,崇尚个人主义,反对传统封建思想,为了表示“革命”和“进步”,他还推倒过庙里的泥菩萨,甚至自剪发辫,自改服饰,大有复明之志。唐迪风思想的转折发生在1920年前后,据唐君毅《(孟子大义)重刊记及先父行述》记载:“吾父于儒者之学,亦盖初不相契……及华西大学时,尝出题,命学生历举孔子之失云云。民国九年,……而其学遽变。”[2]14自此,唐迪风全面转向了儒家的性理之学,“卒于孔佛二老,得闻胜义。自矢求向上一着,以终吾年”[2]95便成了他下半生的追求。因此,每每忆及先夫,浮现在陈卓仙脑中的始终都是丈夫为中国文化命脉赓续而忧心、操劳的画面和场景,“吾君每言及孔孟学术垂绝,辄感慨欷歔。毅然以振起斯文自任,并以此教学子,授课时常常披肝裂肺,大声疾呼,痛哭流涕。其苦心孤诣,吾常为君技泪。因以‘徒劳精力,于人无补’之言劝君。君曰:倘能唤醒一人,算一人。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吾非智者,唯恐失人。吾不得已也。”[2]299而事实上,唐迪风也的的确确将自己的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在了孔孟之道的传播和宣扬上,他“颂孔孟朱陆于举世不喜之时”[2]9,不畏惧众人的非议,不迎合时代潮流的喜好,坚持自己的立场和选择。与此同时,他还把传统的性理之学与现实生活结合起来,将性理实践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之中,以性理的标准严格约束自己,而不仅仅只是为他人制定一种“无我”的标准。“唐迪风民胞物与、悲心忘我、断绝私利的救世之心并不止于教书育人,更见于日常细事,所谓‘膏火无资,而歌声若出金石。古人所难,不图于今见之。诚之所至,何事不成。’”[3]8唐迪风所追寻的性理之学,绝不是一种束之高阁的虚妄理论,而是一种具有极强的实践性、及物性的行动指南。他把传统的性理之学贯穿到混乱的现实之中,并以此重整现实与文化的秩序。在理想与现实的碰撞中,唐迪风将性理之学的精义转化为具有强大现实干预性的文化力量,并实现了家-国的同构。因而唐迪风的性理之学总是格外关注民生疾苦和支离破碎的传统文化,期冀通过性理之学的传承与现代性转化实现儒家正统文化的复兴,并以此构建一个传统框架内的新社会,实现社会与文化的双重重构。
(二)陈卓仙对唐迪风思想文化观念的接受及其创造性转化
1905年,唐迪风与陈卓仙结褵。二人虽然属于包办婚姻,但并不影响婚后二人如胶似漆、相敬如宾的夫妻之情,再加之丈夫的开明和婆婆的宽容,陈卓仙对家庭生活和其间的人伦关系十分看重。“忆我年十八来归,彼时与君浑然孩童也。君长我一岁,颇能好学。我乃不知所从,居则惟女红是务。出则联袂以嘻以游。先姑爱子媳若命,略不责所以。人有讥笑言于先姑者,先姑弗顾焉。我恃而无惮,益恣其憨状逾年。”[3]296陈卓仙少年时不曾进学,仅接受过相当有限的传统教育,对传统文化尚不熟悉,更不用说对五四刮来的时代新风有多大程度的接受了。陈卓仙的文学启蒙是从丈夫那里开始的,在《五月十日周年致祭三首(其二)》一诗中,对此有所提示:“结褵廿七载,道义相与之。虽曰为夫妇,实乃吾良师。而今谁相勉,有过谁箴规。眷念勖我殷,无以报心期。”[3]135可见,唐迪风不仅是陈卓仙家庭关系中的夫君,还是她本人的授业恩师。从这个意义上讲,陈卓仙所谓的文化选择其实只有唯一的通路与可能性,那就是接受丈夫的影响并将其转化为自我的内在生命与文化结构。当然,不可否认的一点是,不论从输出者还是从接受者的角度来看,其中输出与接受的姿态都是诚挚的、自愿的,因而双方的选择都是一种从主体出发的自由选择。在《杂感二首(其一)》中,陈卓仙则真实地描述了夫妻二人的日常状态:“曲肱固已乐,举世少复诚。幸有二三子,曷若共隐沦。言之不我鄙,挚意加温存。素心两相惬,完质刚坚贞。拳拳漆投胶,馥馥兰扬馨。”[3]140唐迪风对妻子不仅有日常的关怀与体贴,最为难得的是,二人秉承诗礼乐教、涵养情性的大传统,他们追求的夫妻之境,同样是“道义相期人[3]12,这一点在《祭迪风文》中说得更为清楚,“忆君语我有云:学非求功利也。尽其在己而己。我习焉不察,凡所为,莫不与君背驰。及其弊端百出,君凡引为己咎,自责其过,而我仍长恶不悛。君又以《涵泳篇》等置我侧,更亲磨墨裁纸,令我钞书,意我游心于此以纾积弊。”[4]67夫妻二人互相扶持,道义相期,可以说他们的婚姻因此而具有了某种“典范”性质。也正是在儒家伦理的“典范”意义上,陈卓仙与唐迪风在思想形成了一种文化性质的共同体,这一共同体的形成起自唐迪风的思想转折,经由夫妻二人日常生活的实践与贯通,最终在二者的思想发展中渐成气候,并直接指导了陈卓仙的日常生活与诗歌创作。
陈卓仙的思想资源直接来源于唐迪风,在唐迪风的指导和现实生活的启发下,形成了以性理为核心的儒家思想观念。陈卓仙的性理观与唐迪风基本一致,略有不同的是,与唐迪风相比,陈卓仙显然更喜欢从细腻、光滑的细节中发掘生活中的性理,也更喜欢将性理融于琐碎、重复的现实生活中,赋予现实生活以诗意与哲理。在《忆丹凤街旧寓》一诗中,诗人有钱买书,却无钱买米,家徒四壁,穷得老鼠都在光天化日之下跑出来找粮食的环境里,夫妻二人照样能于小窗之下“静简庄周说剑篇”,其乐陶陶,穷而不坠读书之乐,以读书抗拒贫穷,这种境界与兴趣,不是寻常夫妻能做到的。[3]9而其中的精神力量,恰好来自诗人所提倡的性理之学。“半方天井逼邻墙,反映全凭粉垩光。习篆灵蜗夜书壁,窥人饥鼠昼寻粮。苔痕枢纽闲门绿,瓦缝飞尘日色黄。最好围炉风雪里,小窗相对读蒙庄。”[3]91诗人不仅将性理视为一种文化观念,更是把它作为一种生活的实践哲学加以提倡,并试图通过对生活细节的解剖、打磨和抛光,获得某种贴地而行的实质性力量。也正是儒家的“虽穷而不坠青云之志”[5]157的理想信念直接鼓舞了诗人的实践,“感君子之诚兮,继道绪之绵绵。磨涅不缁磷兮,原无损于白坚。念国之无人兮,痛匏瓜之空悬。求仁而得仁兮,余又何怨乎天。”[3]142这种性理的精神使得诗人在丈夫去世后饱受离乱之苦,生活拮据,却不怨天尤人、自怨自艾,并相信自己能够力持众雏,继续前行。概言之,陈卓仙在日常生活中追寻性理的文化理想,在日常生活中构建性理的文学世界,实现了性理的日常化与文学化,并进一步将其视为人生中最重要的价值信条加以实践,完成了日常化和文学化的性理。
二、“感通”:沟通天人、连接幽明的姿态、方法与路径
“感通”是儒家性理之学的关键概念,也是陈卓仙在其悼亡诗中实现沟通天人、连接幽明的一种真挚姿态,更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方法与路径。而欲实现这一目标,则不得不借助于“感通”的同理与共情机制。
(一)“感通”:一种真挚、同情和理解的姿态
一体感(Einsfühlung)是一种深层次的生命感受力,它能超出个别有机体自身的限制而获得对其他生命机体的直接感受。它的基本特点正是把另一个生命机体的感受作为自己的感受来对待。[6]而“感通作为再生一体感,它的存在方式跟一体感相似”[7]114,都是努力克服自身限制以抵达对方精神世界,从而获得对对方充分理解的一种意图和认知方式。在陈卓仙的文化观念中,感通是其性理之学的核心与关键,她不仅将其视为抵达对方精神世界、进入对方文化宇宙的方法和路径,还把感通作为一种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加以说明和运用。同时,感通在陈卓仙的文化世界中还体现为一种真挚、同情和理解的姿态,不论是待人接物还是赋诗作文,皆以诚挚待之。如《记梦》一诗:
人天虽乖隔,至诚能感通。魂兮归乎来,窗月光玲珑。忽睹坐观书,故衣故时容。惊疑旋复喜,喜极泪沾胸。何期三秋别,于今一旦逢。儿女沉哀疚,遑论独我躬。子今果在此,原非昨梦同。明明非昨比,晓日升已东。顾我但微笑,何必形影从。死诚得所归,生乃实懵懵。死生与离合,执此皆愚庸。闻之心断绝,欲呼声转穷。欲听耳无聪,欲视眼无瞳。隐约君颜色,遽尔乘晨风。[3]49
在丈夫亡故后,诗人凭借着“至诚”感通到了丈夫的亡灵,实现了一种在场的交流和沟通。这种感通是以现实存在为原型构造的,而绝非建构在虚无缥缈的想象之上,也就是说,这种感通是有深刻的心理基础和现实依据的。诗人与丈夫生前经常在一起秉烛夜读,研习儒家经典,当自己触碰到丈夫的亡灵时,第一眼看到的仍然是丈夫刻苦读书的情境,这固然可以理解为一种现实的心理映射,但如果不是诗人与亡夫心灵相通,是无法进行如此完整有效的心理交融的。更令人为之动容的是,诗人并没有单向迫近对方的内心,而是由己及彼,再由彼及此,实现了双向的情感流动和交融。诗人不仅目睹了亡夫的夜读,还感受到了来自亡夫的微笑和关怀,这种由主体出发进入对方世界,再由对方的能量结构进入自己的心灵世界的多维度感通,形成了一种新的存在结构。在这一结构中,人与人之间的人格实现了最大意义上的平等,也正是在这一基础之上,陈卓仙与丈夫建立了一种新的家庭伦理关系。“结褵廿七载,道义相与之。虽曰为夫妇,实乃吾良师。”[3]135诗人与丈夫明为夫妇,却不止于夫妇,两人亦师亦友,互相尊重,在学道中相互扶持。而在日常生活中,丈夫也给予了诗人完全的尊重和支持;据说1919年陈卓仙在蜀中率先截发,竟而惹得“非议蜂起,官禁示”,身为丈夫唐迪风挺身而出,坚决支持妻子的前卫行为,“文喻众,呈惩官,不稍退”[2]7。唐迪风非常爱惜自己的“妻逸”,亲自督导其读书向学,甚至还帮妻子抄书。而妻子也深深理解了丈夫诸多行为背后的苦心,将其内化为自身生命结构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也正是这种深切的理解,在诗人与亡夫之间才能建立一个同位的场域,实现二者充分的交流。“呜呼迪君!素与君心心相印,兹独无感应乎?呜呼迪君!即不能形影相接,希常于魂梦相通。梦中偶见君,忽非可亲之容。岂以我平日好持己见,与君争论,故以此不屑之教诲以教诲我乎!呜呼吾君!平曰启发我者,无所不用其极也。恨我役役终年,不知何者为学,更不知君之所以教。忆君语我有云:学非求功利也,尽其在己而已。我习焉不察,凡所为,莫不与君背驰。及其弊端百出,君反引为己咎,自责其过,而我仍长恶不悛。”[3]297诗人在祭文里解释了自己与丈夫的梦遇是基于心灵的感通,在丈夫的良苦用心面前,诗人是充分理解的,因而诗人才能进入亡夫的内心世界,体验亡夫的心灵世界。也正是深切地体验了亡夫的内心世界之后,诗人才切身感受到了丈夫对自己的一片真心和丈夫在妻子身上所体验到的失落情绪,诗人也因此而感到莫大的内疚和遗恨。
在《昔同游》一诗中,诗人用今昔对比的手法,突出了昔日丈夫健在时自己不能全心学习,而今丈夫亡故,想要请教却已无人可问的内疚和悲痛。在《序言》中,诗人已做了说明:“迪常与余谈论,多属性理。惜余未细心领悟。两年后,触处发现其意,警然契于心,因益伤迪不复起矣。曩即无以告慰,今将奚以为?终成孤陋,而增自哀。”[3]145在诗中,诗人更是将这种内疚和遗憾更为真实、立体地展示出来,“放歌两忘言,悠然天界敞。声挟松风回,宛转应山响。同心极娱乐,事倏成已往。何忍重登临,中心凄以怆。相彼水更清,月亦比前朗。澄澄涵空明,渺不分天壤。神魂若左右,俨然共欣赏。”[3]145在两人构建的“同域”中,天地已浑然一体,即使丈夫人已亡故,诗人却仍觉得他就在自己身旁从未离开,自己的情绪也必然为亡夫所捕获,所以她也不得不控制自己的情绪,以免引起亡夫的伤感。在陈卓仙的悼亡诗中,生与死已经融合为同一世界,她凭借感通沟通了天人,打通了幽明两个世界的界限,实现了万物间完整、全面的交流。
(二)同理与共情:实现“感通”目的的方法和手段
诗人以自我内在的诚挚姿态为实现其沟通天人、连接幽明的目标奠定了基础,那么她在其悼亡诗中是如何具体实现感通,并进而沟通天人、连接幽明的呢?其中就涉及到感通最为重要的心理机制——同理和共情,也就是说,诗人是凭借人类之间的同理心和共情结构达成感通,并进而实现感通的系列目标的。“同理心就是指能够设身处地站在他人的立场上,用他人的价值观去观察和体验其感受并作出判断,自然成为人类所尊崇的共同价值观。”[8]155在同理心的驱动下,个体与他者的关系不再处于萨特“他人即地狱”[9]81式的模态中,人际关系摆脱了“二元对立”的现代模式,回归到人与人之间最为理想的状态。值得注意的是,陈卓仙的“同理心”可能来自于儒家传统的仁义观,与儒家强调的推己及人一脉相承。陈卓仙在她的悼亡诗《杂感二首(其一)》中对此也有所呈现:
惟君多苦心,生而即孤惸。孝慈特兼常,视人皆弟兄。持道正人伦,卓荦穷六经。仁以为己任,学希集大成。行年逾不惑,万里求师正。风云岂不险,洙泗承其清。竟师大嘉许,解颜欢相迎。谓为圣人徒,不图遇于今。虽乏膏火资,长歌金石声。学幻三年归,仍载壁书赓。兴文斥异端,人禽肆力争。终赖固穷节,义利辨益精。卷之藏于密,放之六合盈。宣尼厄陈蔡,而君谁重轻。子路犹愠见,道高终难明。君其何自苦,敦道岂忘形。曲肱固已乐,举世少复诚。幸有二三子,曷若共隐沦。言之不我鄙,挚意加温存。素心两相惬,完质刚坚贞。拳拳漆投胶,馥馥兰扬馨。感结忽伤悲,我悲君泪零。收泪顾言他,故故怡我情。只今一回首,不见君影形。神魂长相依,恐君为不宁。礼佛强自宽,以此酬生平。天乎胡此酷,追念独怦怦。卜葬期何日,泥土应无倾。恨我不得力,莫安君之灵。夙昔委穷达,遑计身枯荣。忧乐以天下,遑顾身后名。理也可奈何,天地终无情。[3]140
诗中大量援引儒家典故以明心志,对儒家经典的娴熟也显示了她的思想源流,她以儒家的性理之学为纲,重新审视动乱年代的人际关系,以期建立一种新的人际关系。诗人不仅把自己的位置置换到丈夫的心灵结构中,还积极吸收了来自丈夫的心灵能量,使得情感能在彼此的心灵世界中自由流动。就这一点而言,陈卓仙又超越了传统推己及人的人际观念,达到了一个更高的高度。而在追忆亡夫时,诗人也总是从往事的细节中提取出生活的光亮,并赋予生活中的人与事以诗意。在细节的摩挲中,体现的是诗人与亡夫心灵的共情。诗人在意丈夫生前的每一个细节,并试图将丈夫生前的回忆完整地保留和还原,也正是这份珍视,体现了诗人的真诚,而这种真诚,也正是共情实现的前提。在彼此坦诚相待的基础之上,心理不设任何防备,情感的共同结构也才得以形成。“共情 (empathy) 是指个体知觉和理解他人的情绪并做出适当反应的能力。”[10]299人类的共情是个体基于与他人进行交互从而不断发展的,也就是说,只有形成交互才能形成共情。在陈卓仙的笔下,这种交互无处的触发点不在,既可能是孩子的病情,也可能是夫妻间的琐事,围绕着这些生活中的“一地鸡毛”,诗人与亡夫形成了生活、文本与心灵空间的三重互动。在这些最为真实的互动中,两人总是为对方考虑,体察对方的情绪,形成了一种交互式的共情。在《忆昔》一诗中,亡夫似乎与天地相知,感应到乱世之悲,而自己也与丈夫心有灵犀,透过丈夫的心灵触碰到时代的棱角,“忆昔伤时语,分明现此时。仁心无隔绝,世乱已先知。天遣斯文丧,每遗君子悲。同情成独慨,何用此生为。”[3]144这中间就涉及到了共情中情感的传递和流通。也正是通过心灵的同理和共情,陈卓仙实现了与天地万物的感通,从而打通了天地、幽明的联系,将自身与世界融合;但同时她又不破坏万物的秩序,而是在尊重世间万物的前提下自由穿梭,通过真挚的情感力量抵达彼岸。
三、由悲悯通向达观:一种悼亡境界的提升
陈卓仙对悼亡诗中的个人性悲伤实施了一种“普遍化”转化,进而将其提升为一种人类间的悲悯之情。面对如此沉重的生命议题,陈卓仙并没有用“逃避”或“隐逸”的方式消解死亡的价值,相反,她站在一个更为广博的位置,从个人性与普遍性的情感中提取出更为一般性的生命本质,体悟到生死之间的相互转化及其辩证联系,从而赋予了生命更为丰富的内在价值。
(一)从悲伤到悲悯
“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11]33。哀悼亡者是悼亡诗主要的情感表现,它寄托了诗人对亡者的诸多情感,表达了诗人面对亡者时内心的复杂感受。相比生命诞生时的喜悦,死亡则意味着一种悲伤情绪的弥散。死亡标志着主体自我的丧失,它反映了自身与此岸世界联系的减弱,也昭示了自我意识的泯灭。对他者,尤其是亡者的亲人而言,死亡意味着一种客观对象的丧失,而这种丧失意味着主体完整性的破坏,为了再度实现自身的完整性,悼亡主体迫切想要找回丧失之物,而丧失之物却已漂流至遥不可及的彼岸,因而悼亡主体只能寻求一种客体的副本以代替丧失之物,从而完成自身心理与人格的平衡。而在追寻客体的过程中,悼亡主体为了实现心理的宣泄,往往会以自我贬低,甚至自虐的方式寻求心理的平衡。在这一过程中,悼亡主体往往表现出诸如沮丧、悲伤、自我评价降低等诸多情绪特征。所以不难发现,悼亡诗的底色是凄凉悲怆的,不仅从悼亡主体的情绪特征中能够发现作为创作主体的悼亡主体的影响,而且从客体丧失这一维度也能发现相关的影响。悼亡主体的眼泪是这种悲伤情绪的凝结之物,它表征了悼亡主体的情绪和心理。在《壬申夏四月二十七日回忆一首》中,诗人“不觉泪已洒”[3]131,但主体的情绪并没有通过满目的眼泪得到释放,悲伤的情绪也没有被幼儿所捕获,因此自己不得不“强与儿游嬉”[3]131,本来已经足够深沉的悲伤仍要抑郁于心,因而伤感愈加深沉。而在《五月十日周年致祭三首》中,诗人已悲伤到了无以复加的地点,心神仿佛出游一般,似乎直接看到了亡夫的身影,“灵右泣所娇,抚慰神若存。啼饥依余怀,恍惚睹君形。”[3]134伤心欲绝之处,诗人内心梗塞,“祭君君不食,哭君君不知”[3]135,仿佛夫君无形中与自己拉开了距离,这更增加了诗人的惆怅。尤其是在今昔的对比之中,这种伤感与惆怅表现得更为突出。“只今一回首,不见君影形”[3]141,昔日君在身侧,两人相依相靠,如今蓦然回首,却连夫君的身影都难以捕捉,这种最低程度的要求在对比中显得格外突出,也从另一个方面衬托了诗人的悲伤情绪。“三年旷游迹,今来夫谁使。望中千万人,独不见之子。”[3]149昔日携手同游,而今独自一人,昔日君在身侧,而今独君不存,两相对比之下,悲慨不言自明。“矫矫比翼鸟,巢居泰华颠。饥食琼树浆,渴饮清冷渊。早出晚来归,双飞影翩翩。量力事颉颃,守辙终余年。严霜虽切肤,体意自便便。谐声天宇阔,丽羽日辉宣。何物兴妖氛,一翼罹其愆。感此崩五内,魂魄共遐迁。”[3]143诗人用拟人的手法描述了丈夫生前夫妻二人的美好生活,同时也隐含了今日丈夫亡故自己独自支持的凄苦和悲凉境遇。“忆昔伤时语,分明现此时。仁心无隔绝,世乱已先知。天遣斯文丧,每遗君子悲。同情成独慨,何用此生为。”[3]143诗人采用明暗两种对比手法,追忆昔日生活之惬意即意味着对当下生活的一种反思和厌弃,但诗人却并不直接点明,而是由读者加以想象、补充。这也从另一个更为现实的角度表明,诗人的悲伤不仅是丈夫的去世所造成的,还有许多现实存在的问题困扰着诗人,也正是这些生活中必须一一处理的现实问题,加深了诗人的悲痛。尤其是当诗人看见那些与亡夫相关的事物时,心中刚要平静的伤痕又隐隐作痛。“手置衣与衾,一著一心酸。娇儿解我意,母暖父心安。”[3]147当诗人拿起针线,编织衣服时,不禁勾起诗人的心结,而这些类似的事物与场景竟是如此之多,以至于诗人根本无从躲避,内心的悲楚总被时刻刺醒,以致身心两疲。
除此之外,诗人还经常从孩子的视角和维度表达这种悲伤的情绪。而这一视角和维度的好处在于:第一,孩子作为弱者,尤其是失去父亲的孩子,是值得所有人同情的对象,因而从孩子的视角出发无疑会增加叙述的情感力量,博得更多的理解和认同;第二,孩子作为父母的结晶,是联系父母的情感纽带,但孩子又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因而是作为一种客观力量而存在的,当诗人以孩子的视角介入时,无疑会产生一种客观的效果和力量,因此其言说也更有说服力;第三,孩子具有一种天生的灵性与敏感,对世间万物的感知是最为敏捷的,因此从孩子的视角去表达情感,显得更为直捷、真实;最后,孩子是无知的,也是无辜的,也唯有无知才是客观的,因为无知即为虚空,摒弃了一切价值判断,借由这种无知,情感的客观性得以增强。比如《幼女三首》就是从孩子的视角出发的:
夕阳斜射池塘里,挟策归途独延伫。
夜梦呼爷泪湿衣,朝来窃向阿兄语。
(其一)
偶市樱桃不忍食,趋庭供奉父灵侧。
萧萧风过幕帏开,背立中堂频掩泣。
(其二)
儿哭父兮母泪收,父思儿兮谁解愁。
惄如捣兮我心忧,宛在望兮天尽头。[3]152
(其三)
三首诗都写幼女宁孺思念父亲的情状,“其或独立路边,等候下学之兄姊;或夜梦广父,醒来向哥哥悄语。或购买樱桃而不忍自食,已经懂得供奉父灵。背立中堂泪眼婆娑者当不止小女一人。至此诗人笔锋一转,则谓亡人念子之苦何以告慰。此种背而傅粉之法,极富表现力。诗不自言其思夫,而情实自见”[3]153。诗人表面是写子女对父亲的思念(当然,这种思念是真实的),实际上却是写诗人对亡夫的思念,而念久之不得,愁苦抑郁于心,心中思念自然转为无可排遣的悲痛了。“伤哉无父儿,相依怯离去。哀哀相背泣,切切相宽语。聊以托性命,含悲终年暮。悠悠者苍天,夺我平生故。”[3]138失去父亲的子女与失去丈夫的妻子同样悲惨,因此二者也就具有了身世的类似性,自然产生同病相怜的感觉,因而诗人不仅是从母性的角度去写子女的悲伤,更是从同病相怜的角度抒写了这种悲伤的共同性,使这种悲伤上升为一种具有普遍性质的情感。
(二)通向达观
陈卓仙的独特之处在于,她不仅将具有个人性质的悼亡诗写得悲切而真实,还把这种个人性的情感贯穿到时代的巨变中,从个人细腻的情感延伸至世间万物的广博,从个人性的悲伤抵达对人世间的悲悯,在获得了更为宏阔的观察视角后,这种深广的悲悯也借由宇宙和世间万物的力量转化为超脱的力量,而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无疑是儒家的性理之学与佛道的通达之理。经由儒家的性理之学,陈卓仙在其悼亡诗中能够潜入现实,发掘出其中深广的悲悯力量;而经由佛道的通达之理,陈卓仙又能从悲伤中跳脱出来,从更为广阔的视角面对死亡,因而态度也就变得更为超然。诗人通过感通把世间万物结为一体,在面对自身丧夫之痛时,诗人也会将这种疼痛的心理体验推广到他者身上,因而能有更为完整的感同身受。虽然他人所经历的未必如自己所经历的一样,但其情感的内在逻辑却是相同的,所以诗人能够通过自己的个人之痛体察人世的悲痛。尤其是在动乱的时代,这种同感就具有了更大的可能性,而当诗人把自身的疼痛经验用于体察他者之痛时,就溢出了诗人界定的家庭关系,从而进入到一个更为复杂的社会系统内,诗人对亡夫、家庭的关怀就拓展至整个人类世界,而他的悼亡诗也因此具有了更为深广的悲悯力量。在《杂感二首》中,诗人虽遭丈夫亡故之痛,却毫不抱怨,仍然自勉自强,这是因为她从个人的悲痛中获得了一种群体性力量,当个体与他人的人生遭际相遇时,纵是不同的人生样式,却也会在共同结构中得到感发,获得力量。在《壬申夏四月二十七日回忆一首》中,诗人字字白描而句句情语,悲痛至极,然而这种悲痛却绝不是诗人一人独有,世间还有成千上万个悲剧在同时上演,因而诗人又将这种悲痛化为人世间的一种悲悯,自己所承受的痛苦也无非是世人已经或正在承受的万千痛苦中的一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宿命,每一个个体都有自己必须承受的“生命不可承受之重”[12]202。在体悟到自身与世间万物的关系之后,诗人便把自身纳入到宇宙的秩序之中,从更为广博的视角去审察自身以及世间万物所经历的悲痛,才发现自己只不过是天地间的沧海一粟,而这些个体的悲痛也就逐渐失去了主观渲染的疼痛效果,情绪也得到了平复和超越。如《遣悲怀》一诗:
天地生万物,各遂其常理。雨露滋芳华,风雷厉柔靡。仁人赞化育,立德修文纪。而曰仁者寿,胡不保之子。岂伊凤不至,于何伤麟死。世方逐横流,滔滔者皆是。悬景自孤光,天风无定止。躬欲使其淳,人斯谁与己。惟感平生言,惧同草木毁。朝获闻大道,夕死斯可矣。泰山竟尔颓,吾其奚仰止。同穴知何年,永痛无穷已。正声久不闻,悲歌犹在耳。即命救人间,夫何充天使。世诚不可为,宁灭先圣轨。圣轨固昭彰,子去谁率履。形骸虽幻化,精诚实相契。待当休明世,吾子复兴起。 至人值嘉会,驾言心转喜。全家欢重聚,情钟良足恃。吾子居何方?安得以语此。哀思如循环,天应成人美。[3]139
诗人站在更高的角度,从宇宙万物中观察自身的悲痛,也就获得了对自身状况更为客观的认识,尽管这些悲痛对于自己的人生非常重要,但在宇宙万物间又算得了什么呢?与其悲悲戚戚寻死觅活,不如重整河山继续生活,殊不知对亡者最好的安慰便是把生活的秩序与边疆整顿得完好如初。因而诗人也就不局限于个人的狭小视角,而是把自身置于更为广阔的世界,从而获得一种超脱和解放。这种超脱和解放固然受了佛道思想的影响,但不可忽略的是,陈卓仙的超越是在经历了人生的大悲大痛之后才有所顿悟的,而且这种超脱也是置于人类整体的视野之上才产生的一种结果,所以陈卓仙的诗骨里仍然潜藏着那些深刻的悲天悯人,她对现实的关切并没有因此走远。
四、结语
陈卓仙的诗学观念和人生追求都深受丈夫唐迪风的影响,在她的悼亡诗中,经由细节的考察,不难发现诗人对以性理之学为核心的儒家理想的孜孜追求。尤其是性理之学中的感通,几乎成了诗人沟通天人、连接幽明的妙法,其真挚、诚恳的情感和姿态是不难体察到的。也正是因为感通的贯通作用,诗人得以理解亡夫,也得以理解自身,心中的凄凉悲怆难以抑制,便发而为歌。更为难得的一点是,诗人并没有沉浸于个人的情感世界之中,而是经由感通将这种悲痛的情感拓展为对全体人类的悲悯之情,并从一个更为广博的视野超越了人类的悲哀情绪,实现了情感的自由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