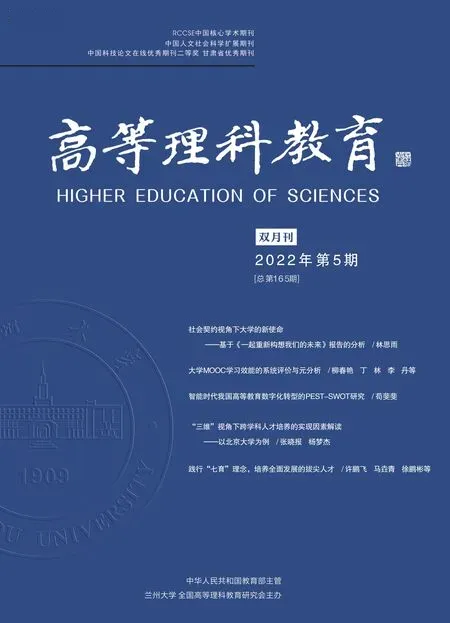英才之用
邬大光
二十大报告中,“中国式现代化”是最重要的关键词,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教育的支撑,“中国式教育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基。早在一百多年前,黄炎培赴南洋考察教育时曾说,“今后世界,兵战乎、商战乎、皆学战耳。欧战之结局,将使科学价值益高,而视教育益重。”此处的“学战”就是教育之战。我们目前面临的国际局势如中美贸易战亦是同理,表面上看是中美之间的经济较量,其背后是一种更深层次的较量,是科技水平的较量、人才素养的较量、创新能力的较量。我国在中美贸易战中所遭遇的一系列“卡脖子”阵痛,止痛的出路在于提高教育和人才的竞争力,尤其是高等教育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支撑能力。
早期东西方对教育的理解均置于个体价值和知识价值层面进行讨论。西方认为“知识就是力量”,东方认为“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苏联卫星上天之后,美国的《国防教育法》第一次把教育上升到了“国防”的高度,“社会进步是站在大学的肩膀上”,这一新认识赋予了高等教育更深刻的涵义。
教育首先面对的是作为个体的人,教育与个人的命运息息相关,教育改变命运是对教育价值的认可。但社会发展到今天,教育也与国家的发展休戚与共。个人以“知识改变命运”为动力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既赋予了教育对人的发展价值,与此同时,将国家的发展寄希望于教育,也是教育的重要性使然,即教育也可以改变国家命运。
此次二十大再次把“科教战略”单列为国家战略,提出了“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更加强调教育与人才的社会之用与国家之用,这既是对古代“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化用,也说明今天我们迫切需要将选才与用才作为国家昌盛、人民安乐的重要条件。如王安石论材:“材之用,国之栋梁也,得之则安以荣,失之则亡以辱”;欧阳修有言:“才者不用,用者不才”。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我国在人才培养方面已经累积了一定基础,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但是,人才培养的质量却并不“拔尖”。另一方面,国际间的人才流动,我国长期处于“顺差”阶段。这说明人才对科技强国的“支撑”能力还有待提高,对人才的吸引能力还有待提高,对人才的使用能力更有待提高。
“人才支撑”是二十大报告中另一个教育关键词。报告明确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现代语境中,“支撑”有支持与服务之意,一是如何为人才提供支持与服务,二是人才如何为国家发展提供支持与服务,即解决“为谁培养人”的命题。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人力资源面临新的挑战。当前我国人才培养的核心问题,早已不限于数量,也不完全止于质量,根本问题是要解决高等教育所“育”之才与所“需”之才之间的适配度,用好人才这个第一资源。“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目的是为了培养人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目的是为了支持国家现代化建设,“育”与“用”是发挥英才“支撑”之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呼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