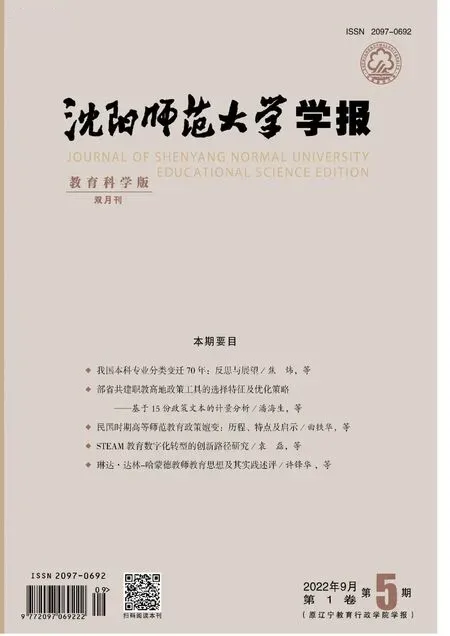教育如何以人为本:一种人学视角的追问
李枭鹰,郭新伟
(大连理工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院,辽宁 大连 116024)
教育“从人而来,向人而去,与人同转”[1],无论时空如何更替,这一点永存不变。因此,教育不能“人空场”。这不仅意味着“教育为何要以人为本”[1]并非一个毋庸赘述的问题,也意味着从人学视角来追问“教育如何以人为本”是一种务本的追问、必需的追问、终极的追问。教育当以人为出发点、轴心和归宿,以自我塑造、谋求幸福、丰实灵魂、升华境界、延拓生命为责任、使命、目标、承诺和担当。
一、指引学生自我塑造
教育根本上是人的一种社会实践,为了培养人、发展人、塑造人,以及释放人自我塑造的潜质和能力。从张楚廷先生关于“人本教育思想”[2]的主张来看,“为了人”的教育过程可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教育“让人像人”,即帮助人实现从“自然人”到“社会人”的转变,使人从一个“自然实体”成长为一个“社会实体”,使人具备基本的认知能力和必要的赖以支撑认知、形成和发展素质的非认知能力,这是人之所以为人而非动物的重要“分水岭”;二是教育“让人更像人”,即让一个个活生生的“社会人”或“社会实体”变得更有知识、更有能力、更有智慧、更有思想、更有格局、更有高度、更有视野、更有境界,完成一系列“更”的升华和超越,从一种粗糙的、单调的、低水平的生命状态,跃迁和进化至一种更精致、更丰实、更高层次的生命状态。在“为了人”的教育过程中,外在力量固然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否则受教育者会四处碰壁却不得要领。然而亦要看到,培养人、发展人、塑造人表现为手段与目的的统一,在短时间内是目的,而长久来说,皆是人自我塑造的手段。无论是教育“让人像人”还是教育“让人更像人”,二者的实现及其带来的教育之世代延续和生生不息,都扎根于教育的过程,这个可看作人通过“自反”来实现“自增”的过程,亦即受教育者自我塑造的过程。
人的自反性和自增性肯定个体天赋潜能的存在,同时指明通过教育途径开发天赋潜能和实现自我塑造的基本理路。具言之,人都是在外力的助推下自我生长、自我完善和自我超越的,任何人都不能代替别人去完成这些活动。在教育中,学生并不是教育影响的被动接收者或消极承受者,之所以时常称之“受教育者”,乃是出于同“教育者”的指称对应的考虑。相反,他们必须自己去“解构”、自己去“建构”,在解构与建构的超循环中实现螺旋式发展,完成从“像人”到“更像人”的飞跃,在“成人”的基础上追寻“成完人”“成大才”等更高层次的目标。在真善美的价值规约下,每个学生都可以且应当遵从自身的天赋潜能,成长为其所希望的样子,形成和发展独立的自我、真实的自我,成为“本人”而非“他人”,成为真人而非“假面之人”,尽显个性化的迷人光彩。当然,这一切必须在“成事”中完成,因为人只能在成事中获得成长;在成事中,成己、成人和成才方有所凭、有所依、有所靠。
学生好比一粒蕴含无限潜能的种子,而教师乃至教育要做的是为之提供阳光、水分、温度、土壤等适宜生长的条件,使之长成参天大树并结出累累硕果。这意味着教师与学生的双重解放;意味着教育要将自主探索的选择权重新交付给学生;意味着教师只是“领进门”,而学生“修行在个人”;意味着师生之间要建立起一种平等的对话与沟通关系,教师不能异化为工匠,学生也不能异化为被雕刻的原材料。在实现受教育者自我塑造的教育中,学校也要摆正定位。一方面,学校为学生的成长和自我塑造创建平台,为他们自主选择、自由思考、自觉探求、自我决断及独立地反思、质疑和批判创造环境,而非千方百计地提供现成的知识、完整的知识,或者将大部分的教育时间单一地困守课堂之上、囿于教师的学术领地之中,让学生按照预设好的轨道一路前行。这种预设性的教育面向的是学生整体而非个体,容易带来整齐划一、千人一面的消极结果,将教育异化为一种模式化、技术化、程序化、量产式的流水作业,使本应该与众不同、丰富多彩的人生简化和扭曲为“轨道式人生”。另一方面,学校亦非血淋淋或冷冰冰的“规训场”,必须使学生远离权力的控制和监视。为此,学校要禁止权力以“伪善面孔”隐藏在任何一个角落,杜绝权力以形形色色的样态被教师操持和把玩而攻向任何一名学生。工业化的教育、冰冷的制度安排,只会泯灭学生的个性、扼杀学生的自由、戕害学生的天赋,导致教育失去育人之真、公正之善、和谐之美。
二、成就学生谋求幸福
教育以获得幸福为主要目的。19世纪俄国教育家乌申斯基就曾说过:“教育的主要目的在于使学生获得幸福,不能为任何不相干的利益而牺牲这种幸福,这一点当然是毋庸置疑的。”[3]213在今天,一方面,为了幸福的教育依旧是理论界历经岁月荡涤而传之不朽的声音,正如有学者所言,“从最美好和最深刻的意义上说,所有的教育都应当是幸福教育”[4]。教育理当指向人的幸福,也必须为人谋幸福。一切以牺牲人的幸福为代价的教育都是彻头彻尾失败的教育,无论它给予人多少知识或技能。另一方面,现实中的教育却被不同程度地演变为一份“苦差”。很多时候,这样的教育非但对提高学生的幸福感鲜有裨益,甚至还生出许多“副作用”,有损学生的健康,残害学生的心灵。这之下隐藏着价值观念的偏颇和背离。正如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所指出的那样,当今“价值序列最为深刻的转化是生命价值隶属于有用价值”[5]141。这并非一种健康的、合理的、正义的转化,教育不可“同流合污”,而须纠正这一谬见。站在生命价值的高度,教育绝不能“幸福空场”,幸福空场的教育一定不是好的教育;站在生命价值的高度,教育要全面服务于人的幸福、着力于拓宽人的幸福道路、提升人的幸福品位、延长人的幸福生命。
人的幸福有理性幸福和感性幸福之分,二者既有区别又存在联系、相互对立又辩证统一,这源自人本身既是理性的又是感性的。理性幸福和感性幸福的来源渠道不尽相同,各自需要付出的努力和汗水也存在差异。相比之下,前者要比后者艰辛和复杂得多。细言之,人的理性幸福主要孕生于人的完美性与达到它的可能性之间距离的缩短,孕生于人之生命的整体、人之精神世界的丰实及人之理性价值的实现,孕生于自我的觉醒、依赖性的减退、审美能力的递增、本质力量的释放。“大多数人的所作所为,以及对逆境的忍受,背后秘而不宣的动机其实都是为了获取幸福、保有幸福、找回幸福”[6]66,这里所体现的即为理性幸福。某学生为了“拿下”即将到来的考试,“忍痛割爱”,挥别费时而无用的娱乐,最终斩获傲人成绩,由此带来的满足和欣喜同样是理性幸福的例证。感性幸福则主要孕生于可见的、可感的直接刺激及生理和心理的快感,而非灵魂的丰实、价值的实现、信仰的尊重。如饥肠辘辘之人突获一块面包,栉风沐雨之人来到一处屋檐,阔别故乡的游子归来时的喜悦,久经阴霾的天空乍晴时的明朗,以及物质或言语的奖励带给人的直接慰藉等。理性幸福不否定感性幸福,二者并不矛盾、冲突,反而内在统一、相得益彰。无数的人生体验告诉我们:象征感性的激情一旦衰减或退去,理性的动力将随之弱化或萎靡;理性一旦缺失,感性也会信马由缰而迷失方向。为此,教育在鼓励和引导学生追寻理性幸福的同时,切不可无睹甚至打压感性幸福的激发与催化作用,而要使学生从理性和感性两个维度都能体会幸福。一方面,学生自当发展扎实的学术能力,产出丰硕的学术成果,但背后不能是巨大的“生命阴影”或“快乐缺失”,应是灿烂的阳光和漫溢的幸福。幸福源自真实的生活世界,而生活世界绝不是纯粹理性主义的,因为纯粹的理性主义违背人性的完整性,是桎梏人的巨大“囚笼”,由其支配的教育必是一种异己力量,只能造就畸形的个体。另一方面,幸福不等于轻松或休闲,教育也绝非越感性越幸福,简单的轻松愉快带来的幸福是肤浅的幸福、消磨意志的幸福,以及可能让人丢掉大好前程或发展空间的幸福。教育要让学生学会拒斥当下之安逸或快乐的诱惑,教会学生通过付出劳动和智慧抵达幸福的彼岸。
幸福既是教育的永恒主题,也是教育理论研究的永恒主题。我们需要在教育系统之中,遵循教育的一般规律并吸收一切有价值的教育理论或教育思想的营养,譬如生命教育、生活教育、情感教育、快乐教育、闲暇教育、通识教育、赏识教育、超越教育等。它们立足于不同的角度或视域,从不同的维度洞见人的自然性、社会性、生成性、存在性、实践性和整全性等特征,隐藏着通往幸福的教育路径。教育可以从中探寻幸福生发的理论依据,探索“幸福空场”的规避策略。
三、唤醒学生丰实灵魂
人有思想、有灵魂,而人的思想和灵魂源自教育。教育是一项灵魂工程,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言,“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智和认识的堆集”[7]4。这是教育的本质和真谛。人不能没有灵魂,教育不能缺少灵魂,学校也不能追求那种“失去灵魂的卓越”。从某种程度上说,“学生”只是一个称呼或名字——那些接受正式教育的人所共享的一个称呼或名字,它本身是符号的、抽象的和空洞的,若不填充名副其实的灵魂,则无异于“空空的皮囊”。灵魂的核心是内涵,亦即内在涵养。从此意义上看,丰富和充实灵魂亦即发展个体的内在涵养。
长期以来,教育界存在一种“唯智主义”,亦即唯知识、唯理性至上,似乎除了这二者,教育别无其他。固然,人类在历史长河中创造了许多不可磨灭的美好事物,熟知、洞悉乃至记忆这些事物是每个人最重要、最基本的内涵,但这并非内涵的全部。人的内涵是一种综合性、系统性的内在涵养,这意味着教育必须塑造“完人”或“整全之人”。由此,单纯的知识教育或专业教育是不完整的,只会造就擅长考试的“伪人才”和某一领域的专才或某类人才。钱穆先生曾经有言,仅仅注重“智识之传授”的教育只能培养出“不通之愚人”[8]。怀特海也指出:“我们的目标是,要塑造既有广泛的文化修养又在某个特殊方面有专业知识的人才,他们的专业知识可以给他们进步、腾飞的基础,而他们所具有的广泛的文化,使他们有哲学般深邃,又如艺术般高雅。”[9]1爱因斯坦于1952年应《纽约时报》教育编辑请求而写的一份声明亦曾告诫我们:“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学生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社会伦理、准则)有所理解并产生热烈感情,那是最基本的。他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上的善有鲜明的辨别力。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更像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10]310
反观当前教育,中小学阶段“唯分数”“唯排名”“唯升学率”的“三唯”势头仍在不同地区不同程度地上演。虽然素质教育的呼声已经响彻多时,但是流于形式、只做“表面文章”的现象屡见不鲜,这更为应试教育提供了可乘之机,致使素质教育名亡实存。大学中,专业教育“特立独行”的惯性也相当程度地被保持着,专业化、技术化、模式化、功利化的倾向尚未得到修正,专业知识的灌输和专业能力的培养始终占据不可撼动的至尊地位。相比之下,通识教育及其课程的开设仅是辅助或补充。事实表明,这种“生产流水线式”的教育或经由裁剪的教育,一方面造就了大批高层次专业人才,以及在考试中“游刃有余”、善于“披荆斩棘”的“学霸”;另一方面也“产出”了不少“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或者灵魂贫瘠的“机器人”。人是一种整全性存在,是一种集合自然性与社会性、肉体与灵魂、感性与理性、情欲与理智等多重矛盾关系的统一体。教育理当尊重、呵护、捍卫人的整体性、统一性和辩证性,否则人就不能被称为完全意义上的人。尤其是灵魂的贫瘠或缺失,关系到人的失落、瓦解,以及整全性、统一性的破坏。没有灵魂的躯体无异于行尸走肉。
学生灵魂的填充和丰实是多入口和多途径的,而有些入口或途径尤为重要和关键。目前来看,最需要重视的是师生之间的平等对话与沟通,即师生需要从单向的“独白式说教”步入双向的“对话式交流”,邀请对方走进自己的内心世界和灵魂深处。诚如此,将意味着“学生的教师”或“教师的学生”成为历史,取而代之的是“学生式教师”或“教师式学生”,即“通过对话,学生的老师和老师的学生之类的概念不复存在,一个新名词产生了,即作为老师的学生或作为学生的老师。在对话过程中,教师的身份持续发生变化,时而作为一个教师,时而成为一个与学生一样聆听教诲的求知者,学生也是如此。他们共同对求知过程负责”[11]80。教育从“单向度理性塑造人”转向“双向互动实践生成人”,让学生在师生平等对话与沟通中生成自我,在自主行动与探索中创造自我。
总而言之,教育并不只是单纯的知识或专业教育,灵魂的塑造也绝非僵硬的说教和听从能够实现的。教育必须以丰富人的生活世界和生存本真为根,在师生的双向奔赴中走出外在化和空心化的窠臼。强行“灌注”的专业教育或知识技能教育只能给学生体内装上一堆没有温度的“知识石块”,而且彼此之间常缺乏关联,不仅于灵魂和涵养无益,还会导致学生无法学以致用。
四、照亮学生升华境界
境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无事不在。大境界惠泽整个人生,不仅关乎个人的快乐和幸福,也关系到周遭人的快乐和幸福。大境界是一种觉悟和修为,也是一种正能量和积极力。自古以来,有思想、有能力、有作为者不乏其人,然而有大境界者寥若晨星。
人要有境界,每个人当为有境界之人。人生之路漫漫且瞬息万变,绝非一条行云流水的坦途。在人生这条路上,每个人难免会遇到林林总总的拐点和岔路,踏上形形色色的征程和路途。这些路有时直,有时弯;有时宽,有时窄;有时顺畅,有时受阻。人有时走在林荫大道上,有时步入田间小径,有时踏上崎岖山路,有时又会误入那泥泞不堪、步履艰难的穷途和险途……而且,何时启程又何时结束,往往非人力所能完全掌控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就无可作为,只要有“长风破浪、直挂云帆”的勇气和魄力、“一路风景一路歌”的安之若素和处变不惊,林荫大道和田间小径自有它的春阳如沐、微风习习,而崎岖山路甚至所谓的“穷途末路”也可能“峰回路转”,在“山重水复”中邂逅“柳暗花明”。如果我们理解生命的意义、悟得生命的真谛,歧路也有别样的收获与光景。无论走在什么样的路上,学会体验、品尝、欣赏和享受才是“真理”:在直时体悟直,在弯时欣赏弯;在宽时感受宽,在窄时体验窄;在受阻时经受逆境的洗礼,在顺畅时享受遂愿的幸福。正如赫拉克利特在论证辩证法时所言:“结合物是既完整又不完整,既协调又不协调,既和谐又不和谐,从一切产生出一,从一产生出一切。”[12]23-24面对生活世界,我们应当把完整与不完整、协调与不协调、和谐与不和谐等相反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使不同的音调合奏出最美、最和谐的旋律。这就是境界,教育理当为之开道、铺路和奠基。
蒙培元曾言:“中国传统哲学都是人生境界之学。”[13]23在此背景下,我们需要借鉴其中的优秀思想,返本开新,为新时代的“境界教育”提供养料。尤需指出的是冯友兰的“四境界说”(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分别从生物本能、物质利己、社会利他、宇宙觉解的范畴理解和探求人生的意义与价值。虽然有学者认为该理论存在“根本性迷失”,即“由于主观觉解支撑起的境界实质上只是一种虚无的心灵体验,从而造成了主体内在精神境界与客观人生实践的脱节;由于对理、道体及宇宙等范畴中人性道德内涵的彻底抽空,又导致了其本体与境界的完全断裂”[14],但不能否认,该理论对于形塑当代人的心灵境界仍有不容小觑的指导价值。置于当代语境下,胸怀、责任感和使命感当属境界的要义,也是孕生境界的土壤,甚至与境界具有“同质性”和“同构性”。其中,胸怀与具有宇宙人生觉解、自诩“宇宙一分子”的天地境界相通,责任感和使命感则内含社会性和利他性的道德意味。三者都有层次之分,大胸怀、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是大境界。对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的《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指出:“教育必须教导人们学会如何在承受压力的地球上生活;教育必须重视文化素养,立足于尊重和尊严平等,有助于将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方面结为一体”“促进正义、社会公平和全球团结”[15]3。这无疑是对“何为大胸怀、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的诠释,暗含服务“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大境界。
五、点燃学生延拓生命
人是自然的存在,也是超自然的存在,还是生命长度与厚度相统一的整体性存在。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但并非只有一种。有人将生命划分为自在生命和自为生命[16];有人则将生命划分为自然生命、精神生命、价值生命和智慧生命[17]71;还有人将生命划分为肉体生命、精神生命和社会生命[18]。
延拓生命是每个人的夙愿。生命之长并非长寿,延拓生命也并非延拓寿命,意义才是生命的底蕴。人的一生是一种成人的过程、一种生命绽放的过程、一种实现人生价值的过程。人的生命意义正是源自这种“成人、生命绽放和人生价值”的实现,这也是生命延拓的要义。学生是一个发展中的人,一个完整的、具有独立意义且尚未完全长成的人,更需要通过教育使其向着未来延长与拓展生命,敞开解构与建构自我,不断实现自身的意义与价值。
生命的延拓要求每个人都要遵从自己的内心,活出个性、底色和精彩,否则全人类的解放、自由和幸福就是一句空话。世界万物都是个性化的,世界也因为万物的个性化而多姿多彩,因为万物的多姿多彩而魅力无穷。自然世界是多样化的,人类社会也需要多样化,人类社会的多样化又根源于人的个性化。为了实现人的个性化,教育不能是产品加工,不能按照固定的模具进行批量生产,而要遵从每个人的天赋塑造不一样的人才。学校或教师一厢情愿设计的“轨道式教育”,在根本上无视了学生的天赋,这无异于“让鱼高飞、让鹰凫水”。教育要让学生成为自己,学生也要允许自己成为自己。人只有成为自己,而非任何“第二个谁”,才能活出风格、活出优雅、活出美丽、活出价值。我们反对学生的同质化和去个性化,而主张尊重每一位学生的兴趣和爱好,发现和释放每一位学生的天赋和潜能,创造最佳的教育环境让学生在自己最感兴趣和最有天赋的领域或方面充分发展。
生命的延拓意味着“生命之花”的现实绽放。存在主义认为“存在先于本质”,生命在体验中绽放,人生意义在体验中彰显。换言之,生命质量的滋养、生活意义的获得,只有回归“现实生活世界”才能实现,只有建构“可能的生活世界”才能达成。每个人的生命意义与价值、生命灵动与创造,都是在“认识你自己”中孕育和生成、在社会实践中彰显和释放的。每个人都在现实社会中定型,在现实社会中实现社会化。整个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每个人都是在社会关系中实现生命的绽放的。对此,西班牙大提琴家、指挥家帕布罗·卡萨尔斯(Pablo Casals)有言:“我们应将全人类视为一棵树,而我们自己就是一片树叶。离开这棵树,离开他人,我们无法生存。”[15]12从该意义上看,没有“我们的意义与价值”就没有“我的意义与价值”,“我的意义与价值”存在于“我们的意义与价值”之中。“认识我自己”必须先认识“我们”,而“认识你自己”也要先了解“你们”。当然,“我”与“我们”是相互消解的,一个个“我”的离去消解了“我们”,而“我们”的存在又消解着一个个的“我”;“你”与“你们”也是相互消解的,一个个“你”的离去消解了“你们”,“你们”的存在又消解着一个个的“你”。可见,生命的意义与价值是综合性、整体性、系统性和整生性的,人与人相互联结在一起,成就各自的意义与价值。
教育即生活,生活即体验,体验即教育。教育不只是求知,也不只是“为求知而求知”。教育不只是在知识的海洋里畅游、在知识的森林中漫步、在知识的太空中翱翔,还求真、求善、求美、求益和求宜。教育是可见、可感、可悟的真实生活,是尚个性和尊自由的自主生活,是注视当下和观照未来的此刻生活,是意义与价值齐头并进的整体生活。学生是活的存在,只有在生活世界才能感知自己,也才能活出意义与价值。教育不能牺牲当下的生活来换取未来的生活,不能牺牲今天的幸福来换取明天的幸福。受教育不只是为了获取一张“学历文凭”,也不只是为了谋求一张特殊的“营业执照”,而是出于增长自身的知识、发展自身能力和提升自身的素养的需要,为了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为了自由地生活在真实世界里。总之,教育理当是一种真实生活,一切学子都理当回到真实的生活世界中去珍惜、呵护、尊重、享受、升华自己的生活,在真实生活中从经验世界走向理性世界,从现象世界走向本质世界,从有形世界走向无形世界,从必然世界走向自由世界;在真实生活中品尝教育的全过程,体验人生的每一次“再出发”。
六、结语
“教育如何以人为本”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即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时空背景下也会给出不一样的答案。这个问题源于“人到底该如何发展”和“社会究竟需要怎样的人”。其中,“人到底该如何发展”是根本的,但要受到“社会究竟需要怎样的人”的影响;“社会究竟需要怎样的人”是重要的,却要受到“人到底该如何发展”的规约。与此对应,教育既要适应人的全面发展需要,也要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这是追问“教育如何以人为本”的基调。
一切教育皆是特定时空下的教育,我们需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地对“教育如何以人为本”作出认识与行动上的抉择。从人学视角来看,我们需要自我塑造的教育、谋求幸福的教育、丰实灵魂的教育、升华境界的教育、延拓生命的教育。毫无疑问,这只是基于当前的某些教育缺失且从人学视角对理想教育的“一种追问”,并未囊括教育的所有“应然态”,也并不意味着全盘否定当前教育的所有“实然态”。譬如,在肯定和强调自我塑造的同时,来自教师、学校、家长等外力的塑造同样不可或缺;在强化通识教育、情感教育、快乐教育、幸福教育等教育理论或思想的同时,也并不否定知识、技能的授受和练习。无论在任何阶段,知识、技能等的教育都是必不可少的。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语境下,我们所批判和摒弃的绝不是知识或技能,而是“唯知识”“唯技能”的极端化。另外,正如自我塑造、谋求幸福、丰实灵魂、升华境界和延拓生命的教育并不代表人本教育的全部要义一样,从人学的视角来理解教育可能是最务本的视角、最必需的视角、最终极的视角,但也绝非唯一的视角或唯一切口。教育的内外部关系规律提醒我们,教育不仅关乎人的发展,而且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归根结底,教育所培养的人都必须是“社会人”,社会是影响教育如何作为的重要标尺。鉴于此,从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视角来理解教育,同样不失为应有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