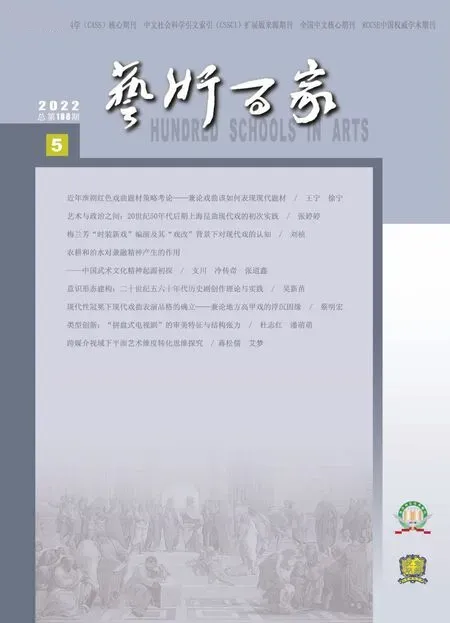意识形态建构: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历史剧创作理论与实践∗
吴新苗
(中国戏曲学院 戏曲研究所,北京 100073)
“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1]663-664,毛泽东对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深入而辩证的阐述,深刻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文化艺术工作的实践。 戏曲作为当时最受大众欢迎的传统艺术,同样被纳入新政权的意识形态建构工作,接受改造和重塑,新编戏曲的创作,更是受到这一原则的制约。 相较于和现实有着天然联系的现代戏,新编历史剧如何通过历史题材内容体现出“新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成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历史剧创作实践和理论批评的核心话题,时人见仁见智,有各种尝试,也有很多争论。 本文即以此为视角,既讨论历史剧在意识形态建构方面的具体表现,又揭示历史剧因此遭遇的问题。
一、从“反历史主义”谈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戏曲创作中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即“当处理历史题材和古代民间传说的时候,把许多只能产生于一定的历史条件中的人物和事件,拉扯到现代来,加以牵强附会的比拟,或是把只能产生于今天的观念和感情,勉强安放到古代人物的身上去”[2]。 例如:《玉堂春》中的苏三最后闹起了革命;许仙参加起义军并杀死法海,带领白娘子一起上山落草;郑里(真理)老人教牛郎织女劳动,宣传劳动创造世界。 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这种现象被称为“反历史主义”。
其实,这种情况之前就已经存在,只是在20 世纪50 年代初表现得更为集中,杨绍萱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代表。 他在1950 年至1951 年期间陆续创作了《新天河配》《新大名府》《新白兔记》《愚公移山》等多部新编历史剧、神话剧,在这些作品中,他不仅大搞鸽子象征和平、鸱鸮象征美帝国主义等种种影射,还在《水浒传》《白兔记》等传统故事中加入不符合史实的民族战争内容,以及妇女解放、统一战线等现代思想意识。 杨绍萱时任文化部戏改局副局长,是戏改的主要领导者之一,在业界具有很大影响力,因此他作为“反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受到艾青、何其芳、光未然、阿甲等人的猛烈批评。 以最基本的文学常识看来,“反历史主义”这种混淆古今的创作显得非常幼稚可笑,实在不值一批。 但吊诡的是,杨绍萱在受到批评后反而理直气壮地坚持己见。 艾青的批评文章被刊登在《人民日报》上,杨绍萱给该报连写三封信进行质问,并发表《论“为文学而文学、为艺术而艺术”的危害性——评艾青的〈谈“牛郎织女”〉》为自己辩护,这引来了更多的批评。 《人民日报》的一篇综述中说,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收到了批评杨绍萱的“来稿、来信二百七十三件”①。 “反历史主义”成为众矢之的,杨绍萱被罢免职务,逐出了戏改领导层。
杨绍萱那些为自己辩解的文字,并非完全意气用事,而是相当清晰地折射出当时新意识形态的巨大威力。 “现在要依据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来处理我们的历史剧,从内容到形式,就应以反映中国社会发展史为主要任务”[3]41,杨绍萱将反映中国社会发展史作为历史剧创作的主要任务,这与新政权成立伊始普遍展开的政治学习是一致的。 当时,政府通过各种报刊、书籍、宣传标语和学习班,在全社会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而其中最关键的是关于社会发展史的学习。 艾思奇在一篇谈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的文章里指出,“只求经过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主义的学习中,较有系统地建立起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1)劳动创造世界的思想;(2)阶级斗争的思想;(3)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 掌握了这些基本的观点,许多不了解和想不通的问题就往往能够自己迎刃而解。由此进一步,不论是参加工作,或继续更深入的学习,都有很大的便利”[4]35。 在全国各地举行的艺人讲习班中,社会发展史是一门必开的课程,讲授关于劳动、阶级、国家等历史唯物主义知识。 杨绍萱将历史剧创作完全当作了一次次社会发展史的课堂教学,当作了对现实中民族战争和阶级斗争进行宣讲的教材。 所以,他批评反对者是“为了神话而神话”,是“打击了抗美援朝戏曲工作者,帮助了杜鲁门”,并认为反对者“引出了一个严重问题,那就是什么思想在支配着戏曲文艺运动,这就关系了无产阶级文艺运动领导权的问题”②。 在杨绍萱看来,自己通过戏曲宣传劳动创造了世界、歌颂民族革命、支持妇女解放、提倡统一战线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领导戏曲文艺运动的表现,掌握着无可置疑的真理,所以他理直气壮地批评反对者。 这种极端自信也来自他在延安时期获得的荣光,即作为《逼上梁山》的主创者受到毛泽东的表扬,这让杨绍萱产生了以“戏剧革命者”自居的心态。 事实上,《逼上梁山》本身就是一部带有“反历史主义”印记的作品,在杨绍萱的回忆中,延安观众“看戏变成了上课,有的同志一边看戏一边记笔记”[5]18,这一幕仍历历在目,当年通过戏曲来宣传马列主义,今天为何就不行呢?
问题出在他将《逼上梁山》中已经初见端倪的“反历史主义”发展到了更加突出、更加不协调的地步:用老牛和破车结婚来喻示劳动工具对人民生活的决定性作用,太过荒唐;卢俊义的妻子贾氏在燕青和春梅(代表奴隶阶级)的影响下,认识到丈夫参加民族革命的进步意义,从而也转变过来,和卢俊义和好如初。 这样通过改写流传久远的经典故事来阐释现实中的政治意识,“不但是破坏了民族文化的遗产,也是把我们当前的政治斗争加以歪曲和庸俗化了”[2]。 杨绍萱不断在戏曲中图解一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用力过猛,显得滑稽可笑,从而走到其动机的反面,不但谈不上艺术,而且没有起到他所追求的意识形态宣教效果。
艾青等人对杨绍萱及其“反历史主义”剧作进行批评,一方面是为了维护传统文化遗产、戏曲艺术,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厘清意识形态建构方式从而使其更为有效,因为“反历史主义”不仅不能起到建构意识形态的作用,反而以其滑稽可笑的方式破坏了意识形态的建构。 怎样才是有效的方式呢? 马少波在1951年撰写的一篇文章里,清算了“反历史主义”“不尊重历史条件,歪曲历史真实,将历史人物现代化,把历史事迹与现代人民革命斗争的事迹作不适当的类比”的做法,同时指出“单纯的无批评的强调‘历史真实’”也是不对的,要“把历史的真实与对于今天现实的影响与作用,有机的联系与统一”。[6]1这就是后来历史剧创作中广为遵循的“古为今用”原则。 概言之,在对“反历史主义”的批判中,“古为今用”作为一个有效的方式和原则被确定下来。 但,什么是“历史真实”? 历史剧怎样才算发挥了对现实的影响与作用? 两者又如何有机联系与统一? 人们的认识并不统一,这就使得历史剧创作的理论与实践陷入长期争论中,莫衷一是。 更发人深思的是,尽管“反历史主义”在20 世纪50 年代初就遭到大规模彻底批判,但这种倾向一直是此后历史剧创作中最为难缠的顽疾之一,这不能不让人推测,“反历史主义”或许就是强化历史剧意识形态功能带来的必然结果。
二、题材选择和人物形象塑造
为了发挥历史剧对现实的积极作用,做到“古为今用”,剧作家首先要考虑好历史剧的题材。 “我们自己的民族的过去事物必须和我们现代的情况、生活和存在密切相关,它们才算是属于我们的。”人们经常援引黑格尔的这番话,作为历史剧题材选择的理论依据,并得出这样的结论:“只有那些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与时代精神息息攸通的历史题材或历史生活,才能揭示出积极的思想意义。”[7]71而在当时以各种运动形式进行国家治理和民众思想改造的时期,政治运动和政策条文成为现实生活和时代精神的主要内容。 因此,能够与当下政治运动、政策条文产生联系,或有一定相似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就势必成为历史剧创作者的首选。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了两次历史剧创作高潮,都体现出这种题材选择的规律。 第一次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时期,以京剧《唇亡齿寒》(朱慕家、王颉竹合编)为代表,出现了很多“假道伐虢”题材的历史剧。 信陵君窃符救赵、六国联合对抗暴虐强秦的故事,也成为剧作家乐意选择的题材,华粹深《窃符救赵》是此类代表。 据马少波统计,同时出现的信陵君题材剧作有十七种之多。 第二次在1959 年至1962 年期间,由于中苏交恶,国家强调发奋图强、自力更生,同时因毛泽东发表关于“海瑞精神”的讲话,邓小平提出“编一点历史戏,使群众多长一点智慧”的倡议,历史剧剧作喷涌而出。 该时期有写民族战争中英雄人物的剧作,如《满江红》《金山战鼓》《澶渊之盟》等;写历史上有进步意义的君王,如《则天皇帝》《卧薪尝胆》之类;写农民起义领袖,如《唐赛儿》;写历史上的清官,如《海瑞上疏》《海瑞罢官》《强项令》。 其中卧薪尝胆题材有上百个剧团竞相上演,其他像岳飞、武则天、海瑞也成为比较热门的题材,每个题材出现过两种以上的作品。
题材雷同是颇值得注意的现象,除了这些题材比较适合现实中的政治运动、政策条文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剧作家为尽量避免题材选择错误,于是产生了一种从众心理。
历史剧以历史人物为主角,所以选材时首先要考虑如何评价历史人物。 20 世纪50 年代初,对电影《武训传》的大批判使得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变得极为敏感,甚至导致对一些在民间千百年来为人们所赞美的历史人物进行批判的不良风气,甚至包公、岳飞等都遭到了基于阶级属性的批判。 虽然这种不良风气很快得到纠正,但人们在评价历史人物时仍然小心翼翼,这导致较长时间里以真实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为题材的历史剧创作比较稀少。 1959 年1 月,郭沫若发表《谈蔡文姬〈胡笳十八拍〉》一文替曹操翻案,引起了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大讨论,逐渐形成历史界关于人物评价标准的共识,除了阶级标准之外,“评价历史人物的基本标准是看其在历史上人物的作用”[8]27。 以历史的眼光,考察人物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而不仅仅是将阶级出身、归属作为评价人物的唯一标准。 往往是领导人肯定过的,或史学界充分讨论过并有定论的,或翻案了的历史人物,才能成为历史剧的主角。 这成为剧作家规避错误评价历史人物的一种模式,因此导致历史剧题材的高度雷同。
与此相关的是人物形象塑造。 已经得到新意识形态认可的历史人物及其故事,优先被选为历史剧的题材,但具体这个历史人物怎么塑造,仍然会令作者大为挠头。 这里会出现两种不同的倾向。
一种是彻底美化历史人物。 历史剧创作之初就是为了体现“时代精神”,剧作家通过塑造正面的历史人物来宣传民族战争中的爱国主义精神、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反压迫的战斗精神以及为民请命的公仆精神,以实现其现实意义。 歌颂历史人物就是歌颂时代精神,所以被歌颂者就不能有缺点。 比如大量《卧薪尝胆》同名剧作,基本都删除了西施这条线索,即使保留了西施这个人物,她也不再是越国派去的奸细,而是一个被掳的越国少女。 范钧宏《卧薪尝胆》原稿写吴国索要美女,勾践等遂将西施送去,剧中有西施离别前的抒情唱段,非常动人。 但后来范钧宏听说别人写的西施都是被抢去的,他也把情节改成西施被抢去,唱段只好割爱。 人们不敢写西施是被勾践送给吴王的,因为那样就使得勾践成为一个阴谋家,而且,如果越国的复兴事业中竟然有“美人计”的功劳,那在今天是否还值得歌颂就成了问题。 从这些人物形象塑造的细节处理上,我们就能感受到意识形态建构中剧作家面临的巨大压力。 范钧宏当时大吐苦水:
写作过程中,就出现了这么一种现象:在虚构故事情节上,胆子很大;在描写勾践性格上,胆子很小。 我们怕犯错误,因而也不敢教“勾践”犯错误。 自己的顾虑和别人善意的提醒,形成了清规戒律:忍辱负重要削弱,复仇思想不能提,性格上的缺点要避免,策略性的斗争方式别乱用,不太“正义”的不能写,不符合今天政策的应注意……如此这般,剩下来的就是表面“高大”,其实空虚,多少还有点今人思想的人物了。[9]88
为了避免触犯各种“清规戒律”,剧作家们选择按照现实中的政治标准、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来塑造(美化)历史人物,从而让人物形象符合主流意识形态。 这种情况下,人物难免就高大空,还带有现代人的色彩,严重些的就又滑入“反历史主义”的窠臼,出现茅盾在他那部谈历史剧的长篇论文里所指出的各种“啼笑皆非的描写”③。
但还有一种相反的倾向是在塑造人物时刻意添加“缺点”,以表明主人公的历史“局限性”。 粤剧《寸金桥》描写近代法国侵略广州湾时,遂溪县令李钟钰带领乡民与外国侵略者展开斗争的故事。 在《毁村》《过营》《誓师》《逼界》几场戏中,李钟钰作为民族英雄的形象得到了很好的塑造,但作者为了表明李钟钰作为统治阶级的局限性,在最后两场戏中让他变得软弱起来,描写李钟钰率先撤离了阵地,同时让之前没有太多铺垫的农民领袖陈耀邦成为领导斗争的核心人物。 这样一来,人物形象塑造就前后不统一,给人生硬割裂的不完整感。 剧作家如此写,说到底还是怕犯错误,担心因为没有写出历史人物的局限性而受到批评。 的确有读者、批评家拿着放大镜寻找剧本中的各种问题。 比如京剧《满江红》中写了两个细节:一是岳飞接到诏书后,仍然准备北渡抗金,直到十二道金牌传来才作罢;二是岳飞在大理寺看到岳雷、张宪被绑,有一个意欲冲出去的动作。 有评论者认为这样塑造岳飞形象,就没有写出一个无限忠于君王的封建统治阶级人物的局限性。
这里问题来了,同样是担心政治上出错,但有些历史剧对主人公无限“美化”,有些却要刻意增加“缺点”以显示局限性,为何会出现两种截然相反的倾向呢? 我们很难找到准确答案,该美化还是该刻意增加“缺点”,并没有规律可循。 勾践题材的剧作中也有刻意写其缺点的例子,这类剧作通常是为了强调人民群众才是越国复兴的主要力量。 相同的是,无论“美化”还是刻意写“局限性”都是为了契合意识形态,这主要取决于剧作家考虑要从哪一方面契合。
也有一些论者认为写历史人物当然不能不反映出历史局限性,但“美化”是在歌颂中摒弃了所有局限性,而刻意写缺点也不是正确的处理方式,“所谓写出历史人物的局限性,实质上无非也就是说要写出历史人物的具体性。 什么时代说什么话,什么阶级说什么话……局限性表现在历史人物身上是具体的、整体的、贯串的,而不是抽象的、割裂的、孤立的”[10]25。他们希望剧作家真实地、完整地塑造人物形象,认为在这个过程中历史人物值得歌颂的优点和作为局限性的缺点,就自然而然呈现出来了。 这旨在让剧作家在塑造人物时不要过多受到“现实意义”和“历史局限性”这些政治话语的影响,更不要在剧作中机械地、公式化地表现出来。 显然,这种声音是理性的,也符合艺术创作规律,但在当时实践起来并不容易,更多的历史剧仍然摆脱不了人物塑造时无限美化或割裂地刻意写缺点的倾向。
三、人民群众的力量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1]1031,唯物史观中,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 因此历史剧如何表现出人民的力量,从而体现人民在历史创造中的作用,就成为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 这个问题在写农民起义的历史剧中比较好处理(起义者就是人民群众的一分子,这种题材本身就是要表现人民群众的力量),但在写统治阶级英雄人物题材时让剧作家大费周章。
比较常见的一种处理方法,是将人民群众作为支持这些英雄人物的重要力量,剧中予以比较重要的角色,或有专门表现群众的场面。 1950 年华粹深创作的《窃符救赵》堪称这种模式的代表。 该剧主要表现信陵君、平原君、如姬等封建贵族为了国家利益抗击侵略者的故事。 剧中出身守门小吏的侯嬴就是人民的代表,是他启发了信陵君,让后者知道抗秦不仅是为了兄妹之情,更是为了天下,所谓“秦师东来,我大梁亦难幸免,秦肆虎狼之心,有并吞天下之志,它必要扫平天下,然后甘心。 邯郸如若为贼所陷,则天下永无和平之日,受害者岂止赵、魏两国而已”[12]58。 侯嬴献出如姬窃符的计策,让朱亥帮助信陵君夺取军权,最终救了天下百姓,而自己却献出了生命。 这个人物没有太多的戏,但是在他的推动下,信陵君的抗秦事业得以成功。 另外,在表现平原君毁家纾难,招募民军以抗秦时,华粹深也专门写了一场邯郸百姓与平原君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的群众戏。 最后一幕,信陵君、平原君、如姬和赵魏两国百姓齐聚侯嬴的墓前,祭拜他,“齐祝告成仁勇烈老英雄,多亏你献计救苍生……从此后齐心携手享太平”[12]80。 从整个叙事上看,贤明的贵族阶级的愿望与人民的愿望是一致的,他们齐心协力保卫了国家,赢得了和平,这一构思线索非常鲜明,呈现得也比较成功。 众多写越王勾践的戏曲中,人民群众同样起到支持他、推动他发奋图强的作用,但有些剧作过于强调人民群众的作用,使勾践这一主人公显得非常软弱。 本来代表人民群众的人物形象并非最主要的角色,但过于强调人民群众后“反客为主”,上面提到的粤剧《寸金桥》就是其中一例。
将人民群众作为点缀,贯穿始终,这也是比较普遍的做法。 这里,人民群众不是斗争的重要力量,主要起到线索作用、衬托作用。 海瑞题材戏曲,皆属于此种。 《海瑞上疏》中,嘉靖皇帝听信道士之言,要修建玉芝坛,仙人巷的几百户人家失去安身之所,施象清、倪树庆作为百姓的代表向海瑞诉说苦情,这是促使海瑞上疏的重要戏剧情节。 海瑞系狱,施象清等人“跪香请命”,表现了人民与清官之间的浓厚情谊。最后一幕更有象征意义,嘉靖皇帝去世后,海瑞官复原职,施象清等一众百姓赶来迎接,天空飘起雨来,这时舞台上撑起一把大伞,海瑞邀众人避雨,感叹道:“可惜我这把伞太小了。”施象清说:“有这样一把,也就难得的了。”[13]51在群众的衬托和别有意味的情节、台词的渲染之下,剧作点出海瑞是人民保护伞这样的题旨。 《澶渊之盟》是一部基本没有群众的戏,但剧作家也不忘安排两名唱小曲的村姑来点缀一下,通过她们的唱来赞美寇准抗击金兵的历史功绩。 最后一幕,寇准罢相归乡,还与两位村姑话别。 代表人民利益的人,总是受到人民的热爱,主题意蕴就在几笔点缀中被四两拨千斤地揭示出来。
将人民群众作为主角来写,让他们直接参与斗争,这种叙事模式比较少,因为这会影响对本来要着重赞美的历史人物的塑造,甚至造成主题的不统一。也有处理得比较好的,评剧《钟离剑》[14]就是这样一部作品。 该剧同样是写勾践发奋图强的故事,但与其他同类题材构思完全不同。 勾践复国的主线上,铸造兵器成为一个核心事件,于是精于铸剑的钟离泉老人成为重要人物,他隐藏于深山之中,为越国铸造兵器,后又被吴国绑走,展开了与吴国君臣面对面的斗争。他勇敢而机智,在此之前已经将技术传授给孙女素女,为越国最后获胜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武器。 勾践和钟离泉祖孙的两条线索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既表现了越国君民上下团结一致的爱国精神,同时也体现了勾践在复国事业上代表人民的意愿和利益,因此赢得了百姓的支持,最终获得了胜利。
关于在历史剧中是否一定要出现人民群众的问题,人们有针锋相对的争论。 这集中表现在对《淝水之战》的批评中。 故事取材于前秦与东晋的一场名战,它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 作者为了表现人民的力量在这场战斗中的重要作用,设置了耿义这样一位义军领袖,在关键时刻,他带领农民部队给予前秦致命一击。 沈起炜在《上海戏剧》上发表文章,认为历史剧大都注意人民群众的作用,“但是也似乎有一个套子,就是常常请义军出场来解决问题”[15]33。 他指出剧作家在《淝水之战》中设计耿义这样的人物和相关情节,并不符合历史真实,因为没有任何历史记载表明此战是由于义军帮助才取胜的,而且在东晋时期农民对庄园地主的依附性很强,无法形成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军队。 此后,《上海戏剧》发表了多篇讨论文章,蒋星煜对沈起炜的观点进行了批驳,认为史料上并非说东晋时期没有起义军,只是比较零星或者规模很小,历史剧本身也可以对史料进行提炼加工,从而塑造典型。[16]25沈起炜对此又进行了反批评,指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编撰的《中国通史简编》、吕振羽编撰的《简明中国通史》等根据现有史料分析淝水之战,认为前秦失败是其内部原因决定的,晋军能同仇敌忾也是原因之一。 而另外增加起义军,于史无征,而且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不一定有大规模的起义军队伍,所以,在“基本情节、主要人物及其活动,早已经为人熟知”的情况下,《淝水之战》这样写,弄得半真半假,既不符合历史事实,又会导致历史教育出现问题,中学生会以为淝水之战是“幸得耿义领导的义军相助”才取得胜利。 沈起炜也强调并非处处都要按照历史基本情节来写,“在采取历史上的大场面为题材时,才有这个必要”[17]24。 接着,唐真、宁富根等人也加入讨论,分别支持沈、蒋二人的观点。 宁富根坚持认为“应该从人民群众本身来突出人民群众的作用,而不是借助于人民群众以外的任何形象力量”[18]17。 另一方则认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任何阶段的历史现实总会出现能反映人民意志的人物。重申值得歌颂的英雄人物,本身就是代表人民群众的意愿,岳飞、韩世忠、杨家将这些人虽然在帝、王、将、相之列,但得到了人民的支持,起到了领导和指挥人民的作用。 是否要直接写人民群众,应该由题材决定,而不能为了反映人民群众而违背历史真实。[19]26
显然,只有直接表现人民群众,才算贯彻了人民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的说法,非常荒谬。 但在当时,这种观点却比较常见,按照这种观点创作的剧作家也不在少数。 这不但破坏了剧作艺术的完整性,造成不必要的枝节,而且正如沈起炜所说,这种虚构偏离了历史真实。
四、历史真实
随着历史剧创作兴盛,关于历史剧的理论批评也繁荣起来。 历史学家吴晗在1960 年12 月25 日的《文汇报》上发表《谈历史剧》一文,引起了关于历史剧的大讨论。 此后,吴晗又陆续写了《再谈历史剧》《论历史剧》等多篇讨论文章,但仍沿袭了《谈历史剧》中的主要观点。 其核心论点是:
历史剧必须有历史根据,人物、事实都要有根据。 历史剧的任务是反映历史的实际情况,吸取其中某些有益经验,对广大人民进行历史主义爱国主义教育。 人物、事实都是虚构的,绝对不能算历史剧。 人物确有其人,但事实没有或不可能发生的也不能算历史剧。 ……历史剧的剧作家在不违反时代的真实性原则下,不去写这个时代所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而写的是这个历史人物所处的时代完全可能发生的事情,在这个原则下,剧作家有充分的虚构的自由,创造故事,加以渲染、夸张、突出、集中,使之达到艺术上完整的要求。[20]
在这里,他提出了两个话题并表明自己的看法:一是历史剧的界定问题。 吴晗认为当代的新历史剧,必须在事情、人物上有历史根据,所以他将《杨门女将》《十二寡妇征西》《秦香莲》《柳毅传书》等完全虚构的古装戏排除在“新历史剧”概念之外,称其为“故事剧”“神话剧”。 二是历史真实与虚构问题。 因为他将历史剧界定为必须以真人真事为依据,所以他认为历史剧的艺术虚构必须遵循“真实性原则”,即“不去写这个时代所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而写的是这个历史人物所处的时代完全可能发生的事情”。
王子野、辛宪锡、马少波等人都不同意吴晗关于历史剧的界定的观点,他们认为历史剧指的是以古代生活为素材的戏剧,“戏剧家只问事件可能不可能,不问真有不真有”[21]。 “杨家将中有史可考的只有杨业、杨景、杨文广三个人,但是舞台上激动人心、多色多彩的杨家将的爱国故事和光彩照人的杨家将的英雄形象,难道不正是剧作者追求更高的真实的结果吗?”[22]53事实上,人们很快就不再纠结于历史剧的界定问题,而是把第二个问题“历史真实与虚构的关系”作为焦点,其关键又在于对“历史真实”的不同理解上。 反对吴晗的论者,认为吴晗错将被记载的历史事实当作了“历史真实”,追求“无一字无来历,无一事无出处”,是将历史教科书和历史剧混淆起来,实际上限制了历史剧的虚构性。 吴晗的确有将“历史真实”表述为“过去人们的实践,在特定时期确实发生过的事情,历史家用科学态度如实地把它记录下来”,但他也绝对承认虚构的重要性,强调“只能虚构在剧作家所写的特定时期可能发生的事情,而决不可以虚构这个特定时期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只有这样,才能到达到历史真实性与艺术真实性的统一”。[23]39实事求是地说,吴晗的观点中有一些表述不够准确的地方,有时过于注重历史事实的真实性。 作为历史学家,他似乎过于强调历史剧承担的历史教育功能,担心虚构历史上不存在的事件,会“歪曲了混乱了祖国的历史,降低了历史剧的教育意义”[20]。
反对者认为历史真实应该是一种超出历史事实的“历史本质真实”和“更高的真实”。 毫无疑问,这种提法更为合理。 王子野、李希凡等人广泛援引亚里士多德、莱辛、黑格尔等先贤关于艺术虚构、历史剧与历史真实关系的观点并进行阐发,的确深化了关于历史剧创作的讨论。 但问题是,这种“本质真实”到底是什么呢? 在当时的背景下,指导现实生活的政治意识同时也指导了人们对历史的认知,所谓“历史本质真实”无法不被打上政治烙印,带上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 所谓历史事实的真理,与现实生活的真理,趋于同一化。 剧作家“总是凭借今天的观点,凭借今天的生活体验去认识过去时代的社会生活,并反映过去时代的社会生活的”,于是“剧作家为了把‘事实的真理’揭示得更鲜明、更深刻,就完全有权利通过概括、集中、提炼等艺术手法,对‘事实’做出必要的‘变动’”,也就难以避免通过改变历史来符合现实需要。[24]这样一来,历史剧达到了“古为今用”的目的,表现出了时代精神,在现实生活中有了合法性。 对于众多越王勾践题材戏曲作者来说,这个故事经过提炼、概括后反映的“历史本质真实”就是今天所需要的“奋发图强”精神,越国君臣、人民在民族压迫中奋发图强,终于战胜了强大的敌人,开始和平幸福地生活,无不是对当下国际关系和政治现实的一种隐喻。在这一创作理念指引下,在“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统一的原则下,很多现实中才有的思想、语言和生活元素,以“虚构”(可能发生)的理由进入剧本,从而又陷入“反历史主义”泥淖。 这种“片面地解释艺术虚构,把艺术虚构强调成可以‘创造历史事实’的万能法宝”[25]的情况,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皆非个别情况。 剧作家们纷纷诉苦,过多地考虑如何与今天的“时代精神”合拍的问题,“这一下子,就把步伐跨大了。 有的是并不自觉,有的是有所觉而欲罢不能,有的则是一马当先有意为之”[26]85。 有些人是自觉迎合,有些人是无可奈何,有些人是在政治主宰生活的环境下潜意识里以为理所当然,于是,历史剧成为对当下政治运动、政策条文的图解和说明。
事实上,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历史剧创作实际来看,并没有那种完全依据历史事实而不讲虚构的笨人,相反,大胆、随意虚构甚至过于浪漫化想象的主观化、公式化剧本比比皆是。 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吴晗对于历史剧概念的界定,以及对于历史真实与虚构问题的讨论,有着重要现实意义。
除了吴晗,当时还有几位重要论者的观点也值得重视。 王季思认为历史剧不仅要表现“特定历史时期的时代特征”,还要有“特定历史时期的生活习惯和语言运用”,他质疑郭沫若《武则天》过于现代化的语言和人物思想。[27]124茅盾在批评卧薪尝胆题材历史剧时指出问题的关键,即“史书所没有的,剧作家可以想象,可以虚构,但是必须从二千四百年前越国的现实基础上进行虚构,而不是从我们今天的现实基础上进行虚构”[28]120,试图将历史剧创作拉出比附、影射现实的泥沼。 《戏剧报》发表的评论员文章中指出:
历史剧配合政治任务不可能像现代题材剧目那么密切,它对现代人主要的教育作用是历史的经验教训,古人在阶级斗争、民族斗争和日常的生活斗争中所显示的智慧。……描写历史人物必须把他放在那个时代和阶级的典型环境中去表现;无论是环境描写或者人物描写,必须是入情入理的。 所谓入情就是人物的心理逻辑、人物的思想感情和情绪;入理就是人物的外部逻辑、人物之间的相互关系、戏剧冲突、情节结构等等。[29]5
这里虽然还在不断强调阶级等意识形态,但提出历史剧创作应该塑造合情合理的人物形象的观点,将问题回归艺术创作本身,已经难能可贵了。
五、结语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几部比较成功的历史剧,如《钟离剑》《满江红》《澶渊之盟》《金山战鼓》《海瑞上疏》《则天皇帝》《强项令》等,正是在大关节尊重历史事实的框架下,围绕人物形象塑造合情合理地进行艺术虚构。 这些剧作既具有较为鲜明的历史感,符合历史真实,同时人物性格鲜明,具有一定艺术感染力,也富于教育意义,在当时成百上千的历史剧作中,实属凤毛麟角。 限于篇幅,这里无法一一细致分析。 但更多的剧作,在尽力体现意识形态建构功能时,被各种条条框框的意识所束缚,背离了艺术的真谛。 回溯历史,无论成功之作,还是更多的失败作品,共同提供了一个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历史剧理论和实践的真实镜像,借此镜像,我们认识历史并反思历史。
① “本报自十一月三日发表杨绍萱同志的《论“为文学而文学、为艺术而艺术”的危害性》一文后,各地读者纷纷提出意见。 截至十二月三日止,本报已收到读者来稿、来信二百七十三件。参见《批判杨绍萱在戏曲改革中的反历史主义倾向》,载于《人民日报》1951 年12 月5 日。
② 杨绍萱写给《人民日报》的信,附在《论“为文学而文学、为艺术而艺术”的危害性——评艾青的〈谈“牛郎织女”〉》一文后,载于《人民日报》1951 年11 月3 日。
③ 《谈历史与历史剧》中举出很多剧本中勾践形象塑造的问题:“不但会像我们的下放干部那样从事农业劳动,与人民‘四同’,而且还有今天我们所理解的‘以农业为基础’的观念;越国不但大兴水利,大搞农业,而且还大炼钢铁,还请外国专家帮助铸造武器,改良农具;越王勾践不但自己卧薪尝胆,而且还搞三反运动。”参见茅盾《关于历史和历史剧》,作家出版社,1962年版,第120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