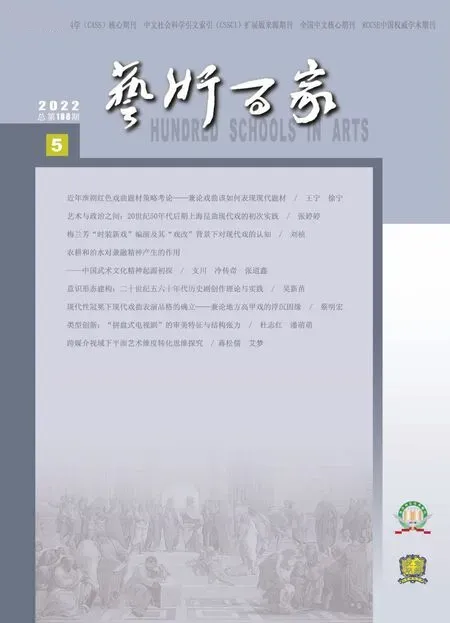类型创新:“拼盘式电视剧”的审美特征与结构张力∗
杜志红,潘萌萌
(苏州大学 传媒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影视类型的认知,总是基于影视创作实践的探索,创作实践无止境,类型认知也要与时俱进。 赖亚尔提出:“类型可定义为模式、形式、风格或结构,他们超越单个影片,指导影片制作人的制作,引导观众欣赏。”阿伯克龙比认为此话“也适用于电视”[1]49。近年来,在我国电视荧屏上频繁出现一种新的电视剧类型,它的结构与传统的单本剧、连续剧、系列剧均有所不同,往往由多个小故事拼接在一起形成一部作品,服从于某个重大主题,如抗疫报告剧《在一起》《最美逆行者》、献礼剧《功勋》《理想照耀中国》《我们的新时代》《我们这十年》、扶贫剧《石头开花》《脱贫先锋》《约定》等。 对于这类电视剧,学者们有的称之为“单元剧”,有的称之为“时代报告剧”,还有的称之为“集锦式电视剧”或“拼盘式电视剧”。 本文从类型分析视角对此类剧作的概念进行辨析,分析其结构特征和审美张力,并对如何提升其质量提出建议。
一、概念辨析:结构作为类型之维
划分类型首先要确定划分标准或维度。 一般来说,划分电视剧类型,一是依据题材内容,二是依据结构形式。 由于文化背景不同,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划分方法,依据题材内容划分出来的类型往往产生交叉,呈现出模糊和不稳定的特性。 依据结构形式来划分,类型的定义则比较稳定和清晰,比如塞尔夫在《电视剧导论:类型与媒介》中将电视剧划分为单本剧、系列剧、连续剧等[2]91-108,每种类型一旦确定,就不大可能同时又是另外一种。 在我国,学界一般比较认可塞尔夫的划分方式。 从1958 年第一部电视剧《一口菜饼子》播出到现在,在60 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从剧场剧到单本剧,从系列剧到连续剧,我国电视剧的结构样式不断创新。 近年出现的这些剧目类型,从结构上看不同于以往,其概念使用还比较混乱,应该给予其一个相对稳定的概念定义。
本文认为这些呈现出新的结构类型的电视剧应该被命名为“拼盘式电视剧”,有以下几个理由:
首先,“拼盘”一词属于烹饪学范畴,指在一个盘子里,几种不同的菜肴共同组合成一道菜。 它代表了一种特殊的搭配和组合概念,这种搭配和组合并不是随意而成,而是有着内在的逻辑或出于对风格的考量,比如为了颜色优美、营养均衡、口感丰富,或为了造型多姿多彩、相映生辉。 从这个意义上说,“拼盘”概念可以很好地概括这类电视剧的结构特点,即一部剧由多个不同的人物故事拼装在一起,单个故事彼此之间不尽相同,共同的题材和主题使其统合为一个整体,同时因为主体多元、角度多样,将它们组合在一起能够达到各有特色又和谐共生的效果。
其次,“拼盘”比其他称呼更能准确概括此类剧作的结构特征。 如“单元”一词,带有静态意味,偏重于强调各个故事的独立性;“集锦”则容易被理解为没有内在关联的汇聚,或者是收藏式陈列。 相较于“单元”“集锦”等概念,“拼盘”既是名词又是动词,带有强烈的主观能动性色彩,更强调整体性和协调性,可以概括这种剧类“形散而神不散”、特别注重内在关联的结构特质。
最后,“拼盘”并不意味着每一个被拼合的小盘无足轻重,每一个小盘里的菜肴可能由不同的厨师专门制作,各扬所长,最后小盘被拼装在一起作为一个整体呈现在食客面前。 “拼盘式电视剧”也是如此,多位导演各自独立完成其中的一集或几集,这一集或几集既是独立的人物故事,又与其他剧集形成互文性关联,构成更大的时代背景或主题框架下的叙事整体。
因此,本文认为“拼盘式电视剧”可以定义为基于同一题材和主题讲述多个不同故事,同时又将这些故事作为一个整体播出的电视剧。 它可以由一位或多位导演独立或合作完成一集或几集剧情,各自塑造不同的人物,描绘不同的场景,讲述不同的故事。“拼盘式电视剧”可以作为除单本剧、系列剧和连续剧之外的新的剧类名称,正式进入电视剧类型和结构的大家庭。 本文把“拼盘式电视剧”(简称“拼盘剧”)作为一种新的结构类型来定义近年出现的这类剧目,并将其概念化,这对学术研究和创作探讨具有重要的认识论价值。
当然,也有人提出用“时代报告剧”来命名此类电视剧,如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在正式会议报告和文件中,使用“时代报告剧”这一名称组织、策划了疫情防控、精准扶贫、建党百年、“一带一路”等重大主题的电视剧创作,因此涌现出一大批不同主题的“时代报告剧”。 虽然这些剧多采用“拼盘”式结构,但“时代报告剧”与“拼盘剧”这两个名称却不可等同,也不可互相取代。 因为“时代报告剧”是从题材内容角度来命名,“拼盘剧”则是从结构角度来定义,“时代报告剧”可以不采用“拼盘”式结构,同样,“拼盘剧”也不一定都是“时代报告剧”,换言之,“拼盘”式结构并不为“时代报告剧”所专有。
二、“拼盘式电视剧”的结构美学
结构既是一种剧作类型的认知路径,又是在剧作类型规范指导下创作出的影像的构成框架。 一种结构会生发一种审美认知,即剧作的结构可以塑造观看者的审美接受思维,让观看者形成新的观剧体验和习惯。 笔者仔细考察和概括“拼盘剧”的结构要素和创作模式,发现其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审美特征。
(一)共同主题下的独立短故事拼装
它既然被称为“拼盘”式结构,那么就一定要有拼盘的内在逻辑或理由。 “拼盘剧”的内在逻辑基础是鲜明的主题或共同的情景、社会背景。 目前采用“拼盘”式结构的“时代报告剧”大多具有宏大而鲜明的主题,比如献礼、扶贫和抗疫。 “拼盘式电视剧”以主题为核心,多个篇章均围绕统一主题创作,起到宣传主题的作用。 一般来说,电视剧中如果出现多个时空场景和多条故事脉络,就极易让观众产生游离感,而“拼盘剧”的每一个片段都有专属的叙事主体,虽然各情节单元表面并无关联,但因为“拼盘剧”有凝练的主题,所以无论其在故事结构上发生怎样的改变,都不会让观众感觉剪辑“撕裂”。
举例来说,《功勋》讲述了于敏、孙家栋、袁隆平、李延年、黄旭华、屠呦呦、申纪兰、钟南山等8 位为中国作出重大贡献的功勋人物的不同故事。 该剧采用每6 集讲述一个人物故事的结构,每个故事的叙事风格不同,但因为全剧由共同的主题统摄,所以多个故事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完美的整体。 《在一起》以2020年武汉抗疫为共同主题,选择不同行业的人物为故事主体,采用每2 集讲一个故事的结构,表现全社会各行各业的普通人在疫情阴霾之下承受的压力和痛苦,以及他们的选择和抗争。 《石头开花》同样是每2 集讲述一个故事,聚焦扶贫工作中的十大难题。 剧作讲述了在十个贫困情况不同的地区,基层干部、群众和社会扶贫力量齐心协力摆脱贫困的故事。 从结构上看,每个被拼装的“拼盘”都是一个独立的短故事,每个短故事的主人公和情节脉络各不相同,分别构成完整而独立的叙事。
“拼盘剧”的结构模式与单本剧、系列剧、连续剧的结构模式明显不同。 虽然“拼盘剧”的每个故事看起来都像单本剧,但是因为“拼盘”之间有内在关联,形成整体叙事,所以“拼盘剧”的内容比单本剧丰富、厚重得多,也更具观赏性。 同时,因为这些剧中没有足以支撑全剧的固定人物角色,所以“拼盘剧”又与系列剧有所不同。 系列剧(如《编辑部的故事》《我爱我家》《重案六组》等)也是每一集讲不同的故事,但是其一般有几个固定的主要人物。 最后,因为“拼盘剧”中每个故事都独立成篇,所以它不用像连续剧那样受缚于故事的连续性,即观众不一定要按照剧集顺序观看“拼盘剧”,这大大符合了今天人们的观看习惯和观看心理。
随着手机、平板电脑等媒介深度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人们每天不得不用大量时间来处理各种信息,体验不断加速的社会生活节奏,不再有心情坐在电视机前从容观剧,而多元观看终端也解除了先前观众与电视剧播放时间的约定。 从某种意义上说,“拼盘剧”的出现或许正好迎合了这种生活节奏。 同时,“拼盘剧”的结构也让观众获得了类似观影的体验。以2022 年播出的《我们这十年》为例,该剧每4 集讲述一个独立完整的故事,4 集的时长相当于一部加长版电影,这样既可以保证故事讲述得细腻、完整,又能够让观众获得类似观看一部电影的情节满足感和体验。
(二)群像中的个体呈现与“轮转的主体性”
“拼盘式电视剧”通过塑造大背景下的群体“雕像”来反映宏大主题、再现时代精神,从而整合出一种集体叙事,引发观众的家国情怀共鸣。 “拼盘式电视剧”人物众多,主要角色分集轮流出场,进行群像式呈现。 这一特点在抗疫剧《在一起》中表现得最为充分。 该剧每2 集讲述一个故事,故事的主角分别为抗疫过程中不同身份的人,从武汉各医院的医护人员到外卖小哥,从公安干警到基层社区工作者,从援鄂医疗队队员到各地疾控中心流调队伍,等等。 每个故事都由两到三个主人公共同演绎,这一安排使这一部剧有了多达几十位主人公,众多主人公集合在一起,构成了同一个主题框架下的“群像”。 同时,这些主人公又分别担当了2 集剧情中的叙事主体,他们的身份、性格和精神品质都被细致地刻画,因而每个人物形象都真实而饱满。
这样的一种叙事结构,让群像中的每个个体都能从自我角度来体验、审视和表达各自的情感、态度,并展开自己的行动,从而获得属于自己的主体性。 语言哲学认为,人们开口说话时,不可避免地要使用“自我概念”来建构人的主体性(subjectivity)。 “言语者用人称代词‘我’建立起一个观察和认识主体,从而建构自我意识和自我概念。 ……语言提供主体的表达形式,而语言形式的使用,即具体的言语行为,则产生人的主体性。”[3]9-15面对疫情,每个故事中的主人公都在言说自己的认知,也体验和感受疫情给生活带来的冲击和改变。 他们言说自我并投入集体战斗,从而获得鲜明的主体性。 主体性“是一种存在(existing)的感觉……主体性使得人们可以‘以自己为话题’与自己对话,并促使人们使用创造性的语言表情达意”[4]258。 获得主体性,可以让每个抗疫者不再是“被言说的客体”,进而让观看者自我代入,体验主人公的体验,感受主人公的感受,这样观看者就被“定位”在主体的位置上。
这种“轮转的主体性”结构,不同于电视连续剧中那种固定的主体性——所有剧情都围绕几个主人公展开,其他人都只是配角,主角眼中的“他者”,很难获得自己的主体性。 而主体轮转的“拼盘”式结构中的人物,就像是在一个巨型转盘上的雕塑群像,转盘不停转动,群像中的每个人都能转到观众面前并停下来讲述自己的故事,讲述完毕后,转盘转动,轮转到后面的主人公。 可以说,正是这种“拼盘”式结构让《在一起》这部剧很好地解决了多主体性展示的问题,这是根据题材内容进行的独特创造,给观众带来新鲜的审美体验。 该剧在某种意义上真实地反映了疫情时代社会的本来面貌,即在抗疫的大舞台上,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务高低,每一个人都是责任主体,大家只有同舟共济,才能携手战胜疫情。 同时,该剧以小人物为主体重构个人与国家的关系,让人感受到自己和祖国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使人产生归属感和民族自豪感。
(三)“各表一枝”:集体协作下的同台竞技
从创作实践层面看,“拼盘”式结构中的每个故事都独立、完整,因而剧作可以由不同的导演摄制团队和演员阵容分头同步进行拍摄和制作,这种类似传统古典章回小说“各表一枝”的叙述方式,极大提高了电视剧的制作效率。 我们仍以《在一起》为例,每个拍摄团队和演员阵容都只负责演绎总时长90 分钟的2 集故事,这只相当于一部微电影的工作量,因而比起动辄几十集的连续剧,这种方式的操作周期较短,一般两周就可以完成。 多个摄制团队同步操作,也大大缩短了整体制作周期,这让“拼盘”式结构电视剧可以从容应对某些较为紧迫、讲究时效的特殊创作任务。
更重要的是,这种“各表一枝”的高效率操作方式是提高电视剧作品质量的重要机制。 虽然各个团队有自己的独立故事脚本,但是因为最终要合在一起成为巨大的“拼盘”,所以就意味着整部剧的各部分要在播出时“同台竞技”,剧集创作成为一场关于导演和演员功力的比赛,观众或有意或无意地对不同单元的故事进行比较,这无形中给了每个团队类似参加比赛的压力。 当然,这种压力同时也是动力,它激励着每个团队高质量完成自己负责的独立故事,不给整部剧拖后腿。 正是这种既合作又比拼的协作机制,促使每个导演团队和演员阵容必须拿出全部精力和创造力,让自己负责的这个“拼盘”部分不要“掉队”,从而保证了整部剧的质量,并使之呈现出丰富多彩的艺术风格。
以抗疫剧《在一起》为例,该剧的不同单元由不同导演执导,带有他们独特的艺术风格,不同单元之间风格与风格的转换也非常巧妙灵活。 例如《生命的拐点》直面与病毒遭遇的主战场——医院,表现医生们的大无畏精神和大爱仁心;《摆渡人》以外卖小哥的游动视角,表现疫情带来的灾难和疾苦,以及普通人克服恐惧后投入战斗的心路历程;《救护者》用近乎实录的镜头再现军地医护工作人员联合作战的具体细节和专业精神;《同行》以两位已各自回家过年的青年医生重返抗疫一线的过程为情节脉络,带有爱情喜剧色彩,给抗疫剧增添了温暖和浪漫;《搜索24 小时》借鉴悬疑片的风格,演绎流调人员遭遇的困难并表现他们的智慧……只有在“拼盘”式结构下,这种同台竞技才能展现出如此风格鲜明的艺术表现力。
再以《功勋》为例,全剧由郑晓龙担任总导演,由毛卫宁、沈严、康洪雷等8 位导演各执导一个人物的独立故事。 该剧获得了良好的收视份额和口碑,“据‘中国视听大数据’(CVB)统计,全剧48 集揽获20.455%电视观众,回看用户规模始终位居黄金时段电视剧第一”[5]。 在“献礼”的主旋律命题下,《功勋》做到了兼顾市场娱乐性、爱国主义教育和不同导演艺术风格的个性展现,超高的完成度体现了几位导演的深厚功力。 该剧由于主题特殊,选角标准非常严格,整部剧有三十多位优秀演员加盟,其中八位主角无一是“流量”明星。 在这场同台竞技中,主演和配角都贡献了精湛演技,把人物塑造得非常饱满,让观众在一部剧中能够欣赏到众多不同类型演员的表演风格和艺术魅力。
三、“拼盘式电视剧”的结构张力
从某种意义上说,电视剧类型的演变史,也是一部类型之间通过杂交、混搭而不断创新的历史。 一方面,“类型的定位,可以吸收和稳定习惯于看某种类型节目的忠实观众”[1]51;另一方面,影视创作手法本身的开放性和灵活性,使得剧目类型结构表现出混搭和模糊的特性。 同时,随着新技术手段的出现,电视剧的表现手法和创作观念也不断变化,结构类型不断革新。 因此,类型的固定和变革是推动电视剧创新的结构张力。
当然,采用新的结构类型并不意味着就能出现好的作品,目前我国“拼盘剧”依然处于良莠不齐的状态。 这些剧作的主要问题包括人物形象不够丰满、细节缺少生活体验、故事情节简单生硬、图解主题意味过浓、各个“拼盘”故事水平参差不齐等,这说明一些创作者需要充分认识到“拼盘式电视剧”的结构张力,把握好类型的约定性与灵活性之间的平衡,从而提升“拼盘式电视剧”的艺术水平。
(一)“拼盘”时长要服从于人物形象塑造
“拼盘剧”的每一个故事的时长都相对较短,一般只有一到两集,因此没有太多时间用于塑造人物形象。 但是电视剧毕竟不同于专题片,不能只满足于表达主题,还要致力于塑造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形象。因此,“拼盘剧”要设定恰当的时长,为塑造人物形象服务。
目前看来,每一个“拼盘”故事以时长不少于2集(每集45 分钟)为宜。 故事如果时长少于2 集,则很难展现跌宕的情节或展示生动的细节,人物性格和形象刻画难以有较大的施展空间。 例如《理想照耀中国》每集用短短30 分钟讲述一个人物的故事,而且时间跨度极大,很多情节缺少细节支撑,故事流于肤浅的概念图解,剧集之间的排列也缺少内在逻辑,让观众感觉摸不着头脑。 这样的创作方式导致人物形象苍白,缺少主体性,只能沦为宏大叙事下的某种符号或标签,不能走进观众心里。
但是,每个“拼盘”故事的时长太长,也不利于“拼盘剧”结构优势的发挥。 如果一个故事讲了好多集还没有讲完,会让观众忘记这是“拼盘剧”,以为它是电视连续剧。 比如,在献礼剧《功勋》中,每个人物的故事用6 集时长来讲述,这虽然让故事背景交代得更充分,情节设计和细节刻画得更从容,人物角色塑造与具体环境联系得更紧密,但是又使观众觉得故事展开过于缓慢,在一个故事里停留的时间过长。 2022年广受赞誉的《我们这十年》,则是用每4 集一个“拼盘”的方式展开故事讲述,显得更为恰当,体现了“拼盘剧”的结构优势。 如果说连续剧展现的是人物的成长或变化,偏重纵向的深度,那么“拼盘剧”则是展现同一主题下人物故事的共通性,偏重横向的广度。无论如何,人物塑造仍然是第一要务,只有人物故事真实可信,主题表达才能有所依托。
(二)巧妙构思故事,让抽象主题落地
如前文所述,“拼盘式电视剧”的每个故事的时长仅相当于一部电影或微电影,它对主题的诠释力量来自多个故事的拼装与合力。 相对于电视连续剧而言,“拼盘剧”通过在平面上的铺展表现主题,而不是垂直向的深入。 这种结构具有先天独立性,会导致故事之间的弱关联,这样一来,就可能使剧作对主题的诠释只是一种低水平的重复。 同时,对于常年沉浸于欣赏连续剧结构的电视观众来说,“拼盘剧”结构往往会带来单本剧容易产生的“陌生感”:刚刚结识了一个人物,熟悉了他的生活,很快就要再换一个人物,又要重新认识和熟悉他,这种不断重复的陌生感,很容易让观众感到不能与人物“共同生活”。 因此,如果能让观众在前一个单元故事中认识接下来单元的主人公,就会激起他们极大的观看兴趣。
以《在一起》为例,每个“拼盘”故事表面独立,但是编导巧妙埋下暗线,将不同的故事勾连起来,不仅很好地解决了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问题,还做到了主题表达的统一。 埋下暗线的方式是让人物交替出现在不同的故事中,同一人物在不同单元中出现可以将不同的故事勾连起来。 例如,在第1 集和第2 集《生命的拐点》中,主角是江汉医院的医生们,为他们送“爱心口罩”的快递员是第3 集和第4 集《摆渡人》中的主角外卖小哥辜勇。 在《生命的拐点》中,辜勇是一个不起眼的配角,而在《摆渡人》中,他成为主角,作为外卖小哥的他,在特殊时期发挥了“摆渡人”的作用,为不能出门的人们送去需要的东西和温暖。他为在医院做志愿者的贾长安送去医生们需要的口罩,贾长安的女朋友正在江汉医院接受新冠肺炎治疗,这里的医护人员便是《生命的拐点》中的主角。这种主、配角色在不同叙事链条中的互换,产生了一种视角转换效果,让“轮转的主体性”得以实现,加强了每个独立故事之间的关联,从而深化了主题。
当然,这种设置人物关系和加强故事关联度的方式,需要有现实基础。 《在一起》的设置之所以完全合理,是因为它讲的是同一座城市中的故事。 假如故事发生在不同地方,这些人物就不大可能关联起来,那么电视剧创作者就要在每个“拼盘”中巧妙构思故事,挖掘和丰富细节,让抽象的主题能够落地,让真实的生活折射主题,而非直白地表达。 以《我们这十年》为例,全剧故事的发生地涉及河南、新疆、广东、浙江、北京、内蒙古、宁夏、湖北、贵州等十多个省市,还有一些非洲国家。 如果强行让这些故事发生关联难免显得有些牵强,摄制组采取让主题落地的创作思路,这样就使每个故事都有真实的生活做支撑,鲜活的生活场景和生动的人物故事让观众几乎忘记了主题的存在。
(三)处理好宣传性与艺术性之的平衡关系
由于故事短小精悍,加上多个摄制团队同时操作,“拼盘式电视剧”往往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制作。因此“拼盘式电视剧”适用于有时效要求的主题宣传,特别是献礼题材和时代报告题材的电视剧,都对播出时间有要求,错过了宣传的时间节点,也就失去了播出的意义。 但是,对电视艺术作品来说,无论为了什么样的宣传主题,都必须把艺术性建立在宣传性之上,没有艺术性,主题宣传就很难取得好的效果。可以说,艺术性是宣传性得以附着的基础和产生效果的前提。 因此,电视剧创作者要尊重创作规律,把握好宣传性和艺术性之间的平衡。 电视剧创作不是“贴标签、喊口号”,而是要用鲜活的人物、精彩的故事、出色的影像语言来诠释宏大和抽象的主题。 优秀的“拼盘剧”必先让观众获得审美体验,才可能让其接受剧作的宣传宗旨和主题意涵。
我们仍以抗疫剧《在一起》为例。 该剧除了上文所述的结构优点之外,还在情节设计、矛盾展开、悬念营造、细节表现等方面颇具匠心,例如其根据每个“拼盘”故事的氛围和基调做相应的影调、色调设计,让画面呈现出某种“电影感”。 正是因为该剧在艺术表现手法上非常用心,所以其才取得了较好的传播效果。 不少观众坦言,观看此剧时常常情不自禁地陷入剧情场景中,忍不住掉下眼泪。 正如某位网友所说,“说它是迄今为止最好的抗疫剧,丝毫不为过”[6]。同样,今年观众热议的《我们这十年》,也是在剧本、表演、摄影、场景设计、节奏、风格等方面颇为用心,让一个个人物故事深入人心,才获得了良好的口碑。 其中《唐宫夜宴》《热爱》《沙漠之光》的主人公在现实生活中都有原型,故事充满了生动的细节,又有曲折的情节,主人公解决困难的过程反映了时代变化的印记。 这种扎根生活、以小见大的创作思路,让十一个故事都从生活细处落笔,通过小切口反映大主题,以小人物折射大时代,也让每一个观剧者能切切实实感受到这十年中的自己。
四、结语
综上所述,“拼盘式电视剧”是中国电视剧对电视剧结构类型的一次创新。 “拼盘式电视剧”有着汇聚多元艺术个性的结构优势,还有着广阔的探索和创造空间,它可以容纳多元风格的共存,同时,相对独立的分段叙事能够更好地支撑剧作主题的艺术表达,在对宏大主题的演绎方面,其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随着采用“拼盘剧”创作模式的优秀剧作不断增多,“拼盘”式结构类型剧或将成为记录国家进步和时代变迁的重要艺术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