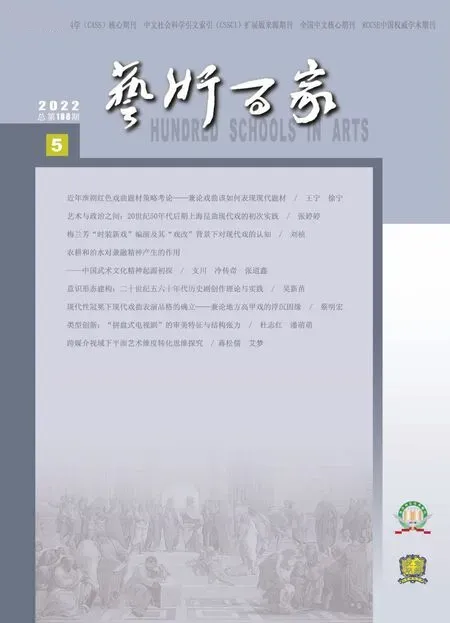中国民族歌剧“本土化”音乐创作的形成路径及启示∗
张婧婧
(南京晓庄学院 音乐学院,江苏 南京 211171)
一、问题的提出
如果从20 世纪20 年代黎锦晖创作的儿童歌舞剧算起,那么直到今天,中国歌剧已经走过了百年的发展道路。 通过《中国歌剧史1920—2000》[1]、居其宏《中国歌剧音乐剧通史》系列丛书①我们可以对中国歌剧发生、发展的历史概况有清晰的了解。 百年来,中国歌剧创作从无到有,我们既可以从纵向上梳理出儿童歌舞剧、小调剧、秧歌剧、话剧加唱型、戏曲音乐型和歌舞型等由简至繁再至多类型并存的中国歌剧历时发展脉络[1]2,也可以从横向上把握当前中国歌剧呈现的“歌舞剧、歌曲剧、正歌剧、民族歌剧和先锋歌剧”[2]9-10五种类型歌剧竞相绽放、新作迭出的繁荣景象。
如果说歌剧是人类“音乐艺术皇冠上的明珠”,那么在中国歌剧百年发展史中,在多种类型歌剧的创作实践基础上,“民族歌剧”无疑是中国歌剧这“皇冠”上那颗耀眼的“明珠”:以“一白一黑”(《白毛女》《小二黑结婚》)、“一湖一江”(《洪湖赤卫队》《江姐》)为代表的民族歌剧所达到的艺术高度、所取得的辉煌成绩,至今仍被人津津乐道。 民族歌剧经典作品不断复排上演,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观众追捧、专家赞誉,其中的经典唱段传唱不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神州上下“人人会唱《洪湖水》,处处齐歌《红梅赞》”的景况时至今日仍有迹可循……可以说民族歌剧中的经典作品是新中国文艺创作发展史上当之无愧的“高峰”。
民族歌剧创排的成功得益于多种因素,其中音乐创作是关键要素之一。 所谓歌剧,即“用音乐展开的戏剧”(瓦格纳语),即以音乐作为主要表现元素和手段来推进情节发展和戏剧冲突,刻画人物形象的舞台艺术[1]7。 所以音乐元素与戏剧元素是其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两个元素。 因此,民族歌剧成功创作的关键在于其音乐创作符合中国观众的审美心理和偏好,具体表现在其音乐创作与民歌、戏曲音乐的有机融合,特别是音乐戏剧性的展开吸收了传统戏曲声腔,以及运用板腔体结构模式创作歌剧人物的唱段,并留下大批经典板腔体咏叹调作品。 那么,这种音乐创作路径是如何形成、发展的? 对如今的民族歌剧创作有何借鉴? 其间积累的音乐创作经验对民族歌剧及其他类型中国歌剧创作实践有怎样的启示? 相关问题成为本文关注的焦点,笔者不揣谫陋,对相关问题作了一些思考,水平所限,文中不当乃至错谬处,恳请歌剧创作者与专家批评指正。
二、歌剧在中国的“在地化”与“本土化”
中国民族歌剧“高峰”的出现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之前有“高原”作铺垫,“高原”的形成也是从起步阶段开始一步一步积累而来,这个过程及表现,“中国歌剧史”相关论著已有详细的梳理。 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笔者进一步提出,歌剧进入中国先经历了“在地化”,在继续发展中又进一步“本土化”。 笔者认为两者的区别在于:“在地化”是外来文化融入本土文化,“本土化”是传统文化融入本土文化。 民族歌剧以民歌、戏曲为基础的音乐创作代表着歌剧“本土化”的完成。
“在地化”是与“全球化”相对的概念,是指在一定疆域内人口、制度、习俗、文化等具有稳定性和恒常性。 “在地化”偏重客观,相对而言是一个被动的过程。②具体到歌剧,作为一种“舶来品”,歌剧在中国的产生、发展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有着密切的关联。 歌剧在进入中国前,在欧洲已经有了四百余年的发展史,有意大利正歌剧、德国歌唱剧、法国大歌剧和喜歌剧、瓦格纳乐剧、维也纳轻歌剧等多种类型,是西方艺术的集大成者。 由于中西音乐形态、音乐文化、审美心理的巨大差异,歌剧在进入中国后,必然经历适应中国人审美心理、欣赏偏好的过程,即“在地化”的过程。 中国最早出现的一些歌剧音乐剧即是这种类型的作品,如《王昭君》(萧梅编剧、张曙作曲,1930),《扬子江暴风雨》 (田汉编剧、聂耳作曲,1935),《西施》(陈大悲编剧、陈歌辛作曲,1935 年)等。 这些早期的作品基本是按照西方正歌剧的音乐思维、体裁形式来创作的中国正歌剧,但其中音乐素材选用自地方民歌。 根据戈晓毅的研究与考证,《王昭君》的音乐创作就取材于粤剧音调和广东音乐,采用西洋美声唱法,乐队编制是以西洋管弦乐器为主、中西乐器混编的小型室内乐队。[3]《扬子江暴风雨》则呈现“话剧加唱式”的歌剧范式,这种范式操作起来比较简单、易行,创作周期短、成本低、易于制作,满足了当时斗争环境的需要,但聂耳在这部歌剧中创作的《码头工人歌》《卖报歌》等唱段独具匠心,且传唱至今。 总体上,早期歌剧作品或是以西方歌剧为框架,或是用“话剧加唱”的简单方式,代表了早期的歌剧创作者在摸索中不断地前进,并且这种探索方式在后世仍有发展,涌现出《伤逝》《原野》《苍原》《雷雨》《诗人李白》等多部优秀的严肃歌剧(正歌剧)作品。
中国歌剧“本土化”偏重主观,是在歌剧“在地化”基础上,进一步深度借鉴中国民歌、戏曲、曲艺中的音乐元素进行创作,并以戏曲板腔体创作主要人物大段成套唱腔为核心特征的。 这一“本土化”过程,萌芽于黎锦晖创作的儿童歌舞剧,如《可怜的秋香》《小小画家》等;发展于“延安秧歌剧运动”,以《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秧歌剧为代表;成熟于“新歌剧”《白毛女》创演的成功。 “民族歌剧”的定名源于“新歌剧”,而“新歌剧”的“新”就已经体现出歌剧创作者在体裁形式、创作手法的底层逻辑和理念上与之前歌剧创作不同,形成了具有自身音乐特色的创作模式。
很多艺术形式开创者的认识、理念和创作思路往往对其后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黎锦晖在创作儿童歌舞剧之初就走的不是西欧各国先搬演再模仿意大利歌剧,而后发展本国歌剧艺术的老路,而是在“在借鉴西洋歌剧的先进经验、继承中国民间音乐和戏曲艺术深厚传统的基础上,坚定走创作中国新型的音乐戏剧艺术之路”,而这一道路“在整体上预示出中国歌剧未来发展的整体路向”[2]18。 黎锦晖有这种认识和创作思路与他自身深厚的民间音乐积累密不可分,他本人“偏爱俗乐,喜唱民歌”,与民间曲艺艺人、戏曲艺人有密切的往来[4]36-38。 因此他在创作中常采用民间小曲、传统曲牌加以创造性改编,如他在《麻雀与小孩》中就使用了【大开门】【苏武牧羊】【银绞丝】等传统曲牌填词,且歌词朗朗上口、通俗易懂,非常适合儿童演唱。 虽然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还有其他仿照西方歌剧体裁形式的歌剧创作,但黎锦晖所开辟的这条道路却在“延安秧歌剧运动”中得以承继并发扬光大。
“延安秧歌剧运动”的开展有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 首先是20 世纪40 年代,一批左翼文艺家涌入延安及各抗日根据地,中国歌剧的创作及演出中心逐渐转移到延安;其次,1942 年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鼓舞了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人民生活,并纷纷进入陕北农村,掀起了学习、挖掘、整理民间艺术的高潮。 其中对陕北秧歌这种民间歌舞形式进行提炼和改造卓具成效,一方面用富有时代气息和生活感的内容简单设置故事情节,另一方面运用专业作曲技法对原始音乐素材进行加工、改编,由此创造出表现根据地革命生活、鲜明人物形象的新型秧歌剧,其中的代表就是被称为秧歌剧“双璧”的《兄妹开荒》《夫妻识字》。 两部秧歌剧的音乐创作取材于陕北民歌和当地的眉户戏音调,在演出形式和音乐创作上较为简单,具有陕北民间音乐典型的形态特征,贴近当地人民群众的欣赏习惯。 而大型秧歌剧《惯匪周子山》则在演出形式、戏剧结构、音乐创作上均有大幅度的扩充,为大型歌剧的创作、为歌剧“本土化”进一步的推进积累了经验。
“新歌剧”《白毛女》的横空出世标志着歌剧“本土化”的完成。 《白毛女》虽然是在秧歌剧基础上发展而来,但初始版本仍未超越秧歌剧的程度和形式③,而是改编成五幕歌剧取得了成功,在戏剧性和音乐创作两方面均达到很高的水平。 戏剧性方面,其取材于晋察冀边区流行的“白毛仙姑”的民间传说,并在此基础上创造性地改编,去除民间传说中封建迷信元素,改为革命主题的现实主义歌剧台本,并且剧本的文学性、戏剧性也达到了很深的造诣。 音乐创作方面,《白毛女》采用戏曲音乐中板腔体和联曲体相结合的方式展开戏剧性:用简短的歌谣体抒发剧中人物简单的情绪和情感,典型唱段如《北风吹》《扎红头绳》等;通过板腔体表现人物激动、复杂的情绪和情感,典型唱段如喜儿的咏叹调《恨似高山仇似海》等。另外在一些吟诵调中《白毛女》也借用秦腔、河北梆子中的板式,利用传统戏曲中的垛板配合吟诵加强戏剧语言的冲击力,如杨白劳《老天杀人不眨眼》唱段等。 从中可见《白毛女》并非对民歌、传统戏曲音乐演奏、体裁形式、音乐结构体制简单的借用、移植或改编,而是根据戏剧冲突、人物形象对民歌旋律、传统戏曲声腔与板式结构作反复、展开、变形、再现。 由此可见其中贯彻了原创性的音乐创作理念,真正符合歌剧“用音乐展开的戏剧”的定义,因此《白毛女》创作的成功标志着歌剧“本土化”的完成。 而“新歌剧”也即被冠以“民族歌剧”,随后这一定名得到理论界和观众的普遍认可并延续至今。
歌剧在中国经历了“在地化”与“本土化”历程,虽然在吸收、借鉴民族民间音乐元素进行音乐创作,展开戏剧性方面有相同的地方,但具体采用的创作理念、体裁形式却有着较大差异,甚至可以说是完全不同的创作路径,这也导致中国歌剧形成了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 居其宏认为中国歌剧划分为五种类型,提出“泛歌剧”概念,李吉提针对此提出了“西体歌剧与民族歌剧”两种类型的歌剧划分方式[5-6]。 笔者认为,西体歌剧、民族歌剧在相当程度上其实对应了歌剧“在地化”“本土化”的两种形成路径,并在当前对应了严肃歌剧(正歌剧)、民族歌剧各自最具代表性的形态,共同推动中国歌剧创作不断向前发展。
三、民族歌剧音乐创作“本土化”的新发展
民族歌剧创作在20 世纪40 年代至60 年代形成第一次高潮,“高峰”作品频现,引领一时风气。 尽管民族歌剧再一次迎来“高峰”已经是三十年后,歌剧《党的女儿》《野火春风斗古城》接续了民族歌剧的“一脉单传”[2]306。 而后有影响力和传播力的作品寥寥无几,文化和旅游部从2017 年开始实施“中国民族歌剧传承发展工程”④,以大力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红色文化为己任,鼓励和倡导大批文艺工作者投身于民族歌剧的创作,展现出了蓬勃发展的创作趋势,涌现出大量凸显中国特色、中国文化、中国精神的民族歌剧作品。 通过全国优秀民族歌剧展演、中国歌剧节等,集中推广具有民族歌剧特色和较高艺术质量的作品,对深入有效地推动我国民族歌剧“本土化”的新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民族歌剧《沂蒙山》《马向阳下乡记》《呦呦鹿鸣》等优秀作品的呈现,昭示着中国歌剧艺术发展步入了新的阶段,展示出民族歌剧旺盛的生命力和创作力。
今天的“新发展”是在创新上的传承,亦是在传承上的发展。 可用李吉提教授总结的民族歌剧音乐创作“三大支柱”来概括:“民族音色”(民族唱法和民乐演奏)、“民族旋律”(来自民歌素材)、“戏曲板腔体”(中国式的戏剧咏叹)。⑤这三大支柱在当前优秀民族歌剧创作中均有所体现,并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动向:民族音色的选用更为多元和宽容,更多服务于戏剧性的展开;民歌旋律的运用偏重凸显地域性音乐文化特色和音乐形态特征;戏曲板腔体继续在主要人物核心唱段创作中发挥基础性作用。
以近年来广受好评的民族歌剧《沂蒙山》⑥为例。歌剧《沂蒙山》取材于抗日战争时期山东沂蒙山地区的真人真事改编,展现“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 民歌素材方面,歌剧《沂蒙山》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如何运用《沂蒙山小调》的问题,作曲家栾凯介绍,他在处理《沂蒙山小调》时,考虑这首广为流传的民歌曲调不仅传唱度高而且影响深远,因此这首歌曲不能不用,但用多了又会冲淡歌剧的原创性。 最终,作曲家将《沂蒙山小调》拆分使用,有机地糅入全剧音乐中,让乐队“在序曲、幕间曲、前奏、间奏中反复出现,进入唱段则使用原创音乐,全剧在最后一首海棠的咏叹调《沂蒙山,永远的爹娘》副歌高潮处才完整出现一次《沂蒙山小调》的旋律变奏”[8]。 可以说这种处理方式时隐时现,反复强调,让观众既熟悉又能听出新意,可谓匠心独运。 《沂蒙山》中除了使用山东民歌元素进行创作,还继承并发展了民族歌剧使用戏曲板腔体创作主要人物核心唱段的传统。 吴可畏撰文指出,在《沂蒙山》剧中夏荷的咏叹调《沂蒙的女儿》和海棠的咏叹调《苍天把眼睁一睁》中,“作曲家在表现剧中人物悲苦状态的时候,均运用戏曲板腔体来创作唱段,这与古典戏曲的音乐气质是十分贴合的”[9]53。 这种音乐创作的理念和方法较为典型体现出民族歌剧创作的特色。 在咏叹调之外,剧中对宣叙调作了技术性处理,叙事段落的唱词采用合辙押韵、结构规整的韵文写成,使其更接近“咏叙调”,更具有旋律性。 这种处理手法也是在民族歌剧不断摸索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并在多部民族歌剧音乐创作实践中得到检验,已经成为叙述性段落唱词较为常用的处理手法。 在民族唱法方面,《沂蒙山》根据戏剧性展开的需要,对民族歌剧唱法进行了多元化的尝试,将不同类型的唱法(民族、美声)和不同的音色(抒情男高音、戏剧男高音和男中音等)有机融合,丰富了民族歌剧音乐创作的表现力和厚度,也实现了歌剧中人物和情节的平衡,满足了当代观众对民族歌剧求新、求变的审美期待。
对于民族歌剧音乐创作的创新,我们应该持鼓励态度,李吉提在《中国民族歌剧音乐创作的得与失(上)——写在歌剧《白毛女》首演75 周年》一文中总结:“如果75 年后还仅守着对歌剧《白毛女》以来创作套路的惯性思路前进、而忽视了对新时代国内外歌剧音乐发展和人们对当代歌剧需求变化的感知,那么,我们民族歌剧创作的道路是不是会走得太过单一和狭窄? 是否从根本上也违背了《白毛女》的创新理念和探索精神?”[5]15这一反问振聋发聩,指出了中国歌剧发展的原动力,值得相关从业者深思。 通过中国歌剧百年的曲折发展道路不难看出,音乐创作的出发点始终是与国家的命运和发展建设紧密相连,在注重音乐艺术性的同时突出了作品的功能性价值。 借鉴欧洲歌剧的创作手法融合具有民族特色的艺术表现形式,实现了时代性、民族性、观赏性、戏剧性的统一。我们应以每个时期不同的审美需求为出发点,通过运用不同的创作手法,积极探索让人民群众接受和喜爱的音乐。
四、民族歌剧音乐创作“本土化”成功的启示
中国民族歌剧音乐创作的“本土化”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下,在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中形成的。民族歌剧创作者在融合古今中外优秀艺术元素方面贡献了高度的智慧,其成功经验为今天继续推动中国歌剧事业的蓬勃发展提供了若干重要启示。
(一)关于音乐融合
民族歌剧音乐创作“本土化”的成功,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就是要立足民族民间音乐文化传统,深入掌握其音乐形态特征与精髓,同时怀有广大的胸襟、高远的格局,不断借鉴、吸收外来优秀的音乐形式、音乐体裁,在立足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发展、创新性转化,使这些引进的音乐形式、音乐体裁能够被国人所接受、喜爱,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事实上,这种吸收外来优秀文化使其不断“本土化”的模式是自古以来中国音乐文化发展的传统。先秦时期的“四夷之乐”不断进入中原,奠定了中国音乐文化的基础;魏晋南北朝西域歌舞涌入,直接推动了隋唐燕乐歌舞的繁荣,营造了这一时期中外音乐交流的盛世景象;宋元之交南北方音乐进一步融合,助推了戏曲艺术形成;明清之际中西音乐交流加强,学堂乐歌开启了“新音乐”;“五四”新文化运动后西方艺术大规模的涌入;等等。 因此,看似歌剧进入中国后的“在地化”“本土化”形成了自己独立的发展路径,但我们把视野拉长,则发现这仍是中国音乐整体发展格局下中外音乐成功交流融合的又一生动实例。
(二)关于音乐创作“本土化”的历史嬗变
其一,创作思路。 欧洲歌剧几百年来的发展历程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创作形式和表演形式。 我国歌剧经历了“在地化”,逐渐形成了民族歌剧“本土化”,这要归功于文艺工作者作为中国歌剧的探索者、实践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把人民群众的喜好和认可放在首位,抒写属于人民的音乐的道路。 一味地“全盘西化”或者“硬套西化”已经不符合社会审美需求,伴随着国家的发展,国际社会地位的提高,强国观日益凸显,即“民族主义”音乐创作导向发展,是我们文化自信和开放观念的体现。 作曲家金湘提出的“歌剧思维”(交响思维)⑦,强调树立总体思维,剧作家、作曲家必须具备综合的素养,将文学、戏剧、音乐、舞台融为一体。 推陈出新,将客观的故事情节、人物情感、戏剧冲突转化为咏叹调、宣叙调、重唱、合唱等音乐形式,呈现“为人民”的“本土化”创作意识,是现代社会需要持续探索的创作路径。
其二,音乐呈现。 歌剧是集音乐、戏剧、舞蹈、美术等各种元素于一身的综合舞台艺术。 早期的音乐创作生搬硬套模仿西方的创作形式,戏剧多以叙事为主,伴有冲突性剧情。 进入新时代,音乐创作逐步突出展现民族特色的音乐元素,在继承戏剧的叙事性基础上,对冲突性、色彩性、抒情性有了更多的重视。 通过音乐和戏剧,进而塑造一个个鲜明的人物形象,这也是音乐创作的首要目的,更是评价一部歌剧打动人心的重要指标,如《呦呦鹿鸣》中诺贝尔奖获得者屠呦呦,《马向阳下乡记》中农科院助理研究员马向阳等,都是舞台上让人记忆深刻的典型化的人物形象。
从中国歌剧创作的体裁看,有完全按照西方歌剧创作模式进行创作的《秋子》,作为我国正歌剧形成的标志,该剧采用美声唱法的同时,通过西方歌剧的形式、题材、创作技法,运用西洋管弦乐队伴奏,呈现咏叹调、宣叙调、间奏曲、叙事曲、舞曲等表现形式;有融合了中国民族民间音乐、戏曲元素创作的《马向阳下乡记》,该剧汲取正歌剧技法,以中国戏曲为基本元素,自然糅合宣叙调、咏叹调、重唱、合唱;也有将中国民族元素与西方作曲技法相互融合的作品《尘埃落定》,该剧为西洋正歌剧模式的民族化,大量吸收、运用藏族民间音乐元素,将宣叙调、咏叹调、重唱、合唱融入作品,并在配器、和声与场景音乐的交响化上做了大胆而成功的尝试。 不论是哪种音乐呈现形式,歌剧的“民族性”都在不断地被强化,体现出讲好中国故事,坚守中国文化,坚定文化自信,传承民族精神的导向。
中国歌剧近百年的发展道路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民族歌剧和中国文化密不可分,“民族性”是歌剧创作必须坚持的。 “人民的歌剧必须以民族风格和民间形式为圭臬。”[10]10“歌剧”,“歌”在前“剧”在后,顾名思义,音乐是歌剧的重中之重,以“歌”为“剧”服务,“剧”与“歌”融合,把音乐写得让听众记忆深刻和喜爱,这部歌剧就成功了一半。
其三,社会功能。 纵观中国歌剧百年的发展脉络[11]:20 世纪20—40 年代初,中国歌剧的萌芽期和探索期的作品更多地体现了民主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麻雀与小孩》等);20 世纪40—50 年代,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新秧歌运动推动发展了一批以时代为背景,弘扬革命精神的秧歌剧(《兄妹开荒》《白毛女》等);20 世纪50—70 年代,中国歌剧进入新中国成立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多元化时代,戏曲板式歌剧如《红珊瑚》《王贵与李香香》等,民间歌舞剧《刘三姐》等,借鉴西方大歌剧手法和元素创作的《阿依古丽》等,兼容西方创作手法,融合中国戏曲板腔体结构而创作的《洪湖赤卫队》《江姐》等,都以坚定民族信仰、贴近群众生活的角度进行音乐创作的呈现;20世纪80—90 年代,在外来艺术和审美的渗透、相互交融下,音乐创作有了分化,有沿袭西方正歌剧形式的创作如《伤逝》《原野》等,也有积极探索融合中国特色“本土化”的音乐创作如《从前有座山》《党的女儿》等,创作者在“民族性”的道路上探索前行;2000年至今,随着国家的强大和国际地位的提高,歌剧创作的社会需求也更加清晰。 在坚守民族特色的前提下,新时代民族歌剧的音乐主题、音乐创作更加多元化,个性化,用不同类型的作品传递着正能量和时代价值观。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衡量一个时代文艺成就最终看作品。 推动文艺繁荣发展,最根本的是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中国歌剧的社会需要被推向了一个新高度,在人民需求和政策的扶持下,中国歌剧发展进入了繁荣期。 一方面讲好中国故事、中国文化能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和推广;另一方面民族歌剧的创作紧随时代脚步,蕴含着鲜明的“红色基因”,传递民族精神,传播理想信念,引导一代代中华儿女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三)关于民族歌剧的形成
民族歌剧音乐创作通过长时间的摸索与实践,找到了一条道路,其以吸收民族民间音乐元素、传统板腔体戏曲结构体制为基础,但主导型创作思路是运用西方歌剧主题贯穿发展手法来展开戏剧性。 正如居其宏指出的,“《白毛女》音乐整体戏剧性思维的最大特色,则是在如何对待中外音乐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发展问题上遵循科学态度和辩证思维,创造性地合理兼用西方歌剧主题贯穿发展和我国传统戏曲中板腔体相结合的方式来展开戏剧性”[7]。 这种结合强调原创性的音乐创作,与传统戏曲套用固有的联曲体、板腔体结构进行的创作,在根本逻辑上形成了差异。 因此民族歌剧这种音乐创作实践不仅继承了民族民间音乐和传统戏曲创作的传统,而且还在此基础上推动了这些传统进一步发展。
虽然中国民族歌剧呈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蓬勃发展趋势,但在这背后我们不得不承认依然存在着诸多发展困境和挑战。 作品选材局限,缺乏创新,观众喜爱度不高,作品功利性强,艺术质量不高,国际影响力不足等,均值得我们深思。
五、结语
歌剧在中国的落地、生根可以说是“中国艺术由传统型向现代型、由民间型向专业型战略转轨的产物”[12]5-8。 当然这一转型、转轨并非一蹴而就,中间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形成了多种丰富的歌剧类型,这一过程可以通过“在地化”“本土化”两种类型进行观察,表现为西体歌剧、民族歌剧两大主要类型。 两种类型的创作在音乐创作底层逻辑和理念方面有根本不同,但民族歌剧无疑代表了我国歌剧创作的最高水平,并可以屹立于世界歌剧艺术之林。
时至今日,歌剧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艺术发展水平的重要参照标准。 但相较于经典民族歌剧达到的“高峰”,目前我国民族歌剧的创作虽有“高原”,亦不乏亮点,但距离“高峰”仍有不短的距离。 正如习近平主席在文艺座谈会上指出的,我国文艺创作在改革开放之后虽然也有脍炙人口的作品,但同时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 习近平主席指出的这些问题是切实存在的,需要我们引起高度重视。
近年来,中国歌剧的发展拉开了新的篇章。 国家艺术基金的设立,2017 年文化部召开“中国民族歌剧创作座谈会”,设立“中国民族歌剧传承发展工程”,评选民族歌剧重点扶持剧目等举措,从政策导向、资金支持、演出支持等多个方面为中国歌剧的发展提供支持和保障。 希望民族歌剧创作沿着此前形成的优良传统,在未来有更好的发展。
① 由居其宏担任总编撰的《中国歌剧音乐剧通史》丛书包括:《中国歌剧音乐剧创作历史与现状研究》《中国歌剧文学特性历史审视与美学视野》《中国歌剧音乐剧理论思潮发展与嬗变研究》《中国歌剧音乐演出历史与现状研究》《中国歌剧音乐剧生存现状与战略对策(咨询报告书)》;另有3 册唱段精粹,《中国歌剧音乐剧唱段精粹·美声唱法卷》《中国歌剧音乐剧唱段精粹·通俗唱法卷》《中国歌剧音乐剧唱段精粹·民族唱法卷》;DVD《中国歌剧音乐剧场面精粹》(共3 盘)。 丛书内容囊括中国歌剧音乐剧近百年历史发展进程、创作思潮、美学品格、风格样式、文学特性及表导演艺术、专业团体艺术生产模式和生存现状等,对中国歌剧、音乐剧的发生、发展做了全景式展示。
② “在地化”“本土化”的意涵及对应的“客观融入当地”“主观融入当地”参考自读秀“在地化”词条。 笔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发,认为“在地化”是一个被动过程,“本土化”是一个主动过程。 参考词条地址:https:/ /book. duxiu. com/EncyDetail. jsp?dxid= 403694259675&d = EF11854F3AD08173B1CA6A8A00236 41F&stitle=%E5%9C%A8%E5%9C%B0%E5%8C%96。(2020-4-25).
③ 《白毛女》最初版本的艺术面貌较为陈旧,曾走过弯路。 根据《中国歌剧音乐剧创作历史与现状研究》,《白毛女》最初主创团队创作的“剧本采用朗诵诗剧文体,音乐创作依据秧歌剧经验以现成的秦腔、眉户调配曲,表演上则参照戏曲模式”。 由此可见其初始版本仍未脱离秧歌剧的形式。(居其宏《中国歌剧音乐剧创作历史与现状研究》,第44 页)
④ 文化部从2017 年开始对民族歌剧的创作、生产、普及推广、人才培养、理论研究等进行扶持。
⑤ 李吉提教授除了总结出民族歌剧音乐创作的“三大支柱”,并对这三方面有详细的阐述:民族歌剧讲的应该是中国故事,采用民族唱法,突出民族乐队音色。 作曲技术则表现为凸显中华民族语言和音乐风格腔调、韵味,尊重中国人偏爱旋律表述的审美习惯。 其音乐的陈述方式也与中华民族的民歌、戏曲关系更为密切。 小型或轻型的歌剧可能具有一定的民族歌舞风格特点,而大型或戏剧化程度高的作品,其音乐的陈述结构中则可能汲取大量的传统戏曲演唱套路(如板腔体“散一慢一中一快一散”的速度布局之类)以更方便地揭示戏剧矛盾冲突。 此外,在歌剧的舞美和演员的舞台表演、身段等,也常采用中国人所熟悉的歌舞、戏曲表情程式而有别于西方。 详参:李吉提《中国民族歌剧音乐创作的得与失(下)——在温故知新中寻求发展之路,第12 页。
⑥ 《沂蒙山》由山东省委宣传部、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临沂市联合出品,山东歌舞剧院创排的大型民族歌剧。 栾凯作曲,王晓岭、李文绪编剧,黄定山导演。
⑦ “歌剧思维”,是作曲家金湘从事歌剧音乐创作多年,经过长期实践与思考提出的一个美学理念,强调在创作伊始就要树立总体性思维,既要科学对待音乐与戏剧的关系,又要正确联合作曲、编剧、导演三大核心人物,实现三位一体,共同构思与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