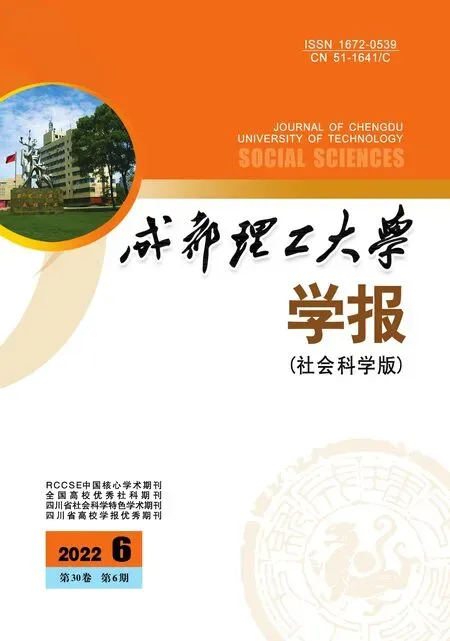符号·生命·幻象
——苏珊·朗格论艺术的表现方式与生成机制
赵 洁
(浙江大学 外国语学院,杭州 310058)
从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提出“数理形式”开始,形式这一概念便进入西方美学漫长的发展谱系当中。古希腊时期的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分别提出“理式”与“形式因”,将形式看作美与艺术的本体存在方式,其所体现的“一元论”逻辑成为18世纪康德美学中“先验形式”的思想来源。古罗马时期的贺拉斯提出“合式”概念,将形式与艺术看作对立因素,这一“二元论”思想又影响黑格尔将形式看作绝对理念的相对范畴。20世纪以降,语言哲学、心理学的发展推动形式美学迎来又一次发展高峰[1]9-22。俄国形式主义与英美新批评所关注的“语言形式”、结构主义关注的“结构形式”、心理分析关注的“意识形式”共同拓展了形式美学的存在样态。这一时期,多种理论形式的繁荣也引发了其对艺术本质的争鸣与再阐释。
面对艺术领域中形式论与表现论的分野,以德国哲学家厄恩斯特·卡西尔与朗格为代表的符号美学提出了“符号形式”概念,试图将人类情感与艺术形式综合在一起。在20世纪形式与艺术渐趋分离的二元困境中,朗格将整体性精神作为艺术哲学的基本诉求,体现了她对形式与艺术“一元论”观念的继承与坚持。对此,有研究者指出,“朗格美学理论建构的真正哲学基石是现代文化整体观,她以卡西尔的符号学理论作为自己艺术哲学思想展开的关键词,对20世纪西方美学进行了一次整体性重构”[2]。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国内对朗格的研究从符号美学思想的解读延伸到其与中国美学思想的比较方面,大体呈现出从 “本体研究”到“接受研究”的迁移趋势。已有研究也敏感地关注了朗格符号美学的整体性特征,但对其艺术存在形式的整体性观念却鲜有涉及。对此,本文由表及里对朗格符号美学中的艺术表现和艺术本质进行探讨,深入探究艺术的生成机制,尝试揭示其艺术符号美学的思想精要。
一、符号:艺术的情感表现
朗格曾在《情感与形式》(1)中提出自己的核心艺术观点——艺术,是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的创造[3]51。朗格将艺术看作以人类情感为质素、以符号形式为外显的统一综合体,而在朗格之前,卡西尔便已在此方向作出尝试。这位新康德主义的代表人物,被誉为“柯亨最优秀的学生”,发展了康德对艺术的判断,并将艺术研究的方向从理性批判引向文化批判。康德曾在其著名的“三大批判”中,将人的情感能力看作“反思性的判断力”,以美、崇高、艺术为主的审美判断力和目的论判断力共同构成了反思性的判断力。他认为,艺术的目的是表现美,实现社会情感的普遍性,使人的审美愉快(即共通感)经验地传达出来。卡西尔沿着这一思路,进一步认为艺术并非对经验给定之物的被动表现,而是包含了一种确定的意义,获得了特殊的观念化的内容[1]381。用卡西尔自己的话说,“它们创造出了自己的符号形式”[4]210。语言、神话、艺术、宗教等都是“人性”这个圆周的扇面,由它们构成的文化体系是人类精神纯粹表达的世界[4]212-213。换言之,卡西尔将“符号”作为人类精神与形式之间的中介物,认为“一切符号形式都是人类精神的产物”[1]386,并将艺术世界定义为符号世界。由此,卡西尔沿着康德“理性批判”的道路进一步开始了“文化的批判”,并确立了人类精神的“赋形原则”。
1946年,朗格翻译了卡西尔的《语言和神话》。1953年,其又在《情感与形式》的扉页上写道:“谨以此书纪念厄恩斯特·卡西尔。”正因朗格在思想上对卡西尔的人类文化符号学的观点有所继承,西方学界以“卡西尔-朗格符号论”命名了这一艺术符号美学流派。朗格接受了卡西尔的“赋形原则”,并对符号进行定义——符号是我们用以抽象的某种方法[3]5。朗格认为,在人类的全部本能中,本能的智力活动就是符号活动。与符号相比,信号是事件的一部分,可以指称确定的事物,具有一一对应的关系。而符号是概念的媒介,是具体客体抽象之后的产物,并非事件的代指,它的内涵是事物之间的逻辑关系。符号不仅包含了主体、信号、客体三个要素,还包含了“概念”。其他动物只能识别信号,人却可以进行复杂的符号活动,并通过符号的抽象作用为人类的情感赋予形式,这就是人与其他动物的本质区别。
除了卡西尔外,维特根斯坦前期的逻辑哲学语言观也深深影响了朗格。维特根斯坦认为,世界是由客体及其之间的逻辑关系构成的,语言通过描述客体、表达逻辑关系来传递世界的意义。然而问题在于,语言符号具有线条性、历史文化性和概括性的特点,不能完全准确地表达人的情感感受[5]。而且,并非只有可阐述的东西才能被真正感知到。因此,逻辑语言不是万能的,它不能表达的部分正是艺术表达的开始。意识到这一点后,朗格区分了以艺术为代表的表象性符号与以语言为代表的推论性符号,认为推论性符号用以表现理性领域内清晰确定的抽象原则与概念的形成过程,表象性符号表述人类感性领域内难以名状的内心情感与生命体验。由此,朗格在艺术对情感的表象性作用中确定了艺术的表现性特征。
朗格强调,艺术表现就是对情感概念的呈现或显现[6]120。它是所有艺术的共同特征[6]13,也是艺术的主要功能[3]80。换言之,艺术的表现性原则使符号勾连情感,使形式具有意味。同时,艺术形式与我们的情感生活同构,二者体现出逻辑类似的关系。朗格指出,逻辑形式是一种可以抽象出来的概念[6]18。艺术是一种抽象的表现性符号,对情感的符号表现催生了艺术形式的生成。因此,艺术品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就是情感的意象,朗格将其称为艺术符号[6]129。艺术符号的每个成分都不能离开符号本身而单独存在,但艺术中的符号代表不同的意义,作为作品的组成部分参与了作品的形式构成,是表现性形式的构成成分,不是整个艺术品传达的“意味”的构成成分[6]131。由此说明了艺术符号与艺术的符号之间的区别——艺术符号是将经验客观化或形式化,后者仅仅是普通符号[6]134。
在卡西尔符号学思想的启发下,朗格将艺术看作表象性的符号,认为它表现的正是语言这类推论性符号无法阐明的情感与生命。同时,她受到克莱夫·贝尔的启发,将艺术形式看作“有意味的形式”,指出了它与生命的逻辑类似关系。由此,朗格厘清了艺术、符号、形式之间的关系——艺术是以“活的形式”传达生命现实这一概念的符号手段[3]97。
二、生命:艺术的终极观照
朗格将符号与形式看作艺术的表现手段,通过抽象作用探讨了情感与形式的对应关系。但在朗格的艺术哲学中,情感与生命发挥了更为核心的作用。早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便认为诗歌是对情感的模仿,18世纪的康德将艺术看作人类审美判断力的主题之一,认为艺术在本质上诉诸人的情感能力。19世纪的浪漫主义思潮也十分注重艺术对个体情感的表现作用。朗格继承了西方美学将艺术看作情感表现的古典观念,认为艺术可以表现情感。但其思想又与过去美学史上强调艺术表现情感的“表现论”有所不同。以克罗齐与科林伍德为代表,他们认为艺术表现的是艺术家的个人情感,即“自我表现”。朗格却认为,艺术品表现的是关于生命、情感和内在现实的概念,它既不是一种自我吐露,又不是一种凝固的个性,而是一种较为发达的隐喻或一种非推理性的符号,表现的是意识本身的逻辑[6]25。朗格质疑了“自我表现”说的情感指涉范围,认为艺术家表现的不是个体体验的瞬间情感,而是经过抽象之后人类的普遍情感,亦即一种“广义的情感”,是任何可以被感受到的东西[6]14。
为了更为清晰地表达自己对于艺术情感的定义,朗格提出了“内在生命”(inner life)的概念。她认为,“我所说的内心生命,是指一个人对其自身历史发展的内心写照,是他对世界生活形式的内在感受”[6]7。艺术表现的情感是主体面对客观现实时表现出的感受,它既是一种感觉能力,也是有机体活动的一个方面,而不是生命活动的结果,甚至“生命本身也就是感觉能力”[6]7。艺术要表现情感,就是表现有机体生命活动最本质的部分。由此,朗格既界定了艺术表现的情感范围,将自我的瞬时情感扩大为人类的普遍情感、生命的整体经验,也将感发性感受和接受性感受结合起来,共同组成了感受的范围[7],还通过艺术形式与生命活动之间的逻辑对应关系,确定了艺术表现方式。甚至可以说,朗格确定了一种艺术表现原则与标准:“如果想要使得某种创造出来的符号激发人们的美感,它就必须以情感的形式展示出来,必须使自己作为一个生命活动的投影或符号呈现出来,必须使自己成为一种与生命的基本形式相类似的逻辑形式”[6]43。
朗格进一步阐明了有机体生命形式的特征。她认为,有机体具备动力形式、有机结构、有节奏的组合、特殊的发展规律这四个特征[6]49。具体而言,生命的运动是永恒的,表现生命感觉的符号形式也由此获得了一种永恒的生长性与运动趋势。自然界的有机体为了保证生命获得延续,必然要进行同化活动与新陈代谢活动,二者交替进行使生命体呈现出永恒的、纯粹的动态形式。同时,运动催生了节奏的产生,有机体所有的活动都是有节奏的活动,从心跳、呼吸到生存,无不具有节奏性。再者,有机体必须是整体统一的,任何一个有机体都不可能靠单独器官成活,除非有机系统协调配合,因此生命活动是有机的。最后,有机体都在生长活动和消亡活动的平衡中获得成长,呈现出不断发展的规律。
在此基础上,朗格强调了艺术与生命之间的逻辑类似关系,并指出“艺术形式与我们的感觉、理智和情感生活所具有的动态形式是同构的形式”[6]24。艺术形式将情感生命转化为表现内容时,一并继承了情感生命原有的内在逻辑。她进一步阐释道:“你愈是深入地研究艺术品的结构,你就会愈加清楚地发现艺术结构与生命结构的相似之处。正是由于这两种结构之间的相似性,才使它们看上去像一种生命形式,使它看上去像是创造出来的。”[6]55换言之,艺术作为一种表现形式,就是运用符号的方式把情感转变为诉诸人的知觉的东西,将主观经验形式化、客观化。人们甚至可以从中感受到生命力的张弛,或者毋宁说,艺术就是一种生命形式[1]393。这一论断在两层意义上证明自身:其一,艺术的形式是从生命情感中抽象得到的;其二,艺术在成型后也具备生命形式的特征,从而具有了超越客观现实的审美内涵。
那么,一件优秀的艺术作品应具有何种生命形式的特征呢?朗格认为,它包含动态性、有机性、节奏性、成长性这四个特征。举例而言,一首经典诗歌作品,每一个词句都构成了它的有机整体性。如果艺术家要对部分不足之处进行更改,那便意味着作品的“整体意味”将被改动,新的审美形象又会生成。诗句语言创造出独特的艺术魅力,语言的韵律与张力就是它的节奏性。节奏会产生动态的艺术效果,使人读来仿佛感受到它的生命力在不断流动、成长。因此,诗歌艺术作为艺术的一种,具有生命形式的上述特征。其他艺术领域,也是如此。朗格将艺术看作生命形式,使得她的艺术符号美学呈现出生命本体意义上的亲切关怀。
值得注意的是,朗格将情感与生命看作艺术本质的做法,植根于彼时的现实基础。当分析理性、工业制造、资本主义市场交换为西方现代美学话语模式的构成提供了三股基本力量时,人的精神领域却成为无法踏入的禁地。如何在现代性视野中关怀生命与情感,是当时十分紧迫的美学诉求。在生命哲学的视阈下,生命的发展与转化过程形成了历史,孕育了艺术,使“表现”获得了生命的根基。这为朗格提供了启迪,她认为人类的情感通过艺术得以保存,并超越时间与历史成为永恒,而人类又通过直觉性的艺术知觉来把握艺术品中的情感特征。因此,艺术深入人生,为情感赋予形式,保存且传达了人类共有的情感体验。正是在情感的维度上,艺术参与了文化历史的建构。此时,朗格对艺术与生命关系的探讨,使形式从静态的审美层面上升到现实的历史层面,摆脱了以往将形式自封于艺术领域而难以面向历史的困境。
三、幻象:艺术的生成机制
朗格将情感与生命看作艺术的本质,但如何使其本质借由形式体现仍是一个的问题。实际上,朗格将艺术形式看作表象性符号的思想暗含了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法。朗格以符号的抽象性特征为情感赋形,抽象性原则即成为艺术生成的关键原则。朗格认为,艺术并非对情感的刺激和净化,而是情感的表现,而最成熟的艺术表现手法就是那种导致高度感性显现的非语言抽象能力[6]103。在这一点上,朗格的导师——英国哲学家、数学家怀特海给了她极大的启发。
1927年,朗格师从怀特海并开始符号逻辑的研究。怀特海是过程哲学的代表人物,认为宇宙具有动态的、整体的形式,世界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即“过程就是实在,实在就是过程”,整个宇宙就是由各种事件、各种实际存在物相互连接、相互包含而形成的有机系统。自然、社会和思维乃至整个宇宙都是活生生的、有生命的机体,处于永恒的创造和进化过程之中[8]。同时,怀特海也十分强调在哲学研究中运用数学的抽象原则。受怀特海的启发,朗格十分注重符号逻辑所要求的抽象思维能力,但她并非直接将科学中的抽象原则运用到艺术研究中。朗格特别指出,艺术表现的是人的感性世界,艺术抽象的形式是表现动态的主观经验、生命的模式、感知情绪的复杂形式[6]168。因此,艺术所需要的抽象与科学或语言所需要的抽象十分不同,艺术抽象是对形式或结构关系的认识方法。朗格将艺术抽象看作艺术创作的前提,她认为,每一件真正的艺术作品都有脱离尘寰的倾向,它所创造的最直接的效果,是一种超越现实的“他性”(otherness)[3]55。他性既指艺术对现实的超越,又指艺术的幻象性和符号性。正因他性,艺术才具有情感教育功能[9]。在此基础上,朗格提出了著名的“艺术幻象”理论。
朗格将基本幻象看作形式领域的基础,认为它包含在虚幻形式的发生当中。基本幻象以不同的方式决定了不同的艺术领域[3]101。换言之,基本幻象的建立正是艺术门类的区分依据。与此同时,一种艺术也可以体现出多种艺术的特征,正如诗歌可以具备音乐性,文学也可以具备诗的语言。各种艺术门类之间并非相互孤立、互不交融,它们之间可以发生互渗现象。朗格将这种适用于各门艺术之间交叉关系的无所不在的原则称为同化原则[6]81。凭借这种同化原则,朗格进一步指出了二级幻象的存在——基本幻象决定艺术作品的真正本质,二级幻象赋予艺术创作以丰富、灵活和广泛的自由[3]137。朗格通过艺术抽象原则与艺术幻象理论揭示了艺术的生成机制,为了更系统地搭建艺术符号美学体系,她详细地论述了不同艺术的基本幻象。
在朗格看来,绘画、雕塑与建筑的造型艺术创造了不同形式的空间幻象:绘画取材于生活景象,在平面世界里创造了虚幻的景致;雕塑凝聚着拟人化的幻想,创造的是虚幻生命体;建筑则构建了不同人的生活场所和文化范围,创造的是种族领域的想象。可以看出,朗格不仅以幻象的方式囊括了艺术的空间问题,使现代性的空间概念投射于艺术领域中,也以十分幽微的方式回应了艺术与现实的关系。如果建筑创造了种族领域的边界幻象,那么艺术也具有隐含的政治立场。这一看法在种族问题频发的美国具有微妙的现实指向性。
同时,朗格也探讨了音乐的基本幻象。早在朗格之前,就有许多哲学家将音乐看作最为直观地表达情感的艺术手段。19世纪“绝对音乐”概念的提出更是从音乐的自足性中确证了艺术形式的自足性,进而表明了音乐在艺术中的独特地位。朗格在这样的艺术传统中,也将音乐看作艺术符号形式的典范。她指出,“生命的、经验的时间表象,就是音乐的基本幻象”[3]128。与造型艺术创造的空间感相对应,音乐的绵延是一种时间意象。它中止了一般意义的时间,展现一种生命片段,使时间可听,使时间形式连续可感,使人的情感贮藏在音乐中。而且,伟大的音乐也会创造出气势磅礴的空间感,在时间幻象内出现的虚幻空间可以看作音乐的二级幻象。与音乐相关的舞蹈以虚幻的力作为自己的基本幻象,它是由虚幻的姿势创造的力量和作用的表现[3]200。舞蹈通过虚幻的力表达强烈的情感体验,将主观意志具象化。此处的力不同于物理世界的直接作用力,它是一种强烈的自我意识,是对异己的反抗,是顽强意志的主观体验[3]373。如果说舞蹈对个体生命的展现及主体精神的张扬指涉的是审美现代性中非理性的面向,那么朗格则通过对舞蹈幻象的阐述反证了以主体创造与表现为核心特征的现代主义美学主张。此外,朗格还探讨了语言艺术的基本幻象。在她看来,诗人创造了纯粹完全的经验形式,这种纯诗生成了虚幻生活的幻象。由于诗歌在语言艺术中具有统率地位,其余的语言艺术形式,诸如文学、电影、戏剧等则以不同的语言形式发展了虚幻生活的不同面向:文学创造的是虚幻的过去,它以虚构的历史采取了记忆的表达方式,是一种回忆的模式[3]306;电影创造的是虚幻的现在,以模仿白日梦的方式将人们带入虚幻的当下,并在当下的映现中成就自身;戏剧采取了命运的模式,创造的是虚幻的未来[3]356。其中,喜剧展现了自我保护的生命力节奏,悲剧则展现了自我完结的生命力节奏[3]406。朗格以文学、电影和戏剧对应了虚幻生活的不同阶段,所秉持的分类依据是各种语言形式的生成机制与呈现方式。尽管这种分类呈现出新意,但稍加思索便可发现,这种机制主要滋生于古典传统,对其后的语言艺术发展很难发挥出合理的阐释性。如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正是以描摹虚幻的当下的方式发挥自身的批判性,若在朗格的幻象体系中看待现实主义文学,则会在相当程度上削弱它的价值。
明晰了艺术生成所需的艺术抽象,也阐述了艺术创作所追求的艺术幻象,朗格还关注了艺术鉴赏的问题。朗格认为,艺术家通过艺术品将人类的情感客观地表现出来,而欣赏者需要艺术知觉才可以把握、读懂艺术品。所谓艺术知觉,就是对艺术品的表现性的知觉。情感不是再现出来的,而是由符号排列和组合起来的幻象表现出来的,在符号中把握和发现这种情感的能力就是艺术知觉。对于艺术品的欣赏者而言,这是一种顿悟力或洞察能力[6]57。受到德国格式塔心理学家鲁道夫·阿恩海姆的启发,朗格指出了艺术知觉的最先步骤——直觉。在朗格之前的柏格森看来,生命冲动的绵延和创造是直觉的,对世界的感悟也是直觉的。直觉以生命的表现为目的,不仅是审美经验生成的前提,还是生命延展的动力源泉。因此,在以分析理性为内核的现代社会,直觉是作为其对人的压抑的反面出现的,艺术家通过形式将生命的直觉过程展现出来。
无疑,柏格森对直觉的论述启发了朗格,但朗格也在此基础上发展了自己的直觉观。她将直觉看作基本的理性活动,认为“它包含着各种各样形式的洞察,与真假无关,只与事物呈现的外观有关。对艺术表现性的知觉就是一种直觉”[6]62。艺术的直觉是一种原始逻辑经验,从一个完形的知觉开始,对艺术品整体内部的组成要素进行识别[6]159。当直觉完成,人的意识会自动开始对艺术品的整体知觉。因此,艺术鉴赏的第一步需要理性的直觉与完形的艺术知觉。
至此,朗格从艺术创作的角度,以艺术抽象与艺术幻象理论揭示了艺术的生成机制,指出了不同艺术门类的主要特征,也从艺术鉴赏的角度,指出了欣赏者所需的直觉与艺术知觉能力。不仅如此,朗格的理论还强调了艺术教育的功能与艺术治疗的积极意义。可以说,朗格的艺术符号理论涵盖了艺术创作、鉴赏、教育等各个方面,具备了一种整体性的品格。
四、结语
苏珊·朗格的艺术符号美学涉及了众多的艺术领域。她综合地吸纳了卡西尔与怀特海的哲学思想、贝尔的美学思想以及阿恩海姆的心理学思想,将以情感为主的表现论与以符号为主的形式论糅合起来,也将逻辑的力度与历史的深度统摄起来,完成了对艺术存在方式的整体性考察。她所建构的符号形式的哲学美学体系是19世纪西方美学领域“语言转向”的延续和推进,使艺术被界定为符号语言。[10]同时,也有评论家指出,朗格的符号美学思想实际上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论形态,一种是本文所着力论述的表现性理论(Expressive Theory),另一种是可感知性理论(Perceivable Theory)[11]。前者引导人们关注艺术的形式,后者引导人们关注艺术所蕴含的情感。虽然两种理论形态不一,但也并非完全抵牾,可以同时存在于一种艺术当中。正如一座宏伟的教堂在表现性理论层面通过教堂尖顶暗含了人们对上帝的无限接近,在可感知性理论层面又将上帝的影子投在街道上,从而展现出人们对基督教的信仰。以此为例,正因朗格的符号美学思想展现出整体性、多领域、全方位的品格,具备了面对同一艺术的不同阐释路径,它才能以更宏阔的视野深入具体的艺术问题中去,发挥出更大的阐释效度。
注释:
(1)已有学者对苏珊·朗格的《情感与形式》中“情感”(feeling)一词的译法进行修正,认为此译法易与emotion、affect等词造成混淆,因而改用“感受”一词。因本文采用早期译本,故而继续沿用“情感”的译法。为避免用词混同,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