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书在旁,从不孤单
朱彩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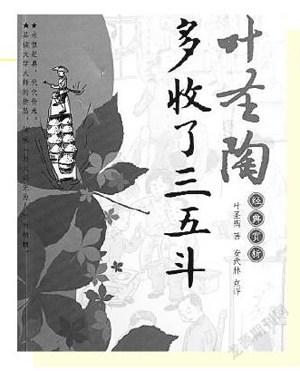
毕业于华南师范大学,潮州市瓷都中学高中物理老师,从教二十年。
从小,我喜欢看书,一书在手,其他都不管不顾了,一门心思尽快把整本书看完。用妈妈的话来说,没书时我爬墙爬树,比男孩还野,捧着书的我则半天不动,像个小木偶。
最初看连环画,有《永不消逝的电波》《霍元甲》《少林寺》等影视热门,也有《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异》《隋唐演义》等古典名著。虽然不识字,看着画面,回想相关的电影电视或者老人讲过的故事,连猜带蒙,意兴盎然。那时候,全村的连环画我基本都看遍了,善良的乡亲若是买了新的,纷纷招呼我一声。
1985年上坡尾小学后,小小的校图书室,是我幸福的小天地。庄天、刘禄侯等语文老师不嫌麻烦,对我十分爱护,允许我借作文选回家细看与摘抄好词好句。
1989年,我转去了石鼓小学,学校图书馆的藏书更丰富了,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365夜童话等,让我如痴如醉。郑渊洁的《童话大王》更是深得我心,皮皮鲁和鲁西西这对性格迥异的双胞胎兄妹相爱相杀、共同冒险,小老鼠舒克和贝塔开着飞机闯荡世界……那时候,小小的我,开始相信,只要有梦想,只要敢闯荡,就可以拥有更广阔的世界。
弟妹正值好奇心旺盛的时候,总缠着周末放假回家的我讲故事,每天至少六个。
一个又一个童话故事后,弟妹紧紧盯着我不放:
“然后呢?”
“还有呢?”
为了满足弟妹的好奇心,我自己硬着头皮,现编现讲,怎么有趣怎么来,将他们最感兴趣的长袜子皮皮故事又延续了半学期,乐得他们哈哈大笑。
书,仿佛是一叶小舟,将我从贫苦简朴的农村生活,载到了丰富多彩的另一个世界。
1991年,我考上高州中学。高州中学学风鼎盛,提倡好读书、读好书,一日三读——早读、午读、晚读,各种读书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
学校的阅览室摆满了各种杂志报刊,课后总坐满了同学,跑慢一点的同学只能站着看。
学校图书馆则成了我最向往的地方,还书、借书、看书,成了我周一活动课的三部曲。同学们笑说我恨不得住在图书馆里。
我的确恨不得把所有书都看一遍,如饥似渴地阅读《野火春风斗古城》《红岩》《青春之歌》《高山下的花环》《边城》《基督山伯爵》《飘》《汤姆叔叔的小屋》等。书里不仅有夸张的想象与繁华的新世界,还有沉重的苦难和强硬的脊梁,机智勇敢的李金环、稳重坚贞的江姐、三度决裂的林道静、天真活泼的翠翠、永远彪悍面对明天的斯嘉丽等一系列女性更是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的语文老师张洁,年轻优雅,打扮时尚,会弹吉他,是很多同学心目中的女神。她上课时声情并茂,有時候又很调皮。
我至今仍记得上叶圣陶《多收了三五斗》时,张洁老师仿照柜台上的账房先生,夹着一支粉笔的手按着课本,从眼镜上边透出鄙夷不屑的目光来:“乡下曲辫子!”
全班哄堂大笑。
张洁老师没有笑,依旧一脸冷淡:
“一块钱钞票就作一块钱用,谁好少作你一个铜板。我们这里没有现洋钱,只有钞票。”
全班突然安静下来,在张老师冷淡的语气与不变的鄙夷眼神里,感受到粜米旧毡帽朋友的满腹心酸和无奈。
每次两节连堂语文阅读课,更是我们的快乐时光,有时主题阅读,有时话剧角色扮演。更多时候张洁老师从图书馆借来一堆文学名著,每人随机分一本,阅读,然后挑一个点,写读后感。
有同学凑巧分到不喜欢的苏联大部头小说,要换一本。
张洁老师说不同的书有不同的营养,每一本书都有自己的价值,别先入为主拒绝它。
那时候的我,看书贪多求快,哗啦啦地翻书页。张洁老师课后劝我:
“看书不能只图痛快,要静下心来细嚼慢咽。”
我举起手中的笔记本,说自己也有摘抄好词好句。
“摘抄了等于看了?品味到词句背后的意思与作者的意图了?有自己的看法与观点了吗?”
张洁老师细声细气的三连问,让我无言以对。对呀,别人的东西再好,没真正消化吸收,始终是别人的。
读书百遍,其义自见,放慢速度,认真品味一本书,我留意到了许多曾经忽视的细节。从浮光掠影的猎奇与简单的摘抄好词好句,再到记录自己读书感想思考,灵活运用到作文中,我感受到了读书的乐趣,作文经常被评为范文,诗歌与散文也不断发表到学校希望文学社刊物上。
如今,张洁老师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八年了,我人到中年,杂事繁多,每当拿起一本书沉浸在书的世界里,总会格外平静、舒展。
良师在心,好书在旁,阅读路上从不孤单。
文摘
“先生,给现洋钱,袁世凯,不行么?”白白的米换不到白白的现洋钱,好像又被他们打了个折扣,怪不舒服。
“乡下曲辫子!”夹着一支水笔的手按在算盘珠上,鄙夷不屑的眼光从眼镜上边射出来,“一块钱钞票就作一块钱用,谁好少作你们一个铜板。我们这里没有现洋钱,只有钞票。”
——叶圣陶《多收了三五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