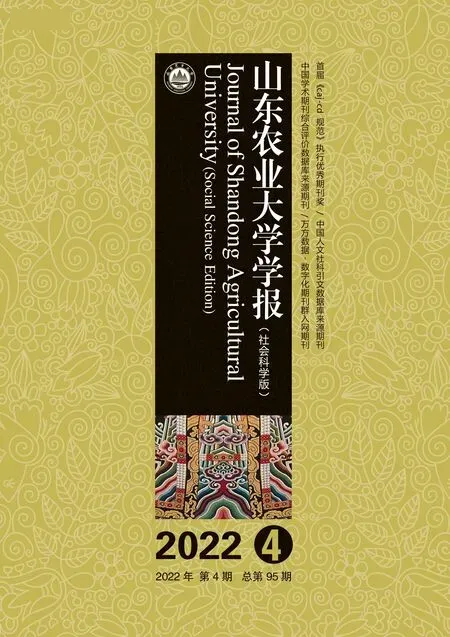国家化视角下以生活方式为表征的村落变迁史
——浙东北H县场前村的演变历程
□戴维娜
[内容提要]国家化视角下,乡村发展受不同阶段国家权力的影响,村落变迁以村民的生活方式为表征。以生计模式为表征的乡村经济改革记录了国家乡村治理各阶段的成效,国家权力通过影响乡村建设主体进而掌控着农村发展的方向。以风俗习惯为表征的村落记忆与乡村文化的传承有利于村落共同体延续,但文化滞后性的存在对村落现代化发展产生阻碍。场前村落的变迁具有历史与现实的普遍性,现代社会推动村落转型既要重视国家的引导作用,也要保障乡村的主体性发展。
村落在中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村民生活方式的演变是村落变迁的重要表征,生活方式包括展现经济状况的生计模式和村落文化记忆的风俗习惯。国家权力介入是造成村落裂变的直接因素。通过对村民生活方式的历史性展现,记录国家力量影响下村落的变迁史和村落中人的命运史,能够为农村、农民现代化发展的命题提供一种基于长程历史视野的思考路径。
一、问题提出
乡村裂变,大多是国家权力介入的结果。在中国乡村发展研究中,国家化与社会化有本质的不同,与国家化相比,社会作用的实施方式太过曲折隐蔽,所采用的配套机制又太过复杂,在人与人的互动中被不断生产与再生产。因此,国家化为视角的村落变迁研究更有利于观察者了解乡村变革的过程,找到乡村记忆传承的意义。国家化本身虽不是研究的核心,却是贯穿分析对象重要的存在。
既有学者的研究中,国家与村落的互动体现出国家权力对乡村的作用。杜赞奇借用“权力的文化网络”来表现国家权威在基层社会的塑造,即国家主要是通过在各种形式的文化网络中塑造权威的形式来保持国家对村落的价值整合。[1]206-210从国家的层面看,中国村落一直处于社会大系统的基层,处于国家的治理体系中,并在漫长历史形塑出“家户制”传统,这一传统影响着村落的形成及其演化。[2]徐勇认为,在关系叠加视角下,乡村范围内“家”既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体现着血缘关系;又作为纳税单元与国家,作为构成单元与村落建立起双重地域关系。基于血缘与地域关系双重叠加的家户制政治形态蕴涵着乡村社会与国家的相互渗透和包容。[3]
在对村落转型的研究中,一些学者提出类似“村落的终结”的说法,龚春明、朱启臻对“所谓村落的终结”理论进行分析后认为,村落在快速城镇化与现代化背景下,其固有的内在价值所彰显的意义更为积极和深远,在很长时间内,并不会出现所谓终结,相反有可能转型成更高的发展。[4]李飞、杜素云提出,在当前村落转型中,国家应当承担起保护责任,农民也应当积极参与。[2]国家与乡村社会存在巨大的张力。吴毅认为,地方性知识对社会变迁具有能动性作用,现代性和国家必须实现与地方性知识的对接和互融才可能影响社会变迁。[5]姬会然、慕良泽等人的研究认为,农村文化要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国家必须回归公共文化引导者和公共文化服务者的角色,使乡村社会成为孕育农村文化的主要主体。[6]
基于现有研究,本文以国家化为视角,以一个村落村民的生活方式,包括生计模式和风俗习惯作为考察点,用历史社会学的方法呈现浙江东北部名为“场前”(今改名为海城社区)的村庄变迁史,通过细致的乡土观察和丰富的史料记录揭示中国发达乡村社会的深层矛盾和裂变本质。这将帮助探讨百年来,国家权力影响下乡村经济改革与乡村文化的现代化适应过程和发展状况,以及长期历史框架下村落的产生和继替。
二、生计模式:乡村经济改革与村民的生活水平
农民的生活水平是乡村建设好坏的直接展现。围绕国家乡村发展政策,对特定历史背景下村民生计模式进行细致考察,能够深入探讨国家化过程中乡村经济改革和村民生活水平的变化。
场前村古时称砂(沙)腰村(下统称砂腰村),是一个具有传统沿海乡村特色的村落。古代砂腰村海沙场,由于产盐,设立了转盐运使司衙署。县志记载,“去县东北18里。明正统元年(1436)都御史朱鉴奏移海砂盐场场署至砂腰村白马庙东(即今场前)后,渐有集市。”[7]42
史料称,砂腰村是对面街,石板路,商铺林立,远近闻名。正因市场的繁华,据说在场前中桥(原供销社早晚商店)西南侧靠河滩边,还设有一块下马石,来司衙署或逛风情街的人,必须在此下马,牵马行走。出来后,回到此处再上马,可见当时的砂腰村交易广泛。在生计模式上,砂腰村大多数人是做长工和灶丁(煮盐者古称灶丁)的,也有出海捕鱼为生的。清末直至解放前期,因战争等影响,90%以上农民无地少地,靠租种本乡及县城地主的土地耕耘。[7]610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权力介入乡村的形式发生转变,国家和乡村社会共建了互动的场域。对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阶段划分,至今学术界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本文支持魏后凯对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三个阶段的划分,将1978年改革开放与2002年党的十六大作为两个分界点。根据这两个分界点,大体可以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历程分为集体化发展(1949-1978年)、市场化发展(1979-2002年)和城乡融合发展(2003年至今)三个阶段。[8]在场前村,国家权力的介入凸显出了三段村落裂变的记忆。
(一)国家“在场”:集体化发展阶段(1949-1978年)
相比于解放前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政权、军事和群众团体的活动,1949年5月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H县城后,才真正体现出共产党“政权下乡”对该地乡村带来的深刻影响。通过土地改革,共产党的政权组织第一次真正地下沉到乡村,摧毁了非正式权力网络的根基。人民公社在农村建构起了功能性的权力网络,使农民感受到国家的“在场”,离散的乡土社会被高度整合到国家政权体系中来。[9]
1952年土地改革是以国家行政手段推行的,农民既获得了土地所有权,也获得了土地的使用权、经营权。多数场前村老人仍清楚记得土改的情形。
“上面派人下来,队长就带着人分田,先分田地,再分自留地,家里人多就多分点,人少就分得少。”今年89岁高龄的老人郭某的娘家在姚家村,十九岁嫁入场前村,她谈到,“到了场前村我是没有自留地的,我的自留地在娘家。”
1955年土地集体化,土地由农民个人私有变为集体所有,实行统一经营,按劳分配。农业合作化运动后的人民公社,将土地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集体所有制变更为人民公社所有制。集体化和农业合作社运动不仅阻碍了土地资源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也颠覆了农村社群的权力结构、村社准则和社群观念。
“吃大锅饭的时候很穷,每顿都是粥,好一点有菜粥,每家人拿着盆去食堂打饭。”
“家里人多就打得多,人少就打得少,食堂打粥的人清楚这个量,不会给你多盛。”
当问起生计模式时,调研者王某表示:
“除了种地,没其他活。种地也是分工的,女人拔秧,男人摊田,年轻人种田,水稻丰收了就一起拿镰刀割,让年轻人挑回去,那时候哪有机器,都是人力。”
“当时都种什么?”
“稻谷、毛豆种得多,得吃得饱的。”
1982年初,中央指出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各种责任制,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正是基于安徽等地区各种责任制试点的成功以及中央对此制度的肯定,让场前村所在区域不再持观望态度,开始实行承包到户,是全国范围内较晚实行包产到户等责任制的村落。
“承包到户后日子才好起来,也能吃饱了。”这一点得到调研对象的一致认可。
集体化时期,场前村发展的步调按照国家政策要求平缓推进,国家权力全方位向农村渗透并对其整合,这一阶段场前村的建设并没有区别于全国大多数乡村的发展特色和优势,这一状况是进入市场化后才改变的。
(二)率先突破:市场化发展阶段(1979-2002年)
1983年前,H县的商业领域还处在计划经济年代。1983年场前村恢复乡建置,属海塘乡,彼时的海塘乡与西塘桥镇属于同一行政级别(现同归于西塘桥街道)。两相对比,西塘桥镇上的商铺,98%都属国营或集体所有制开办。西塘桥镇上的供销社承担着西塘地区海塘、西塘、元通三个乡的商品调剂。1984年,H县个体劳动者协会率先在西塘桥试点,由县工商局和县个体劳动者协会组建了“西塘桥地区综合服务公司”,主要业务是为三个乡的个体经营户及广大群众,提供价格实惠的商品批发兼零售服务。个体劳动者协会的举措,瞬间打破了西塘桥乃至H县商界计划经济一直由国营及集体单位垄断的局面。
已退休的原新城社区村党支部书记姚老告诉笔者:
“1984年,我怀揣着每月能挣到67元工资的喜悦,来了西塘桥地区综合服务公司工作。公司运营的相关手续完善后,我们先后到深圳、慈溪、余姚、金华等地,与供货商直接联系进货,减少省、市、县三级中间商差价环节,降低商品批发和零售成本。综合服务公司每年都要在镇上开4次以上的商品展销会,与‘老大哥’(供销社)在西塘地区市场展开激烈的商业竞争。那时候,西塘桥小镇南北街上集聚的商场和商铺总数不超过20家,但货架上的商品也是琳琅满目。每逢节假日、展销会期间,三个乡的农民成群结队,都会来西塘桥镇上赶集。在这里能买到紧俏的电子产品、名牌自行车、电视机、时髦的衣服,以及凭票计划供应的部分商品。当时的西塘桥小镇也算得上繁荣昌盛,这样的光景延续约6-7年时间。”
九十年代初,姚老所在的“西塘桥地区综合服务公司”与县工商局个体劳动者协会自行脱钩,转包给个人经营。他本人也下海经商,投入了个体户大军的行列。随后,国营单位也开始全面转制,承包给个人经营,所有的民用商品(如国家一类物资化肥、农药等)全部放开供应。同时,三个乡的大超市、乡村小店也陆续开业,农民不出村组也能买到想要的商品。
90年代市场经济浪潮下,场前村中很多农民选择外出打工。广州深圳是首选地。倪某是1992年在妹妹妹夫的介绍下出村打工的,最初去的是和香港隔岸对望的深圳市沙头角的一家工厂,住宿条件非常差。倪某告诉笔者,那时候村里几乎能去的都去打工了,她已经是第二批了,他妹妹妹夫是1990出去的,算是第一批。她们都从事服装业,在广州的一个香港老板投资的工厂里做真皮衣服,一般是7、8月份外出打工,“上半年都没活,下半年才做真皮服装”,即便这样,一年也可能要换好几个工厂。“(因为)刚去(那里打工)很辛苦,工作多是多,但找不好,时常不顺心,就会换厂,有时候一年要换四五个厂。”倪某如是说。
1993年,倪某一行人来到横广,这边的住宿条件较原来好了很多,“我们住在华侨村,那边的房子很好,但仍有一些人舍不得花钱,晚上睡在香港人投资造的楼房的楼顶上。”当谈到一年能挣多少钱时,倪某告诉笔者,因为都是下半年去,月份不定,一年差不多都是一万来块,好一点的年份能挣到1.5万,相比村里的服装厂,工资高了几倍。据了解,那时候,场前村的服装厂工资非常低,一年到头做下来可能挣不到两千块。这也是村里很多人愿意离开家庭,奔赴广州打工的主要原因。
1992年至1995年,倪某每年7、8月随同伴去广州打工,年末回来。1996年下半年,倪某怀着二胎孩子转去海宁打工,同样是做真皮服装生意,“也不是怀了孩子才不去广州,主要是那时候海宁服装生意也已经很好了,差不多也能挣这么些钱”。
海宁市与H县相邻,往后几年,H县的服装生意也愈渐繁荣,当地的服装厂增多,2000年以后,场前村内陆续开了多家私人服装厂,规模虽不大,但工资待遇尚好,吸引了很多当地劳动力,场前村大多数人再不必选择出远门挣钱。
市场化阶段,在国家改革开放大浪潮下,场前村所在的西塘桥地区抓住时代机遇,从计划经济到个私经济,从小城镇集聚型转移到乡村开放型发展模式,真正走在了全国乡村建设的前列。90年代后,家庭型的小作坊、个体经营商店占据了镇上商业房屋。与此同时,村民从出外打工到家门口挣钱,从一穷二白到建房造厂,生活水平逐渐提高,私人工厂也越来越多,整个村庄呈现出一幅新景象。
(三)政策推动:城乡融合发展阶段(2003年至今)
2002之后,场前村的青年人大多选择非农产业维持生计。相比而言,村落中的老人更勤于耕作,六七十多岁的老人种地挣钱在当地十分常见。西塘桥地区的农业生产以粮油、棉花、畜牧业为主。那时,一个普通的四口之家大约可分到3.5亩的土地,其中水田是一亩八分。春季收油菜,夏秋忙于采棉花,之后又要收稻谷,一年四季只有冬季不算农忙季节,还要顾着家中的鸡鸭猪和种植的当季蔬菜。这是村落拆迁前十几年间场前村大多数老人的生活状况。一方面,他们的子辈除了种水稻、小麦,很少花时间种植其他作物,因此存有闲置土地可以供他们进行粮油、棉花的种植。另一方面,人多地少是当地的劣势,H县的人均土地只有1亩左右,通过农业翻身十分艰难,因此年轻一辈大多不愿意从事农业。一定程度上说,2002年以来政府实行的征地拆迁政策,也是为了形成土地规模,促进农业发展。
90年代后场前村各家的贫富差距开始拉大,影响家庭经济状况的因素越来越多,首先迈出脚出门打工的人,投资建厂的人,出县跑生意的人大多赚了钱,成为村落中首先富起来的一批。不过,村落中大多数人真正富起来还得归于国家政策对区域发展的指导和推动。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将农村改革发展的重点从农村内部逐步转移到城乡之间。2002年西塘桥街道的征地拆迁政策正式拉开序幕,区域内第一批村落迎来拆迁。拆迁户与非拆迁户的贫富差距得以拉开。
此外,举世瞩目的杭州湾跨海大桥规划建设也在这年尘埃落定,场前村所在区域建设被摆在长三角经济发展的重要位置上,这也让场前村民对地区发展充满信心。杭州湾跨海大桥投入运行后,地区迎来飞速发展的时期,乡村规划也随之发生转变。2004年2月,新城村(场前村与姚家村合并后的名称)委托海盐经济开发区管理。地区政府开始大范围地征地拆迁,招商引资,鼓励农民转变生计方式,入职工厂。从2020年度经济总量的数字来看,场前村所属街道占据比例远高于县内其他镇(街道),居民年支配收入位于H县首位。
集体化时期,场前村还是一个经济十分落后的村落,场前村人过着有上顿没下顿的日子。改革开放带来发展的契机,场前村人力求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生活,80年代地区政府和经营者勇于率先突破,90年代村民勇敢迈出家门,出外打工挣钱。国家力量或明或浅,或强或弱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乡村建设。2002年后,在党中央“统筹城乡发展”的政策指引,以及杭州湾地区建设规划中,村落经济发展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村民的生活水平上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概括而言,集体化时期国家引路,农民跟随;市场化阶段国家退后,农民向前;城乡融合发展阶段国家在背后推动农民前进。国家权力介入通过影响乡村建设主体进而掌控着农村发展的方向。
三、风俗习惯:村落记忆与乡村文化的传承
乡村文化是村落发展的内核,国家权力作用势必影响村落既有文化的走向。
(一)庙宇文化:国家认可下的地方宗教信仰
宗族家族观念、传统惯习与信仰等要素构织的乡村文化网络深刻影响着国家政权建设的顺利进行。场前村落中家族众多,村落之人姓氏混杂,其中很多是后期陆续迁移到该地,后因战争影响又搬离一部分。史料记载,古时砂(沙)腰村风情街东边有几个大户人家祝氏家族、郭氏家族、金氏家族、潘氏家族、马家等等。司衙署迁来砂(沙)腰村后,先后有孔家、胡家、王家等家族,陆续迁之砂(沙)腰村定居。有的在司衙署做官,也有的在道班做官,有盐仓管账的等等。战乱期间,时官跑掉,暂由金家管理。可见,场前村人家族意识淡薄有其历史缘由。
传统中国文化中缺少宗教[10]97-106的理论总结也不适应场前村。H县佛文化深厚,庙宇林立。这些寺庙均在官方的管控中,也常常作为高校佛文化研究的基地。在官方的默认和推进地方文化建设的现实要求下,当地人佛教信仰浓厚,具有共同信仰的村民时常交流,结伴出行。按照当地习俗,每家每户在春节、寺庙菩萨生辰等特定节日必去烧香拜佛,祈求全家平安健康。场前村,虽存在无宗教信仰的个人,但没有无信仰的家庭。在“保佑全家来年平安健康”的祈求中,去寺庙烧香拜佛不再是单纯的宗教信仰,而是以家户为单元的风俗传承与习惯记忆。又因村落靠海,流传着因水患而生的各类传说。这些故事和传说经常与佛文化融合在一起,成为乡村记忆传承装置的重要材料。《闲窗括异志》记载:
在县北十八里砂(沙)腰村(现西塘桥街道新城社区场前)有一座白马庙。相传,当湖初陷时,白沃使君跃马疾走不及,遂驻马以鞭指,得湖东南一角,水至不没。今此地独高,后人于此立庙,一在砂(沙)腰,一在乍浦,皆称白沃庙也。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乍浦失守,有夷酋率党乘马将犯海盐,道经砂(沙)腰村白马禅寺前,无故坠马而陨,馀余众骇退(白沃使君,顺帝永建二年令也)。[11]
县令白沃使君因这一传说被神化,寺庙也因这一传说显得愈发神秘。场前村白马禅寺始建于隋炀帝年间,一直是该区最兴旺的庙宇。寺庙设有正殿、偏殿、山门,有白马石碑和僧人,正殿供拜佛四尊:大王老爷及夫人,白沃使君及夫人;两旁还有四大金刚。每年有三次庙会特别兴旺:即二月廿五、八月十二、十月初八,四邻八乡的人都来烧香。抗日战争期间,古迹白马禅寺被毁坏。六十年代,有场前供销社建造“场前棉站”,但仍有信众在棉站内外朝拜。2007年民间自筹资金,建一个小庙供信众烧香,民间多称为“大王庙”。2019年,民间又一次自筹资金重建白马禅寺。
地方政府对村落佛文化的肯定,无论是通过官方文献记录下与此有关的神话传说,还是诸多间接性的支持措施,诸如批准寺庙活动的开展和重建,都使得村落佛文化在当地得以世代传承并对村民生活产生深刻的影响。在乡土社会,根深蒂固的信仰往往比陌生的法律规定更有约束力。统一的信仰有利于维护村落秩序,使宗族力量较弱的村落更有凝聚力,也更有利于地方政府对乡村的管控。
此外,地方政府也受益于庙宇文化对村落发展的助力。明朝时,砂(沙)腰村风情街就已开始接待四面八方来白马禅寺烧香的信众。从古至今,白马禅寺香火旺盛,远近闻名,吸引了上海、杭州等多地的信众。2007年之后,民间自筹建“大王庙”得到官方批准,场前村村民于每月农历二十五来寺庙烧香,届时会开庙会。庙会带动了村落市场,乡土文化与宗教文化在互动中更加契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村落庙宇文化。
(二)供拜礼仪:乡村发展政策与共同体的延续
文化认同是村落共同体存在的核心要素。在场前村,家族意识虽较弱,家户意识却很强,因此,以家户为单元的祖先供拜和各地方神的供奉是比佛教信仰更为重要的村落惯习,这是村落祖先一辈辈传承,一年一年教导下形成的村落意识,这一套文化礼仪关系着家户的兴衰和村落共同体的凝聚。从表面看,官方一般不干涉民间的供拜活动,就地城镇化为核心的乡村发展政策也不对以家户为单元的民间信仰活动有所限制,甚至对村落共同体的延续有所助力,但也恰是无明文性的限制,以及就地拆迁政策对村落文化的保护,村民搬入安置社区后,将传统村落中的供拜礼仪一同搬入。熟知这套礼仪的家庭具有潜在的共同体身份。
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诸多内容相似,场前村落这套供拜先祖和祀地方神的文化也有固定的时间规定。一年有三次供拜祖先的时期,分别是除夕、清明、农历七月半。当地人方言称“请太太”。若当年家中有小辈结婚,结婚前后,要额外供拜一次祖先,告知祖先这一好事。当地祀土地神的日期和供拜祖先的日期相同,顺序上,往往是先祀土地神,即当地人称“请公公”,再供拜祖先,即“请太太”。灶神是每家每户供奉在厨房的神仙,保佑家中人平安健康的家庭保护神,村落拆迁前场前村人家家有土灶,灶神就贴在土灶上方,也有直接将灶神刻在土灶上方的瓷砖上的,因此当地人方言常称为“灶头公公”。村落拆迁后新建的安置社区内不再有土灶,一部分家庭仍会将灶神贴在自家厨房内,即使不贴灶神的神像,大多数人仍相信灶神会跟着自家一起搬到安置房,也依然按照以往几十年的习俗在农历腊月初四、腊月十四、腊月二十四、除夕、正月初一、正月初四、元宵日、正月二十四和清明这九天按时供奉。
此外,农历八月十五要拜月光菩萨,也说月光如来,当地人称“月王大帝照四方”要拜“月公公”才能保佑来年庄稼长得好。即使大多数家庭已不再耕种,这一习惯仍被保持。农历七月三十拜地藏王菩萨,目的是祈愿健康平安,也希望保佑升官发财。在村落供拜文化的传承上,传统与现代的差异大多在供拜的礼仪上。村里那些耄耋之年的老人非常注重供拜的礼仪,
“祀土地神的时候要倒酒(一般是黄酒),供拜祖先要倒饮料。”
“祀土地神的酒盅要朝南,筷子放在盅前面,要一把一把摆;供拜祖先时桌子要朝东朝西放,两边还要加上长凳,桌面上筷子的摆放也不同,要一个酒盅一双筷子这样靠着长凳的方向排两排。”
而这些老人的儿子女儿辈,多数年龄在四五十岁,在供拜礼仪上经常只记得一些常规的礼仪形式:点上一对蜡烛、上柱香、摆上为供拜准备的一桌菜或者是几种水果(其中一种被当地称为“圆子”的糯米制品经常被作为极佳的供拜品)、香燃尽后按传统给祖先和各神烧纸质的金元宝、银元宝。如今村里中年一辈的村民对一些细节性的供拜礼仪经常会重复询问家中老人,也不再专门制作供拜所用的糖糕、年糕,在供拜物品上没有他们父母一辈严谨。而他们的下一代,如今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大多连供拜的日期也记不全了。
近年来,安置社区陆续规定,禁止居民在室内使用明火焚香点蜡,禁止居民在楼道焚烧祀品。迫于指令,居民供拜用的蜡烛开始换成通电式的无烟型蜡烛,不少家庭会选择一个铁质的大桶在楼道中焚烧纸质祀品,待铁桶冷却后再放回以备下次供拜活动。
培育和发展农村公共文化固然要强调农村文化的实体性、规范性和信仰性。[12]文化滞后性的存在也说明,地方政府希冀在乡村快速转型过程中革除某些不合时宜的传统风俗是艰难的,官方规范在风俗引导上往往不会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在村落中得到世代传承的风俗礼仪在乡村转型时受到国家的关注:在乡村现代化发展中考虑它们是文化糟粕还是村落共同体意识的延续。地方政府在制定乡村发展规划过程中,往往因为难以把握两者的程度选择避而不谈,但当地近20年征地拆迁政策经验得到的启示是,即使官方以默认的方式认可村落风俗习惯在安置社区的延续,后期社区发展仍无法避免对某些风俗进行约束。即便如此,这些顽强存在和延续着的价值观念,在一定条件下依然能发挥伦理道德方面的规范和整合作用。
四、总结与思考
国家视野下对场前村村民生活方式的长期观察,可见村落变迁始终围绕着国家乡村建设的发展规划进行。以新中国成立、1978年改革开放以及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统筹城乡发展”为分界点,场前村经济变迁可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前,主要表现为多元生计方式的有效结合,最终构建起一个具有中国历史上传统沿海乡村特色的村落;集体化时期是第二个阶段,计划经济时代,出现过吃上顿没下顿的状况。一直到70年代,农村大多数人家吃不饱穿不暖;第三个阶段是改革开放至2002年,80年代农村开展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包产到户,既解决了温饱问题,又解放了部分劳动力,一部分人得以先富起来。90年代市场经济,大部分农民外出打工或经商开厂,农民的口袋慢慢鼓起来;第四个阶段是2003年至今。2002年后场前村落的发展主要得力于国家政策优惠和地方政府治理取得的现实成效。以杭州湾跨海大桥为基础的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了H县与长三角各城市之间的交流,2002年至2017年当地政府实行征地拆迁政策改变了区域经济发展结构,场前村迎来了新的发展道路——农村道路走向城市道路。场前村村民也在这一地区历史潮流中迎来新的发展道路——农民道路走向市民道路。
与直接作力于经济建设相比,国家权力介入村落发展对民间文化的影响是间接性的,产生的结果也更复杂。一方面,以就地拆迁为核心的乡村建设规划实现了对共同体意识的维护。在落实城乡统筹发展政策,推进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地方政府对村落庙宇文化的间接性支持以及对民间风俗礼仪的默示性认可有利于传统村落共同体意识的延续。另一方面,村落文化具有滞后性,文化滞后强调在快速的村落变迁过程中,村民的风俗习惯无法短时改变,村落思想意识无法适时转换,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乡村向城镇转型。现代社会,村落文化可以独立自主地运行,但离不开对国家的依赖。由知识精英创造出来的大传统与基层群众创造的小传统[13]在某种程度上必须能够协调配合。因此,现代村落转型的文化困境是如何在国家引导下,坚持主体性发展农村文化,使之既能适应村落变迁及区域经济发展,又能巩固共同体的凝聚力。
以推动农村经济改革和文化建设为目标,国家权力应该从更宏观的角度引导乡村转型。政府引导乡村发展首先要了解村落历史和传统,正确看待乡村社会传统的惯习性文化形态,因地制宜探索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其次,也要适当放缓脚步,从细微处入手,脚踏实地走稳村落转型的每一步。再次,坚持以人为本,走群众路线,优先解决村民利益相关事项。最后,要从乡村发展的长远利益出发,分清主次,统筹规划。例如,在农村文化传承上,既要弘扬主旋律,实现国家主流文化的乡村社会化,又要尊重文化的内生性和本土性,国家应作为文化基础设施的提供者,引导农民继承村落特色文化,推进乡土文化自主发展。
乡村发展是国家发展的一部分,也是国家治理的缩影。场前村落的变迁具有历史与现实的普遍性,引发了关于传统乡村向现代乡村转变、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继承与融合等诸多思考。从砂腰村到海城社区的历史经验启示,国家权力作用于乡村发展,国家如何引导决定着现代农村向何处转型,村落现代化发展的关键是融汇现代优势,在国家引导和社会自主中定位角色,坚持主体性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