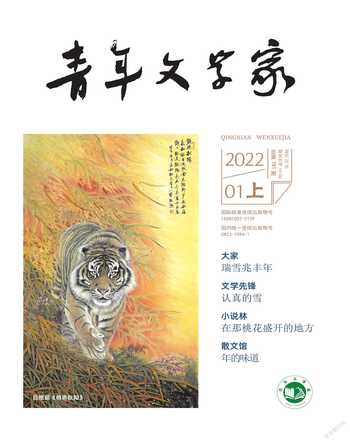野菜不褪色
赵晓英
春雨下得唰唰唰,田野洗得绿油油,一溜烟地跑回家,自己仿佛瞬间变回了那个快乐的少女。
“妈!”一边习惯性地喊,一边眼眸一掠,“哈!又要吃饺子了,真好。”
饺子是茵陈馅儿的。不用妈说,我从颜色、味道上已经判断出来了。“三月茵陈四月蒿,五月割了当柴烧。”这人间三月天,可不正是吃茵陈的季节!
我的家乡叫“洪水”,名字听着吓人,它却是宽展、养人的平川。洪水河两岸土地平旷,适合草木萌发,各种草一到春天就应时而生,陆续登场:蒲公英、車前草、马苋菜、苦菜……还有许多叫不上名字的草,它们以草为名,却大多可以食用并且可以入药。它们一同在我童年的记忆里疯长,在我绵长的人生之梦里盛开、凋谢,如此循环。茵陈仅是其中的一种。
茵陈其貌不扬。它的颜色不鲜亮,姿势也不大气。它总是软塌塌地贴着地面,一副任人践踏的样子。但它的根又深又长。人们采茵陈的时候,只采它的叶片,不会把它连根拔起。这样,过不了几日,新的叶片又生发出来了。茵陈在中药里挺有名,有清热利湿、疏肝利胆的功效。用它做饺子馅最好,还可以凉拌、煮饭。它的清香味道弥漫了整个三月。
马齿苋,叶片青嫩肥厚,红润茎梗水灵灵的,也贴着地皮,略比茵陈好看。它来得也晚。春天接近尾声时,它才不紧不慢地吐出几片淡淡的小绿叶,只有到了盛夏,它才尽情地铺展开来,显示自己的生命力。马齿苋的茎软软的,醋一泡即可下饭,剁碎了可和到玉米面里蒸窝窝头。那金黄、碧绿的混色已经够看,马齿菜那沁人心脾的香气更是别具一格,无可替代呢。
灰菜长得很高大。它的叶片肥厚,背面呈灰色,但是迎着阳光看去,这灰色里居然含着丝绒般的轻紫。一般的叶子都是美在面,它却美在背,这是让我感觉惊奇的。不过照例,灰菜也是在青嫩季节上桌的。“花开堪折直须折”,草也一样。过了季,它长成了五大三粗的模样,也就没法儿吃了。
扫帚苗终其一生都与人有着密切的关系:春天的嫩苗可吃,味道清新,口感柔软;夏天就开花。花朵清丽,花期很长。我家院墙外面的扫帚花已长多年,深深浅浅的粉和紫,让人一望见家门就有一种走进春天的愉悦。没有谁刻意地种过它,它就像是不请自来的精灵。后来无意中发现,它居然就是传说中的“格桑花”。天哪!我印象中,一直以为格桑花是长在雪域高原的。格桑梅朵……这么美的名字是它的吗?早先秋风起,花枯茎黄的时候,人们可以截取它的植株捆扎成大号的扫帚。我想这就是它这个俗名的由来。幸好现在的人们很少自己动手做扫帚了,就让这美丽的花在人类的夏天里一直盛开吧!
香椿炒鸡蛋是各地常见的风味小菜。香椿算野菜吗?应该也算吧。它虽然是从那么大的树上摘下来的,可它是货真价实的野味,大棚里是长不出这东西的。不过它的可食期也短,每年只有很短的时间可吃到这种地方风味。一到万物萌生的季节,有些吃货悠悠踱进农家乐,竟是专门来吃香椿炒鸡蛋的。叮叮当当的切菜声响过,跟着就是“滋啦”一声,炒锅里的香椿苗伴着黄黄白白的煎鸡蛋,金黄里点缀着粗粝的绿,“滋滋”冒着热气就上了桌。这美气!
香椿算野菜,那么榆钱、槐花……都得算吧?小时候捋榆钱、槐花的往事,中年以上的人哪个能忘?榆钱窝窝、槐花拨烂子,各有各的香,就算这样简单地写一写,也会引动味蕾,让人食指大动。犹记小时候的理想,便是有朝一日白面、大米管饱,现在早就超越了这个目标,情思却又返回了童年,重新向往那朴素的野性和简单的制作,那原汁原味的田野气息。梭罗说:“野地里蕴含着这个世界的救赎。”那么这回归,也许就昭示了野菜永不褪色的价值呢。
37915003382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