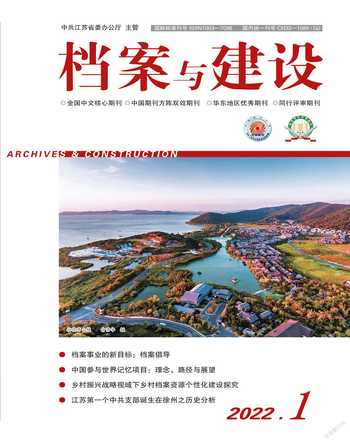面向公众教育的档案文献遗产开发:实践图景与未来展望
卜鉴民 邵亚伟 吴飞
摘 要:档案文献遗产开发与公众教育具有内在关联,且相互促进。当前面向公众教育的档案文献遗产开发实践呈现的特点包括:多主题探索,打造地方特色文化名片;多形式呈现,丰富公众体验感与获得感;多主体参与,营造活跃的社会文化氛围。在档案信息化建设、用户需求日益多元化等现实背景下,面向公众教育的档案文献遗产开发工作应当以“大协作观”为新理念引导,基于用户需求开展更精细化的服务,嵌入和应用新型数字技术。
关键词:档案文献遗产;公众教育;文化遗产
分类号:G273.5
Development of Archival Documentary Heritage for Public Education: Practice and Future Prospects
Bu Jianmin1, Shao Yawei2,3, Wu Fei4
( 1.Suzhou City Archives, Suzhou, Jiangsu 215001; 2.National Science Librar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90; 3.Department of Library, Information and Archives Management of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of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1400; 4.Suzhou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Archives Management Center, Suzhou, Jiangsu 215001 )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archival documentary heritage and public education are intrinsically related and promote each other. The current archival documentary heritage development practice for public education is multi-theme exploration, creating a cultural business card with local characteristics; multi-form presentation, enriching the public’s sense of experience and sense of gain; multi-subject participation, creating a lively social and cultural atmosphere. Under the realistic background of archives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and increasingly diversified user needs, the development of archives and literature heritage for public education should be guided by the new concept of great cooperation, carry out more refined services based on user needs, and embed and apply new digital technologies.
Keywords: Archival Documentary Heritage; Public Education; Cultural Heritage
以公众教育为目的和表现形式,深挖档案文献遗产中具有记忆性、历史性、启示性的因子,架起社会公众与其之间的紧密桥梁,是档案文献遗产开发拓展广度与深度的有益探索。2015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通过《关于保存和获取包括数字遗产在内的文献遗产的建议书》(以下简称“2015年《建议书》”),指出:“会员国应通过鼓励开发有关文献遗产及其在公众领域存在的教育和研究的新形式和新工具,改进文献遗产的获取。”[1]
在现代社会教育体系中,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科技馆等公共文化服务机构承担了极大的公众教育职能,推动了公众教育理论探讨的深化与实践水平的提升。其中,面向公众教育的档案文献遗产开发在我国亦广受关注。新《档案法》强调要“加强档案宣传教育”“鼓励档案馆开发利用馆藏档案,通过开展专题展览、公益讲座、媒体宣传等活动,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2]《“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提出“到2025年,档案公共服务、文化教育能力明显提升”的明确目标。[3]在国家大政方针的引导下,各地纷纷出台相应政策并开展了形式多样、主题丰富、影响广泛的实践活动,将“面向社会公众开展宣传教育”纳入档案文献遗产开发之中。
现有相关研究主要从档案馆视角切入,探究公众教育发展演变[4-5]、域外经验借鉴[6-7],聚焦特定主题[8]或形式[9]。少有研究跳出单一主体视角,从“档案文献遗产开发”这一客体出发,阐述其与公众教育的内在关联。本文基于调研结果,对相关内容进行梳理,在阐述两者内在逻辑基础上提出现有实踐特点,并据此展望未来,以期为档案文献遗产开发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
1 公众教育与档案文献遗产开发的内在关联
1.1 目标指向的共通性
公众教育与档案文献遗产开发目标具有共通的指向性。根据《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10],公众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暗含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当中,其目标既具有自身特性,亦相合于后者。公众教育致力于“提高广大青少年和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和科学文化水平”[11],满足公民基本文化需求,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12]世界记忆项目将其愿景设定为“全世界的文献遗产属于所有人,应出于所有人的利益予以完整的保存和保护,并在充分尊重文化习俗和客观现实的前提下,确保文献遗产能够永久地被所有人无障碍地利用”[13]。档案文献遗产开发目标承接这一愿景,既是对档案文献遗产“本身生命的延续”,也是对社会公众获取利用需求的有效回应。另外,档案文献遗产开发活动本身处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序列之中。“满足公民基本文化需求”成为其目标之一。
1.2 服务对象的交叉性
公众教育与档案文献遗产开发均面向社会公众,两者在服务对象上存在交叉性。《中国大百科全书》将“社会教育”定义为:“狭义上,指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以外的一切社会文化机构、社会团体组织和其他形式的社会主体对其成员所进行的教育。”[14]公众教育隶属于社会教育[15],具有非确定性且无明显边界的服务对象,这与“档案文献遗产应被所有人无障碍地获取和使用”有异曲同工之处。两者服务对象的交叉性为彼此的互动与融合提供可能性。
1.3 双向促进的互动性
一方面,档案文献遗产作为“生动素材”,嵌入公众教育。档案文献遗产因其自身的原始性、客观性、真实性等成为公众教育“鲜活的教科书”。公众教育作为一种非正规教育,首要目的是对社会大众进行精神文化、思想道德层面的熏陶,再辅之以必要或有意义的专业知识传播与推广。例如,美术馆在普及美术知识、宣介美术作品的过程中,多以培育公众的审美能力与创新能力而非传授专业艺术技能作为公共教育的主要任务。[16]从这个角度来讲,档案文献遗产作为书写悠远历史、蕴含丰富文化、承载精神文明的信息资源,正是开展公众教育的“生动教材”。
另一方面,公众教育作为中介形式,助力档案文献遗产价值实现。以公众教育為中介形式,深挖档案文献遗产中的多元要素,构建社会公众的“记忆之场”,是实现档案文献遗产价值的有效途径。面向公众教育的档案文献遗产开发,既是保护档案文献遗产、传承历史文化的客观要求,也是满足社会公众精神文化需要的有益探索。
2 面向公众教育的档案文献遗产开发特点
为深入了解档案文献遗产开发实践,笔者选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浙江省档案馆、西藏自治区档案馆、苏州市档案馆等机构,并辅之以世界记忆项目福建学术中心、世界记忆项目苏州学术中心,对其展开深度访谈。调研结果显示,面向公众教育的档案文献遗产开发呈现出三大特点:
2.1 多主题探索,打造地方特色文化名片
在支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助力宣传社会主流文化的同时,档案文献遗产馆藏主体也结合自身资源和地方文化特色,有针对性地开展顺应时代背景、迎合公众需求的主题教育活动。《“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便在“档案文献遗产影响力提升工程”中要求突出世界记忆项目福建学术中心(以下简称“福建学术中心”)的侨批文化研究优势和世界记忆项目苏州学术中心(以下简称“苏州学术中心”)的丝绸档案资源优势。[17]
在以“百年恰是风华正茂”主题档案文献展为典型代表的爱国主义教育之周,围绕丝绸文化、侨批文化等地方特色文化,着力开发相关档案文献遗产资源的公众教育活动层出不穷。例如,苏州市工商档案管理中心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大运河文化传承的指示精神,深挖丝绸档案中的近代民族工业文化,结合“江南特色”打造文化品牌。总体而言,面向公众教育的档案文献遗产开发横向上拓展文化边界,将其所蕴含的文化精粹与社会主流文化相关联,构建起更具多样性、民族性与生命力的文化场域;纵向上坚持时代性与历史性的辩证统一,在新时代背景下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激活历史文化与社会记忆。档案文献遗产借由公众教育到达“用户端”时便是一场聚合多元要素、融合多样特色的“文化盛宴”。
2.2 多形式呈现,丰富公众体验感与获得感
面向公众教育的档案文献遗产开发因社会环境、文化传统、教育资源、馆藏主体自身发展水平以及受众等因素影响,具有不同的发展阶段和表现形式。基于乔治· E· 海因(George E. Hein)在其著作《学在博物馆》(Learning in the Museum)中提出的教育理论模型[18],面向公众教育的档案文献遗产开发主要呈现出四种具体形式。
首先,视社会公众为被动的知识接收者,面向社会公众开展传统的专题讲座、主题展览等活动。例如,苏州市工商档案管理中心在开发丝绸档案时,积极推动世界记忆项目进校园。[19]其次,面向社会公众开展更具互动性的“参与式”教育活动,具体包括知识竞赛、文创产品开发、图书出版等,使公众更具参与感和获得感。例如,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出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书》《南京政府档案遗存珍档》等珍贵档案汇编。再次,鼓励社会公众开展“探索式”学习,主动汲取知识并感知文化。例如,法国国家档案馆设立“档案艺术工作坊”,积极邀请青少年参与戏剧表演、音乐演奏、档案复制品制作等活动,探索档案教育与艺术培养的融合之道。[20]最后,开展“建构式”教育,支持受众在与档案文献遗产互动过程中基于已有的专业知识水平主动构建认知、开展研究。例如,苏州市工商档案管理中心积极向高校借力,由来自中国人民大学、苏州大学、上海大学等处的师生力量共同投入到丝绸档案的科学研究与开发利用当中。[21]
此外,在数字化转型的大趋势和档案信息化建设的行业背景下,面向公众教育的档案文献遗产开发被赋予更多的技术性、学术性、艺术性、互动性与趣味性。新加坡国家档案馆就曾设计开发基于网络的多媒体在线国民教育展览。[22]江苏省档案馆打造“30秒带你穿越南京长江大桥”互动小程序,云南省档案馆基于数字人文视域构建南侨机工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平台等[23],均是档案文献遗产开发面向公众教育的有益探索。总之,发挥档案文献遗产的公众教育价值并不囿于具体的活动组织形式,而是以目标为导向、内容为关键、创意为加持。上述众多教育表现形式并非互无关联或相互冲突,而是相辅相成、保持内在的统一性与连续性,公众由此获得更丰富且深刻的参与感与体验感。
2.3 多主体参与,营造活跃的社会文化氛围
当前,“多主体参与”愈发成为各级各类政策引导的重点。档案文献遗产开发逐渐脱离“单打独斗”的模式,基于合作的多元治理格局日益形成。一方面,复合型人才、跨领域人才、其他专业人才的身影逐渐出现在档案文献遗产开发实践当中。例如,云南省少数民族语文指导工作委员会人员和云南大学高性能计算中心人员合作开发云南规范彝文排版系统,助力彝文伦理档案文献遗产的数字化建设。[24]另一方面,跨机构、跨领域、跨专业合作日渐常态化。例如,苏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世界文化遗产古典园林保护监管中心、苏州园林博物馆等多家部门与苏州学术中心共商合作,打造“第七档案室”多元化IP体系。总体而言,面向公众教育的档案文献遗产开发需要社会力量融合多方资源、协同参与,共商、共建、共享档案文献遗产。
3 面向公众教育的档案文献遗产开发展望
3.1 新理念引导:融入“大协作观”视域的文化遗产体系构建
《“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提出要“促进世界记忆项目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其他遗产项目协同发展”。[25]档案文献遗产同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相互关联、互为补充,同时又各有侧重、各具特色。在现有跨机构、跨地区、跨领域协作基础上,立足于整个文化遗产体系高度,以“大协作观”审视档案文献遗产开发实践,促进其与相关遗产融合建设,既契合于文化多样性和整体性保护的原则,又有助于构建更加宏大、完整、系统的叙事结构。未来,以“合作”为主基调,在现有的跨机构、跨地区协作基础之上,在领导重视程度、经费保障、版权保护、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等现实问题上予以更多的关注和投入,将档案文献遗产置于整个文化遗产体系之中,在公众教育实践中赋予其更多的价值实现形式势在必行。
3.2 服务精细化:用户细分与受众拓展
当前,档案文献遗产开发实践多以资源为导向。随着用户需求逐渐受到重视,公众教育用户细分与受众拓展的特点将日益凸显。在用户细分方面,档案文献遗产館藏机构可针对主要受众群体开展需求调研与分析,构建用户画像。如针对青少年或在校学生群体开展互动性、趣味性较强的教育活动;针对广大社会公众开展覆盖面广、传播率大的主题展览;举办学术论坛,为学者开展研究提供支持等。
在受众拓展方面,随着科学研究范式变革和知识生产活动日益呈现跨学科融合趋势,越来越多科研人员将成为档案文献遗产的潜在利用者,社会公众的休闲利用需求亦不断增强。《“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主张实施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宣传推广计划等活动。为此,相关机构有必要拓展公众教育实践的受众群体,以提升档案文献遗产影响力。如综合分析档案文献利用和参与公众教育活动的用户数据,通过多种传播渠道和形式宣介档案文献遗产;搭建与用户互动的平台,举办用户交流活动;收集用户反馈,优化、调整教育活动。
3.3 新技术赋能:积极拥抱数字技术
当前,档案文献遗产开发形式多聚焦于实体层面,亟待借力数字技术进行创新。一方面,现有实践表明新型数字技术的嵌入和应用在档案文献遗产的保护和开发利用方面有巨大潜能。安卡·克劳迪娅·普罗丹(Anca Claudia Prodan)就曾指出实证主义会导致对文献遗产的片面解读,基于批判性视角运用数字技术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数字文献遗产的多重意义。[26]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NHE)启动人文社会科学信息基础建设工程,推出“数字人文计划”(Digital Humanities Initiative),对档案文献遗产、古籍善本等进行保护和开发。[27]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在公众教育领域的应用亦赋予其更多可能性。如虚拟现实技术、三维图像技术、数字展厅技术等在博物馆领域的应用,使用户观展体验更具互动性与趣味性。2021年7月3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0年)》,指出我国教育信息化2.0行动成效明显,国家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日益完善。[28]在国家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政策引导下,档案文献遗产开发实践积极拥抱数字技术,既符合档案信息化建设的行业发展趋势,也能够助力教育信息化建设,开展更加便捷、普惠、精彩的公众教育实践。
*本文系2020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世界记忆项目建设体系与中国策略研究”(项目编号:20CTQ036)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与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档案局.关于保存和获取包括数字遗产在内的文献遗产的建议书[EB/OL].[2021-12-11].https://www.saac.gov.cn/mowcn/cn/c100450/2021-02/18/4077d201410f4efbb0038431bb29076f/files/50140f988e2e4b e5975d0b30c35995cd.pdf.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档案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EB/OL].[2021-12-11]. https://www.saac.gov.cn/daj/falv/ 202006/79ca4f151fde470c996bec0d50601505.shtml.
[3][17][2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档案局.中办国办印发《“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EB/OL].[2021-12-8]. https://www.saac.gov.cn/daj/toutiao/202106/ecca2de5bce44a 0eb55c890762868683.shtml.
[4]谭必勇.如何拉近档案馆与公众的距离——解读西方公共档案馆公众教育职能的演变[J].图书情报知识,2013 (4):85-94.
[5]王云庆,宁现伟.谈档案馆公众教育的发展演变[J].档案学通讯,2014(2):4-8.
[6][20]王玉珏,杨太阳.法国档案馆公众教育服务体系建设及其启示[J].档案学研究,2016(5):103-109.
[7]王玉珏,张晨文,陈洁.美国国家档案馆公众教育服务的发展[J].档案学研究,2017(5):106-112.
[8]张芳霖,段莉莎.档案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理论根基、发展现状与优化路径[J].北京档案,2020(8):6-10.
[9]王晓璐.国内档案网站公众教育服务体系建设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15:12.
[10][12]中国人大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EB/OL].[2021-12-10]. http://www.npc.gov.cn/ zgrdw/npc/xinwen/2016-12/25/content_2004880.htm.
[11][14]林伟.社会教育[EB/OL].[2021-12-11]. https://www.zgbk.com/ecph/words SiteID=1&ID=116071&Type=bkzyb&SubID=49179.
[1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档案局.世界记忆项目简介[EB/OL].[2021-12-11]. https://www.saac.gov.cn/mowcn/ cn/c100449/sjjyxm.shtml.
[15]宁现伟.档案馆公众教育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14:16.
[16]杨应时.美术馆公共教育[M].北京:东方出版社, 2020 :3-5.
[18]Hein G E. Learning in the Museum[M].London: Routledge,2002:25.
[19][21]陈鑫,程骥,吴芳,卜鉴民.地方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开发研究——以苏州丝绸档案为例[J].档案与建设,2020(6):42-46.
[22]Khoon L C, Ramaiah C K, Foo S. The design and development of an online exhibition for heritage information awareness in Singapore[J]. Program: electronic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ystems, 2003(2):85-93.
[23]黄天娇,邱志鹏,于雯青.数字人文视域下南侨机工档案文獻遗产开发路径研究[J].浙江档案,2021(10):21-23.
[24]华林,邓甜,李帅.论彝族伦理档案文献遗产资源建设问题[J].兰台世界,2018(08):23-25.
[26]Prodan A C. Memory of the World, Documentary Heritage and Digital Technology: Critical Perspectives[M]// Edmondson R, Jordan L, Prodan A C. The UNESCO Memory of the World Programme: Key Aspects and Recent Developments. Berlin: Springer, 2020: 159-174.
[27]李子林,龙家庆,王玉珏.交流与合作:美国数字人文与档案领域的互动及启示[J].档案学研究,2020(2):130-137.
[28]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0年)》[EB/OL].[2021-12-8]. http://www.gov.cn/xinwen/2021-07/03/content_5622668.htm.
3565501908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