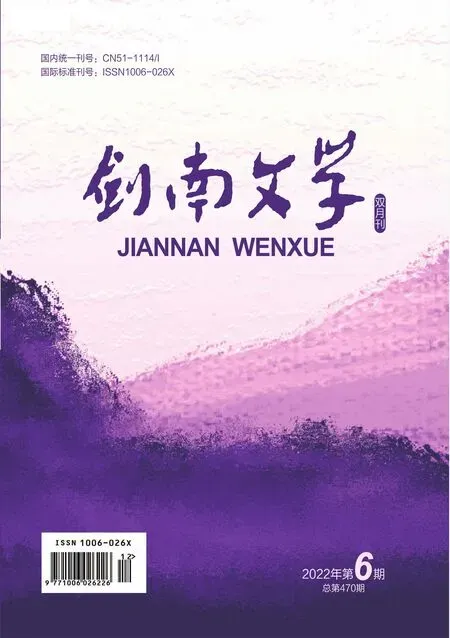山 居(组诗)
□潘玉渠
仲夏夜
此刻,夜如樊笼
将虫鸣、风絮圈禁在一小块花园里
月光从云端流入
在西墙上投影出的假山轮廓
宛如一个面壁的囚徒
这让我想到一些陈年往事
想到一些不恰当的言行
最终围成了内心的困境。
……水塘边,柳条舞动腰肢
飞蛾在路灯罩内努力突围
它们执着的样子
让我顿生效仿之念——
效仿它们遵从内心
向自由探出半截身体
逐一解开人生的死扣
砍竹帖
一斧下去,那竿竹子连同它
撑起的春天
晃了几下,便坍塌了
而舔舐着新鲜汁液的斧子,愈发锃亮
好似一道锋利的目光
折射出凛凛寒意。其实
竹子死后,广义上的春天
会更加开阔——
更多的笋子,得以伸直腰身
以蓬勃的绿意
治愈土地的暗疾
就像高手对弈,胜败
在一瞬间切换
有时用一步死棋
便可换取一场迂回的胜利
镜中山茶
在镜中,我扶墙而立
与另一个自己互为验证。
我低头,灯光从眼角掠过
一丝温暖的触碰
如乱世中的一瞥,亦如
久违的问候。
而你静止不动,以美人之态
俯瞰自身
仿佛每一片叶子都是账簿
记录着生活的债务
……庆幸这样的亏欠
“是昵称,也是白色面具”
让暮春以来我欠你的所有恍惚
皆可兑现
山居
有小樽饮酒,小瓶插梅
不可揭破的心事,如涩涩的铜锈
在香炉上呈环状延伸。
大雪之暮,时间放缓
居室冷如冰窖
三两声寒鸦之鸣
在树梢间来回震荡
让世界坠入旷阔的空白
而我,既不打算出门
也不怜惜窗外那丛
负重摇曳的斑竹
只愿自顾自地恍惚
自顾自地见烛花炸裂
待春风拂来
暑中即景
暑中,宜静坐
宜调慢时间,演算另一种人生
城市的体温过于灼烫
玻璃幕墙折射出的白色光束
像一个巨大的括弧
将形形色色的人
圈禁在一种难以删减的疲态中。
广告牌面目浑浊
行道树萎靡不振
车辆迟缓,如甲壳虫爬行
汽笛、电焊、空调外机的轰鸣
统统被烈日放大
仿佛一种潦草的合奏
刮擦着耳膜
占卜
龟甲无用,蓍草失灵
卜辞只会平添心事
小沙弥漫不经心,僧衣上的油渍
水墨一样盛开
而放生池里,锦鲤乱作一团
硬币堆如山丘——
它们不礼佛,不求签
进了这山门
只求果腹,不听
佛号与钟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