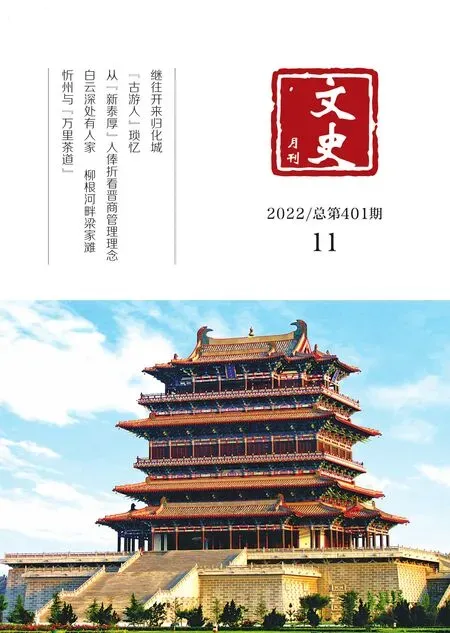先秦『邑』考
◇ 李 鑫
在先秦传世文献中,“邑”是区别于自然生长的一般性村落的特有名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出了特有的含义。
在最早的传世文献《尚书》中,“邑”主要指代的是王朝都城或“类都城”,如“夏邑”(《汤誓》《多方》)、“新邑”(《盘庚》)、“商邑”(《牧誓》《酒诰》《立政》)、“大邑周”(《武成》)、“新大邑”(《康诰》)、“洛邑”(《召诰》《多方》)、“新邑洛”“天邑商”(《多士》)。而如果结合殷墟卜辞所载,“邑”的指代就出现了多义性。但无论“邑”的早期含义如何,其在整个先秦时期所表现出的政治属性是十分明显的。
“邑”是一种政治建构的产物。《礼记·祭法》载:“天下有王,分地建国,置都立邑。”《礼记·王制》:“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这些记载应是对当时社会政治状况的高度概括。至少在周王朝时期,“邑”已有明确的政治归属。《国语·晋语四》:“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隶食职,官宰食加。政平民阜,财用不匮。”此时的邑已是这一政治体系中的重要一环。
“邑”不以规模大小划分。文献中多处出现“百室之邑”(《左传·成公十七年》),“千室之邑”(《论语·公冶长》),“千家之邑”(《墨子·号令》),“万户之邑”(《韩非子·说林上》),“万室之邑”(《商君书·兵守》),“十室之邑”(《荀子·大略》)等。可见,只要具备一定的政治条件,无论大小均可称“邑”。这种称谓从另一层面反映出人口对于“邑”的重要性。“邑”从根本上承载的是政治体系中的人口。
作为政治人口承载体,“邑”在农业社会中便是农业资源的聚集地。《墨子·尚贤中》载:“贤者之治邑也,蚤出莫入,耕稼、树艺、聚菽粟,是以菽粟多而民足乎食。”《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载:“中牟之民弃田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管子·揆度》载:“大夫散其邑粟,与其财物,以市虎豹之皮。”《吕氏春秋·察微》载:“楚之边邑曰卑梁,其处女与吴之边邑处女桑于境上。”通过以上资料大略可以推断,周王朝时期“邑”中人口还是以男耕女织为主,这为整个政治体系提供了最基础的物质资源。因此,东周时期不断有夺邑、取邑、赠邑的事件发生。随着社会的发展,“邑”的商业功能逐渐显现。《吕氏春秋·疑似》载:“邑丈人有之市而醉归者。”战国时期文献中出现的“城市邑”(《战国策·赵策》),“有市之邑”(《战国策·齐五》)等称谓,则反映了邑在历史演进中形态上的逐渐多元化和政治经济功能上的逐渐复杂化。
“都邑”二字连用在先秦文献中出现较晚。《周礼·地官司徒》载:“凡造都邑,量其地,辨其物,而制其域。”《周礼·夏官司马》载:“掌建国之法,以分国为九州。营国城郭,营后宫,量市朝、道巷、门渠,造都邑亦如之。”《礼记·月令》载:“是月也,可以筑城郭,建都邑。”至晚在战国时期,“都邑”一词已具备了成熟的语义,是国家建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表现出了明确的政治规划色彩。
《管子·治国》载:“故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叁徙成国。”该条史料除了反映“邑”“都”“国”在政治建构上的层级关系外,更重要的是表达了当时的人对这三个概念的理解,即明显区别于自然生成的村落,是某一政治体系中的组成部分。
综合以上分析,“都邑”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早期城市概念,伴随着社会政治体的长时段演进,至晚在东周晚期完成了语义上的成熟建构,且一直为后世沿用。“都邑”一词既表现了中国早期城市显著的政治建构特性,又在先秦文献中具有较广泛的涵盖性,可以作为中国早期城市研究的规范性概念使用。同时,在这一概念框架下,“国都”“都鄙”“都城”“城邑”等概念可以并行使用,这也体现了这一概念本身的包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