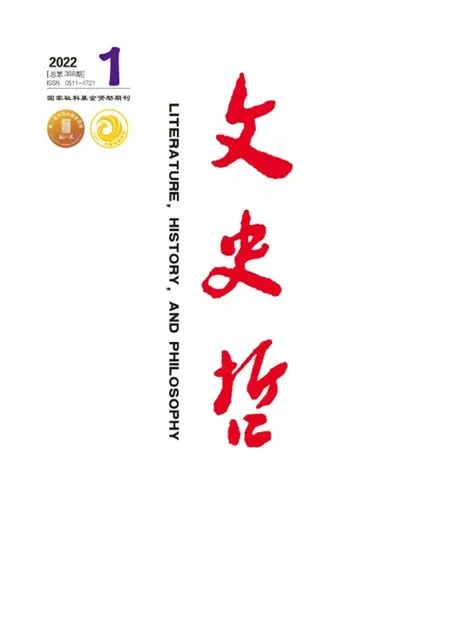“四海之内皆兄弟”与人类和平的可能性
伍晓明
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诗经·小雅·棠棣》
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汉文帝时淮南民歌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鲁迅
一、格言的问题
如果四海之内皆兄弟,是否就会有人类和平?这也许是一个问题,或应该成为一个问题。
“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是源于《论语》的一句格言。格言之为格言即在于,它已被抽离于本来的、具体的、特定的语境,并因此而具有了一种进行普遍化的力量。本来可能是针对某一具体情况的特定陈述变成了一个似乎普遍的命题,而普遍之为普遍即在于囊括万有、毫无例外,这就是文化传统中的格言的力量之所在,但格言之为格言也在于,唯其为格言,所以我们倾向于不再思想这一格言本身,而仅视其为理所当然。由时间和历史染上光泽的格言所具有的经久不衰的迷人外表让我们觉得可以高枕于其上而无忧。这就是说,格言在赋予我们以可能的洞见和智慧之时,也可以让我们变得盲目和愚蠢。我们“耳熟能详”地重复那些似乎并不需要给出任何注解(不需要给出注解是因为格言的普遍性赋予其享有匿名性的特权)和阐释的格言,并以之作为无可置疑的但其实是未经审视的权威来支持我们的论述或断言,同时却忘记了提醒自己,我们最熟悉的东西其实也经常是我们最不熟悉的东西,或最应该加以思考的东西。正因为如此,在重复“四海之内皆兄弟”这一格言并将之联系于人类和平这一主题时,我们才需要问:“如果四海之内皆兄弟,是否就会有人类和平?”之所以需要提出这一问题,正是因为对此我们可能立即就倾向于给予一个肯定的回答:“当然!”而这很可能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需要提出一个有关这一格言本身的问题来为我们的思想惯性减速或制动。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首先需要分析兄弟关系本身,然后才可以进一步考虑:兄弟关系是否可以被扩展至全世界,或怎样的兄弟关系才有可能被扩展至全世界,从而成为人类和平的基础?“如果四海之内皆兄弟,是否就会有人类和平”这一问题也要求我们思考人类和平本身的意义。我们所谓“人类和平”说的究竟是什么?人与人之间怎样的关系才可以或应该被称为和平——真正的和平,持久的和平(康德的理想)?如果真有一种和平可被论证为是人类——我们——普遍渴望和乐于接受的和平,如果这一和平的实现又真可以建立在一种普遍的兄弟关系之上,那么我们——今天的我们,生活在这个柏林墙倒塌30年后历史不仅没有像弗朗西斯·福山希望的那样终结,而世界却日益变得更加动荡不安的我们,又将如何具体地因而也是逐步地有限地追求这一人类和平的实现?
为此,除了需要其他哲学灵感,那些来自另一者或另一传统的灵感,我们也需要蕴含在自己传统之内的思想智慧的激发和鼓舞,但古代的智慧只有在经过现代的思考之后才有可能成为可以指导我们在当代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中摸索前行的智慧。也正是为此,我们需要回到自己的传统。在这一传统中,为了本文所欲探讨的特定问题,我们需要回到儒学,重温儒学,因为格言“四海之内皆兄弟”就出自儒学经典《论语》。回到是为了重新出发和前进,重温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和回应我们自身的现实处境。“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也!”(《论语·为政》)这不正是儒家圣人孔子的教导?对于我们来说,自诩可以为师当然也许太过狂妄,但作为学者,尤其是作为以儒学思想或思想儒学为己任的学者,为了能在这个也许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思想的时代,向愿意思想者提供些许可能的新鲜思想,为了知现代之新而重温儒学之故,这难道不正是我们不可忘却和无法推卸的责任?
因此,为了人类和平,为了其可能的实现,或为了至少能够开始思考人类和平这一重要问题,我们试图回到并重温“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一耳熟能详的格言,以期发现一个可能的思想起点,因为这一格言所表达的似乎正是一种古典的人类和平——“天下太平”——的理想。
二、司马牛与子夏的对话:君子何患无兄弟
格言化的“四海之内皆兄弟”出自《论语·颜渊》的一段对话,对话发生在孔子的弟子司马牛和子夏之间:


是的,还忧虑和恐惧什么呢?子夏认为司马牛不必忧虑和恐惧。当然,这是说如果自己首先是君子或致力于成为君子,至于小人则可能就未必了。君子以自己的言行使普天之下四海之内的人都是自己的兄弟,所以不必担心自己没有兄弟,或没有自己的兄弟。所谓“自己的兄弟”就是俗语“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这一意义上的兄弟。“亲”指具有直接血缘关系,所以兄弟有时也被称为“同父”或“同姓”(见于《诗经》等经典的说法,“同姓”即“同母”),即同出于一父或一母。子夏的话扩大了本来意义上的“兄弟”的所指,使其成为一个隐喻,用来指一种没有直接血缘亦即并非同父同母的人类关系。根据子夏的说法,没有自己的兄弟——同出一父或一母的兄弟——没有关系,因为天下之人皆可成为兄弟,前提是一个人自己必须首先按照君子的标准行事待人,但本来意义上的兄弟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司马牛与子夏这段对话中却并未明言。子夏劝慰司马牛不必害怕没有兄弟的话语中仅仅蕴含着一种似乎不言而喻的假定,即本来意义上的兄弟关系本身是没有问题的,或是不会出问题的。本来意义上的兄弟关系在此已被理解为可欲的关系、理想的关系,因而应该成为普遍的人类关系的典范或基础。只要我行事敬而无失,待人恭而有礼,本来意义上的兄弟关系就可以“扩而充之”,遍于天下,于是“四海之内”即“皆兄弟也”。我们就这样有了“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一在中国传统中流传两千五百年之久的格言。然而,虽已耳熟能详,但这一格言究竟在教导着什么,我们可能并不清楚,所以我们才应该问,如果天下人都是兄弟,或都成为像兄弟一样的人,就真的不再会有人与人之间的争斗,而和平——人类的普遍持久的和平——就可以在人间实现了吗?
三、《诗经》描绘的兄弟关系的两面:“兄弟急难”与“兄弟阋于墙”

上述这些疑惑或问题表明,“四海之内皆兄弟”这一总是被从正面理解和引用,似乎无可置疑的格言,其意义其实仍然暧昧不明。当然,这一格言在字面上并无含混之处,但此话其实却可以用不同语气在不同语境中说出。作为一个陈述或一个断言,这是肯定普天之下四海之内的人都是某种意义上的兄弟;而作为一个召唤或一个命令,此则可以是要我们——全体人类——努力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兄弟。的确,是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兄弟,因为这一兄弟关系应该不是一种“阋于墙”的关系,而是一种可以为对方舍生忘死的关系。而且,这一“某种意义上”的兄弟关系当然也不可能基于同一父母,尽管据说现代人类皆出于六万多年前在非洲的同一祖先。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成为,第一,本来意义上的兄弟关系为何不能始终保证兄弟之间不会“阋于墙”?这就是说,被认为应该相亲相爱相助的兄弟关系为何不能阻止兄弟的相争相斗相残?第二,我们——仍然分化为或分裂成不同国家、集团、阶级、性别的人类——如何才能在“四海之内皆兄弟”这一召唤或这一命令之下结束彼此之间经常远甚于“阋于墙”的残酷战争状态,成为真正相亲相爱相助的兄弟,从而实现人类和平?
四、中国历史上的兄弟相残:占有与权力
在中国历史上,兄弟相亲相爱相助的典故当然也有,但被记载下来的数量似乎远逊于那些兄弟相争相斗相残的著名案例。前者可以举出商代末年兄弟二人互相推让君位、最终耻食周粟而一起饿死于首阳山下的伯夷、叔齐,为了让三弟季厉继位而逃往蛮荒之地并断发文身的周太王之子太伯、仲庸,著名的“二十四孝”中因恐后母之子吃苦宁可忍受后母虐待而不让其父休妻的闵子骞,以及宋代苏轼、苏辙兄弟等;后者则可以举出舜之弟象屡欲谋害其兄,周公旦杀弟管叔鲜,最终演变为兄弟相残的“郑伯克段于鄢”,齐桓公小白之假鲁国之手杀兄子纠,秦二世胡亥之假诏杀兄公子扶苏,汉文帝刘恒逼死其弟淮南厉王刘长(这就是本文篇头淮南民歌“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所讽之事),曹丕逼死其弟曹雄及欲害其弟曹植,西晋武帝司马炎之逼死其弟齐王司马攸,刘宋文帝刘义隆诸子之间的相残,隋朝太子杨勇与晋王杨广、汉王杨谅之相残,唐太宗杀其兄太子建成及另一兄弟的“玄武门之变”,唐高宗李治杀庶弟吴王李恪,明朝太子朱高炽与汉王朱高煦、英宗朱祁镇与代宗朱祁钰、太子朱常洛与福王朱常洵等相斗相残,清朝清太宗皇太极与睿亲王多尔衮明争暗斗,以及清圣祖玄烨诸子之间被后人大大戏剧化了的所谓“九龙夺嫡”。这一还可以继续开列下去的名单尚不包括一些较少为人所知但却更为凶狠狂暴的兄弟相残,如五胡十六国时期后赵明帝石勒的子孙之间的互相残杀,以及五代十国时期南汉殇帝刘玢之弟刘晟(刘洪熙)弑兄夺位并杀害十八位兄弟中的十五位(最为疯狂的是在公元947年,同一天里竟有八个兄弟被杀)。
兄弟之间的这些相争相斗相残情节或有不同,而且或许有人也会对将周公旦和李世民等列入其中有异议,并对其他某些事例之是否属实存有疑问。如果篇幅容许,这些不同情节当然需要具体分析,但它们似乎皆可归结到一点之上,即追求占有,或追求权力。这里可能会被提出的一个反驳是,上述兄弟相争相斗相残之事几乎皆出于帝王之家(当然,我们之所以只看到这些也是因为,普通人没有历史,亦即并未被历史记载)。因此,是“罪恶的权力”——权力对人的诱惑,人对权力的追求——腐蚀了似乎本该纯粹的兄弟之情。诚哉斯言也!权力当然腐蚀人,尤其是“惟辟作威,惟辟作福”的帝王权力,即只要得到就可以任己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兄弟之情似乎抵挡不住这种绝对的诱惑、绝对的腐蚀,但这一能够绝对腐蚀兄弟之情的绝对权力又意味着什么?如果占有最终可以归结为对于权力的占有,那么对于权力的占有就意味着对于那能够保证“我”之占有的占有。“我”所占有者需要被保证和被保护,而“我”之权力就是“我”之占有的保证和保护。“我”要占有某物,但另一者可能也想占有“我”欲占有者。如果没有保护自己之所占有者的力量,“我”就可能失去自己所占有者。权力首先就是让“我”能够实现占有和进一步占有的力量。能占有权力者一开始总是那些能“以力服人者”,无论此力是否被美化为德,直到此种用以征服他人之力在传统国家中被结构化和制度化为可以继承——或可以争夺——的帝王之位。

五、兄弟关系何以并不保证相亲相爱相助:“我”作为潜在的谋杀者
兄弟之间的相亲相爱相助并非必然,而兄弟之间的相争相斗相害则随时可能发生,因此,中国传统中才有针对兄弟关系而大力倡导的悌道或弟道(其他传统其实也不例外),而兄友弟恭之事也由此成为中国传统中具有教化意义的美谈。需要表彰兄友弟恭之道恰恰表明,兄始终可能不友,而弟则始终可能不恭,兄弟之间的不友不恭始终有可能发展到兄弟相残,但我们这一传统中根深蒂固的信念仍然是:是兄弟就一定会相亲相爱相助。因此,男子为了保证彼此忠诚不贰就要拜为结义兄弟。结义兄弟的誓言是“不要同年同月同日生,只要同年同月同日死”,这是在说,虽然不是本来意义上的兄弟,但胜似本来意义上的兄弟,因为即使是亲兄弟可能也做不到共同离世或一起赴死。在中国文化中,刘备、关羽、张飞桃园结义传为佳话,以大哥宋江为首的梁山泊一百零八结义兄弟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但宋江的兄弟义气最后却表现为在自己临死之前毒杀对他最为忠心的结义兄弟李逵,因为担心他会在自己死后造反。这究竟是兄弟相亲相爱相助的极致,还是某种扭曲的或隐含的兄弟相残,论者可能见仁见智。中国文化中结义兄弟现象之普遍已经从某一方面表明,虽然历来不乏兄弟相残之惨剧,我们仍然深信兄弟必定因而也必须相亲相爱相助,所以本来意义上的兄弟关系才被扩展来表示非血缘关系的人与人之间的生死不渝之情,虽然排他性的结义兄弟远未达到“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境界,甚至还经常成为排他性的集团势力(黑帮团伙都是老大带领下的“兄弟会”,老大就是大哥或长兄)。
如果即使本来意义上的兄弟之间也会发生相争相斗相残,人们为何还会相信兄弟应该相亲相爱相助?这一信念的根源何在?本来意义上的兄弟是具有同一血缘的同胞,同一血缘意味着共同起源和共同归属,共同起源和共同归属意味着不同部分为同一纽带所维系。汉语中以“手足情谊”来描述这一共同起源和共同归属——我的手与足生于同一身体,属于同一身体,我们因而相信它们当然不会自相残害。源于拉丁语“frater”(兄弟)一词的英语“fraternity”(更通俗的说法是“brotherhood”)或法语“fraternité”也表达着同样的信念,所以这一意味着“兄弟关系”的“fraternity”或“fraternité”才也表示着“将人类大家庭的所有成员结合在一起的普遍之爱”,并最终成为法兰西共和国《人权宣言》的三大原则之一而在汉语中以“博爱”为人所知。这是欧洲版的“四海之内皆兄弟”。我们似乎久已习惯于假定,这样的兄弟关系应该就是人类关系的原型、典范或基础,所以“四海之内皆兄弟”才会成为我们的理想或我们的召唤。
然而,共同血缘之所以并不必然保证同胞兄弟之间的相亲相爱相助,乃是在于兄弟其实并非同一身体之手足,而是互相分离的个体,是每一人都会用第一人称“我”对自己兄弟说话的独一无二者。而“我”作为不欲受任何外在限制者,从根本说就是他人的潜在的谋杀者,因为正是他人阻碍“我”所追求的完全和绝对的占有。正是因此,基督教的第一戒律才是“汝勿杀”(Thou shalt not kill),而其他宗教也多有类似戒律。勿杀是不可杀人,佛教则将勿杀的戒律扩展至一切有生命者——勿杀生。这一戒律没有明确说出但已经隐含传达的恰恰就是,“我”作为“我”不仅是他人的潜在的谋杀者,而且也是其他生命的潜在的谋杀者。这一点只要想一下人经常表现的那种对动物的专横傲慢残忍冷酷就可理解。勿杀生即使仅对于佛教来说也不仅只是出于慈悲和怜悯。这里的根本问题是伦理的:“我”——如果“我”能够开始反问自己的话——有权利杀另一者吗?无论另一者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其他生命,也无论此杀是出于任何似乎可被辩解为正当的理由(例如为了营养),佛教的回答会是:否!杀是对另一者行使最绝对的支配,支配到无须再操心如何维持这一支配,而我其实却并没有权利支配另一者。正因为深刻意识到这一点,佛教才会将勿杀的戒律扩展至一切有生命的动物。
然而,“我”虽然也许从未想到要深切严肃地反躬自问是否有此权利,却似乎总会自然而然地知道或相信我有此权力。权利、权力——这对其中只有一字之差的现代汉语概念的区别与联系值得我们重新反思。“我”之不知自己是否有此权利,却(经常是不自觉地或自以为是地)知道自己有此权力,是因为“我”作为“我”即意味着占有,占有则最终意味着权力的占有。能占有已经是“我”之权力的显示,而占有了权力——由制度暴力即国家机器保证的权力——则可以保证进一步的乃至最终的、绝对的占有。追求权力和占有权力是“我”作为“我”之自发性。历史上所记载的兄弟相争相斗相残之事最终均归结为争夺和保证自己对权力之占有,而兄弟在此就是阻碍“我”之绝对占有或“我”之绝对权力的另一者。只要是他人就会妨碍“我”所追求的占有,“我”的兄弟恰恰就由于共同血缘关系而比其他人离我更近,近到可以最直接地妨碍“我”。“妨碍我”意味着,妨碍“我”的自由,妨碍“我”的占有,妨碍“我”的权力,或一言以蔽之,妨碍“我”对权力的自由的占有。正是在此意义上,兄弟才可能是“我”最欲消灭者,是“我”首先欲除之而后快者。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而在任何他人可能希望睡于我之卧榻旁边(或卧榻上面)之前,兄弟通常可能正是首先与“我”自幼即同榻而眠者。在此意义上,“我”之兄弟可能正因为恰好是“我”的第一竞争者而成为“我”最不能相容之他人,因为他这样就成为对“我”——对“我”的权力和对作为权力的“我”——的最大直接威胁。“我”即权力,而权力就是占有和控制和支配。在中国传统社会,帝王之位是权力的巅峰和峰巅的权力,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帝王之家的兄弟相残才最典型地表现了我对他人的绝对的不能容忍。一般来说,他人作为他人——作为另一者——就是需要“我”之容忍但又经常令“我”难以容忍者,而对于帝王来说,最不能容忍的经常就是兄弟这一不可睡在权力之榻旁边甚至睡于其上的他人。
六、兄弟作为唤起“我”之羞恶与辞让之心的他人:放之四海的兄弟关系

直到“我”能够开始反问自己,“我”是否有权利占有?这就是以羞恶之心为开端的义的发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义意味着公正。兄弟在此,在“我”身边,在“我”面前,“我”却要占有一切、支配一切,这公正吗?“我”难道不应该为自己羞惭并且憎恶自己吗?但羞恶之心何时才可能涌现,以至于能够让“我”辞让,或更准确地说,逼“我”辞让,甚至让“我”代兄弟赴汤蹈火?当“我”兄弟切近地站到我面前之时!因为,妨碍“我”的绝对占有和绝对权力的兄弟也是质疑“我”的占有和权力——“我”的自发性或我的自由——之人。“我”面前的兄弟本身对“我”就是一个质问,一个可以让“我”向自己提出问题的人,一个可以让“我”怀疑“我”从未怀疑过的占有和权力的人:“我”凭什么就应该占有这一切?兄弟本身的存在或兄弟的存在本身就已经是对“我”的一种可怜的恳请:请看顾“我”,请勿害“我”,因为我们同父同母,我们有共同的血缘。具有传奇色彩的七步诗故事以生动的戏剧性表现了这种恳请。据说曹植在其兄魏文帝曹丕的威逼下已经成诗一首,而作为帝王的曹丕仍不放松,要求其弟再以“兄弟”为题于七步之内作诗一首,不成即要严惩。兄欲据弟能否以“兄弟”本身为题立即作诗一首而决定惩罚与否,似乎颇具反讽意味。曹植于其兄限定的时间之内吟出了那首著名的短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可能是中国传统中最为人知的恳请兄勿害弟的文学话语。作为兄长的曹丕欲害其弟是因为他不能容忍任何他人妨碍作为帝王的自己对权力的绝对占有,尽管其冠冕堂皇的理由似是要约束弟之行为之不检,而作为他人的弟弟曹植,则在其兄面前以其针对这一相残局面的诗作,最切近最直接地质疑了其兄潜在的谋杀冲动。
因此,兄弟是“我”在追求占有和权力——占有的权力和权力的占有——的自发或“自然”道路上可能最会妨碍我的他人。然而,首先能够质疑“我”之自发性的可能也是兄弟,因为兄弟是不止一个意义上的与“我”最近者。正是挥之难去的兄弟置“我”于对自身之存在的疑问之中,因而也置“我”于对兄弟的不可抵赖的应承或责任之上。兄弟在此既是“我”的同胞,也是另一者,是他人,是“我”必然已经为之和必须继续为之做出应承和负起责任者。只有由此出发,真正的兄弟关系,一种超出单纯的家族和血缘的兄弟关系,一种超出郑庄公与共叔段、齐桓公与公子纠或李世民与李建成式的相争相斗相残的兄弟关系,一种不仅抑制了自己的潜在谋杀冲动,而且甚至可以为兄弟牺牲自己的关系,才有可能建立。因此,在一个据说伦理道德久已处于全面沦丧的危险之中的时代,问题并不在于单纯以加强说教的方式重新提倡传统的兄弟之谊、手足之情、骨肉之爱,乃至天下四海人类之和,而在于首先鼓励人回到人皆有之的恻隐之心和羞恶之心。二者则皆由他人为“我”彰显。“我”是被他人置于必须做出应承和必须为之负责的地位之上的,而“我”之兄弟虽是同胞,也是他人,而且首先或经常是与“我”最近之他人。面对他人,“我”之恻隐之心会被触发。面对他人,“我”之羞恶之心开始萌动。“我”于是能够开始为自己羞惭,质问自己为何就该占有,就该支配。“我”并不是自愿友爱,自愿为善,而是面对他人即不得不如此,就像将入于井的孺子很难让“我”掉头不顾一样。如果“我”出于利害考虑而在孺子面前最终一走了之,则必然会在事后为自己没有伸出援手而感到羞惭和懊悔。真正的兄弟关系——一种并不需要也并不可能建立在血缘之上的兄弟关系,一种普天之下四海之内的普遍的人类兄弟关系——由“我”必然要对他人做出的无条件应承开始,而人类和平也必然由此才开始有切实的基础和实现的可能。
人类和平——除了意味着每个独一无二的说“我”之人能在面对他人之时由于被唤醒和被激发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和辞让之心而抑制自己固有的潜在谋杀冲动,对他人做出无条件的应承,为他人负起无止境的责任,并运用由此而生的辨别是非的智慧即孟子所说的“是非之心”以在人间确立公正的关系和秩序,让所有人皆可受到一视同仁的善待,从而无限地推迟可能的战争的到来,人类和平还能意味着任何别的什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