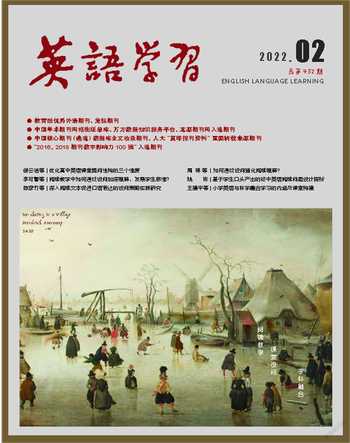蒲柏的宗教世界观和新古典主义文艺思想
文 / 耿瑞
引言
新古典主义在法国的盛行,与当时欧洲弥漫的理性氛围以及科学进步有关。在十七世纪上半叶,经过一场狂热的宗教战争后,欧洲社会的思想氛围开始朝着理性的方向倾斜,自然科学成果更是加剧了这种倾向。法国新古典主义强调遵循理性,摹仿自然,这也是十七世纪中叶整个欧洲的特征,仿佛整个宇宙都在按照一成不变的规则运行。法国古典主义者多半是笛卡尔的信徒,“我思故我在”承认上帝必定存在,上帝即最高和最完满的实体;唯理论是“天赋神授”的,这是一种类似本能认可的秩序原则。由于新兴资产阶级的力量很薄弱,这种妥协性也体现在文学上:高乃依、拉辛等古典主义者只能在王权的庇护下谋求发展。
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深受法国古典主义的影响,他的作品有明显摹仿布瓦洛《诗的艺术》的痕迹。布瓦洛崇尚的理性是蒲柏古典主义文艺理论中的自然,也是笛卡尔在《方法论》中所说的“良知”,即一种普遍永恒的人性,因此具有普遍性,并能以不变的标准来检验艺术之美,而无论理性还是自然都是“天赋神授”的,毕竟产生于十七世纪的法国古典主义文艺是以君主专制为背景的,穿着罗马帝国“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马克思等,2012)。
相比于其他英国新古典主义批评家,蒲柏的态度似乎更加刻板,仿佛没有受过莎士比亚的伟大文学传统影响,而是与他所推崇的贺拉斯、朗吉弩斯和布瓦洛等人若出一辙。但笔者认为,蒲柏对新古典主义的理解是比较宽容和开明的,《论批评》不是对布瓦洛的复制,而是蒲柏的理性信仰“迎合”时代的产物。蒲柏的理性是上帝心灵的反映,跟阿奎那的理性与信仰不谋而合:他们并不盲目崇尚上帝,而是在理性的上帝中认识宗教的普遍性和包容性,认为上帝的理性是最完美的理念,而自然是造物主的理性,艺术的过程必须摹仿自然的过程,艺术摹仿自然就是摹仿造物主心灵的过程。这种哲学依据不仅反映了蒲柏处于君主专制的阶级统治背景,而且也流露出他的宗教宽容和反宗教主义的信念。出于天主教徒的敏感和普通教徒的信仰,蒲柏痛恨政治动荡带来的变化,于是他从政治的束缚中解放自己,不属于辉格党或者托利党。这里也不妨说,蒲柏的文学批评观顺应了当时的政治审美情趣。那些不信奉英国国教的人是“被动的雅各宾派”,而蒲柏由于身体上的残疾和宗教的信仰在“政治”面前全身而退。他把自己的所有观点都向宗教“坦白”。因为害怕得罪人,他只能以隐晦的语言呈现他的古典文学批评观点,也会下意识地在两个完全对立的教义之间转换,所以作品的宗教特征模糊不清。
蒲柏的批评观给人的感觉不是无缘无故的驳斥,而是有特定的批评对象暗含其中。笔者认为,这个假定的“敌人”便是与他宗教信仰相悖的观念。蒲柏注重克制、适度和整体性观念,抵制傲慢自满、狂妄自负、主观臆断和浅尝辄止等思想,这都体现了他迎合天主教教义中的秩序和规则:上帝是自然的创造者和艺术家,上帝安排和控制着宇宙普遍存在的神圣秩序,“最好的诗歌和最好的批评都受到神的启示”(Pope,2008),评论家应向神寻求灵感。总的来说,蒲柏的古典审美原则是笛卡尔唯理性是尊和道德规律的体现,合乎君主专制时代的社会要求,理论上同阿奎那的理性信仰有异曲同工之妙;他确立的“教养”,跟柯勒律治提出的“普及教养 ”相似,都是神学提供的“循环不息的血气和生机”,不过因为不敢跨越思想的界限和社会的秩序,蒲柏的古典审美原则遂含有进步和落后、革命和保守的二重性。
“才子”的降临:理性与信仰
蒲柏出生在一个罗马天主教家庭,由于当时英国法律规定学校要强制推行英国国教,因此他既不能上主流学校,也不能上大学。他童年时代的家庭教师都是牧师,并且都是拒不加入英国国教的天主教徒,他最终在教派中选择了皈依天主教。由于天主教徒处处受到鄙视和暗讽,在蒲柏的早期生涯中,他曾拮据到买不起一本书;文学上的成功招致的种种嫉妒也是他受到很多拒绝和迫害的原因,这些都推动后期蒲柏强烈的反宗教主义思想的形成。此外,蒲柏身患多种疾病,从小就驼背跛腿,身高不到1.5米。尽管求学和仕途之路十分坎坷,他却笃信天主教的独立和自觉,并强烈渴望生活中的独立性和适度性。他花13年的时间翻译了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并编撰了《莎士比亚戏剧集》。没有一种坚定的宗教意志支撑,在那样的时代,即使具有惊人的才华也很难如此高产。而在十八世纪早期和中期的英国,以反对天主教为基础的政治文化,必然使他得到一种不同寻常的宗教文化经历,正是这个经历使得他远离了被宗教政治深深笼罩的宗教争论。
虽然蒲柏希望自己不是虔诚的天主教徒(Papist),也不认为自己是“罗马、西班牙或法国天主教徒,而是一名真正意义上的中立派天主教徒”(Sherburn, 1956),但后人知道,这里“真正”的含义是具有包容色彩和反宗派主义的。同时,他的爱国之心也可见一斑,他不希望再看到国家分裂,憎恨傲慢的、权威至上的天主教徒。蒲柏出生在“光荣革命”的年代,他选择继续做一名天主教徒,一方面是出于对父母宗教信仰的传承;另一方面,他的天主教徒身份能够使他作为受保护的局外人去看待这个否定他的宗教世界。在早期的创作生涯中,蒲柏被指控为异教徒,因为他认为“机智正如信仰,适用于每个人,对于信仰某个宗派,所有周遭都要受到诅咒”(Pope, 2008)。同时,他“谴责自然神论的教义、实践和倡议”(Atkins, 1972)。可以说,蒲柏不是任何宗教的奴隶,与其说他有异教或天主教信仰,毋宁说他是带着宗教的自由主义、普遍主义和反宗派主义思想来表达对俗世的一种兴味关怀。他在《论批评》的开篇就表明,真正的批评家会认识自己和自己的造诣,熟知天才、趣味和学问的高度,懂得自己的极限。这种自我认知是宗教中的“认识自己”原则,即唯有了解自己,才能认识自己的欲望和意志;虽然人不能够摆脱欲望,但能够根据意志去有效地控制欲望。“人在万物中的位置脱离不了堕落和救赎”(蒂利亚德,2020),人不认识自己就跟兽没有区别,无法控制欲望。
蒲柏处在意识形态转型期,他的自我认知原则受到了自然科学和启蒙思潮的影响,因此他的天主教思想也具有自然化和理性化色彩。自然是从蒙昧中拯救人类的手段,也是十八世纪欧洲最重要的主题之一。自然主义思想和理性观念变成了人类的启蒙和信仰,“对于宗教也形成了一种普遍的宽容”(马弦,2013)。蒲柏在诗中表达了一种神圣的秩序与规则:自然是宗教中普遍主义的和谐,这种和谐是辩证统一的,“荷马就是自然”“摹仿古人就是摹仿自然”,宇宙间的一切事物都在自然秩序之内,艺术的各种规则汇集在此,“共同凝聚成普天下人类共同的大合唱”(Pope,2008)。蒲柏号召摹仿古人的艺术,这里的摹仿并不是对艺术或自然物本身的摹仿,而是要摹仿“自然的过程”。“跟随自然”即是跟随上帝创造自然的方式,因为他认为艺术本身能鉴赏自然的产品,却不能制造自然,只有神能创造自然。进一步看,这个自然就是上帝。蒲柏的“自然”和阿奎那对“摹仿”和“自然”的解释标准一致,都把“摹仿自然纳入了基督教神学的传统”(章安祺等,2007),自然里有存而不论的上帝。艺术作品起源于人的心灵,而人的心灵是上帝的受造物,艺术的伟大在于上帝的心灵是自然万物的源泉,万物都是互相关联的。艺术摹仿自然就是摹仿上帝心灵的过程,反映了受造物心灵的理性形式。艺术家荷马等的创造性得益于上帝的形象和创造物,摹仿古人就是摹仿理性的形式,这种摹仿体现出了神圣的智慧和美。
1660年查理二世的复辟结束了内战,但1679年天主教密谋暗杀查理二世的谣言曾被用来煽动一些强烈的反天主教情绪。“光荣革命”为新教的继承铺平了道路,有许多人试图恢复天主教,但处处受到压迫和排挤。在这个转型期的社会变革中,政治上的不稳定为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们增添了失望和虚无的情绪,于是用理性之光启迪人们心灵的启蒙主义诞生了。蒲柏顺应时代思潮的变化,拥护牛顿的自然法则,秉承洛克的理性,反对宗教狂热,赞同笛卡尔的理性主义秩序和体系,主张讲究形式和规范、理智和平衡,于是十八世纪的新古典主义应运而生。蒲柏的古典主义当然也体现了强烈的理性气息,他在为牛顿写墓志铭时说:“上帝说:‘让牛顿降生!’于是一切全都被照亮”(Butt,1963)。蒲柏对人类的力量充满自信,认为现实世界的一切活动都遵循一定的规则,人类可以通过理性把握这种规则。他的天主教理念就是恪守规则和“寻求理性的信仰”。归根结底,理性和信仰之间的联系是建立在一种信念上:人们理解一个真理,然后所有的真理都参与到最终的真理,即上帝之中。赞美上帝是神学最基本的形式,蒲柏在《论批评》开篇就说“最好的诗歌和最好的批评都受到神的启示”(Pope, 2008)。他在另一部作品《人论》中暗示,他的写作目的是“为向世人昭示天道的公正”、解释邪恶的存在、探索人在宇宙中的地位。蒲柏相信上帝创造了一切,并且将宇宙万物安排在各自的位置,相互牵连和制约,形成了“伟大的生存之链”,整个自然和宇宙都是上帝的艺术杰作。他所诉诸的理性,不是启蒙哲学家们宣扬的个体主义和世俗的理性,而是阿奎那和其他中世纪思想家所说的理性,是人性中普遍存在共有的东西。阿奎那是一个信奉原罪的天主教徒,对他来说,“自然法最根本的含义是行善和避免邪恶”(Cunningham, 2009),人性中存在种种弱点,理性的认识由人的信仰得以完善,上帝是绝对真理,理性真理最终归结为上帝真理。这个真理是人性中普遍存在的共有的东西,它接近于浪漫主义者强调的普遍原则(universals,亚里士多德的说法)。不过浪漫主义反对一味遵循先人的作品,而蒲柏恪守摹仿古人的传统。他的这种矛盾的观点正是出于天主教对他的影响。那时的社会反对天主教的一切神谕,于是在表现艺术的技巧之中,蒲柏不断地含混自然和信仰的界限,迎合社会现状,丝毫不流露他内心常存的“半信半疑”的信仰。天主教普遍抵制完美主义的观念,认为只有纯洁的、未被玷污的、完全顺从的成员才算完美,而这样的人根本不存在,所以“犯错者为人,谅错者为神”(Pope, 2008),人性都是有弱点的。他赞同古典审美理论都认同的主张,即艺术家应该“解释宇宙的奥秘”,只是他的这种“奥秘”蒙上了神学的面纱,增添了信仰和虔诚的能量。阿奎那是在基督教的原教旨主义话语中解读意志与理性的,而蒲柏明显有阿奎那的那种把理性主义渗入信仰的特点,这也说明了蒲柏与阿奎那一致,都在用天主教和基督教双重信仰的视角看待理性的上帝。
天主教的道德整体观
人类的自由使得人类成了道德行动者,根据行为的道德判断选择对与错。天主教不认为人的行为是被事先安排好的,人们会根据自己的判断来选择善抵制恶。传统意义上,这种判断叫作道德良知,唯有道德之人才具有这些美德,因为他们对凡事都没有过于偏爱,能做到“避免走极端”“不超过自己的能力谨慎行动”(Pope, 2008)。避免片面走极端的办法便是专注于传统,正如艾略特的个人服从传统的观点一样,蒲柏既避免不同又保持这种对立,如他所言:“才智和判断力经常对峙,这意味着互帮互助,就像夫妻间的扶持”(Pope,2008)。传统是天主教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传统意味着“传福音”,这与蒲柏强调的新古典主义传统不无关系。
作为天主教徒,蒲柏恪守古希腊和古罗马诗人的创作风格。蒲柏相信,“福音”从开始到今天一直被传授、保存和流传下来,所以批评家“学习古老的规则,效仿自然(造物主)就是效仿古人的规则”(Pope,2008)。同时,只有当自然和巧智真正达到和谐和统一,人类才能在上帝的规则指挥下融入这个整体的和谐秩序中。巧智意味着和自然一样重要的感知,与我们所说的智力或想象不同。巧智这个词在《论批评》中平均每十六行出现一次,似乎在呈现一种各司其职的等级。巧智也意味着与上帝同在,是真正反映自然的结果,但 “艺术如此广大,巧智如此狭隘”(Pope,2008),艺术是整体,巧智是部分,遂应让巧智顺从艺术这个整体,才能实现和谐统一的美。“所思寻常有,妙笔则空前”(Pope,2008),有了“艺术”整体上的神圣和光辉,巧智才得以在“自然的感动和震撼中得到陶冶与提升”(Hooker,1959)。蒲柏的思想中有着天主教教义中的整体意识,这种强烈的整体观体现在“无论局部因素如何惊艳,都不会产生非凡效果,但如果将他们和谐统一起来,形成一个整体,就能展示出震撼的美” (Pope, 2008)。他的反宗教主义思想贯穿在整体和谐的文学批评和艺术创作中,美的源头是整体,局部的不和谐乃是上帝有意为之,是为了让“伟大的生存之链”和谐美好。同阿奎那的观点一样,蒲柏也认为只有在整体的大背景下思考道德生活,跟随上帝,才能完成人类生命的轨迹,要坚信上帝并回到上帝那里安守各自的位置,才能获得幸福。
蒲柏的“中庸”()在于他“不是任何宗派的奴隶”(Atkins,2013),反宗教主义和包容主义是蒲柏的审美原则。他曾对朋友坦言,他不属于任何国别的天主教徒。他的古典文学审美也践行了这一包容主义,以避免产生过于极端的积极或消极的结论。从本质上讲,这一包容和普遍主义传统也具有自然神论主义色彩,但他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批判了自然神论的教义,所以他不太可能信仰自然神论 。蒲柏的研究学者阿特金斯认为蒲柏的反宗派主义不是拘泥于教义的自由主义,而是作为普通信徒的信仰,并用德莱顿和艾略特的作品来对比这一论点。笔者认同这一观点,蒲柏在天主教和国教之间来回转换,甚至他自己都认为“它们之间没什么不同”。像蒲柏这样感知力非常强的诗人,他肯定能很明确地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和想法。他认为“好行为要比好信仰更重要”(Cruttwell, 1960),因为普通生活的“表象”和“现实”一样重要,普通生活就是“表象”,为了社会群体乃至国家层面整体的和谐,人们没必要纠结自己到底是皈依何种教派的“现实”,只要“迎合”生活的整体和谐就是对的。
蒲柏是否只信仰天主教暂且不论,但他的古典审美原则确实具有强烈的人性关怀,他不希望社会再次出现分裂,他的整体观也是出于迎合英国社会现状的一种回应。和大部分的奥古斯丁天主教徒一样,蒲柏愿意相信“现代奇迹”,比如他的古典审美原则、相信天使的存在等,而这些“奇迹”都是罗马天主教不赞同的。为了迎合社会主流的新教,他弱化自己的宗教倾向,只能做自由主义信徒。当他的医生沃巴顿问他原因时,他给出的理由是“不想树敌和不愿给任何人带来坏处”(Cruttwell,1960)。他质疑宗教转换会给社会带来坏处,却又时常在新教和天主教之间转换古典的审美态度。唯一不变的是他的宗教道德规则,这也是有益于社会的宗教宽容的关怀规则。他认为诗歌的规则是符合诗歌本性的,和宗教道德规则一样,是自然规律的反映。他在诗歌中没有刻意求新,而是迎合社会,以最易于读者接受的方式揭示教义的道理。蒲柏认为人类必须形成好的道德良知和行为规范,并培养谨慎、公正、节欲和不屈不挠等美德,它们与神的信仰、希望和上帝的爱并肩前行。他的“中庸”和普遍主义思想乃是天主教徒的道德整体意识使然。
笔者认为,蒲柏又是十足的基督教道德主义者,他强调的自我认知深受伊拉斯谟的基督教道德影响。伊拉斯谟认为,人的最终胜利在于认识自己,认识自己是通往美德的大门。“认识自己”包含很多道德知识,而蒲柏巧妙地从奥古斯丁基督教的层面来让自己保持在中立状态。无论是包容主义,还是迎合社会的做法,都是蒲柏意在凸显的终极人性价值,他执着地调和亚里士多德的理性和基督教神学这两种权威,强调道德意义上的信仰,摒弃种种人性中的陋习。这些和阿奎那的理性信仰看起来有很多共同之处,他们都试图理性地思考上帝和事物的本质,用理性论证上帝,对理性的世界既虔敬又进行了严肃的考量,只是蒲柏没想过从审美批评中表达他所归属的宗教,更不想违背他的天主教祖先的智慧。
傲慢与谦卑
批评家需要公正的判断和谦卑的自我认知。蒲柏认为上帝是公正的,没有任何人会在“存在的大链条”中占有有利的地位,公正就是秩序。同样,蒲柏也认为评论家应该避免骄傲,应该尝试去感受和分享作者的写作精神。新古典主义作家的作品大多包含讽刺和说教,以抨击人类的“骄傲”。在误导人们形成错误思想的许多原因中,傲慢是“傻瓜们屡试不爽的恶习”。蒲柏提醒批评者:“作者不能完成比他想要的更多”,在每一部作品中都要考察作者的意图。真正的批评家应该具备诚实、谦逊和无畏的品质,并祈盼从“愚蠢的骄傲”中解脱出来,拥有包容性,“教我体会别人的苦楚,隐藏目睹之过错,我宽恕对人,人宽恕对我”(Pope,2008)。蒲柏发现教会只是一个教派,教会也是存在偏见的,唯一能去除偏见、保留公正的做法是“中庸” ,它应是每个人拥有的一种思维能力。批评家要特别提防“愚蠢无知、头脑空虚、内心顽固的骄傲,它是愚人们无法躲避的罪过”(Pope,2008)。若人产生了骄傲,就企图超越上帝给他安排的位置,那样就违反了自然;骄傲会使批评家和诗人都忽视真理,使得他们无法运用智慧和判断力。克服骄傲的办法是运用恰当和正确的理性,“让正确的理性驱走乌云的阻挡”(Pope, 2008),避免盲目自信、“极端的傲慢”或主观臆断,虚心听取来自朋友甚至仇敌等各方面的意见,并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认识到学问上的浅尝辄止、狂妄自负和自娱其好等都是为了满足一己私欲,都是不良的错误行为,忽视了艺术真正的价值。骄傲是恶德之一,批评家要提高道德要求,将道德和古典审美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拥有良好的“教养”和明辨是非的判断力。诚然,这些还远远不够,“傲慢在机智失败时进行诡辩,填满了所有的空虚感”(Pope,2008),那么人类如何抵制“傲慢的诡辩”,才能抵抗人性中种种弱点的诱惑呢?或许这就是蒲柏要表达判断和关怀的途径:通过宗教上反对傲慢的办法来解决批评家可能会犯的错误。天主教神学的最基本信念是由于原罪的影响,人类生而有缺陷,而治愈的良药是上帝给予人类最体面的礼物,这个良药就是谦逊和自我认知。
在宗教的艺术观中,正如在生活中一样,最受赞誉的是谦卑法则和对无度的限制,《论批评》通过使人谦卑的方式来完善理想的批评家,并认为把人性和知识结合起来的毫无偏见的批判家才能臻于完美。这种人性包含同情和判断力,判断力内在于同情中,正如批评内在于文学中。蒲柏的观点切合了《哈姆雷特》中展示的人:“在行动上像天使,在理解力上像上帝,但又可能有一切卑劣”(蒂利亚德,2020)。与其说人类有天使般的行动力,毋宁说天使教会人类谦卑的摹仿,“天使不敢涉足之处,笨伯争先涌入”(Pope,2008),这种愚蠢的“笨伯”之所以不如天使谦卑,是因为人类的判断能力具有局限性。蒲柏用阿奎那对比天使与人的方法来揭露人类的自大和无知。阿奎那认为人的认识能力有三个等级,最高的是天使的认识能力,这种能力所认识的对象是个体质料的形式,是个体事物的知识,而人的认识能力不纯然是身体器官的活动,而是包含身体形式的灵魂,人只能借助个体事物去认识抽象的事物。换言之,天使与人的区别是天使的理解力是本能的,而人需要经过学习理性去抽象才能获得,不能直接把握事物的本质,而“笨伯”却总是自我感觉良好而不去虚心学习。学习是人特有的属性,唯有通过学习,“笨伯”才能够部分地了解上帝的意识。所谓学海无涯,人类的能力总是有限的,所以人要学会谦卑,不能狂妄自大,学习智者(天使)谦卑,不轻易铤而走险,才能逐渐认识事物的本质。谦卑也是天主教里重要的道德教义。天主教非常关注并且宣扬谦卑准则,这也是蒲柏对当代批评家的建议,更是对自己作为教徒克制的体现。蒲柏的古典审美原则确立的“完美批评家”确实是出自天主教的道德良知,对“完美”的定义应该具有既兼顾整体又不失偏颇的“公正”。这些都是克服傲慢的正确理性,这种理性源自天主教徒的虔敬,理性也是谦卑的必然结果,他的古典主义审美思想也得益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