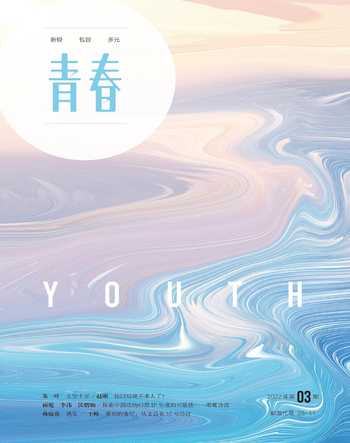童寯的客厅:从文昌巷52号经过
王峰
无数次从南京文昌巷52号经过,我并没有见到一只猫。
那只猫,我是在童明的微信头像上看到的。它四脚凌空,一往无前,正跨过那灰蓝灰蓝的天空,把身后凌乱的电线甩出几条生动而优美的弧线。
猫曾经在文昌巷52号院子搅起阵阵声响,在一位被世人遗忘的建筑师的画纸上留下过些许踪迹——童寯老人生前虽然不苟言笑,但很喜欢猫,在门上特意给猫留了个小门,方便猫进出起居室。
我是在杨廷宝的作品展上见到童明的。由于涉及大量建筑作品和历史资料,这场展览由两位中国工程院院士和一名东南大学教授共同策划设计,以纪念杨廷宝先生120周年诞辰。或许是随手拎的帆布包里装了太多建筑同仁惠赠给他的书,或许是忙于布展劳累所致,五十出头的童明看上去身体削弱,一张谦逊的脸浮游在人群中,这让他成为当天活动的一条略嫌低回的暗线。
开幕当天,童明同时以东大教授身份导览了这场展览。在其中一件作品面前,童明不由停了下来。童明介绍,这件作品当年因经费紧缩并没有按杨廷宝的设计完成,最终是按另一位建筑大师童寯的方案完成。童寯正是童明的祖父。他所指的这件作品,正是位于南京中山北路的原国民政府外交部办公楼,这也是童寯当年加入华盖建筑事务所后参加的第一个项目。其时,杨廷宝所在的基泰和童寯参与合伙的华盖,在上海和南京的不少项目上有过较量和竞争。
童明的讲解点到即止。
就在这一年的前一年,纪念童寯先生120周年诞辰的活动,以另外一种形式进行。
童寯只比杨廷宝长一岁,二人出生同月同日不同年,先后进入清华学校和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学习。后来,杨廷宝和童寯二人又在南京一起共事数十年,童寯曾表示:“我和杨廷宝到美国在同一所大学学建筑专业,学的课程一样,生活工作一样,观点又凑巧一样,在学术、技术、艺术各问题上,我们没有争论过,不是由于客气或虚心,而是由于看法一致。研究室在处理问题上,只要是他说过的,我就不重复,完全同意。”
杨廷宝去世后,童寯在病榻上为其写下悼文《一代哲人今已矣,更于何处觅知音》,稿纸有多处被泪水浸湿。文章大部分的篇幅是温馨的回忆,描述了他和杨廷宝人生轨迹的诸多重合之处;悼文末尾的一句话是:“作为我的知心朋友之一,他的下世,对我尤其是进入桑榆晚景的老境,打击是难以用语言形容的。”
杨廷宝离开后的第二年,童寯去世。
童明是在后来才知道,同为建筑博士的妻子悄悄写了一本关于童寯的书。张琴曾表示,她第一次见到童寯是1990年夏天的一个晚上,穿过一条又窄又长的通道,推开客厅的门,乍然惊见他在墙上的镜框中瞪着她。逝去的时代,就像一团看不见摸不到的迷雾,却凝聚着活生生的具体的人和事物。张琴试图从一个人的角度写那一代知识分子身上的时代性,其聚焦点让人恍然明白,那个年代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拨开历史的层层迷雾,走近那个群星闪耀的年代,那些彰显出人物个性和命运的细节总是分外打动人:其时,尽管在事务上有竞争和较量,但华盖建筑事务所的赵深、陈植、童寯三位合伙人,和身处基泰的杨廷宝保持了终身的友谊。在“中国建筑四杰”中,童寯与杨廷宝更是肝胆相照。关于童寯后来为何未能应梁思成北上的邀约选择留在南京,有一种说法就是,童寯舍不去与杨廷宝、刘敦桢的交情,“更有三位夫人及三个家庭之间的和睦亲善之情。”张琴在其《长夜的独行者》中写道:“童寯生性封闭,不喜交际,在南京和杨廷宝、刘敦桢以及张钰哲的友情是他漂泊人生中最大的慰藉。”
在这本书中,张琴还写到,童寯在原南京军区总医院开刀,听到杨廷宝因突然发病住院而子女一时赶不回来,就让两个儿子中的一个去照顾杨廷宝。后来,是童寯长子童诗白在杨廷宝那里住了一整夜,一直到第二天等杨廷宝的侄女赶到才回家。童寯出院后,不顾自己极度虚弱的体质,硬是要到病房探望杨廷宝,“两位老人,两双手长久握在一起,不舍分开。其情其景,让在场的所有人都为之动容。”后来,在从北京治疗回南京后,童寯又第一时间让儿子童林夙陪同去看望杨廷宝的遗孀陈法青。童林夙在世时回忆:“他回到南京第一件事就是要我踩三轮车,带他到杨廷宝伯伯家和刘敦桢伯伯家看望杨伯母和刘伯母。因为刘伯伯和杨伯伯两位老人都先后过世。”即便老人相继去世,他们的后人还在延续父辈留存在学界难能可贵的友谊。
显然,童明没有去宣泄这些内容。当天的主角只有杨廷宝。
展览现场的人群中,有人在窃窃低语,“我们去听听童老在讲什么。”童老,在几十年前,这是建筑人对童寯的专称。目光所到之处,童明的手正指向杨廷宝为孙科设计的作品。
2020年是童寯先生诞辰120周年,这一年,童家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童明的父亲童林夙教授去世,一是童明将工作关系转至东大。童明说:“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方便修缮童寯纪念馆。”我见过他在上海武康大楼前拍的一张宣传照片,画面尽得海派文化精髓,童明正沐浴在一片黑白调的光影当中,他独自撑着一把伞,太平洋的风正从东边吹来。
而在南京,他坐在咖啡馆一隅,等他拿出童寯住宅的改建方案时,脸一下子亮堂了起来。
文昌巷是一条极具南京特色的街巷,有持续热闹的时候,也不乏片刻的清靜和寂寥。从外面看,位于文昌巷52号的童寯住宅,似乎只是一座普通的老式清水墙建筑,一点也看不出有任何设计过的痕迹。如果不是从院内挂墙伸出几枝植物,它更像是一面水泥墙壁。这样一座由童寯本人自行设计建造的住宅,至今已有74年历史,甚至一度被东南大学建筑系作为小住宅样板,组织学生参观实习;2002年则被列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
童寯住宅主楼为英国别墅风格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采用毛石墙基座、红砖清水外墙,斜屋顶上覆以红色平瓦,朝南为大面积白色玻璃窗,自然采光充分,空间流畅;北侧设有门房;房屋四周为庭院,院内植有火焰松和木兰等各类花草树木,全年常青,四季花香。童明说,童寯住宅在建筑学领域具有重要的价值,“在南京仅有杨廷宝故居与之相应,在全国范围更是寥寥无几。”
童寯去世前后,童寯次子童林夙教授一直居住在文昌巷52号,直到2020年因病去世。童家后人很早就对童寯住宅的处置达成一致,即对其进行长久維护,使之发挥更大的社会效益。为了能够更好地疏解并承担日常营运及展示功能,使童寯住宅本体能够完好保持原状,以历史原貌进行展示,其西侧将建设附馆,一方面将为童寯纪念馆的日常营运提供必要的使用空间,而且也可以结合周边环境的整治,为纪念馆营造更好的历史文化氛围。也就是说,除了童寯住宅本体、中部绿化庭院,以及整修扩建的后屋部分,童寯住宅西侧红花地绿地经适当改造,将建造200平方米左右的附属建筑。
这个新增加的附属建筑,从南到北,由四个不规则的屋脊构成,整体呈斜坡折叠式;和童寯住宅本体屋顶一样,都是一溜红色,极具动感和现代性;现有场地中变电箱将通过与加建建筑融合设计的遮罩进行隐藏,使用和立面材料相同的竖向格栅进行装饰。完工后的童寯纪念馆将形成东、西两个可分可合的布局关系:东部的童寯住宅作为纪念馆主体建筑进行展示,定期对外开放;西部的附属建筑平时通过童雋故居原有入口进入,同时也可通过另外的独立次入口进入。这座重要的民国建筑将承担收集、整理、展示和研究功能,转型成为一座有关中国近现代建筑发展历史的小型博物馆。
在祖父的手笔附近,埋下一颗种子,让它自然生长,长成它自己该有的样子。
作为童家唯一继承祖父建筑衣钵的后人,童明再次被推到了前面。
童明自称是这个家族的守护者,有着不能逃脱的义务感,“像一只风筝,无论飞多远,都被一根线牵着。”他也曾试着逃离过,结果总有一只无形的手将他再次抓回来。这个家族的人,身体里似乎总流淌着一种逃脱的因子。童明的父亲童林夙,当年是因父亲一人在南京孤苦无依,被从北京调回来的,并且从事了一个跟此前并不相关的专业。等到童明的兄长童文高考时,他的第一志愿是还没更名为东南大学的南京工学院无线电系,而第二志愿是建筑系。那一年,他超常发挥,在得知他的成绩后,童寯把自己用过的三角板、丁字尺等建筑制图工具悉数捐给了学校的建筑研究所。童文后来成为华为5G首席科学家。
等到1986年,童明参加高考,其时,童寯已经去世三年,但祖父的影响依然还在。当时,“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观念正流行,童明填报了数学专业。表格上交不久,家里人接到童明三爷爷童村从上海打来的电话,向他们严肃提出要求:一定要将专业改成建筑!他希望家族最小的孙辈能继承哥哥童寯未完成的事业。童明的母亲为此与他谈了半天,童明同意了,一口气在东南大学建筑系读了七年书。研究生毕业时,童明计划又一次逃离,这一次,他想去的地方是美国,最后却仍以失败而告终。对这段经历,童明后来有着明晰的回忆,可见此次逃离对他人生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总算撑到最后去乌鲁木齐路的美领馆办签证。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排队很长,几乎一直排到复兴中路,两三个小时也就刚到门口。进到里面又是乌压压的一堆人,好不容易挨到窗口,一个上午就已经过去了。我觉得他们是故意将签证窗口设计成那样的,里面的地平要比外面高20—30厘米,再加上签证官估计要有2米多高的个头,给人的感觉就像是站在当铺的台阶下,不由得气短。当时给我做经济担保的是我在美国的堂兄,签证官问到谁作经济担保时,我就顺口回答了my brother,结果似乎就给他提供了一个口实,任凭我再怎么解释我们家里习惯将cousin都叫哥哥,也没有用了,似乎你就是撒了一个弥天大谎。花费两年的时间,为的就是这一时刻,但却被很荒诞、很轻描淡写地废掉了。两年中各种各样的辛苦,最后就这样被轻飘飘地废掉了。当时感觉脑子一片茫然……
童明后来去了上海,他说是为了爱情,那个后来为童寯写了一本小书的妻子去了苏州,而上海离苏州似乎要近一些。童明在同济大学读博士,一直读到最后留校任教,其研究方向也从建筑设计转向城市规划。谁也没想到,上海既是童明在研究生毕业时逃离失败后的一个缓冲带,同时也是他多年以后再次回到南京的助跑点。
他1993年离开南京,2020年回到南京,可谓兜兜转转,他的身上似乎更折射出了他作为童家后人的命运感。他调动起此前所有的记忆和学识重新打量、认识南京这座古城,并在对童寯住宅的扩建中,再次走进祖父的世界。
事实上,童明不止一次说过,他一开始学建筑时感觉非常痛苦,一度陷入迷茫当中,他以为建筑就是盖房子,而且到了研究生时期,他成为被抓着干活的对象,直到后来整理祖父留下的手稿,才越来越了解建筑,越来越深刻认识到童寯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独特性。
1937年,童寯完成了《江南园林志》的手稿,仅附录的文献举略,就包括了班固的《汉书》、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沈括的《梦溪笔谈》、周漫士的《金陵琐事》、文震亨的《长物志》、李渔的《闲情偶寄》、陈诒绂的《金陵园墅志》,等等。童寯在其中,还提出了疏密得宜、曲折尽致和眼前有景的“三境界”,某种程度上与他曾经的老师王国维进行了精神呼应。而在收研究生时,《古文观止》中柳宗元所写的《梓人传》是童寯要求的精读篇目,柳宗元笔下的这位梓人,即有工程设计、规划、监理之能,似乎正是建筑师的祖师爷。当时有一位日本访问学者田中淡,特别想考童先生的研究生,但他拿到考题就绝望了,考试要求把《梓人传》翻成白话文,再译成英文。
20世纪70年代末,童寯接待欧洲的一个代表团,他们竟然以为中国的园林是从日本传过来的,童寯决定在《江南园林志》之后,再写一本关于中国园林的书,而且是用英文写,他希望到那时来中国旅游的外国游客人手一册。《东南园墅》成为童寯向世界介绍中国古典园林之美的经典著作,同时也是其晚年于病榻上用英文书写的最后一部著作。
1981年,《东南园墅》英文初稿完成,直到1983年3月,童寯仍在病榻上口述该书结尾部分。1997年,《东南园墅》经清华大学教授汪坦由英文译成中文,才出了第一版。“为什么要写这个?有多少人愿意看?又有多少人看得懂?”当年童寯的长孙童文帮助祖父录入书稿时,曾经这样问过童寯。童寯沉吟良久,说了一句,“后人总比我们聪明。”
2018年,童明对祖父的著作《东南园墅》进行了全新翻译,“唯文人,才能因势利导,筹谋一座中國古典园林。即便一名业余爱好者,虽无盛名,若具勉可堪用之情趣,亦可完成这一诗性浪漫之使命。须记之,情趣在此之重要,远甚技巧与方法。”在以浅近简洁雅致文言重译《东南园墅》的过程中,童明不但重新传达出童寯先生英文原著的真意,他本人对园林的理解也已接近祖父达到的那个境界。
关于这位建筑师,似乎对他的一切认识都还在路上。
2020年,在童寯先生120周年诞辰之际,一封跨越南京和北京两地的家书被发现,这成为童家后人再一次打开和认识童寯精神世界的通道。
这封信写于1979年,是童寯写给他的大儿媳的,用的是全英文,开头即称她和她的丈夫童诗白为“朋友”。信纸非常薄脆,童寯将两页打字纸仔细粘贴在了一起。
童寯先生的大儿媳郑敏,是中国新诗历史上一个重要流派九叶派的代表之一。在她百岁寿诞之际,童明摘录了被他称为大妈的一首诗:当你看到月亮时/你在想地球/当你看到地球时/你在想太阳/当你看到太阳时/你在想别的太阳/当你看到婴儿时/你在想老人/当你看到老人时/你看不见婴儿/就像看不见别的太阳/那距离得太远太远了/无限是无法看到的,然而/你意识到它的存在/它的光和引力是一张/看不见的网/一切都在其中。
从两位老人的通信中,童家后代再一次发现了寄居于他们身体内的性情密码。
20世纪70年代末,社会百废待兴,童寯与郑敏用英文相互通信,显得非同寻常。他与郑敏推心置腹地探讨学问,阐述他的各种观点。他们的关系是平等的,而观点是可以争论的。
在这封信里,童寯展现了他对西方文化的巨大热情:因《新英汉词典》主编身份而出名的林同济是其清华舍友,他来南京时,童寯亲自安排接待,将客厅边的书房改成林同济夫妇的卧室,两个单人床,各放一个床灯,两床羊毛毯子,并给他准备了一本英文版斯宾格勒《西方的衰落》,这是典型的英国旅馆Inn的布置;专门设计菜单,第一天晚上,为他们接风的是西餐和张裕红葡萄酒,冷餐是镇江肴肉、皮蛋、炒花生、黄瓜,热餐是咖喱鸡饭、土豆泥、炒西洋葱和罗宋汤。到了第二天晚上,画风一下子变为螃蟹和茅台酒。
建筑因为人而变得可亲、可读,由童寯住宅衍生出的故事太多了。比如,童寯和朋友交流,说英文时连续不绝,会随意切换中英文,以找到最适配最有力的表达方式;重阳节这天,他会到太平门中科院宿舍去找天文学家张钰哲、陶强夫妇,和他们一起徒步登顶南京九华山,而张钰哲又是什么人呢?他曾根据殷墟甲骨文记载武王伐纣时有新星爆发、古籍描述的亮度和西方天文测试的历史数据,用公式计算考证出武王伐纣的准确时间。
1930年,童寯自美国经欧洲游历回到沈阳,应约加入梁思成创办的东北大学建筑系。自此以后,他再也没有机会踏出国门,但他始终保持着平视世界高度的目光:不论是订阅《建筑实录》;还是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他让在美国留学的儿子按照他开列的书单往南京寄了二十多种建筑书籍,其中就有柯布西耶的《模数制》和现代建筑史家吉迪恩的经典著作《空间、时间与建筑——一个新传统的成长》;“文革”期间,他在休假期间还跑到系图书室借外国刊物,为了方便大多数不能直接阅读外文原文的师生,他还为当时的南京工学院建筑系资料室编写了数百份国外建筑文章译介资料。
童明说爷爷自1956年之后,一直“以一种隐居的方式,梳理全球性的现代建筑思潮”。文昌巷52号,在喧闹之中隐藏着极大的沉寂,清水墙内,童寯正度过生命的漫漫长夜。在他去世30多年后,他的孙媳妇张琴用一本书记录了其最后20年的生命印迹,书的扉页所引用的一句话即来自王国维的《莎士比传》:“一面与世相接,一面超然世外,即自理想之光明,知世间哀欢之无别,又立于理想界之绝顶,以静观人海之荣辱波澜。”
童明眯着眼睛笑道:“老张开讲。”
责任编辑 陆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