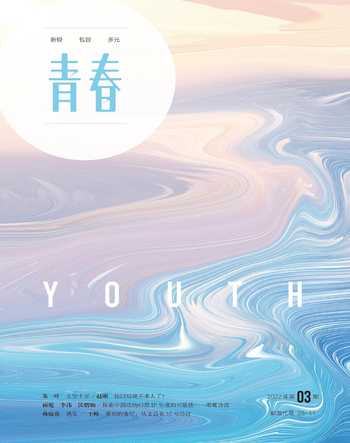你以后就不求人了?
赵刚
对门邻居家姓王,户主是一个五十多岁的中年妇女,我叫她王阿姨。开始时我们两家关系挺好,我妈妈经常和她结伴去二条巷菜场买菜,一路上张家长李家短地聊个没完。即便哪天不做饭了,两个人也会约着去菜场逛一圈。这对于她们仿佛是一种健身运动。
王阿姨原本是三口之家,一对母子外加一个儿媳;儿子和儿媳去年结的婚,结婚两三个月便闪离了,原因不明。王阿姨的儿子与我同一年出生,是一家医院的厨师,长相肥硕,颇有点职业风范。我们就称他胖子。胖子结婚时我还参加了他的婚礼,只是没想到刚结就离了。
结婚之前的胖子是个挺随和的人,颇有点没心没肺混吃等死的世界观——不然也不可能长得如此肥硕。可自打离婚后就像变了一个人,拼命地想赚钱——他认为老婆跟他离婚是嫌他穷,嫌他没有本事挣钱。其实在我看来,他那个老婆还真不是一个嫌贫爱富的人,她能跟胖子结婚已经表明了这一点,但是胖子自己非这么认为,离婚后削尖脑袋想赚钱。其他的事情也就不说了,有一天居然打起我们家门前那一小块空地的主意了。
我们两家都是一楼,我们家靠外侧,门前有一小块空地,有半个篮球场大小。母亲在这块空地上拉了一根晾衣绳,平时晒晒被子、晾晾衣服什么的,偶尔也会有一些孩子过来跳绳、打打羽毛球什么的。有一天傍晚突然从外面开来了一辆小车停在这里。听到动静我出门查看,司机是个四十多岁的陌生人,我说你怎么把车停到这里了?
司机说是王晓波让我停这儿的。王晓波是胖子的名字。
我说王晓波没权利让你停这儿。
司机说这不是王晓波家吗?
这是我家,他家在对门。
司机:不对呀!他说可以停这儿的,我把钱都给他了。
我问什么钱?
司机:我们说好这个车位一个月500块钱。
我这才知道胖子把这块空地当车位卖给了别人。我没好气地对司机说,这事我不管,反正你车子不能停这儿,他收你钱你找他去!
司机央求无果便给胖子打电话,十分钟后胖子回来了,见到我掏出两包香烟往我口袋里塞,指着司机说,这是一个朋友,临时把车停一下,过两天就开走。
我说好像不是这么回事吧!你收人家每月500块钱把它当车位卖了吧?
胖子怔了一下,瞟了司机一眼,人家的确有难处,你帮帮忙!
我说这就不是帮忙的事。我也帮不了。
胖子不高兴了,拉下脸道,你这人怎么这样啊?停顿了一下,他突兀地冒出了一句,你以后就不求人了?
我愤愤地回了他一句,就算开饭店我也不会找一个三流厨子!
话音刚落,他“喔”的一声怪叫着扑了上来,稍一使劲就把我掀翻在地——严格意义上他是用身体直接把我压倒在地的……胖子不是一个会打架的人,把我扑倒后并没有对我大施拳脚,只是用山一样沉重的身体死死地压住我,压得我浑身乏力动弹不得。就在这绝望的关头,出门买菜的王老太太回来了,看到他儿子和我缠斗在一起,也不管我是吃亏一方的事实,抓起一根生茄子就朝我脸上抽,一边打我一边还鬼哭狼嚎地喊着,快来人啊!他们欺负人了!他们欺负人了!茄子抽在脸上并不是太疼,不知是茄子太软还是因为老太太的力量太小,但是她抽打的动作挺吓人,而胖子更是被她的喊声刺激,一张脸被一股奇怪的力量扭曲并不住地抽搐,嘴唇一个劲地哆嗦着,随时要张嘴咬我似的。在担心被生吃的恐惧刺激下,我生含了一口气,瞅准时机先避开一次茄子击打,脖子抬起脑袋直接撞向胖子的面门,“噗”的一声直接把他撞翻了出去;他双手捂着面部,在地上翻滚着,血液从手指缝里流了出来,也不知道哪里被撞破了,鼻子、嘴或额头……
事情最后以那辆小车开走而告终。车子开走了但是事情没完,那天我妈出去看一位老同事回来晚了一点,本来也不知道下午发生的事,人走到门口遇到一个要好的邻居给她说了这件事情。老人家心疼儿子,蹬蹬蹬跑到对门跟王阿姨交涉,两人一言不合又吵了起来。我妈说话也有问题,她说我们家小东可是个读书人……王阿姨心里就琢磨,你们家孩子是读书人,别人家孩子活该是流氓?顿时火起,两人又是一顿大吵,最后还无聊地惊动了110……
这事过后我们两家就不说话了,平时见到就跟没见到一样。不仅我和胖子不说话,我妈妈和王老太太也不说话了,双方的儿子和对方的妈妈也不说话。这一局面直到项南来了之后才被破解。
项南的性格开朗,成天笑嘻嘻的,每见到一个邻居都热情地打招呼,阿姨长叔叔短的,哪怕遇到一个刚放学的孩子她也会亲切地招呼一声,小朋友放学了?没几天她便和一院子的邻居混熟了。所有的邻居都很喜欢项南,跟母亲说,小东眼光不错,一定要抓紧了!其中只有两个人不喜欢项南,第一个是我妈妈,第二个是对门的王阿姨。
咱们先说第二個。
项南大概第二次或者第三次来我们家时在楼道里与王阿姨迎面遇到,项南快乐地跟她打了招呼,阿姨好!王阿姨面无表情地闪身出了楼道,吭都没吭个响儿。项南在门口愣怔半天,进门后问我,对门那家人对我有意见吗?
我问怎么了?
项南把刚才的事说了一遍。我说她不是冲你的,告诉了她此前发生的事情。项南愤愤地说,就算你们吵过架也没必要拿我撒气呀!一点素质都没有。
其实我只说了一半的原因,以我阴暗的心理揣测,另外一半的缘由归结于嫉妒:他们家的媳妇刚离婚就跑路了,随即我们家就来了一个人见人爱的女朋友,这事换做我我也不高兴。
从那以后项南再遇到对门的邻居也不主动打招呼了。然后有一天,项南下班来我们家,一进门就神秘兮兮地问我,你猜刚才我遇到谁了?
我说谁呀?
项南压低声音,对门的老太太。
我警惕地——她又怎么你了?
项南说没有,我刚进院子她就满脸堆笑地跑上来跟我打招呼,还问我是不是在银行工作……
她想干什么?
她听说我们行最近向内部员工推出了一款理财产品,年利率比较高,问我能不能帮她买一点?
我说你别理她。
项南为难地——我已经答应她了……
这件事的最终结果如何我没再过问,就后来事态的发展衡量,结果应该是令人满意的。
一个周末的下午,我从外面回来,进门时发现项南端坐在厨房大餐桌上捧着一本书犯傻——项南喜欢我们家餐桌。我们家有沙发有床,可她待得最多的地方却是厨房里的这张餐桌。她一没事就坐到餐桌上看看书、抽根烟什么的,或者什么都不干,双手抱着腿,下巴抵在膝盖上看着窗户外面发呆;我们家厨房有一面比餐桌还大的落地窗户,视野无遮无挡,视力好的人从窗户里甚至能看到——梦想。为她这毛病,我妈妈没少在我面前嘀咕,意思说她没礼貌,缺少家教云云。
看见我进屋,项南腾地跳下餐桌。你可回来了!
我问干吗?
项南说我饿了,正犯愁要不要出去吃点东西?你回来就好了!
我说你傻呀!都饿成这样了还瞎琢磨啥呀?
项南开心地说,我在等老天爷啊!我相信他老人家不会丢下我不管的。
被人需要是一件开心的事情。我正要说话,门铃响了。我走过去拉开门一看是对门的王阿姨,她端着一只热气腾腾的碗笑眯眯站在门口。看见我似乎很诧异,你回来了?我还没说话她追问了一句,小南姑娘在吗?我一时没反应过来,她从我身体一侧看见了项南。小南姑娘快来!
项南凑了上来。因为门口太窄,她被我整个挡在了身后。她先在后面推了我两下,想让我放她过去。我心里有点不舒服,硬着身体没理会,她见状干脆一猫腰从我的胳肢窝下钻了出来,头和脖子伸出来后身体却被我一收胳膊温柔地夹住了。项南不好意思太过挣扎,顺应着我的身体的力道伸着头对王阿姨说,阿姨你找我呀?
王阿姨:我刚刚包了一点饺子,送一点给你尝尝。
我伸手要接,王阿姨却避开了我伸出去的胳膊,委婉地将一碗饺子递给了项南。等一碗饺子平稳地被项南接到手中后她似乎才想起我,转向我不无歉意地说,今天时间紧包得不多,下次再请你吃吧!
我差点没哭起来。什么人啊?会不会说话?
王阿姨离开前还又叮嘱了项南一句,吃完碗就放着,我一会儿过来拿回去洗。说着话蹬蹬蹬地回去了,砰地关上了门。
我们退回房间掩上了门,项南捧着一碗热腾腾的饺子咯咯地乐开了。我不无醋意地说了一句,其乐融融一家人啊!魅力挺大的呀?
项南说我怎么闻到了一股醋味?
我说你拉倒吧!我是好心提醒你,别遇到一个人就当是自个儿的亲戚,你知道她是不是人販子或者做传销的?
项南息事宁人地说好了好了,人家对我好还不是看你面子?别小肚鸡肠的了,一起吃点吧!
我瞥了一眼桌子上的碗,差不多也就七八个水饺,只够一个人吃的,我说得了,我还是下方便面吧。
自此之后我们两家的关系缓和了许多,没多久我妈妈和王阿姨又成双成对出门买菜了。
母亲表面上对项南客客气气,私下里却并不看好我和项南之间的关系。一是觉得我这么多年没个正经职业,稍微头脑正常点的姑娘都不可能跟我有结果的。至于谈恋爱,那不过是姑娘们因为无聊拿我找点乐子——母亲还是怕我吃亏——此外她对项南的一些生活习惯也看不大惯。项南是一个粗枝大叶的人,平时来我们家什么事都不做,胃口还特别好,吃起饭菜来特别地不讲究,有几个菜吃几个菜,没有也可以不吃,但是只要一吃起来不吃完是不会停下筷子的。说起来也挺奇怪,那么精瘦的一个人,如何能吃得下那么多?问题还在于能吃也罢了,吃完饭帮忙洗个碗擦个桌子也是应该的吧?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哪一个刚来家里的女朋友不是低眉顺眼积极表现?项南却不,吃完碗筷一扔转身点起了一根香烟。母亲有一次实在忍受不了了,嘀咕了一声,小女孩家抽什么烟?项南笑嘻嘻地回了一句,我抽的是女士型烟。还有一次,项南吃完饭扔了碗刚摸出一根香烟要点,母亲阴沉着脸对我说,你今天把碗给洗了。我还没说话,项南就朝母亲嚷嚷起来,他是男的不能干家务活儿!母亲问那你准备洗吗?项南顿时嬉皮笑脸起来,阿姨你看哦,我不是还没嫁到你们家嘛,现在就洗碗挺没面子的。这样吧,等我嫁过来后,我保证不让你洗一次碗!母亲听了她的话满心欢喜地洗碗去了。
项南就有这种能耐,嘻嘻哈哈之间就能把人哄得百般开心任劳任怨。当然让母亲任劳任怨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项南的工作。项南在银行工作,用现在的标准衡量算得上是一名白领;我以前的那些女朋友一小部分是在校大学生,另外一大部分是文艺女青年,大多属于有思想、有理想、有品位却不能自食其力一族。跟她们在一起时我三天两头就要张口跟母亲借钱,母亲对她们恨得咬牙切齿。自从认识项南之后我再没跟母亲借过钱……母亲始终觉得我能找到项南是高攀了。
大部分的情况下项南是能搞定母亲的,但唯一一次的失败便导致了我们之间的分崩离析。
起因是项南单位里面建了一批住宅,本单位员工可以用极低的价格购买。项南争取到了一套两居室的房子,她打算让我跟她合买。大致的计划是我们两个人凑个首付,以后的还贷及各种费用她来承担。这个条件无论对于男人或者“俘虏”而言都算得上很“优待”了。其中的问题在于即便是首付,两个人分摊也要二十万左右(当时的价格),这对于一个生下来就一直处于“待业”状态的人而言并不是一笔小数目。而且钱这种东西你有了就有了,没有就是没有,没什么好挣扎的(内心)。项南说起来是要我跟她合买,实际上的指向却是我妈妈的钱。当然这也无可厚非,现在年轻人买房子谁不靠家里?否则以他们的收入两三辈子也别想买一间厨房。一天晚上项南来我们家,吃过饭后把我拽到房间里问,你跟你妈说房子的事情了吗?
我说这几天挺忙没顾上。实际上是我不知道该如何跟老人家开这个口。
项南说单位下通知了,这个星期就要缴款,否则算自动放弃。你还是抓紧问问吧!
我说行!
项南眼睛一转,要不你现在就去问问吧。
我说没必要这么急吧?
项南坚决地——就现在!
我只好硬着头皮去了母亲房间。
母亲正在桌子前写毛笔字。老人家最近莫名其妙地爱上了写毛笔字,一有时间就拿起笔划拉两下。至于她的字嘛!怎么说呢?人家写毛笔字叫书法,她老人家写字约等于画画。就是这样。当然对一个退休的老人而言,只要她不跳广场舞就已经够给我面子的了,我不能要求太多。看见我进来母亲停下笔招呼道,来看看我今天的字!
我说我想跟你说件事情。
她问怎么了?
我咽了一口唾沫,把项南的购房计划说了。
老人家还没听完就一口给拒了,还问我,为什么要买房子?
我说项南说这是一个福利,放弃怪可惜的。
老人家一皱眉头,没这个道理!一个东西本来并不需要,因为福利就非要买吗?
我说也不能说不需要。我们总是要结婚的,买的房子可以作为我们以后的婚房。
母亲“哼”的一声,她如果真要和你结婚,你就是要饭的她也会结;她如果不想跟你结婚,你就是买给她一座长江大桥她还是不会跟你结……而且我们家又不是没房子,虽然面积小了点,毕竟也是三室的,结婚也是够的。她摇了摇头,现在的孩子张张嘴巴就买房子买房子,也不看看自己有没有这个能力!
母亲的观念太过迂腐,但是意思已经表达得很清楚,就是不管我们买不买房子,反正她不会掏一个子儿出来。
房间里落入无边的沉寂,压得我心里发慌。我靠着门又站了一会儿,然后默默地退了出来。母亲提起笔继续写字,头也没回地嘱咐了一声,请把门带上!
我回到自己的房间,项南迎上来问,怎么样?
我摇摇头,心里弥漫着一丝无以言表的愧疚。我觉得自己快哭了。
项南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她居然不支持?不会吧!现在这种价格能买到这样的房子换任何一家都不晓得高兴成什么样子了!
我说可是我说服不了她……
项南略一思忖,这样吧,我去跟她谈谈!
我吓了一跳,你别去!
项南:没事的!她伸手揉了一下我的头发,出去了,走到门口又扭头朝我笑了笑,好像在说,别担心……然后隔壁响起了敲门声,我听见门后面母亲的声音,请进!
那天项南在母亲房间待了七八分钟,在这段时间里我像一只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坐立不安。我总觉得情况不妙,要出事,要出大事。究竟什么事却难以预测。七八分钟后项南气冲冲地回来了,脸色铁青泪水涟涟。我问怎么了?她没理我,拿起沙发上的手提包掉头就走,动作迅捷态度坚决,拦都拦不住,拉开大门蹬蹬蹬地走了……
项南就这样消失了,而我却不知道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短短七八分钟之内母亲的房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一切又是怎么发生的?我后来问过母亲,母亲极不友好地反问,你怎么不去问问她?我当然也想问项南,但是却没有机会了。自从那天离开之后项南再没登过我们家的门,并随之掐断了与我之间的一切联系。我给她打过电话,她的手机号码已经停用,然后包括邮箱、QQ、微信等所有的联系方式都逐一被屏蔽或者删除。迫不得已之下我去她的单位找过她一次,也没见到她。她的同事告诉我项南已经调到另外一个网点工作了,至于哪个网点对方不肯说。
从银行出来后我没有乘车,默默沿着人行道向前走,在一个十字路口时遇到了红灯;路中央的一个交警拦下了一辆压线的面包车,打着手势让面包车先靠向路边……我站在路口等着红灯变换,身旁站着一位胖胖的中年妇女,右边是一位中学生模样的少年;少年的鞋带松了,他弯下腰想重新系一下鞋带,绿灯却在这时亮了,几乎与此同时,那位中年妇女开始过街;看到身边的人突然启动,弯腰系鞋带的少年慌了,感觉自己被某种生活抛下了,也不顾刚系了一半的鞋带,下意识站起身跟着中年妇女的步伐向前走了起来,刚走了两步便踩了自己的鞋带一下,脚跟打了屁股似的,只好蹲下來继续系鞋带,路中央的交警向他做了一个快速通过的手势。中年妇女正好走到交警的身边,看了警察一眼,再扭头看了看蹲在路中央的少年……
那天的天气挺好,阳光紧贴在城市的表面,在行人和车流中穿行,高楼、商店和道路两侧的大型广告牌也处在行走中,即便运动中的车辆与行人停滞。
无论如何这一次的失恋对我的打击巨大。这话的意思并不是指项南在我心目中的地位无可替代,而是说她抽身的方式让我无法接受。我和项南都不是彼此的初恋,我们都有过没能善终的一段或数段感情经历,但是此前的每一次失恋都是有迹可循并逐渐昭然若揭的,即便相互跺脚谩骂起码也是一种通告,无论有多不舍内心起码还是知道结局的。而项南这一次是在我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突然抽身的,这属于不宣而战,她胜之不武。直到这时我才发现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如此脆弱,昨天还与你同床共枕温情脉脉的那个人有一天翻身下床后就不见了,连一句再见都没有。说好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呢?说好的一日夫妻百日恩呢?说好的宁羡鸳鸯不羡仙呢?
接下去我进入了一种混乱的时间模式,每天都要睡到下午两点钟左右才醒,起床后立即出门;自从项南离开之后我在家里一分钟不愿多待,多待一分钟都感到呼吸困难。出门后我随便吃点东西就开始喝酒,有朋友就找朋友一起喝,找不到朋友就自己喝。我以前是不喝酒的,还浅薄地觉得爱喝酒的人怎么着都有点神情含混无病呻吟。可等自己喝上了口才发现酒真是一种奇怪的物质,虽然初尝味道并不友好:白酒火辣辣的呛口,红酒酸涩,黄酒有点齁,啤酒则洋溢着一股淘米水的味道,这几种味道都不太令人舒服。但是只要坚持喝下去,你会发现在最初的味道之后,别有一股滋味从你身体内部的各个通道涌现;它们齐聚于你的肺腑间,并通过呼吸弥漫到你的全身的每一个关节,这是一种让人不能自已的温度,让你有一种如沐春风一般的惬意。喝酒的人期待着的其实就是这种惬意,喝酒的人等待的就是这种时刻……
我后来喝得多是啤酒。因为每天都需要在外面消耗掉很长一段时间,需要拉长喝酒的时长,虽然其他的酒我也喜欢,但是时间一长算起来的费用就有点吃不消;啤酒则不然,三块钱一瓶,喝个十瓶二十瓶的也就几十块钱,在所能承受范围之内。每次喝完酒——真实情况是每次等再也喝不动了,时间差不多已经是深夜一两点钟了,也到了酒吧打烊的时间,直到这时我才会晃晃悠悠地回家。每次我都是走回家的。深夜时分的出租车都不愿意带酒鬼的,久而久之我也习惯了步行。在这个城市,这一条街的街灯几乎每天都像眼睛一般看到一个醉鬼东倒西歪地横行在大街上。他有时会朝着空旷的大街大叫大嚷,跟臆想中的某个人争吵……他感觉已经永远失去了项南……
三个月之后我结婚了。
对于婚姻你让我说什么好呢?首先我认为婚姻对于现实生活的意义不大,其次我觉得婚姻是一桩我不能理解的知识,即使通过学习也无力达到的某种状态。所以我从不以为自己会结婚,尽管我喜欢异性,即便如此我依然不信任婚姻,但是我信仰异性……说起异性我还得再多唠叨几句。仅从个人经历衡量,这就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接力跑,你从青春期起跑,从一个女人跑向另一个女人,从少女跑向姑娘,从姑娘跑向姑娘,从姑娘跑向少妇(也有从少女直接跑向少妇的,或者把少女直接跑成少妇的)。一个一个的女性就像被人塞在你手中的接力棒,你握着她们奋力奔跑,跑完一段路程再将她们传递给下一个男人,转手接下另外一个女性,再跑。不跑到婚姻你永远不知道哪一个女性才是你的最后一棒;有的人即便到了婚姻还会接着跑——他跑习惯了。我不带目的地跑了许多年,从一开始就不为最后一棒的奔跑,但是结果还是无辜地把自己跑成了最后一棒。于是我结婚了。
对于这一场毫无准备的婚姻我无法说得太多,我只能说这完全是一场生活中的意外,并不在我的人生计划之中,所以当它如一块从天而降的砖头准确地砸在我的脑袋上的那一刻,除了注定的头破血流之外就是那恼人的一阵接一阵的自我眩晕了……结婚的前一晚,母亲和几个亲戚在为明天的婚礼做着各种的准备工作,忙忙碌碌叽叽喳喳,我坐在一旁默默地抽烟,亲戚(两位表姐)说烟味太难闻,你出去抽吧!
院子里有一棵枇杷树,每年的五月全院的邻居都会来到树下摘枇杷吃。我夹着刚抽了一半的香烟出了门,准备去枇杷树下把这根烟抽完。刚出了楼道一眼看见枇杷树下已经站着两个人了。借着暗淡的光线依稀辨认出其中一位是对门的王阿姨,另一位是一个年轻女子,年轻女子的脑袋埋在王阿姨的怀里低声哭泣。我觉得奇怪,王阿姨家里并没有其他女性,难道是此前与胖子离婚的儿媳妇回来了?从背影看倒是很眼熟,我忽然想起一个人,脑袋“嗡”的一声,抬腿就要奔过去。王阿姨看见我了,她隐秘地朝我竖起一只手掌;笔直的手掌刀一般迎刃而立,仿佛要斩断汹涌而至的一切事物……我硬生生站住了。年轻女子还在恸哭,压抑着哭声朝向内心深处挣扎,犹如从五臟六腑撕裂而出一般,听得人头皮阵阵发麻。王阿姨一边拍着她的背部一边小声安慰着,快别哭了!你这样对他也不好对不对?女孩子还是摇头痛哭。王阿姨叹了一口气,小南姑娘啊!阿姨知道你心里难过。我一直觉得你们俩是最合适的……
项南“哇”的一声号啕大哭起来。王阿姨吓了一跳,走!我们出去说。她半拖半拽地把项南拽走了。我看着她们俩的背影慢慢地走出院门消失在夜幕中……我哆嗦着把手里的香烟递向嘴唇,递到一半胳膊突然没了力气,垂下了,嗓子眼儿像堵着一块硬硬的东西,吐不出也吞不下,死死地哽在那里,然后眼泪呼地涌出了眼眶,随即便泣不成声;一开始我是站着的,哭着哭着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我站不动了,手里半截香烟不明原因地熄灭了——难道有一滴眼泪经过了烟头?我坐在地上痛哭流涕,面前不时有邻居经过,却没一个人管我。我在这个院子住了二十多年,与大部分邻居形同陌路,我平时不理他们,他们也不理睬我。所以此刻大家有此表现也属正常。我活该!
我至今依然记得那天的场景。在我人生最危险的时刻,一位邻居母亲一般挺身而出,为我挡下了最后一轮扫向我的挟着雷电的疾风劲雨。我能记住的就是这个。
这也是我与项南的最后一面。
第二天我的婚礼如期举行。婚礼很成功,两家人都很开心。中途我拽着新娘子给王阿姨敬了酒,王阿姨说了很多祝福我们的话,什么百年好合白头偕老等等。
责任编辑 菡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