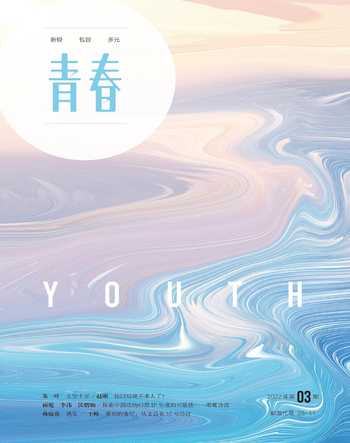死亡主题的轻与重
汪雨萌
在我收到的投稿中,有很多作品都会写到死亡,他们写老人的临终,写孩童的夭折,也写谋杀、自殺、意外。我惊讶于这一代写作者对死亡叙事的执着,并且看到他们在书写死亡的过程中所展现出的截然不同的路径。
最近逛B站的时候,一个关于90后、00后养老问题的视频吸引了我的注意,但相比视频本身,视频的弹幕与下方的悲观评论更令我震撼。虽然竭尽所能陈述主人公死亡的必然性,但这种必然性在我看来恰恰是脆弱而苍白的,甚至带有一种媚俗的美学倾向,好像死亡是他们唯一能够反抗生活的武器与途径。这些作者选用很多沉重的、痛苦的词汇、意象、描写方式来包裹他们笔下生活事件“轻”的本质,将故事推向一种极端的“为赋新词强说愁”。
死亡是文学作品中逃避不开的主题,但我认为它不该如此之轻,不该只是承载一次单独的死亡行为,也不该是一种草率的编织作品高潮的技术手段。它的背后应当是对人类生命、生活与社会关系的整体思考,方才能为这个主题赋义。“行只影单的个人不能构成衡量其生命与垂死的标准,他对世界和共同组成他生命之路的周围人的关系,是多种多样的、交替变化的,不断影响他的反应和行动,要是没有这些关系,我们的生命也就是不可思议的了。”这是贝克勒的《向死而生》对死亡的一种基本理解,也是我本次选择水笑莹与李玉新两位同学的作品的原因。这两篇作品虽然文体不同,主题也不完全一致,一个写了夭折的孩子所遭遇的家族的遗忘,另一篇则在不断寻求逝者与生者之间的记忆联结,但它们有一点是相通的,它们没有将死亡作为一个事件来看待并书写,而是将其看作关系节点和情感联结,力图用个人的死亡延伸出尽可能多的蛛网,网住面对死亡时丰富而驳杂的世情与人性。雅思贝斯曾说:“亲人之死……就像那崇高的时辰一样也会转化为永恒的现在意识。”但他也补充说“终结,沉陷在忘却之中,仿佛从未有过”。对于年轻的写作者而言,家族是死亡叙事的重要切入口,也是他们将这一主题变得更“重”,更有哲学意味的一种方式,通过面对死亡时人展现出的兼有遗忘与回忆的薛定谔状态,作者能够更突出死亡作为一种恒久而必然的存在所承载的消逝性的人生结构和对人类面对自由剥夺时的无奈与反抗,能够将这一主题在哲学的层次上进行表达。就我个人而言,我更愿意看到这样的作品,它们是有分量的,是复杂的,即使他们的语言会很朴实,甚至会稍稍偏移出文学表达的范畴,即使他们的作品不一定有很跌宕起伏的故事,我都愿意推介,甚至试图用它们来对抗一些青年写作者的暴力、疼痛、死亡美学。
我们需要好好地思考死亡,也该认真地安放它在文学中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