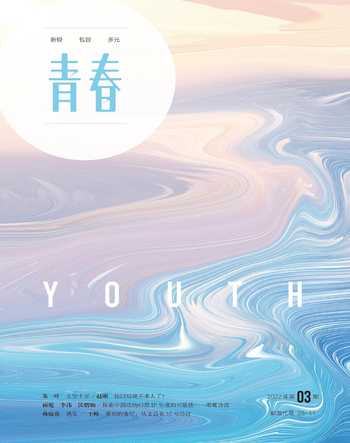书中日月长(外一篇)
徐旸
我的外公,极瘦。
瘦得像一竿劲峭的竹,或一阕宋人的词,画在纸上,写进书里,只需驱遣伶仃的一痕墨色,便显出嶙峋的骨相,抖露出峥嵘的棱角。那棱角并不锐利,而是如大字的笔锋,只在毫端的转折中,带出些孤高与斩截的意味来。
很多年后想起他,总觉得外公是一位畸零之人,满身的不合时宜,好像同这世间始终格格不入。但那时的我却犹自茫然无知着。我的目光逡巡过外公的书架,那里有李太白,有辛弃疾,有薛涛,有柳如是。我尚幼弱的手指掠过沾染着沧桑的书脊——那里因频繁的翻阅早已泛黄发脆,以至于会让我想起门外的酢浆草上,那些纤薄的蝴蝶。
但蝴蝶可以去往天南水北,我出生起便已老去的外公,却只能被书房的四壁围困着,被这个小小的县城圈禁着。他于夜里点一盏灯,跋涉过唐宋元明,但脚步却始终没能迈出这一方逼仄的天地。书籍是他的城墙,垫高了视野,亦是他的堡垒,仿佛避入其间,便可不理会春秋冬夏,人世浮沉。
我从未了解过他,至少在我生命起初的十年里。于我而言,他留下的记忆其实很浅,浅到只剩下一身瘦骨,几声咳嗽,满壁旧书;浅到只记得幼时的我曾坐在他膝前,听他教我背着“秦时明月汉时关”,那时他的声音已然老矣,当中似可闻见依稀的风声,苍然而高古。而我似懂非懂地重复着,声音从当时传至当下,稚嫩与沧桑渐次重叠,仿佛在这之后的岁月中,我仍旧循着他的念诵,一字一句、亦步亦趋地跟随着。
又一个十年之后,外公的学生与好友将他生前的文稿整理出版。那时已然长大的我,目光在触及那本书的一刹,竟仿佛清晰地看到了回溯的时间。纵然生死相隔,纵然暌违十载,却借助那些文字,重新认识了他。那时的我沉迷于《楚辞》,尤爱那字句的瑰玮,而似有默契地,他也早在许多年前,取《山鬼》篇中一句,为自己的文集定名为“独后来”。
“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路险难兮独后来。”或许,于外公看来,书是幽篁,亦是云翳,身处其中,有时会觉遮天蔽日,仿佛一生都无法抵达其终点。而这长路迢遥亦险难,后来者谁?后继者谁?当时的他,是悲从中来,还是心存期待?我无法知晓,但我仍想告诉他,其实,我们都在这条路上,尽管步履维艰,却始终不曾偏离。
母亲在书店工作。我幼时徘徊其中,从木头架玻璃橱盛行的上世纪九十年代看到了如今。书中亦有流行,可一波波风潮似黄沙吹尽,最后不朽的,只能是经典,正如外公书架上我所见过的那些。而于外公所著的书中,我也拾掇起那些发生在我出生之前的零星往事。譬如他曾省吃俭用,托我的母亲陆续购齐一套《二十四史》;又或者,他曾于满是尘灰的旧纸摊上,收得一本《杜工部诗集》;再比如,他曾因学生的提问,在那个没有电脑、无法搜索的年代,于厚重的《汉书》中,查阅某一句话的出处。
数十载寒暑交替,我的家也屡次搬迁,小城中南北辗转,书却是越攒越多。许是心有执念,最近一次搬入新居的时候,母亲也购回了一套《二十四史》。六十三册次第排开,银蓝交织的书封古雅素朴,白炽灯下,泛着温润的流光。它于书架上静立着,沉默着,等待着,我却没有勇气去阅读。但母亲说,书留着不要紧,总会有被翻开的那一天。
两年前,我校对一本教辅,当中涉及了众多史书文段。无奈之下,只好一次次地拜托母亲在那套《二十四史》里寻找,而后再拍照传给身在异乡的我。这一差事令母亲不胜其烦,却只得照做不误。只是有一次,她在拍完《旧唐书》里的《王勃传》后,似是无意地念叨了一句:“要是你外公在就好了。”
那一瞬间,我的脑海中出现了短暂的空白。若是外公还在,看到了如斯鲁钝,却还勉强算得“有志于学”的我,是会欣慰,感叹那长路不“独”他一人,仍有“后来”者;还是会失落,觉得我仍旧辜负了他的期望呢?
我永远无法探知他的想法了,他早已长眠在了二十年前的那个春日里。后来才知道那一天是“世界读书日”,虽多半为纪念莎士比亚与汤显祖而设,我却依旧心存宽慰,只因外公一生的收笔,与这一天是如此相契。
在书中,我同外公一次次骤然重逢,有时他还年轻,有时他已苍老。我可以读到他的骄傲他的得意他的心气,亦能体察他的愤懑他的失落他的不平,而书,也承载了我们一家三代人的执念,从我的外公,到我的母亲,再到我。
有些事无须言明也不必道破,一如家风,本身便无形而无质,靠耳濡目染,靠潜移默化。我从未领受过外公正式的教导,却试图去继承他对书籍的虔敬。虽然在旁人看来,他只是个清贫的教书先生,两袖清风,身无长物,寂寂无闻,可他的痴与执,却由血脉传承并示以儿孙,浸润在被他,被母亲,被我翻开的书页里,迢递过数十载的光阴。
外公曾改写老杜一联,聊以告慰平生:“笔耕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在这个人心浮躁的时代,他带着一身棱角,不知世故也不屑世故,瘦得只剩下一把傲骨,穷得只剩下一室旧书,甚至到最后在我心里,连他自己也活成了一本书,纵然早被画上了句点,但其中的意蕴与风骨,却值得我一读再读。
书中日月长。而我,也会像他一样,用自己的一生,去推敲路过我掌中,丰盈厚重如生命的,每一部书。
拂落时针上积满的尘埃,循着百年的风雨,走回一段历史的起初。时间的潮音激荡在耳畔,而我翻开波澜壮阔的近现代史,思绪在与他相关的文字上一再停驻——
想起他,如想起一条江流。
发轫于淮安,绕转过沈阳,从江南的杏花春雨到东北的白山黑水,他穿越大半个中国,流离在漫漫的求学之路上。疮痍遍布的土地奔来眼底,哀哀生民的疾苦刺入心中,令他在少年时,便许下“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宏愿。此后南下天津,浮槎日本,远渡法国,他用脚步丈量着土地,以信念书写着信仰。一次次的驻足,无法使他停留。他一路奔走,一路前行,民族的命运牵系于心,令他那英气熠熠的剑眉始终紧锁,也让他试图从云翳密布的困境中,找到一条人民解放、国家发展的道路。
“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面对滔滔而去的逝水,他曾在前往日本的轮渡前,信筆写下这样的绝句。少年的心中尽是拏云壮志,却从未有一隅留给了自己。那颗“济世”的种子,是一星火光,点燃了崇高的理想,成为他全部的初心。
如一条在大地的裂隙中流淌的江流,纵行过千里万里,也从未忘记自己是为何而出发。当战火逼近,他断然舍弃了巴黎的生活,乘着那一艘归来的航船,回到了深爱的故国。之后岁月倥偬,他任职于黄埔军校,指导过东征北伐,在四起的硝烟里,投身去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而后又领导南昌起义,对着国民党反动势力打响了抗争的第一枪。那枪声响彻夜色,振聋而发聩,让民众的心魂为之战栗,也让他的信仰愈发坚定。起义结束,他隐去姓名,转为地下工作,依旧战果卓著。数年后,他又奔波在长征路上,运筹于根据地内,带领革命军队,冲破敌人的“围剿”,辗转于战火与兵燹、狂澜与险峰之间。
如江流一般,他向着心中的目标奔涌而去,百折不屈,九死不悔。
那时战争的硝烟覆盖着整个中国,有人在卖儿鬻女,有人在谋求升迁,有人挣扎在贫病交加之际,有人沉沦在声色犬马之中。而他则为了国家和民族而上下求索。数十载呕心沥血,数十载筚路蓝缕,数十载戎马生涯,他终于和同志们一起,带领人民赢得了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胜利,在这片历尽贫敝与屈辱的土地上,建立起一个崭新的中国。
如江流一般,他慈让温和,大公无私,以明澈的心地,守护着祖国与人民。
外交场合,他巧妙斡旋,以机敏的词锋震慑世界;谈判席上,他进退从容,对国家与人民的利益分毫不让;生活当中,他以身作则,时刻保持艰苦奋斗的共产党人本色。儒雅谦和的谈吐,包裹着内里的锋芒,纵然已非战争年代,他也依然是一柄剑,藏刃于鞘,时刻警醒地面对着外患与内忧。身居总理之位,他鞠躬尽瘁,严于律己,勤政为民,以自身的崇高风范,成为后世学习的楷模。
他用自己生命的长度,如江流一般,灌溉了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他用自己一生的心血,如江流一般,泽被了人民;他可以锋芒毕现,可以摧枯拉朽,可以用自己心中的火,烧开那深邃的,曾似乎永不会被点亮的夜色;同时,他又是如斯的温和端方,俯仰无愧于天地,行止无愧于人心,以至于在史书的字里行间和后世所流传的故事里,尽可看见他冰雪肝胆,坦荡心胸。
他这条江流,横亘在共和国的魂魄与民族的记忆当中。所来处,是苦难蒙昧的旧社会,所去向,是光明灿烂的新中国。这一路浩浩汤汤,壮怀激烈,纵然战火交加,风霜险恶,路途艰难,群敌环伺,他历经坎坷而又一往无前,带着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与使命,冲垮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重整了那一片百废待兴的古老土地,让河山明朗清晏,让人民安居乐业。
江流之水,至柔而至刚。
江流之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江流之水,纵然已入海口,仍能恩泽后世。
我合上那卷历史,但心头的火焰,却早已被他,和同他一样的那些人所引燃。他们有同样的初心,他们有同样的使命,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他们的努力,书写了这伟大而多艰的一百年。任凭日月轮回,世事嬗变,有些信仰却深深地植入灵魂,让如我这样的后来者,在循着历史,循着前辈的步伐前行时,仍能被那些曾经的人与事打动,从而更加笃信而坚定地,走在这一条道路上。
这一条道路,而今已换了模样。高铁飞机一日千里,手机信号覆盖全球,东方大国业已崛起,他所期盼的盛世,已经初露峥嵘。而无论是战争年代里,还是和平岁月中,脚下这片土地,永远会涌现出如他一般的英雄。那些人,或戍卫边防,或执教深山,或白衣披甲,或坚守岗位,都在各自或伟大或平凡的事业中成就了自己——因为,只要心中有人民,心中有民族,心中有国家,便能无愧于自己共产党人的身份,无愧于自己的初心和使命。
想起周总理,便如想起一条江流,只因其生命的长度虽能计数,但精神卻如水,永远激昂,永远坚定,永远向前,永远不朽。
责任编辑 青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