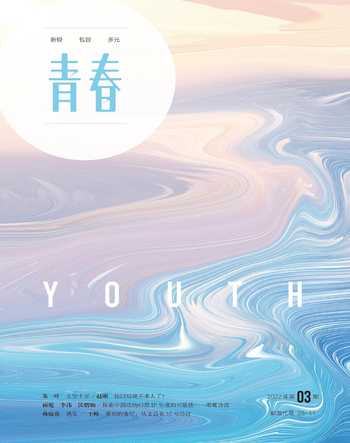遇 见
惊蛰日,阳光轻软,一只沉睡的小蛙醒来了。
冰雪已消融。它从松软了的泥土里慢慢拱出来,就在我经过的小石子路旁。新出的草芽稀稀疏疏,并不能完全遮住它的行踪。我放轻脚步,跟着它,一直往河边去。它跳跃的身姿是那样的虎虎有生气,一点儿也不像是刚从冬眠中醒来的样子。
河并不大,却长,曲曲弯弯的。慢慢沿着岸边走,可以清晰地望见树木的细枝、花朵的软瓣倒映在水里。水是流动的水,总会有波纹来改变水下的光线,折射,再折射,魔术师一般,把一棵树变成了另外一棵树,把一丛草变成了另外一丛草,把一些叶子变成了另外一些叶子,把一朵花变成了另外一朵花。
河边不像公园里的别处,有园林工人打理得齐整,杂草随意散乱地生长,透着一股野趣。东边的河岸上,密密麻麻落着许多白石头,脚踩上去,会发出松脆的声响。许多人爱到这里来玩,有大人,也有孩子,他们喜欢把小石子握在手里朝水上打水漂,慢慢地,小而薄的石子便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一些鸡蛋一样大的圆石或更大一些的扔不动的石头。
夏天的黄昏,在河边散步的人会听到大石头下传出青蛙清亮的咏叹调,它们是喜欢热闹的生物,就像树上的蝉,一唱起来就没完没了。不知它们的圈子里是不是有柳泉居士笔下的蛙神,啥时候心情好,也送一个美丽的姑娘来凡间与多情的书生成亲。
有一年夏天,一些充满热情的年轻人曾到河边来办过一个音乐节。他们在沿岸的草丛里放飞从遥远的地方运来的萤火虫,门票卖出去几百张。宣传画册中,萤火虫飞起,一闪一闪,亮如远星。可是,那一次的活动却可以称得上是惨败。因为长途跋涉,萤火虫在运输过程中就死了大半,到了这里,那些来观赏的人,带了瓶子来,拿了透明的袋子来,几只甚或几十只地装走,能顺利飞到草叶上亮一会儿的萤火虫寥寥无几,黑灯瞎火的,还差一点发生踩踏事故。那些气急败坏的责骂和吵闹,让原来预备好要在河边台上表演的音乐节目草草收场。那些年轻人因此从中得到了一点人生经验:无论做什么事,光有热情是不够的,一些细微的瑕疵,终会使原本周全的计划功亏一篑。
秋冬之际雨水少,河水浅下去,岸边石子与石子之间的水洼里生出青葱的植物,铜钱草也有,野茼蒿也有,红蓼也有,许多小鸟会飞到这里来休憩。它们之中,我只认得白鹭和鹊鸲。白鹭有仙气,靠近不得。倒是那些鹊鸲,它们似乎并不惧怕人类。有时候,我在岸边坐着,它们也会落到石头上来饮水,或者到水洼里洗澡——它们洗澡的姿势非常干脆,像扎猛子一样,整个小脑袋和身体埋进水里,然后迅速地抬起来,从头到尾抖一遍,如果有慢动作可以重新播放,这会儿就能看到数不清的水珠从它们的羽毛里飞射而去。它们黝黑的眼珠、黑白相间的羽,长得有些像喜鹊,但尾巴比喜鹊短,也比喜鹊多一些贵族气。打理干净了,它们便异常轻疾地飞到附近的树枝上,飞起来的时候,翅膀并没有张开,似乎只凭一口真气上去,像武侠小说里的轻功高手。
这条河,离人迹远一点的边岸上,一年到头,从春天到冬天,总有人坐着钓鱼——他们长时间一动不动,像老僧入定。只在鱼上钩的时候、坐乏了站起来抽烟的时候,或者暮色西垂该收竿回去的时候,他们才会动起来。
有一个爱夜钓的年轻人,常常独自在暮色降临时来到河边,这时,其余的人都走了,只有他一个人沉默地坐在那里,看上去孤零零的。周围的光线一点一点弱下去,一直到消失,蓝色的钓灯幽幽地亮起来,鬼火一样射在水面上,他用这个来照浮子,一有鱼儿上钩,浮子就会往下沉,他得看准时机把鱼竿提上来。
多半时候他都不出声。
月亮像一只透明的小钩,浮起在水里,周围静悄悄的。
我经过河边许多次,从没看到过他钓上来鱼。我想,总会钓上来一些吧,一个这样年纪的人,应该不会有耐性将相同的失败重复上几遍甚至几十遍。有时候,我在边上看了许久,想问问他平时靠什么生活,却最终没有勇气开口。因为他从不与人对视,脸上现出的,也不是年轻人常见的活泼的神色,而是令人沉重的冰霜。
就算问了,他也一定不会回答吧。人与人之间,想要坦诚相见,应该得有经历年月的友谊作为基础,两个陌生人之间,心底隔着那么多的关卡、壁垒和丛生的荆棘,怎么可能呢?
春天刚起头的时候,公园并不是明媚、灿烂的,等到下过一两场雨,千万条枝子上钻出柔嫩的新芽,芽上缀着湛清的水珠,整座公园才像是被神奇的魔力唤醒,各种在秋天之后落光的叶子、各种在夏天之前凋敝的花朵,全都重新回来了,一片片、一朵朵,生在枝头,灿烂、明媚,时常会借着小风卖弄风情。这时节若去公园,不知不觉,流连的时间会愈加长久。
春光融融,原本清寂的上午和黄昏会变得不同。只要天光晴好,在公园南边的广场上会来一些人,他们大多上了年纪,穿着白色的练功服,裤脚和袖口都有松紧带束着,衣襟上有盘扣。等他们操练起来,就可以看明白,他们练的是太极拳。这么多人,将一套拳法练下来,一点儿也不出错,委实令人惊叹。屈膝、沉肩、转身、抬腿……从起势到收势,皆舒缓从容,充满张力,单从背影看,好几个,根本看不出年纪。
不知道他们中有没有真正的武林高手。电影《太极张三丰》中对这种可以“疾雷过山而不惊,白刃交前而不惧”的功夫有过精彩的演绎,可是,像我这样普普通通连三脚猫本领也没有的人,哪怕想破脑袋也不会明白,仅仅施展拳脚,便能以柔克刚以弱胜强以小力胜大力,便能兵不血刃所向披靡?在寻常人看來,那不就是螳臂当车以卵击石蚍蜉撼树吗?许多人都不太愿意相信没有亲眼所见的东西,我也一样。
广场周围种着几棵大树,只有六月间满树撑开粉色轻柔的小羽扇,我才知道那是合欢。
那些人操练完了,会在合欢树下歇一会儿,嘻嘻哈哈聊一阵,拾一两朵刚刚飘落的合欢花戴在发间。这鲜美的点缀,可以让所有的人工发卡黯然失色。这会儿,他们换了轻松的表情,已经不是先前严谨的习武者,而是俗世里快乐的凡人。
从河东边往北,快要离开这片河水的地方,建着一座木头矮亭,这里曾是我和爱芬经常见面的地方。我们靠着栏杆,长时间看平静的河水。河边的蒲苇长得茂密,尤其是秋天,苇花开起来的时候,白茫茫的一片,完全把我们遮住,这让我有一种安全感。有时候,我们还在亭子里坐着,别的人来了,我们不愿意走,就坐着听别人说话,直到那些人离开。很多人很无聊,爱芬这么觉得,我笑着赞同她,其实我们何尝不是如此。她跟我說了很多单位里的事,觉得自己一直在忍耐。我觉得她有些敏感,一些在我看来无足轻重的人或事总是在动摇她的内心。我劝她看开一些,有时候可以耳目失聪的。但是,她好像并不愿意听我的,她还是愿意当一个热血青年。
爱芬平时没啥别的爱好,就喜欢写点东西,写了,没有地方发表,就自己花钱去打印店打印了,装订成书,还会在扉页上签上名字赠给我。我看过她的作品很多次,有几个故事写得挺好的,我觉得就算随着年月的增长、人生经验积累得够多,我也写不出那样好的故事。
她后来爱上了写诗,经常去外地参加一些有许多陌生人的诗歌聚会。她在黄山的一次活动上结识了一个外地的男诗人,互生好感,俩人打电话、书信往来了好久,后来男诗人居然来我们这边教书,两个人还结了婚。那段时间,她常把他们合写的诗带来给我看。我不太喜欢诗,尤其是写得很怪的诗。我虽然不会轻易批评,但也没有违心地赞扬,不过,我觉得,他们志同道合,这样也算是不错吧。可是,没想到,两年还不到,他们就散了。
爱芬离婚以后,我没有再见过她。我曾经给她打过几次电话,她都没有接,发短信给她,也不见回。翻看记录,与她最近的一次短信联系也已经是在三年前,那年的中秋节,我给她传了一个祝福短信,祝她节日快乐,她没有回复。之后的时光,我们之间只剩下虚无。
我有时候去公园,经过那个亭子,看见里面空荡荡的,想起她曾经坐在亭子里,脸上有笑地对我说话,我的心里便会有些难过。她失去了她的爱情,便将自己困于心灵的孤岛,这样可以疗伤吗?
我不知道。
公园的入口有两个,一个在西边,一个在南边,南边那个是正门口,平时有门卫守着,不让推车的小贩和骑车的人进去。
西边的入口没有门,林木荫翳,比南边冷清。沿着一条干净的鹅卵石小路往里,不远便可遇见一尊白石头雕像——那是一个身材修长的古人,以帻覆髻,神情坚毅,目光炯炯,他手里拿着竹简,宽大的衣袖、长衫,皆临风飘然。看上去像是一位思想家,要么就是文学家,雕像底座并没有文字说明,所以并不知道刻的是谁,更不知道是哪位匠人刻的。他是那样的栩栩如生,好像吹一口气就可以解了定身术直接活过来。
雕像周围有几棵鹅掌楸,在别的公园里,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的树。它们的叶子长得很奇特,就像古人穿在身上的马褂——那宽大的褂子,不光有袖,有腰身,还有下摆。摘几片来带回家里,一两天后,叶子起了褶皱,就更像马褂了,仿佛穿脏了,脱下来欲拿到溪边去洗的。鹅掌楸在五月里会开花,花朵就像描了金红色图案的酒杯,一只只立在枝叶间,忽隐,忽现。
等到秋天,这成千上万件绿马褂会变得通体金黄,隐隐透着一种贵族之气,这才是这棵树最耀眼的时光。
公园里,白天是安静的,有时候慢慢走上一圈,会一个人影也不见……看见的,只有那些独自生长、独自开花的植物。传到耳边来的声音也很有限,有时是风声,风吹动树叶发出窸窸窣窣轻而细碎的声响;有时是鸟声,各种不同的鸟儿在这里唱歌。我有时候会想,因为会开花,因为会唱美妙的歌,所以,在它们的生命里,不会有冷清和寂寞这样的概念吧。
无数次地去公园,自幼芽于枝头新萌直至斑斓的秋叶披上清白的冷霜,公园里,没有一刻景致会完全相同。即便立于同一棵树下,今日阳光下所见与昨日雨水中所见,今日微风中所见与昨日轻雪中所见,今日鸟鸣中所见与昨日寂静中所见,总有一些细微的差别,但是这种差别又都并不明显,往往是模糊的,只有人类的心灵能感觉到。就在夜的帘幕即将垂临的时刻,天边所有的颜色:玫瑰金、珊瑚白、宝石蓝,皆一一消隐,如果人的眼睛能将这个过程细分到秒、毫秒,甚至更短的微秒,有那么一瞬,我们便可以看见,所有的枝干、树叶,一起隐去了,只剩那些浅浅颜色的温柔的花朵,仿佛脱离了一切支撑悬浮于空中——这便是黄昏和夜晚的分界,就像一扇门,推开它就是从生到死,就是从阳至阴,就是从宏大归于渺小,从清明归于混沌……
天一陷入黑暗,路灯便亮起来了。柔和的灯光,照着弯弯曲曲的小径,照着挨挨挤挤的枝叶。许多次,那些枝子不安分地伸到小路上来,擦着人们的头发或手臂,叶子柔软,碰到手臂上,像亲切的抚慰,让人茫然的内心瞬间安静下来。
小径上,时常会迎面跑过来一条大狗,浑身黑色,它被一个个头很高的年轻人牵着,擦身而过的时候,能听见狗呼哧呼哧的喘气声。遇见次数多了,大黑狗会热情地朝我摇摇尾巴,那么高大的狗,看上去却那样和善,我从不曾怕过它。有时候,我也会轻声招呼它,像招呼一个老朋友,但这是我和它之间的友谊,与它的主人无关。
道旁的一些长椅上,常坐着一些恋爱中的情侣。他们八爪鱼一样热火朝天地缠在一起,连经过的脚步声也惊扰不了他们。遮蔽他们的,除了茂密的植物,就是无边的夜色,他们好像构建了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世界,别人的声音传到他们这里只会反弹回去,别人的视线扫到他们这里,也只会让别人羞愧,感觉自己是一个偷窥者。
一个黄昏,我在南边的广场上看见几个小姑娘,她们跟在一个帅气的男生身后,巴巴地问他:“如果我们以后来看你,你会见我们的吧?”她们花骨朵一样,热烈而单纯,让人不忍心拒绝。那个男生比她们大不了几岁,但是高大帅气,站在她们中间,就像一只鹤。他很干脆地回答:“那当然,无论什么时候,你们来看我,我都会招待你们的。”
其实,这样的承诺是最靠不住的,这些可爱的小花朵们以后就会知道。现实并没有那么容易,而且,往往不美,甚至残酷。我只是静静地目送他们的身影,希望她们能尽快忘了他。
我是一个极无方向感的人,在这座阔大的公园里时常会迷路,我通常就是走到哪儿算哪儿,有时候,走了好久,会因为被某一棵树或某一处景致吸引,反复拐到一条相同的路上去。
公園里有几棵我非常喜欢的树,十月樱算一棵,桥边的朴树也算一棵。
进入秋季,多数植物显露出萧索的境况,这会儿,西边土坡上的那棵十月樱却开起花来。寻常所见的樱花多是重瓣的,且在春天的时候开,一团一团,有清淡的香气。这一棵却不同,竟然选择在十月里绽开笑脸。它的花朵也不似其他春天开的花朵那般深粉,而是白色的,单瓣,花蕊有一点点红,素洁而美丽。
一群蚂蚁选了这棵有树洞的十月樱做窝,这或许就是它们所认为的风水宝地——因为洞口有苔藓,还晃悠悠地探出一棵植物的小芽。蚂蚁们步调一致,用嘴将树洞深处它们不需要的木屑挖出来,运到洞口吐掉,一只接着一只。我不知道它们的工程会设计得多大,要进行多久,我也不知道我这样视而不见,算不算是以对蚂蚁行善的名义对一棵美丽的花树作恶。
桥边的朴树静静地长在那里,好多年了,和弯曲的小桥构成了一道风景,我喜欢趴在桥栏上,看它伸过来的叶子,非常多的绿叶,密密层层,每一片叶子皆筋脉清晰,有柔和的弧度,像是画出来的。白天从树旁经过的时候,只会感觉它长得好看,树影浓密,而在夜晚,它的身影隐入夜色,不能看清轮廓了,却发现它的香气比日间更加浓烈,让任何一个经过的人都不能忽视。这是一棵在温暖湿润的环境中生长起来的树,能长成如今这样,具有这样强烈的吸引力,我觉得是它一直保持初心,没有长偏的缘故。
初秋的某个夜晚,就是在这棵树旁,我竟然迎面遇见了那个人。
柔和的路灯光里,我看见他脸上温和的笑——许多已经淡去的记忆便倏忽而至,汹涌澎湃,几乎将我淹没。许多年前,他也曾这样问我:“你好吗?”
我不知道,我脸上是不是仍然保持着平静的笑,他大约是看不出,我的心里仿佛擂响了许多只大鼓,我竭力用安静掩饰着内心的混乱——许多年前那个青春的身影、灿烂的笑脸,全都在这一瞬间坍塌碎裂化成齑粉,眼前这个微微发福,额上皱纹堆起,鬓边白发苍然的人,真的会是他吗?
可是,我在他的瞳仁里,也看到了同样被生活这张粗粝的砂纸打磨得千疮百孔的我,心里不禁涌来一阵悲凉。和许多年前一样,他和我要去的方向截然不同,注定只能擦肩而过。
一直记得当年他在宿舍里播放的那首歌:“我的女孩,不是你不好,有些问题,确实存在……”
眼泪终于不争气地漫出我的眼眶。
作者简介
孙敏瑛,女,中国作协会员,作品散见于《青年作家》《清明》《雨花》《青春》《散文》《人民日报海外版》 《文学报》等,并被《散文海外版》《语文教学与研究》(学生版)《意林》(少年版)《青年文摘》《法制博览》《时文博览》等转载,著有个人散文集《一棵会开花的树》,小说集《暗伤》。有多篇散文入选年度精选集。
责任编辑 青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