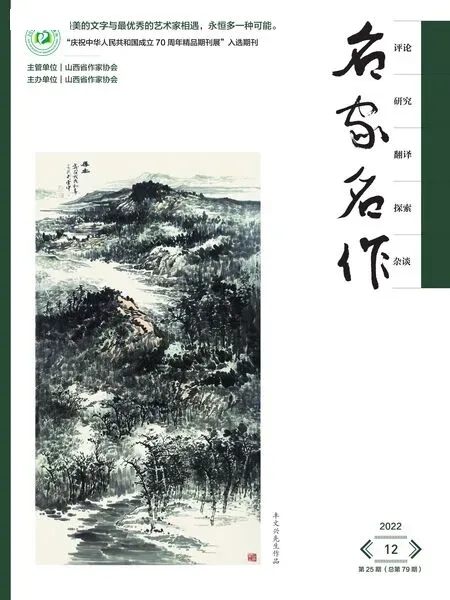电影中的瘟疫叙事类型
吴雨宁 曹传红
从公元前430—前427年的“雅典鼠疫”、公元6世纪地中海的“查士丁尼瘟疫”,到我们熟知的欧洲中世纪的“黑死病”,再到21世纪初的SARS和埃博拉病毒,可以说,人类的发展史也是人类与瘟疫的抗击史。而对瘟疫的文学化转述也具有漫长的历史,足以构成自己的谱系。《十日谈》便是薄伽丘以中世纪黑死病为背景创作的;《鲁滨孙漂流记》的作者丹尼尔·笛福所著的《瘟疫年纪事》(1722年)讲述了1665年发生在伦敦城的大瘟疫;加缪的《鼠疫》(1947年)和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1985年)都是在瘟疫的背景下揭示人性沉沦和爱情隐喻。而对于人类面对瘟疫的思考,电影也一直从未缺席,并随着媒介载体的发展日益成为瘟疫叙事的重要场域。1995年美国上映的《极度恐慌》(Outbreak)是根据埃博拉病毒事件改编的,2009年上映的日本电影《感染列岛》是以禽流感为背景。2011年9月美国上映的影片《传染病》(Contagion)灵感来源于SARS病毒的疯狂传播。2013年8月上映的韩国电影《流感》,故事源于当年的非典和禽流感真实事件。不难看出,艺术来源于生活,每一次人类历史上的瘟疫爆发都会推动瘟疫文学和影视进入创作的高产期。但无论是文学名著还是影视经典,每一次成功的虚拟叙事背后都是现实世界中一次真实发生的重大灾难,共同构成数代人独特的瘟疫记忆。1976年由科斯马图斯执导的《卡桑德拉大桥》(The Cassandra Crossing)开创了一种瘟疫叙事电影的经典模式,自此之后,多名导演编剧在此基础上融合了更多的元素,使电影中的瘟疫叙事呈现出空前丰富的类型。盘点近些年电影中的疫情叙事,笔者认为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叙事类型。
一、超现实灾难叙事
灾难片是以自然界、人类或幻想的外星生物给人类社会造成的大规模灾难为题材,以恐怖、惊慌、凄惨的情节和灾难性景观为主要观赏效果的电影类型[1]。
而瘟疫毫无疑问是人类世界面临的巨大灾难,因此在一些瘟疫电影中很容易找到灾难片的基本元素:它们通常也采取超写实的手法,巧妙利用电脑特技和音响效果,以较为夸张的方式营造出一种末世灾难景象和惊悚绝望的氛围。这就是瘟疫叙事中最常见的一种类型——超现实灾难叙事。以前文提到的《极度恐慌》为例,这部电影以其紧凑的剧情、宏大的场面,加上奥斯卡影帝的加持,赢得了当年的口碑、票房双高。片中通过两组超长镜头,把支离破碎的符号性元素通过蒙太奇的手段合理地组接在一起,教科书般完整地展现出埃博拉病毒传播的不同途径,营造出逼人的悬疑惊悚气氛。大多数电影在营造恐慌的气氛时总是喜欢用“突变”来烘托气氛。但是,“突变”在很多时候带来的仅仅是视觉上的冲击,很少能够给观众造成一定的心理影响。而《极度恐慌》选择病毒作为“突变”的因子,虽然没有具体的形象,但是成功营造出了一种未知的恐怖感。
此类电影有时也会融入一些诸如丧尸、外星生物等科幻恐怖元素,为真实事件增添超现实特征,以烘托出人类所处的渺小脆弱境地。《惊变28天》(28Days Later)和《我是传奇》(I Am Legend)分别再现了英国伦敦和美国纽约这两个国际大都市是如何因病毒入侵丧尸变异而瞬间沦落为地狱之都的。《惊变28天》中空无一人的医院、堆满尸体的教堂和一片狼藉的城市,使科幻与现实场景完美融合,给人如临其境的代入感。在威尔·史密斯主演的影片《我是传奇》中,人类因病毒感染而大批死亡,没有死掉的人病变成躁狂嗜血的丧尸,白天藏匿在阴暗处,夜晚四处活动攻击人,纽约瞬间沦为空城,人类世界几近遭到毁灭。再如另一部美国电影,2007年上映的《致命拜访》(The Invasion),讲述了一种古怪且陌生的太空生命体依附在爆炸产生的碎片上抵达地球,并最终变成病毒开始迅速扩散,病毒通过体液和针刺传染,被感染的人变成了一个个没有感情的宿体,整个世界危机四伏,病毒之下,秩序被推倒,文明被颠覆,人类即将彻底失控。当然,这些元素同时也是电影卖座的噱头,甚至成为高票房的制胜法宝,它充分利用了观众对未知的恐惧,从视觉和心理上形成双重压迫,从而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和感觉刺激,这种悲剧快感达成了一种另类的审美效果。
虽然超现实灾难叙事电影在题材内容和处理方式上是背离传统的现实主义风格的,是对人类恐惧的奇观呈现,但归根结底都是在失真的镜头话语中探讨真实存在的社会问题——面对瘟疫,人们的恐惧感与虚无感会比灾难本身带给社会更多的问题,而渺小的人类能否真的依靠自己避免走向灭绝,这个疑问将长久地回荡在每一个走出电影院的观众心中。
二、个体情感微观叙事
与超现实灾难叙事电影刻意渲染的宏大末日场面不同,个体情感微观叙事电影将镜头微焦于瘟疫大背景之下小人物的人性与人情。透过瘟疫这个放大镜,早已被日常化的亲情、友情、爱情等一切人类情感都被空前激发,重新迸发出巨大的能量,转化为把把利刃,回击着同样被瘟疫放大的恐慌、冷漠和残忍。当死亡的威胁将大多数人追逼到末路穷途之时,仍有人会为了心中的情感,主动选择反身直视死神,义无反顾地去拥抱死亡。
在此类瘟疫电影所涉及的所有情感中,母爱叙事恐怕是最富表达力和共情力的,也得到了众多电影导演的青睐。比如,金成洙编导的电影《流感》(The Flu)中女主角金仁海(秀爱饰)是一位女医生,同时也是一位单身妈妈,她的双重身份设定将她置于伦理的两难境地,一面是作为医生的职业道德与良知,另一面是作为母亲无条件的爱与责任。金成洙导演在叙事上的阶梯性设计使观众的情绪随着叙事的层层推进逐渐达到高潮,先是隐瞒女儿病情带她进入安全区,而后担心女儿等不到抗体研制直接用活人试样,最后当政府决定放弃这座城市下令军队开枪,金仁海挺身而出为女儿挡子弹,那一刻,肆虐的病毒在母爱的光辉之下也黯然失色。
相比母爱的无私与深情,瘟疫电影中对爱情叙事的处理更为狂热、无序,甚至拥有堪比瘟疫的强大杀伤力。最具代表性的影片当数《霍乱时期的爱情》(Love in the Time of Cholera),正如影片的标题所揭露的,霍乱被迫退为叙事的背景,而真正可怖的是主人公这种横跨半世纪的无法名状的爱情:疯狂的、隐秘的、粗暴的、羞怯的、忠贞的、柏拉图式的、放荡的、转瞬即逝的、生死相依的……另一部改编自文学作品的影片《魂断威尼斯》(Morte a Venezia)是导演维斯康蒂根据小说《威尼斯之死》改编的。瘟疫除了作为叙事背景,同样起着营造氛围和隐喻主人公情感变化的作用。影片的结尾处主人公阿森巴赫为了爱情甘愿染上瘟疫命丧威尼斯。瘟疫既是一种描绘感官享受、张扬情欲的方式,同时又是一种表达情感压抑、直击死亡的途径。1995年上映的法国电影《屋顶上的轻骑兵》(Le Hussard sur le toit)中的爱情叙事将瘟疫进行了更加浪漫化的处理。当男女主人公携手穿行在病毒肆虐的疫区时,前路未知,生死未卜,村庄可以被毁,乌鸦可能迁徙,尸体也会腐烂,但是爱情却不会随着这些冷酷的现实而消失褪色。在灾难面前,爱情并不是生命不可承受之轻,这是骑士精神的浪漫,也是霍乱时期的爱情。
不难发现,在个体情感微观叙事电影中,瘟疫本身被“悬置”了,而关乎瘟疫的家国情怀、集体利益、社会道德等宏大的概念也一同被“悬置”了。影片将特写镜头对准了个体生活中的每一个“此在”与“当下”,帧帧都生动地再现了鲜活的人性与浓烈的世情。或许,个体的情感表达在此时此刻成了人们面对残忍冷漠病毒的一剂麻药,或是唯一的解药。
三、人性弱点暗黑叙事
揭露人性的阴暗与残酷是非常冒险的行为,无论是否借由艺术的表征。如尼采在《善恶的彼岸》中指出:“凝视深渊过久,深渊将回以凝视。”当你审视邪恶的时候,邪恶也如同一面镜子审视着你的内心。即便如此,电影人在处理瘟疫题材时,还是无法回避对自私、贪婪、冷漠、邪恶等人性弱点的无情揭露。此类电影共同传达出一种观点:无论何时,瘟疫本身不是最恐怖的,面对灾难,真正致命的是人内心深处潜藏的黑暗与邪恶。因此,危机不只来自外在的病毒,更来源于我们人性的沦落。正如在电影《传染病》中主人公基弗预言的那样,人类的恐慌会比病毒带来的问题严重得多。[2]
华纳兄弟在2011年出品的电影《传染病》由史蒂文·索德伯格执导,在叙事结构上,影片放弃单一主线而采取了四条主线平行叙事的结构,以现实主义的风格绘制了当灾难来临时的浮生百态众生相。然而,在这部电影中并没有刻意宣扬人性的光辉与温情,也没有像传统灾难电影,在影片结束的最后一分钟,突然出现了一个披荆斩棘、上天入地,于千钧一发之际救人于危难的孤胆英雄。相反,它利用大量的镜头呈现了社会的失序与人性的阴暗:病毒出现的消息像它本身一样被迅速传递出去,人们立刻乱成一团,各自保命,生活物资和相关药品被抢夺一空,警察和护士相继罢工,引发场场暴乱,甚至出现了因为疫苗而导致的绑架案。不只是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民众和国家机器的矛盾也逐渐被揭露出来:在大城市强制执行宵禁,为了维持稳定封锁州界,某些政客为了推卸责任寻找替罪羊,各州和国家之间存在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数年,数十年,甚至数百年花费代价建立起来的道德体系,在朝夕之间被相互碾压的人性粉碎,并最终崩塌。而在影片的结尾处对瘟疫根源的揭露,更是导演对人性罪恶的最高级别审判——导致这场人类灾难的正是人类自己。
此类电影还存在另外一个共同点——影片中对人性的黑暗面的表述充满了象征意义,以寓言的形式隐喻时代的灾难。正如苏珊·桑塔格所说:“阿尔托、赖希、加缪这些彼此非常不同的作家做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尝试,想把瘟疫当作最阴森、最具灾难性的事物的隐喻。”[3]费尔南多·梅里尔斯执导的电影《盲流感》(Blindness)改编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萨拉马戈的小说《失明症漫记》,影片中的瘟疫是一场会使人失明的白色眼疾,失明症迅速蔓延,整个城市陷入了一场空前的灾难。被感染的人们失去的是视力,世界失去的是秩序与文明。一群人失明,世界陷入恐慌;所有人失明,人性弱点暴露无遗:傲慢、妒忌、暴怒、懒惰、贪婪、贪食及色欲,吞噬着几千年来构筑的完美人性。最终,人类因此毁灭。由丹麦鬼才导演拉斯·冯·提尔自编自导自演的电影《瘟疫》(Epidemic)以一种更为先锋实验性的手法讽刺了人性与善恶之间的相对性。在影片最后,冒险外出行医的梅斯梅尔医生发现自己其实就是那场瘟疫的始作俑者,他就是病源的携带者,是他传播了这场瘟疫,所有的人都在受尽折磨,而他却以为自己是一个解救者。
如上所述,大多数的人性弱点暗黑叙事电影都选用了“人类—瘟疫—人类”的回环叙事模式,即由人类引发的瘟疫最终反噬人类自身。疫病可以通过有效的医学手段治愈,但当身体上的病疾逐渐转化成精神上的崩塌,直至全面失控,人性的沦落使人类将高高举起的巨大石块最终砸向了他们自己,成为荒诞而真实的寓言。
四、结语
叙事的本质是讲述,叙事中无法回避讲述者自身的观点和立场。电影中的瘟疫叙事虽然处理的是瘟疫主题,其实是创作者通过瘟疫对人与世界、人与他人、人与自我关系的纯粹解剖,刀刀充斥着深刻的批判与内省。在灾难的探照灯下,渺小无助、手无缚鸡之力的弱者与征服病毒拯救世界的英雄并不相斥;人性的无私大爱与邪恶阴暗也不矛盾;对生命本源的追问和对死亡价值的探索最终殊途同归。因此,无论是超现实灾难叙事、个体情感微观叙事,还是人性弱点暗黑叙事,都不仅是关于瘟疫的预言性叙事,而且是一种面对瘟疫的精神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