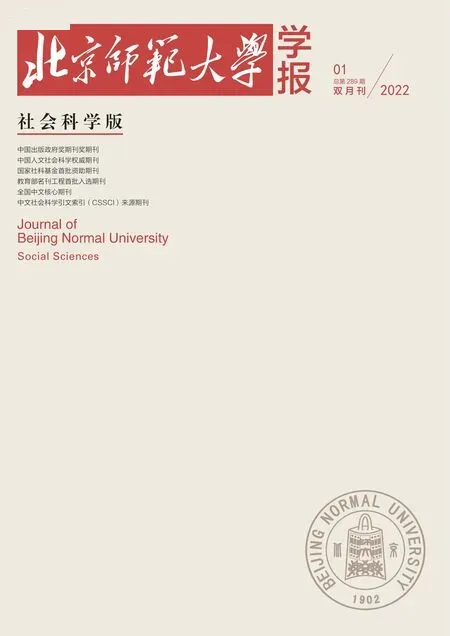精英与平民的“疏离”和“相遇”
——以霍夫施塔特与拉什民粹主义论述为中心的考察
安 然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875
美国学术界对民粹主义的研究自20世纪30年代至今,经历过三次热潮和转向,形成了肯定和批判两种传统(1)第一次高潮出现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约翰•希克斯为代表的正统派对民粹主义抱以肯定和同情态度,认为19世纪末的人民党运动根源于工业垄断资本崛起造成的农民经济困境,开启了进步主义运动的先河。参见John D.Hicks,The Populist Revolt:A History of the Farmer’s Alliance and the People’s Party,Minneapolis:Minnesota University Press,1931。第二次高潮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以理查德•霍夫施塔特为代表的修正派对民粹主义运动提出质疑和否定,认为其起因并非农民经济处境恶化,而是农民对自身地位下降的反应,其反犹倾向是麦卡锡主义的思想源头。参见〔美〕理查德·霍夫斯达特:《改革时代——美国的新崛起》,俞敏洪、包凡一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三波研究从20世纪70年代延续至今,研究取向出现分化。一部分研究者认同正统派,驳斥修正派证据不足、结论牵强,同时运用跨学科的方法,从新的角度对正统派观点进行了修正和补充。参见Norman Pollack,The Just Polity:Populism,Law,and Human Welfare,Urbana: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87。另一部分学者坚持修正派的负面评价,认为民粹主义是一种煽动和破坏力量。参见Michael Kazin,The Populist Persuasion:An American History,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5。。自由派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1916—1970)和右翼民粹主义史学家、社会评论家克里斯托弗·拉什(Christopher Lasch,1932—1994)可算两位典型代表:前者开创了美国民粹主义研究的批判传统,后者则将右翼民粹主义改造为一套社会批判理论。他们对民粹主义的看法既针锋相对、立场各异,又存在歧见之下的交叉与共识,其各自代表的精英与民众立场疏离又相遇、拮抗又互补。就两者对民粹主义及相关问题的论述进行比较分析,不但有助于廓清美国民粹主义研究的基本语境,而且可以借此透视其背后更宽广的理论图景。遗憾的是,既往研究关于霍夫施塔特与拉什思想关联的考察,仅限于个人交往和学术渊源的层面,并无对二者思想体系的深入比较。本文将由此入手,考察二者思想体系的异同,探究其背后的内在逻辑结构及现实成因。
一、两种视野下的民粹主义研究
霍夫施塔特与拉什的民粹主义研究代表着不同理论视野下的两套话语:前者以温和自由主义的理性化视野,开创了自由派文化精英的民粹主义批判传统;后者以右翼民粹主义的道德立场,提供了基于内部视角的抗议与申辩。
在早期研究中,“民粹主义”一词在美国学术界特指由19世纪末深陷经济困境的美国中西部农场主发起的人民党运动,被视为进步主义运动与罗斯福新政的先声,推动了体制改良和民主化的进程。霍夫施塔特颠覆了这个传统。他将民粹主义的内涵扩大化、负面化了。作为一种根植于本土的非理性政治观念、社会情绪和思维方式的综合,它可追溯至19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杰克逊民主。它在人民党运动中大规模爆发,波及进步主义运动,被罗斯福新政遏制,随着麦卡锡主义的崛起再度泛滥。
霍夫施塔特区分了民粹主义的两种类型:一是矛头向上的反精英主义。在工业扩张浪潮中地位下降的农场主仇视东部的有钱人和“道德败坏”的城里人,通过联合、游说、道德控诉、建立第三党等形式与之抗争(2)〔美〕理查德·霍夫斯达特:《改革时代——美国的新崛起》,俞敏洪、包凡一译,第43、67,6,49,67,21,28,28,2,28页。;二是目标外指的本土主义和种族优越感。“平民主义和进步主义运动染上了极浓厚的本地人对移民浪潮的反对情绪(3)〔美〕理查德·霍夫斯达特:《改革时代——美国的新崛起》,俞敏洪、包凡一译,第43、67,6,49,67,21,28,28,2,28页。,呈现出“严重的地方主义”、“排外主义、民族主义”和“反犹太的色彩”(4)〔美〕理查德·霍夫斯达特:《改革时代——美国的新崛起》,俞敏洪、包凡一译,第43、67,6,49,67,21,28,28,2,28页。。反智主义是两类民粹主义共同的思维特征,即以直观经验或主观成见排斥自己不能理解的“智识”(intellect)。智识不同于“智力”(intelligence),“智力追求把握、运用、排序、调整和评估,而智识是头脑中的批判性、创造性和沉思的一面,是检查、思考、怀疑、理论化、批评和想象”(5)Richard Hofstadter,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New York:Vintage Books,1962,pp.25;407,23;154;145-146.。换言之,智力是生物性、技术性的,而智识是社会性、思想性的,是基于怀疑精神和批判意识的高级文化创造。民粹主义的本质,就是政治上的反智主(6)〔美〕理查德·霍夫斯达特:《改革时代——美国的新崛起》,俞敏洪、包凡一译,第43、67,6,49,67,21,28,28,2,28页。。
民粹主义的根源包括个体因素与体制因素。个体因素就是农场主的非理性心态,即所谓的“地位革命”。在霍夫施塔特看来,人民党运动的真正原因,不是东部大资本剥削带来的客观经济困境,而是西部小农场主自身对社会发展的拒斥。他们迷信自身作为社会道德楷模与中坚力量的“土地神话(7)〔美〕理查德·霍夫斯达特:《改革时代——美国的新崛起》,俞敏洪、包凡一译,第43、67,6,49,67,21,28,28,2,28页。,拒绝承认工业垄断资本的崛起、“农村价值体系和宗教信仰的崩溃,以及土地神话顶峰时期道德论调的逐渐被摒弃”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必然趋(8)〔美〕理查德·霍夫斯达特:《改革时代——美国的新崛起》,俞敏洪、包凡一译,第43、67,6,49,67,21,28,28,2,28页。。自我定位与客观现实的巨大落差使其“感到困惑和愤恨(9)〔美〕理查德·霍夫斯达特:《改革时代——美国的新崛起》,俞敏洪、包凡一译,第43、67,6,49,67,21,28,28,2,28页。,遂滋生出反智的民粹心理。体制因素即民主政治的非理性潜质——对平等主义的过度诱导所导致的“大众化冲动(10)〔美〕理查德·霍夫斯达特:《改革时代——美国的新崛起》,俞敏洪、包凡一译,第43、67,6,49,67,21,28,28,2,28页。。民粹主义“建立在这个国家的民主制度和平等主义情绪中”,“它长驱直入我们的政治,是因为它与我们对平等的热情联系在一起(11)〔美〕理查德·霍夫斯达特:《改革时代——美国的新崛起》,俞敏洪、包凡一译,第43、67,6,49,67,21,28,28,2,28页。。普通人的政治能力备受推崇,仿佛“他们的声音就是民主的声音,就是道德本身(12)〔美〕理查德·霍夫斯达特:《改革时代——美国的新崛起》,俞敏洪、包凡一译,第43、67,6,49,67,21,28,28,2,28页。;平民情结蔓延到文化领域,“随着大众民主获得了力量和信心,它加强了一种普遍的信念,即天生的、直觉的、民间的智慧比文人和富人有教养的、过分讲究的、自私的知识更优越(13)〔美〕理查德·霍夫斯达特:《改革时代——美国的新崛起》,俞敏洪、包凡一译,第43、67,6,49,67,21,28,28,2,28页。。智识阶层被视为与权势阶层沆瀣一气的“局外人(14)〔美〕理查德·霍夫斯达特:《改革时代——美国的新崛起》,俞敏洪、包凡一译,第43、67,6,49,67,21,28,28,2,28页。。
霍夫施塔特曾被包括拉什在内的很多学者批评为具有文化精英主义倾向:“他的作品令人遗憾地强化了一种倾向,即美国自由主义者将自己视为一个文明的少数群体,一个由乡巴佬和其他‘反知识分子’主导的社会中的开明精英。”(15)Casey Blake and Christopher Phelps,“History as Social Criticism:Conversations with Christopher Lasch”,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1994,80 (4),p.1317.但这种精英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理性精神。霍夫施塔特强调民主的质量,要求个体在制度理性下保持行为理性:一要思想进步,顺应社会发展潮流;二要开放多元,包容其他利益集团;三要行事温和,摆脱被迫害妄想症式的“偏执狂风格”(16)参见:Richard Hofstadter,“The Paranoid Style in American Politics”,in Sean Wilentz,ed.,Richard Hofstadter,New York:Library of America,2020,pp.503-504。。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霍夫施塔特对20世纪50年代麦卡锡主义泛滥、批判思维濒于“毁灭性凋零”的回应(17)Richard Hofstadter,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p.3.,他希望通过反思非理性力量在美国的历史前因,发掘其社会土壤,反冲当时极右思潮的压倒性力量。
拉什出生在人民党运动的发源地——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市,是美国思想界重要而颇具争议的人物。他一生思想多变、数次转向,从自由主义到激进左翼,再经保守转向,最后落脚于右翼民粹主义。
拉什发展了霍夫施塔特对民粹主义的广义界定:将其历史上溯至美国的农业中产阶级传统,认为它与杰斐逊、杰克逊和林肯民主一脉相承,同时扩展其社会内涵,把它与社会主义并列为反资本主义的两大模式(18)〔美〕克里斯托弗·拉希:《精英的反叛》,李丹莉、刘爽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年,第5页;Christopher Lasch, The True and Only Heaven:Progress and Its Critics,New York:W.W.Notion & Company,1991,pp.221-225;Christopher Lasch,The Agony of the American Left, New York:Alfred A.Knopf Inc.,1969,pp.3-5。。右翼民粹主义是二战后新出现的类型,吸收了一部分社会保守主义(19)二战前后,美国保守主义沿着两条路线复兴:一支是主张自由放任的经济保守主义(有人称之为自由意志主义),以弗里德里希·奥都斯特·哈耶克、米尔顿·弗里德曼、默里·罗斯巴德等为代表;另一支是维护传统价值观的社会保守主义(即传统主义),以拉塞尔·柯克、理查德·韦弗等为代表。的主张,相当于具有社会保守主义观念的民粹主义,或拥有底层思维的社会保守主义(20)Christopher Lasch, The True and Only Heaven:Progress and Its Critics,p.505.,接近被西蒙·利普塞特视为美国立国五大基本信条之一的朴素民粹思想(21)Seymour Martin Lipset,American Exceptionalism:A Double-edged Sword,New York:Norton & Company,1996,p.31.。关于民粹主义的起因,拉什与霍夫施塔特的看法截然相反。他认为,导致民粹运动爆发的“主要的威胁似乎并不源于底层的群众,而是来自社会的顶层”(22)〔美〕克里斯托弗·拉希:《精英的反叛》,李丹莉、刘爽译,第19,41,3,51,59,7、12,67、130-142,68页。。民众的愤怒情绪主要是因为“那些在阶梯之上的人早已把梯子撤掉了(23)〔美〕克里斯托弗·拉希:《精英的反叛》,李丹莉、刘爽译,第19,41,3,51,59,7、12,67、130-142,68页。;民众社会观念的保守倾向要归咎于精英们拒不接纳乡土大众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致使其不被倾听、无处发声而愈发保守。霍夫施塔特将民粹主义作为社会批判的对象,而拉什以右翼民粹主义为尺度进行社会批判,其内涵包括:
第一,反对全球精英,重建地方社会。拉什反对的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精英,而是专门从事全球性业务的国际化精英。20世纪以来,资本全球流动和跨国企业的兴起造就了一个在国际市场上运筹帷幄、获取财富的“新阶级”。“他们的忠诚是国际性的,而不是地区性、国家性或地方性的(24)〔美〕克里斯托弗·拉希:《精英的反叛》,李丹莉、刘爽译,第19,41,3,51,59,7、12,67、130-142,68页。,“他们看待周围世界的态度基本上与旅游者无异,这种态度不可能让他们对民主有任何奉献”。右翼民粹主义的精髓不是排外而是“守內”:“热爱土地”、“把根留住(25)〔美〕克里斯托弗·拉希:《精英的反叛》,李丹莉、刘爽译,第19,41,3,51,59,7、12,67、130-142,68页。,培育社会责任感,守护民主的根基。
第二,捍卫本土主流文化,抵制多元文化主义。拉什认为,当前美国社会的一大问题是“精英的思想越来越偏狭,这意味着政治意识形态与普通公民所关注的事务完全脱节(26)〔美〕克里斯托弗·拉希:《精英的反叛》,李丹莉、刘爽译,第19,41,3,51,59,7、12,67、130-142,68页。。自由派和激进左派精英尤甚:前者热衷于干预和控制,不信任大众的自治能(27)〔美〕克里斯托弗·拉希:《精英的反叛》,李丹莉、刘爽译,第19,41,3,51,59,7、12,67、130-142,68页。;后者在多元文化的名义下打压本土主流文化,将种族平等、女权、同性恋权利等置于核心议程,对能力危机、政治冷漠等根本问题却不闻不问,沦为本末倒置的“伪激进”主(28)〔美〕克里斯托弗·拉希:《精英的反叛》,李丹莉、刘爽译,第19,41,3,51,59,7、12,67、130-142,68页。。右翼民粹主义要立足于本土主流大众文化,对此进行反制。
第三,恢复自由资本时代的社会主体和生活方式。“平民主义的根本是维护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这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被普遍视为公民美德的必要基础。(29)〔美〕克里斯托弗·拉希:《精英的反叛》,李丹莉、刘爽译,第19,41,3,51,59,7、12,67、130-142,68页。小资产阶级是19世纪自由资本时代的社会主导阶层。拉什将这个以自主性、公民美德、社区精神著称,堪称美国市民社会原型的中下阶层作为右翼民粹主义的载体,希望推动其复兴、重塑美国的社会机体,“当世间的男男女女不是靠政府而是在朋友和邻里的帮助下为自己谋利时,民主才能真正实现”(30)〔美〕克里斯托弗·拉希:《精英的反叛》,李丹莉、刘爽译,第4页。。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进入阿兰·沃尔夫称为“政治右转、文化左行”的时期(31)James Davison Hunter and Alan Wolfe,Is There A Culture War?A Dialogue on Values and American Public Life,Washington,D.C:Pew Research Center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2006,p.55.:在经济领域,新保守主义市场化改革因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迅速展开,一批国际化资本家应运而生,以全球市场为导向竞争、逐利,冲击了本土中下层的利益;而在社会领域,自由化进程稳步推进,并日益占据主导地位(32)Christopher Lasch, The True and Only Heaven:Progress and Its Critics,pp.505-507.,威胁到一部分观念保守的中下层所捍卫的主流价值观。拉什站在身受经济与文化双重打击的本土中下层立场上,将经济激进主义与社会保守主义糅合为一套以道德为中心的社会改造方案:机会平等的生产条件、公开平等的对话机制、个体独立和生产主义、社区互助与多元社群文化、宗教虔信和道德自律等等,抵制经济保守化导致的两极分化和社会自由化带来的主流文化边缘化的趋势。
总体上看,两位学者在各自的学术视野下,对民粹主义作出了截然不同的历史评价:霍夫施塔特秉承现实的改良思维,将民粹主义视为非理性的历史失误,体现了民主化进程中的危机和病灶;拉什在眼光向下的保守倾向下,将扎根地方、立足本土主流价值的右翼民粹主义当作针对当前病症的解毒良药。
二、社会批判中的分歧与交错
两位学者对民粹主义的看法依托于各自的思想体系。在与民粹主义相关的社会运动、社会结构、制度环境,乃至更根本的现代性问题上,二者的观点时常相悖,但也有交叉。
(一)对社会结构与体制运行的不同判断
霍夫施塔特与拉什对民粹主义的歧见直接来自对民众运动的认知差异。霍夫施塔特注意到民众运动蕴藏着影响历史进程的强大力量,因而格外关注其中的非理性成分和反自由、反进步的危险倾向,冒着犯众怒的风险提出批判(33)Richard Hofstadter,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prefatory note,p.vii.;而拉什则看到民众运动的虚弱,认为美国的民众运动缺乏系统的理论指导和成熟的斗争策略,分裂短视,难当大任(34)Christopher Lasch,The Agony of the American Left, pp.5-8.,民主化的真正问题是民众力量太弱,而非太强。
对民众运动的态度与两人对社会结构的理解有关。霍夫施塔特认为农场主阶层的衰落是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其民粹心态的症结在于未能调适自身的角色冲突以适应时代:作为卷入商品化进程的市场主体,这个阶层承担着“硬的商人角色”,讲求实际,参与改良,而作为一家之长的社会主体,这个阶层代表“软的农村传统”,保守懦弱、感性冲动(35)〔美〕理查德·霍夫斯达特:《改革时代——美国的新崛起》,俞敏洪、包凡一译,第43-44、99页。。社会的发展要求农民顺应历史趋势向前走,对抗潮流是反理性的表现;拉什承认小生产者阶层必将衰落,但认为其社群主义的生活方式、自我改善的工作观和质朴的人格情感具有超越时代的价值,在社区解体、自恋主义盛行的现代社会,应该保有一席之地(36)Christopher Lasch,“A Reply to Jeffrey Isaac”,Salmagundi,1992,93,p.100;〔美〕克里斯多夫·拉斯奇:《自恋主义文化》,陈红雯、吕明译,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88年,第1-4章。。民粹传统的衰落是现代社会结构失衡、理性化走过头的征兆,右翼民粹主义复兴正是对此的纠正。
在更深的层次上,两者的差异体现了对体制运行现状的不同判断。霍夫施塔特对现行体制大体上是乐观和认可的:对资本主义经济,他抱有现实主义的接受态度,承认工业化、城市化、垄断的必要性,也肯定消费经济的价值(37)〔美〕理查德·霍夫斯达特:《改革时代——美国的新崛起》,俞敏洪、包凡一译,第143、255页。;对政治体制,他赞许罗斯福新政的“试验精神”和“在健全的工作秩序中对一种经济实行民主化”的改良做(38)〔美〕理查德·霍夫斯达特:《改革时代——美国的新崛起》,俞敏洪、包凡一译,第143、255页。;在社会层面,他主张开放多元,“使不同风格的智慧人生成为可能”(39)Richard Hofstadter,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p.432.。对于期待渐进改良、社会进步的霍夫施塔特来说,民粹主义那种诉诸旧的个人主义秩序和半虚构、半过时的道德理想的反体制运动只能制造问题,不能解决问题。拉什相对悲观,现实秩序在其笔下是一番退化景象:消费主义甚嚣尘上,家庭衰败,社区衰退,道德沦落,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巨型公司以及为之服务的官僚国家的兴起削弱了人们的自信与日常生活的能力”(40)〔美〕克里斯多夫·拉斯奇:《自恋主义文化》,陈红雯、吕明译,第247页。。他不纠结于右翼民粹主义真实的历史形态,只将其作为一套为现实问题量身定制的社会改良方案的代称。
(二)两种思想体系下的不同批判尺度
进一步看,二者对民粹主义的不同论断基于两种思想体系下不同的批判尺度:霍夫施塔特作为二战后美国史学界“共识论”学派中自由派的代表,以理性化为标尺进行社会批判;而拉什放弃了自由主义、激进左翼的方案而保留其目标,在社会保守主义的道德维度下进行后期的社会反思。
霍夫施塔特具有先天的理性气质。他早年曾加入美国共产党,但与同时代左翼青年不同的是,其动机是追求更好制度的“责任感”而非激情驱动(41)“Hofstadter to Harvey Swados”,January 20,April 30,1938.转引自:Eric Foner,Who Owns History?Rethinking the Past in a Changing World,New York:Hill and Wang,2002,p.27。。他的社会批判专注于美国社会进程的非理性表现,“为理解非理性政治塑造一个国家的力量提供了独特的视角”(42)David S.Brown,Richard Hofstadter: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6,pp.142,194.。对于极端保守派,他高度警惕,其作品中“关于美国政治文化的最具原创性的研究”主要来自对极右翼的“恐惧、愤怒或幻想(43)David S.Brown,Richard Hofstadter: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6,pp.142,194.;对于温和保守派,他反感其对体制的驯顺和对美国传统的溢美(44)Richard Hofstadter,The Progressive Historians:Turner,Beard,Parrington, New York:Knopf Doubleday Publishing Group,2012,pp.448-449.,这是促使他反思民粹传统的原因之一;对于自由主义,他身在其中但不受其束缚,持有一种圈内人的严格自省。在学术创作早期,霍夫施塔特“从内部冷酷无情地批评”自由主义(45)Benjamin Serby,“The Dialectical Liberalism of Richard Hofstadter”,Society,2018,55,p.143.,质疑罗斯福新政“缺乏方向感”(46)〔美〕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美国的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崔永禄、王忠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314页。。在二战结束时所写的一篇未刊论文中,他直指新政自由主义缺乏清晰的理论指导,来克制内在的集权倾向和应对国内外事务时可能出现的危险动向(47)Anne M.Kornhauser,“Richard Hofstadter’s Liberalism Problem”,Society,2018,55,p.147.。在政治倾向逐渐转向温和后,他的自我审视的严苛标准始终如一。对自由派受制于平等观念而未能深入推进社会反思不满,试图展示其应有的反思力度,是霍夫施塔特批判民粹主义的另一个原因。
拉什的学术生涯延伸到20世纪90年代初,他目睹了二战后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盛衰交替,问题意识发生了明显变化。他后期的思想有一个隐含前提:政治和经济领域的改革走到尽头了,新政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的辩论不过是有话语权者的意识形态之争,“来回拉锯”、了无新意(48)〔美〕克里斯托弗·拉希:《精英的反叛》,李丹莉、刘爽译,第70-71页。。右翼民粹主义是作为超越党派政治和意识形态两分法之外的“第三条道路”被提出的。对于自由主义,拉什与霍夫施塔特一样,是一位“尖锐的、有时甚至残忍的批评家”(49)Jon K.Lauck,“Christopher Lasch and Prairie Populism”,Great Plains Quarterly,2012,32(3),p.183.。他着重批判自由主义的三种倾向:一是用政府干预代替社会自治的控制论倾向。干预理念带来的不是解放的哲学,而是控制的蓝图(50)Christopher Lasch,The Agony of the American Left, p.10.,一个试图组织一切的政府什么都组织不了,只能使家庭和社区遭到破坏(51)〔美〕克里斯多夫·拉斯奇:《自恋主义文化》,陈红雯、吕明译,第243页。。二是对道德的淡漠。他批判凯恩斯主义对道德原则的悲观和放弃(52)Christopher Lasch,The True and Only Heaven:Progress and Its Critics,pp.72-77,38,507.,认为自由主义助长了消费主义的泛滥和中产阶级的自我沉溺(53)Jon K.Lauck,“Christopher Lasch and Prairie Populism”,Great Plains Quarterly,2012,32(3),p.188.。对于当今的社会衰败和道德危机,经济保守主义是始作俑者,自由主义是共谋。三是社会议程的偏斜。“自由主义者以一种上层阶级的腔调为受压迫者辩护。他们帮助黑人、妇女、同性恋者以及其他法律歧视的受害者的善意努力具有家长式作风(54)Christopher Lasch,The True and Only Heaven:Progress and Its Critics,pp.72-77,38,507.,导致自由派阵营分裂、新保守主义借势崛起。这三点批判正对应着右翼民粹主义的三个支点:社会自治、道德基础、反对身份政治。这种道德立场也构成拉什对左派和保守派的批判尺度:新左派背离了左派传统,玩世不恭、极端自我、奉行无政府主义,并且与自由主义一样热衷于通过不民主地掌握文化权力来推进片面的社会议程(55)Jeffrey Isaac,“Modernity and Progress:An Exchange (I.On Christopher Lasch)”,Salmagundi,Winter 1992,93,p.85.;经济保守主义者代表大资本利益,“挪用”右翼民粹主义的话语利用民(56)Christopher Lasch,The True and Only Heaven:Progress and Its Critics,pp.72-77,38,507.,要对经济不平等和消费主义泛滥负责;社会保守主义者“看到了问题但没能给出让人信服的解释和解决方案”(57)〔美〕克里斯托弗·拉希:《精英的反叛》,李丹莉、刘爽译,第133页。。在此,拉什的右翼民粹主义表现为一种在保守派的社会道德中扎根,竭力向自由派和左派的经济平等伸展枝叶的扭曲存在。
(三)两种发展观的不同指向
更具决定性影响的是发展观的差异。霍夫施塔特持有以多元主义为基础的进步史观,认为社会发展趋向多元化格局,多元冲突推动历史进步。他批判主流史学的一元论倾向。一是进步主义史学的社会冲突一元论和经济决定论。沃农·帕灵顿以贵族派与劳苦大众之间的深深裂痕和持续冲突(58)Richard Hofstadter,TheProgressiveHistorians:Turner,Beard,Parrington,pp.437,454,462,454,463.,作为社会矛盾的惟一历史解释,过于单薄;查尔斯·比尔德关于城市精英颠覆农业民主秩序的“准民粹主义声明”,忽略了整个事件的复杂性(59)David Brown,Richard Hofstadter: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pp.199-200,197,xiv.;弗里德里希·特纳将西部视为美国民主和美国特性原发地的边疆假说,包含着“对美国人种族血统的暗示”,尤其值得警(60)David Brown,Richard Hofstadter: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pp.199-200,197,xiv.。二是共识论史学的社会形态一元论。“作为一套洋洋自得的普遍化理论”,它没有看到或不承认冲突存(61)David Brown,Richard Hofstadter: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pp.199-200,197,xiv.,无视历史的多元性与复杂性。霍夫施塔特对两大主流史学派都忽略了渗透在美国生活中的种族、人种、宗教和道德冲突表示震(62)David Brown,Richard Hofstadter: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pp.199-200,197,xiv.,赞赏战后新史学在这方面的突破。面对多元冲突,他呼吁“礼让”与共存。“一种更微妙、更无形但至关重要的道德共识,我称之为礼让(comity)。礼让在一个社会中存在的程度是那些参与其竞争利益的人对彼此怀有最基本的尊重。(63)David Brown,Richard Hofstadter: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pp.199-200,197,xiv.政治理念上,自由派与保守派保持“相互批判”,避免“双方的人都为自己的知识地位过分自满”(64)〔美〕理查德·霍夫斯达特:《改革时代——美国的新崛起》,俞敏洪、包凡一译,第10页。;在学术领域维持健康的复杂性,进步史学与共识论史学达成和解,“受各自辩证法的约束(65)David Brown,Richard Hofstadter: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pp.199-200,197,xiv.。他本人后期的历史观就是对冲突论和共识论的融合与超越。
在多元进步史观下,霍夫施塔特对社会发展抱有乐观透达的态度,“渴望拥抱未来而不是纪念过去(66)David Brown,Richard Hofstadter: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pp.199-200,197,xiv.。他欢迎旧传统的湮灭,期待新体制的创生,反对“津津于后顾而不思前瞻”的消极心态(67)〔美〕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崔永禄、王忠和译,导言,第1页。,主张摒弃对民族怀旧的虔诚,直面前人留下的难题(68)Benjamin Serby,“The Dialectical Liberalism of Richard Hofstadter”,Society,2018,55,p.142.。在新左派运动的高潮中,他虽然不赞成激进学生的破坏性做法,但拒绝公开反对学生,甚至在1968年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园事件后自我反思,承认反对者对自己民粹主义研究的批评是正确的(69)Jon Wiener,“Why Richard Hofstadter Is Still Worth Reading but Not for the Reasons the Critics Have in Mind”,https://historynewsnetwork.org/article/30629/,2021年8月6日。。拥护多元、支持进步是霍夫施塔特用以衡量理性化程度的标准,民粹主义那种简单极端、静止怀旧的发展观,在其眼中自然是反理性的代表。
拉什表现出坚定的反多元主义和反进化论立场。反多元主义主要指向文化领域。在他看来,“20世纪60年代以来震动美国的文化斗争,更准确地说其实是某种形式的阶级斗争”(70)〔美〕克里斯托弗·拉希:《精英的反叛》,李丹莉、刘爽译,第12-13、11、177页。。而新左派及其“后学”文化左派却舍本逐末,其倡导的多元文化主义不但以文化民主的表象掩盖了而非解决了问题,而且“使怀有敌意的少数族群沉浸于一种无法用理性讨论的信仰中(71)〔美〕克里斯托弗·拉希:《精英的反叛》,李丹莉、刘爽译,第12-13、11、177页。。因此,右翼民粹主义必须着力推动文化“一元论”,凸显本土主流文化。
拉什也明确反对进化论。他“拒绝将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作为现代进步观念的基础”(72)Thomas Bender,“The Historian as Public Moralist:The Case of Christopher Lasch”,Modern Intellectual History,2012,9(3),p.741.,批判经典现代化理论的传统-现代两分法(73)Christopher Lasch, The True and Only Heaven:Progress and Its Critics,pp.167;82-84,114;373.,被称为20世纪晚期“美国的卢梭”(74)Ronald Beiner,Philosophy in a Time of Lost Spirit:Essays on Contemporary Theory,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97,p.139.。晚年的拉什总结出一个能够解释各种主义遭受挫败的总根源——对进步的执念。保守派的怀旧与自由派的乐观“是一体两面的共谋产物”(75)Casey Blake and Christopher Phelps,“History as Social Criticism:Conversations with Christopher Lasch”,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1994,80 (4),p.1332.,都建立在传统=落后、现代=进步的两分法和进化论思维之上,前者认为传统只存在于永远失去的过去,结果陷入了“勇气危机”,放弃努力,徒劳哀(76)〔美〕克里斯托弗·拉希:《精英的反叛》,李丹莉、刘爽译,第12-13、11、177页。;后者相信“生产力的扩张能够无限期地继续下去”,社会公正能够自动实现,最终因对发展的艰巨性缺乏心理准备而遭遇幻(77)Christopher Lasch, The True and Only Heaven:Progress and Its Critics,pp.167;82-84,114;373.,被称为20世纪晚期“美国的卢梭”(78)Ronald Beiner,Philosophy in a Time of Lost Spirit:Essays on Contemporary Theory,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97,p.139.,堕入信心危机,“变得愤世嫉俗、痛苦和怨恨(79)Christopher Lasch, The True and Only Heaven:Progress and Its Critics,pp.167;82-84,114;373.,被称为20世纪晚期“美国的卢梭”(80)Ronald Beiner,Philosophy in a Time of Lost Spirit:Essays on Contemporary Theory,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97,p.139.。更好的选择是“希望”,即相信进步的可能性而非必然性,争取改进但不强求结果,“坚持声称生活的美好但并不否认那种足以令人失望的迹象(81)Casey Blake and Christopher Phelps,“History as Social Criticism:Conversations with Christopher Lasch”,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1994,80 (4),p.1332.。
综上,两位学者对民粹主义的看法根植于对现代社会的认知,其立场迎面相撞:霍夫施塔特对理性化和社会进步抱有坚定信念,期待建立以理性个体为基础的宽容多元的社会,以自由派文化精英的忧患意识审视社会发展的干扰项,比如民粹主义;而拉什强调理性有局限、进步有边界,向往以有活力的社区和主流文化为支撑的道德生活,认为在进化论思维驱动下随意丢弃宝贵传统,比如民粹主义,才是现代社会最大的问题;前者是悲观的乐观主义者,忧心忡忡地发掘危险倾向,但支持现代性,对“人类的温暖感和技术上的潜力”抱有信心(82)〔美〕理查德·霍夫斯达特:《改革时代——美国的新崛起》,俞敏洪、包凡一译,第272页。,后者是乐观的悲观主义者,开明接纳人性的缺陷与社会的不完美,但思想底色是沉重的现代性忧思。
但与此同时,他们的思想又因各自的杂糅性而产生了一系列“交叉点”:霍夫施塔特承认保守派倡导的资本与市场,认可激进派对社会平等的追求,以具有保守色彩的精英主义姿态,追求自由派社会进步的目标;拉什认同保守派的有限理性、自由资本的前提,保留了激进派社会经济平等的目标,试图通过富于自由派非暴力色彩的平等公开对话,达到社会保守派的社会自治和道德规范。
三、思想底层的同构与互补
霍夫施塔特与拉什都专注于社会批判,前者长于讽刺,后者以严厉著称,但二者彼此间从未正面交锋。霍夫施塔特包容、鼓励拉什的挑战,而拉什论及霍夫施塔特时表述委婉克制,甚至称其“在很多方面一直是我思想领域的主导者”(83)Casey Blake and Christopher Phelps,“History as Social Criticism:Conversations with Christopher Lasch”,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1994,80 (4),pp.1317,1315.。这里有私交的成分(84)霍夫施塔特与拉什有师生之谊,拉什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期间,曾为同系任教的霍夫施塔特担任过半年科研助手,参与其主持的课题,此后一直保持学术联系。,也有学术渊源的缘由(85)两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了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的理论,并受美国社会学家C.赖特·米尔斯的深刻影响。,但恐怕与两人在民主、理性、道德、传统、进步等基本问题上的同构性和互补性关系更大。
(一)民粹与民主
霍夫施塔特经常受到的一个指责是他对民粹主义批判过甚,对民众过于苛刻。这主要是由于他经常将“过度阐释”当作引发读者关注的“创造性的策略”(86)David S.Brown,Richard Hofstadter: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p.144.,而其思想的另一面却被读者忽略。实际上,他也将理性批判的目光瞄准上层,尖锐地批判共和党极右翼资本家与政客的非理性(87)Richard Hofstadter,“The Paranoid Style in American Politics:An Essay”,in Sean Wilentz,ed.,Richard Hofstadter,pp.521-524.;而他在对民粹运动的严苛批判中,寄托着深切的同情:“批评是一种内省”,“旨在指出这一传统的局限,使它摆脱伤感以及自满的情绪——简言之,即是执行它的反对者所逃避的,只能由它的支持者担负的任务”(88)〔美〕理查德·霍夫斯达特:《改革时代——美国的新崛起》,俞敏洪、包凡一译,第9-11、274页。。这种对民众深沉而隐晦的情感、对民主化命运与道路的忧患,正是霍夫施塔特学术动力的来源。
拉什遭遇的严厉责难是:对民主没有给予严肃关注(89)Jeffrey Isaac,“Modernity and Progress:An Exchange (I.On Christopher Lasch)”,Salmagundi,Winter 1992,93,p.91.。其实,自称右翼民粹主义者的拉什,并没有盲目的大众崇拜情结。他很清楚民粹主义的局限,“我无意于将下层中产阶级文化的狭隘性与地方性最小化,我也不否认它产生了种族主义、本土主义、反智主义,以及自由主义批评家们频繁引证的所有其他邪恶。”(90)Christopher Lasch, The True and Only Heaven:Progress and Its Critics,pp.17,24.拉什是从另外的角度思考问题的。在他看来,当今民主制的关键威胁不是“外患”,而是“内忧”,即自身的运行方式,“海外极权主义或集体主义运动对民主的威胁少于来自民主内部的对自身心理、文化、精神基础的腐蚀”(91)Christopher Lasch, The True and Only Heaven:Progress and Its Critics,pp.17,24.。民主的问题要用民主的方式来解决,“民主应该是解决问题的一部分(92)Casey Blake and Christopher Phelps,“History as Social Criticism:Conversations with Christopher Lasch”,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1994,80 (4),pp.1317,1315.。右翼民粹主义“代表着质朴的行为方式和平凡、直截了当的说话方式”,是“民主的真实声音”(93)〔美〕克里斯托弗·拉希:《精英的反叛》,李丹莉、刘爽译,第78页。,也是目前能找到的维护民主良性运行的更好方法。
关于民主制,两人有两个基本共识:一是重视个体责任。霍夫施塔特强调民众要尊重智识,自我改进;拉什提出民众应遵守社会规范,重塑道德根基。两者从理性自律与道德自律的不同层面对民主制下的个体提出要求。二是承认体制内的个体行动与流动空间。两人都不否认现行体制存在层级性和流动阻碍,但又都认为体制内的个人具有突破结构障碍的能动性。霍夫施塔特对罗斯福新政“实验”的肯定、对民粹主义运动“地位革命”论的诊断,拉什的“希望论”发展观和对20世纪初激进知识分子“社会异乡人”的改革动机分析(94)指进步主义时代的转型社会没有给这些知识分子留出位置,使其自我感觉无处置身,思想发生激进变化。Christopher Lasch,The New Radicalism in America:The Intellectual as a Social Type (1889—1963),New York:Vintage Books,1967,p.101.,都说明二者对个体心理和个人行动的重视,人是能动的,体制可改良。
根本而言,在两人苛刻的批判背后,都是对民主体制的深刻认同。这种认同感在霍夫施塔特的作品中既有直接的感性流露:“经过了集中营、纽伦堡法令,格尔尼卡轰炸以及莫斯科审讯,美国的任何东西看起来都是清新的,充满希望的(95)〔美〕理查德·霍夫斯达特:《改革时代——美国的新崛起》,俞敏洪、包凡一译,第9-11、274页。;也有间接的理论表达,比如他对新左派知识分子拒绝与政权合作的明确反对。他认为,新左派为自身文化精英身份与其平等主义政治理念之间的矛盾而深感愧疚(96)Richard Hofstadter,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pp.416-418,393,407-409,419,429.,因而对体制采取了矫枉过正的决绝态度,“认为疏离是他们惟一可采用的、适合而高贵的立场”(97)Richard Hofstadter,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pp.416-418,393,407-409,419,429.。但这种“疏离崇拜(98)Richard Hofstadter,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pp.416-418,393,407-409,419,429.的本质是逃避主义,“最终只是在寻找一个‘位置’或一种姿势(99)Richard Hofstadter,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pp.416-418,393,407-409,419,429.,没有真正担负起知识分子的社会责(100)Richard Hofstadter,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pp.416-418,393,407-409,419,429.。拉什经历了大半生的思想巡回,最终将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在社会道德领域,这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放弃了经济、政治改造的和解。他曾自述:“如果我似乎花了很多时间攻击自由主义和左翼,那么这应该更多地被视为一种尊重,而不是排斥。”(101)Casey Blake and Christopher Phelps,“History as Social Criticism:Conversations with Christopher Lasch”,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1994,80 (4),pp.1311,1332,1326.在早年思想激进的时期,拉什就呼吁要改革不要颠覆(102)Christopher Lasch, The True and Only Heaven:Progress and Its Critics,p.28.,“即使在我们有缺陷的民主制度下,基本的自由依然存在。如果连这些都被摧毁,自由派和激进派将一起倒下”(103)Christopher Lasch,The Agony of the American Left, pp.203-204,65.。他与霍夫施塔特一样反对“疏离政治”,即反对以是否“愿意将自己的身体置于危险之中来衡量”行动的价,认为有缺陷的民主可堪改造、值得保留。
(二)理性与道德
霍夫施塔特倡导理性化,体制改良、群体行动都要与理性合拍,而拉什看似反理性,但理性的标准隐身在其思想前提中。他一直强调“理性人”和“更温和、更务实的政治观点的重要性”(104)Christopher Lasch,The Agony of the American Left, pp.203-204,65.,批判阶级统治的非理性(105)〔美〕克里斯多夫·拉斯奇:《自恋主义文化》,陈红雯、吕明译,第32页。。拉什将知识分子界定为既以思想为业又以之为乐,能够客观评论社会的人(106)Christopher Lasch,New Radicalism in America,Introduction,p.ix.,这与霍夫施塔特对智识的理解异曲同工。二者都抵制反智主义,对反智主义的缘起也存在共识。霍夫施塔特分析了反智主义的四个来源:宗教反智主义,指宗教的情感至上和反理性主义倾向;政治反智主义,即凭借道德优势采取政治行动的民粹主义;商业反智主义,指直接经验和技术实用主义对智识的蔑视;教育中的反智主义,比如以大众化、实用化标准取代专业标准和学术训练的进步主义教育(107)也有学者将霍夫施塔特的反智主义概括为三种类型:反理性主义、反精英主义和不思考的工具主义。Daniel Rigney,“Three Kinds of Anti-intellectualism:Rethinking Hofstadter”,Sociological Inquiry,1991,61(4),pp.434-447.。拉什也提出过三条反智路径:一是“思维的操控性习惯”,指激进派知识分子幻想依靠计划和管控解决社会文化问题的另类反智主义(108)参见Christopher Lasch,The New Radicalism in America,chap.9;Robert B.Westbrook,“Christopher Lasch,The New Radicalism,and the Vocation of Intellectuals”,Reviews in American History,1995,23(1),p.187。;二是多元文化主义的滥用,在教育领域表现为以直接经验和相对主义的多元文化代替经典文化和实实在在的知识普及(109)〔美〕克里斯托弗·拉希:《精英的反叛》,李丹莉、刘爽译,第132-137、11、59页。;三是意识形态的泛化,将“知识等同于意识形态(110)〔美〕克里斯托弗·拉希:《精英的反叛》,李丹莉、刘爽译,第132-137、11、59页。,导致固执己见,“丧失了自我批评的能力,而这种能力的衰退正是知识传统行将灭亡的最确凿的标志”(111)〔美〕克里斯托弗·拉希:《精英的反叛》,李丹莉、刘爽译,第132-137、11、59页。。可见,二者都认为技术实用主义、民主原则的泛化和自由主义教育有损于理性的发展。

综合来看,霍夫施塔特对道德的警觉并非反道德,而是试图“减缓”美国自由主义史上“最根本和最长久的错误”——间发的道德冲突(117)〔美〕理查德·霍夫斯达特:《改革时代——美国的新崛起》,俞敏洪、包凡一译,第8、11页。;拉什对理性的敌意也不同于反理性,只是对理性的扩张能力过度敏感,担心其越界。霍夫施塔特警惕作为理性凌虐者的道德,拉什批判作为道德替代品的理性,二者共同的潜台词是:理性与道德理应各司其职,互不侵犯。
(三)传统与现实
霍夫施塔特的反传统,反对的主要是将传统神圣化的自满心态,对于美国自由传统本身是肯定的。其早期作品《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虽然以讥诮的口吻表达了“大胆的激进主义”,却从反面证实了保守派共识论的主张:美国各政党和政治派别之间存在基本共性(118)Jon Wiener,“Why Richard Hofstadter Is Still Worth Reading but Not for the Reasons the Critics Have in Mind”,2021年8月5日,https://historynewsnetwork.org/article/30629/,2021月8月6日。,对财产权、经济个人主义和自由竞争有着共同的信仰(119)Benjamin Serby,“The Dialectical Liberalism of Richard Hofstadter”,Society,2018,55,p.142.,其基础就是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霍夫施塔特理想中的自由主义,是一个既有重心又能发展的体系(120)美国学术界对霍夫施塔特的自由主义观有不同看法,有学者认为他同时接纳古典自由主义和新政自由主义,但未理顺二者的矛盾关系,参见Benjamin Serby,“Dialectical Liberalism of Richard Hofstadter”,Society,2018,55,pp.142-145;有学者主张他只接受新政自由主义,参见Anne M.Kornhauser,“Richard Hofstadter’s Liberalism Problem”,Society,2018,55,pp.146-152。本文认为霍夫施塔特对两种自由主义持和解态度,且有明确定位:古典自由主义提供了制度根基,新政自由主义带来了突破变革。,因而他对传统抱有矛盾犹疑的态度:既担心过度尊崇传统会妨碍必要的体制调整,又担心变革走得太远,使“自由主义所有口号和技巧……转化为非自由主义的目的”(121)Benjamin Serby,“The Dialectical Liberalism of Richard Hofstadter”,Society,2018,55,p.143.。而拉什推崇传统,是基于现实的考量,试图在自由派和保守派之外另起炉灶,信仰、情感和道德的力量填补两派共同造成的“情感和精神的匮乏”(122)Christopher Lasch,The True and Only Heaven:Progress and Its Critics, pp.371,532.。他的“传统”经过严格筛选,意在“从过去的民众激进主义,以及更普遍的道德家们对进步、启蒙和无限雄心的广泛批判中找到很多的道德灵感(123)Christopher Lasch,The True and Only Heaven:Progress and Its Critics, pp.371,532.。
两者的思想倾向与两种在美国由来已久、相互制约的政治传统——对多数人暴政的警觉和朴素自信的大众情结——遥相呼应。这两种传统最初表现在联邦党人和杰斐逊的对立中,历经百余年的民主化和工业化,滤掉了过时的阶级偏见和反工业化成分,在霍夫施塔特与拉什关于民粹主义的对峙中转化为一对新的制衡关系:对普选制度下民主质量和个体理性的关注与对全球化、后工业化时代民主动力和道德基础的担忧。二者尽管指向不同,但肯定底层传统、解决现实问题的出发点是一致的。
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是两人最明显的共性。社会批判纵贯霍夫施塔特的整个学术生涯,从开国元勋到普通民众,无一不纳入批判视野;拉什惯于逆潮流而动:生长于中西部进步传统和新政时代,却终生批评进步主义和自由主义,极右思潮泛滥之际左转,新左派运动勃兴时右倾,新保守主义得势后拒绝保守主义。社会批判成就了两人的洞察力、预见性和超越时代的影响力。如果说霍夫施塔特的现实意义在于“将对美国政治阴暗面的焦虑与对传统智慧的怀疑态度结合在一起”(124)Jon Wiener,“Why Richard Hofstadter Is Still Worth Reading but Not for the Reasons the Critics Have in Mind”,2021年8月5日,https://historynewsnetwork.org/article/30629/,2021年8月6日。,那么拉什则将对美国社会现实的焦虑与“对传统智慧的转化再利用”合二为一。
(四)启蒙、进步与多元主义
社会启蒙是霍夫施塔特与拉什共同的主张。两人都相信思想的力量,认为知识分子应该贡献思想,而不是直接卷入政治(125)Thomas Bender,“The Historian as Public Moralist:The Case of Christopher Lasch”,Modern IntellectualHistory,2012,9(3),pp.734-735.。但霍夫施塔特希望知识分子发挥“引领”和“立异”功能,强调社会对知识分子的尊重(126)Richard Hofstadter,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pp.430,404.;而拉什强调知识分子要主动与社会连接,“以一种有人会听到的方式来写作”(127)Casey Blake and Christopher Phelps,“History as Social Criticism:Conversations with Christopher Lasch”,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1994,80 (4),pp.1320-1325.。彻底的制度变革需要知识阶层的社会启蒙与大众社会运动的深度结合(128)Christopher Lasch,The Agony of the American Left, pp.58-59,40-43.。
对于启蒙的共同信念揭示了二者发展观的共同点。霍夫施塔特对历史多样性、复杂性的重视使其进化论保持了温和色调。他对社会进化持谨慎态度,对进步的风险代价理解颇深,不认可特纳那种“着迷于将文明的发展划分为一系列不同的进化阶段,……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以一种清晰的模式出现和重复”的线性进化论(129)Richard Hofstadter,The Progressive Historians:Turner,Beard,Parrington,p.51.,认为“在处理人、社会习俗和政治道德事务方面,这种永恒和绝对追求的弊端很快就暴露无遗”(130)〔美〕理查德·霍夫斯达特:《改革时代——美国的新崛起》,俞敏洪、包凡一译,第12页。,这与拉什的思路高度一致。而拉什反对的实际上也是线性进化论。他否认对自己“不加选择地拒绝进步本身的可能及现实”的指责(131)Jeffrey Isaac,“Modernity and Progress:An Exchange (I.On Christopher Lasch)”,Salmagundi,Winter 1992,93,p.86.,明确承认社会进步的可能性,比如美国的社会平等化议程已取得重大进展,多数美国人已不是种族主义者,这与温和自由主义的代表阿兰·沃尔夫的看法一致(132)Alan Wolfe,One Nation,After All,New York:Viking,1998,p.16.。他的希望论发展观也留有进步主义的印记。
在社会观念日趋自由化的背景下,拉什对文化多元主义的非议显得格外“右倾”,但客观来讲,他反对的不是多元主义本身,而是其过激倾向。拉什主要针对新左派的文化多元主义,认为过分抬高边缘群体亚文化恰恰剥夺了文化多元性和选择权,抵制特殊的多元化,才能恢复真正的多元化。这与霍夫施塔特反对将反智行为当作民主化动力、“错把从周围看到的更苍白、更无效的智识表现当成智识本身(133)Richard Hofstadter,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pp.430,404.的说法不谋而合。拉什曾严厉批评美国社会运动的“宗派主义和边缘性”,呼吁民众运动保持包容性和普世性(134)Christopher Lasch,The Agony of the American Left, pp.58-59,40-43.,还支持温和民权运动,称赞马丁·路德·金为“自由主义最后的英雄”(135)Christopher Lasch, The True and Only Heaven:Progress and Its Critics,p.392.。拉什获得的学术评价高度分化:理查德·罗蒂始终将其归为极左派的代表(136)〔美〕理查德·罗蒂:《筑就我们的国家:20世纪美国左派思想》,黄宗英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43-44页。,斯蒂芬·霍尔姆斯视之为反自由主义的保守派(137)参见〔美〕斯蒂芬·霍尔姆斯:《反自由主义剖析》,曦中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五章。;左翼评论家警告读者提防其“法西斯吸引力”,右翼批判其“顽固不化的社会民主主义者”的“生态焦虑”和对资本主义的攻击(138)Christopher Lasch,“A Reply to Jeffrey Isaac”,Salmagundi,Winter 1992,93,pp.98-99.,这说明其思想本身就具有复杂性和多元性。
(五)互诘与互补
两位学者的思想各有洞见和悖谬,对于彼此理论和逻辑层面的盲区,客观上能够相互质疑并互补。
理性化和文化精英主义导致的理解局限是霍夫施塔特民粹主义研究的一大缺陷。他对反智主义的界定最初力求严谨,将独立思考和批判性作为智识形成的前提,指出智识不同于知识,知识分子并非必然拥有智识。但论述展开后,这一区分逐步淡化,对知识分子的敌意基本等同于反智主义。这为他的论证带来了逻辑困难。比如,他一面批判进步派具有道德本位的民粹倾向,一面指责其对手反改革派顽固反智(139)Richard Hofstadter,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pp.186-188.。那么在这两股主导当时历史的对抗性力量中,谁是智识的代表?他认同垄断资本的崛起是历史趋势,但推动这一趋势的恰恰是“反智”的商人们。如果智识缺位无碍于社会发展,这是否意味着智识并没有多么重要?这显然不是霍夫施塔特想要的结论。问题的关键是:智识的标准是什么?主体是谁?霍夫施塔特的答案是:智识来自对理性的尊重,尤其表现为对知识分子的尊重。
拉什的切身经历直击了这一理论的盲区:这位自封的右翼民粹主义者、受霍夫施塔特赏识的知识分子,是智识的还是反智的?此外,如果“美国确实存在一个可辨识的民粹主义知识分子传统”(140)Daniel Rigney,“Three Kinds of Anti-intellectualism:Rethinking Hofstadter”,Sociological Inquiry,1991,61(4),p.442.,这一类知识分子是智识的还是反智的?进而,智识是否可能存在于知识分子甚至严格意义上的智识分子的对立面中?拉什提供了另外的思路:反智主义只为理解美国知识分子与社会的紧张关系提供了一半解释,另一半解释在于知识分子的自我感觉:他们对于自身作为一个团体所遭受的攻击过分敏感了(141)Christopher Lasch,New Radicalism in America,Induction,pp.x;x,xi.,而这又是社区传统衰落、社会共同感式微、各种自治文化彼此割裂的产(142)Christopher Lasch,New Radicalism in America,Induction,pp.x;x,xi.。拉什的这一看法拥有来自左右两派的支持:左翼激进派社会学家C.赖特·米尔斯提到过环境的控制性对知识分子智识基础的威胁(143)〔美〕C.赖特·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杨小东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75页。,保守派学者托马斯·索维尔认为知识分子的某些思维特征使其可能开出完全错误的社会治理药方(144)参见〔美〕托马斯·索维尔:《知识分子与社会》,张亚月、梁兴国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第四章。。拉什还提出,智识具有非理性的来源。对基层生活经验、民众思想状态与精神情感的把握和共情,开放舆论环境中各方观点的公开争鸣,都可以促成智识,民粹主义本身也可以成为一种平衡社会发展的智识。
拉什的困境,首先来自过度批判带来的解构性。他终其一生与各种流行思潮作战(145)Christopher Lasch,The Agony of the American Left,p.138;Christopher Lasch,The World of Nations,New York:Random House,Inc.,1973,p.194;Christopher Lasch,Haven in a Heartless World:The Family Besieged,New York:Basic Books,Inc.,1977,p.4.,一系列批判之后,失去了自身的立论基础。右翼民粹主义只承诺了一个面向下层、重塑传统的大原则,但具体包括哪些内容、如何落实则付之阙如,可能的路径已被他自己提前否定了。其次是道德阐释的模糊性和理想化。拉什大致提出过两个建设性思路:一是开放对话机制,但这更像是为他认为处于弱势的本土主流文化寻找一个自信发声的理由。根据霍夫施塔特对民粹主义的研究,当大众处于非理性状态时,公开对话如何确保消除偏见、达成共识?他提供不了答案。二是以19世纪本土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为参照,重建社会体系。而霍夫施塔特提示,大众并非天然正确,道德也不止一种形态。应该采用哪种道德?又如何证明其合理性?此外,霍夫施塔特的分析还凸显了拉什所看重的道德载体的非道德性:19世纪农场主集团本身也有市场投机性,民粹主义中包含强烈个人主义倾向(146)Jon K.Lauck,“Christopher Lasch and Prairie Populism”,Great Plains Quarterly,2012,32(3),p.195.。
总体来看,两者的思想存在同构性,相互挑战又彼此补充,实际距离并没有表面那样大:霍夫施塔特相信理性、立足现实,但也尊重道德、认可传统,反对民粹是为了维护民主,支持现代性;拉什则立足道德、呼唤传统,但也承认理性,启用民粹同样为了维护民主,反理性限定在抵制理性万能论、平衡现代性上,而其本身也是一种原生态的现代性。
结 语
霍夫施塔特与拉什都是典型的“智识型”学者,在强烈的现实关怀和同样强烈的理想主义的驱动下,为社会和时代发展提供了各自的富有预见性的独特理解:前者看到现代化进程中非理性力量膨胀的威胁,近年来民粹主义在全球的崛起,尤其是特朗普的上台,再度掀起霍夫施塔特热;后者预见到现代社会中理性崇拜的危机,“文化战争”硝烟再起,使拉什的反思重新进入公众视野。
不同流派往往会有意或无意地极化对方观点、放大彼此分歧,以凸显自身的合理性与独特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双方必然存在真正的对立。霍夫施塔特与拉什正是这种情况。二者对民粹主义的看法大致呈现如下规律:在具体史实和现象层面,观点对立和视角差异明显;在体制批判和发展观层面,观念相左,但有交叉,分歧主要来自问题意识和对发展策略的不同侧重;在最底层的体制和价值认同层面,表现出很强的内在同构性。从表层、中层到底层,两种思想的距离逐渐缩小,有张力而能互补,共同支撑起一个富有现实批判性和理论创造力的“智识”空间。
霍夫施塔特的民粹主义批判代表了严谨审慎的主流改良传统,而拉什的右翼民粹主义体现了美国版本的“执拗低音”——一种长期沉积、绵延在本土社会土壤中的自我维护的朴素本能。二者视角各异、路径有别,但都对体制的运行现状和潜在问题进行严正审视,对制度根基和价值基础予以深度认可、精心呵护,其基本出发点都是对人的关注:作为个体的现代人应该怎样生活、作为整体的市民社会和民主政治应该如何组织运行。霍夫施塔特曾指出:“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的文学中充斥着虚无主义,其他社会学科被推向狭隘的实证主义探究,历史可能仍然是艺术中最具人性的。”(147)Richard Hofstadter,The Progressive Historians:Turner,Beard,Parrington,p.466.霍夫施塔特的精英化、理性化主张与拉什的平民化、道德化呼吁,在针锋相对的外观背后,都指向这种终极人文关怀。这正是两者智识的共同来源。学术界对于类似的言辞之争,或许也应报以开放的态度,关注其背后同源异流、各具智识的制度反思与人文忧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