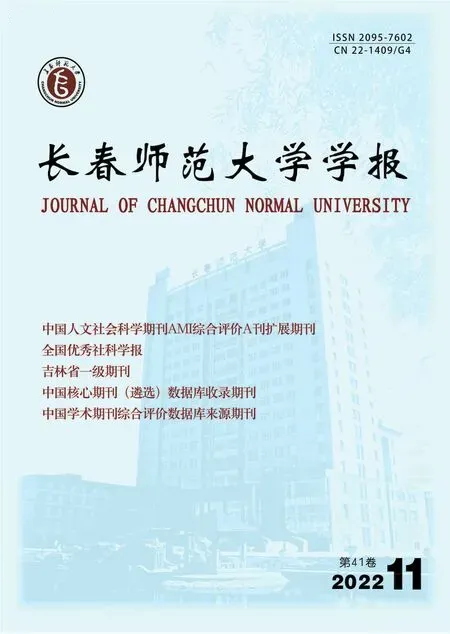原型理论与道家思想关联性探析
侯 帅
(东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荣格在其自传《回忆·梦·思考》中记载,少年时期的他常坐在一块石头上,思考自己究竟是坐在上面的“我”,还是被坐在下面的石头。这个困扰荣格整个童年的“石头难题”恰与中国“庄周梦蝶”的故事有异曲同工之妙。荣格认为这是他与东方道家的精神牵绊,“逍遥”自在,“齐物”物化。东方道家的思想一直贯穿于荣格的人生中,这种东西方超时空的精神交流与思想同归给予了荣格思想的贯通性,使得荣格成为中国道家忠诚的思想信徒与追随者。
梳理荣格的理论思想与著作,不难发现古老的东方文化是他的重要理论温床,他的理论思想中内嵌有深深的东方文化烙印。特别是荣格的“原型”概念,其理论范畴与道家思想有深刻的内蕴层面的关联。本文将通过对比分析荣格的原型理论与道家思想,力求探寻二者之间的深层次关联,更深层次地理解荣格及其原型说。对二者联系的探讨,或亦可为中国传统思想提供一个新的解读视角与相位。
一、原型与“道”的不谋而合
西方“原型”概念的出现距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它早在圣·奥古斯丁时代就已为人所用,与柏拉图的“理念”同义。但是作为一个重要的心理学概念,直到20世纪荣格建立起分析心理学,提出“集体无意识”及原型理论后,“原型”一词才重新进入大众视野。1936年10月19日,荣格在伦敦圣巴赛缪医学院作《集体无意识的概念》报告,阐释了其对原型的定义:“不同于个人无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情结(complexes)构成,集体无意识的内容基本上是由原型构成。”[1]36换句话说,原型便是集体无意识的内容。荣格对此进一步解释道:
原型概念是集体无意识概念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关联物,它表示似乎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种种确定形式在精神中的存在。神话研究称它们为“主题”;在原始派心理学中,它们相当于列维—布留尔的“集体表象”概念,在比较宗教学领域,它们被于贝尔(Hubert)和莫斯(Mauss)定义为“想象的范畴”。很久以前,阿道夫·巴斯蒂安(Adolf Bastian)称它们为“初级思想”或者“原始思想”。这些参照物非常清楚地表明,我的原型概念——实际上是一种业已存在的形式——并非是孤立的,而是在其他知识领域中得到了承认与命名的东西。[1]5
荣格不满以往柏拉图的理念图示,也不同于圣·奥古斯丁的神学角度和康德的“先验图式”,他对以往的“原型”概念进行了批判与匡正。荣格指出:“如果谁继续像柏拉图那样认为,他就必然会为自己的时代错误付出代价,目睹理念的‘超神圣的’——形而上学的——本质被放逐到无法证实的信仰与迷信范畴,或者被仁慈地交给诗人。”[1]64“原型”概念在荣格这里一改过度理性的趋向,力图恢复原有的感性内容。在荣格看来,现代西方人的精神世界已经出现危机,现代科学与理性的快速发展虽然带来了物质层面的极大改善,但是工具理性的扩张却成为人类思想的枷锁。人类在不断追求物质与动物本能满足的同时,精神世界却开始变得空虚。所以找寻现代人心理危机的根源成为荣格思考的出发点,他判断,目前状况的端由实为现代人在理性的蔓延中丢失人类的根基,内心深处缺乏对灵魂的憧憬与渴望。荣格认为,尼采等人所张扬的酒神精神并不能解决当下的人类问题,人类需要探寻共同精神家园中的原始灵魂——原型来自救。荣格借助“原型”手段,是为了探寻人类生命精神本源,找出一条返回现代人感性深处的道路。
在荣格看来,原型是人类精神世界里预设的先天无意识的基因,它是人类作为智慧种族发展史的缩影,是人类思维与感性相结合而成的一种稳定结构。荣格说,每一个原始意向里都内含着人类精神与命运的碎片,残存着人类祖先在历史中反复出现的典型情绪,并始终遵循这条道路前进。“它就像心理的一道道深深开凿过的河床,生命之流在这条河床中突然奔涌成大江”[2]121。荣格将原型比作河床,强调原型的生成与孵化功用,也突出了原型自身的层层积淀过程。这条“河床”不仅承载着人类心灵的过去,更代表着作为整体的种族未来。
有别于西方,中国特殊的历史实践与思维方式并未促成“原型”概念的产生,但是中国的文化哲学中有极为相似的概念与命题。荣格曾高度评价中国文化,认为古老的东方文明早已经给当下的西方世界开出了“药方”,“原型”“集体无意识”等概念亦能在中国文化思想中找到认同与共鸣。在他看来,中国哲学思想中存在宏大且奥妙的心灵感悟与思维模式,而这其中又以道家思想为卓著。道家学说中蕴藏着西方所忽略的精神价值——“天人合一”“自然无为”等思想无疑是治愈现代人深层痛苦的良药。道家思想的核心概念——“道”,在某些特质上与原型理论有内在的联系与概念的共鸣。“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家将“道”视为最高境界,力图走向善美合一的“天人合一”境域。可以说,“道”不仅仅是哲学范畴的概念,同时也包含物质运动的规律,兼有宇宙观和世界观,融汇着人类心灵的感性、思维与直觉等。道家的环形宇宙观之中,精神和物质统一生成“气”,而气可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3]144,这正是中国人思考的原始模式,故荣格称其为中国的思想原型。老子说:“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道德经·第十八章》)。这句话表明了万物虽都处于运动变化之中,但是皆有其“根”,这个“根”就是“道”。“道”实为万物所生所长之源,具有“原型”的意义。荣格明确指出了“原型”与“道”之间的相关性,即二者同为宇宙万物的原初状态,皆具整体性,呈现对立与统一的和谐。
可以看出,不论是荣格的原型论还是道家思想,它们相同的研究对象都是作为整体的人,都是作为共同体人类的深层精神世界。它们的共同追求是探寻人类一致的心理积淀与感性基础,从而摆脱时空、民族等差异的束缚,完成对人类精神世界共同原则与定式的书写。
二、原型与“天人合一”的殊途同归
荣格指出,原型就是集体无意识的内容,故谈及原型就不得不涉及集体无意识。与弗洛伊德不同,荣格认为无意识可以分为个人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其中个人无意识位于表层,集体无意识则居于心灵深处。荣格认为除了完全个人性的即刻意识,人类存在着第二套精神系统,“这一系统具有在所有人身上完全相同的集体性、普世性、非个人性本质。这种集体无意识并非单独发展而来,而是遗传而得的。它由事先存在的形式、原型组成”[1]37。如果说个人无意识带有很大成分的独立色彩及个性,那么集体无意识则是与生俱来的,在所有个体身上都显现着大体相似的内容与行为模式,是超越个人的共同心理基础。荣格同时指出,集体无意识具有全然客观的性质,既如宇宙般绵延,又面向世界开放。“在那里,我是每一个主体的客体,截然不同于我的平常意识,因为在平常意识中,我总是客体的主体。在那里我与世界完全合一,如此深刻地成为世界的一部分。以致我轻而易举地忘记了我是谁”[1]20。可以看出,与传统西方文化中强调个体价值而推崇“天人相分”不同,荣格强调主体与客体的互换与交融,突出了个人与世界合一的状态。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不谋而合,两者都倾向于将原本生活经验和科学中内外世界的绝对划分相对化。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哲学本身就是一种“泛哲学”,即认为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是直觉感应式的,当哲学内容经过时间检验被论证为合理并传世之后,便成为“一种具有普世意义的含盖一切人的准教义”[4]9-19。
老子是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以他为代表的道家一直骋目于人生议题,在关注个体的同时又飞跃于人道之上,以天道寓人道,以宇宙的高度审视人生,意图在尘世间为久居泥土之上的人类找寻精神上的出路。荣格深受道家思想启发,宣告与过去注重物质实体的科学主义心理学决裂,从而将目光转回原始人类社会与神话,从生命之初、理性之始探寻人类曾拥有的精神家园。从荣格对原型的描述来看,原型的生成与中国的“天人合一”思维模式特点有同频共振之处。对于“天人合一”的思想,儒道两家皆有所释,但儒家侧重个体与社会的关系,讲究“以人合天”;道家则关注个体与自然之和,主张人事效法“天”。可见在侧重点上,荣格的原型与集体无意识说同道家的“天人合一”有深刻的契合点与共鸣之处。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二十五章》),庄子也提出“以人合天”的思想。一般而言,人们谈及“自然”的时候往往是客观的,是有别于“人”的。但道家认为,人与自然并不能分为什么主体客体,因为人既是自然的一部分,也在自然中存在。“道法自然”,从本质上来看就是“人法自然”。人在自然中的存在同世间万物一样,是与生俱来、无法改变的。天与人皆源于“道”,故二者归为统一。可见,道家对整体人类的生存范畴有极其深刻的认知,是对该场域中各要素之间整体关系的深刻把握,而这种认知的内容就是对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探讨。随着“典型环境”的时间强化,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其内容便是荣格口中的“原型”内涵。
众所周知,神话是人类童年时期萌动意识的表达,是人类的第一批精神产品。同时,神话也是原型的重要载体与表现形式,原型从本质上看其实就是对宇宙秩序从感性认知到理论抽象表达的复现,所以原型始终在伴有感性因素的基础上对宇宙秩序规律进行把握。“天人合一”的观念同样映射着人对天的感应,这里面就包含着人对万物之序的通晓与感悟。特别是荣格心理学中的核心概念——“自性”,更加彰显这两者的相通之处。
自性象征着人格的组织原则,自性的周围亦环列着其它原型以及这些原型在情结中的显现。自性处于集体无意识中的核心地位,是整个人格的内核,与其他原型一起呈现出和谐有序的整体性。同时,荣格区分了“自我”与“自性”的概念,他认为“自性”包含意识和无意识,而“自我”是意识的中心,所以“自性”包含“自我”。荣格认为“自我”应当顺应“自性”的发展,如果“自我”肆意成长,就会导致个体的失衡而产生精神错乱。为避免这种现象,人必须以“个体化”(individuation)方式完成“自性”的实现。“个体化”就是使人真正做回自己,实现人格完整与均衡的发展。这种自觉的“个体化”人格整合的过程,贯穿于整个人类发展史,可以说荣格的“自性”实现和中国“天人合一”的精神是并行不悖的。若一个人通过“个体化”实现自性或者达到“天人合一”境界,他便可达到“圆满之境”,被称为“圆满”之人,可实现完全内部现实与外部环境之间的融洽与和谐。荣格对这种自性圆满之境推崇备至,他认为这种境界如同“道可道,非常道”的“道”,因为完美而不可言状,而实现这种境界的人便是真正意义的“现代人”,他们“面对着未来的深渊,头上是浩瀚的苍穹,脚下是整个人类及其一直淌隐到原始迷雾中去的全部历史”[5]220。而老子所认为的“得道者”正是对荣格眼中的“现代人”的刻画:
“绝学无忧。唯之与阿,相去几何?美之与恶,相去若何?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傫傫兮,若无所归。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澹兮其若海,飂兮若无止。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且鄙。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6]150
老子认为自己在众人兴高采烈之时能独自淡泊宁静,如同不会嬉笑的婴儿,亦如无家可归的浪子;众人盈余、光辉之时,自己却常有不足、愚昧混沌;特别是自己与众人不同,“而贵食母”——以守道为贵。这种婴儿般的质朴归真,心静神定、独异于人的品格,不仅是说的老子自己,更是其他“得道者”的真实写照,展现出得道者内外同修、与天合一的本质力量。老子通过对婴儿、自然的一系列描述,向众人展示了“得道者”的愚人形象和得道境界。这种境界便是返朴还淳、九转丹成的境界,是以退为进、以减为增的境界。这个境界包含着无尽的浪漫与神妙,负有东方思想境界的特殊美韵,因此成为中国文学中神仙境界的原型。荣格意识到能达到这种境界之人寥若晨星,只有实现无意识的“自性”与意识的“自我”的相辅而行才有可能达到这个境界。正是基于如此判断,荣格开启了探寻现代人“重返精神家园”之路。
诚然,老子不可能从人与原型的角度解答“天人合一”之人的特征,但是我们可以判断出当他在论述人与天、人与道的关联时,其实就如同在阐释人与原型的关联,就是与原始人心灵之中的原型在对话。
三、阿尼玛、阿尼姆斯原型与“阴阳和合”的同心合流
“阿尼玛”和“阿尼姆斯”是荣格理论中重要的原型概念。阿尼玛指的是男性无意识中的女性部分,阿尼姆斯则是女性无意识中的男性部分。阿尼玛和阿尼姆斯都属于心灵结构中深藏的异性人格部分,在特殊的环境下会以多重象征化形式激活显露出来,内含着强大的独立能量,可以给予人重大的积极影响。
荣格认为,人的心灵及情感深处暗藏难以察觉的双性倾向。伴随着漫长历史的变迁,男性不断与女性接触、交融,从而形成了原型阿尼玛;与之对应,女性生成了原型阿尼姆斯。“通过千百年来的共同生活和相互交往,男人和女人都获得了异性的特征”[7]53。荣格认为,不论生理性别如何,心理上都会拥有男女共性的特点,这种心理上的性别互存共处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呈现。
荣格划分出阿尼玛与阿尼姆斯两大原型,初衷是建构人格的完整,而人格完整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两性互融的人格。物种特性将人类划分成生理男女这两大群体,两者彼此差异又联系紧密,以此为基础的人格特质同样有殊之处而又形影相依。为了达到人格的调和稳定,就必须给予人格中异性部分展现的可能与表露的自由。假设一个男性强行压制女性气质的外显,完全按照社会的规定展现其男性气质,则他的阿尼玛始终会是原始未开化的状态,造成他无意识中含有柔弱的性质。所以一些被传统视角划分为“硬汉”的男子,其内心深处亦会十分柔软。与之对应,女性如果压制自己的阿尼姆斯的展现,其无意识深处也有通常男性所展现出的气质。传统的社会观念过于重视生理性别与心理气质的一致性,所以阿尼玛与阿尼姆斯经常处于受压抑的状态。
如何汲取两性人格之优势以整合自己的人格结构,这是荣格聚焦的问题之一。前文已述,荣格将人格划分为“自我”与“自性”,虽然“自我”处在意识的中心位置,但其经常受到现实外部世界的控制,所以只得趋奉现实原则,“自我”因此便压抑住了部分人格特征。但是“自性”的存在作为一种先天的集体无意识,促使个体与其异性一面进行交汇,同时驱动消释两性之间的畛域,以此到达“双性统一合融”的新境界。荣格对阿玛尼和阿尼姆斯概念的阐释以及对人格深处两性问题的探讨,展现了其本人的性别互补与和谐观念,而这与道家的“阴阳和合”观有相通之处。
需要指出的是,“阴阳并重”或“阴阳和合”并不单指狭隘的男女范畴,它更是一种阴阳对立的宇宙生成论。道家认为万物皆是阴阳的对立与统一,这突出表现了中国传统哲学思维中的同一与平衡性。在道家思想中,“阴”“阳”被视为基本的哲学范畴。如《庄子·天下》:“《易》以道阴阳。”《太平经》:“无奇辞,一阴一阳,为其用也”。因此,荣格将道家的阴阳互补、相生互动思想视为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与思想特质。
虽然道家以阴阳出发涉及的更多是宏观层面的问题,但在宏观之中也渗透出对两性观念的思考。在两性关系与地位问题上,道家比儒家更为开明,更加符合现代人的“男女平等”价值观念。于道家思想基础而言,“道”是宇宙之根本母体,那么包括男女在内的世间万物皆由其产生且衍化而来。以此为据,男女之间并无本质区别。老子也经常使用“母”“雌”“牝”来形容“道”,比如前文提到的“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中的“母”就被认为代指“道”。
如果说儒家从家庭与社会关系层面考虑两性关系,道家便是将两性关系纳入自然宇宙的秩序中进行关切。道家认为整个人类世界处于原始未完成的状态,单独的阴或单独的阳皆非完整的存在,只有经过阴阳融合,才可以形成完整的世界。正所谓“男女各出半力,同志和合,乃成一家”[8]182。单纯的男性或女性都是非圆满的,只有与异性进行互补才可以实现完整的人格。《太平经》亦云:“故有阳无阴,不能独生,治亦绝灭;有阴无阳,亦不能独生,治亦绝灭……故男不能独生,女不能独养”。道家的“阴阳和合”可以指男女两性和谐共生,构成有机统一体。这种“和合”思想是在肯定男女之间存在差异和矛盾的前提下,追求两性之间的动态平衡及协调统一。
荣格与道家对两性的关注目的都是寻找建构生命完整的方式。不论是荣格对“阿尼玛”原型与“阿尼姆斯”原型的讨论,还是道家对“阴”与“阳”关系的描述,二者并非单纯的对性别视角的认知,而是通过性别观谋求一个更为强大完满的超性别力量。这种力量的本质源泉就是阴阳共存同在,是对两性能量的整合与升华,是单极的阴或单极的阳远远不可能超越的。根据文化人类学的相关研究,荣格思想之所以与东方道家在该领域产生共鸣,其根本原因就是二者思想皆源于原始人类群体祈求从两性交融调和中构建完整强大的心理结构和精神力量。这种观念具有跨越东西界限的能力,是整个人类寻觅“终极力量”的集体无意识。这种集体无意识伴随着时代的演进而不断复现,具有跨文化的广泛性和共同性。
四、结语
荣格作为西方最重要的心理学家之一,对东方思想进行了大量的吸纳与比较研究,特别是中国古老的道家思想对荣格的一生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而这种跨越种族地域、贯穿东西的思想共振实现了某种程度上的互补,从而为全体人类回归共同的精神家园做出了本质上的贡献。“原型”“道”“天人合一”等概念的紧密关系不仅体现了东方文化对西方现代思想家的深刻影响,还体现出东西思想家在面对全人类共同议题上的探索与争鸣。对荣格而言,中国思想是一面不可或缺的镜子,它可以映照显现出西方高度理性表面下的深层感性缺憾,而荣格正是在东方思想的照耀下才构架出“西方文化为体,东方思想为用”的跨文化思想理论。毋庸置疑,荣格对中国文化精神的深度汲取与思想贯通,引发了后世对荣格思想的极大热情与持续关注。这也为中国学者带来一个重要的思考维度: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时代背景中,如何将中国的传统文化与当下的实践相结合,实现东方古老智慧的焕新?如何突破地域文明的隔阂,实现人类命运整体性的伟大构建?面对这些问题,或许我们可以从荣格对东方思想的接受逻辑和创造性转化中得到启发,那就是立足于中国思想文化根基,在人类整体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认知下,从更广泛的世界思想层面进行创造性融合与吸收,以开放包容的心态进行符合时代氛围的学术实践。
——从体、相、用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