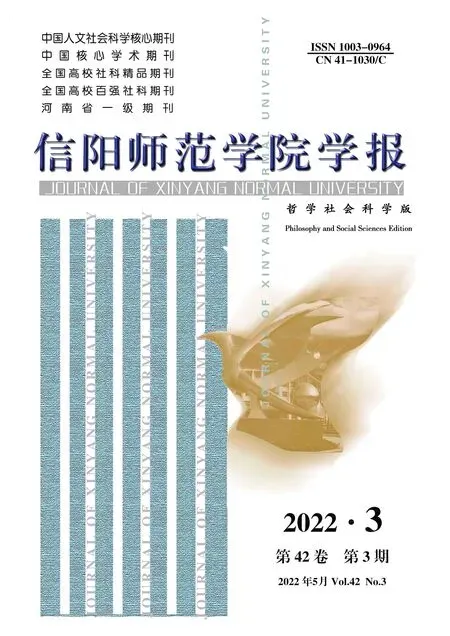平原叙事的坚守与延伸
——李佩甫文学访谈
吴圣刚,韩冰莹
(信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
李佩甫是坚守本土并获得茅盾文学奖的河南作家。作为“中原作家群”的重要代表人物,李佩甫把自己的生命体验用文字的形式种植在平原上,执着探索着特定地域的生命状态和生命意义,坚守着对中原文化和乡土精神的探寻。几十年来,他笔耕不辍,先后创作出“平原三部曲”和《平原客》《河洛图》《红蚂蚱 绿蚂蚱》《学习微信》《无边无际的早晨》等一系列优秀中长篇小说,从具象的平原到心中的平原,他用手中的笔建构着“文学中原”这一壮阔景观。
2021年4月28日下午,根据约定,我们在郑州与李佩甫会面,就李佩甫小说的开头构思,以及文学创作相关问题进行了3个小时的深度访谈。李佩甫对40多年文学实践、思考、探索、经验做了全面的回顾和总结,涉及作家的创作心理、情绪、状态,小说的开篇布局、结构安排、结尾,人物形象塑造、故事推进、叙述方式、小说语言,以及文学的价值等重要问题,不仅具有理论意义,更具有实践意义。
根据录音,整理如下(注:吴圣刚、韩冰莹提问统称为“问”,李佩甫回答统称为“答”):
一、开头奠定作品的写作情绪和方向
问:李老师,您好!自从找到创作领地以来,您先后创作出“平原三部曲”和《平原客》《河洛图》等众多优秀长篇小说,关于您的小说创作,您曾多次提到小说的开头问题。您是如何看待您的长篇小说开头的?
答:长篇小说写作最困惑的时期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当时,我尚未找到自己的写作领地,但我特别注重对文学语言的追求,讲究质量高的语言。其一,我认为语言与一个人的思维形态、思维方式以及个人的站位、角度、格局关系很大。其二,讲究语言还是建筑学意义上的。一部长篇小说实际上就是盖一座宫殿,若无宏观的思想、无建筑意义上的考虑,是写不好小说的。中短篇可能一个意念、两三个细节、寻一段生活便可写成,而长篇不同,像大房子一样,需要的材料很多,针对某个选题可能收集了几十年的材料仍觉得不够。要清楚我的长篇是写什么的,然后是怎么写。我一般在长篇写作开始的头一段甚至是头一句话定下整个作品的写作情绪和写作方向,心里清楚要用清一色青砖或红砖来建造这所房子,如情绪的状态或是时间的跨度等。我比较注重开笔的方向,它和作品的行进方向、语言的形态关系很大,若开头开不好,可能整部作品就废掉了。开头是个定位,找到一个定位点,才能慢慢写下去。
问:据说荣获茅盾文学奖的作品《生命册》,在创作初期为了找到开头第一句话,就花费了您1年的时间,甚至写到8万字又废掉,您还记得您最初是如何设置这个开头的吗?最后是怎样选定“我是一粒种子”这句话作为开头的?
答:《生命册》是写了《羊的门》《城的灯》之后,想有新的突破,想找到适宜的结构,想用第一人称写一个当代知识分子50年的心灵史。最开始想从城市入手,从一场车祸、出车祸以后的重大打击写起。我是出过车祸的,当时父亲偏瘫,肝上又有问题,在去给父亲看病的时候,我坐在车前边,车撞得稀里哗啦。不客气地说,我是喝过自己的血的。我想用个人经历开笔,以父亲对儿子说话的口吻叙述,“孩子,我到这个年龄,住在医院里……”讲述自己的过去。一开始写车祸故事性很强,故事情节也很精彩,但语言、情绪始终不准确,对孩子的诉说太具象,太固定,不是一个人50年后想将一生认识传达出去的诉说。写作的过程中我一直怀疑,咬牙写了8万字,仍觉得语言情绪、思维情绪不太对,最后全部废掉。
当时我在长葛挂职,当过2年副市长,走了7个乡,开头废掉后我又去当年下乡的地方住了1个月,因为自己知道要写什么,回到这个地方重温过去、以唤醒脑海中对土地的记忆和感觉。设计一下特定地域是怎样的地域,房子在哪、水在哪、路在哪。回来后重新开头,仍然不行,直到换了写作地点,从书房来到卧室重新开始,才找到了第一句话“我是一粒种子”。这句话和后来的写作方向一致,将从农村到城市的当代知识分子经历全部涵盖。主线是当代知识分子的情绪流、心理流,但也有一些分散的点,分散的树枝,之所以敢称之为《生命册》,正是因为有群像,若只是三五个人物是用不起这个名字的,吴志鹏背后站了很多人,是这些人成就了他,也塑造了他。后来,我把这部长篇称为树状结构,我要种一棵树,所以才说我是一粒种子,开笔就来源于此。很多人认为吴志鹏和虫嫂、骆驼相比写得最差,我不认同。我虽未描写吴志鹏的脸与外形,但将他的精神全写出来了,我把50年的认识放在他身上,通过吴志鹏的思想、精神历程把各种人和事、把这块土地表现出来。我写土壤与植物的关系也正在于此,写特有的土地长出来最好的植物是什么,为何长成这个样子,是总结式的。很多人坚持说《羊的门》写得最好,可能是因为情节更强,批判性更强,但不客气地说,《羊的门》我只写了一年半,也未考虑结构,《生命册》我写了3年,而且把50年的生活全砸进去,树状结构也是专门设计的。叙述的语气更客观、更平缓,表达了一种更宽容的态度。
问:您的一些作品是直接进入故事,如《城的灯》《羊的门》采用的是第三人称,《送你一朵苦楝花》采用第二人称,《豌豆偷树》《城市白皮书》则是使用日记体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这些叙述手法都各具魅力,您是怎样决定选用何种叙述手法的?《生命册》这部长篇同样用第一人称叙述,您是怎么考虑的?
答:这和叙述方式、使用感觉有关,我还写过一部中篇,使用的是书信体。人称是写作表现的方式,第一人称较为亲切、自由,表达个人内心情绪更细微,但也有局限,只能是你看到听到的。第三人称写作最自由,但写到人物内心时便成了妄猜。人称只是使用的问题,最根本的还是一个作品的精神和情绪问题,它决定写什么、往哪里走、如何更好地表现人物。
《生命册》严格来说是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混合使用,是心理流。我想象他当时是什么样,但实际写到人物时还是使用第三人称。精神上是第一人称,因为是吴志鹏的心灵史,但有时间跨度,若是单一的时间就不可能这样写,是50年时间的跨度将听到的传闻和他接触到的人与事结合起来,如叙述老姑父临死前想听听国家的声音,人称的使用主要是为了写作的方便。
问:对于小说创作来说,开篇与结尾都很重要。您的小说开头独具魅力,结尾的安排同样别具匠心。《生命册》以一片干了的、回不到树上的树叶结尾,您在写下这个结尾时有考虑与开头相呼应吗?怎样理解这一结尾与开头的关系?
答:是呼应的。一棵大树是怎样生长起来的,这个树,包括土壤,从种子到长成大树后叶落归根,是一个完整的意识。但这个结尾不单是这一句话,最后一节都是结尾,这个结尾也重写了两三次,有这样一句话是不够的,是老姑父的葬礼挽住了结尾,葬礼是一种仪式,汗血石榴又抖了个包袱。葬礼一开始写得比较松,是关于回去不回去的问题,不是很满意。后来写成这样,也是费了功夫的,也是几次修改后得以完成的。
问:《羊的门》结尾安排也特别吸引人,在众多的狗叫声中结束故事,您能谈谈这一情节的创作缘由吗?
答:小说结尾也是很困难的,每个作家都想写好结尾,但都有一定难度。“编筐编篓,重在收口”,结尾极其重要。《羊的门》结尾也花费了大量心思,修改了很多遍,后来别人批评说写得太残酷了,我写作时并没有这个意思,一心想创作出一个好的结尾,只是从艺术上考虑,未考虑其他问题,就想把尾巴甩起来。《羊的门》是写得最有信心的一部长篇小说,之前不太敢承认自己是中国作家,写完后觉得自己可以称得上一个作家了,这部小说我每章都精心地创作,想着把口收好,当时觉得还可以,终于松了口气。每一次都是重新开始,总的来说《生命册》的开头和《羊的门》的结尾花工夫最多。《城的灯》是为结尾而结尾,为了把结尾挑上去,有些故意和勉强,相对来说差一点。
二、写自己最熟悉的领域才能左右逢源
问:除了《生命册》这部作品,我也重点关注了您其他长篇小说。每部小说开头您都会花费大量心思吗?
答:《生命册》花力气最多。(20世纪)80年代初写作相对不那么讲究,找素材也找得很苦,因为当过工人,最早的中短篇写工人生活多一点。后来突然发现自己早年在姥姥家的生活是可以写的,《红蚂蚱 绿蚂蚱》是进入对自己最熟悉的生活领域的写作开始,发现自己能占有的,和别人有区别的就是中原。之前写小说总认为自己写得不好,但这部小说当时《新华文摘》《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都选载了,全国评奖仅差一票,给了我一定的信心。说起来我运气不好,有三次都是差一票获全国奖。《学习微笑》也被《中篇小说选刊》《小说月报》选载了,评奖差一票,《无边无际的早晨》被全国所有选刊选载,想着评奖没有问题,结果当年没有评。我热爱写作,不是为评奖,而是真正的热爱。这可以说是上天赐予的恩惠,找到适于我做的事情,就是“面壁”。
问:是坏事,也是好事。这促使您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永不停歇,保持着超越自我的动力。河南作家中,真正对河南、对平原写得最好的就是李主席(李佩甫),一直坚守在平原。刘庆邦不如您写的辽阔,周大新集中在南阳盆地,刘震云主要写豫北延津,阎连科是占领豫西嵩县,你虽未把豫南、豫北、豫西都纳入作品,但豫中平原辽阔,是整个河南的腹地,能够体现中原的特征。
答:我是找到平原,占有平原,从乡村出发,包括乡村和城市。我每年都会下去走走,发现河南是最苦的一块地方,查县志便知,历史上很多年份都是饥荒年,常有“大饥”“人相食”这样的记录。同时战乱频繁,杀气很重,人头像草一样,金戈铁马打过来无法防守。河南是最易被征服的一块土地,是块绵羊地,百姓最听话,还有一大优点,就是同化力和包容性。当年的犹太人是号称世界上最不易被征服的民族,我去过以色列的博物馆,还保留着一个开封的犹太人建筑遗址。犹太人两次被灭国,四处逃窜,但无论他们逃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只要有10个人,便马上选出一个精神领袖,与逃亡在世界各地的精神领袖保持紧密联系,并且一直严格遵循民族生存习惯与传统的生活方式,但他们在开封却彻底被汉化,改变了生活习性。中原文化的力量在于包容性、同化力,几百年虽落后愚昧,但不会被灭绝,有自我复苏的一种内在的血分子,能够生生不息。
问:这让我想到《羊的门》的开篇,细致描绘24种草的样貌与名称,以湍急时间流速列举许昌这个地方的天灾战乱,也正是这些铺垫为呼天成经营“乡村城堡”奠定了基础。您认为河南的环境究竟给您笔下的人物一种什么样的性格?
答:16个字:吃苦耐劳、坚韧不拔、不择手段、生生不息。历史上有句话“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楚人所处之地有山有水,生命有依托。而河南一马平川,无形可依,河南人是活于群体之中,个体力量很弱,所以有“屋”的意识,建房子寻找庇护之所。但历史上这是一块很好的土地,四季分明,平均温度16.8摄氏度,插根棍子便能发芽,适宜人类生活,但因战乱、黄患、宋代以后有文化有钱的人南迁,后来才逐渐没落了。
问:《羊的门》中呼天成这一人物形象塑造得深入人心,不能否认的是,像呼天成、蔡五这样的人确实能带领村民逐渐走向富裕,能不能谈谈您塑造这一人物的原因以及对他的看法?
答:我早年当知青下乡时当过生产队长,当时每年冬季各生产队长、大队支书要在公社开会,得以见识了很多大队支书。后来来到郑州后,经常去各县看看,也见过很多优秀的村支书,呼天成是综合众多村支书后捏合成的人物。另外,《羊的门》又是我切入中原的第一部长篇,正面写中原这块土地上生长出来的村级优秀人物。村级干部像村长、村支书往往是一个村庄最智慧的人,或宗族势力最强的人,或当兵后回村的人。村庄领导人是最能代表这个地域集合性优点和缺点的人物。我思考的是我们国家这样的土壤容易出现什么样的人物,他为何会长成这个样子,这和特有的地理环境有关。虽带有批判性,但最易产出的就是这样的人物,也是优秀人物。
问:您也有一些作品是采用“引子”进行开头,如《李氏家族》《等等灵魂》《河洛图》等。就您的新作《河洛图》来说,写300多年前的康氏家族,以一个历经磨难的算命大师的叙事视角,回望历史,融汇古今。就我的阅读感受而言,加入陈麦子的视角,使作品有了更深长的叙事意味。当时是什么契机促使您写出这篇作品?您是怎么考虑设置叙事视角的呢?
答:康百万家族我实际了解的非常晚,过去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个康百万庄园,来到郑州10年之内仍不知道巩县(现巩义市)有个康百万。直到郑州市市委副书记康定军找到我让我进行写作,又猛然想起来小时候听姥姥讲过,中国有三大活财神:沈万三、阮子兰、康百万,才真正知道了康百万庄园。康百万庄园是巨大的,但除了房子还在,康家主支脉的后人基本都不在了,去采访时得到的也基本都是传说,没有现成的家族记载。我认为历史是这样的,过去的生活口口相传后变成传说,然后演变为故事、寓言、最后成为神话。康家是真实存在的,传说故事也有很多,但并没有翔实的记载。
问:我读这部作品感觉与之前作品不太一样,小说写得具有传奇性,因为没有翔实的资料,所以靠把传说编织起来,呈现出一种传奇性。
答:是的,人物虚构的成分较大,写作的时候有难度,全是传闻。开头采用陈麦子的视角也是基于这样的原因,穿越14代,康家从明清时期兴盛起来。家里第一桶金怎么来的都说不清楚,有传说是来自明代王爷的后裔,明代晚期有位王爷的姑娘为了躲避杀身之祸被康家收养等。其实最早是开饭店起家的说法相对真实一点。最开始是写剧本,后来又重新改了一下。
问:《河洛图》中开篇详细描写中国传统的五行、使用如丁酉年癸丑月庚申日这样的天干地支纪年法,这样写的原因是什么呢?
答:这些都是有具体的时间框定的,如(20世纪)50年代消灭麻雀、大跃进时期,不知道天干地支纪年法的读者不会去细究,但我个人是细究过的,这些年代都有具体指向和定位,若直接写出来的话会担心不让表现被删掉。我们的民族多灾多难,我们是怎样一步步走过来的还是与此有关系的。《河洛图》与其他作品是有区别的,在中原西部,巩义这块地方不得了,为何改革开放后迅速成为全国百强县,是因为历史上这块土地上便有经商传统,这样的记忆一代代传承,底板很快可以复活。
问:您一直致力于人与植物的书写,无论是《羊的门》中的草,还是《生命册》中移栽到城市的种子、会变形的树,或是《平原客》中的古桩梅花,都凝聚着您对中原大地的深刻思考。您是怎样想到这些植物意象的?
答:《羊的门》是为了宏观地把握这个地域,要找到合适的情绪,就找到了草。找到草进行表达获得成功后,意识到对这块地域植物的描写有助于对作品、对特定地域的表达。所以《生命册》不再写草,选用地域的树,《平原客》是写鄢陵这一作为南花北迁的中转站的地域,这个地域最典型的表达就是蜡梅。表现这个地域的特定土壤、植物是为了区分地域,中原植物更能代表中原,写中原热土不只是人的问题,是各种各样的生长的生命状态都进行展现,这才是平原。
问:您的语言也非常值得关注,其价值丝毫不逊于您所讲述的故事本身。特别是一些河南方言的使用,如“谷堆”“傲造”“喷大空”等等这些,读来让人觉得格外亲切。在《城的灯》中您还专门列举了上梁方言,您是有意加入这些河南方言来进行写作吗?
答:上梁方言是不存在的,是个人化的,有意制造的。写作时不刻意考虑使用方言,是先天储备的问题,也不考虑地域,只是寻找能够最准确表达这个地域的句子,但会有种潜移默化的影响。生为这片土地上的人,这块土地的土壤、气候,包括接受的教育,接触的人物都会对写作产生影响,会不自觉地用河南的方言、情绪进行表达。
问:20世纪80年代,各种西方文学的风格流派传入中国,中国作家都在努力地学习西方叙事。这些对您的创作有没有产生一定影响?《平原客》开篇有段描述:“许多年过去了,副市长刘金鼎仍然记得,那行走在路上的‘咯咯噔噔’的车轮声。”这样的书写是否受到马尔克斯《百年孤独》开头的叙事技巧影响呢?
答:(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各种风格流派的作品涌入中国,我更有阅读条件,一天到晚都在阅读中度过。阅读西方的作品对我的认识是产生了一定影响的,但这影响不是具象的,不是模仿各种流派,也曾尝试过但不成功。80年代是中国作家对各种风格流派的吸收时期,但消化起来也需要时间,更重要的是变成自己的文字进行表达。《百年孤独》对中国作家有“毁灭性”的影响,中国作家想逃避时间观念都很难,小说开头第一句展现巨大的时间跨度,面对死亡时一种过来式的态度,是一种新的认知形式,人拖着磁铁在大街上行走,各家的铁器都跟着磁铁走的细节是想象力的巨大改变。人们会惊讶:“哦!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写!”想要完全摆脱西方的影响很困难,我每次极力想摆脱,但个别时候还是有影响。
问:如前所说,在《生命册》中您采用树状结构将众多零碎的片段组合成整体,又使用“见字如面”“给口奶吃”这样的暗线成为贯通全文的血脉。有评论将您的这种安排称为“草蛇灰线”,您认同这样的看法吗?这可以看作是您对中国叙事传统的一种吸收借鉴吗?
答:确实使用了“草蛇灰线”,因为《生命册》的写作是有难度的,虽是主人公的心理流,读起来亲切一点,但背后是一个个点,叙述了很多背景式的人物,若语言质量稍差,则会影响可读性,也很容易写散。为了内在的紧密联系,因此采用主人公的内心独白吸引读者往下阅读,使用传统结构的埋藏手法,在一章章、一节节推进时埋藏一些隐笔、暗线,有意在阅读感觉上提供一些帮助,让结构更加紧密。因看过许多古典文学的东西,知道传统的这种结构方式,算是对中国传统叙事技巧的学习使用。
问:我注意到您在《河洛图》小说开篇中使用预叙点明康家的财神发迹史,以及刚提到《生命册》的“草蛇灰线”,可以说您在创作手法上更多采用中国传统技巧,在众语喧哗的当代文学语境里,您是怎么坚守传统的?您对于现代主义技巧有何看法?
答:在认识、观念、意识上吸收很多西方的文学思想,学习西方的文艺思潮,但怎样将这些消化变为自己的东西,各人有各人的表述方式。我首先就是要找到自己的写作领地,即中原,最开始关注是许昌周围几个县,后来逐渐扩而大之变成个人心中的平原。然后在这块土地上挖掘出自己对生命状态的思考,得出个人的看法,若只是一味沿着西方路子走,将一直是别人的思维。我一直说要写出东方式的、我们特有的这块土地上人和植物的生命状态,这是我的研究方向。中原最代表中国,是灾难深重又生生不息的一块土地。每个人对西方吸收的程度不同,很多人通过对西方进行模仿找到新的表达形式,但我还是更愿意变成自己的东西。在文本意义上西方走得更远一些,但中国作家要建立自己的文本还是有很大难度,文本形式上想要超越具有一定难度。
三、每一次写作都是重新开始
问:《城的灯》开头“桐花的气味一直萦绕在童年的记忆里”,以主人公冯家昌童年的经历写起,您也曾提到,一个人的童年决定人的一生,这一开头的安排是否就是您这一观点的体现?
答:这是两个概念。我的观点有过转变,过去认为金钱是万恶之源,后来认为贫穷对人的戕害超过金钱对人的腐蚀。如一个人的童年,早年缺吃缺穿,受人欺负,心理会是不健康的,相反,在健康的环境中长大,备受呵护的话,缺憾相对会少一些。一个人的童年决定人的一生,是说和他的思维走向、所受的环境教育有关系,但也不是完全绝对的,阅读会一定程度上清洗人的灵魂,修正个人的价值观。《城的灯》是集合了早年当知青时对乡村的一些记忆,如点心匣子和乡村的一些生活细节等,浓缩和集合对农村苦难生活的理解。农村的孩子由乡村走向城市,最早连鞋都穿不上,走向城市后一步步发生变化,早年对其影响很大,是写逃离。
问:《金屋》中的杨如意成年之后的改变,是否是他的童年经历在无形中塑造他的性格?怎么看待《平原客》中李德林的变化呢?
答:是的,正是写《金屋》时观点开始修正。现在很多贪官早年都吃过苦,《平原客》中的李德林倒是另外的原因,他是读过书,在美国读博士,是慢慢被腐蚀的。他早年也是吃过苦的,虽读过书有一定的认识,但被包围时老病根发作,童年的不健康对他也会产生影响。俗话说几代才能成就一个贵族,实际上是指精神的高贵,这是需要许多物质来铺垫的。给予永远是高尚的,索取永远是低下的,站的角度不同会有巨大的心理差距。
问:您的童年生活对您的创作有没有影响?
答:我出身于一般的工人家庭,早年家庭困顿,父亲是鞋厂工人,一个月45元,养活5口人。那时都是在家里接生,未去过医院,用剪刀自己剪脐带,容易出风,上边已经死了三个孩子。到我的时候也出了问题,据说拾粪老头已经到了门口,活不过来的话就要扔到乱坟岗了。因一连死了几个,据说父亲借了30块钱带我到医院打了一针青霉素,才得以活过来,因为是救过来的,家里对我呵护更多。童年印象最深的也有对苦难的理解,我是挨过饿的,小学一年级时每天都觉得饿,当时上学是6天,周六下午背上书包走二三十里路到姥姥家为了吃几顿饱饭,当时一个表姐常领我去庄稼地偷玉米吃,高尔基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中有对苦难的描写,那时便对苦难有所认识,又对应自己的生活,一下子就点醒了。
另外,童年时因家中无书,我又特别喜欢有文字的东西,到处跟同学借书看。小学三年级时我已是家中最有学问的人了。后来凡是关于文字的外事活动,如给亲戚写信、登记户口等都是由我出面。到少年时期,下乡前后我已有县图书馆、市图书馆、工人文化宫、地区图书馆的四个借书证,到处借书看。说老实话,我是我们家最早吃面包的人,在文字中见识桌布、窗帘、面包、蜂蜜、伦敦等等,在文字中见识了整个世界。后来去北京人民大会堂开会,也不觉得天安门高大,因为早已在文字中见识了各种各样的建筑。父母不识字,不会限制我看闲书,大量的阅读让我在书中走遍了整个世界。“文革”时看过尼克松的《六次危机》、日本田中角荣的传记,以及各种哲学书籍等。
问:中西方哪些作家作品对您的影响比较大呢?您现在都读些什么书?
答:我读的书比较杂乱。中国作家的底板与营养钵是俄罗斯文学,如普希金、托尔斯泰、契诃夫等。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的作家,受俄罗斯文学影响最大。那油画般的、诗一样的文字,以及俄国歌曲的那种博大、苍凉与忧伤都对中国文学影响很大。在某一个时期如七八十年代,苏联当代文学影响较大的两个作家:艾特玛托夫、拉斯普京,以及80年代国外各种风格流派全部进入中国,最前沿的这些作家包括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各个年代的作家及作品,对于中国作家都有很大影响。对我来说,中国每个时期的好作品、西方的如《百年孤独》、米兰·昆德拉《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以及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的个别作品我都会看。我是看文字的,若文字头几段写得非常好就会看下去,若觉得文字情绪不对就放掉。因为文字是一个作家的品位和格局的重要体现,不是随便写出来的。
现在的话别人说得非常好的作品是要看一看,也看一些杂志。另外也会看一些乱七八糟的书,这是由于早年形成的一些坏习惯,早年阅读速度极快,一两个晚上就看一部长篇,好多字不太认识,以至多年后有些字的意思才明白,但读音还是错的。
问:从您的小说来看,您的创作一直紧跟时代,小说《金屋》开篇便描写杨如意金碧辉煌的新屋,揭示金钱对人的巨大诱惑。《生命册》开篇移栽到城市的种子是否也暗含着城市化的过程,直击中国当下的变迁?
答:作家是离不开时代生活的。当时受西方的某些影响,《金屋》故意在意象上使用象征性的东西,可能不太到位。《生命册》写一个当代知识分子50年的心灵史,也囊括中国50年的变化;写一个人50年对自己的认知,对这段社会生活的认知,各种各样的生命状态及走向,并反观自己向何处去。因此,50年后对自己仍是发问式的,对一生走向、对生命质量的发问,是问号而不是句号。
问:《平原客》中通过赫连东山与90后儿子赫连西楚生存方式和价值选择的冲突,讲述了具有时代气息的当代生活。正如何弘老师所评论,这是您在揭示“平原客”精神生态的同时,对生长于城市的“平原二代”的全新书写。您认为一个作家在创作时应如何与现实生活拉开距离,祛除浮躁心理?
答:《平原客》描绘两代人生活,更当代化一些,现实生活也有很多这样的情况,两代人冲突很大。作家既要深入时代生活,又要与其保持距离。正如一个当了60年的农民,最熟悉的就是自己的生活,但只有跳出生活,拉开时间和空间的距离才有可能看清楚。作家同样如此,与时代保持一定距离才能看得更清楚。我原来在许昌时,写作上对家乡的认识还是有局限的,来到郑州后,又走过很多地方再回头看家乡看平原,感觉就不同了,有了参照,产生了一种分析性的思维进而重新认识。生活不是文学,在脑海中浸泡很长时间,经过个人认识发酵才变成作品。作家个人的思维融在其中,看似人物在说话,实际上是作家对时代生活的重新认识,这个认识有品位和格局的差别。
问:像《平原客》来源于生活中的真实案件,也经过了个人的加工?
答:是的,这个案件10年前听说过,10年后才开始写,是有巨大差异的。我是很多年后又去了鄢陵,刚好有个村支书请吃饭,说到吕德彬是他们村的人,才知道原来是老乡,然后才想起10年前的案件。后来的一些故事加入了我的一些生活储存,借用鄢陵这个花卉中转站,借用这块土地种出了这一人物,已经不是吕德彬本人。赫连东山这一人物是创造出来的,和多年生活储备有关,我采访了7个郑州市区级检察院,跟一些法官聊过天,使用许多别人的东西,都是移花接木再造的,既不是原有生活,也不是单纯某一个人物给予的启示,是众多人物的浓缩。我写《平原客》时还采访过省看守所的一个政委,聊犯人不同的情况。小说不是报告文学,经过一定的时间,大量的生活经历经过发酵、改变、浓缩,最终才凸显出来。
问:您从事写作很早,文学道路至今已有40多年。有评论称您的创作,年轻时没有井喷现象,年过50之后也没有减速,而且越来越炉火纯青。这几十年中,您的文学观念有过怎样的发展、转变?
答:我是老牛破车式的,是阅读和写作拯救了我。我认为每个人一生当中有个最适宜他做的事情,若找到了,便能左右逢源,我稀里糊涂半睡半醒地找到了适于自己生存的方式。少年、青年时期不知道要做什么,阴差阳错成了作家。有时行文当中会产生快乐,早上起来泡杯茶,情绪很好时写得很顺也会很快乐,找到一个最好的细节、一个能准确表达的句子,会有“指甲开花”的感觉,反之便会苦恼。文学观念不断延伸,对世界、对特定地域的生命状态一次次重新认识,思考特定地域的生命状态和生命意义,思考人的生存怎样才是最好的生存,这是一个不断认识的过程。我也会出去走走看看,尤其是两大革命:生物革命和互联网革命对人影响较大,这三四年变化巨大,更需要重新认识。
问:您对文学的价值怎样理解?对于我们文学专业的人来说,您认为我们应该怎样对待文学?
答:我一直觉得文学对时代生活没有用处,也不解决任何个人问题,文学是无用的,但也是无价的。比如一把椅子,可以从工艺上材质上算出它的价格,但有些东西无法算出价格,如百米赛跑跑了九秒、足球赛踢进一个好球。文学对个人的物质生活没有用,但对丰富和滋养人的精神有巨大作用。不客气地说,文学拯救了我,若不是读了这么多书,我可能就变成了另外一种人。早年看了一些书,建立了对美、对生活质量的标尺,对个人来说,文学可清洗、修正人。
问:文学不可能让你成为富翁,但却是人精神上的财富。文学作品不能变成你的实际生活,但读了之后会从中得到启迪与共鸣。
答:对,增长一些见识,像沙盘一样,看到各种各样的人生,有时会让你避开一些东西。我当年根本没想过学习作品的结构、语言,完全就是享受式、消遣式地阅读,这会潜移默化影响人。对于文学专业的人来说,还是要多看些作品,甚至建议不是研究性的读,而是兴趣式、滋养式的阅读,这样对人生会有好处。
问:2020年8月,15卷《李佩甫文集》出版,这称得上是您几十年来写作的成就。您现在是否觉得写作更加得心应手了?或者说通过写作,又有着新的困惑在产生?
答:从1978年元月开始发表作品到现在已经42年了,对个人来说,是个阶段性的总结。成就谈不上,我是比较努力的,一直想写好作品,每一次都有遗憾,都不是特别满意,觉得应该写得更好。我想避开曾经写过的东西,害怕重复,但有时候记忆中的东西会成为惯性,每次都想重新开始,但有一定困难。
现在迟迟不敢开笔,在文本上想有更新的发现,有更新的表现形式,更新的语言认识很困难。
问:还会继续坚守在平原这片领地上吗?
答: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