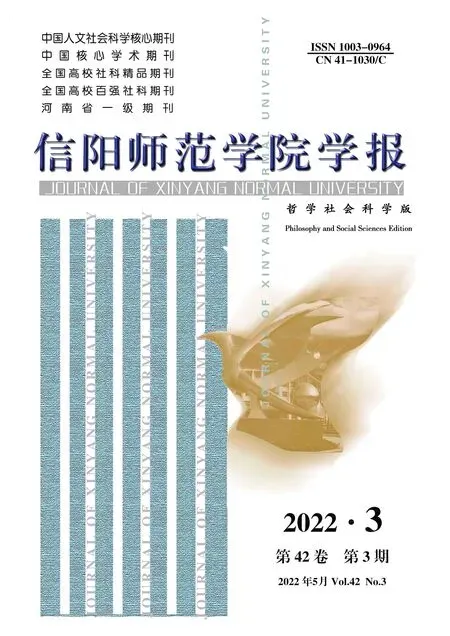施莱尔马赫《论宗教》中的社会性原则
黄 毅
(信阳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
一、施莱尔马赫宗教观的诠释问题
施莱尔马赫是公认的19世纪新教神学之父,然而他也极可能是“欧洲所有主要神学家中最为人所误解的神学家”[1]9。
在20世纪前半叶,人们对施莱尔马赫神学的理解几乎都受制于新正统派的诠释。正如尼布尔所说:“一种对现代基督教思想史的受制于巴特主义的理解统治着神学。”[2]11可以说,新正统派炮制了对施莱尔马赫宗教思想的“标准解释”:对于施莱尔马赫而言,宗教就是“对无限的感觉与鉴赏”[3]31,它是“对宇宙的直观”[3]33,它是“一种特定的情感”[4]5,即“绝对依赖感”[4]12,它缺乏任何社会、历史性的维度。因为作为宗教之基础的情感完全是内在的、主观的、私人的,所以任何外在的因素——例如教仪或教义,宗教团体或传统等——都必须排除在宗教的本质之外。
近年来,上述误解不但没有得到缓解,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变得更为严重。许多学者认为施莱尔马赫把宗教看作一种纯“私人的”事件:施莱尔马赫把宗教完全限制在宗教个体的内在领域,从而使它完全与公共领域隔离,即与社会、文化和历史的可观察的领域隔离,并因而免于批判性考察。提出这种诠释的有格蕾丝·詹特伦(Grace Jantzen)、蒂莫西·菲茨杰拉德(Timothy Fitzgerald)、以及罗素·麦克基安(Russell McCutcheon),其中,麦克基安的批判最为尖锐。他批评道:“施莱尔马赫通过把宗教重构为一种不可量化的个体经验,一种深层情感,或者一种直接的意识,从而在宗教的有文化的蔑视者那里捍卫了宗教。”[5]4此外,他还认为以施莱尔马赫为代表的研究方法,一方面“试图在主体的私人的、神秘的领域以及纯意识中来保护公共和社会性的元素”,另一方面又“假定宗教不能被解释为不同文化或历史因素及过程的产物”[5]5。
上述诠释的问题在于,它不是从施莱尔马赫神学著作的整体而是从其中的小部分——主要是《论宗教》的第二演讲和《基督教信仰论》的第三节和第四节——来理解施莱尔马赫的宗教思想。遗憾的是,这种自以为是的标准诠释长期束缚着人们对施莱尔马赫宗教思想的认识。同时,人们在阐释施莱尔马赫宗教思想时也总是把眼光仅仅盯在《论宗教》的第二演讲和《基督教信仰论》的第三、第四节,而对其他演讲以及《基督教信仰论》的其余部分视而不见。
基于对《论宗教》的深入阅读与理解,笔者试图发现一个不同的施莱尔马赫形象。笔者认为,社会性原则其实是《论宗教》的建构性原则,它不仅仅体现在本书第四和第五篇演讲中,甚至在讨论作为“直观与情感”的宗教本质的第二篇演讲中,社会性原则实际上也多次被提及。虽然施莱尔马赫直到第四篇演讲才明确地将宗教的社会性原则作为主题予以讨论,但实际上,该原则在其他演讲中一再出现。社会性原则实际上是贯穿《论宗教》一书始终的根本性原则。在施莱尔马赫那里,宗教社会对于作为宗教本质的“直观与情感”而言,并非可有可无的“辅助选项”,而是“必须被接收的规范性现实”[6]23,也就是说,宗教社会是敬虔的建构性要素,是其必不可少的中介。
二、“上帝之城”“天国的联盟”——宗教社会作为宗教本质的建构性原则
(一)宗教社会的中介功能
虽然施莱尔马赫在《论宗教》第二篇演讲中把宗教的本质界定为“直观和情感”,但这种本质决非主体主义、个体主义的。施莱尔马赫在第四篇演讲的开篇就写道:“宗教过去是,它也必然地必须是社会性的。它不仅存在于人的本性中,而且它也完全优先地存在于它本身的本性中。”[3]106这句话单独来看似乎也可以理解成:当人们已经体验到宗教感时,他就需要有同伴来分享他的情感。林贝克就是这样理解施莱尔马赫的,他认为施莱尔马赫的宗教情感只出现在“前反思的经验领域”[6]21,而无须团体及其传统的影响为中介。他认为施莱尔马赫所说的教义命题只是单一维度的个人情感的流露,它没有任何规范性与真理诉求。在林贝克看来,施莱尔马赫宗教理论的问题在于:“它把公共的团体传统只看作个人在自我实现中可选的辅助,而不是必须被接收的规范性现实。”[6]23
然而,如果我们再仔细考察第二篇演讲中的一段话,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施莱尔马赫实际上主张社会性不仅是宗教感的结果,而且是它的必要条件。在那里他说:
很久很久以前,第一个人仅仅是同自身和自然在一起,不过神祇高高在上地主宰着他,神以不同的方式同他打招呼,但他不理解这些,也就不能应答神祇的招呼;他的伊甸园是美丽的,天体从美丽的天空给他倾泻万丈光芒,却激发不出他对世界的感觉,他自身也不能从他心灵的内在之处发展出来……由于神祇了解到,他的世界一无所有,这么长时间他都是孤身一人,就给他创造了一个女伙伴,这时才在他的内心激起了富有生命和精神的声音,只有这时他才张开眼睛看世界。在他的肉之肉中,在他的腿之腿中,他发现了人性,在人性中他发现了世界。从这一瞬间开始,他变得有能力倾听上帝的声音和应答上帝的招呼。[3]51
基督教传统思想认为每个人都需要他人。在这段话中,施莱尔马赫运用了这一思想,他甚至以此为基础做出了更激进的表述,即当人还只是完全孤独的时候,他甚至无法听见上帝的声音。他明确地说只有人“发现了人性”时,他才能发现世界,并且“从这一瞬间开始,他变得有能力倾听上帝的声音和应答上帝的招呼”[3]53。显然,施莱尔马赫的这个论断不仅表明人们想要分享宗教经验,或者说社会性不只是宗教经验的结果,而且表明如果割断了与他人的关联,那么人们甚至无法获得宗教经验。换言之,社会性是敬虔必不可少的条件,敬虔是经由社会性为中介的。
因而,当施莱尔马赫宣称我们只有在人性中才能发现宗教的“素材”时,他是在一种强调的意义上意指个人与上帝的关联无法在与他人相分离的条件下实现,或者说,我们只有首先与他人相关联,才能经验到敬虔。施莱尔马赫在1821年出版的《论宗教》的第3版中更明确地谈到这一点:“我们观察到,只有在与他人的交往中,宇宙整体才如何向我们清晰地展现,以及我们才如何达到对它的直观以及与它结合为一体。”[7]78
问题在于宗教社会之必要性的根据何在呢?宗教为什么“必然地必须是社会性的?”施莱尔马赫为此做了几点论证。首先,他认为人类思维与活动中蕴含了这样一种冲动:使内在发生的东西外在化。一个人在内部越感受到激动,那么他就有越强的冲动去表达他的情感。施莱尔马赫说道:“某种东西越热烈地刺激它,越内在地浸润其本质,动机也就越强烈地受到触动,有力地驱使他去直观身外别的东西,好亲身证明,他眼前所遇到的东西无非就是人性的东西罢了……我们这种特别不寻常的关系是不可或缺地要内在地变成公共的本性。”[3]106-107其次,施莱尔马赫认为宗教沟通对于自我认识是必要的。他说:“他何以应该把恰恰对他表现出来的最大、最不可抗拒的宇宙的影响力为自身而保留呢?……因为除了这个东西之外,没有什么给他留下了那么深的烙印,他仅仅从自身出发不可能认识到自我本身。”[3]107再次,由于宇宙是无限的,我们在受宇宙直接感动时所能把握到的,只是宇宙的一个部分,“而关于他不能直接达到的部分,他想至少借助于一种其他的媒介来感知”[3]108。也就是说,宗教沟通是互动的,一方面人们倾听他人的言说,另一方面他通过自己的言说来传达宗教情感。施莱尔马赫认为,在宗教沟通中,“说话和倾听也就同时对每个人都是不可或缺的”[3]108。
(二)“无词之语”——宗教沟通的恰当形式
由上可以看出,施莱尔马赫认为宗教沟通的必要性是宗教社会性的缘起,那么宗教沟通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呢?这是一个非常关键也易于引起误解的问题。它关涉语言在宗教沟通中的地位问题。事实上,人们对施莱尔马赫宗教思想所做的主体主义、神秘主义指责的根源就在于此。
由于施莱尔马赫认为宗教沟通的“最真正的对象,无疑就是要求直观和情感”[3]107,因而宗教沟通是一种情感沟通,而并非思想沟通。情感沟通与思想沟通的区别在《论宗教》中就已经呈现出来了,后来也成为施莱尔马赫在其《伦理学》讲座中讨论的主题之一。在那里,施莱尔马赫明确地把沟通分为两类:一类是通过语言形式,在思想与认知层面上的沟通;另一类是在情感层面上的以艺术为形式的沟通[8]890。在施莱尔马赫看来,语言主要用来交流思想,增长知识。人们在语言中“理解”思想,情感则需要借助艺术的形式来传达。
既然宗教主要是一种直观和情感,那么宗教沟通所主要采取的形式就是艺术。为此,施莱尔马赫对只以语言形式来沟通宗教的做法表示不满,他说:“言辞只是我们的直观和我们的情感的阴影。”[3]83施莱尔马赫甚至认为他不能准确地通过言词把他的直观和情感描述给他的听众,因为正是他的描述“亵渎”了它。他为这个事实而感到惋惜,即“对于我的演讲而言,宗教最纯真的精神就丢失了”[3]42。
施莱尔马赫之所以认为语言是宗教沟通的不完美工具,是因为他对语言与反思意识关联的理解。我们的意识生活一方面在于从外部世界接收感官印象,并根据思想的范畴来整理这些印象;另一方面在于把外部世界用作表现自我的工具。换句话说,反思意识必然要与对象和事物打交道[3]42。语言最初是在人类的反思意识中产生的。因而语言已经从以主客同一为其特征的直接意识中脱离出去,在语言中主体与客体的对立已经形成。他解释道:
反思把两者分离开了,谁又能够对属于意识的东西说点什么,而不首先通过这种媒介呢。不仅在我要传达宗教情怀的内在行为时,而且在我要把它们只当作我们内心的观察素材并想把它们提升为明晰的意识时,立刻就要进行这种不可避免的区分……我们也不能够逃脱这种分裂的命运。我们无非能够在这种被分离的形态中再次敦促和告诫其产物是表面的。[3]42
由于作为宗教之本质的“直观和情感”是直接的,在那里主客体之间的分裂尚未产生,因而在某种意义上,它们无法用与反思意识相关联的语言来描述。
与施莱尔马赫对语言形式的批判相应的是他对艺术形式的重视,他特别强调音乐与宗教沟通之间的密切关系。他认为人们“最内在心声的最确定、最可领会的表达”不是通过“限定性的言语”,而是通过“无歌无调的音乐,就是神圣者当中的音乐,它是无词之语”[3]110。这种“无词之语”究竟是什么意思?什么又是“无歌无调的音乐?”情感的直接性是否意味着敬虔的不可说性?确实,施莱尔马赫自己的上述表述很容易给人造成布鲁纳式的误解:宗教语言与概念对于宗教的神秘内核来说是完全不相关的。
然而,对施莱尔马赫而言,沟通又必须是确定的,世上“绝无什么普遍的东西和不受限定的东西,只是说它们只有作为某种个别的东西和在一种完全限定的形态中才能被给予和传达,因为通常要是不存在某物,事实上就什么也不存在”[3]113。正因此,施莱尔马赫并没有完全否定语言在宗教沟通中的作用。他甚至认为宗教必须以“言语”的方式来沟通。他说:“宗教不可能不以演讲家的全部功力和语言艺术说出和传播。”[3]109这是因为语言是具体的和有限的,而只有有限者才能展示无限。因而,施莱尔马赫所说的“无词之语”不能理解成情感的不可言说性,它只是用来提醒人们语言的局限性:不同的语言在某种程度上都可用来沟通特定的情感,但又没有哪种语言能够完全理解情感。更关键的是,“无词之语”告诫人们要警惕宗教沟通中的“僵死的文字”,即那种脱离了原初宗教经验的语词,“只有当宗教被驱逐出活生生的社会时,它才不得不将它多重的生命隐藏在僵死的文字里”[3]108。施莱尔马赫甚至认为:“不是信仰一部《圣经》的人有宗教,而是那个无须《圣经》,但自己能够创造一部《圣经》的人有宗教。”[3]70在此之后,施莱尔马赫确实运用他自己创建的解释学理论对新约《圣经》提出了激烈的批评。
虽然宗教沟通必须采用语言的形式,但由于语言的局限性,宗教人士就必须用各种艺术形式来弥补这种局限。宗教人士必须利用音乐和视觉艺术来使得他们的言语沟通更加形象化。正如施莱尔马赫说:“在只是和风悦耳地轻声配上诗人词语的圣歌和合唱中被直观到的东西,是限定性的言语不再能把捉得到的(东西)。”[3]110艺术家们通过其“神圣的艺术杰作”把他们所把握的宗教感固定在图画中,并“向那些人描述天国与永恒,作为欣赏的和统一的对象,作为你们的诗歌所仰望的东西的唯一不竭的源泉”[3]8。以这种方式,“思想之声和感觉之音如此相互支持和交换,直到一切都饱满并完全被神圣和无限者所充满”[3]110。
三、理想宗教社会的特征
在论证了宗教社会对于敬虔的必要性之后,施莱尔马赫试图在《论宗教》第四篇演讲中对于理想宗教社会的特点和组织结构展开更深入的讨论。他在1799年4月5日写给赫兹的信中认为教会应该是所有人类的组织与关切中最高贵的。
由于宗教社会是由宗教沟通所自然形成的,所以施莱尔马赫对宗教社会特征的讨论,是以他对宗教沟通特点的讨论为基础的,实际上这两个方面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一)宗教沟通必须是完全自由的、自愿的行为。
在同样写于1799年的名为《一种社交行为理论的研究》一文中,施莱尔马赫详细阐述了“自由社会”的概念,在这种“自由社会”中,行为“既不与外在目的相关也不受其规定”[9]20,它与那些受特定的诸如政治、职业和家庭因素影响的行为相对立,因为人们在自由社会中“只是自由地展示自己的力量,人们也可以进一步地发展他的力量,他不受外在的规律而只受自身内在的规律的影响”[3]21。决定自由社会行为特征的只不过是参与者的性格、兴趣和欲望,因为“根本不能设想这个社会的目的在于它自身之外……因而一切行为的目标只不过是思想与情感的自由展示,借此所有成员相互激励、相互提升”[3]24-25。
自由也被施莱尔马赫看作理想宗教社会的特性。我们从施莱尔马赫对“上帝之城”的描述中可看出这一点:
但愿我能够从上帝之城的丰富而丰盛的生活中给你们描绘出一幅图画,那里的居民聚集起来,每一个都充满天生的活力,愿意将其自由散发,圣洁的欲望充满一切,每个人所取得的东西,就是从别人愿意给他呈现的东西中领悟到的。如果一个人走到其他人的前面,不是凭什么职务或约定使他有这样的权利,不是傲慢与狂妄使他自以为有这样的威望,而是灵性的自由冲动,是每个人与所有人最神圣地融为一体的情感冲动,是最完善的平等冲动,是每一种诸如最先和最后之类的世俗秩序的废除。[3]109
因而,安德鲁·多尔也把施莱尔马赫的理想宗教社会称为“宗教式的自由社会”[10]106。正因为宗教人士之间的行为都是自由的,所以“哪里有野蛮地诱人向一个个别的实定宗教形式的改宗,哪里有那个恐怖的所谓我们之外无救恩的格言呢?”[3]112理想的宗教团体不会有意使其他的宗教人士改变宗教信仰,也不会诱使无神论者皈依宗教。诚然,宗教人士总是以言语和艺术来传达他的宗教,并期待能够从听者那得到反应,但是如果这种期待并没有实现,“它都岸然鄙夷每一种新奇的诱惑,每一种粗暴的方式,而镇静地坚信那种与它亲如兄弟姐妹的气息互动的时机尚不成熟”[3]80。
理想宗教社会的自由性也就意味着它完全是为了宗教自身的目的,而不受任何其他目的的干扰。施莱尔马赫特别反对教会与国家的联合,以及它对国家的屈从。“只要一位君王宣布一个教会为一个法人团体,一个有其自己特权的社团,一个在市民世界有声望的人格,而这不会产生别的,无非就是已经出现了的那种不幸的状况”[3]125。国家把自己的特殊利益带进了这个精神性的团体,从而污染了教会纯洁的灵性团契。所以,施莱尔马赫号召“废除教会与国家之间所有的这种关系吧!——这是我至死不渝的加图式警世格言,或者我要一直活到亲眼见到这种关系被摧毁为止”[3]132。
(二)理想的宗教沟通要求沟通双方的交互性,没有哪一方是纯粹被动的
如施莱尔马赫说:“在真正的宗教社群中所有的交流传播都是相互的,驱动我们说出自己真心话的原则,同那种使我们倾心于与陌生人接触的原则,具有内在的亲缘性,所以,作用与反作用是以密不可分的方式相互联系的。”[3]115在宗教中,师傅与门徒之间并不是决然对立的,门徒对师傅的追随不应该是“盲目的模仿”,“门徒不是因为你们师傅为了教育他们而造就的,相反,是因为他们为了宗教选择了师傅,你们才是师傅”[3]83。与之相反,在流俗的教会中,“所有人都只愿意接受,只有一个人应该给予,完全被动地以同一种方式通过一切器官让所接受的一切在自身之内起作用……只是从不考虑对其他人的反作用”[3]116。施莱尔马赫认为,那些只能完全被动接受的人只是“宗教的负极”,因为“他们内心没有宗教居留”[3]116。他们只有“一种小学生的机械模仿”,而并未把握宗教的真谛,他们只能“紧紧攥住那些僵死的概念,死守宗教反思的结果并贪婪地对此囫囵吞枣”[3]189。
宗教沟通的交互性使得理想的宗教社会具有流动性,而没有严格的等级性。教会是为了宗教情感的不断沟通和加深的目的而产生的,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在教士与平信徒之间不应该存在严格的等级差别,他们之间“不是个人之间的区别,而只是状态和事务之间的区别。”于是:
每个人都是教牧,只要他在这个他特别为之献身的领地上,把其他人吸引到自身这里来,而且他在这里能够表现为是一个技艺精湛的行家;每个人都是平信徒,只要他自己在他不熟悉的宗教事务上跟随他人的艺术和指点……在这里,每个人交替地既是领导也是平民,每个人既跟从别人的力,在自身他也能感受到这种力,他也用这种力去治理别人。[3]110
施莱尔马赫把这样的理想宗教社会描绘成“天国的联盟”,它是“一个完善的共和国”,在这里根本不存在“可恨的独裁贵族制”[3]110。施莱尔马赫甚至认为,这种天国的联盟,“是人的社会性的最完善结晶”,它是比“你们世俗的政治联盟更有价值的联盟,因为政治联盟只不过是一个被迫的、短暂的和过渡性的作品”[3]110。
(三)宗教沟通是互补的
宗教的互补性是由于宗教的无限性和个人的局限性。每个人都意识到“他只把握到它的一个狭小部分,而关于他不能直接达到的部分,他想至少借助于一种其他的媒介来感知”[3]108。因此,虽然不同宗教人士之间的宗教情感可能千差万别,但这些差别“通过社会性的联系,像汁液一样相互流通交融……因而在最疏远的元素之间也存在许多过渡,没有绝对的冲突,没有完全的分离”[3]111。对自身有限性的意识使人们能够欣赏他者的多样性,无限只有在多样性中才能更充分地启示自身。
宗教沟通的互补性使得理想的宗教社会具有统一性而不是分裂的。施莱尔马赫认为,真的宗教团体不会有分裂和争吵,只有那些在形而上学和伦理学体现出来的对“构筑体系的欲望”的宗教团体才热衷于分裂和争吵,因为它只建立在“赤裸裸的单调性”之上[3]37。施莱尔马赫认为,只有那些“僵死文字的信徒们,才满足于喧嚣和吵闹的世界”,而“真正观看永恒的人们永远都有宁静的心灵……他们以这种宽广的视野和对无限的情感,看到了在他们自己的领域之外存在的东西”[3]38。于是,“一切存在着的东西,对宗教而言都是必然的,一切可能存在的东西,对宗教而言都是无限之物的一幅不可或缺的画面……宗教让虔敬的心灵感到一切都是神圣的,有价值的,甚至连不神圣的和粗鄙的东西也是如此……宗教是一切自命不凡和一切片面性的死敌”[3]38-39。
除上述提到的自由、流动性、统一性之外,施莱尔马赫还多次论述了宗教社会的根本伦理特征——爱。虽然施莱尔马赫没有明确阐明它们之间的关系,但是笔者认为爱是宗教社会自由、流动性和统一性的前提。正因为人与人之间充满爱,所以人与人之间不存在严格的等级关系,也不可能完全分裂,人们更不可能用“暴力”或者“引诱”让他人改宗。
“爱”对于施莱尔马赫早期伦理学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例如,施莱尔马赫写道:“爱是物理学与伦理学之间最直接的枢纽……爱是个体存在的原则……如果没有爱,那么存在与生成之间就没有同一性。”[8]345据布兰特·索克尼斯(Brent Sockness)的考察,爱以及个性与共性之间的张力问题正是施莱尔马赫在1800年《独白》中所关注的伦理焦点[11]32。
然而,笔者将要说明,“爱”不仅是施莱尔马赫伦理学著作的主题,而且也是《论宗教》一书的主题之一。爱构成了理想宗教社会的根本伦理特征。正如施莱尔马赫所说:“为了直观世界和拥有宗教,人才必须找到人性,他只是在爱中并通过爱才找到人性。”[3]51宗教只有在对他人的爱中并通过对他人的爱才能发现。值得注意的是,仅仅在《论宗教》第二篇演讲中,就有多达6次提到“爱”这个概念。而且在《论宗教》1821年的版本中,施莱尔马赫进一步强调了爱的重要性,他说:“对爱的渴望一旦得到满足并得到持续的更新,它就立即变成了宗教。”[7]72施莱尔马赫在这里谈到的“爱”不是抽象的对宇宙的爱,而是人与人之间的爱,因为只有“我们走向人性”,才能“为宗教找到素材”[3]51。而且人们只是通过他者才能真正发现宇宙,施莱尔马赫说:“人性本身对你们而言就是真正的宇宙,其他的一切只有当它们同人性有关联并环绕人性时,你们才把它们算作是宇宙。”[3]52
施莱尔马赫进一步把爱描述为以“亲缘”为纽带的兄弟姐妹之爱。他说:“如果我们在对世界的直观中也关注到了我们的兄弟,而且这对我们是这么清晰,如同他们中的每一个在这种感觉中简直无区别地就是同一个人,那我们是什么?人性的一个真正表现,而没有每一个人的定在我们又如何必定缺乏对人性的直观?什么比所有这些直观——它本身与意念和精神力没有区别,包括内在的爱和倾心——更加自然?”[3]63在《论宗教》第四篇演讲的结尾,施莱尔马赫再次强调了人类共同的亲缘关系——“它们同契共道,是一个兄弟联盟”[3]138。他接着写道:“每个人越是接近宇宙,每个人也就越多地与他人心心相通;他们越是融为一体,就没有人只有自我的意识,每个人同时也有他人的意识,他们不再只是众人,而且是人类。”[3]138施莱尔马赫还使用了“邻人”这个概念,他说:“哪怕每个人只同最临近的人有联系,但他在一切方面和一切方向上也都有一个最临近者,他事实上也就同整体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了。”[3]112施莱尔马赫在此利用了“邻人”在词源上的原始含义:邻人就是与人最亲近、最亲密的人。因此,施莱尔马赫所讲的爱可以具体地规定为邻人之爱。
也许我们会问,为什么我们实际上都是邻人?施莱尔马赫认为这是由于人们所具有的共同本质,由于人们之间的一种“亲情”[3]63。在谈论理想宗教社会的段落中,施莱尔马赫明确提到了人们所具有的“公共的本性”[3]107。正是这种“公共的本性”构成了所有人之间的纽带,构成了“一个普遍的联合体”[3]112。在《论宗教》1821年的版本中,施莱尔马赫反问道:“我们如何会感知不到这种联合呢?”[7]76在那里,他强调人们在本质上的关联性将会自然地在人们心中产生“对一切苦难和痛苦的最深切的怜悯”[7]78。也就是说,在后面的版本中,施莱尔马赫更为强调“邻人”的圣经含义。
四、结语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从否定的角度讲,对施莱尔马赫宗教观那种巴特式的“标准解释”显然很难成立了,因为它忽视了《论宗教》中丰富的社会性维度。从积极的方面来说,我们发现施莱尔马赫在对宗教的社会性论证中引入了一个重要的伦理学主题:邻人之爱。施莱尔马赫认为以邻人之爱为其根本伦理特征的宗教社会是敬虔的必要条件,而非只是其结果。施莱尔马赫日后在各个方面广泛运用了这种邻人之爱的伦理学,例如,他关于改革刑法、废除死刑的建议,关于修改国际法和防御性战争的意见,他对以武力在发展中国家推行殖民统治的厌恶,以及改善工人劳动条件的建议等。因此,施莱尔马赫所宣称的作为“个别的人和这一个(意指上帝——笔者注)”[3]60的中介的邻人是真实的他者,而不是人们用以达到其目的、敬虔的手段。我们可以说,施莱尔马赫的这个伦理学主题使他避免了两个危险:一是与上帝的无中介的、神秘主义的直接关联;另一个是对中介的无差别的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