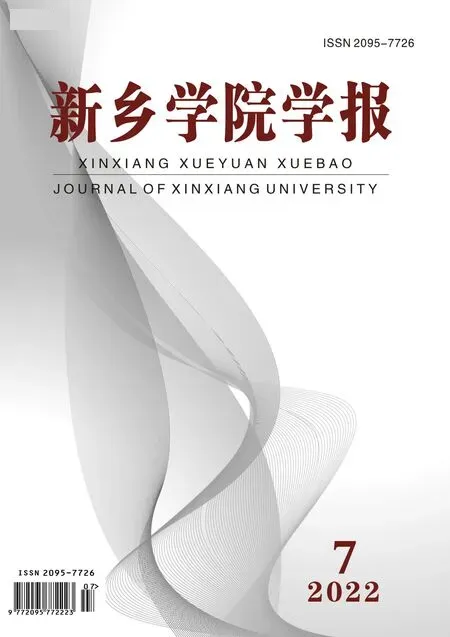魔幻现实的面孔与黑色幽默的调性
——论刘震云《一日三秋》的表现形式和艺术旨归
吴昊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在中国当代文坛,刘震云是一个极为擅长把日常伦理和智性思考结合起来,书写世俗时代的荒诞与孤独、寓言与反讽的作家。他的小说承载着一个现代知识分子作为民族文化审视者和中国心灵勘探人的历史使命感,以故乡“延津”的人事风华为原点,对转型时代下普通民众的精神焦虑和生存困境、社会价值伦理秩序的更迭变换进行全方位的透视与分析。作品于一地鸡毛的世俗人情中为生活角落和边缘地带里不断下沉、日益惶怵的现代魂灵塑像,通过“喷空”和“说话”的民间形式,解构与重构、编码与解码现代生命在每一瞬间的情感经验和存在意义。刘震云的小说无论是“讲史”,还是“说今”,都呈现出一种别出机杼、具有辨识性的艺术形式和美学风味——在立足于古典叙事资源的基础上,汲取西方现代和后现代的先锋笔法,使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魔幻与现实、方言与歌谣、幽默与讽刺、沉重与轻逸、复调与对位等美学镜像在他的小说中“叠合交叉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寓言文本和狂欢化、戏谑化文本”[1]。
2021年7月,《花城》杂志首发了小说《一日三秋》,这是刘震云自《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出版之后,暌违四年,为“重构”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活伦理”所做的一次文学求索之旅,也是其时隔多年再为故乡延津“谱志立传”的最新力作。这部小说一经出版发行,便受到了学术界和读者群的热捧与赏识。对于熟知刘震云文学世界的读者而言,《一日三秋》不啻于一部返回写作原乡、重复“刘氏美学”的作品,它几乎熔铸和聚合了作家以往创作的全部技巧和审美元素。但这部小说并没有停滞在旧有美学的藩篱之中,而是冀求尝试集先锋性和民间性、叙事力量和格式塔韵味于一身的文体实验,在辗转腾挪中开辟出新的艺术空间。正如李敬泽所言,“《一日三秋》是刘震云的秋天写作”,它具有成熟的艺术气质和隽永的思想品格,是作家在旧有美学风格的根柢上孕育出来的焕然一新的文学创作景观,把“中国现代以来的文学始终没有处理好、没有充分命名的”中国人内在的生命经验和情感体会“处理得幽微阔大,急管繁弦,一笛凉月”[2]。质言之,刘震云这场通过语言文字来质询现实人生“存在与虚无”之镜像、对人性人心进行探幽和烛照的“精神还乡”之旅,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精神哲思上的启迪,还有表现形式与艺术策略上的冲击和感染。
一、本土化的魔幻现实主义与“喻启性观照”
虽然“魔幻现实主义”一词是拉美文学的舶来品,但中国并不缺乏滋养和繁衍魔幻现实主义的土壤。新时期以来,当代文学面临着“愈益明显的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冲突”,莫言、陈忠实、陈应松和范稳等作家,“在经历了现实主义写作模式和现代主义写作模式的双重实验之后”,开始在立足于中国大地的基础上寻求思维中心的转移和艺术模式的突破,实践一种本土化的魔幻现实主义叙述美学,“在深刻的精神还乡中找到了表现世界和人性的自我途径”[3]。所谓本土化的魔幻现实主义,是指借用和融汇具有本土特色的神话传说、文化习俗、梦境想象、巫风觋雨与谶纬迷信思想,通过变形、荒诞、夸张以及时空交错、虚实相生的手法,来反映、揭露和讽喻现实。这种美学形式和创作方法在新时期作家的笔下屡见不鲜,在刘震云以往的创作(如《故乡相处流传》)之中也能够找到一些痕迹,和同时代的作家相比,这种风格标识虽然还不够明显,但已经隐然成形。到了新作《一日三秋》中,作家将这种陌生而又熟悉的叙事模式用到了极致,这使得小说的艺术形式具有神奇瑰丽的特征。
在魔幻现实主义的烛照下,小说《一日三秋》存在着多个层面的叙事空间:一是现实层面的叙事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主要围绕陈长杰、李延生、樱桃及其子一辈陈明亮、马小萌等人的悲喜人生和情感纠葛展开叙事。另一个是贯通怪力乱神之说、神鬼巫术之道的非理性魔幻空间,这个空间来源于现实,却又超越现实,以反常态的形式,与现代人苦难庸常、困顿麻木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展开沟通对话,对现代和后现代文化语境中底层民众由于生存价值悬置、主体意志沦丧而无力挣扎、无地彷徨的现实状况进行勘探和审视,并“试图在理性与非理性之根中,意识和无意识之源中重新发现救治现代痼疾的希望,寻求弥补”由于金钱利益的引诱、伦理秩序的束缚、生存环境的压迫“所造成的人性的残缺和萎缩的良方”[4]。那么,刘震云是如何来建构这个具有魔幻色彩的奇异空间,对个体现实境遇的爱与怕、痛与苦进行触摸和书写,并以此来完成对人类的文化心理结构、存在之思和生死之谜的“喻启性观照”的呢?
首先,作家以花二娘进入延津人的梦境索要笑话这个民间传说为支架,设置了一个具有本土气息的“神话情境”。在传说中,花二娘和她的情人花二郎相约在延津渡口见面,但花二娘在延津等待了三千年,“错过了无数次春江月明”,也没有盼到在“爱人肩头痛哭”的那一天,于是她变成了一座望郎山。由于生前的孤苦伶仃、悲凉凄恻,死后成仙的花二娘再也不愿意看到风霜苦恨和辛酸的眼泪,她来到延津人的梦中索取笑话,并以此实施“奖罚措施”:能够将其逗笑的,奖励一颗柿子,反之则要背她去喝胡辣汤,在她的重压之下心肌梗塞而死。正因为如此,延津人无论白昼怎样痛不欲生、呼天抢地,夜里也要时刻铭记着携带几个笑话入梦。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神话情境与小说的现实叙事空间是彼此交织的,如主人公陈明亮就多次梦到过花二娘前来索要笑话。在当代社会和当代的文艺作品中,“神话的复活”具有深刻的能指与所指性,显然,刘震云在《一日三秋》中虚构这样一个荒诞不经的神话传说,其用意不在于凸显出神话结构本身所具有的审美张力,而是要借助这种“人类精神对现实世界的虚假的或理想性的超越方式”[5],来言说人们平时不以为意的生存困境和人生哲思,给人以心灵上的颤栗,使我们从生活的漠然状态中醒觉过来。正如卡西尔所言,“神话的真实意义和深刻性并不在于它的结构所启示的东西,而在于神话结构隐匿起来的东西”[6],因此解读神话的关键在于找寻到神话背后所隐藏的喻指性内容。关于花二娘的神话传说之谜,其症结有两点:花二娘为什么要找笑话,笑话为何会成为决定延津人生死的命运棋盘。
或许当我们进入历史与现实的深层文化结构、“此在”与“存在”的生存本体论之中,便能找寻到一些契机来解答这两个具有寓言性的谜题:对花二娘这个人物形象进行追本溯源,不难发现,她是冷幽族的幸存者,讲笑话是冷幽族人反抗生存之苦难和现实之荒唐的重要手段,但在活泼国的新国王和他的权力捍卫者们看来,笑话是社会秩序不庄重、不严肃甚至动荡的罪魁祸首,于是,他们血洗了冷幽族。封建纲常伦理和传统文化体制借助统治阶级的力量扼杀了“笑话”,普通民众在权力秩序和命运桎梏的双重压迫之下,重新坠落到物质贫困和精神痛苦的泥淖之中。然而,逃到延津的花二娘并没有因此重拾起生活的希望和欢乐,她等待了三千年也没有等到自己的情郎,最后被父权文化的阴影和苦难生活的沉疴所吞噬。对花二娘而言,三千年的等待与思念也是三千年的绝望与虚无,“时间在无意义的连续中已经停顿,自我在记忆淆乱中开始丧失,存在的所指在不确定的个人视野中模糊和消失,人的个体性生存和生命的本真存在也被这一虚无境地所溶释或化解”[7],正是这种虚无的境地逼迫曾经擅长讲笑话的花二娘只能去延津人的梦境中寻找笑话,以此来缓解她内心深处的孤独、痛苦和虚妄。在小说第三部分的结尾处,花二娘在梦境里告诉陈明亮:有一个人因为难以治愈的宿疾,附在她身上整整三千年,迫使她寻找笑话。这一点睛之笔的寓意是不言而自明的:存在的虚无和此在的迷离是人类亘古如斯的生命难题,也是人类千百年来无法根治的顽疾。它附着在我们的生命历程中,迫使我们去寻找“笑话”。人们要么做“乐观的西西弗斯”,日复一日地推动着巨石,挑战命运,顽强生活;要么成为“悲观的西西弗斯”,死在滚动的巨石之下。对于延津人而言,他们亦是如此。樱桃、吴大嘴等人并不是死在了花二娘寻找笑话的“游戏”之中,而是死于他们自我对待苦难生活和虚无境地的悲观心态之上。当他们无法勘破生命的谜题,无法忍受岁月的艰辛时,他们便陷入到一种“此在”的“慢性虚脱”状态,再也“无力穿越世界之夜的黑暗而达到一种生存的澄明”[8]。刘小枫曾在《拯救与逍遥》中以震聋发聩的声音告诫人类:“如果不是在绝望的同时力图消除绝望感,在痛苦的同时祈求抹去痛苦的创痕,生命就没有出路。”[9]73这句警醒之言也从侧面揭示出了一条现代人类吊诡的生存法则——在这个人类看似拥有一切,实则一无所有的时代,把我们逼上自杀绝境的并不是苦难本身,而是在面对苦难时,我们内心深处的怯弱、茫然与绝望,以及“漂浮于无目的性的虚无中”[9]62的无能为力感。由是观之,刘震云通过这一离奇荒诞的神话故事,对现代人类的生命之谜和存在之思进行了喻启性的观照,让读者在艺术光芒的照耀下获得精神哲思上的启蒙: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存在的个体都无法摆脱生命的孤独和虚无,但我们可以通过强大的主体精神意志(寻找笑话和讲述笑话可以看作是建构主体精神意志的一种方式)和理想追求来缓解生命的孤独,赋予生活以意义。
其次,作家描绘了一幕幕打破人与鬼/神界限,幽冥相接、阴阳相通、时空穿梭、奇异魔幻的神秘场景。在小说《一日三秋》中,人间与冥世犹如白天与黑夜自然衔接,现实与梦境交织缠绕,死而复生、亡魂显灵、神鬼附体和人鬼对话的场景随处可见。死去的樱桃在乱葬岗不堪忍受孤魂野鬼的欺凌,便附身于李延生身上,要求李延生带她前去武汉,让陈长杰帮她迁坟;天赋异禀、未卜先知的算命先生老董能够测算出人们前世今生的命运,为人们排忧解难、祛病除魔,还可以通过“直播”的方式,召唤亡灵精怪前来与活人对话;无独有偶,巫术高超的马道婆既能以魇术之法让附身在照片之上的樱桃神魄颠倒、痛不欲生,又能预测到自己未来的困境,于是她做了一个顺水人情,托身于萤火虫,指点陈明亮救走樱桃,以便在若干年以后让他帮助自己脱离苦海。这些超现实的魔幻场景,充分展现了延津本土乃至于华夏民族民间的巫鬼文化信仰。巫鬼文化“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世俗的、关乎生存方式的文化”[10],它是普通民众“借助神灵的力量”,“处理和解决人在社会及与自然打交道时遇到的难题”的“最快捷、最简易的方法”[11]。在小说中,李延生、陈明亮等人遇到难以解决的生活难题时,都会向神通广大的算命先生老董求助,寻巫问道已经成为延津人司空见惯的一种生活方式,深深植入到了他们的灵魂骨髓之中。至于作家对樱桃附体、马道婆“顺水人情”的书写,则彰显了盛行在民间文化中的“因果际会”“善恶有报”的思想,这种思想统摄了市井百姓的生活方式和处世原则,甚至成为他们心中的道德律令。樱桃之所以附在李延生的身上,是因为他们曾经在戏曲《白蛇传》中饰演过夫妻;马道婆之所以良心发现,放过樱桃的鬼魂,是因为四十多年后的恶果需要四十多年前的善行来化解。因此,从这些层面来看,刘震云在《一日三秋》中的返魅书写,绝不是为了魔幻而魔幻,而是以此作为突破口,“深入到信仰巫鬼的民众的心灵深处,探索底层民众隐秘的文化心理和潜藏的心灵奥秘”[10]。诚然,神鬼之言和通灵之说并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现代人类精神虚无的生存困境,但它的确为伤痕累累的普通民众提供了一座能够缓冲苦难的平台和寄托心灵的灯塔。
此外,小说还塑造和渲染了一系列具有灵怪化特征的动物形象。这些形象“被作家赋予了种种灵性和奇异的品质……是传达小说主旨和作家的思想认识、主观情志的重要工具”[12],如瘸腿的小黄皮、催人耕田的牛以及陪伴陈明亮多年的京巴狗“孙二货”等。刘震云在《一日三秋》中倾尽笔墨来描绘这些带有魔幻色彩的动物形象,并不只是为了增添小说的审美风景,而是要通过“背面敷粉”“对比烘托”的手法来写人,以动物的有情有义来反向观照现代人性的虚伪和自私。在现代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人类道德滑坡和精神萎缩的时代弊病逐渐浮出了现实地表。进入新世纪以来,从《一腔废话》《手机》到《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刘震云的小说一直在言说着这种现实的焦虑,虽然他并没有也难以找寻到拯救的良方,但作为一名当代作家,认为自己必须承担起“看到、触到、抓到现代的终极悖论时刻”[13]的历史责任,坚守住“道德审判被延期的”[14]精神领地。因此,在新作《一日三秋》中,他对这一“希望用文字达到而未曾达到”的国民性批判与诗性救赎再次进行了书写、演绎和阐释。
二、“刘氏”黑色幽默与世俗时代的人生本相
“黑色幽默”这个风靡一时的后现代主义批评词汇是法国批评家布勒东的“发明”,指的是用幽默/喜剧的方式表现黑色/沉重的内容(即悲剧、死亡、痛苦和绝望等具有负面色彩的内容)。从初登文坛到获得茅盾文学奖,黑色幽默是刘震云小说创作中一以贯之的叙述风格,但他笔下的黑色幽默并不是西方后现代主义“作坊”里的复制品,它宅兹中国、扎根本土,从河南民间诙谐文化的宝库中汲取艺术养分,具有独特的审美风韵和思想质地。刘氏黑色幽默以拧巴式的“语言”作为存在的寓所,以诙谐风趣的叙事腔调和写作手法为通道,在现代生命的废墟上,对悲剧性的命运、失落的精神世界、浪漫的诗性理想、分裂的言说主体进行反讽、戏谑、去蔽和烛照,给予读者难以忘怀的情绪体验和思想启迪。这种别具一格的黑色幽默艺术延续到了刘震云的新作《一日三秋》之中,作家通过“变与不变”的艺术探索和美学承继使烦恼人生的喜剧外壳与悲剧本质得以显现。
细读小说文本,最先映入读者眼帘的黑色幽默表征是反英雄式的人物塑造和混乱化的时空建构。在小说《一日三秋》中,无论是主角陈明亮,还是配角陈长杰与李延生,他们都不是顶天立地、“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的伟大英雄,与其他作家笔下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意识和人道主义精神的正面形象也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他们是各种矛盾心理和复杂性格的聚焦体,时而正义凛然时而又逃避怯懦,时而大公无私时而又薄情寡义,时而坚守至善至真的人性光辉时而又高举精神胜利法的旗帜,在飞短流长、鸡毛蒜皮的世俗庸常中演绎一场又一场令人啼笑皆非的喜剧或闹剧。“李延生武汉之行”是小说前半部分浓墨重彩书写的一个情节片段,在武汉安身立命的陈长杰,念及往日情谊,邀请李延生到武汉来参加他的二婚婚礼,这本身是件好事,但在李延生这里却犯了难,因为“去武汉来回的火车票一百多块钱;参加陈长杰的婚礼,随礼起码得五十块钱;加起来快二百块钱;而李延生每月的工资才六十五块钱;去一趟武汉,两个月的工资都不够”[15]。李延生虽然重情重义,但生活拮据、老实惧内的他只能在慨叹“奈何,奈何?咋办,咋办?”[15]之余,给陈长杰写信谎称自己脚崴了,不能下地。戏剧性的是,一个月后,由于樱桃的附身,李延生不得不去见陈长杰。为了不惊动妻子胡小凤,顺利往返武汉,李延生可谓是绞尽脑汁、花样百出,开启了一场一波三折、笑料百出的借钱之旅。刘震云对李延生的“撒谎”行为与“借钱”之旅进行了“运镜”特写,以幽默诙谐的笔法把特定时代下优柔寡断、懦弱萎顿和敷衍逶迤的国民劣根性描绘得淋漓尽致,并由此折射出社会底层民众的生存焦虑、情义羁绊、人伦变异与精神创伤,以及在面对现实生活的桎梏约束和人情冷暖时的渺小、妥协、无助和辛酸。黑色幽默小说往往“摒弃了传统意义上的时间和空间的概念”,使“小说的现实性被大大削弱,虚幻性和荒诞性却因此而增强”[16]93,在小说《一日三秋》中,不仅现实时空(陈明亮等人日常生活的时空)与幻想时空(花二娘的传说统摄下的时空)杂糅交错,而且历史文化时空也与现代生活时空混淆叠合,如被长江之水卷走的樱桃鬼魂,竟然穿越到了一千多年前的宋朝,并神奇般地复活了,作家以樱桃的鬼魂为纽带把上个世纪的武汉和宋朝的九江这两个迥然不同的时空连接在了一起,两个时空对接所产生的反差和荒诞效果,使读者在 “发出上帝般的笑声”[16]94的同时,也领悟到人生只不过是一场悲喜交织的幻梦。
其次是反讽手法的运用。在小说《一日三秋》的文本中,反讽叙事的笔法可谓是俯拾即是,如戏剧《白蛇传》中饰演白蛇的樱桃和饰演法海的陈长杰在现实生活中成了夫妻、瞎子老董算命的屋子被他称作“太虚幻境”、找老董算命的人太多需要提前“挂号”、老董召唤神灵鬼怪上身与活人通话的过程被美其名曰为“直播”。这些对经典文学作品《红楼梦》和对民间传说《白蛇传》的戏拟与滑稽模仿、对医院术语和网络用语的情境误置,构成了小说反讽叙事装置的重要组件。此外,小说还通过大量的言语反讽来架构小说幽默叙事的轻逸空间。如陈长杰给樱桃和李延生讲戏,调侃“《白蛇传》的戏眼,是下半身惹的祸”[15],这句令人捧腹大笑的戏谑之语又何尝不是对陈长杰由戏结缘的两段婚姻所导致的人生悲剧的反讽?当然,在小说《一日三秋》中也不乏“总体反讽视阈下的命运悲歌”[17]。“总体反讽指涉的是人类总体的存在处境和终极命题”[18],“诠释‘存在处境’和‘终极命题’避不开的就是人类的‘命运’”[17],而对人类命运的言说恰恰构成了我们探索人生之谜的关键一环。因此,“总体反讽”总是以轻盈的叙事技巧抵达生命存在的沉重之思。可以说,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是命运反讽下的牺牲品:花二娘在延津人的梦里索要笑话,却始终不知她苦苦等待了三千年的情郎早就死在了延津人的笑话中;生前不会讲笑话,被笑话“压死”的吴大嘴,为了博阎王爷一笑,获得投胎转世的机会,苦练成为讲笑话的高手,而曾经以讲笑话为拿手好戏的陈长杰却在高压的生活环境中丧失了讲笑话的能力;年轻时横行霸道、为非作歹的孙二货到头来成了一个痴呆老人,他满嘴胡话,连人都认不清了,却还挂记着自己来世他生的前途命运;靠扫大街供儿子出国留学的郭宝臣并没有因为儿子的出人头地而安享晚年,他的儿子郭子凯以“中英文化差异”这个荒唐的理由将他“遗弃”在了养老院里。这些人物不管男女,无论善恶,都被命运捉弄,活成了一个荒诞的笑话。红尘尽头,繁华落幕,所有的前途命运、金钱名利和爱恨情仇其实都只不过是一场空,而能够在我们生命旅途中留下痕迹的往往是那些人生重要时刻的情感体悟和思想启迪,这种情感体悟和思想启迪包含着我们对故乡的思念、对亲朋好友的牵挂与爱恋、对生命存在意义的顿悟、对世间万物的关怀以及对烦琐人生和苦难命运的乐观与通透。正是因为这些重要的时刻承载着如此厚重的生命馈赠,所以它们的每一瞬间对我们而言,都是一日如同三秋。作为现代人类的我们经常遗忘了这些重要的人生时刻,丢弃了厚重的生命馈赠,于是我们在寻找“笑话”的路途中活成了笑话。
再次是拧巴式的语言风格。“拧巴”是新世纪以来频频出现在刘震云的小说创作及其研究成果中的一个重要关键词,正如曾军所言:“在《我叫刘跃进》的写作中,刘震云明确将……河南式幽默概括为‘拧巴’,并在后来的《一句顶一万句》中将这种‘拧巴’的河南式幽默发挥到了极致。”[19]“拧巴”这一北方方言与汉民族共同语中的“别扭”一词含义较为接近,也可以将其理解为不顺畅、不搭配、不协调,或纠缠错乱的意思。所谓“拧巴”式的语言风格,是指打破常规的词汇搭配和句式语法的章程,充分调动汉语词汇错综复杂的词性、色彩和语义,使其笔下的语言文字呈现出陌生化、缠绕不休和迂回幽默的特征。刘震云之所以在他的小说中不厌其烦地采用拧巴式的语言,是因为在当今这个时代,“世人无不处于拧巴的生存状态,伦理道德的坍塌衰微乃至荒诞虚无似乎反而成了生活的恒常本质”[20]。拧巴式语言一方面以其形式的迂回缠绕、荒诞诙谐瓦解了小说文体的庄重与和谐,使之呈现出幽默风趣的调性,另一方面反映了纠结杂乱的生活伦理和吊诡离奇的命运逻辑对人们思维模式和言说方式的深度影响,展现出语言和生活的异质同构性。在小说《一日三秋》中,拧巴的语言风格主要体现为折绕句的使用。“折绕”在陈望道看来,是一种修辞格,指“有话不直直截截地说,却故意说得曲折,缴绕”[21]。折绕句在刘震云的小说中十分常见,《一日三秋》也不例外,如“既然是一个人,李延生不去,也没有什么特殊;但正因为是一个人,不去就显出来了;显不显得出来不打紧,既然只通知他一个人,可见把他当成了在延津唯一的朋友,不去就显得不仗义了”[15],“只是一张火车票,要坐两个人;看着是一个人,其实是两个人;跟人说,人不会信,会说他疯了;事情有些荒唐,但实际情况就是这样;如是别人遇到这事说给他,他不会信;现在他把同样的事说给别人,别人也不会信”[15],都是典型的折绕句。这些拐弯抹角、芜杂缠绕的句子将李延生矛盾纠结的心理写得入木三分,也将凡尘俗世里千丝万缕理不清头绪的人际考量和情理纠葛,以及错综复杂、混乱拧巴的生活逻辑展露无遗。
三、结语
无论是20世纪80年代末以客观的写实风格和尖锐的讽刺精神为大环境下小人物的烦琐人生立照存言的《一地鸡毛》,还是暌违四年、重返写作原乡,以魔幻现实主义的笔法和黑色幽默的创作技巧为当代社会晦暗的生活角落点一盏明灯的最新力作《一日三秋》,都殊途同归地展现了刘震云文学世界里始终“在场”的人文关怀与现实观照、对生命本真命题的恒定性探索以及对人类存在与虚无之谜的未竟找寻。由此可见,在几十年漫长的写作生涯中,刘震云一直坚守着现代小说家的终极使命——对人类本真生命的存在体进行智性勘探和诗性“道说”,从新写实主义到本土化的魔幻现实主义,他从未停止过以笔墨丈量世界和用语言刺破黑夜来进行文学求索之旅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