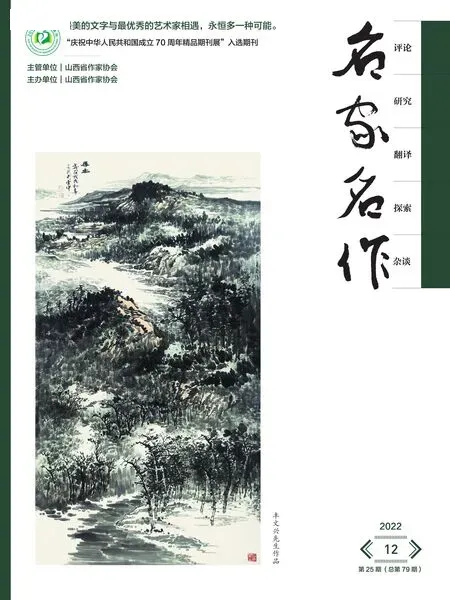厄格罗绘画中的极简色块研究
——以人物油画为例
郭 筠
尤恩·厄格罗是继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和卢西恩·弗洛伊德(Lucian Freud)之后英国当代画坛公认的大师之一,其作品在艺术形式上独树一帜,哲学思想与艺术美感达到高度的统一。众多研究者或对其别具一格的“+”极致考究的测量方式进行探讨,或对其画面中的透视画法及几何结构进行构图研究,而笔者希望从厄格罗的艺术生涯中改变最为明显的色彩入手,对画家具象绘画中的极简色块进行探索式研究。
一、色块下的理性精神
在厄格罗的作品中往往能看到画家放置在空间环境中的单个对象,它们可能是日常生活中的各式水果,或是插在花瓶里的一枝花,抑或是各种姿态的人体模特,反之极少出现场景性的画面。这种绘画方式与古希腊雕塑中延续下来的古典理性精神极为相似,用理性的素描、宁静的色彩,追求画面的秩序感。
画家常选取站立或端坐的人物,从人物的小幅度动作及严肃表情,遵循模仿自然与理想化结合的现实主义法则,即理性严谨地分析人体结构,表现出古希腊人神合一的精神追求。《无辜者的大屠杀》中是厄格罗临摹普桑的作品创作的,他用理性的平面化色块概括激荡人心的情节,这样的提炼与升华,把原本静穆、崇高的历史画面变为形式的分析,增强了 “简约”的现代感。从两幅风格迥然不同的《无辜者的大屠杀》可以看出厄格罗“均衡、稳定、简洁”的艺术理念是对传统的继承,但其表现却有别于古典大师。普桑所追求的古典主义要求表现理想化的境界,强调美的基本原则是协调和单纯。相比而言,厄格罗绘画中的画面更加简洁,去掉了多余的修饰,把具象的事物理性地分解为色块的衔接。他追求的“均衡、稳定”不单单是构图的稳定,更多的是作品中造型、色彩、内在结构和外在形式等各要素的和谐。
厄格罗这种对古典主义绘画作品理性的继承,受现代主义意味的构成美感影响,“现代艺术之父”保罗·塞尚同样受普桑影响,画面大多以几何化形式构成,画中充满了线条、形式、色彩和体积之间的关系,被认为是“原始的单纯 ”①王南溟:《现代艺术与前卫克莱门德·格林伯格批判理论的接口》,上海大学出版社,2012。。以毕加索为代表的立体主义画派,吸取了保罗·塞尚这种用几何图案对形象进行处理的绘画方法,抛弃传统的三维空间透视表现方法,对空间和对象进行分解后重构,形成分析立体主义。②艺术家将物象进行拆解,将人或物各个面向的形象同时置于一个画面中,直接的视觉效果就是一个个块面凌乱地堆砌在一起,色彩被缩减到近乎单色画的灰黄、灰绿调,而物象的实际形象则是通过对某个局部特征符号式的描绘被暗示出来。厄格罗的恩师威廉·孔德斯居姆,继承了这种理性思维画面所呈现出的严谨的写实风格,对物体和画面反复对比,以画笔为测量工具精准测量,因测量而留下的水平和垂直的痕迹,往往停留在物体转折的部位,形成独具一格的绘画风格。厄格罗的绘画受到了这种理性思辨的影响,造就了其庄严静穆、严谨理性的个人风格。
二、平面化色块对形体的塑造
厄格罗在进行艺术创作时往往会避免随意化,克制感性成分,运用严谨的测量方式精心安排、描绘画面中的每一个细微之处,色彩的处理手法表现了他注重对几何块面的塑造。这种绘画效果使描绘的物象的边缘看起来像是被刀片切割过一样,与画面整体的几何形式感相辅相成,画面整体散发出一种类似于古希腊雕塑般精简而理性的质感。在其绘画后期,他在严谨的测量方法的基础上,将大小不一的色块通过不同颜色衔接出具象的绘画,实现了由古典到现代性色彩的转变。
纵观画家的绘画历程,改变最明显的无疑是由古典向现代性色彩的转变。从厄格罗早期人物绘画《站立的裸体》(如图1)中可以看出受罗杰斯对物体的块面塑造、孔德斯居姆线性元素及测量方式影响较大。在此时期,厄格罗绘画中出现众多的坐标痕迹,它们以曲线停留在人体肌肉的交界处,或者以短线标记在骨点的转折处。经过严谨测量及理性分析,厄格罗将被描绘的物象安置在充满坐标结构线的空间中,达到三维空间感。此时厄格罗绘画中的颜色厚重且色调统一,有典雅的古典韵味。但从厄格罗1957年的作品《苏珊坐姿》(如图2) 中可以明显看出,有别于1951年所画的《站立的裸体》,此时的他在严密的标尺测量手法基础上寻找色彩对形态的塑造力,整个人物都笼罩在绿色的氛围中,红色皮肤的人和大面积的绿色形成对比,端坐在椅子上的女性通过亮部的冷色和暗部的暖色拼接形成立体感,古典主义细腻柔美的色调下初见色块分析的端倪。

图1 《站立的裸体》尤恩·厄格罗/作

图2 《苏珊坐姿》尤恩·厄格罗/作
根据个人访谈可追溯到“现代主义之父”保罗·塞尚对画家的影响,保罗·塞尚希望用色彩重新创造自然,后印象派主义不再是印象派或是新印象派风格的延续。他认为,素描是正确使用色彩的结果。①[美]阿纳森:《西方现代艺术史》,邹德侬、巴竹师、王挺译,人民美术出版社,1994。保罗·塞尚在印象派的基础上对色彩的运用具有理性的逻辑分析,他将色彩视为造型表现的重要组成部分,运用近乎数学的抽象以表现各个平面间结构的和谐均衡,基于理性客观物象进行简化与重构,将杂乱无章的客观物象归结为简洁的几何化形体以传达绘画的内在精神。例如,《红色扶手椅中的塞尚夫人》(如图3)中,保罗·塞尚通过色彩的冷暖对比表现人物身体各部位的结构起伏,脸部受光的暖肉色、暗部藏在阴影下的冷青色、衣服在阳光的照射下产生紫色的色块与背光的黄绿色的对比等用色块直接营造体积。虽不同于传统学院绘画中所强调的重素描轻色彩的思维模式,但是整个画面构图严谨、色彩饱满、造型结实,在丰富的冷暖对比中显示出强烈的整体感和空间感。将厄格罗和保罗·塞尚相似的作品进行比较,可以感受到厄格罗虽崇尚意大利古典绘画,注重对画面感的把控,展现出理性下的真实感受力,但画面开始走向简约且有秩序感的色块。

图3 《红色扶手椅中的塞尚夫人》 保罗·塞尚/作
三、形式简化带来的构成美感
格林伯格曾说:“封闭的画框和色彩都不是绘画所独有的,唯有二维平面性是绘画特有的条件,不属于其他艺术。”因此,现代主义绘画必然朝向平面性,并提出了“形式简化”原则。厄格罗后期作品在以色塑性的基础上,用简单的色彩层次强化画面的明度与纯度,构成了富有张力的画面色彩,使画面达到一种既和谐又有冲击力的氛围。
厄格罗真正的色彩革命开始于1964年,《裸体与绿色的背景》相较前期作品,色彩的厚重感减弱,明度提高,色彩倾向明显。厄格罗认为:“这幅作品是我离开艺术学校后画的真正严肃的画之一,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这是一种自由,这是我想要画的最‘抽象’的画面,这只是一件自由的作品。”②王宇航:《理性的构成之美——尤恩·厄格罗作品分析》,硕士学位论文,中国艺术研究院,2022。将厄格罗后期的作品《女孩和树》(如图4)与色域画家马克·罗斯科的绘画作品《无题2》(如图5)进行对比,可以更为直观地看出厄格罗绘画中的抽象色块。马罗·罗斯科认为,绘画应尊重其平面化的本质特性,而不是特意去创造一个三度空间的幻象。运用理性的观察方式分析物体结构,抛弃造型、光线、景深、 形状等传统绘画语言的因素,将复杂的事物极简化凝练。

图4 《女孩和树》尤恩·厄格罗/作

图5 《无题2》马克·罗斯科/作
厄格罗曾经说过他也欣赏那些似乎与他的绘画主张背道而驰的艺术家:波洛克、纽曼,以及罗斯科等。③冯长根:《尤恩·厄格罗绘画的几何形式语言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曲阜师范大学,2020。厄格罗也许从他们那里获得了对几何化形态和色彩平面形式的理解,他运用对现代艺术的哲学思考完成画面,将光色进行压缩形成色域,在不破坏原本物体构造的情况下,用简洁的色块塑形,在理性与构成中来回游走,创造出新的艺术形式。从《女孩和树》中可以看出人物的头部、躯干及背景均有明确的色彩倾向,几个明显的大色块构成了画面的色彩结构,与马罗·罗斯科的绘画相似,试图通过明暗减弱主体物与背景的界限,将笔触减少,追求画面的平坦性,使其充满宁静,达到一种哲学上的高度。
四、简约美感背后的思想性
厄格罗在描述自身创作时曾说:“我是在画一个思想而不是一个理想,我基本上是在尝试画一幅布满控制意识的、有力而和谐的、有结构的作品,我不会让机会躺在那儿,除非它已经被征服,假如我以为它不能陈述什么,我不会有意留下一笔。”①刘茂营:《以几何元素构建古典性 ——厄格罗艺术特色研究》,《美术文献》2020年第11期,第56-57页。从作品名字很容易发现,艺术家绘画的主题多是私人的情感和凄美故事,画作不仅表述着他的艺术理念,还承载着其精神内涵的流露,能唤起观者对时间流逝的关注和对生命永恒的思考。
《支撑》中厄格罗抓住了女士沉思的瞬间,注重刻画模特的内在精神,对色彩和造型做了相应的减法,并进行有意味形式的加工,大面积明亮的黄色烘托出少女情怀,引发观者猜想。相似的色调在厄格罗的晚期作品中表达的感觉却截然不同。在《双正方形,双正方形》中,厄格罗虽然也运用了不同色度的黄棕色,但在这幅画中,这些色彩组成的是孤寂的氛围。苍凉的色调笼罩着模特,模特蜷缩着的身体象征着对时光流逝的无力,印证厄格罗弥留之际的心态,寄托着在有限的生命里追求无限的精神内涵。
厄格罗在形式美的基础上,用微妙的色彩构建着对生命不同状态的思考。简练的色块用最质朴的形式将物象的本质呈现在观者面前,在创造美的同时,将对哲学层面的认知展现出来,与观者形成一种精神层面的交流。
五、结语
“绘画性”中形式感的产生,对创作者的主观创造力和视觉敏锐度都有着非常高的要求,确保艺术作品既符合基本的美学规律又能赋予其相对鲜明的个性化特征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厄格罗对传统艺术进一步反思,提炼前辈的艺术精华,用理性的观察方法描绘物象的本质的同时,用抽象色块链接的方式赋予物象体积,打破传统绘画的明暗对比和阴影的绘画方式。 这种对色彩近乎苛刻的精确度,使厄格罗在绘画语言上有极强的雕塑感及明亮的诗意。在创造美的同时,厄格罗也将哲学认知埋藏在具象之下,使作品与观众产生精神层面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