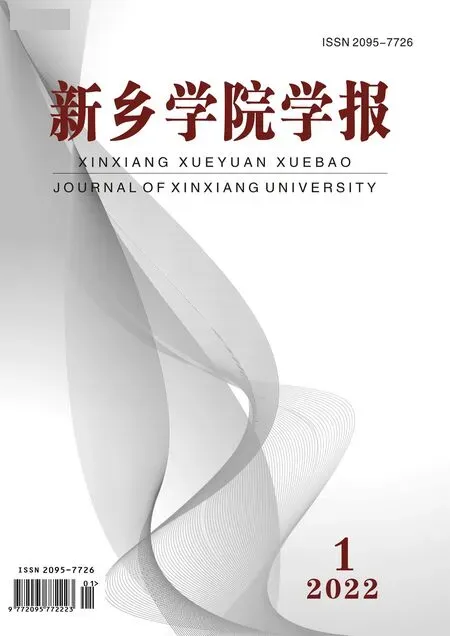基于柏拉图“洞穴之喻”的现代人囚徒困境分析
汪 红
(沈阳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4)
现代人因为个体局限性而无法走出自己的思维洞穴,常常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错失良机或做出错误选择,这就是现代人的囚徒困境。“洞穴之喻”是柏拉图哲学中的一个著名寓言,在这里柏拉图指出了现象世界和理念世界的对立,认为至善是人类永恒的价值追求,是指引人类从现象世界走向理念世界、摆脱蒙昧的“太阳”。深刻理解柏拉图“洞穴之喻”的思想内涵,可以帮助现代人打破囚徒困境,更好地把握世界运行的客观规律,提升对世界的认知水平。
一、柏拉图“洞穴之喻”的思想内涵
柏拉图在《理想国》第7卷中借苏格拉底和格劳孔的对话提出:“我们把洞穴换成可见世界,火光替换成太阳的能力,还有把从地穴到上面世界并在光亮之下看见东西的一系列上升过程替换成灵魂上升到可知世界的上升过程。”[1]223在这里,柏拉图将世界区分为可见世界和可知世界,可见世界指人们眼睛看见的实在物,可知世界指善的理念世界。可见世界和可知世界又各分为两部分。可见世界的第一部分是影像,即人们周围的动物、植物以及一切可见物的影像,这部分对应人的心理活动是想象。第二部分是实物,即人们周围的动物、植物以及一切可见物,这部分对应人的心理活动是信念。信念不是知识,是一种基于对客观存在的认识,它还没有上升到知识范畴,属于意见范畴。可知世界也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一种科学性的数理概念,它的对象并不直接可见,需要通过一定的逻辑推理演算才能获得,暂且称之为理智。第二部分是善的理念,这部分内容已经上升到哲学领域,无论从哪个维度看它都是最高范畴,可以说已经达到了真理,但比真理更为可敬。除了上述区别,可见世界对应人的灵魂状态是想象和信念,可知世界对应人的灵魂状态是理智和理性[1]217—219。从人的认知能力的发展看,可见世界对应的是人的感性认识阶段,可知世界对应的是人的理性认识阶段。
“洞穴之喻”是柏拉图在《理想国》第7卷提出的。书中假设一群人从小生活在洞穴中,他们的脖颈和手脚被捆绑着无法转动。他们身后有一堆燃烧的火,横贯洞穴有一条小路,路边建有一堵矮墙。由于洞内的囚徒只能看到火光投在洞壁上的影子,于是他们认为影子就是真实的世界。有一天,一个囚徒挣脱绳索,磕磕碰碰地走到洞口,发现外面有阳光的世界才是真实的世界。当见过外边真实世界的囚徒回到洞穴告诉洞内的人真相时,洞内的囚徒们无法接受这一现实,他们心中的精神支柱突然崩塌,宁愿杀死去过洞外的人,也不愿意承认外在本真世界的存在。在这里,柏拉图说的那个去过洞外的人,其实指的是自己的老师苏格拉底。虽然他知道自己回到洞穴会面临许多困难,甚至可能会被杀死,但他依然坚定地回到洞穴告诉囚徒们洞外的真实世界,这就是哲学家的使命,即立志帮助民众走出洞穴并升华他们的思想。
解析柏拉图的“洞穴之喻”可以发现,它的每个喻体都有不同的内涵指向。其中,“囚徒”象征现实生活中那些不进行深入思考的人,他们所处的世界如同黑暗的洞穴,因为被周围的人和环境所迷惑,被这些“锁链”束缚而无法转身、无法站立行走,看不到真实的世界。“影子”象征人类通过视觉、听觉、触觉等感官形成的认知的狭隘性。虽然影子是一种具有迷惑和欺骗性的假象,但是在全身都被紧紧捆绑的囚徒心目中,影子就是真实的存在[2]。这时如果有一个智者来引导囚徒,他们就不会被“影子”所蒙蔽,将会成为能辨别真伪、积极向上的人。挣脱绳索、走出洞穴的人象征愿意接受教育、追求真理的人,柏拉图称他们为智者或哲学家。哲学家“以至善的理念作为指引,使得个体不断实现自身灵魂内部的和谐,以及与整体宇宙的联结、协调,以此引领个体不断超越自我的自然局限,实现灵魂的不断上升和视野的不断拓展”[3]。
二、现代人的囚徒困境
虽然柏拉图的“洞穴之喻”距离今已有2000多年,但其中蕴含的深邃思想历久弥新,它能帮助我们寻找现代人产生囚徒困境的原因。
(一)基于经验主义的盲从
柏拉图“洞穴之喻”中的囚徒,基于经验认为洞壁上的影子就是真实的存在。现代人在成长过程中,虽然从咿呀学语开始就受到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的熏陶,但很少有人对其正确与否进行思考。这就是说,所有人都相信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是正确的,即使有人产生怀疑也会受制于环境而否定自己的观点。如此一来,人们如同洞穴中的囚徒一般,思考能力逐渐弱化,判断力和鉴別力逐步下降,认为影子就是真实的世界,同伴的说法就是真理。人们从小被灌输的观念一旦内化为一种信念,就会成为枷锁牢牢困住人们的思维。这种思维的“洞穴”造成人的无知,使人无法获知真理,在学习和工作时无法取得进步。
(二)路径选择时产生错误
柏拉图“洞穴之喻”假设走出洞穴的囚徒回去后质疑洞壁上的影像,绝大多数囚徒会认为他疯了,都嘲笑和讽刺他,甚至想杀掉他。如此一来,洞内的囚徒会更加认同同伴的观点,错误的知识在其大脑中的印象会更加牢固,进行决策时就会采取从众行为。正如《理想国》第6卷中所讲:“难道您不认为脱离知识的意见看起来实在很盲目吗?即便挑出其中最好的也是盲目的。换句话说,那些脱离理性来发表意见的人,与那些碰巧走对了路的盲人有什么差别?”[1]212现代人由于知识量的差异与思维固化程度的不同,在看待一件事情时会形成不同的观点,进而做出不同的选择。比如,在寻找职业时,知识量不够的人往往忽视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选择职业时犹豫不定且容易受他人意见的影响,结果就会经常做出错误的选择。
(三)本领不足产生的畏惧与逃离
“洞穴之喻”中走出洞穴的囚徒一时不能适应洞外的阳光,他眼冒金星,非常难受。因为洞内的火光和洞外的阳光相差甚大,囚徒的眼睛常年感受弱光,习惯了洞内的黑暗环境,一旦站在阳光下,他的眼睛感到刺痛、胀疼,甚至觉得会失明。这时,囚徒一定会产生恐惧心理而想逃回洞穴去。这种情况放在现代人身上,那些不愿接受新事物,不愿打破自己的思维瓶颈而故步自封的人,也会有这种心理。他们害怕自我提升过程中的艰辛和劳累,在思想和行动上都会产生巨大的排斥心理。比如,现代职场人面临工作压力,学生面临升学压力时,都会因能力不足产生恐慌心理。一旦面临的压力超过自己的心理承受能力,当事者就可能快速逃离该领域。
三、现代人的囚徒困境解析
现代人根据自己的固有经验开展行动,在选择时经常做出错误决定,做事时由于能力不足经常产生畏惧心理,那么,人们为什么会深陷柏拉图所说的囚徒困境而无法自拔呢?
现代人陷入囚徒困境在于不能获知善的理念。柏拉图认为“善是知识和真理的源泉”[1]216,囚徒们无知的原因在于不能获知善的理念。为什么囚徒不能获知善的理念?原因在于善的理念只存在于可知世界之中,而囚徒们的意见处于可见世界。按照柏拉图的观点,善的理念只存在于洞外有太阳的世界,现代的“囚徒”们因为从小受社会历史条件的束缚而被禁锢在思维的“洞穴”之中,所以无法认识善的理念,无法砸碎枷锁而获得更多自由。
现代人陷入囚徒困境的原因在于错知和少知。与绝大多数囚徒赞同洞壁上的影子就是世界的全貌一样,现代人也很少质疑他人的观点。缺少独立思考,就容易产生错知。少知是由于现代人未能获得足够的知识,知识储备不足以解决自己遇到的问题。无论错知还是少知,都会使人无法走出思维的洞穴,只能徘徊于可见世界与可知世界之间而无法进入善的理念世界。按照柏拉图的观点,洞内的感觉世界和洞外的理念世界的差异在于“前者是杂多的、相对的、变动的、暂时的,后者是单一的、绝对的、不动的、永恒的理念”,“对于洞穴内的人来说,不仅洞外的真实存在对他们是隐而不显的,而且他们对于洞内/洞外的差异也是一无所知的”[4]。
囚徒之所以惧怕洞穴外的阳光,是因为适应洞穴外的世界是一个艰苦的过程。囚徒习惯了之前黑暗的、只有微弱光亮的生活,突然来到洞外阳光普照的世界,一下子变得难以适从。刺眼的阳光,使囚徒睁不开双眼,精神上自然产生对太阳和外部世界的恐惧。柏拉图认为:“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他只能一步一步慢慢学会在洞穴外面的高处看东西。 ”[1]221-222现代人习惯于固定的工作模式,喜欢做简单轻松的事情,如果突然让他做难度高的工作,就会感到艰辛和痛苦。因而,现代人之所以陷入囚徒困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能忍受从感性认识阶段进入理性认识阶段的艰苦过程。正如柏拉图所言:“灵魂在学习中的艰辛和痛苦要远远高于体力劳动,这种痛苦只有灵魂体会得到,而肉体体会不到。”[1]243
四、摆脱囚徒困境的路径选择
理解了柏拉图的“洞穴之喻”,现代人只有不断冲破思想的牢笼,积极求知,勇于超越自我,才能摆脱囚徒困境,找到自己人生的阳光。
(一)解放思想,突破思维的枷锁
解放思想是走出囚徒困境的第一步。世界变动不居,人的思想也要与时俱进。正如《易传·系辞下》中所说:“《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5]如果人的认知和思维方式不能因时而变,人就会像柏拉图笔下的囚徒一样活在影子世界当中,永远看不到真和美的东西,更看不到善。所以,在现实生活中人只有与时俱进,才能打破思维的枷锁,实现自我发展。同时,按照柏拉图的灵魂回忆说,每个人的灵魂“天然地曾经关照过永恒真实界”[6]34,只不过灵魂在进入肉体时被玷污了,遗忘了各种知识,需要通过一些具体事物进行刺激,让灵魂产生回忆,即“从杂多的感觉出发,借思维反省,……这种反省作用是一种回忆,……举头望见永恒本体境界那时候所见到的一切”[6]33。因而,只要解放思想,就能打破固化的思想藩篱,使人的大脑得到放松,“回忆”起更多的知识。
(二)注重教育是关键
柏拉图认为人出生前灵魂已经拥有理念知识,只是出生后由于受到种种条件的限制而忘记了。除了第一个走出洞穴的人,洞内的“所有囚徒都缺乏自我解放、转离变化世界、凝视能够认识真正实在的能力”。“面对心灵无法自主转向的欠缺”,教育作为一种使“灵魂转向”的技艺被人发明出来[7]。教育就是要引导灵魂走出洞穴,从洞壁的影像开始,先看到火光,再看到洞口,最后看到阳光下的世界[8]。就此而言,“洞穴之喻”揭示了人是否受过教育的差别:受过教育的人能见到真实世界,能真正看到善,从而成为最幸福的人;而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只能生活在洞穴之中,只能看到影像而看不到真和美的东西,永远是不幸的人。因此,对现代人而言,通过教育,特别是自我教育能帮助人们“回忆”起和具体事物相关的知识,从而发现人的禀赋、提升人的能力,防止把他人的错误知识当作真知,避免因知识不足而选择错误,让每个人做好与自己能力相一致的事情。
(三)用理性控制欲望
柏拉图认为教育能使“灵魂转向”,此过程需要理性的引导,只有让理性占据主导地位,才能使激情服从理性并协助理性制约欲望,进而达到教育的目的。在《斐德若》篇中,柏拉图写到人的灵魂分为三个部分——灵魂、激情和欲望,好马代表激情,顽马代表欲望,御车人代表理性。就人类来说,御车人同时要驾驭两匹马,其中一匹驯良、一匹顽劣。好马在驾驭过程中只需御车人进行劝导,而顽马则要御车人随时鞭打脚踢,因为如果不对顽马进行长期管束,车辆就会随时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现代人在学习和工作中同样如此,也必须用理性控制自己的欲望来保证正确的前进方向。因为在理性和欲望的较量中,一旦人的灵魂被欲望所掌控,人便会随心所欲而自我放纵,必然会使工作和学习与预定的目标相背离。所以,我们要让理性随时管教、鞭笞那匹顽马,尽可能减少顽马不听话的次数。也就是说,要让理性为人们的灵魂掌舵,最理想的状态是让灵魂马车无车可拉,灵魂深处不再有良马和顽马[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