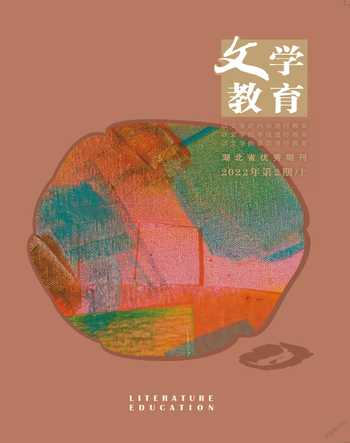认知暴力视角下《所罗门之歌》中的派拉特形象
林羽璇
内容摘要:托妮·莫里森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非裔女作家,其黑人女性作家的身份赋予她独具匠心的写作视角,她的作品也揭示出黑人女性真实的生存困境。自1997年出版以来,《所罗门之歌》就受到了众多读者的关注与好评。国内外学者对于《所罗门之歌》的文学研究主要集中于对主人公奶娃的解读,而小说中的女性小人物,如奶娃的姑姑派拉特,则有待挖掘。本文基于后殖民主义理论,尝试以斯皮瓦克的“认知暴力”概念分析派拉特的边缘困境及其在困境中所患的“失语症”,并在此基础上解读派拉特在困境中的反抗与其对文化身份的探寻。
关键词:《所罗门之歌》 派拉特 认知暴力 边缘困境 失语症
《所罗门之歌》以黑人飞行的神话为基础,讲述了黑人的寻乡之旅,展现了美国北方与南方的冲突,并批判了其背后的种族对立,是莫里森的代表作之一。后殖民理论对于《所罗门之歌》的解读有着重要作用,而斯皮瓦克的“认知暴力”这一概念,对于小说人物的研究有着重要参考价值。斯皮瓦克曾在其著作《属下能说话吗》中将认知暴力定义为“把殖民者主体构成他者的计划”(100)。由此,被殖民者被孤立于社会及政治权力之外,沦为了“属下”。伴随着权力的丧失,被殖民者的话语权被瓦解,属下便不能“说话”了。
小说中对于派拉特的着笔不算多,但笔者认为她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富有魅力的,对自由与平等充满激情与向往的女性角色。值得一提的是,派拉特的名字与英文单词“飞行员”相似,且派拉特虽然一穷二白,但无论去哪儿都携带地理书,因此部分学者认为派拉特一生都在追寻自由的旅途中,是“黑人文明的代言人”(王守仁 84),同时也是主人公奶娃的寻乡之旅中的“引路人”(Peach 68)。然而随着对文本的深入探索,不难发现派拉特这一人物的悲剧性,其追求自由平等与保护黑人文化遗产的旅途与风雨兼程:她实质上被孤立于白人社会,黑人社区,甚至是戴德家族之外,因而是斯皮瓦克眼中游走在社会边缘的“失语的属下”。
本文拟借助后殖民主义理论中认知暴力这一概念,分析派拉特的边缘处境,揭示派拉特在边缘化的过程中出现的“失语症”,并进一步解读派拉特如何在被殖民主义,消费主义与男权中心主义所渗透的社会中,重塑自己的黑人文化身份,并重获自主话语权。
一.孤立于中心之外——边缘的飞行者
“斯皮瓦克的使用中,‘认知暴力’指帝国主义以科学、普遍真理和宗教救赎这样的话语形式对殖民地文化进行排斥和重新塑造的行为”(李应志 60)。毫无疑问,这种形式的“软暴力”(61)会导致被殖民者文化主体性的逐渐沦丧,进而造成被殖民者被排挤至文化中心之外的边缘化处境。在《所罗门之歌》中,派拉特作为一名黑人女性,正反映了当时其所处阶级的真实境况:在父权制与帝国主义“两座大山”的排挤下夹缝生存,苟延残喘。
小说中,派拉特是一位被赋予了神秘能力的传奇人物。在派拉特落地前,她的母亲已难产而死,然而,她挣脱了母亲的襁褓,带着她没有肚脐的“光滑肚皮”由一个深渊爬向了另一个深渊。她神秘又恐怖的出生,预示了她与其他黑人的隔阂。在某种意义上肚脐象征着“重复性”(龚莉岚 44),意味着一代代女性困于依附男性和繁衍生命这一循环的枷锁之中,进而暗示了女性应当安守本分地生活在这的禁锢之下,服务于以男性为中心的家族与社会里。派拉特一出生就没有脐带,这样神秘而明了的出场设定从一开始便寄寓了莫里森对她的厚望,希望她以反叛的血肉之躯去挑战男权中心主义所制定的规则。事实证明,派拉特确实没有让她的缔造者失望。不同于常人,派拉特的童年经历了家破人亡,手足失散,这个本能在爱与关怀中无忧无虑成长的女孩一夜之间被迫沦为孤儿。然而,这个苦命的人并没有向命运屈服,而是踏上了寻找家园与自我的航程。这一路颠沛流离,曲折离奇,派拉特使劲浑身解数,干了数不尽的脏活累活,只为了寻找自己的容身之处。但现实往往事与愿违,派拉特的勤劳,真诚,与热情换来的是本族裔男人的侧目与女人的碎语闲言:“那些男人叫她美人鱼,女人们把她的脚印打扫干净并且在她的门口悬上镜子”(莫里森 153);她独特的肚皮所象征的勇敢独立与反叛反而使她和她可怜的女儿与外孙女被孤立于黑人族裔之外。
派拉特不仅拥有非同寻常的出生与人格,还践行着自己独具一格的生活方式。小说伊始,莫里森就对奶娃的父亲麦肯·戴德的残暴形象进行了入木三分的刻画。在莫里森笔下,麦肯是那个时代一名典型的戴着“白面具”的黑皮肤商人。他视金钱为一切行动的信条,而视自己同胞的性命如草菅;消费主义金钱至上的冷漠价值观对麦肯精神的蚕食,使得他的良心与怜悯荡然无存。麦肯俨然已将黑人文化中友爱互助的价值观抛诸脑后,且对自己族裔所承受的痛苦视而不见。然而派拉特作为麦肯的亲姐姐却与其所秉持的冷血价值观大相径庭:她对西方文明以财富衡量成功的倡导嗤之以鼻;她与自己的女儿与外孙女在城市贫民窟里仅仅依靠自制酒水的生意与新鲜水果的采食维生;她所有行囊仅包括一袋尸骨,一本地理书,几颗石头,以及一个装有自己名字的耳飾。这种至简的生活方式背后,既体现了派拉特对于过往的密切联络,也是其对于塑造其人格的黑人文明之敬畏(Ahmad 66)。因此,尽管派拉特落户于一个现代化白人至上的城市,但仍然拒绝由白人倡导的消费主义观,拒绝购买工业化现代社会所谓的“必需品”(如燃气,自来水),并引领着一种纯粹又原始的,与现世格格不入的生活。
显然,派拉特从骨子里就带着的反叛及其独具一格的生存方式注定使这名女勇士遭受世人的隔绝,且被迫承受黑人文化与白人文化的双重排挤,在边缘奄奄一息地飞行。
二.陷入在沉默之中——失语的飞行者
在被边缘化并逐渐沦为“属下”的过程中,被殖民者的语言系统也同时被摧毁。“在父权制与岛国主义之间……妇女的形象消失了”,女性进而也陷入了失语的境地(斯皮瓦克 126)。这里所言的失语症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失去了发音能力”的病理症状,“而是指他们不能用自己的方式进行思考和文化表达”,进而“丧失了自己的文化主体性……从而被迫处于依附状态”(李应志 61)。小说中的女性人物亦是如此,她们难以从女性视角出发叙述自己的独特经历,更丧失了作为黑人族裔的文化主体性。
派拉特的童年恬静而美好,她的父亲老戴德用自己的真情实感紧紧维系着这个贫穷但有爱的三口之家,并经营着自己用汗水换来的富饶的“林肯天堂”。然而白人殖民者的贪婪觊觎终止了这个三口之家的丰收与天伦之乐,他们在“林肯天堂”这篇富饶的土地上暗杀了老戴德,让小派拉特一夜之间从天堂坠入地狱,迫使这个年仅几岁的孩子流离失所,开启了寻找自己的漂泊之旅。然而,派拉特一生也没能歌颂真实的自我:她错听了父亲对她母亲“兴”(Sing)的呼唤,误以为父亲在鼓励她歌唱,因而失去了母亲的名字;她没能理解“所罗门”(Soloman)的真正含义,误将“所罗门”歌唱为“售糖人”(Sugarman),从而失去了家族的名字。“售糖人飞走了,售糖人走啦,售糖人掠过天空,售糖人回家喽”(莫里森 50)。——她的歌声清脆响亮,愉悦了他人,却没能歌颂最真实的自我与灵魂。殖民者不仅掠夺了派拉特一家的钱财,也剥夺了她作为一名女性真实叙述自身经历的可能性。
在白人主导的主流话语中,“东方人是……被加以审视的”,因而“东方就与西方社会中的某些特殊因素(罪犯,疯子,女人,穷人)联系在一起”(萨义德263-264)。大多数黑人在失去话语权的社会中都难以反抗,甚至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自身被强加的恶人形象。从白人的视角与话语规则出发,派拉特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疯女人”。童年恐怖的遭遇给予了派拉特异乎寻常的成熟,她继承了“本该”属于男性的自力更生的奋斗精神,依靠自己的勤恳劳作筑造了一个简陋但幸福的家:“威士忌……成为派拉特稳定的谋生手段。这种技能给她时复一时、日复一日的自由”(莫里森 153);她用自己黑人女性独特的爱与智慧哺育了女儿与外孙女;她贫穷但乐观,尽管深陷帝国主义的囹圄,经历了一世的苦难,但临终前仍坚持黑人族裔所弘扬的博爱团结的价值观:“我会爱他们大家的。要是我认识的人再多些,我也就可以爱得更多了”(莫里森 346);她以自己的身体力行揭开了女性独有的“后人道主义”本色,“体现了令人难忘的本质和人性中的闪光点”(任冰 50),也打破了男权社会强行拷在女性身上的枷锁。不幸的是,派拉特所拥有的勇敢、独立的特性,冒犯了男权主义的规则,因而被自己的同胞宣判了女性不该犯的“原罪”。固执而勇敢的抗争换来的是黑人族裔众叛亲离,派拉特在这样的孤立无援的处境中失去了言说对黑人族裔之爱的能力。
无论是出于白人殖民者的迫害,还是由于黑人族裔的排挤,派拉特作为那个时代为数不多的独立女性注定无法融入被帝国主义和男权主义教条渗透的社会。她无法言说,只能在时代的旋涡里陷入沉默,沦落成失语的飞行者。
三.风雨兼程——无畏的飞行者
事实上,沉默与失语作为小说中黑人女性的症状,并不意味着妥协或放弃,因为“属下(在沉默中)能够通过反抗主流话语的方式,实现自身的某种程度上的发展,从而构建属于反帝者的光明前景”(Lawson 150)。莫里森笔下坚毅且乐观的派拉特就是一位沉默的勇士。为了冲破种族主义与性别歧视的双重枷锁,重获话语权,派拉特终其一生都在追求独立的人格,保护她的家人,并尽其所能继承黑人文化中的仁义与大爱。
小说中,尽管派拉特失去了家园、自我身份、甚至是发声的权利,但在寻找家园的旅途中,派拉特逐渐重塑了自身的话语体系,构建了其独特且独立的女性身份,是小说中边缘女性人物的模范。值得一提的是,这位女勇士用于反抗不公的有力武器之一是其口中的歌谣。派拉特的歌声清脆动人,像磁铁般吸引着麦肯,让其“感到白天的烦躁从身上消失了”(莫里森 29),并暂时抽离了现代物质世界的冷酷与疲惫;她的歌声婉转悠扬,使奶娃流连忘返,沉溺于她简陋而充满爱意的温柔乡;她的歌声娓娓道来,在音符之间向丽巴和哈格尔传递着在穷苦中仍要努力劳作的价值观。派拉特的歌声激励着自己与家人,婉转地向族人诉说着自己重构女性话语体系的勇气与决心。
此外,不同于狡诈且残忍的兄弟麦肯,派拉特以女性特有的勇气与爱为保护罩,在种种压迫下不仅坚毅地守护着家人的安全,还捍卫着周围女性发声与抵抗强权的权利。在得知奶娃的母亲露丝被厌弃时,派拉特借助药物帮助露丝怀孕,并以此抵抗麦肯的欺凌。很多时候,迷药都是男性用以迫害女性的毒药,而派拉特以男性迫害女性的利器反扑男性,在女性深处弱势地位的社会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彰显了女性智慧,捍卫了女性权力。在丽巴被男友威胁时,作为母亲的派拉特不顾力量的悬殊奋起反抗,击退了施暴者,并夺回了丽巴作为女性的尊严与话语权。侵犯者胸前留下的血与伤是派拉特反抗男权的勋章,再现了派拉特在那个男女地位极度不公的年代,“以暴制暴”的壮举。当哈格尔因奶娃的抛弃丧失理智与意志时,作为外祖母的派拉特想尽一切办法帮助这位坠入深渊的女孩重拾对生活的希望与信心;而后哈格尔过世,派拉特又对奶娃暴力相向,大快人心。派拉特对于哈格尔的维护与安慰与对奶娃的咒骂与报复从某种程度上表现了派拉特对弱势女性的同情与痛心,和对强者欺凌的不屑与憎恶,凸显了派拉特捍卫女性主体地位的坚韧与无畏。
与此同时,坚毅独立的派拉特拒绝沦为白人文明的囚徒,对捆绑了麦肯与奶娃的所谓“先进”的霸权式价值观视如敝屣。麦肯与奶娃作为社会的既得利益者,在有形与无形之中都将自己的财富与地位建立在黑人同胞的痛苦之上,他們与本族裔的割离,最终也导致了自我的迷失。极具戏剧性的是,作为二者亲眷的派拉特尽管活在社会底层,即使饱经沧桑与不公,仍将黑人文化中仁义、善良、与勇敢的价值观视为自己的行事原则,将自己对于黑人文明的记忆、黑人族裔的归属、以及黑人身份的认同作为人生准则——派拉特在苦中作乐,与风雨作伴,用歌声重塑了女性的话语,用智慧与勇气维护了女性的尊严,用爱与善良守护了女性独立的人格,是莫里森笔下无畏且伟大的飞行者。
本文基于后殖民主义视角,对《所罗门之歌》中派拉特的边缘地位进行了分析。笔者认为奉行“金钱至上”的帝国主义文明与宣扬“女性依附于男性”父权主义价值观是导致派拉特边缘困境的罪魁祸首;困境里的派拉特无法真正讴歌自己的根与灵魂,也无法表达自己对黑人族裔的热爱与归属,进而沦为了一个失语者;然而派拉特不甘于在边缘无声地飞行,并在其颠沛流离的人生之旅中以自己的歌声为利器,以智慧为武器,以爱为力量反抗压迫,重塑了女性话语,保护了女性尊严与人格,重构了独立的黑人女性身份。正如小说中所言,作为祖先的所罗门飞越了山川与河流,而作为后裔的派拉特则带着女性独有的勇敢与智慧飞向了平等与自由。
参考文献
1.Ahmad, Soophia. “Women Who Make a Man: Female Protagonists in Toni Morrison’s Song of Solomon”. Aligarh Muslim University 28.2 (2008): 59-73.
2.Lawson, Victoria. Making Development Geography. London: Hodder Education, 2007.
3.Peach, Linden. Toni Morrison.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95.
4.龚莉岚:“《所罗门之歌》中‘肚脐’的象征意义”,《散文百家》04(2017):43-44。
5.李应志:“认知暴力”,《国外理论动态》09(2006):60-61。
6.莫里森·托妮:《所罗门之歌》。译:胡允桓。海南:南海出版公司,2013。
7.任冰:“论《所罗门之歌》的后人道主义思想”,《当代外国文学》33.04(2012):46-53。
8.萨义德·爱德华·W:《东方学》。译:王宇根.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9.斯皮瓦克·佳亚特里:《从结构到全球化批判:斯皮瓦克读本》。编:陈永国,赖立里,郭英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10.王守仁, 吴新云:《性别·种族·文化—托妮·莫里森与美国二十世纪黑人文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作者单位: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