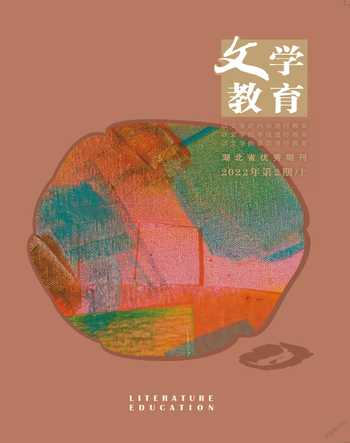一场宽阔明亮的精神性缔结
铁凝的《信使》是一个关乎“信”的故事。什么是“信”?人言为信。所谓“送信人”“报信人”,其身份就锁定了“信”的内涵与边界。“信”也是中国儒家文化的“五常”之一,然而,我们当下显然是一个“信”快速崩塌的时代,不但其载体从可触可感趋向于没着没落(网络),就连内容也已经微化甚至表情包化了。
或许铁凝正是有感于此,写下了关于“信”的郑重篇章。一对闺蜜陆婧与李花开的家境和际遇不同,婚恋各有曲折。陆婧爱上了从北京来的父亲的同学、已婚的“肖恩叔叔”;李花开嫁给了有私房独院、以画彩蛋为生的远房表哥起子。由于陆婧的恋爱颇见不得人,于是托李花开转情书,地址就是起子的独院。李花开要上班,所以信件往往由“永远在家”的起子代收。这是一桩私密加亲密的事,如果起子是“有信之人”,便会是两个女人友情中的“催化剂”和“甜蜜素”。不料这是个卑鄙小人,不但无“信”,还将“信”当作了威胁陆婧的工具。每次收到信,他都会将信纸偷取出来拍照,于是“信使”成了闺蜜关系恶化的“引爆器”。
说起来,起子的目的倒也并不多么卑下,他无非是以此为要挟,让陆婧的文教局局长父亲帮他调到一个“铁饭碗”单位。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通过这些不体面的信得到一份体面的工作”。清高的陆父闻之震怒,此事既然不成,起子便将信的照片发往陆婧和肖恩的单位,还有陆局长。陆婧被父亲赶出了家门,愤怒之极的她给李花开打电话大嚷了一通,就此绝交,然后去了北京,闪婚嫁人。三十多年来,她一直以为这是李花开和起子的合谋,她的友情、爱情和亲情一起被埋葬了。
故事说起来并不复杂,但铁凝却以巧妙的叙事将一个不复杂的故事讲出了丰盈动人的韵味。在“倒叙/现实”的闪回和嵌合中,一个包裹在友情中的关于爱、信、守的故事被层层剥露开来,每一层都携带着强烈的冲突和戏剧性,也带来了两个女人关系的陡转与突变。一场关于“信”的误会在三十多年后才被解开。原来,起子干的事李花开一律不知晓。在得知陆婧被“出卖”后,怀有身孕的她从房顶上跳下来,只为了逼迫起子离婚。之后,她跛着一只脚回到老家生下了儿子,与初恋结婚。儿子善跑,进了國家队。她退休后便随儿子来到北京,开了一家体育用品商店。丈夫留在老家开发旅游业,亦有不错的前景。
铁凝的情感倾向和价值判断是鲜明的。“信使”起子玷污了“信”之名,就算有私房独院,也留不住单纯美貌的妻子。与猥琐的男人相比,两个女人的形象格外地精彩、漂亮。这漂亮不单指外貌,更是她们的有情、有义、有坚持、有担当。陆婧在被起子的威胁惹恼后,一把抓起烧水的铝壶,倒入炉火正旺的炉膛,用力地摔门而出;“轴女子”李花开为了朋友而决绝地与起子离婚,为了离婚不惜命地从房顶上跳下,跛了腿也不后悔。这是何等地快意恩仇,凛然刚正!用她的口头禅“值吗”来说,这些又“傻”又“轴”的行为很“值”。因为人生必须得要有这么些个刚烈的时刻,才扛得住那些言而无信、背信弃义、忘恩负义带来的致命打击。这些看上去“无用”的抗争成就了两个女人,她们成为了彼此生命中最重要的“信使”:一个恢复了对友爱的信念,内心重新圆满;一个离开小人,嫁得良人,用自己的“信”挣来了后半生的安心和稳妥。
一个“信”字,让我想起了年轻时读过的小说《千江有水千江月》,台湾作家萧丽红所作,主人公名为大信和贞观。“女有贞,男有信,人世的贞信恒常在”,可惜一场苦恋,终因大信无“信”(信件和信诺)而结束。
我又想起了鲁迅先生的《铸剑》,无数人喜欢它的壮烈、奇诡、跌宕起伏、惊心动魄。我却喜欢它传递出来的两个字:一是“义”,二是“信”。黑色人帮眉间尺复仇,不为私利,只为道义;黑色人向眉间尺要他的头和剑去复仇,说:“你信我,我便去;你不信,我便住。”眉间尺举手抽剑,从后项窝向前一削,头颅坠地时,他将一条冰似的青剑递出。人间大信,莫过于此。
在当代文学中,像《信使》这样直接以“信”为主题的故事并不多见。“信”是人对自己立下的“契约”,这看上去容易,实际上是一场艰难的跋涉和持守。铁凝用炉火纯青的技艺,举重若轻地传达出了这场精神性的缔结。当“有信之人”被证实为是卑鄙小人、“有信之地”化为乌有时,关于“信”的信念依然是存在的,依然有人愿意为了不知能否兑现的“信”而做好了付出生命代价的准备,这是《信使》带给我们的宽阔和明亮。
曹霞,文学博士,著名文学评论家,南开大学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