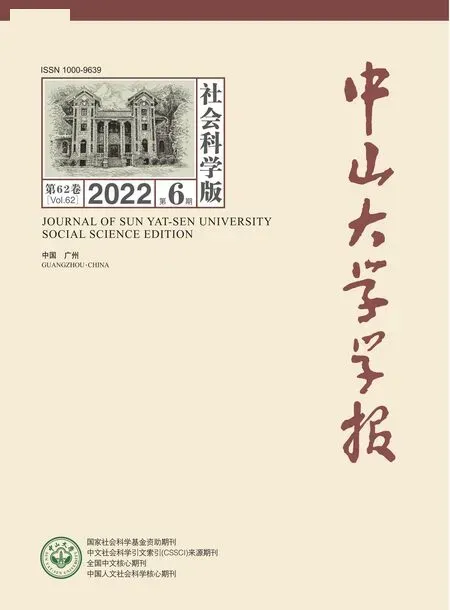上海流亡犹太人的精神变迁与身份认同*
——析乌尔苏拉·克莱谢尔小说《上海,远在何方?》
刘炜
引论
德国女作家乌尔苏拉·克莱谢尔(Ursula Krechel)的历史小说《上海,远在何方?》(Shanghai fern von wo)取材20世纪三四十年代犹太人流亡上海的历史,勾勒出一幅犹太难民在虹口隔离区的全景图,给德语读者描绘了一个遥远陌生的流亡者世界。2013年,韩瑞祥教授将这部作品翻译成中文出版,《三联生活周刊》《郑州日报》《信息时报》等媒体都先后刊登了介绍文章,小说于次年获得了鲁迅文学奖的翻译奖。为此,德国歌德学院在北京举办了作家与译者的对话。同年的北京国际书展上,克莱谢尔女士与中国作家李洱就“乡土与流亡”这一主题展开了对谈。
作家善用不同的笔法演绎春秋,上海作为犹太人的流亡之地,多次成为当代德语叙事描写的对象。除了当事人回忆录性质的文本外,近年来还出现了多本受众较广的德语历史小说,除了《上海,远在何方?》,还有洪素珊(Susanne Homfeck)于2012年在德国出版的面对青少年的小说《用筷子吃蛋糕》(Torte mit Staebchen)。另外,布克斯鲍姆(Elisabeth Buxbaum)于2008年出版的讲述自己父辈亲身经历的小说《过境上海:流亡生涯》(Transit Shanghai:Ein Leben im Exil)也颇受好评。同时,在跨文化和反法西斯的语境下,中国作家也注意到了这一题材,如2005年徐勇谦的《梦上海酒吧》和2009年严歌苓的《寄居者》,也都以这一时代和事件为背景进行过文学创作。
关于这段历史和与此相关的文学作品的研究不在少数,往往从史学和文学叙事手法的角度进行分析阐述①研究在沪流亡犹太人历史的学术机构,首推上海社科院以潘光和王建教授为代表的上海犹太研究中心以及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潘光的新书《来华犹太难民研究(1933—1945)》总结整理了有关来华犹太人研究的最新学术成果。同样,外国学者I.Eber编纂的《犹太难民在上海1933—1947:文件编选》(Jewish Refugees in Shanghai 1933-1947:A Selection of Documents)汇集了许多相关领域的资料和线索。另外,国内外学者都注重当事人回忆录的整理和研究,因为回忆录、采访记录等一手资料一直是本领域的主要一手史料,如Heppner于1995年出版的《避难上海:二战期间犹太隔都回忆录》(Shanghai Refuge:A Memoir of The World War II Jewish Ghetto)。此外,学者庄玮以记忆文化理论为依托,著有《犹太人流亡上海(1933—1950)的记忆文化:多元媒介性和交融文化性》一书,受到日耳曼学界关注。关于本文关注的《上海,远在何方?》这部小说,2008年奥地利文学杂志《手稿》(Manuskripte)上就刊登了Hedwig Wingler的推介文章。翌年,Hannelore Scholz-Lübbering则从女性视角分析了书中的东方形象。2010年,Henrike Walter在德国《流亡》(Exil)杂志上发表了分析小说文本结构的论文。此后,本人的《上海作为他者的避难所:乌尔苏拉·克莱谢尔的〈上海,远在何方?〉》(Shanghai als Schlupfloch der Anderen:über Ursula Krechels Roman Shanghai fern von wo)发表在德文杂志《文学之路》(Literaturstrasse)2011年第12卷,分析了作品人物在沪的流亡经历。2013年,王越的《从〈上海离哪里遥远〉到〈地方法院〉》则介绍了女作家获奖的两部代表作品。由此可见,这部作品在获奖后受到日耳曼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有意思的是,无论是专业研究还是文学作品,都存在一种对在沪难民犹太身份的不言自明。似乎“犹太人”这一称呼能涵盖当事人的所有身份,但这种大而化之的做法显然忽视了难民身份背景和身份认同的复杂性。虽然历史研究者,包括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考证梳理了大量难民的身份源起,但对在沪犹太难民身份认同的内涵和变迁却少有关注。这一现象正是本文研究的缘起。
以《上海,远在何方?》为例,书中许多人物就其出身、教育及职业经历而言,很少涉及犹太教、犹太文化等族裔背景,他们是欧洲大城市中常见的已经完全归化的普通市民阶层中的一员。如同弗洛伊德、茨威格、爱因斯坦这样的知识分子,所谓犹太裔的身份仅仅是个人文献档案中特定栏目的属性,几乎等同于我们今天少有提及的籍贯。在沪流亡时期,他们身上族裔身份的体现,很多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被动现象。根据上海社科院的最新研究,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估计曾有约三万拥有犹太裔背景的各国公民因受纳粹德国的迫害,作为无国籍难民过境或滞留于上海②潘光主编:《来华犹太难民研究(1933—1945):史述、理论与模式》,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72页。。这种无国籍状态成了流亡犹太人在沪所特有的社会身份,也成了日后日本占领军将其圈禁居住的理由。就此而言,时代的大背景是造成这些人身份复杂性与矛盾性的主要原因。对纳粹而言,这些人是被驱逐出境和注销国籍的犹太人;对上海租界工部局的管理部门而言,他们是难民;对当地中国人而言则又是洋人。按照霍尔的理论,这是一种被边缘化和丑化的形象,是一种中心主流意识推动下的被动选择③江玉琴:《论当代流散文化中民族性的消解与重建——兼谈斯图亚特·霍尔的流散理论》,《深圳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这些身份在被确定和使用时,都不曾考虑到,也无需顾及当事人的感受和认同。
换言之,小说中很多人物的犹太族裔身份认同是在流亡地上海才逐渐得以体现并强调的。当时在上海的各种负责犹太难民安置的慈善机构运转有序④在当时上海的公共租界有不少犹太难民救济组织,如“Shanghai Jewisch Communal Association”(缩写SJCA),“Shanghai Jewish School”(缩写SJS),“Shanghai Volunteer Corps”(缩写SVC),“Shanghai Ashkenazi Collaboratin Reflief Association”(缩写SACRA),“Hebrew Immigrant Aid Society”(缩写HICEM),“Committee for the Assistance of European Jewish Refugees in Shanghai”(缩写CFA或COPMAR),“American Joint Distribution Committee”(缩写JOINT)等。,满足了难民最基本的温饱要求,也使得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难民被汇聚一处,被动指定和确定了犹太身份。同时,共同的语言和文化也成了维系和重构族裔认同的纽带与媒体,在上海虹口促成了新的对犹太族裔的认同。共同的文化圈为族裔的重构提供了可能,具备了霍布斯鲍姆所说的“民族主义原型”⑤[英]埃里克·霍布斯海姆著,李金梅译:《民族与民族主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4页。。由此看来,作品中大多数流亡者在沪的经历也是他们犹太族裔身份的再确认之路。
小说中的人物流亡上海,于逆境求生中更能体会到不同文化和社会间差异对身份认同的影响。他们所经历的身份认同的变迁和重构,体现的正是侨易学所强调的“因侨而致易”①叶隽:《变创与渐常:侨易学的观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8,19,90,126页。。如叶隽在《变创与渐常:侨易学的观念》一书中提出,侨易学探讨的是“文化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人类文明结构形成的总体规律”②叶隽:《变创与渐常:侨易学的观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8,19,90,126页。。《上海,远在何方?》作为一本历史小说,本身就是社会文化和历史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和记录当时在沪流亡犹太人的思想、情感和经历,讲述了上海流亡犹太人群体的生存状态。正因如此,侨易现象在书中人物的经历中会有不同程度的体现。有鉴于此,本文尝试依托侨易学的理论,以乌尔苏拉·克莱谢尔的历史小说《上海,远在何方?》为例,对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流亡犹太人身份认同中体现出的侨易现象进行分析。
一、因“侨”而致“易”——犹太人在上海流亡生涯中的精神变迁
侨易学强调因“侨”致“易”,认为侨易现象是“在质性文化差结构的不同地域(或文明、单元等)之间发生的物质位移,有一定的时间量和其他侨易量作为精神质变的基础条件,并且最后完成了侨易主题本身的精神质变的现象”③叶隽:《变创与渐常:侨易学的观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8,19,90,126页。。毋庸置疑,克莱谢尔笔下犹太难民在上海的流亡经历就符合这一定义。他们长期游走于不同文化区域之间,需要面对自己身份的变化,这种经历本身就是一种精神变迁,而这种精神变迁的核心是围绕着犹太族裔身份所造成的结果展开的。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此种侨易现象当属侨易理论中的“异则侨易现象”④叶隽:《变创与渐常:侨易学的观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8,19,90,126页。。如前所言,小说中人物在上海所经历的侨易现象是当时错综复杂的历史、政治与社会因素造成的。就像小说一开始介绍陶西格先生时所提的问题:
你能想象移栽一个人吗?你能想象这个人被移栽后的情景吗?一只沉重的大手将一个人从家里,从他的城市里拖出,拎着他放置到另一处地方,另一个大陆上。⑤Ursula Krechel,Shanghai fern von wo,Salzburg,Wien,Jung und Jung Verlag,2008,p.7,7.
这种突兀而至,甚至是斩草除根式的位移,决定了流亡犹太人所经历的侨易现象必然非比寻常,具有明显的被迫性,体现在人物的精神变迁上。若以小说中来自维也纳且信仰社会主义的律师陶西格先生为例,这种强加于身被当作罪名使用的犹太族裔身份,显然无法被认同,但在当时当地却不得不面对和接受。
抵达上海虽然算是躲过了一劫,但1941年12月日本人偷袭珍珠港后,上海公共租界被日军占领,这些被注销原先国籍的在沪流亡者又被日本占领军当作无国籍者圈禁居住在被后来研究者称为虹口“隔都”的隔离区⑥“隔都”是Ghetto一词的音译。本意指犹太人聚居区,形成于中世纪欧洲对犹太人的歧视性政策。在德国纳粹统治期,犹太人被隔离囚禁于此,最终也由此走上去集中营的不归路。将上海日本占领军治下的虹口隔离区称为Ghetto并不确切。首先,这一隔离区是日本占领军设置的,与纳粹德国的排犹主义无直接关联。这里针对的是在上海生活的无国籍者,虽以流亡犹太人居多,但还有其他无国籍者,如此前因俄国革命而流亡中国的白俄,而拥有苏联国籍的犹太人却不在圈禁之列。此外,此区域中还生活着上海本地居民。犹太人所受限制显然与欧洲纳粹统治下的犹太人隔离区不可同日而语。,被迫以新身份再次走上侨易之路。对于惊魂稍定,刚刚适应了流亡地的犹太人而言,这次被迫迁居不但又是一次斩草除根式的位移,而且造成了难民群体的集中居住,此后的生活便如小说中的书商拉扎鲁斯所述:“我们不再允许离开这个城区,除非有特殊许可和证明。”⑦Ursula Krechel,Shanghai fern von wo,Salzburg,Wien,Jung und Jung Verlag,2008,p.7,7.纵观历史,鲜有像犹太人这样的群体在短时间内经历两次“异则侨易现象”。但不得不承认,被圈禁居住的共同命运,使得他们的犹太人族裔身份再次得以被动强调。
无论书中的人物,还是历史上数万之众的在沪流亡犹太难民,都经历了栉风沐雨的侨易之路。他们当中承受住精神变迁的人,才得以成为幸存者。因为在流亡这种极端情况下,侨易首先是一种物质和生理适应现象,即必须设法使自己活下去。作家花费大量篇幅描述陶西格夫人抵达上海后,在一家餐厅制作苹果卷的细节,其用意正在于此。因为“这套苹果派就是救命稻草,就是个奇迹”。于是,陶西格夫人
立刻就成了厨娘,这位新来的就被用洋泾浜英语称为Miss(小姐)。弗兰西斯科·陶西格算是撞大运了。她立马就获得了一个活计。①Ursula Krechel,Shanghai fern von wo,p.36,9,204,33,203,54,308.
作家由此强调陶西格夫人对新身份的接受,维也纳上流社会那位“会弹钢琴,说好几门外语”②Ursula Krechel,Shanghai fern von wo,p.36,9,204,33,203,54,308.的女士,变成了忙碌于上海虹口区一家餐厅的厨娘。在当时的情况下,犹太流亡者所经历的苦难不仅是战乱带来的不公和残忍,而且必然还有面对异文化种种荒谬的无奈。为生存而改变和接受自己的身份认同,正是这个弱女子经历的精神变迁。
在流亡地,所有的难民自动被归为两类,能适应的人得以偷生,反之则很快被严酷的现实所抛弃。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适者生存是流亡者异则侨易现象的真实写照③作者在《达尔文主义与文学》一书中指出,达尔文进化论中“适者生存”的准测同样体现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强者及适应周围环境的人拥有更好的生存机会。在流亡生涯的极端环境中,此种现象更为明显。Werner Michler,Darwinismus und Literatur,Wien,Bohlau Verlag,1999,pp.108-110.。正如小说在讲述流亡犹太人被日本人圈禁在虹口隔离区时所述:
日本人颁布的新法令把难民分成两类:一类有机会离开犹太人区,另一类则由于绝望和缺少离开犹太人区的希望,变成了住在犹太人区的密切观察者、守护者和释放囚犯,无声无息的见证人。④Ursula Krechel,Shanghai fern von wo,p.36,9,204,33,203,54,308.
这又一次身份认同的转变和重新定位恰是生存的基础,只有改变自己去适应环境,才有可能走完侨易之路。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陶西格夫人后来才有可能成为其他流亡者眼中的“走运的人”⑤Ursula Krechel,Shanghai fern von wo,p.36,9,204,33,203,54,308.,因为她可以拿到“特殊通行证,犹太人区的居民中或许有百分之五或十的人才拥有这种令人梦寐以求的特殊证明”⑥Ursula Krechel,Shanghai fern von wo,p.36,9,204,33,203,54,308.。多年后,她也才有可能和有资格作为幸存者回忆并讲述在上海度过的日日夜夜。
发生于不同地域之间的物质位移是产生侨易现象的前提,在小说中,上海作为地理概念涵盖了相关的气候、环境、基础设施等因素,这也是犹太流亡者首先面对的“质性文化差结构的不同地域”⑦叶隽:《变创与渐常:侨易学的观念》,第21页。。这种差异直接而生硬,会迅速改变一个人的面貌,并进一步引发当事人内心世界的精神质变。犹太难民在外滩码头下船之初,还努力维持着西方人的体面。但当他们随即被一辆辆敞篷卡车像货物一样运往难民收容所时,身心所受到的冲击显然不是卡车条凳舒服与否的问题,而是巨大的心理落差。犹太难民在上海所经历的精神质变,恰是以此种巨大的心理落差为起点。而其侨易的成功与否,也是以能否平复心理落差,适应新身份以图生存为前提的。或者说,其经历的侨易现象首先取决于当事人是否具有面对现实且适应现实的主观愿望,其次才是能否具有适应现实的客观条件。
流亡者若想完成入乡随俗这一精神变迁,就必然要与过去划清界限。唯有如此,才能避免在严苛物质环境中,再背负精神和心理失意落魄的重压。严苛的现实使他们无法再维护个人起码的生活尊严,原先引以为傲的作为独立个体的人,现在成了群体中的一员,毫无个人隐私与尊严。小说中的犹太书商拉扎鲁斯说过:
这里只有群体,可是作为一个欧洲人,你会把这种人和物的群体当成一种痛苦的损失,一种个人感的损失,这是曾经作为一个独一无二的人才能感到的损失。⑧Ursula Krechel,Shanghai fern von wo,p.36,9,204,33,203,54,308.
而后来日本占领军治下的隔离区,则更是“一个丧失自我的学校”⑨Ursula Krechel,Shanghai fern von wo,p.36,9,204,33,203,54,308.。犹太流亡者如果不能放弃那个曾经的身份,则无法抓住转瞬即逝的救命稻草。比如陶西格先生就一直无从体会上天的眷顾,整天郁郁寡欢。就连餐厅老板娘给他递上一大杯咖啡时,他都“充满疑虑地嫌咖啡太淡”①Ursula Krechel,Shanghai fern von wo,p.37,51,23,41,41,24.。
在小说中,侨易现象的精神变迁还意味着放弃甚至否定曾经认可的价值体系。小说主人公拉扎鲁斯原先是柏林选帝侯大街上的著名书商,有家创建于1830年的百年老店。而在上海街头,他
做残书生意,有发黄、发黑的,有书角被撕裂的,还有缺少封皮的,都成堆出售。②Ursula Krechel,Shanghai fern von wo,p.37,51,23,41,41,24.
像小说中的许多人物一样,他也“愿意入乡随俗:一切都得从头学起”③Ursula Krechel,Shanghai fern von wo,p.37,51,23,41,41,24.。然而,从头学起在这里指的却是学习“骗人的必要性”,因为他知道:“如果你不骗人,那你活该会被人骗。”④Ursula Krechel,Shanghai fern von wo,p.37,51,23,41,41,24.这也是一种对流亡犹太人所经历的侨易变迁最直接,也是最令人心碎的阐释。
在侨易现象中,地域间的差异也意味着不同文化乃至文明之间的冲突。试想小说中犹太裔的人物在欧洲的小康生活如果不被纳粹统治的暴力所中断,那他们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跨越千山万水到不知远在何方的上海去体验梅雨、战乱,并与中国社会和历史发生交集。再者,在前全球化时代,文化与文明间的差异更为巨大,因而带给人的冲击也更加有力。对流亡者而言,这种冲击显得尤为沉重。东西文化间本就有的差异,经由语言的隔阂,会造成更多的困窘。这种差异并非今天作为新兴学科的跨文化交流所强调的独特性,能给人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相反,它往往在流亡者最艰难的时刻才显现出来,折磨他们,加深其苦难,在精神和肉体上形成更大的障碍与煎熬。因此,这种跨文化的差异对流亡犹太人产生的是落井下石的效果。只有能够熬过这段苦难的人,才会讲述和反思自己所经历的侨易现象,因而也才会像作家笔下的拉扎鲁斯那样不无庆幸地强调:“他在上海生活过,他在上海活下来了。”⑤Ursula Krechel,Shanghai fern von wo,p.37,51,23,41,41,24.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小说中人物身上发生的精神变迁,围绕其犹太族裔身份所造成的在沪流亡生涯展开。这种族裔身份在一开始是一种模糊且被动的接受,但在故事最后他们离开上海时,已经变得清晰且确定,并在后来的回忆与叙述中得以延续和强调。
二、侨易现象中的“恒常”——流亡犹太人的身份认同及其正负效应
侨易现象中不仅有“因侨致易”的一面,还有“恒常”的一面⑥叶隽:《变创与渐常:侨易学的观念》,第20页。。流亡者历经劫难,抵沪时已面目全非,完全失去了昔日的风采。在这种情况下,“恒常”不变的只剩下其潜意识中对自身文化和身份的认同与定位。现实的荒谬在于,这里的“恒常”是他们在失去原先身份后才逐渐意识到的。在过去的生活中,作为“德国人”或“奥地利人”的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国籍)并行不悖。直到逃亡至上海外滩下船时,身份认同危机才经由救助委员会之口一语成谶:
从现在起,你们就不是什么德国人和奥地利人了。你们从现在起就是个犹太人。⑦Ursula Krechel,Shanghai fern von wo,p.37,51,23,41,41,24.
对于许多流亡者而言,正是这一通告唤醒了他们身上所承载的却不被意识到的“恒常”。在作家笔下,仅有因犹太出身而受到纳粹迫害的难民,少有与犹太宗教信仰相关的描写或阐述,甚至连犹太宗教活动中作为“物质文化核心”的犹太礼拜堂及其布置⑧Ulrich Knufinke,Die Dinge der Synagoge,Nathanael Riemer(Hg),Einführungen in die materiellen Kulturen des Judentums,Wiesbaden,2016,p.152.,在文本中都少有提及。换言之,这些欧洲来的流亡者不再被允许继续做原先的“自己”,必须接纳新的身份后才能投入新生活的创建。而失去身份的认同,既不意味着能与过去做一个了断,也不意味着能够借此融入当地,他们得到的仅仅是撒在自己苦难历程伤口上的一把盐。由此可见,无论是“犹太人”还是“无国籍者”,其实都是难民身份危机的表现。
恰是在这种混乱的无所适从中,侨易中“恒常”的一面,即潜意识里对自身文化和身份的认同,才能在流亡生活的诸多细节中得以彰显。他们在被封闭的限制居住地中重新安排了生活,但这种所谓的新生活却几乎是对过去的复制,于是小说中的沃尔夫博士看到“一个小德国出现了,有作坊,有食品店和咖啡屋”①Ursula Krechel,Shanghai fern von wo,p.53,53,pp.108-109,p.178.。这种独特现象甚至在当时上海的新闻报道中就已经成为话题,如在沪流亡犹太人创办的德文周刊《黄报》就曾报导,1939年5月,流亡犹太人在上海开办了29家咖啡馆和1家香肠厂②Adolf Josef Storfer(Hg.),Gelbe Post,Wien,1999,p.85.。在小说中,
外国人按照他们自己的风格建造办公楼和住宅楼,想把自己国家一些熟悉的东西移栽到上海来,用这种熟悉的氛围将自己隔绝起来。③Ursula Krechel,Shanghai fern von wo,p.53,53,pp.108-109,p.178.
他们似乎认为以这种方式,能够延续自己曾经的身份。然而在这些被移植过来的习以为常中,不见踪影的恰恰就是犹太风俗中诸如门柱圣卷(Mesusa)、门楣题字(Hausinschrift)、托拉经卷(Torarollen)等典型细节④Nathanael Riemer,Das jüdische Haus in siener Materialität,Nathanael Riemer(Hg),Einführungen in die materiellen Kulturen des Judentums,Wiesbaden,2016,pp.50-52.。这同样也表明了难民所谓犹太身份的勉强。小说中多拉·布里格在散步时,怀念“柏林开花的栗子树,怀念他早年住在聚贝尔大街那座院子里的栗子树”⑤Ursula Krechel,Shanghai fern von wo,p.53,53,pp.108-109,p.178.。他们面对残酷的现实,始终无法抛弃过去,总想用曾经熟悉的一切稀释严苛的现实。在历史上,上海虹口区霍山路附近的确形成过一个被犹太难民称为“小维也纳”的居住区⑥1940年3月14日,上海的德文报纸《黄报》(Die Gelbe Post)曾刊文指出,在虹口区出现了“小柏林”“小维也纳”,甚至是“小特拉维夫”。在这里几乎让人不觉得是生活在中国,而是中欧的某座小城。Adolf Josef Storfer(Hg.),Gelbe Post,p.2.,那里出版报纸、杂志⑦王健:《上海的犹太文化地图》,上海: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10年,第130页。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在上海先后曾经有过50多种犹太人出版的报纸、杂志,其中最著名的例如《黄报》。,有着丰富的文化生活⑧许步曾:《寻访犹太人》,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第143页。流亡上海的犹太人中,既有从事电影工作的,也有许多戏剧工作者。他们曾用德语上演过60多部戏剧,甚至还上演了意第绪语戏剧。和宗教活动,甚至还有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的活动⑨Stiftung Jüdisches Museum Berlin(Hg.),Geschichten einer Ausstellung-Zwei Jahrtausende deutsch-jüdische Geschichte,Berlin,Toronto Public Library,2002,p.161.。显而易见,无论是在虚拟的文学世界还是在历史现实中,人们都想尽办法,构建起与过去生活的联系。这些根植于内心的“恒常”最终汇聚成一个抽象的精神家园,填补了认同危机造成的空白。人们希望能够从想象的精神家园中获得慰藉,这种安慰虽能解一时之痛,但终究经不住现实的冲击。失望之后,是更大的失落。
同样,也只有“恒常”才能解释流亡者为什么即使生活在上海,却依然延续着过去的思维定势。小说中的罗森鲍姆夫妇想给新生儿注册一个户口时,似乎忘记了自己流亡上海的原因,几乎本能地去德国驻沪总领馆申报,而在场的纳粹官员给了两人几乎是当头一棒的答复:
您的儿子不能叫彼得·以色列·罗森鲍姆,彼得这个名字在德国只能给亚利安种族的国家公民。⑩Ursula Krechel,Shanghai fern von wo,p.53,53,pp.108-109,p.178.
在他们身上,这种根植于潜意识中不可或缺也不可变更的国家和文化认同感,并未因自身所受纳粹的迫害而稍有变化。这说明侨易现象中的“恒常”在当事人身上是何等的牢固,甚至是顽固。
“恒常”同样还体现在流亡者的饮食起居习惯上。按照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饮食无疑是文化记忆的一种形式⑪Jan Assmann,Kollektives Gedächtnis und kulturelle Identität,Hölscher,T.(Hg.),Kultur und Gedächtnis,Frankfurt,Fischer Verlg,1988,p.15.。持类似观点的还有跨文化学者维尔拉赫,他认为饮食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伴随人的一生,并与语言、社会、权利相结合①Alois Wierlacher(Hg.),Gastlichkeit,Rahmenthema der Kulinaristik,Berlin,LIT Verg,2011,p.11.。同样,马克斯·霍克海默也指出,在饮食行为中,同样可以观察到文明的进程②Max Horkheimer,Bürgerliche Küche,Alfred Schmidt und Gunzelin Schmidt-Noerr(Hg.),Ges.Schriften,Frankfurt,Fischer Verlag,1992,Band 6,pp.237-238.。在小说中,关于饮食细节的描写无处不在。自从陶西格夫人在餐馆里用有限的食材烤出了苹果卷,
越来越多的流亡者来到饭店,因为口口相传,大家都知道那里有烤羊角面包、小面包和苹果派。③Ursula Krechel,Shanghai fern von wo,p.50,pp.7-8,p.162.
在这里,苹果卷成了流亡者家乡的象征,看来“莼鲈之思”是游子的通病。无独有偶,她丈夫临死前念念不忘的居然也是一种家乡的煎饼。
生存得以保证后,“恒常”的文化属性就逐渐得以彰显。上海的各种犹太难民安置和慈善机构不但满足了难民最基本的温饱要求,文化活动也十分活跃。因为抵沪的流亡犹太人多来自大城市,本身拥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在这种情况下,共同的语言和文化就成了维系群体认同的纽带与媒介。虽然很多在沪流亡犹太人此前对犹太族裔身份的认同感十分淡漠,但共同的流亡命运使得求同存异并抱团取暖成了生存法则。在这种情况下,在沪流亡犹太人剧团前后共上演过60多个剧目,其中除了霍夫曼斯塔尔、施尼茨勒等名家的传统作品④[美]戴维·克兰茨勒著,许步曾译:《上海犹太难民社区》,上海: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1年,第236页。,还有反映流亡生涯的现实作品,如西格尔贝格(Mark Siegelberg)与汉斯·舒伯特(Hans Schubert)的《面具落下》(Die Masken fallen)。同样繁荣的还有音乐生活,乃至于在研究中甚至有“音乐上海学”⑤汤亚汀:《上海犹太社区的音乐生活》,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9年,第3页。一说。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作品中人物在沪流亡生涯中体现出的“恒常”,是一种基于潜意识中受母文化影响而形成的生活习惯和思维定势,并非对犹太族裔宗教与文化的认同。
这里要强调的是,在异则侨易现象中,“恒常”是一柄双刃剑,在为无家可归者提供心理安慰的同时,也带来了不适应,使得他们显得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更无法融入本地生活。这些人观察和评判周围环境的准绳,依然是内心恪守的“恒常”。所以尽管那个曾经的祖国如今已经面目全非,甚至想置他们于死地而后快,但这依然无法阻止他们在面对当时上海的脏乱差时,深切怀念家乡的干净卫生和秩序井然。幸存者虽然是流亡人群中最适应侨易之路的人,但在新环境中,“恒常”并不会一下子消失。无论他们的身份是否被现在的纳粹官方政府认可,这些人在被指定为犹太人的同时,还会本能地继续当“奥地利人”或“德国人”。
在异则侨易现象中,因“恒常”而导致的不适应还会带来更惨痛的后果。以小说中的陶西格先生为例,他始终沉浸在过去的时光中无法自拔。低身俯就对他而言犹如削足适履,完全无法想象。他的财产被纳粹认定为“违反道德”并“被雅利安化”,最后不得不逃亡上海,但他依然相信,“人可以主张并合法享有权利,在律师的帮助下实施权利,这没有什么不对”⑥Ursula Krechel,Shanghai fern von wo,p.50,pp.7-8,p.162.。在踏上流亡之路之前,这位曾经的律师和社会民主党人也试图做些实际准备,比如去上了一个缝纫机班,但到了上海,他却只能靠妻子养活。由此可见,此种反映在身份和文化认同中的“恒常”,在流亡上海的极端环境中,会像桎梏般地束缚住这位天涯断肠人,使其陷入不可自拔的沉沦,最后郁郁寡欢地病死。类似的人物还有艾米和她的丈夫马克斯·罗森鲍姆,这对夫妻居然
随身带来一只箱子,装满了手套,大小各异,多种式样,正宗的卡尔斯巴德手工制品。⑦Ursula Krechel,Shanghai fern von wo,p.50,pp.7-8,p.162.
在适者生存的流亡地,这种“恒常”的负面效应只能使流亡者陷入更大的困境。同样,“恒常”的负效应还造成了犹太流亡者与当地居民的交流不畅。尽管他们和中国人同处一隅,比邻而居,但除了因语言和文化差异造成的隔阂外,流亡者潜意识中难以撼动的“恒常”同样也阻碍了双方交流的深入,因此“文化适应”①“文化适应”指的是流亡者对流亡地所属文化的接近与接受过程。但在流亡上海的犹太人身上,这种对异文化的认同和适应是很少见的。Wolfgang Benz,Hermann Graml und Hermann Weiß(Hg.),Enzyklopädie des Nationalsozialismus,München,Taschenbuch Verlag,1998,p.305.在流亡上海的犹太人身上很少能看到踪影,这种隔阂使得他们的流亡在很大程度上孤立于当时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随着二战结束和中国内战的爆发,这条侨易之路随之中断,也很快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若非后世文学家和史学家的不断发掘,这段历史很难成为上海历史中的特殊一页。
结语
乌尔苏拉·克莱谢尔的这部小说《上海,远在何方?》立足于史料,将历史事实和艺术想象融于一体。在这部小说中,体现于人物身上的精神变迁和身份认同构成了人物侨易之路的主要内容。从侨易学的角度看,精神变迁是上海流亡犹太群体的整体特征,相反,恒常不变的是他们对自身身份的认同,具体表现为思维定势和生活模式的固化等方面。本文通过文本解析,考察书中人物为适应环境以图生存所做出的各种努力,进而梳理其走过的侨易之路。
时至今日,无论在德国还是在中国,能够讲述当年流亡上海经历的幸存者已所剩无多。为了防止这一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悲剧被遗忘或篡改,史学研究者投入了巨大精力,从而使这一领域的研究在德国成为一门显学。这段历史当然在国内也受到了广泛关注,纪实频道里的纪录片,博物馆、纪念馆甚至图书馆中的专项史料陈列,都在不断提醒着今天的人们不要忘记历史,尤其不要忘记人类史上这段令人难以启齿的丑陋。而梳理幸存者走过的侨易之路,则有助于后人更好地理解这段历史。
——聚焦各国难民儿童生存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