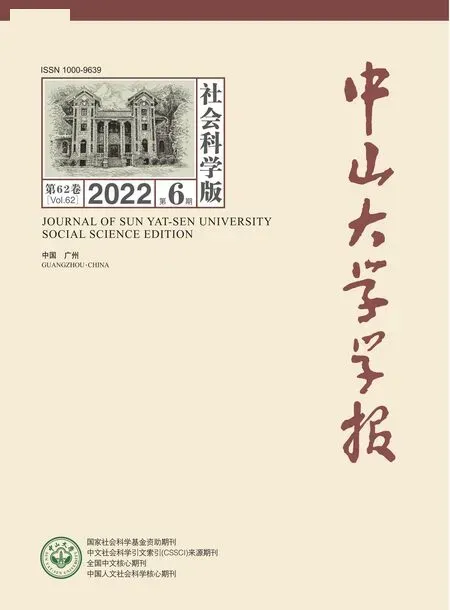从“谱系语文学”“发生学”到数字人文的认识论思考*
郝岚
“谱系学”因福柯1971年发表《尼采、谱系学与历史学》一文而引起学界注意。福柯的“谱系学”(Généalogie)偶尔也被翻译为“系谱学”“发生学”。反向考察,有人认为在中文语境中,与“谱系学“或者“系谱学”研究方法相关的词,对应的似乎主要有三个:“一是仅仅从同一标准进行‘周全’的类型划分,而不追溯其历史脉络的构成‘系列’(spectrum)研究;二是多次进行由母系列到子系列划分的构成‘体系’或构成‘系统’(system)研究;三是既进行类型分析,又进行历史追溯的谱系(Genealogy)研究。”①张慎:《传统谱系学与新世纪以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西南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事实上,这是不准确的。“系统”一词的不同无需多言,Spectrum这样的词虽然偶尔也被翻译为“谱系”,但它主要指的是光谱、频谱等一种有序的排列(an ordered array)组成,缺乏历史性,该词的翻译并不多见,故不做讨论②如Perry Anderson,Spectrum:from Right to Left in the World of Ideas。中译本为[英]佩里·安德森著,袁银传、曹荣湘译:《思想的谱系:西方思潮左与右》,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其中解释了题目:通过“棱镜”观察“分属于政治领域中的左、中、右三派”,“把整个谱系透彻分析一遍”,参见中译本第1—3页。。
真正在西方学术语境中与“谱系学”相关的主要有Genealogy以及Stemmatology(也被译为稿本关系学),常见于校勘学、文献学之中,偶尔也在人文学科历史中出现③如[荷兰]任博德著,徐德林译:《人文学的历史:被遗忘的科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98页,将原文中的Stemmatology译为“谱系学”或“稿本关系学”;英文本Rens Bod,A New History of the Humanities,U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p.274;将Genealogy译为“系谱学”,见中文本第63页,英文本第149页。。这两个词之间有着内在的学理关系,并发生了知识的侨易:从包含到分化,到各有自身的重点学科领域。回顾两者与古老的语文学的关系,它们各自的特征、变迁及其折射的认识论问题,有助于理解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之间寻求共同原则模式的“变”与“常”。
王晓朝教授有一篇文章,探讨了“发生学”“谱系学”的由来与关联,发现在中国学界“发生学”(Genealogy)多被理解和翻译为“谱系学”。文章引证了古希腊的文献,考察了该词的词源和词义,阐明发生学与谱系学的由来,揭示谱系学的基本性质、方法与主要特征,并与发生学作初步比较,认为译成“发生学”或“谱系学”都具有合理性。但他认为“发生学的方法适用于整个哲学领域,而谱系学的方法只适用于伦理学或伦理思想史。讨论‘发生’问题,既可以在一般的语境亦即哲学的语境中进行,也可以在具体的语境中进行”①王晓朝:《“发生学”“谱系学”的由来与关联》,《南国学术》2020年第2期。。该文是在哲学领域辨析的,有其缜密的逻辑和合理性,但就学术史而言并不尽然。因为这个最初是关于罗马贵族家世的词,其学术源头是和语文学(Philology)密切关联的。该词因尼采、福柯而得到学界广泛关注,并非仅因“热爱智慧”的哲学根基,更因该方法来自古老的“热爱语言”的语文学。不能忘记的是,尼采虽是古典语文学的“逆子”,但也是巴塞尔大学的语文学教授;福柯正是充分运用了语文学方法,拉开了现代思想的大幕。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古老语文学的多支系Stammatology如何简化为近乎线性的Geneaology,现代思想界如何因为福柯对语文学家尼采的总结,突出强调了注重起源的“谱系学”(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是“发生学”)。早期Geneaology从罗马贵族回溯家世、到语文学家在古老手抄本中构建关系链条,现代语文学家逐渐发现这个逻辑链条的构建不一定是完整的,可能是破碎缺损的,因此语文学并非只是实践上的、形式化的科学,也包括历史的建构和主观的个人阐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尼采反对起源的本质主义,福柯将之继续推进,为这个词赋予了以历史学的方式、批判地重构某种特定思想∕观念∕概念∕话语等的方法论特征。
与这两个词相关的还有“历史树”(historical tree)、种系发生学(phylogenetics)、世系(pedigree②pedigree一词15世纪才出现,由于出现较晚,本文不再讨论。它来源于诺曼—盎格鲁语péde grue,字面意思是“鹤脚”(crane’s foot),早期是用三条线表示在手稿系谱(manuscript genealogies)中的继承轨迹,如同鸟的足印。见《牛津词典》线上,https:∕∕www-oed-com.virtual.anu.edu.au∕view∕Entry∕139608?rskey=LpRkrh&result=1&prin,2022-3-9。)等词。特别是当代数字人文领域,“谱系学”再次隆重上场,但这里的“谱系”是Stemmatology,因此有必要区分两个“谱系学”的各自特点和术语历史,重温语文学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原则与模型的影响。我们需要从谱系语文学的早期逻辑和发展入手,以便于了解这一古老方法之“变”——它自身的演化逻辑、与其他科学探索的知识侨易、积极互动、互相滋养——以及它一直追求的形式化原则所带来跨学科适用性。
一、谱系语文学与形式化规则
“谱系语文学(Stemmatic philology)对于人文学的意义如同古典力学之于自然科学。”③Rens Bod,A New History of the Humanities:The Search for Principles and Patterns from Antiquity to the Present,1st Edi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p.279.谱系学(Stemmatology,Stemmatics)或者谱系理论(Stemmatic theory,又称稿本关系论)最初是用来修复古典文本的方法,它用来构建修复古典文本的谱系图(stemma),或者家族树(Family Tree)。Stemma来自希腊文στέμμα,表示“王冠、花冠”,至拉丁时代因该物常放于祖先像前,故后来引申为“祖先、世系、谱系树”(ancestry,pedigree,genealogical tree)④《牛 津 词 典》线 上,https:∕∕www-oed-com.virtual.anu.edu.au∕view∕Entry∕189750?redirected From=stemma&&print,2022-3-9。。《牛津难词辞典》中,stemma被解释为“留下记录的家族世系(genealogy of a family);家族树;显示文本与其多样抄本之间关系的图表(diagram)”⑤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Difficult Words is based on The New Oxford American Dictionary,United States in 2001,p.416.。在2020年出版的以此为名的专书中,Stemmatology的意思被解释为“处理存世文本之间的谱系依存(genealogical dependencies)关系的文本校勘(textual criticism)”,关注“文本流传的谱系树”(genealogical tree),有时也写作“stemmatics”①Philipp Roelli ed.,Handbook of Stemmatology:History,Methodology,Digital Approaches,Berlin:Walter de Gruyter GmbH,2020,pp.3-4.。一般而言,单词结尾“-ology”来自希腊文λόγος,表示“意蕴丰富或科学化的表达方式”;结尾是“-ic(s)”,形容词后缀-ικη,来自阴性名词τεχνη,表达“艺术或研究领域”。
西方古典语文学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已存在,中世纪对古希腊、拉丁和《圣经》文本的研究是其集大成的代表:主要包括准确解读古老文本,根据流传文本制作精校本。1777年以德国学者沃尔夫在大学注册为标志,语文学开始学科化,进入现代语文学阶段。从语文学到生物学、哲学再到数字人文,尽管发生了知识侨易,但正是面对海量和多样的研究对象,试图克服主观性、探索形式化、寻找个体之间关系规律和原则的方法,成为万变不离其宗的恒定“高常”②“高常概念”参见叶隽:《构序与取象:侨易学的方法》,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21年,第55页。。在现代语文学发展过程中,语言学成就最卓著,因此19世纪后,“爱语言”的“语文学”常常被当做“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同义词。它主要包含两个部分:语言与文本。两者渐渐分化,越来越多地分别与广义的语言学和文学研究相联系。到20世纪,这一术语在英语世界乃至西方整个人文学科中都被遗忘了。
一般认为,语言学是科学的,但这是不全面的。早在古典语文学中,研究稿本关系的文本语文学就已经在探索科学的原则。因为在文本语文学那里,研究者需要兼具人文学的经验主义与科学的理性思维与怀疑精神。
在1465年西塞罗著作的首印本之前,文本都是抄工手抄的,即使两个抄工同时抄写同一个蓝本,也会留下不同的讹误。早期语文学主要是鉴别版本的真实性,寻找善本、珍本。但随着古典文本越来越多,除去上述工作以外,如何厘定历史上各个文本之间的关系,用枝繁叶茂的当代流传文本,去追溯、修复、拼接、构拟出一个原始的“最佳本”(Codex Optimus)之根,成为古典语文学家的主要工作,这也是历史比较法和谱系学的最重要动力。古典语文学者的重要工作之一,主要就是通过坚实的语言基础,进行爬梳剔抉,确定稿本关系,精校出一个最佳本。
文本校勘学(Text Criticism)原则上经历了两个阶段,先是基于对经典流传下来的抄本进行总结:寻找典范,以此为标准,之后辨别、判定、理解那些古老文本——这主要是经验主义的,因为单纯依靠古典语文学家个人的能力做这些工作,是难以代际更迭持续的,它需要一种易于操作的,具有可重复性、适用性的科学理论方法。第二个阶段是寻找科学规则,然后利用现有各个时期的古老文本,意图去修复和追溯一个所有文本的起源——这是本体论的,是对“文本”这一概念的本质主义信念——认为所有抄本都只有一个稳定、唯一、准确、完整、原始的最初蓝本(这一信念也催发了后来历史比较语言学对“原始”印欧语的构拟)。正因如此,古典语文学中校勘学的显著成果一定在古老典范文本和宗教文本,因为无论是文本还是语言,坚信“存在”一个古老原始的发生学本体,是古典语文学的世界观基础:皓首穷经、爬梳剔抉、用慢读的艺术、“金匠的手艺”(尼采语)制作一个古老精校文本,必须对文本有着如同信仰的笃定。显然,这两个阶段很难截然分开。
处理、理解和鉴别这些文本是关键。因此,文本的校订、修复是主要工作内容。虽然中世纪的学者探索了很多修复文本的技巧,但是理论上仍然缺乏坚实的基础。所有学科的成熟有效方法都并非一人之力。人文学科开创性人物的工作总是备受争议,有些人的确是里程碑式的,比如卡尔·拉赫曼总结的拉赫曼法(Lachmann Method):通过考察每个抄本的“单生讹误”的沿袭状况,考镜现存不同版本之间的源流关系,从而绘制该文本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谱系。
拉赫曼之前,已有多位学者做了基础性工作,其中包括瓦拉(Lorenzo Valla,1406—1457),他发展了一套校勘(textual criticism)的方法,使用至今的三个规则:分别为纪年一致(chronological consistency)、逻辑一致(logical consistency)和语言一致(linguistic consistency)。特别是后者最见语文学者的语言功力,这也是传统语文学的“看家本领”。瓦拉出色的古典拉丁文能力,让他指出了伪作的多个语言错误。瓦拉使用的严谨的语文学方法带有现代科学精神的曙光:将宗教文本也视为一个研究对象,用怀疑和理性主义、逻辑推理、一分材料说一分话。他以文本现象为证据,为谱系语文学(stemmatic philology)打下了根基,而真正把谱系语文学推向修复古老原始文本的是15世纪意大利学者安吉利奥·波利齐亚诺(Angelo Poliziano,1454—1494)。
波利齐亚诺是诗人、哲学家、更是一位版本语文学家。1489年他出版了《杂集》(Miscellaanea),其中提出了他的问题:如果四个文本三个都一致,就应该排除它们,因为它们没有对修复文本提供新材料。他的方法被称为“剔除法”(eliminatio principle)或“最老史料原则”(oldest source principle)①Anthony Grafton,Defenders of the Text,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p.56.。波利齐亚诺这种基于历史方法的语文学是开创性的,因为这被拉赫曼提炼,形式化为影响深远的科学方法。
卡尔·拉赫曼(Karl Lachmann,1793—1851)是19世纪德国著名的古典语文学家,他的主要研究领域在古典学(古希腊和拉丁语文献)、圣经语文学(尤其是《新约》研究)、拜占庭学和罗曼学等。他总结前人经验,将异文、讹误等单独的元素放进了一个系统,依据幸存文本构建可被用于修复原始文本的谱系图(stemma)或者家族树(family tree),对现在被称作谱系理论(stemmatic theory,又译稿本关系理论)或者谱系学(stemmatology)的方法,特别是文本谱系重建(Text reconstruction as genealogy)意义重大,该方法可以说是在欧洲的后现代文本研究之前最主流的研究方法。
科学校勘的首要前提是不迷信通行本(Vulgate text),拉赫曼关注异文或称变体(variant)。另一种差别则被称为“讹误”,分为多生讹误(polygeneric errors)和单生讹误(monogeneric errors)两种,只有重要的单生讹误才可以帮助建立抄本谱系(a genealogy of the copies)②Paolo Trovato,Everything You Always Wanted to Know about Lachmann’s Method:A Non-Standard Handbook of Genealogical Textual Criticism in the Age of Post-Structuralism,Cladistics,and Copy-Text,Padova:libreriauniversitaria.it,2014,pp.54-56.。他主要对文本进行三部分工作:首先是语文学家集齐该文本的所有现存版本,把异文(变体)详细编目,决定幸存版本之间的世系谱系(genealogical)关系——编订谱系密码(stemma codicum)或者谱系图的类型。其次是检验根据现存文本追溯、构拟的“原始”文本是否为真,最后是制作精校本。
请注意以上知识和方法,迁移到今天的数字人文算法的语料库标注中仍然在使用。语文学的学术史证明,它的分析材料从18世纪末梵语被“发现”开始,也越来越多被应用在世界各种语言的关系研究(发展为后来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和今天的世界文学(例如弗朗哥·莫莱蒂对世界上现代小说形式的图绘)③莫莱蒂理论与谱系语文学、历史树之间的关系,参见郝岚:《新世界文学理论“树”的语文学来源及其批判——从弗朗哥·莫莱蒂说起》,《中外文化与文论》2021年第2期。之中。
虽然卡尔·朱姆普特(Carl Zumpt)1831年先编订了一个关于西塞罗《控告瓦列斯》(Cicero’sVerrine Orations)的古典文本的系谱图④雷诺兹认为拉赫曼被高估了,因为在他之前,还有本格尔(J.A.Bengel)在1730年代对《新约》的谱系勾勒,卡尔·朱姆普特(Carl Zumpt)于1831年先编订了一个关于西塞罗《控告瓦列斯》(Cicero’s Verrine Orations)的古典文本的系谱图,以及1847年的雅各布·伯内斯(Jacob Bernays)对卢克莱修抄本的重构。参见[英]雷诺兹、[英]威尔逊著,苏杰译:《抄工与学者:希腊、拉丁文献传播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17页。英文本L.D.Reynolds,N.G.Wilson,Scribes and Scholars:A Guide to the Transmission of Greek and Latin Literature,USA: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p.212。,但必须承认拉赫曼在所有前人的基础上,剔粗存精,进行了高度形式化,清楚说明了哪些规则适用于谱系语文学。由此,稿本关系学(Stemmatology)开始被更注重世系继承关系的谱系法(Genealogy)①Philipp Roelli ed.,Handbook of Stemmatology:History,Methodology,Digital Approaches,pp.549-550.所取代。
我们注意到,拉赫曼制定了很多可操作的科学原则,但他并因此没有把这些阶段都完全形式化,有些部分仍然需要语文学家过眼无数材料之后珍贵的经验和推测,因此语文学凝聚了人文学的推测性和科学的精确性。然而,一旦文本变体的谱系图被组合在一起,拉赫曼断言,很多非常准确的规则就可以运用于它,因此谱系法成为语文学从凭借经验的人文学,到试图探索科学原则的现代学科的转变标志,是人文学科的重要成就之一。
二、发生学、生物学与历史主义
Genealogy来自希腊语γενεά(Geneá),意为传承、生产、代际,以此作为词根,而加上了λόγος(logos)以后,构成了一种考察世代、出身和血统的学问。希腊词根gen表示出生、血统、根本,《圣经·创世纪》(Genesis),生物学的“基因”(gene),词根都与此同源。Genealogy在2001年的《牛津难词字典》中的解释是:“由一个祖先连续追踪的线性谱系”(a line of descent traced continuously from an ancestor)或者是“动植物从早期形式演化发展而来的线形”(a plant’s or animal’s line of evolutionary development from earlier forms)②Archie Hobson ed.,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Difficult Word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189.。
由于关注各个研究对象的世系支脉关系,Genealogy在中国有时也被翻译为“发生学”。虽然在古希腊词源上,该词被翻译为“发生学”或“谱系学”都有一定道理,两个词看似都关心起源问题,但该词在中文语境的内涵外延都有变化与侧重。福柯后来在分析尼采时使用的“谱系法”,事实上缺乏了中文的“发生学”所具有的历史主义③参见王晓朝:《“发生学”“谱系学”的由来与关联》,《南国学术》2020年第2期。他认为福柯的“谱系学”在一定意义上是“发生学”的,但在另一层面上,在反历史主义方面,与中文“发生学”所蕴含的意义又是本质不同的。,此为另一个话题。
与谱系学相关的模型最突出的莫过于树状图,学界最熟悉的是以达尔文为代表的生物学的谱系树,但事实上,语文学早期以手抄本为研究对象,寻找稿本关系的谱系法要远早于生物学。如上一节所言,显示家族关系的树形图首先是在文本语文学(textual philology),特别是在谱系语文学中被制定的,然后启发了历史比较语言学,多年后才在遗传学(genetics)中被成功使用④从19世纪语文学的家族树和谱系原则(stemmatic rules)影响到20世纪遗传学用了一个半世纪,具体论述与判断见Rens Bod,“A Comparative Framework for Studying the Histories of the Humanities and Science”,Focus:The Histories of the Humanities and Science,ISIS-Volume 106,Number 2,June 2015,pp.367-377、368-369,也参见Heather Windram,Prue Shaw,Peter Robinson and Christopher Howe,“‘Dante’s Monarchia as a test case for the use of phylogenetic methods in stemmatic analysis’”,Literary and Linguistic Computing,no.23(2008),pp.443-463。。这是典型的知识侨易,因为在人文与自然科学分化的19世纪之前,人文、社会与自然科学常常互有启发。关于研究对象关系的知识首先产生于语文学,然后类比启发、迁移到了正在起步的生物学,只有狭隘的当代人才会觉得人文学之源语文学不够“科学”。
语文学在19世纪的主要成就集中于历史比较语言学:1808年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1772—1829)出版《论印度人的语言与智慧》,他认为印欧语代表的屈折语是一种高级形式,停滞的黏着语是平庸的,而且这是早已决定、不可改变的,如同自然界的生物。“施莱格尔独特的谱系学思维(genealogical mindscape)有一个神学嵌入……因此就不奇怪印欧谱系学(Indo-European genealogy)会有沙文主义的来世了。”⑤Markus Messling,“Text and Determination On Racism in 19th Century European Philology”,Philological Encounters 1(2016)79-104,p.90.这一思想影响了后人,最典型的就是施莱歇尔。历史比较语文学“产生了一套元叙事,通过印欧语的成功故事,假设了一个熟悉的系谱(genealogy),源自一种特定的文化主义,反对人类的普遍性……产生(generates)了自己的‘伟大历史’”①Markus Messling,“Text and Determination On Racism in 19th Century European Philology”,p.97,86.。
奥古斯特·施莱歇尔(August Schleicher,1821—1868)是一位以语言谱系(Linguistic Stemma)理论而闻名的德国语言学家,他于1850年绘制了印欧语系的谱系图(Stammbäume),还早于达尔文1866年的生物自然选择的树状图②关于比较语言学对生物学的影响,参见Benoit,Dayrat.“The roots of phylogeny:How did Haeckel build his tree?”Systematic biology,4(2003),pp.515-527。此外对语文学、系统学、历史语言学、生物学以及信息科学、地球物理演进学关系中树状图蕴含历史模式的相关性研究,参见Robert,O’hara,“Trees of History in Systematics and Philology.”Memeory della Societa Italiana di Scienze Naturali e del Museo Ciuico di Storia Naturale di Milano,1(1996),pp.81-88。。1863年,在《达尔文理论与语言学》一文中施莱歇尔谈到:“语言是自然有机体,其产生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语言根据确定的规律成长起来,不断发展,逐渐衰老,最终走向死亡。我们通常称为‘生命’的一系列现象,也见于语言之中。语言学是关于语言的科学,因此是一门自然科学。”③[德]奥古斯特·施莱歇尔著,姚小平译:《达尔文理论与语言学——致耶拿大学动物学教授、动物学博物馆馆长恩斯特·海克尔先生》,《方言》2008年第4期。但此处还没有历史的加入。到了1864年,马克思·穆勒(Max Müller)写道:“没有一种科学……比地质学更能使我们这样的语言学习者受教。”④Max,Müller,Lectures on the Science of Language,2 vols.,London:Routledge∕Thoemmes Press,1994,p.14.语言和地质的相似之处不仅在科学性,关键还在于每一层的演进记录了历史,古代语言就如同化石,可以用带有历史主义的眼光回溯过去。由此,Stemmatology简化为Genealogy。麦林斯总结说:
现代语文学的话语被镶嵌在一个认识论框架中,其中符号形式与发展问题交叉。在这一紧张的领域,语文学作品对人和他对世界的不同比喻进行陈述。从这个意义上说,语文学如米歇尔·福柯所言,是由认识论条件与新兴生物学领域类似的认识论条件所决定的,该领域处理生命形式的起源和发展。因此自18世纪以来,语文学开始诉诸于试图解释可变性的生物学概念,比如‘种族’的概念,这也就不足为奇了。⑤Markus Messling,“Text and Determination On Racism in 19th Century European Philology”,p.97,86.
19世纪的语文学在历史比较语言学方面的成就是标志性的,类似历史比较法、语言谱系树等模型也是超越时代的,以至于今天,人们谈到语文学仍然首先想到它。但是,由于它的方法论框架带着强烈的主观阐释色彩,潜在地带有危险的认识论可能性,与殖民主义、种族主义难脱干系,因此,从福柯、萨义德再到马丁·贝尔纳都曾对此展开过批判。
“谱系学”因福柯对尼采的相关引述⑥参见[法]福柯著,钱翰译:《必须保卫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页。而再度声名鹊起,事实上,尼采只是在《论道德的谱系》中对出身(herkunft)和起源(ursprung)有过一小段讨论。熟谙文本语文学的尼采发现,依靠现有材料,重构一个古典时代的希腊并非不可能,但未必可信:“荷马作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作者不是一种历史流传下的记录,而是一个美学判断。”⑦[德]尼采著,韩王韦译:《荷马的竞赛:尼采古典语文学研究文稿选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8页。如果材料充斥着解释,逻辑的链条需要语文学家依据经验去解释而充满偶然性,那么纠缠在作者和作品问题上便意义不大。
这涉及到尼采的历史观:尼采在《历史的用途与滥用》中将传统历史的作用划分为纪念的、怀古的和批判的:“批判的”历史要把过去带到裁判的法庭之上,无情地审判它,但“因为既然我们只不过是先辈的产物,我们也就是其错误、激情和罪过的产物,我们无法摆脱这一锁链。尽管我们谴责这些错误,并认为我们已摆脱了这些错误,我们却无法否认一个事实:我们来自它们”⑧[德]尼采著,陈涛、周辉译:《历史的用途与滥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4页。,这是命定的悖论。
在尼采和福柯这里,Genealogy不再具有神一样的高贵血统,而是非本质主义、非同一性、非连续性的,因为所有的历史和事件是在时间中不断生成(generate)的。Genealogy不相信且无意于追寻唯一的源头,只是分析不同事件的历史效果。在这个意义上,Genealogy翻译为“发生学”是有依据的。
三、“新谱系学”:计算机与生物学的方法论滋养
2014年哈佛大学南亚与梵语语文学家迈克尔·威策尔在《吠陀研究》杂志刊文,该文第六节专门谈到新谱系学(New Stemmatics)。作者首先介绍了19到20世纪欧洲语文学中的印度学,其中谈到最近以来语文学的文本校勘,很多基于计算机技术,其方法的驱动力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生物学的种系发生学的树状(phylogenetic trees in biology)”;它们在分类学或分类单位上都像谱系图,从生物王国到亚种的分层排列,其主要方法论有三个原则:距离法(Distance methods),简约法(Parsimony methods),最大相似法(Maximum likelihood)①Michael Witzel,“Textual criticism in Indology and in European philology during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Electronic Journal of Vedic Studies(EJVS),Vol.21,2014 Issue 3,pp.9-90、p.68.。事实上,威策尔介绍的还不全面,因为种系发生学的关键分类法主要是两种:枝序法(Cladistics)和表型法(Phenetics)。前者关注物种演化史上的分支事件(Branching events),后者关注物种的相似性并进行分类。因此,发生学意义上的谱系学,主要与生物学中的枝序法相关。无论是生物学还是抄本,都需要确定它的特征数据(character data),再确定它的距离数据(distant data)②苏杰:《种系发生学方法在西方校勘学中的应用》,《古典文献研究》第13辑,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507—524页。。生物上的种系发生学中的特征,通过计算机标注转回谱系语文学研究中,就如同拉赫曼法中的异文∕变体(variant)或重要的单生讹误,确定了某一个坐标,再确定其他文本与这些变体与讹误之间的“距离”,就可以建立抄本谱系(a genealogy of the copies)。当代学者分析说:
种系发生系统与文本校勘学(Phylogenetic systematic and textual criticism)针对不同目的处理不同的对象。然而,方法和概念(methods and concepts)的高度相似性允许计算机化的工具从生物学转移到语文学。到目前为止,语文学家大多是生物学方法的“客户”。但在未来,如果这项跨学科工作进一步开展,我们可能会期待两个学科之间的交叉滋养(cross-fertilization)。③Caroline Mace,Philippe Baret,“Why Phylogenetic Methods Work:The Theory of Evolution and Textual Criticism”,in The Evolution of Texts:Confronting Stemmatological and Genetical Methods,ed.by C.Macé,Ph.V.Baret,A.Bozzi and L.Cignoni(Linguistica Computazionale,24),2006,pp.89-108.
研究者虽然借助了计算机工具和种系发生学原理,但在方法模型上,仍然离不开谱系语文学。“新谱系学”借助计算机技术快速扩张,它集合了一批文本语文学研究者,其方法论更多得益于生物学。这些跨学科的方法取得很多成果,有的运用生物学的支序分类法研究文本,有的使用数值分类学重新考察圣奥古斯丁留下的经典,或者运用生物学启发的方法重构了非洲班图语的家族树④Hoenigswald H.M.& Wiener L.F.eds.,Biological Metaphor and Cladistic Classification:A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87;Lee A.,“Numerical taxonomy revisited:John Griffith,cladistic analysis and St.Augustine’s Quaestiones in Heptateuchum.”Studia Patristica,20(1989),pp.24-32;Flight C.,“Bantu trees and some wider ramifications.”Afric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1(1988),pp.25-43.中文相关介绍参见苏杰:《种系发生学方法在西方校勘学中的应用》,《古典文献研究》第13辑,第507—524页。。
以上例证证明,尽管学科分工越来越精细,但知识的侨易一直没有停止,在古老的文本语文学中存在着与今天的数字人文和自然科学一脉相乘的线索:一方面是方法论的形式化与规则系统,另一方面是文本、语言、物种等演化的历史主义描述。语文学是人文学科“被遗忘的起源”,一般人文学科被认为是与“科学”不可兼容的“另一种文化”,但数字人文的出现将数据科学、统计学和语言学等连在一起,“新文科”的提出又令人们重思古典语文学与科学的关系。当然,可以想象,当代数据科学家面临海量文本,思考抓取语料库、词频等问题时,和中世纪的语文学面对大量残破、庞杂手抄本的难题是一样的。
无论新旧,记取语文学的辉煌和黑暗都是必要的,特别是当“谱系学”蕴含着认识论问题时,认清它们的有效和识别它的局限同样重要。谱系语文学(Stemmatology)有三个规则:“穷尽寻找知识的源头(溯源译码);程序性的系统原则(文献修订);逻辑推理原则(确定现存关系)”,在此之后,不仅是古老文本,“语言研究也关乎历史了。人们借助语言间的声音变化,寻找有助于发现印欧‘原始语’(protolanguage)的历时模式”①Rens Bod,A New History of the Humanities:The Search for Principles and Patterns from Antiquity to the Present,pp.280-281,p.215.。根据这三个原则,从现存的庞杂材料(文本的,或者是语言的)中,确定前后古今的层次,梳理出发展轨迹,将之历史化地描述为一个谱系。这一方法的逻辑,与校勘学中的拉赫曼法一样,都是将大量的材料结构化、谱系化,而且“编织”的方向都是由今溯古。尽管材料的链条可能有残破,但研究方法的认识论相信并假设一个关乎人的(并非自然)经验的世界,有一个共同起源,绘制的这个谱系就简化为“发生学”(Genealogy)。学者的工作,就是寻找起源,由“多”归“一”,寻找原始与古老。尼采之所以反对,正是由于他发现这样的语文学的历史主义链条残破,因此提出“超历史”。
谱系法与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树形图尽管有效,但一样有着盲点和问题。它们都有一个假设,就是谱系的追溯,必须在一个线性封闭系统中,但这是不客观、不现实且不全面的。谱系语文学借助古老抄本中的异文和讹误,确定流传至今的各个版本之间的关系,具有非常高效的实用性和系统化意识,但可惜它不可能永远有效,因为它有时只能依靠运气。英国古典学大师豪斯曼在其《用思考校勘》一文中就提醒我们:“校勘不是数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事实上根本就不是一门严格的科学……校勘工作跟牛顿研究行星运动完全不同,更象是狗抓跳蚤。如果一条狗用数学原理研究跳蚤的区域和数量,除非碰巧,否则它永远也抓不住一只跳蚤。”②[英]A·E·豪斯曼:《用思考校勘》,[英]A·E·豪斯曼等著,苏杰编译:《西方校勘学论著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6页。谱系法(Genealogy)总是假定所有异文和讹误的流传都是线性的、垂直传承的,事实不一定是这样。
首先,研究者发现,谱系法并不能确定所有文本的关系。例如很多经典文本被不同时代的读者进行研究性的校读,他们把异文写在页边或者行间。而古代和中古的抄工也不一定只抄一个文本,因为他们会对流传下的几个文本进行比较和择优的阅读,选取有意思的异文(variants),来综合判定和选择一个文本,比如色诺芬《居鲁士劝学篇》(Cyropaedia)就是如此,“其传承已经严重错合,没有复原的希望”③Rens Bod,A New History of the Humanities:The Search for Principles and Patterns from Antiquity to the Present,pp.280-281,p.215.。
其次,谱系语文学假定所有文本都能追溯至一个“原始文本”的原型,而事实上,文本的传承并非是单一直线的,它常常是开放的。原因可能在于:虽然根据现有异文和讹误,编制了一个谱系,但仍然有些文本的差异无法被解释,它可能来自另一个抄本的支系,但至少还不能被认识,这就像比较语言学中也存在一些例外,比较典型的“孤立语言”如仍在使用的巴斯克语(Basque),死语言中的苏美尔语(Sumerian)、埃兰语(Elamtie)等。如果这个讹误被认为是古代就有的,那么一定存在一个传承支系,这个讹误后来也进入传承,于是被纳入后半截的传承,有时这种情况被校勘谱系语文学家也暂时纳入主干传承的某个支系,埃斯库罗斯和欧里庇得斯的剧本大约就经历了这些过程。
再次,很多孤立存在的异文虽然并未在其他版本中发现,但是也是古老可信的,却的确无法被编制在现有的谱系中。最著名的就是意大利卡西诺山(Monte Cassino)收藏的大量珍贵手抄本,常常会出现无法解释的异文,因为它在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具有学术中心的权威性和文本保存的封闭性,因此又保证了文本的“纯洁”,所以只能单独处理。
最后,古代作者在初版之后,常常会在第二版时进行修订和大幅改动,最终两个版本都流传下来了,而且很不一样。那么哪一个应该是“原型文本”呢?他们可能都是作者所为,都是真实的。作者期待后来的版本能覆盖初版时的抄写舛误、串行,但非常困难。就这样,逆推出一个“唯一的”原始文本“原型”的确是困难的。
好在学者发现,从20世纪中叶开始,作为基于文本进行文明研究的语文学已经越来越多使用多因解释(multi-causal explanations),使得盛行于19、20世纪的单因解释(mono-causal or even monomaniacal)退出了历史舞台①Michael Witzel,“Textual criticism in Indology and in European philology during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pp.9-90、p.37.。由此可见,西方古典语文学的发展,是一个试图从依靠熟稔文本的专家个人经验向科学原则摸索的过程,其中仍然不乏专业学者的主观判断,也需要可操作、可应用的科学原则。但对那些原则,需要像对待文本本身一样,带着批判的(critical)眼光严密推理、累积错误、不断完善、谨慎使用,因为永远不存在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
结语
从Stemmatology到Genealogy,经历了从语文学到生物学、哲学,再到数字人文的知识侨易。它们各自带有历史之“变”,却也互有包含与勾连,在重构多个研究对象关系的意义上,都希望寻求原则与模式的共同基础。最重要的是,重新思考“谱系学”“系谱学”“发生学”所对应的到底是Stemmatology还是Genealogy,不单纯是一个跨语言的侨易学翻译问题,更是一个认识论问题。
亚里士多德将知识分为三类:episteme(理论或科学知识)、实践智慧和技艺,其中“在西方哲学史上起主导作用的是episteme,理论知识或科学知识是传统认识论研究的主要对象,[从“认识论”(epistemology)这个词的构成就可以看到这一点]”②郁振华:《对西方传统主流知识观的挑战——从默会知识论看phronesis》,《学术月刊》2003年第12期。。因此由知识侨易而引起或者折射了认识论的变化,本在情理之中。
谱系语文学最初主要确定版本的真假,到拉赫曼聚焦于回溯重构一个“最佳本”,这一知识迁移到历史比较语言学,于是勾画了家族树;生物学将研究对象视为一个有机体:出生、发展、对应环境变化可以做出反应和调试的生命体,对种属关系的基本构想更多聚焦于某一研究对象的祖先和线性回溯。由于19世纪是科学的世纪,生物演化论的知识广泛影响了社会科学研究,甚至包括以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为代表的小说创作,以致人们忘记了这一关注研究对象谱系关系的知识本就来自人文学的源头——语文学。福柯对社会与历史的发生学话语分析,得益于语文学家尼采对古典语文学非本质主义和偶然性的揭示。当代数字人文虽然采用了看似科学的计算机技术,但本质上仍类似对稿本关系的思考,因此在知识模型上,采用了古老语文学对稿本关系的认识。
特纳(James Turner)在其《语文学:被遗忘的现代人文学科的源头》中坦言,“今天的众多人文学科仅开始于19世纪,而追溯它们的数个源头,其轨迹总是回向一个巨大的、古老的事物:有关文本、语言和语言现象自身的多维研究”即语文学,特纳将其概括为阐释的、比较的、历史的及世系的(genealogical)多方位探讨③James Turner,Philology:The Forgotten Origins of Modern Humanitie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4,p.9.。
15世纪的瓦拉主要做的是文本辨析为主的校勘批评(Textual Criticism),作用是辨别真伪,对于利用现有的文本修复和精校古老史料用处还在其次。中间经过波利齐亚诺的“剔除法”,再到“拉赫曼法”。尽管对于拉赫曼是否为谱系法的最初使用者仍有争论④仍有人认为拉赫曼之前的施利特尔(Schlyter)等人是首创者,参见Sebastiano Timpanaro,The Genesis of Lachmann’s method,ed.and tran.by Glenn W.Most,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5,pp.102-118。,但从他开始,古老的一般为树状的谱系语文学在更多场合被描述为一个带有历史主义和生物演化色彩的、回溯性的线状谱系,由此也可知语文学如何与生物学以及对“原始”和“最初”的迷恋密切相关。1840年,拉赫曼用他的方法对《新约》(1842—1850)版本进行了考据(criticism),将古典语文学这门“手艺”(craft)推向科学,综合、全面地完美展示了谱系中的亲缘与世系关系,由此,稿本关系学(Stemmatology)开始被更注重世系继承关系的谱系法(Genealogy)①Philipp Roelli ed.,Handbook of Stemmatology:History,Methodology,Digital Approaches,pp.549-550.所取代。在尼采和福柯这里,Genealogy又超越了谱系语文学自拉赫曼法以来对起源的追溯和对同一性的坚信,它关乎对历史主义的反思,是对连续性、整体性的否认,关注事件如何被话语讲述,因此翻译为“发生学”是有依据和道理的。
两词的主要区别在于,注重亲缘关系的Stemmatology绘制出来的,可能是一个网状,或最常见的是根系众多的树状关系图;Genealogy则聚焦对稿本∕语言∕物种等起源和衍生的关注,绘制的可能更像一个线形图;从认识论上说,Stemmatology主要反映了一个多元的世界观,Genealogy更多与同质性、一神论的叙述难脱干系。值得警惕的是,即使与生物学、计算机等成就互相滋养,也不能过于自信谱系学的客观化。因为历史地看,正是“语文学的文化解释学维度,蕴含着破坏人文主义实践的文化引导方针的危险”②Markus Messling,“Text and Determination On Racism in 19th Century European Philology”,p.83.。福柯唤醒尼采,解构批判的正是一套带有优越性的历史话语叙述的“谱系学”(Genealogy),而不是Stemmatology。正因如此,王晓朝教授雄辩而准确地指出:福柯的谱系学“是一种以起源分析法为主要方法的道德发生学。需要注意的是,福柯试图用所谓的历史感性和实际历史来取代传统的历史主义,持有反历史主义的立场,具有明显的反历史主义特征。在此意义上,福柯的谱系学与发生学是对立的”③王晓朝:《“发生学”“谱系学”的由来与关联》,《南国学术》2020年第2期。。
近年来兴起的“数字人文”计算模型对语言和文本形式化的探索,使得今天在方法论意义上重温古老语文学非常必要,深刻认识到人文学科的形式规则并非完美,需要批判思维和审慎的辨析:这有助于我们各自放下科学的傲慢和人文学的自满,警惕理论模型和形式化假设曾经带来的伦理困境再度出现。
重提古典语文学精校本制作中的谱系语文学和稿本关系学的原则,是因为在学科精细化、各自画地为牢的今天,我们走得太远以至忘记了我们的“母亲”——语文学。文学研究不一定只是阐释之学,毫无原则且与科学无涉;语言学也不全是类似语音学的仪器数据,它也曾有历史的维度和个人的解释空间,而看似科学的“演化论”正是从语文学中获得了历史维度而被称为“生物学的历史主义”。历史证明,在对人所创造的世界的研究中,没有一种学科与方法是全方位普遍适用的,它们都是在具体的语文学实践之中,互相补充、相得益彰,从经验到方法,从公式到科学,再试图在简洁可重复操作的原则中重新加入版本学家、注疏学者、生物学者、哲学家、数据分析者的个人经验,慢慢让研究对象变得丰富立体的。理解了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的知识侨易、交叉渗透、互为滋养的历史,也就不会在数字人文勃兴的时代里,产生不必要的恐慌或对技术过于自信。因为,尽管工具变为数据库和算法,但在标注了文本具体考察点之后,研究者的问题假设和思考原则仍然可能是非常传统甚至古老的。在这一意义上,“谱系学”作为方法、模型与原则,是可重复操作和普遍适用的,这正是古老语文学的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