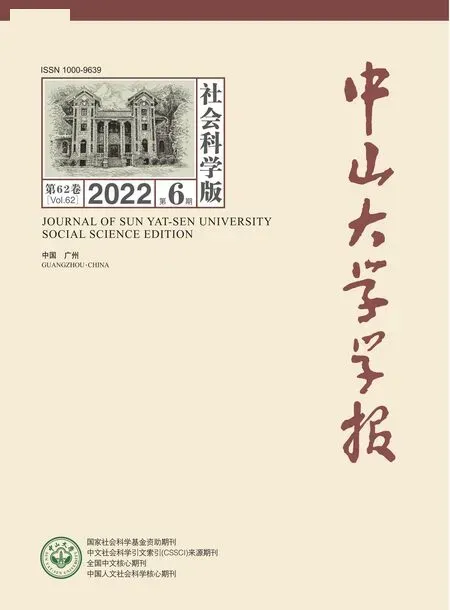文明共识与近代经学观念兴替*
秦际明
国内学界关于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是一个激烈的理论战场,这尤其体现在对经学的态度上,形成了提倡经学和反对经学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近代西学东渐以来,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的自我理解逐渐被摧毁。在西学如何塑造现代中国意识的问题上,学界已有较为充分的探索,汪晖、桑兵、罗志田等人的近代史研究在这方面取得了丰富成绩,孙江主编的《亚洲概念研究》辑刊代表了研究晚清以来中国思想观念之来源的前沿水平①孙江主编:《亚洲概念史研究》第1—8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2022年。。吴义雄更具体指出了19世纪前期西方人对中国的评价如何直接塑造了现代中国的自我认知②吴义雄:《时势、史观与西人对早期中国近代史的论述》,《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6期。。经学的瓦解与中国近代以来世界认知的根本转变直接相关,由此引起了中国传统世界观、价值观及其知识系统的崩解。经学成为被批判的历史之物,经历了双重历史化的过程:一方面被视为已然消亡的历史陈迹,另一方面又因其官学地位而被视为古代政治统治的意识形态工具。不少学者认为经学的本质即在于其政治功能,这当然属于过时的专制政体才有的事物。
经学所经历的历史化转换是中国接受某些西方现代理论路径的必然结果。反对中国传统文化,乃至要求全盘西化的文化态度,产生于西方富强而中国孱弱的社会现实,时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与思维方式对中国的衰落负有责任。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推进,晚清民国以来将中西文化视为文明与愚昧之高下对立的看法已经失去了社会基础,但历史语境中所形成的经学理解仍然流行于当代学界。因此,我们需要对20世纪以来人们理解经学的方式及其理论基础加以探讨,将经学观念的转换放到中国自身的古今之变与遭遇西方后的古今之变的双重视野中加以考察。
一、作为历史之物的经学
经学作为中国古代的官学享有高于诸子百家的地位,其义理被视为恒常之道,有超越时代的意义。近代以来经学历史化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清代以来的经学史学化;二是民国初年以来的史料化;三是经学在政治与伦理上的历史化。清代经学考据学极为繁荣,然而以训诂考据聊补章句之学,却未必能够较为全面地掌握经学的义理结构,通字未必达道。总体上看,与汉、宋学者之治经学相比,清代乾嘉学的主体内容是对经学的文献学考证与历史学研究,对五经的总体义理结构与治道建构缺乏深入探索。章学诚对清代经学提出严厉批评:
著作本乎学问,而近人所谓学问,则以《尔雅》名物,六书训故,谓足尽经世之大业,虽以周、程义理,韩、欧文辞,不难一吷置之。其稍通方者,则分考订、义理、文辞为三家,而谓各有所长。不知此皆道中之一事耳,著述纷纷,出奴入主,正坐此也。①章学诚:《与陈鉴亭论学》,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717页。
章学诚主张经学经世之用在于史,六经本身即是史,通经须通史。三代以上之史即为六经,而三代以下之事六经不载,需要研究三代以降的历史,才能更完整地理解道。通经致用不能仅仅停留于六经文本,而应通达当代之事,撰述当代之史。章学诚表示:“丈夫生不为史臣,亦当从名公巨卿,执笔充书记,而因得论列当世,以文章见用于时。”②章学诚:《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842页。如果忽略章学诚的史官之志,只引其所谓“六经皆先王之政典”,并不能准确地理解其通经致用的志向,因为先王之政典未必可以充作当世之政典。诚如论者所见,“六经皆史”说未必有贬于经,其实在于重视史,主张经寓于史,通过史事以显大道,但清末民国以来的“以经为史”则有完全不同的思想意识③张瑞龙:《“六经皆史”论与晚清民国经史关系变迁研究》,《中国文化研究》2005年第4期。。不过章学诚阐述的是经为古代之政,故为古代之史,但未能阐明古代之经如何理当世之政,未能揭示经与不同时代之政存在更为基础的结构关系,其“六经皆史”说反而成为清末以来“以经为史”说的诱因。
民国经学研究受清代影响至深,并在清人的基础上结合现代西方的价值观念,运用西方学术方法,进一步将经学史料化。民国以来所谓“经学即历史”与此前的类似说法有本质区别。传统经学“以经为史”之说默认经中有道,法随时代而变,道则永恒不变。但在近代以来的理解中,不仅古代之法已然不适用于现代,古代经学之“道”也一并成了历史之物。如胡适解释章学诚之语云:“其实先生的本意只是说‘一切著作,都是史料’。如此说法,便不难懂得了。先生的主张以为六经皆先王的政典;因为是政典,故皆有史料的价值。”④胡适:《章实斋先生年谱》,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第105—106页。“六经皆史料”与“六经皆史”虽一字之差,实有根本差异。比胡适更早的章太炎即已否定了六经之载道,他认为“经者,所以存古,非以是适今也”,“素王修史,实与迁、固不殊,惟体例为善耳”⑤章太炎:《与人论〈朴学报〉书》,《章太炎全集》第4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53—154页。。晚清民国之反经学其实在于反儒家,反儒家的根源在于近代国人在中西之间作了野蛮与文明的高下判断。清代朴学重训诂考据,虽未必通达经学的义理结构,但清代社会仍以儒家政教为根本,作为朴学的经学亦是政教辅翼,当然也不会否认五经载道。清末民国之学者则不然,有了西方文明作为儒家文明的替代物,五经所载之历史已不适用于今日。如此一来,经学即便不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障碍,也决非指导国家重建的义理之书。中国传统经学也因此解体于近代以来史学化的过程⑥参见陈壁生:《经学的瓦解》,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并在此过程中,康有为托古改制的失败以及袁世凯等人的尊孔表现,越发坐实了经学无益于当世的判断。从此以后,不只是经学中的礼法制度不切用于现代社会,经学之“道”也沦为落后民族的愚昧观念,需要通过学习西方先进文明来推行启蒙与教化。经学作为旧时代之物也就成为“国故”,只剩下史料价值。
经学史料化的根源,在于经学所承载的文化传统、政治传统与价值观念在近代变革中受到冲击。西方现代学术的引入,改变了评价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标准与话语体系,认为经学是过去时代的内容,在价值上低于现代西方文明。具体来说,经学本身被视为中国古代政治专制的产物,其政治功能被视为经学的本质所在。当然,经学本身包罗万象,本来并不专用于政治。20世纪中国社会剧烈的政治变革冲击着固有的文化体系,经学作为古代专制产物的观念,具有特别的政治意义,这显然并非中国文化的应有之义。
值得注意的是,晚清革命者怀有民族主义与民主政治双重革命目标,但并不必然反对经学,甚至还会引孔子为同道。对于儒家与经学,革命者固然会出于推翻帝制的需要而反对,但同时也会参酌现代西方政治理念予以诠释,阐发经学中的革命思想,挖掘先秦儒家与五经中的革命传统乃至社会主义传统。清末陈天华《狮子吼》写道:
《书经》上“抚我则后,虐我则仇”的话,不是圣人所讲吗?《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话,又不是圣人所讲吗?一部五经四书,哪里有君可虐民,不能弑君的话……照卢骚的《民约论》讲起来,原是先有了人民,渐渐合并起来遂成了国家。①严昌洪、何广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杨毓麟陈天华邹容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70—271页。
孙中山所阐发的革命理念中,既有来自西方的民族主义与共和理论,也包含了先秦儒家的天下为公与大同理想,并将二者相结合,这对现代新儒家的政治理想与文化观念有深刻影响。晚清民国革命者往往将历史上的儒家分成两截,一截是先秦儒家,与民主、共和乃至社会主义并不矛盾,认为这才是儒家的真面目;另一截是秦汉以降的儒家,与政治权力相结合,成为君主专制的意识形态帮凶。经学往往被视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的政治统治的意识形态,与先秦儒家的子学形态相对。
将儒学史乃至于整部中国历史区分为理想的三代以上与无道的三代以下的做法,在宋代理学中就已流行,朱子即对汉唐之世评价甚低。不过朱子对汉唐儒者亦有肯定之处,将中国历史先秦与秦汉后两段作出完全对立的价值判断的还属近现代,民国初年易白沙将《汉书》所载“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之语改写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正是此类现象的表现②丁四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辨与汉代儒家学术思想专制说驳论》,《孔子研究》2019年第3期。。将“表彰”改为“独尊”,意指汉代的学术专制结束了战国诸子的自由争鸣。易白沙“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语源于对梁启超有关论述的概括,而梁启超的观点又来自日本。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实际上率先开启了对儒家与孔子的批判,并影响了东渡日本的章太炎与梁启超等人,许之衡在清末与柳诒徵在民国初年均指出了这一点③刘桂生:《论近代学人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曲解》,《北大史学》第2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30—131页。。当然,日本人的看法其实也来自西方近代学者对中国古代君主专制的批判。
日本人在明治维新中批判儒家的同时,也在寻找文化替代品,那就是其自身建构的神道教与新习得的西方文明,尽管明治维新本身仍然保留了所谓的“东洋道德”④[美]马里乌斯·B·詹森主编,王翔译:《剑桥日本史》第5卷,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624—631页。。反观中国,若儒家被彻底否定,将用什么来替代儒家在中国文化中的位置?如若不批判儒家,又如何反对中国古代的君主专制,如何塑造合乎时代潮流的民主共和的民族国家?因此,清末的士人与革命者的儒家批判并不十分坚决,而是将儒家分成先秦与秦汉以降两段,以先秦儒家为自由、民主乃至社会主义的思想代表,而以董仲舒以后的儒家作为君主专制的帮凶,并进一步将这两段儒学形态区分为真正的儒学与被统治者利用的经学。当然,这种两分在不同的学者那里有不同表述,在对儒家与经学的定位上也有差异。
陈独秀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中区分了世界共同的一般性道德原则与中国特有的伦理观念两部分①陈独秀:《宪法与孔教》,张宝明主编:《新青年·政治卷》,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60页。。在他看来,“温良恭俭让信义廉耻诸德”是普遍道德原则,这不是儒家伦理落后之所在,儒家伦理之愚昧与落后在于其政治性内容。“儒者三纲之说,为吾伦理政治之大原,共贯同条,莫可偏废。三纲之根本义,阶级制度是也。所谓名教,所谓礼教,皆以拥护此别尊卑、明贵贱之制度者也。近世西洋之道德政治,乃以自由、平等、独立之说为大原,与阶级制度极端相反。此东西文明之一大分水岭也。”②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张宝明主编:《新青年·政治卷》,第43页。周予同在中国古代经典中明确区分了作为学术思想的中国文化与作为专制政治之帮凶的经学。作为文化的经学如《诗经》等,应视为学术内容加以研究;作为宗教与政治的经学,是为古代统治阶级服务的,用以钳制和奴役大众,要作为毒素加以清除③周予同:《治经与治史》,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621—622页。。朱维铮在这方面继承了其师的思想,认为经学“特指中国中世纪的统治学说。具体地说,它特指西汉以后,作为中世纪诸王朝的理论基础和行为准则的学说”④朱维铮:《中国经学史十讲》,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第9页。,主张将经学与儒学区别开来。在翦伯赞、侯外庐、范文澜等现代史家笔下,先秦诸子(不包括儒学)是灿烂的中国文化的重要部分,而汉代建立的经学则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工具,压抑了学术自由,禁锢了人民思想。当代经学研究大家汤志钧概括道:“‘唯经’是从,‘唯上’是听,势致窒息学术,禁锢思想,封建主义的经学,名为研究,实为注疏,而且越来越烦琐,陷入死胡同。”⑤汤志钧:《近代经学与政治》,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7页。20世纪风云激荡的百年对当代中国学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与问题意识都产生了深刻影响,许多学者虽然在政治话语上与百年前的革命者有所区别,但接受了民国以来经学作为中国古代官学所获得的独特政治含义,将这种政治含义视为经学的首要标志,认为作为专制政治附属物的经学早已不适合如今多元民主的时代⑥参见任剑涛:《超越经学,回归子学:现代儒学的思想形态选择》,《文史哲》2019年第4期;李存山:《反思经学与哲学的关系》(下),《哲学研究》2011年第2期;黄玉顺:《中国学术从“经学”到“国学”的时代转型》,《当代儒学》第2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白彤东:《经学还是子学——政治儒学复兴应选择何种途径》,《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1期。。
二、经学历史化与进步史观
经学观念的历史化有一个宏大背景,那就是文明比较的视野。较之中国古人为人类生活共同体所建构的非常完备的经学体系来说,当时中国人所了解到的周边国家在文明程度与人类共同体构造等方面与中国自身文明存在一定差异。基于华夏与周边民族的比较,先儒将自己的经典视为人类全部文明的普适性内容,将“经”定义为常道。近代以来国人理解经学的文明参照物由周边民族变为西方列强,尤其是受甲午战败的刺激⑦茅海建:《晚清的思想革命》,《历史的叙述方式》,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9年,第208页。,在西方近代欧洲中心主义的文野之辨及社会进化论的影响下,形成了以西方为新文明而自贬为落后的文明判断,导致对儒家政教与伦理的自我否定。
那个时代对人类新文明的期盼与信心超乎寻常,1930年,中华民国立法院院长胡汉民召集蔡元培、吴稚晖等人研究民法修订事宜,其核心议题有三个,是否要有姓、是否要有家庭、是否要有婚姻。他们一致认为,在不久的将来,这些氏族社会之物将会消失①赵妍杰:《家庭革命:清末民初读书人的憧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1—2页。。傅斯年就读北京大学时,其宿舍墙上挂着一幅字“四海无家,六亲不认”②王汎森:《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北京:三联书店,2012年,第44页。。如果人类社会进化到无姓、无家、无婚姻,这将是怎样的文明?与破除家庭相应的政治思潮则是破除阶级、废除私有制,追求大同。20世纪初中国涌现出无政府主义、世界主义、天下为公的政治思潮,以及后来对社会主义的接受,这与儒家传统中的大同理想不无关系。康有为、章太炎、吴稚晖、刘师培、孙中山、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熊十力等这些近现代有影响力的人物,看似有着极为不同的思想主张与政治立场,但在一点上是一致的,即人类社会无论经过什么样的发展阶段,迎来的最终阶段是相似的,那就是无家庭、无国界、无族群、无阶级、无政府的大同之世。中国近代以来,西方科学进步与社会进化论、民主思想、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等思潮东来,与中国儒家传统的大同理想相结合,形成了大同说、世界主义、无政府主义及社会主义等诸多政治思想形态,《礼记·礼运》篇所载大同理想是可以实现的。如果对世界文明的进步抱有这样的期待,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家政教尚有何价值可言?因此,民国时期将经学视为“国故”和古代政治统治工具的做法,究其根本,源于一种文明论的意识,即相信现代文明将有极大之进步,而以中国古代为故旧的、不合时宜的文明。
当时国人对文明进步的信心恰与西方的进步史观相应。这当然不是偶然的,西方近代以来的文明论及其历史观对近代中国有深刻影响。西方工业革命的成功带来了空前的文明自信,被认为是人类理性精神和自由的胜利,并且这种胜利可以无止境地持续下去,直至人类获得最完全的理性与自由。就西方的文明观与历史观的演进而言,在基佐看来,人类文明呈现出普遍的线性进步历史,从物质到精神,从社会到个体,较之东方文明的停滞,欧洲文明的演进不可阻挡,成为世界文明的中心③傅琼:《基佐文明进步史观述论》,《史学月刊》2007年第5期。。基佐的文明论深刻影响了福泽谕吉,清末国人东渡日本,又将这种欧洲中心主义的文明论带回中国,从而形成了中国自认愚昧、野蛮而以西方为文明的观念④刘文明:《欧洲“文明”观念向日本、中国的传播及其本土化述评——以基佐、福泽谕吉和梁启超为中心》,《历史研究》2011年第3期。。当然,基佐对中国现代文明史观念的影响只是西学东渐众多线索中的一条,人类进步的信念在康德启蒙理性精神中取得普遍化的哲学解释⑤傅永军:《启蒙与现代性的生成》,《东岳论丛》2008年第6期。。
然而问题在于,判断人类历史进步、辨别文明与野蛮的标准是什么?如果答案是理性,可是理性这个概念本身有待解释,且有工具化之嫌;如果答案是人类的自由,自由的概念同样多义,引起无数且无谓的争论。而且,这两个概念都来自西方历史。欧洲中心主义的问题在于以欧洲历史社会的演进当作人类社会的普遍法则,欧洲历史当作了人类普遍历史,从而导致对其他社会传统的粗暴解释。尤其是在文明观念与价值观念的判断标准上,近代欧洲将其所表现出的富强认定为人类文明的胜利,进而将欧洲的当代形态视为人类全部历史的目的,并以此为标准来评判人类不同社会的历程,从而形成所谓辉格史学。辉格史学指19世纪中叶之前英国辉格—自由党的某些政治家和学者对其历史观与政治信念的解释,他们相信,历史“是不断进步、由传统走向现代、由专制走向自由的线性发展,认为对历史人物的臧否都要放在这样一个目的论式的时间轴上去衡量”⑥霍伟岸、朱欣:《从辉格史观到语境主义:柏克政党理论的阐释及其方法论反思》,《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1年第3期。关于辉格史观可参见[英]巴特菲尔德:《历史的辉格解释》,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裴亚琴:《17—19世纪英国辉格主义与宪政传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这种欧洲中心主义史观构成了西方历史进步论的基本内容。
早期的严复与梁启超,及吴稚晖、陈独秀、胡适、陈序经等人都认为西方现代秩序构成了人类文明演进的重要标准,中国也必然走向这样的现代秩序,中国古代的世界观及其秩序构造因此变得愚昧。在这样的历史判断中,经学作为中国古代世界的文化反映自然成为负面的历史之物,这是西方的社会进化论、进步史观与辉格史学在中国的反响。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最先接受西方历史观的中国学者无不出于儒家,这并非偶然。虽然儒家传统尊奉古圣,但无不相信人类经由教化可臻至上之文明,西方文明的出现不正是往圣之理想的实现①袁进论述了清末民初反儒家思潮中儒家与西方历史进步主义之间的复杂关系,并批评当时学者过于简单地将儒家与西方思想对立起来的做法。见氏著《儒家与历史进步主义》,《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正如前论晚清革命者相信先秦儒家之大同理想即将落实在现代革命中。但对于那些思想深刻的儒者而言,西方现代发展出来的社会形态与儒家对理想社会的构想并不是一回事。严复、康有为、章太炎、梁启超等经过观察,从不同角度否认了西方现代文明即是儒家理想的实现。儒家固然相信圣人教化必然大行于天下,但这个过程未必是线性的,而是在文质互变中上升,也不必以特定的礼法为标准,而是以“仁”为普遍价值。就此而论,儒家不必从中国古代之礼法全然倒向现代西方之礼法,而应在彼此的礼法中观察其各自价值的实现程度。
在此过程中,经学应当形成自身的文明叙事,包括文明的价值理念和实现理念的制度方法。经学自身的文明自觉有赖于当代学者对西方文明历程的深刻觉察,西方文明本身也非线性发展,西方的古代文明传统对现代性的演化有深刻影响,现代文明所隐含的危机尤其需要返回传统的思想观念中加以克服。近代以来中国学者的文明想象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对中国固有之文明的评价,与他们对西方的认知有关。正如甘阳写道:“近百年来,中国人对中国的认识在相当程度上是由对西方的认识所规定。”②甘阳、刘小枫等:《古典西学在中国》(一),《开放时代》2009年第1期。晚清民国时人的西方认知存在巨大的想象空间,因而对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作了超乎寻常的判断。至少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看不到家庭、民族、国家之界限泯灭的迹象。而当我们对西方及现代社会予以更深层的了解之后,在中西文明比较的问题中上自然会产生新的见识。
现代西方所代表的人类方向并非纯善无恶,人类历史的经验也并非全然失效。所谓现代社会也是由传统社会长成的,并不存在现代与古代这两种截然对立的社会形态,就像晚清民国时人所想象的旧社会与新社会的二元划分那样。现代性是多元社会中的政治框架,本身并不包含特定的价值内容,除了自由这一价值内容的可能性条件之外。因此,现代社会的自由框架需要价值实质来填充,这样的价值供给往往来自各文明的传统。尤其是,现代性所蕴含的虚无主义问题无法通过工具理性在自由框架内解决,古代的宗教传统与美德伦理是西方个人主义的重要补充。与此相应,中国社会也需要在其现代性的自由框架中灌注中国的价值内容③吴飞认为,正如西方宗教对西方现代社会的奠基性意义,中国当代学者也应更加重视传统经学的品质,现代社会的文明危机需要返回到各自文明传统中去寻求解决之道。见氏著《从总体上比较中西文明》,《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年第6期。。基于对中西文明更为整全的观察,我们才能摒弃那种将不同社会的历史简化为线性进化的思维,重新理解古代文明传统与现代社会建构之间的复杂关系,这就要求我们在更基础的理论中来解释经学传统与现代中国的关系。
三、文明论视域下的经学观念
从文明论的角度看待经学,意味着将经学理解为一种文明的世界观及其价值理念。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更恰当地把握经学在儒家社会建构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而不只是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寻找有悖于现代社会的愚昧之处。“文明”概念本身包含着二重性,一是指人类历史上的诸多文化类型及其物质实体,二是作为人类应当追求的理想价值。就前者而言,人类文明实践在历史中呈多样化;就后者而言,一般认为真正的文明应当是普遍的。也正因如此,中国近代以来的知识人以西方文明为普遍,那么中国固有文明的地位就成了疑难问题。骤然判断文明之为价值理念是否普遍,进而断定人类历史是否万流归一可能是仓促的,我们需要通过世界不同文明之演进历程的比较来总结文明内容的结构性。我们应将经学理解为一种文明内在结构中的最大共识,倘若没有这种文明共识,一个超大规模的人类生活共同体历经数千年而未崩解,这是无法想象的。
将经学视为中国的文明共识需要回应三方面的理论疑难,一是中国古代并不存在完全一统的思想结构内容,诸学派之间与学者之间存在相当的思想差异,此共识在中国历史中是否存在,如何存在?二是即便我们承认经学为中国古代文明共识,但如前文许多学者所理解的那样,古代文明之物何以施用于现代?三是现代社会多元一体,个体基于其理性独立地认识世界,此共识何以加于现代社会?
首先,将经学视为一种文明共识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古代的经子关系。接受了现代学术自由与文化多元价值观的学者会认为,正是因为经学与政治权力的结合压抑了诸子学,汉代经学的开始就是战国诸子百家争鸣时代的结束。胡适坚持认为诸子不出于王官学,即是主张诸子学自身的独立价值,主张学术思想的多元竞争而反对任何意义上的官学①胡适:《诸子不出王官论》,《中国哲学史大纲》,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99—306页。。对此有学者评论道:“胡适的‘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在明确否定经源子流的观点同时,也淡化了传统四部知识的共同起源与何为中华文化主流精神的问题。”②吴根友、黄燕强:《经子关系辨正》,《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7期。
理解经学与诸子学的关系,需要深入探究二者学术思想的目的与性质。诸子学兴起于战国,其时封建秩序崩解,中国历史社会发生深刻变化,学术界或称之为“周秦之变”。如何重建社会秩序,是诸子百家共同关注的问题,西汉史官司马谈谓之“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③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88—3289,3288—3289页。。经过汉初数十年的恢复,何种思想学说可以反映汉朝立国以来的道路选择,汉代社会的伦理基础是什么,政治合法性从何而来,这些基础性的理论问题亟待解决。如果国家不能基于一定的理论共识加以调整,社会仍有崩解之虞。黄老之学主张内虚静而外用刑法为治,这主要是一种关于治理策略的学说,并不能反映中国社会的基本信仰和基础伦理,也不能阐明政治合法性的来源以塑造稳定的政治秩序。同理,正如《汉书·艺文志》所总结的,诸子皆“六经之支与流裔”④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46页。,儒家、道家、法家、墨家、阴阳家、农家、兵家、纵横家等子学各有其思想指向与现实职守,但任何一家都不能完全代表中国社会,不能完整体现基本世界观、价值观,不能有效提供社会中的信仰、伦理与秩序的价值原则。
五经是先秦时期的历史记载,也是文明基本内容的记载,其中包含了天道与鬼神信仰,社会伦理与政治原则,社会生活的礼仪习俗,经典文献与教育体系,仁义礼智信的基本价值观念等。显而易见,较之诸子学,五经正是华夏古典文明的全面体现,是中国社会最广泛的思想共识与价值共识,也因此成为诸子学的思想文化渊源,构成后者的文化母体。诸子学或是对五经相关内容的补充与发挥,或是异于五经的独特思维方式。司马谈所述阴阳家、儒家、墨家、法家、名家皆有其职守与功能,为社会治理所不可或缺,诸子之间不必然是理论竞争关系,也可以是相互协作的关系⑤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88—3289,3288—3289页。。如此来看,经学与子学可以严丝合缝地纳入社会建构,是否意味着不存在任何思想分歧与理论分歧的余地?经学的统一指的是内容上的至大无外,而非观点上的整齐划一。经学具有丰富的层次结构,文明共识是经学的基底,在这个基底上长出了许多理论分枝,形成诸子百家的思想分歧与治道差异。
经学中的天道观念与五常之道是华夏文明的底层共识,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存在争论的不同学派;并且于经学之外仍有不同的思想体系活跃于中国社会,形成了以儒教为主干,以道教、佛教及其他宗教信仰为补充的文化体系。儒教与道教、佛教的关系从结构上看类似经学与子学的关系。儒教的存在并不完全取消民间宗教的生存空间,民间宗教也并未挑战儒教的主导地位,二者的演变构成中国传统社会的动态结构。之所以说这是一个动态结构,是因为自秦汉至近代的中国历史长达二千年,其间社会形态发生多次变化,作为反映中国社会结构之共识的经学显然也不可能一成不变,而是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中国历史上经与子也非泾渭分明,后世学者往往采子学以补经学,名为经学,实用子学,这表明中国古代的经学体系其实是一个动态开放的系统①参见吴根友、黄燕强:《经子关系辨正》,《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7期。。“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庄子·德充符》),将经学视为文明共识,是与其他文明世界观及其生活方式比较的结果。自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内部来看,无疑可以看到多元、差异的一面,如何将其视为整体,我们可以总结经学所代表的古典世界观与价值观共通的一面,虽然这并非人人所理解、人人所遵从的。
其次,古代社会与现代社会并非泾渭分明的两个社会、两种文明。社会构造从内到外可以划分为多个层次,在物质现实的外在层面,古今之间有显著差异,但就其内在的精神生活与价值观念而言,古代社会与现代社会又并非截然分判。语言、文字、伦理、风俗等作为内与外的衔接,在不同的民族与社会呈现出各不相同的特点。换言之,西方之谓现代普遍性之最显著者存在于物质世界,而一旦关涉内在的精神生活,以及与精神生活有关的语言、习俗、制度等事项,当今世界诸文明传统之间的差异仍然是显而易见的。
近代以来欧洲的进步史观与辉格史观将世界历史的进程简化为欧洲历史的推演,这种欧洲中心主义思维难以内在地获得证明。当代中国社会虽然受西方影响,但中国人的文化身份与精神信仰是什么?面对这些问题,何种普遍的文明观念可以提供答案?人首先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人,人类当下如何生活是眼前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能猝然判断普遍的“人”是什么,不能归纳出人类精神进化的线性道路,那么就应如当下所是的样子生活,而我们的当下所是,其实正在践行着历史期待,正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短语所传达的那样。“中华民族”是这片土地上古老人群的现代集结,“伟大复兴”则是历史与现代之间难以割舍的关联,没有“历史的期望”,现代生活的意义便无所附着。
就此而论,经学所包含的文化内容并非全然属于过去。历史是经学中固有的要素,经学与历史的关系是自经学产生之日起就有的老问题。一方面,经学记载了先王先圣之言行事迹,本身就有史的性质;另一方面,经为常道,经学即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大经大法,具有普世效力。先王政典已为陈迹,如何能对后世的国家政治与社会治理产生实际作用?以汉世为例,如果我们把一个共同体的建构区分为道与法两个层面,那么汉代经学首先塑造的是汉世所应遵循的道,此“道”包含了精神信仰与世界观、伦理秩序与价值观、历史哲学以及生活世界的秩序原则等。“法”指基于道所制定的礼法制度,包括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社会组织及生活习惯等方面。
汉代所行之法与汉代经学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无疑,汉代经学中所包含的伦理规范与习俗对社会组织形态与生活内容均有重要影响,但经学所载先王之事不能直接当作汉代制度,“汉承秦制”这一说法提示我们,汉代所行之制度有具体的历史生成逻辑,而非对经学、经制的直接应用。《白虎通义》是对汉代今文经学的系统性总结,对汉代儒家社会之建构有奠基作用,体现为以阴阳五行为主要解释模式的天道,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人伦制度,以皇帝王霸之退化为主要叙事的历史观,通过封禅、灾祥之说所建立的天人联系,以及寓郡县于古代封建制度的政治思想。我们从中可以观察到,《白虎通义》之世界观、伦理观念及政治原则确实有效地存在于汉代人的信仰与实际生活中,但《白虎通义》所诠释的许多礼制与政治构造方式并非汉代制度的直接反映①参见肖航:《王道之纲纪——〈白虎通义〉政治思想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这说明,尽管经学中的价值原则、制度原理对汉制变更有深刻影响,也为汉代政治建构所继承,但前朝之法非本朝之法,制度不同并不意味着经学之政治功能的失败,它只是在更基础的层面起作用。
在董仲舒公羊学与《白虎通义》中,先王与后王、前朝与本朝之间的制度关系是通过“通三统”的理论来表达的。“通三统学说最为精深的思想意义不在于‘三’,而在于‘通’。正是一切历史社会有着类似的义理结构与治理秩序,‘三’才能够‘通’,而‘通’也就构成了‘三’的基础与依据。”②秦际明:《“通三统”与秩序的政教之旨》,《学海》2016年第5期。不同时代的制度变革是经学本身已经考虑到的历史变化,并从中总结出一般性原理,今天谓之理论,古代则谓之“道”。当然,“道”包括理论,而不只是理论,“道”包含着比理论更多的世界观的根底内容,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从现代社会科学的意义上去理解董仲舒所谓的“道不变”。
经学包蕴的道与法,发挥作用的条件与方式是有差异的。“法”并不统一,是先王之道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应用,具有一定的规范性意义,但不一定具有普适意义。在这个意义上,后世对先王之法应当有所损益,当世应遵时王之法而非过往之法。法的创制离不开道的指导,经学的根本意义在于道,而不在于法。在时王之法普遍有效的情况下,经学便回归思想学术与文化教育领域;而当秩序崩解之际,经学之道与先王之法的范例就成为收拾人心、重建新王之法的文明火种。经学经邦济世之大用即在于此。去古愈远,离先王之时代也就越远,五经的制度意义就越低,对圣人之道的阐释也就更为集中。经学之于中国现代社会亦是如此,法变而道不变。具体而言,尽管新时代的物质环境与制度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学蕴含的作为中华文明核心要素的世界观、价值观始终充当着文化基因与文明信念,并持续发挥作用。
再次,就其感情生活与信仰生活而言,作为理性存在者的“人”更多地体现为理想而非现实。人的感情与信仰需要不是自足的,在相当程度上不是由理性推导出来的,而是来自文化传统、宗教传统与生活环境的熏陶与塑造。人非独居动物而是社会动物、城邦动物的本质即在于人对于社会认同的内在需要。人组成群体所需要的认同必然建基于广泛的世界观与价值观上的共识,并由此构成不同的文明传统与社会习俗。文明、国家和社会的构成系统中必然有最基本的共识内容,这些内容形塑了共同的生活方式。基于共识可以生长出不同的理论分支,但这并不妨碍前者在社会中的普遍意义。现代社会所说的文化多元、言论自由、学术自由等观念与经学未必矛盾,因为经学的基础是中国之为文明的基本共识内容,在此基础上亦有思想与理论的不同。现代所谓多元与自由并不应用于建构社会的基本共识层面,而是针对基本共识层之上的思想层次。
结论
在现代的中国哲学史与思想史叙事中,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以来现当代学者对中国古代的定义和批判,同中国古代学术思想自我理解之间的鸿沟。将经学理解为史学,并进一步视之为历史之物,否认经学对恒常之道的蕴含,甚至仅仅将经学视为政治统治工具,将经学与传统思想内容区别开来,这与先儒对经学的理解相去甚远。我们发现,从历史与政治的角度去理解经学并不能体现出经学的主要内涵,以此来批评古代的经学观念,古代学者必不能屈服。在现代学术话语中,将经学理解为中国之为文明的基本共识,理解为一种文明的核心内容,更能体现经学的基本内容及其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也因此可以弥合古今之间看待经学的巨大差异。
经学作为王官学并不意味着思想专制,而是一种文明形态所表现出的共同生活方式。经学成为汉代官学不仅仅出于国家政治的选择,而是战国以降在寻求秩序重建过程中得出的基本共识。一种文明的生活共同体需要取得基本共识以形成基础性的内在秩序,其主要内容包括关于世界观的神话叙事与历史叙事,共同的伦理观念、政治原则、社会组织形式和日常生活中的礼仪习俗。五经成为官学不是偶然的,这是由五经及其解释系统所包含的一个完备的文明体之内容决定的。离开了五经,诸子百家中的任何一家都不足以单独构成一个社会的思想文化底层设定的结构性需要。从战国诸子对秩序的寻求到汉代经学给出的系统回答,其中包含着中国社会建构的内在逻辑,而非仅仅出于政治权力的意志。例如《仪礼》所载婚礼、冠礼、丧礼等制度,构成华夏文明共同的生活习惯,这些源于礼法习俗的生活方式与专制显然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
英国政治学者芬纳在《统治史》中以国家与宗教的关系为纲,归纳了世界历史上不同类型的政体,却认为儒家社会难以容纳其中①[英]芬纳著,苏百亮、黄震译:《统治史》卷1,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2—23页。。原因在于,儒家社会中的宗教要素消融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政治,在整个国家与社会层面不存在一个统一而独立的宗教性组织。儒家事实上起到了与西方宗教相似的社会作用,但儒家显然又与西方的宗教有所区别。作为儒家社会之共同经典的经学不只是历史政治之物,经学中所蕴含的世界观、价值观以及思想方式仍然鲜活地体现于中国现代社会。将经学视为中华文明的共同经典是恰当的,经学事实上包含着文明的基本要素。
将经学视为一种文明论视野下的结构性要素与文献体系,有助于理解今天我们所要寻求的哲学话语与文化建设所为何事。一个社会中的自由与多元是建立在文明共识基础上的,只有基于这种底层共识,人类才能组织为不同规模的生活共同体,而不至于陷入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自然状态。如此才能像《汉书·艺文志》所建构的经子系统那样,将当代社会中多元的思想观念与文化主张纳入到系统结构中去,将这些不同的思想主张安排在这个系统的不同位置。中国有独特的底层世界观设定,底层世界观的差异并不妨碍表层理论资源的相互借鉴,形形色色的哲学主张在中国文明底层逻辑的基础上仍然可以自由地发挥作用。古代经学与子学的结构安排,儒家与民间宗教之关系,印度佛教的中国化,及三教合流的社会思潮,为我们提供了如何在华夏文明共识的基础上,将社会文化与宗教信仰融合为一个动态稳定系统的历史经验。经学作为文明共识的现代阐释,将为当代思想文化整合与中国话语建构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