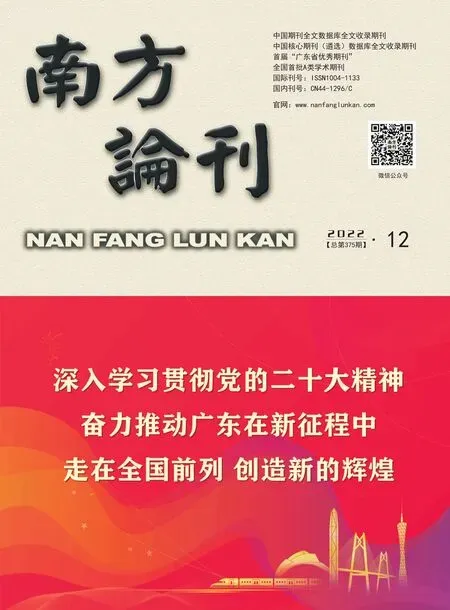拜登政府“印太经济框架”的实质及中国的应对
宋子丰
(北京外国语大学 北京 100089)
2022年2月拜登政府发布《美国印太战略》文件,将构建“印太经济框架”作为该战略行动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2022年5月23日,美国总统拜登在日本访问期间,正式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框架”(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IPEF),初始成员国包括美国、韩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越南、文莱等13个国家。太平洋岛国斐济在三天后宣布加入该框架,成为第14个初始成员国。这一框架作为美国“印太战略”的经济分支,旨在遏制中国发展、巩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经济霸权地位。本文试图探讨拜登政府提出“印太经济框架”的原因,分析“印太经济框架”的特征、实质及前景,并就我方的应对提出建议。
一、拜登政府提出“印太经济框架”的原因
“印太经济框架”旨在促进各成员国在贸易、供应链、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资合作,具体包含四大支柱领域:(1)贸易:推动高标准、包容、自由及公平的贸易,鼓励创新刺激经济活动和投资,促进可持续和包容性经济增长,加强数字经济合作;(2)供应链:提高供应链的透明度、多样性、安全性和可持续性,确保主要原材料、半导体、关键矿物供应稳定并掌握清洁能源技术;(3)清洁能源、脱碳和基础设施:加快清洁能源技术的开发与应用,深化技术、金融合作,支持可持续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竞争力和互联互通;(4)税收和反腐败:促进公平竞争,制定有效的税收、反洗钱和反贿赂制度,遏制印度-太平洋地区的逃税和腐败现象。
拜登政府提出印太经济框架,是内外因素共同推动的结果。面对不断崛起的中国,美国希望巩固地区战略优势;另一方面,美国国内经济下滑明显,民主党面临中期选举压力。具体而言,拜登政府提出印太经济框架的原因有以下三点。
首先,美国将中国视为全面竞争对手。自特朗普上台以来,中美关系发生重大阶段性变化。特朗普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修正主义国家”,拜登执政后将中国视为“最严峻的竞争对手”和“21世纪最大地缘政治考验”。拜登政府推出“印太经济框架”,就是希望遏制中国经济发展、重塑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霸权地位。
其次,美国谋求在印太地区的经济霸权。特朗普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P)之后,美国在亚太地区经济事务中处于被“边缘化”的局面,拜登希望尽快加强与亚太地区的经济联系。美国退出TPP之后,剩下的成员国宣布成立《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CPTPP),但拜登政府无意加入CPTPP,认为该协议依然存在缺陷,不足以应对印太地区的经济挑战。
第三,促进美国自身经济发展。印太地区是最具经济活力与潜力的地区,美国与印太地区的双边贸易为美国带来的外国直接投资高达9000 亿美元,同时创造了300多万个工作岗位,因而印太地区对美国贸易投资与国内就业增长具有重要意义。拜登政府在《美国印太战略》报告中称,美国是印太地区的经济大国,“印太经济框架”将加强美国与该地区的联系,“为今后几十年的技术创新和全球经济发展绘制蓝图”。美国增强在印太地区的经济领导地位,将对其本国企业与工人十分有利。
二、“印太经济框架”的特征与实质
“印太经济框架”以美国利益为优先,内容空洞乏味,印太地区国家实际参与热度不高。遏制中国、重构亚太乃至全球经济体系,是“印太经济框架”的实质。
(一)美国利益优先
在白宫声明中,开篇即强调加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经济领导地位”,确保“美国工人、小企业和牧场主”在该地区的竞争优势。“印太经济框架”表面上是为印太国家考虑,却只字未提双向开放市场、减免关税等真正有助于成员国经济恢复的实际举措,并不会带来互惠互利的经济效应。而在俄乌冲突、疫情反复、经济低迷的大背景下,各国都需要尽快复苏经济。“印太经济框架”实际上是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单向自利的区域贸易体系。2022年9月“印太经济框架”首轮部长级会议之后,印度宣布暂时退出贸易领域的谈判,其理由正是“暂时看不到(对印度的)好处”。
(二)内容空洞模糊
“印太经济框架”与其他传统贸易协定不同,并非通过降低关税、减少监管等“市场准入”机制向其他国家开放自由市场,而是要促进建立“共同制定标准的伙伴关系”。拜登政府发起“印太经济框架”,绕开了美国国会、不需国会批准,灵活性相对较大、对成员国实际约束少,既没有开放合作共赢的经贸实质条款,也没有关税与技术标准的准入门槛,更无逐步施行的时间表与路线图,只像是“某次务虚会的表态与站台”[1]。对此,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萨洛尼·夏尔马作出了掩耳盗铃式的评论,“不要在意具体字眼,要关注‘印太经济框架’将产生的强烈影响”。
(三)参与热度较低
东盟国家对美国孤立遏制中国的“新冷战”并不感兴趣。中国连续5年成为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在半导体、清洁能源领域均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2022年1至2月,东盟与中国贸易额高达1365.9亿美元,同比增长了 13.1%[2]。2022 年初,由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与东盟 10 国组成的全球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自贸区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已正式生效。在RCEP框架下,各成员国简化贸易规则、大幅降低关税,有效促进了彼此之间的务实合作。美国企图单向政策颠覆现有亚太经贸格局、将中国封堵在美国主导的供应链体系之外,这一图谋与东盟各国的利益相违背,必将失败。此外,一些亚洲国家之所以选择加入“印太经济框架”,实际上是希望美国重返“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以帮助本国产品进入美国市场[3]。然而美国没有给出进一步开放市场的承诺,各国积极参与的热情大打折扣。
实质上,美国是借“印太经济框架”之名,构建封闭排他的“小圈子”,以达到遏制中国、重构亚太乃至全球经济体系的目的,“印太经济框架”只是服务美国地缘政治竞争的工具。虽然美国白宫发布文件称“印太经济框架”旨在促进经济体的韧性、可持续性、包容性、经济增长、公平性和竞争力,促进印太地区合作、稳定、繁荣、发展与和平,但美国打着“多边主义”旗号声称要促进地区繁荣,实际上是在削弱中国经济影响力、刻意打造排斥中国的经济框架、重塑美国主导下的亚太地区经济秩序。拜登政府在其《印太战略》报告中直言不讳地指出打压中国的意图:“美国之所以更加关注印太地区,正是因为该地区如今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尤其是中国的挑战。”“印太经济框架”作为美国“印太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寻求在数字经济、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制定规则、建立标准,同时建立排除中国的供应链体系,这一打压中国、遏制中国经济发展的意图昭然若揭。
三、“印太经济框架”的前景
“印太经济框架”实施前景暗淡,将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拜登领导的美国政府内外交困,持续推进该框架的动力不足;虽然该框架对华可能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但负面冲击必将十分有限;成员国不仅对美国已经产生信任危机,还因各自利益诉求不同、内部差异悬殊,对该框架的实际效力存有诸多质疑。
(一)美国推进动力不足
2022年11月美国迎来中期选举,两年后又将举行总统大选,拜登所在的民主党一旦在这两次选举中落败,“印太经济框架”的未来命运就充满了不确定性,甚至有可能出现特朗普退出TPP那样的尴尬局面。“印太经济框架”无需国会批准,其效力只由行政令提供保障和支持,更增加了这一风险出现的可能性。此外,美国国内供应链混乱、劳动力不足、通胀加剧、民众积怨颇多,俄乌危机又进一步拖累了美国经济,拜登政府能否在该框架上始终投入大量精力和资源,令人存疑。
(二)成员国信心缺乏
从成员国的角度来看,“印太经济框架”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成员国对美国已经产生信任危机。2017年特朗普上任不久就宣布退出TPP, 给各成员国留下“心里阴影”。如果2024年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美国是否又会掀起一股“退群”浪潮,“印太经济框架”是否会遭受“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一样的命运?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对外政策缺乏稳定性、难以预测,各国仍感不安,对美国是否愿意对新框架投入太多也相当怀疑。对美信任之崩塌,正如日本京都立命馆大学教授渡边博明所言,“当美国对其他国家说它想干什么的时候,真的很难让人相信它的话。”[4]
第二,成员国与美国存在利益冲突。“印太经济框架”虽然确立了实现经济相互连接的目标,追求数字经济的高标准互联互通,在跨境数据流动和数据本地化存储上确定规则等,但这些目标与多数成员国国内法律法规和市场态度不相吻合[5]。此外,“印太经济框架”在推进贸易自由化方面并未采取实际措施,并未给予成员国更多进入美国市场的机会,令印太地区国家倍感失望。换言之,拜登政府提出“印太经济框架”并不是要进一步开放美国市场,并非旨在振兴印太地区各国经济。拜登继承的是“美国优先”的战略思维,铭记在心的是要为美国“建设更具活力、更强大的经济并为工人家庭创造数百万个高薪岗位”。
第三,成员国内部发展并不均衡,难以协调。“印太经济框架”14个成员国中,既有美日韩澳新等发达国家,也有印度、马来西亚、越南等发展中国家。各国市场开放程度、产业化水平、政策成熟度不尽相同,制定均衡标准将是一大挑战。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贸易的态度也不尽一致,前者更强调公平贸易,后者则强调自由贸易。在各类具体规则制定上,发达国家的标准也难以为发展中国家接受,例如在劳工和环保标准、数据传输、电子商务等领域,越南、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就难以对接发达成员国的标准[6]。
(三)对华影响有限
“印太经济框架”的出台,一方面对中国确实可能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和挑战。首先,中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影响可能被弱化。“印太经济框架”成员国大多属于中国地理周边国家,美国通过塑造遏制中国的地理周边环境,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其次,全球供应链体系“去中国化”。为全面压制中国科技发展,美国试图将中国排挤出芯片、重要矿产等全球供应链体系,一方面通过建立“四方联盟”(美、日、韩、台)以控制全球芯片供应,另一方面通过重塑全球关键矿产品产业链布局,对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所需的关键矿产品的供应造成冲击。
另一方面,“印太经济框架”对中国的冲击必然是有限的。首先,印太各国与中国经贸往来频繁,无论通过“一带一路”还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各国都从与中国的合作中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这些国家很难拒绝规模、潜力巨大的中国市场。其次,中国与多数印太国家已形成稳定的价值链供应链,印太地区也已形成多重多层经济圈格局,美国发起内容空洞、缺乏激励的印太经济框架对各国并没有强烈的吸引力,也难以对业已成熟的供应链体系、经济圈造成巨大冲击。
四、中国的应对措施
2022年7月,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东盟秘书处演讲时,指出当前亚洲两种截然不同的走向:“一种是坚持开放的区域主义,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坚持发展优先,致力互利合作,推动地区国家尽早走出疫情实现全面发展。另一种是重拾冷战思维,大搞封闭式阵营化集团政治,把地区国家按价值观分类,将区域经济阵营化,甚至试图将亚太安全北约化。”[7]美国通过印太经济框架发动“经济新冷战”,迫使印太地区国家选边站队、成为大国博弈的棋子,其遏制打压中国、自私自利的政治目的众目昭彰。对此,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应对“印太经济框架”带来的冲击和挑战。
首先,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落实全球安全倡议。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大力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努力为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坚决反对价值观外交、贸易,摒弃小圈子和零和博弈,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
其次,坚定践行开放的区域主义,促进地区团结合作。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CP)生效实施,加速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向更高水平迈进;积极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与更多国家商签高标准自贸协定;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沿线各国的经贸合作;深化澜湄合作机制,继续发展与东盟的密切关系。
最后,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鼓励自主创新。“打铁还需自身硬”,面对美国试图通过“印太经济框架”排挤中国的企图,我们应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加快国内改革步伐,推进经济转型升级,降低对外依存度,建立独立自主可控的关键技术与供应链体系,减少外部负面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