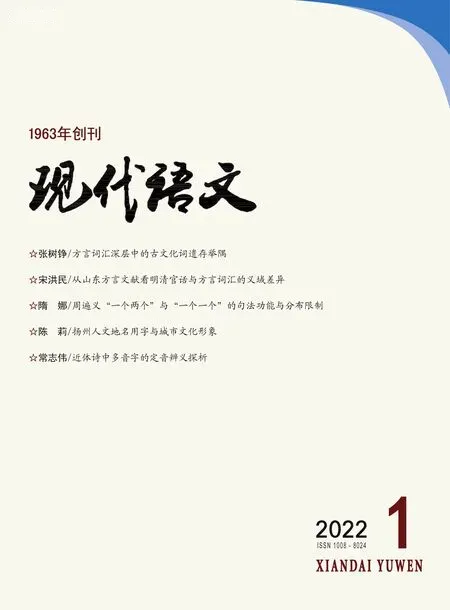四川方言词语“????”考释
王洋河
摘 要:四川方言是西南官话的重要组成部分,保留了大量古语词。从明代至今,不断有学者考证四川方言中的疑难本字,成绩斐然。目前,还未有学者详细考证“”一词,“”乃临时所造的记音字,其本字为“妈”,变异原因是读音的鼻化。
关键词:四川方言;本字;“”
一、四川方言古语词本字考证研究
四川方言是西南官话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北方方言,使用的范围大致包括今重庆、四川、云南、贵州、湖北等地域,其语音、词汇、语法与汉语普通话有很大一致性。由于历史移民的原因,四川方言受到湘方言、闽方言、客家话的影响[1](P10)。尤其是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大量来自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广东、山西、陕西等地的移民迁入四川地区,使得重庆、四川境内的方言面貌呈现出复杂化、多元化的态势。需要指出的是,四川方言是四川和重庆境内的主要方言,相比而言,湘方言、客家话、闽语的使用范围则十分有限。
自近代以来,不断有学者对四川方言词汇进行了深入研究,如缪树晟《四川方言词语汇释》、黄仁寿《蜀语校注》、徐世群《巴蜀文化大典》、黄尚军《四川方言与民俗》、蒋宗福《四川方言词语考释》、纪国泰《〈蜀方言〉疏证补》、汪启明等《中上古蜀语考论》等。此外,黄侃《蕲春语》、姜亮夫《昭通方言疏证》、杨树达《长沙方言考》等研究湖北、云南、湖南方言的著作,对考证四川方言词汇亦有较大帮助。
李如龙指出,汉语方言是历史上形成的,各地方言中都不同程度地保存了一些古汉语的成分,这些方言材料对于古代汉语、汉语史的研究是极端重要的[2](P9)。四川方言同样保留了大量古语词,这些古语词在现代汉语中已逐渐消失。黄侃《蕲春语》云:“固知三古遗言,散存方国。考古语者,不能不验之于今。考今语者,不能不原之于古。”[3](P413)扬雄《方言》、郭璞《尔雅注》、明代李实《蜀语》、清代张澍《蜀典》、清代张慎仪《蜀方言》、民国唐枢《蜀籁》等,均记录了不少的四川古方言词。就当前学界的研究来看,王文虎、张一舟、周家筠《四川方言词典》,蒋宗福《四川方言词语考释》,梁德曼、黄尚军《成都方言词典》,杨小平《南充方言词语考释》等均考证了大量四川方言词语,崔荣昌《四川方言研究述评》则对历代四川方言词语研究予以了梳理与总结。
对四川方言中的古语词进行考证,不仅有助于梳理汉语词汇的发展演化过程,同时亦有利于深入挖掘巴渝本土文化。其中,蒋宗福的《四川方言词语考释》、杨小平的《南充方言词语考释》在古语词考证中取得显著成绩。例如:
衁,《说文解字·血部》:“衁,血也。”《左传·僖公十五年》:“士刲羊,亦无衁也。”该词作“衁子”,又作“血旺”[4](P689)。
?,《字汇·贝部》:“?,贪财貌。”《广韵·候韵》:“?,?,贪财之貌。”四川、湖南等地均用此“?”。杨树达《长沙方言考》云:“今长沙谓多以物入己曰?,又曰。”
閜,《说文解字·門部》:“閜,大开也。”《广韵·马韵》:“閜,大裂也。”四川方言中亦是指裂缝、裂开。
詑,《说文解字·言部》:“詑,沇州謂欺曰詑。”《玉篇·言部》:“詑,谩而不疑。”《类篇·言部》:“詑,欺罔也。”四川话中读[tang],亦指欺骗、诈骗[4](P651)。
倯,扬雄《方言》卷三:“庸谓之倯,转语也。”郭璞注:“倯,犹保倯也。”《巴县志》卷五《礼俗·方言》:“蜀人谓猥琐可憎曰倯。”四川方言中,“倯”亦指慵懒、猥琐。
臑,《广韵·虞韵》:“臑,嫩软貌。”《楚辞·招魂》:“肥牛之腱,臑若芳些。”《蜀语》:“不脆曰臑。臑音如。”绵阳、重庆等地方言依然说“臑”。
搣,《说文解字·手部》:“搣,?也。从手烕声。”《广韵·薛韵》:“搣,手拔也。”《蜀语》:“手裂物曰搣。”
茹,又作“?”。《广雅·释诂》:“?,塞也。”王念孙疏:“?,或作‘茹”。《汉语大字典》引《唐律疏议·杂律》:“诸船人行船、茹船、写漏、安标宿止不如法,笞五十。”长孙无忌疏:“茹船,谓茹塞船缝。”
敹,章太炎《新方言·释器》:“凡非绽裂而粗率缝之亦曰敹。”该词在先秦时期已经使用,如《尚书·费誓》:“善敹乃甲胄。”孔颖达疏:“郑云:‘敹,谓穿彻之。谓甲绳有断绝,当使敹理穿治之。”《新唐书·藩镇传·程日华》:“敹甲训兵。”《蜀方言》:“粗略治衣曰敹。”
奓,《说文解字·奢部》:“奢,张也。从大者声。凡奢之属皆从奢。籀文‘奓。”《广韵·麻韵》:“奓,张也。”《玉篇·大部》:“奓,下大也。”重庆、四川方言中,“奓”亦指张开。
揾,《说文解字·手部》:“揾,没也。”段玉裁注:“没者,湛也,谓湛浸于中也。”唐代李肇《唐国史补》卷上:“旭饮酒辄草书,挥笔而大叫,以头揾水墨中而书之。”
啰謰,该词原作“謱謰”,《说文解字·言部》:“謰,謰謱也。”東汉王逸《九思·疾世》:“嗟此国兮无良,媒女诎兮謰謱。”洪兴祖补注:“謰謱,语乱也。”四川方言中,作“啰謰”,指人啰嗦。
捼,《说文解字·手部》:“捼,推也。从手委声。一曰两手相切摩也。”《广韵》:“捼,捼莏。”《集韵》:“捼,揉也。”今四川方言中,还有“捼面、捼衣服、捼脚、捼背”等说法。
魌头,本指古代驱鬼时扮神者所戴的面具。《周礼·夏官·方相氏》:“方相氏掌蒙熊皮。”郑玄注:“蒙,冒也。冒熊皮者,以惊驱疫疠之鬼,如今魌头也。”王筠《说文句读》:“?头,即今假面。”民国十三年《江津县志·风俗》:“古礼有方相、?头执戈,击圹四隅之说,此其类乎?”[4](P541)现代四川方言中,“魌头”是指便宜的东西。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四川方言中的许多语词似乎很土,却是渊源有自,由于语音的演变,即使是当地人也往往只会说而不知道其本字,当需要形诸书面时,只能根据其读音临时造字。一旦能够考证出其本字,其语音、语义的演变便会豁然开朗。令人遗憾的是,四川方言中的有些词语,仍然未能考证出本字。这些词语并不是汉语体系之外的,只是由于语音变异、词义发展等原因而难以考证。比如,“”一词在四川方言中使用十分广泛,“”字显然是该词语通行后据其读音所造的形声字。一个词语不会凭空产生,那么,其本字是什么,其间又经历了怎样的演变历程?本文试就此加以考辨。C8E55514-531D-42F5-A73B-86BE2AFDB859
二、“”的词义来源
《汉语大字典》对“”的解释是:“方言。小儿称饭为,《蜀籁》:‘隔壁子炖鸡又炖膀,我家还在饿。原注:‘,饭——小儿语。”[5](P4741)“”主要用于西南官话中,如《成都方言词典》:“,(儿语)喂小孩儿吃饭:饭/再一口。”“”,“(儿语)饭:来吃。”[6](P336)
晚清拟话本小说《跻春台》系用四川方言创作,其《双金钏》云:“妈也,娘呀!你今一旦归泉壤,谁与你儿洗衣裳,补巴袍儿油泡涨,定要虱子咬成疮。油盐柴米无一样,举目无亲甚惊慌,你儿哪去寻。”在蔡敦勇校点本中,“”作“”,理由是《康熙
字典·米部》“”字引《篇海》,谓“”同“”[7]。
我们认为,蔡本校改不当。《双金钏》此段中,“壤、裳、涨、疮、样、慌、”押韵,改为“”则已出韵。蒋宗福指出,《跻春台》光绪刻本实作“”,是《跻春台》作者自造的从食、由莽得声的方言字,点校者由于不理解“”这一词语,因而失校[4](P372)。此论甚确。
“”是单纯为记音而临时所造的字,又写作“”,两字唯声旁不同。《说文解字》《龙龛手鉴》等字书及
《广韵》《集韵》等韵书均未收录该字,唯《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据方言材料收录“”字。
从词义来看,“”为儿童用语,特指小孩吃的饭。比如,重庆涪陵方言:“娃儿,乖,快来吃。”再如,四川童谣:“月亮光光,要吃;还没熟,要吃腊肉;腊肉还没耙,要吃糍粑。”
我们认为,“”一词应是由表示乳汁义的“妈妈”词义引申而来,乳汁是婴儿最早的饭食,后扩大指“小孩所吃的饭食”。在中国各地方言中,均存在着以“妈”表示“乳汁”“乳房”义。例如:
[妈头]
山西襄汾、安徽阜阳等地。妈头,指奶头;乳房。
江淮官话,安徽淮南。《淮南民歌》第一辑:“小腳好比钩羡井,妈头好比迷人桥,吐沫子好比迷魂汤。”
[妈子]
西南官话,如湖北天门等地。妈子,指奶头;乳房。
中原官话,如河南固始。妈子,指奶;乳汁。
[妈妈]
东北官话,吉林白城、辽宁锦州。北京官话,如北京“吃妈妈”。妈妈,指乳房;乳汁。清李光庭《乡言解颐》:“谣曰:下雨了,刮搭搭,小孩醒了吃妈妈。京师谓乳为咂咂,乡人直谓之妈妈。”1933年《顺义县志》:“小孩吃乳,亦称吃妈妈。”
冀鲁官话,河北唐山,河北昌黎、保定,天津,山西广灵,山东济南、淄博。如“小孩吃妈妈”。蒲松龄《聊斋俚曲集·禳妒咒》:“听说你媳妇子把你那妈妈都铰去了,你怎么受来?”
中原官话,江苏徐州,山西临汾,陕西宝鸡,山东东平、菏泽、平邑等地,如“小孩吃妈妈”。西南官话,湖北武汉、宜昌。
[妈奶子]
中原官话,山东郯城。妈奶子,指乳房。
由此可以看出,在东北官话、中原官话、西南官话等方言中,“妈”表“乳房”“乳水”义都比较常见。不仅是汉语各大方言中“妈”可表“乳汁”义,在世界主要语言中,“妈”亦与“乳汁、乳房”有着直接的联系。任继昉《汉语语源学》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婴儿感兴趣的不仅是妈妈或爸爸,还有妈妈的乳房或乳汁,这也是婴儿最早、最经常接触的事物。因此,许多语言中的mama还表示“乳房”或“乳汁”。英语的mamma,西班牙语的mama,德mamma和法语的mamalle均为乳房之义。在汉语的一些方言中,“妈妈”可以指乳汁。婴儿逐渐懂得,只要发出“mama”这个音,他所需要的人就会来到身边。作为哺育者的母亲自然而然把这种带鼻音的声音当作对自己的召唤,这在母亲称谓词的形成过程中有重要作用。另外,papa也一样,英语的pap,拉丁语的papilla,瑞典语的patte,立陶宛语的papas,意大利语的poppa,均表示“乳房”或“乳头”。[8](P145)
任继昉在这里阐述了“mama”一词的起源及它与“乳汁”“乳房”义的联系。在母亲哺乳时,婴儿自觉不自觉地将mama与妈妈、乳汁联系起来。因此,mama这一语音形式在世界各地普遍具有“乳汁、乳房”义。任继昉还指出,“吾乡方言中即称乳房为‘妈头子,称乳汁为‘妈子,而绝不称‘奶(‘奶只用来指称祖母)”[8](P145)。类似的俗语民谣还有“十个鱼,八个虾,大姑娘也能吃出妈”,“妈”即指乳汁。
需要指出的是,在今天的四川方言中,“妈”很少表示“乳汁”义,其表乳汁义的主要是“奶奶”。《四川方言词典》:“奶奶,(1)人的乳房。(2)人的乳汁。”如“当初婆婆去世,你还是吃我的奶奶长大的。”[9](P242)《蜀籁》卷一:“一个婆娘两个奶奶,哪有错的。”《跻春台·过人疯》:“还要与你师婆把法赛,杂种儿子今夜要装灾。快些回家吃奶奶,免得羞你祖先台。”类似的词语还有“奶娃子”,指吃奶的孩子,多指婴儿;“奶豚子”,指正在吃奶或断奶不久的小猪[9](P242)。《成都方言词典》:“奶奶,乳房,人和哺乳动物乳腺集合的部分。”如:“夜晚又怕儿叫唤,睡起都把奶奶含。”[6](P168)“奶子”,指奶妈,或保姆。此外,部分方言区称妈妈、母亲为奶子。如:“我们这儿喊妈兴喊奶子。”[6](P167)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四川方言“乳汁”义原本亦由“妈妈”一词来承担;当“妈妈”由“乳汁”义引申指“幼儿所吃的饭食”时,“乳汁”义则改由来自共同语的“奶”“奶奶”承担。
三、“”的语音演变
随着“妈妈”由“乳汁”义引申指“幼儿的饭食”,其语音也发生相应的变化,由[ma ma]变为[mang mang]。查中林指出,“”为儿童用语,可能是“妈妈、咪咪的音变”[10](P255)。此说可从。问题是,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语音的变化呢?C8E55514-531D-42F5-A73B-86BE2AFDB859
我们认为,这主要是涉及到语音的鼻化这一问题。鼻音化与鼻化度是目前学界研究的重点,学者们从生理、语音等方面对此进行了深入探讨。音节是由音素构成的,在单字的实际发音中,声、韵、调会互相影响。一般认为,发鼻音时,口腔气流通道完全封闭,软腭下降,气流从鼻腔流出。不过,现代语音学实验表明,在音素发音时,口腔、鼻腔都会产生或强或弱的能量。石锋等指出,鼻音与口音发音时,都会在口腔和鼻腔内产生气流,具有一定的能量;两者的区别是在于,鼻音与口音发音时,各自所占鼻腔、口腔总能量的比例有所不同[11]。所谓“鼻化度”,是指语音发音时的鼻化程度。时秀娟等曾对北京话单字音中元音的鼻化度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单字音中的响音都有鼻化度,其鼻化度会受到声、韵、调的影响而发生不同的变化[12]。
目前,学界主要是以鼻音计(Nasometer)来计算响音的鼻化度。石锋等学者曾利用Kay NasometerⅡ6400鼻音计对部分方言语音的鼻化度进行了测试。其计算公式为:N=100×n/(n+o)。其中,n表示鼻音能量(nasal acoustic energy),o表示口音能量(oral acoustic energy)。N为鼻化度,N数值越大,则表明鼻化度越高[11]。内在鼻化度大小与元音发音时舌位的前后与高低有关,[a]鼻化度最高,[u]鼻化度最低,前高元音[y]的鼻化度也较低。其中,鼻音辅音[m]的鼻化度在80以上[13]。朱晓农指出,鼻化音不同于鼻音,发鼻化音时气流同时从口腔和鼻腔通道流出,具有口腔和鼻腔的共振[14]。鼻化音可以看作是普通元音附加一点鼻化色彩。在汉语元音中,[a]、[u]、[i]更容易发生鼻化,其中,又以低元音[a]最为常见,原因是在于,发低元音时口腔张大,舌骨肌的一端会带动软腭使它下降,这时咽喉至鼻腔的通道会连通,促使气流通过,从而引发鼻化。
如前所述,“”为幼儿用语,使用对象主要是儿童。在幼儿发[ma ma]这一音节时,会存在较重的鼻化现象,由于辅音[m]的鼻化度通常都在80以上,因而会影响到与之相关的音素。这就导致韵母元音[a]逐渐鼻音化,由[a]变为[ang],于是该词的语音相应地变为[mang mang]。徐世荣认为,元音[a]常在双唇音[m]的影响下发生变异,逐步鼻音化[15]。成年人在与幼儿交流时,往往自觉不自觉地模仿幼儿发音,这在客观上进一步巩固了[mang mang]的地位。[mang mang]一词在四川方言中词义发生引申,产生“(小孩吃的)饭、食物”义,使用频率增加。人们往往只把语言中的语词当作整体使用,而不去过多关注其来源;随着时间的推移,一般人已经意识不到[mang mang]与[ma ma]的意义关系。一旦需要在书面上使用时,只好另造新词“”。
汉语历史上也发生过类似的鼻音化变异例子。如人称代词“你”“他”“我”都是阴声韵,音节末尾为元音,音节结构为“声母+单元音”,读音为你[ni]、他[ta]、我[o]。中古时期,汉语中产生了表示多数的“们”字,当“你”“他”“我”等代词与“们”结合时,“們”字的鼻音声母[m]会产生“逆同化”而影响前面音节的韵尾,使其元音发生鼻音化。徐世荣指出,在北方方言中,人称代词在长期的口语交流中使用频率甚高,发音逐渐鼻音化,变为[nin]、[tan]、[nan][15]。于是字形亦跟着变化,写为“您”“怹”“俺”等。词语的情感义随之发生变化,增加了尊敬、礼貌之色彩。这类鼻音韵尾的增加,主要是受后面音节的影响。
在四川方言中,由于受到[m]的影响而导致元音鼻化的不只“”一词。例如俗语“装猫儿吃象”,《四川方言词典》:“装猫儿吃象,指假装糊涂,如‘谁搞的鬼谁清楚,何必装猫儿吃象呵!猫,又作蟒。吃,又作识。”[9](P473)蒋宗福解释说:“窃以为‘猫儿或当作‘莽儿(义为傻),‘装莽儿即装傻。识象,或当作‘饰相,即装样子。”[4](P833)蒋说未当,本字当为“猫”,“莽”字应是“猫”字发生鼻音化后假借的记音字。[mao]演化为[mang]与[ma ma]变为[mang mang]是同一原理。
李如龙曾依据《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归纳出全国各地方言对“乳房”一词的称呼,共22种,具体如下[2](P96):
个个︱砸儿︱妈儿︱奶头儿︱奶子︱妹妹︱妈妈︱奶︱奶子︱妞妞︱奶奶︱奶妞︱乳头儿︱妈妈儿︱斗斗儿︱咪咪︱妈︱捏捏疙瘩︱灭灭︱芒芒
其中,“个个︱灭灭︱芒芒”之类应是记音词,均表“乳房”义,应由语音变异所致。此处的“芒芒”与“”应当是同一个词的不同记音字形。不仅是四川方言,在辽宁朝阳话语音系统中,同样存在着与普通话差异较大、数量较多的鼻化音现象,这些韵母主要是[ao]、[iao]与以[n]、[?]作韵尾的鼻音韵母[16]。同时,在北京方言、南京方言中也存在着这类语音现象。
综上所述,本文主要是从语音和词义两个角度,探讨了四川方言词“”的来源和演变过程。我们认为,“”一词来自表“乳房”“乳汁”义的“妈妈”,其中的韵母[a]受到鼻音[m]的影响而产生了鼻音化,读音由[ma ma]变为[mang mang],词义也由“乳房”
“乳汁”引申为“小孩所吃的饭食”。当人们意识不到二者的关系时,便另外造出记音的形声字“”。早在明清时期,有些学者已经认识到语音、语义是因时因地而变化的。除历时变化之外,共同语语音在各地方言中也会发生变异,而语音的变化往往会导致词形的变化。这样一来,同一个词语在不同地域就会出现不同的变体。我们认为,其演变机制主要体现在语音和语义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参考文献:
[1]崔荣昌.四川境内的客方言[M].成都:巴蜀书社,2011.
[2]李如龙.汉语方言学(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C8E55514-531D-42F5-A73B-86BE2AFDB859
[3]黄侃.黄侃论学杂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4]蒋宗福.四川方言词语考释[M].成都:巴蜀书社,2002.
[5]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字典(第二版)[Z].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武汉:崇文书局,2010.
[6]梁德曼,黄尚军.成都方言词典[Z].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
[7][清]刘省三.跻春台[M].蔡敦勇校点.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
[8]任继昉.汉语语源学(第2版)[M].重庆:重庆出版社, 2006.
[9]王文虎,张一舟,周家筠.四川方言词典[Z].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10]查中林.四川方言词语之语素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2008.
[11]石锋,时秀娟,冉启斌.北京话语音的鼻化度分析[J].南开语音年报,2007,(1).
[12]时秀娟,冉启斌,石锋.北京话响音鼻化度的初步分析[M].当代语言学,2010,(4).
[13]时秀娟,梁磊.南京话响音的鼻化度——兼论/n、l/不分的实质[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2).
[14]朱晓农.说元音[J].语言科学,2008,(5).
[15]徐世荣.北方话人称代词鼻韵尾的来历[J].语言教学与研究,1993,(3).
[16]迟咏.朝阳话的鼻化音特点及克服方法[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5).
Discussion on Sichuang Dialect Words “Mangmang()”
Wang Yanghe
(College of Literature, Yangtze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8100, China)
Abstract:Sichuang dialect is an integral part of southwest Mandarin. A large number of archaic words are retained.From the Ming Dynasty to the contemporary era, scholars have constantly verified the difficult characters in Sichuan dialect, There is no detailed research of “mangmang()” by scholars.“Mang()” is a temporary phonogram. This word is actually “ma(媽)”. The reason for the variation is the nasalization of pronunciation.
Key words:Sichuang dialect;etymological character;“mangmang()”C8E55514-531D-42F5-A73B-86BE2AFDB8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