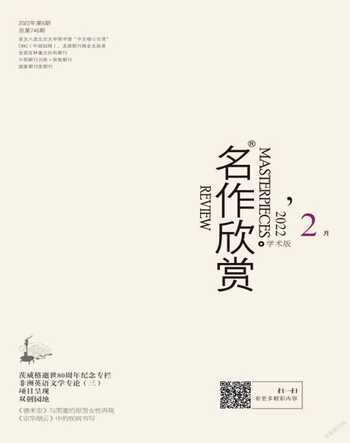《错误》的文本细读与多角度审美
刘开怡 宿静
摘 要: 郑愁予是著名诗人,《错误》是其被公认为写得最好、影响最大、最具代表性的诗作。本文试图从诗歌的古典味、潜层的现代性、遗留的空白感和主题的多义性四个方面对郑愁予的《错误》进行分析,并挖掘该诗的美学内涵和郑愁予高超的诗歌技巧。
关键词:《错误》 古典味 现代性 空白感 别样性
郑愁予在中国台湾当代诗坛被称为“中国的中国诗人”,台湾《文讯》杂志曾经做过一个“最受欢迎的作家”的问卷调查,郑愁予是“诗人”排行榜第一名。而《错误》是其被公认为写得最好、影响最大、最具代表性的诗作,被称为“现代抒情诗的绝唱”。
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本文试图从多个角度挖掘《错误》的美学意蕴。笔者发现,在《错误》中,郑愁予诗歌独特的古典美是其最明显的特点,由诗歌的意象、结构和音律三部分构成,而诗歌的现代性是潜层次的,需要经过分析获得现代性感受,正是这种现代性使得这首诗与传统的闺怨诗相区别,不落于传统诗的旧套里。诗歌空白造成了诗歌的多义,再加上诗歌是多种元素的组合,这些元素与多种主题相联,由此形成了诗歌的多种主题。基于这样的发现,本文将从诗歌的古典味、潜层的现代性、遗留的空白感和主题的别样性这四个方面对《错误》这首名诗进行多方面分析,由此,《错误》的美学内涵和郑愁予高超的诗歌技巧将得到一个比较全面的呈现。现将原诗摘出并为每句编号:
①我打江南走过
②那等在季节里的容颜如莲花的开落
③东风不来,三月的柳絮不飞
④你的心如小小的寂寞的城
⑤恰若青石的街道向晚
⑥跫音不响,三月的春帷不揭
⑦你的心是小小的窗扉紧掩
⑧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
⑨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
一、浓郁的古典味
诗人流沙河认为郑愁予的文字典雅,“多有旧体诗词之美”。《错误》正是郑愁予“文字典雅”之作,具有“旧体诗词”之美,弥漫全诗的是难以化开的古典意味,这种古典意味是意象、结构和音节合力的结果。其中,最明显的是诗歌意象。
意象是诗歌的基本单位,对诗歌的意境构造和诗意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意象的选取、组合、呈现,影响着诗歌的美学风格和审美意趣,也可以呈现诗人的诗学传统。《错误》选取了许多古典诗歌的意象。诗歌第一节,即出现了“江南”和“莲花”两个典型意象,第二节中的意象十分丰富,既有触觉(东风),又有视觉(柳絮、小城、青石街道、春帷、窗扉),还有听觉(跫音),诗人以实体的意象,构建了女子虚幻的内心世界。第三节中,“达达的马蹄”是听觉的意象,马是一种古老的交通工具,“马蹄声”是古诗中常见的意象,是离别与归乡的声音。“薄命常惻恻,出门见南北。刘郎马蹄疾,何处去不得。”(曹邺:《薄命妾》)“翩翩马蹄疾,春日归乡情。”(白居易:《及第后归觐,留别诸同年》)。当古代女子听到马蹄声时,也正是离人归来的时候。“历历花间,似有马蹄声。含笑整衣开绣户,斜敛手,下阶迎。”(和凝:《江城子》)。郑愁予在《错误》中引用了大量中国古代诗歌中常用的诗歌意象,连接了中国古典诗歌传统,将古代意蕴承引到现代诗歌中,形成了凄凉而幽美的意境,富有古意,对传统的化用十分成功,这不得不说是郑愁予《错误》成功的重要因素。
一系列古典意象造就了浓郁的古典意境,除此之外,诗歌的结构和音乐美也不容忽视。关于结构美,第一节和第三节各有两句,遥相呼应,首尾匀称。第二节中,句③④和句⑥⑦字数相同,结构也相似,类似古诗中上下两部分的对称。整首诗显得轻巧精致,匀称和谐,虽然是自由的表达,却有古典诗歌的结构美。再说音律,《错误》一诗中,有许多o音的字:我、过(2次)、落、寞、若、错;在第一节中,“过”和“落”押韵,形成一种流畅的音乐感。同时,句⑤和句⑦的末尾两字“晚”和“掩”押韵,“向晚”和“紧掩”又是③④⑤句和⑥⑦句两组对应结构中的末尾倒装部分。除了音韵的对应以外,诗歌每句末尾词的音调也是有规律的。第一节两句末尾都是四声,而第二节两组对应句的末尾则是“一声+三声”的重复,到第三节,诗句末尾词又是四声。第一节是叙事的开头,用四声落句干净简练。而第二节涉及女子的心理部分,重在抒情,故而有一声的轻扬和三声的低抑,这种音节的扬抑,正好对应了女子的心情起起伏伏,“容颜如莲花的开落”。第三节又回到外在叙事,四声结尾的“错误”和“过客”都有一种斩钉截铁的冰冷色调,即使女子如此多情,但现实却是冰冷的,暗示着故事的悲剧性。
从《错误》的结构和音律中,读者可以看出郑愁予诗歌对语言的用心。郑愁予是很注重语言组织的诗人,他曾说“诗人是有语言特权的人”,现代汉语本身还是很有弹性的,对古文、外来语言的使用,都可以重新来组织,“特别是中国字、词,本身有一种音乐感,有四声”,“唐诗宋词……把中国字、词的音乐感组成了一种至美的形式,没有办法将其置换。那种音乐感和我们的情感本身有一些很微妙的关系”。在《错误》中,诗歌的音乐感与诗歌的情感确实产生了一种微妙的关系。
二、潜层的现代性
虽然《错误》从表面上看,是一首白话版的古代闺怨诗,但细细品味,《错误》是具有现代性的,它与古代闺怨诗有很大的不同。杨牧曾在《郑愁予传奇》 中说:“自从到了现代以后,中国也有很多外国诗人,用生疏恶劣的中国文字写他们的‘现代感觉’,郑愁予是中国的中国诗人,用良好的中国文字写作,形象准确,声籁华美,而且是绝对现代的。” 《错误》 就是一首现代的中国诗。
从表达经验上看,郑愁予的《错误》,传达的是一种现代战争中兵荒马乱、流离失所的经验。“童稚时,母亲携着我的手行过一个小镇,在青石的路上,我一面走一面踢着石子。那时是抗战初期,母亲牵着儿子赶路是常见的难民形象。我在低头找石子的时候,忽听背后传来轰轰的声响,马蹄击出金石的声音,只见马匹拉着炮车疾奔而来,母亲将我拉到路旁,战马与炮车一辆一辆擦身而过。这印象永久地潜存在我的意识里。”这种情感经验展现的是现代人的意识和现代人的精神空间。
从叙事角度上看,郑愁予的叙事视角与传统的闺怨诗不同。郑愁予说:“传统闺怨诗多由男子拟女性心态摹写,现代诗人则应以男性位置处理。”《错误》就是从男子的视角来揣测、摹写女子的心态,尤其是在第二节中,充满了对女子心理的描写。
从整首诗的叙事方式来看,《错误》采用了戏剧化叙事方式。其表现在于:其一,场景有空间转换,第一节是外在视角描写“我打江南走过”,而第二节转向女子的内心视角,将女子的内心实体化为一座凄冷的城。其二,全诗采用戏剧独白诗的语言风格,整个事件是从男子的视角来展现的,而男子是诗中的“我”,女子是男子观照中对应自我的“你”。第一节和第三节,都是“我”的“戏剧独白”,第二节女子作为“你”并没有参与对话。其三,诗中的角色含混。“我等待的女子”、被等待的“归人”、等待“我”的人,构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由于“错误”,我的角色身份对于女子是多重转变的,事件发展经历了开端、发展到高潮、结局的曲线运动,体现了戏剧化的巧妙悬念。这种扑朔迷离的多义和无解能引发读者的好奇。
从诗歌情感上看,《错误》中的感情是淡淡的忧愁,而不像传统闺怨诗那样有着浓厚的哀伤。这种反抒情主义,是现代主义诗歌的一种重要特征。早在现代派重要诗人、新批评派理论开创者艾略特那里,他就提出:“诗不是放纵感情,而是逃避感情,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他反对浪漫主义诗歌毫无节制的情感抒发,而主张诗人必须知性和感性融合、情智合一。在同是台湾现代派诗人纪弦那里,他也反对热烈的情感和过分的抒情。虽然郑愁予是著名的抒情诗人,但他的抒情在《错误》里也得到了克制,“过客”之“过”的事件是偶然的,画面是短暂的,女子的哀愁也是淡淡的,没有泪流满面,正如年深日久的等待的愁味,是缓缓的、长久的。而这种节制的感情,正由于书写视角是从男性出发的,郑愁予诗歌的现代性在叙事视角和情感抒发上得到了统一和整合。
沈奇曾说:“如何使与生俱来的西方诗质在新诗生成过程中的影响本土化、中国化,同时承传并重铸古典诗质的辉煌的同时,而又不减弱对现代意識的接纳、现代精神空间的拓展,确实是个不断重涉的命题。真正有作为的诗人都在这方面付出了努力……”郑愁予的《错误》,正体现了他在这方面的努力,《错误》的古典韵味是在外的,而现代性是在内的,二者实现了完美的统一。
三、遗留的空白感
空白是诗歌中未呈现的部分,是诗歌的裂隙,是诗中的“无”。留白在中国古代的诗论、画论、书法中皆有应用。在西方文论中,“空白”是接受美学代表理论家伊瑟尔的理论术语,伊瑟尔认为“文本与读者之间基本的不对称现象——空白,引起了阅读过程中的交流”,“空白是文本未被觉察到的结合处,由于它们把文本的相互关系划分为图式和文本的透视角度,这样就同时触发了读者的想象互动”。
郑愁予的诗歌,常常描绘的是一个短暂的场景和瞬间,留下了无限想象的空间,需要读者发挥想象力来补足诗歌的画面并完善诗歌的诗意。在《错误》里,郑愁予给读者留下了许多疑问。如,“我”又是谁?在诗中,“我”的经历没有说明,但读者可以根据“过客”联想,“我”可能是羁旅江南的人、漂泊无依的游子、妻子的丈夫、女子等待已久的未归人,母亲的儿子……另外,“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只是针对女子而言的吗?“我”除了替女子悲伤外没有自己的悲伤吗?“我”是“过客”,路过一个苦苦等待另一个天涯浪子的女子,女子固然等不到归人,那“我”又何尝能够回到可以落脚的家、回到“我”的女子身边呢?“我”的悲哀,在于路过的地方不是可以歇息的地方,“我”只能落寞地走过。如果一开始“我”的作用只是一个旁观者,结尾会发现,“我”可能就是诗中对应的“归人”,“归人”和“过客”本来就是一体的。在远方或许也有一个人如这个女子一般等“我”归来而不得,“我”既为心爱的女子的寂寥而悲伤,又为自己不能回到女子身边得到心理的栖息而悲伤。
由于诗歌对“我”、女子、女子等待的归人都没有明确交代,诗中留下了大片的“空白”,所以读者可以任凭自己的想象驰骋,由此形成了对于《错误》多种多样的理解与想象。根据读者对诗歌不同的想象和理解,《错误》就被归到了不同的主题中。
四、主题的别样性
人们对《错误》的主题理解是多样的,它可能是倦守春闺的“闺怨”诗,可能是“妻盼夫归”的爱情诗,也可能是寄托海外游子无家可归的流浪情怀,但这些都和诗人的最初意图有一定的距离。郑愁予在《错误》后记中说:“打仗的时候,男子上了前线,女子在后方等待,是战争年代最凄楚的景象,自古便是如此,因之有闺怨诗的产生并成为传统诗中的重要内容……诗不是小说,不能背弃艺术的真诚。母亲的等待是这首诗,也是这个大时代最重要的主题,以往的读者很少向这一境界去探索。”原来郑愁予赋予这首诗的感情主题是“母盼子归”,而不是“妻盼夫归”,与大多数读者的普遍理解相左。虽然郑愁予说 “诗不是小说,不能背弃艺术的真诚”,但事实上诗歌与作者的关系是复杂的,完成的诗歌未必完全是诗人意图的呈现,虽然读者不能走向作品与诗人相分离的极端,但也没有必要完全按照作者的意图去理解一首诗歌。诗歌不是要求精确的实用性文章和传达性文字,它是一种审美的艺术,追求的不是精确性,而是艺术性。明代王夫之说“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清代谭献说“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而西方文艺理论中的接受美学强调读者对文本的接受作用而否定作者对文本阐释的绝对权威,它们都并不认为作者的思想就完全决定了作品的含义。郑愁予的《错误》就是适合东西方都存在并被人观察到的复杂情况。如果对《错误》只作一意来理解,岂非是限制了《错误》的诗歌内涵和美学意蕴?
所以,笔者认为郑愁予的意图是《错误》诗歌的最真实的解释,但并非唯一的解释。从“母亲的等待”生发开去,联想到郑愁予与大陆隔绝的“文化孤儿”身份,《错误》也可能指向中国大陆和台湾两岸的关系,包含了中国大陆对台湾的等待和企盼,正是这些多重的复杂的意义,让《错误》成为“美丽的”诗篇,也成为传颂万家的诗篇。
郑愁予仅凭《错误》一首诗,便体现出他高超的诗歌技巧,他将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极好地融入了自己的诗歌里,使得诗歌古色古香,意蕴深永,也使古诗在新诗中重新焕发出生机与活力;同时,他的诗歌又表现了现代人的精神内容和现代经验,与同时代人的情感相契合,不落于古典诗歌的窠臼中。郑愁予正如沈奇所言:“他自觉地淘洗、剥离和熔铸古典诗美积淀中有生命力的部分……由此生成的‘愁予风’,确已成为现代诗歌感应古典辉煌的代表形式:现代的胚胎,古典的清釉;既写出了现时代中国人(至少是作为文化放逐者族群的中国人)的现代感,又将这种现代感写得如此具有中国化和东方意味,成为真正‘中国的中国诗人’(杨牧语)。”这个评价极为中肯。
参考文献:
[1]流沙河编著.台湾诗人十二家附诗一百首[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3.
[2]沈奇.摆渡:传统与现代——郑愁予访谈录[J].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评论和研究,1997(4).
[3]刘登翰,朱双一.彼岸的缪斯台湾诗歌论[M].南昌: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12).
[4]郑愁予.郑愁予诗的自选1[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3).
[5]赵毅衡编选.“新批评”文集[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9).
[6]王先霈,王又平主编.文学批评术语词典[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2).
[7]沈奇.美丽的错位——郑愁予论[J].华文文学,2010(2).
作 者: 刘开怡,语文高级教师,重庆市秀山高级中学校教师;宿静,高级语文教师,重庆市秀山高级中学校教师。
编 辑: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