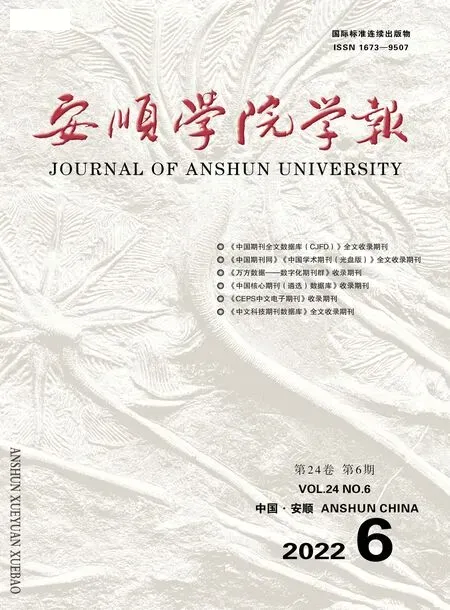时间自觉:农历与屯堡文化的传承
张定贵
(安顺学院政法学院,贵州 安顺 561000)
屯堡研究成果可谓丰硕,涉及诸多方面的内容,但在这些研究中往往缺少“时间制度”的视野,特别是少有屯堡农业生产、民俗仪式与“时间制度”关联的考察。笔者认为,“时间制度”是中国传统社会建构的重大事项和重要因素,屯堡文化之所以能传承至今,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屯堡人一直遵循着中国传统的时间制度——阴阳合历的农历,数百年来他们系统性地、普遍性地将农业生产和民俗仪式嵌入到这一时间制度之中,型塑了屯堡乡村社会和延续了族群文化传统。
一、农历:中国影响深远的传统时间制度
历法,是一种社会管理制度,又是一种法律制度,负责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行。在过去,历法是以法律的形式作出规定的,在清乾隆十六年(1751年)以前都是不允许私人介入的,甚至印刷都不可以,必须得到朝廷的颁布。历法是人类根据天象变化的自然规律,计算时长间隔,判断气候变化,预知季节时间位置的法则,主要分为阴历、阳历、阴阳历。
农历,又称夏历,我国民间通常叫作阴历,但其实并不是纯粹的阴历,而是兼顾月相和日相变化的阴阳合历,对农业生产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真正的阴历,主要是根据月相变化来制定的历法,不考虑回归年的四季变化,与中国民间所称的“阴历”有很大差别。阴历的时间和阳历相比,每年大约差十一天,有时一年会相差一个月。
农历,相传是由轩辕黄帝所创制的,又由于历代王朝十分重视,必须为皇家测算、创制、审定、颁布、印行,因此又称皇历。农历,以月相变化为基础,吸收了阳历的二十四节气,并通过“置闰法”的调整,使之符合回归年。所以,农历反映了太阳、月亮与地球的关系,有朔望变化、季节更替,与月相、日相的运行规律相吻合。“置闰法”是古代中国人民的伟大创举。农历的主要内容为二十四节气,每天标有宜忌、干支、值神、星宿、月相、吉神、凶煞等,由于具有指导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农民农业生产的功能,所以又称为农民历。农历,在中国民间社会俗称为通书,但因通书的“书”与“输”同音,为人们所讳忌,因此又将称为“通胜”。
阳历,即是太阳历,是以地球围绕太阳公转而形成的历法制度。一年有12月,此“月”与月相朔望无关,月份、日期与太阳在黄道上的位置趋于一致,可看到一年四季及其相应的寒暖变化。现行的公历(也叫西历、西元、公元等),是阳历的一种,经意大利的Aloysius Lilius将儒略历改造而成。规定每四年设一个闰年,将增加的一天放在天数最少的2月,因此逢闰年时的2月就有29天,使每四年大约就会一天的问题得到解决。
现行农历沿用清朝的《西洋新法历书》,该历书脱胎于明末的《时宪历》。在四百多年前,在汤若望的主持下,由欧洲耶稣会教士和中国首批天主教徒合编而成。现行“农历”与《时宪历》前的中国历法在“二十四节气”上共享同一个名字,但确定方法、日期不同。明亡清兴后,顺治皇帝直接将《时宪历》更名为《西洋新法历书》,并于顺治二年(1645年)颁布通行。从康熙八年(1669年)灭亡,我国历法一直大体沿用该历书,即是在民间一直沿用至今的“农历”。
民国建立以后,政府强推西历,采用西历或者民国纪年,强行废除农历,但在乡村社会效果并不理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公元纪年。基于民国“废历”运动不彻底的教训,也允许农历在广大农村的存在。随着社会的变迁,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农村发生的深刻变化,人们可能会在建筑动土、婚丧嫁娶、店铺开业、重大庆典等的择日上使用农历,但将农历的社会编排方式与比较系统的族群文化、地域文化传承连在一起,至今仍呈活态传续的屯堡文化当属这方面少见的典型代表。
二、近现代以来屯堡人仍固守着农历的社会文化指令
虽然自近代以来西方的时间制度进入中国,公历制度、星期制度、时钟制度等西方时间制度亦进入屯堡地区。西方的时间制度主要是适应工业社会的产物,作为农耕社会的屯堡在面对官家、在面对与外部社会对接时也是采用这一套制度,但是在内部的农业生产和民俗仪式展开时,在面对日常生活中的很多事情时,屯堡人往往比较多的采用农历这一中国传统的社会时间制度。据民国《平坝县志》记载:“元旦旧惟机关庆祝,社会恒淡漠视之。自民国二十年(1931)起,县政府竭力推行国历,强迫民众以过旧历元旦式过国历元旦,禁止再过旧历新年及售卖旧历书,于是城乡始渐知有此种元旦,渐知有国历”,“立春、雨水、小寒、大寒等二十四节气,端午、中秋等三大节等,名目一同旧历,惟变成国历日期计算。凡社会过旧节气之种种仪式,其无碍于善良风俗或涉及迷信者,仍听群众于新节气内举行。”[1]平坝是屯堡区域的重要构成部分,可以看到进入民国后所推行的“废历”运动,在屯堡区域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政府公开推行阳历即公历,但对老百姓习惯了的农历及相应的习俗则听之任之,实际上是一种“阳”奉“阴”违的障眼法。据一些年岁大的老人说,在过旧年旧节时,刚开始还换算成公历,后来直接不用换算,政府睁只眼闭只眼的。查阅一些相关资料,全国其他农村推行公历时也有类似的状况(参见左玉河《从“改正朔”到“废旧历”——阳历及其节日在民国时期的演变》,载《民间文化论坛》2005年第2期;刘爱华《“新礼”与旧俗的对峙:民国时期废历运动宣传策略误区及其阐释》,载《民俗研究》2020年第5期)。可以说,进入民国以后,政府推行公历,欲废农历,但在具体的实践中特别是在乡村社会出现了典型的“阴”盛“阳”衰状况,并没有达到废农历目的。
在农业生产上,屯堡人普遍采用农历的二十四节气,通过太阳的周年运动,指导自己的农业行为。很多屯堡老人对于“十二节令”和“十二中气”比较熟悉,“节”与“气”的交替出现成为恒久的农业生产法则。
屯堡人习惯使用农历的干支纪法,也就是通过干支来纪年、纪月、纪日、纪时。干支纪年是使用十天干、十二地支来纪年。十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地支对应着十二生肖。十天干和十二地支依次相配,构成60个基本单位,将此作为年月日时的序号,这就是干支纪法。比如公元2018年12月28日上午8点,这一天是农历十一月廿二日,用干支纪法就是戊戌年、甲子月、甲午日、戊辰时。从汉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开始,干支纪年、帝王年号纪年一起成为中国传统的纪年方式,直至清朝灭亡。进入民国后,主要是使用公历纪元,但屯堡人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多采用干支纪年。
农历这一中国传统的时间制度,尽管现在全国其他一些地方仍在使用,特别是农村社会比较常见,但至今仍呈系统性地将农业生产和民俗仪式嵌入到农历的时间制度中,普遍地踩着传统的时间节点、社会编排方式来实现文化传承与社会运行,屯堡应该是比较典型的,这深刻地影响着屯堡人的生产生活和文化生态。
(一)指导农业生产相关行为按照时序进行
屯堡人“尊时守位”,“尊时”就是“不违农时”,就是充分地尊重农历的时间制度来安排农业生产;“守位”就是原来守住自己的军人职责和使命,在清代康熙年间经历“改卫归流”的重大转折点由“军”转“农”之后,守住的是自己“农人”的本分。我们从他们流传的农谚均可看出,这其实不是一般的顺口溜,而是世世代代不断总结、传续的经验通则,它作为一种重要的法则参与了地方社会的建构。比如:
三年两头润,一年打两春。
春分秋分,昼夜平分。
清明要明,谷雨要淋。
立夏不下,蓑衣斗篷请高挂。
夏至五月中,连路吃连路松。
夏至五月尾,财主要后悔。
六月秋,减半收。
七月秋,满满收。
白露不出,寒露不熟。
重阳无雨望十三,十三无雨一冬干;不怕重阳十三雨;只怕立冬一日晴。
白露雾茫茫,谷子田里黄;白露不低头,割来喂老牛。
小满不满,芒种不管。芒种打田不在水,夏至栽秧矮一等。夏至五月头,连路吃,连路愁。
惊蛰冷,打田等;惊蛰热,田开裂。
白雾白茫茫,秋分满坝黄。
芒种栽秧日赶日,夏至栽秧时赶时。
一九、二九荷包揣手,三九、四九冻死猪狗,五九、六九隔河看柳,七九六十三路上行人把衣单。九九八十一庄稼老汉把田犁。
诸如此类的农谚,是屯堡人顺应天时来安排农业生产、预测丰歉的经验通则。
传统的时间制度不仅仅是对农业生产的指导,也是形成农业生产相关仪式的指令机制。比如正月间,跳地戏叫作“迎春神”,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是祈求新的一年在农业生产上的五谷丰登;七月间,跳地戏称为“跳米花神”,这是稻谷扬花之时,庆祝农业生产的大丰收。逢农历四月二十六日神农氏(炎帝)诞辰,过去不少屯堡人家要祭祀。神农是五谷大神,作为从事农业生产的屯堡人是要表达他们的感激。农历四月初八,屯堡人要举行“开秧门”仪式,要吃“乌米饭”,以表示做农业的屯堡人可赶季节栽秧子。农历六月初六,要有“秧苗会”的仪式,这是老年男子的会口,这些老人往往都是庄稼能手,他们要带上祭品到土地庙前祭拜土地和山神,祈求风调雨顺、庄稼丰收。屯堡村寨都有建在村口的土地庙,而且往往不是一座,有的有好几座,如九溪村就高达15座。农历六月二十日,要举行“马王会”,过去养马的人家要祭祀三只眼的“马王菩萨”。农历十月初一,是“牛王会”,这是牛王菩萨诞辰。养牛的人家不让牛劳动,让其好好休息,并喂好饲料、喂糍粑,表示对牛一年辛劳的感谢。
(二)促进商品交易遵循时序、位序进行
屯堡人将中国传统的时间制度与具体空间联系起来,形成了屯堡地区的十二甲子场,以“地支”的十二甲子“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的排序,周而复始地来计算场期,他们为了方便记忆,实际上是以十二生肖来定集市贸易的赶场期。一般是六天为一场,这很明显不同于西方传入的“星期”这一时间制度。每个村寨的场坝常以两个时距相等的生肖为场期,形成了穿梭于各个集市的“转转场”。比如,“子日”鼠场赶旧州,“丑日”牛场赶鲊陇,“寅日”猫场赶二铺、双堡,“卯日”兔场赶尖山、王官堡,“辰日”龙场赶七眼桥,“巳日”蛇场(顺场,做生意的人叫蛇为“顺”)赶旧州、松林寨,“午日”马场赶大西桥镇马场村、山京马场,“未日”羊场赶花街(安顺市西路),“申日”猴场赶二铺,“酉日”鸡场赶尖山,“戌日”狗场赶七眼桥、半山水桥,“亥日”猪场赶大西桥村等等。形成了“天天赶场”的农村集市交易的空间格局。在屯堡,还保留着“龙场”“马场”“羊场”“鸡场”“狗场”“猪场”等地名,而且有一些场市至今仍然十分活跃。十里八村的乡民、小商小贩会自觉地在时间的文化指令下到某一场坝进行集市交易。
时间的“空间化”,空间的“时间化”,“十二甲子场”是屯堡人将农历运用到集市贸易的文化实践,使屯堡村寨之间的商品往来有序地展开,并且在屯堡村寨的总体格局中形成了功能上的不同分工。当然,在这里可以补充的是,屯堡人的赶场圈与婚姻圈是基本重叠的,在信息、交通等有限的传统社会,赶场不仅仅是商品的交换,也是婚姻信息的沟通,不少年轻人的婚姻就是在场市这一村际交往的平台上逐渐达成的,有的是年轻人的直接交流、交往,有的是年长者之间互通信息后撮合的,如此看来场市还形成了新的社会关系及下一步仪式(婚礼)的生产机制。
(三)形成屯堡岁时节庆、会口仪式的文化指令机制
农历这一中国传统的时间制度,不仅是指导农业生产,在屯堡地区更是岁时节庆仪式、会口仪式的文化指令机制,形成了丰富的、周而复始的民俗仪式。西方的公历进入中国后,在城市得到广泛使用,也波及乡村。但在乡村还不是主要的时间制度。在屯堡地区特别突出。农历将一年中的屯堡村落时间设定为若干节庆、会口,形成了与之相对应的多种仪式活动,塑造了影响至今的村落社会年度周期。
我们从屯堡岁时节庆仪式、会口仪式可以看到,屯堡人一年四季都有比较隆重的仪式活动,这些仪式是踩着时序的“节点”而展开的,其实这些仪式并不是他们发明创造的,但比起中国其他汉人地区可以说是他们很好地继承和拓展了的,才使得他们与其他地方有着明显的不同。这是屯堡人吸收中华文化的优秀精华,然后结合黔中坝子和本族群的特点,形成的一套共同传续、共同遵循和共同享用的文化通则和文化符号系统,建构了具有族群特点的仪式文化体系。“从历史的角度看,节庆文化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实践中,早已升华为一道人人遵循、个个通晓的文化指令,从而形成节庆文化的群众的广泛参与性。”[2]22屯堡的岁时节庆仪式、会口仪式对于农耕社会的屯堡人来说,就是一种文化指令,因时间制度而形成了一种参与社会建构的仪式制度。
屯堡社会与过去中国的乡村社会是一致的,仪式大多是周期性仪式,这些仪式与传统“圆形时间观”相吻合。人类对时间有着两种观念,一是“圆形时间观”,主要是通过自然界的季节交替、生物的周期性生长来反映,由此形成人类社会的周期性的仪式活动;另一个是“线性时间观”,主要体现物理时间的一维性,时间是向前运行的,有“逝者如斯夫”的感觉。屯堡地区是“圆形时间观”,周期性仪式象征着时间的周期循环。以过年为例,春节的仪式感表示了新旧之别、新旧轮回,作为现代时间制度的公历则只有“先后之分”,不可能有“新旧之分”“新旧轮回”的观念。现代社会时间观念的无限性,在屯堡地区则通过仪式的循环去感知,有新旧之分的时间就可以无限地新旧更替下去。“接踵而至的节庆日期,所给予人们的首先应是时光的流失感和规整有序的周期感。人类要摆脱混沌空蒙,的确需要一种清醒的时间感和可以把握认识的轮回序列理念”,“简明扼要的节庆日期数字,则显然更易于掌握和确认,从而助其建立简便实用的四时轮回时间观念。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节日之节字,确乎传达出了节日日期之为时光之‘关节’和‘调节’时序的深切意蕴。”[2]3屯堡人一年四季的仪式,清晰地标识出时序的位置,对“节日”“常日”的转换,不断地调节了他们的生产生活。这对于身处农耕社会的屯堡人来说,显然比较重要。我们看到公历这一时间制度,在屯堡地区的仪式生活中几乎没有使用,那是他们在面对现代社会诸多事务时才会体现的制度,比如在城市上班、打工、经商和小孩上学等等,屯堡几乎所有传统仪式都是按照农历进行,所谓“老黄历”就是他们的社会时间。
从时间脉络上看,屯堡人通过一系列的节日仪式调节着诸多的具体事务,仪式本身的意义与乡民深厚的意义实现了相互贯通,仪式的意义在社会需求中发生,每一次的开启又是再一次的重申和强调。“节日是相对于常日而言的,它是中国古人通过对天候、物候和气候的周期性转换之观察与把握而逐渐约定俗成的;节庆民俗则是与农业文明发生、发展同步萌芽出现的,最终形成了一系列适应自然环境、调谐人际关系、传承文化理念的禁忌、占候、祭祀、庆祝、娱乐等活动项目。”[2]前言第1页“常日”对于屯堡人来说是辛劳的,在一年四季中这是常态,“逢年过节”就是对生产生活的有效调节,特别是在过去对于改善“生活”,放松心情,增加节日气氛,这都是一个完整的农业社区社会化进程的自动调节机制。贯穿一年,形成了一个有效的文化链条,成为社区发展的重要动力。“传统节庆实质上是一个高度浓缩的中华文化的有效载体。也可以这样说,在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上,传统节庆在历代先民的精心呵护和拱卫之下日渐形成,最终成为一个贯穿春夏秋冬的‘文化链’。同时,它又转而肩负起凝聚民族智慧、引领文化承继的历史使命。”[2]209屯堡岁时节庆仪式是融合客观时间制度传统和族群主观实践(农耕社会)为一体的时间性文化实践,屯堡地区至今仍然较为完好地保存了这样的“文化链”,这是很多地方缺失的文化资源。
屯堡岁时节庆仪式、会口仪式绝大多数是年度周期仪式,将人的生产生活、精神信仰嵌入一年的时间结构中,成为屯堡人重要的社会建构方式。当然,除了年度周期以外,还有跨年度举行的仪式,标志着屯堡人对于时间的长度体验。这样的仪式主要是屯堡妇女的“过河”仪式,逢龙年才有,也就是要12年举行一次。对于“过河”这样的跨村寨、跨时段的仪式,盛大规模可比喻为屯堡民俗的“奥运会”,这是十二生肖的一个轮回,是对龙年的美好祈盼,而且体现了屯堡民间社会超强的自组织能力。由此,我们也看到了传统时间制度对屯堡人极强的文化指令机制和重要的型塑作用。
(四)“择吉”习俗渗透到社会的生产生活
屯堡人对于“好日子”十分看重,这既反映了他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景,也成为他们举行仪式的一个重要的依据。屯堡人做很多重要的事情都有“择吉”的习俗,这渗透到他们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一般事前要请“先生”看日子,也就是要“好日子”,如果懂的人则要翻看黄历,看看什么时候比较合适(合时),哪一方有利。其实中国传统社会都比较重视择吉术,秦汉时期的《日书》中所记占候时日宜忌的内容,涉及嫁娶、出行等日常行事,也牵涉攻伐、出兵等军国大事。历代官方天文机构,除推算历法和观测天象外,还需负责处理选择军事等国家大事的时间,这一观念渗透到民间底层社会,不仅刊刻了大量的相关择吉书籍,而且成为影响人们生产生活的重要参考依据。当然,在今天的现代社会看来,不一定对,甚至有些被视为迷信,但是作为一种“隐文化”现象至今存在,这对于人们心理的调适是有所作用的。
岁时节庆仪式、会口仪式,这主要是村落社区层面、村际交流层面,大多逢重要的节日节点,基本的时间是固定的,但何时开始,那他们就要选择“吉时”。涉及家庭、家族层面的不少仪式也要看日子,比如修建房屋的动土仪式、上梁仪式、乔迁仪式、开财门仪式等等要看日子,安床、立灶(过去叫打灶头,现在是安放炊灶)要看日子,小孩剃头①要有仪式,婴儿出生的“做大客”仪式、婚丧嫁娶的仪式、修培祖坟立碑等等都要看日子,甚至听说有些人家的子女考公务员也要看日子,何时出门,从哪条路进考场。主要是根据当事人的四柱八字来测定什么日子比较适合做事,避免出现犯冲的问题。其实将看日子泛化也不对,但从人的心理来说主要是一种心情的愉悦和对事情成功的期盼。
概括而言,对于屯堡人的“择吉”事项,主要包括开光、祭祀、嫁娶、纳采、出生、出行、考学、祈福、动土、上梁、安门、安床、立灶、搬家、入宅、入殓、安葬、修造、栽种、开市、移柩(移动棺材)、订盟(如订婚)、拆卸(拆毁房屋)、立卷(订立各种契约)、求嗣(多指求男丁)、纳财、斋醮、修坟等等,除了嫁娶等少数事项有时也会选择公历,主要是遇上国家的重大节庆,如元旦、五一、十一,一般都要依据农历来进行。在农耕社会里,这些都是大事情,是人们在生产生活中投入较多、关心程度较高、影响较大的方方面面,选择吉时吉方,力避凶时凶方,是人们趋利避害的自然行为。择吉就是一个比较功利化的行为,与人们的精神信仰有较大的偏离,但不能据此进行简单的批评。由此也可看到,尽管都是时间,但在中国传统的时间制度中,“时间”不仅有新旧之分,而且还有好坏之别,屯堡人的“看日子”就是想通过择吉避凶,以便实现趋利避害的愿景。“年、岁是择吉习俗中最基本的单位,其他计时符号如干支、五行、二十八宿等,都是以年为依归,相应禁忌规定也是随年而流转。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太岁。而太岁,同样含有年、岁的意义。”[3]73这与农业文明的很多不确定性有关系,屯堡作为农耕社会,乡民不仅辛劳,而且人们的生产生活深受自然界的影响,“清吉平安”“顺顺气气”等这些词汇屯堡人常常挂在口上,这其实就是他们的生产祈愿、生活祈盼、生存祈景。在他们看来,人们不能改变“时间”,但可以选择“时间”对人的正向影响。这实际上是在说明人们笼罩到“时间”之中,“时间”与人的生命紧紧关联,不可大意。选择“吉日”这是人们的主动作为,是对乡民、对家人、对祖宗、对后人负责任的应有态度。所以,在村里,会看日子的“先生”或是其他具有一定民间文化修养的村民,人们会从金钱上或物质上表达自己的意思,也受人们的尊重。通过“择吉”及“意思”的表示,亦可看到人们行为的仪式性和重视程度。
如果从物理时间的角度来看,“时间”是客观的,但如果从仪式的角度来看,仪式又具有主观性,是人们主动地将自己的社会行为与“时间”的连接,并赋予其意义和功能。“‘仪式’不能在所谓‘被迫的’、‘本能的’意义上来理解,而必须在积极的‘表达的’层面来解释。”[3]73
当然,从公共性、私人性的角度来看,村落、族群整体层面的岁时节庆仪式、会口仪式,一旦某个仪式结束之后,就进入了非仪式的日常生活,但其实并不标明屯堡人没有仪式行为的发生,其实私人层面的仪式亦是不断的,只要是逢上人的生命节点或是具有“好日子”,仍然会有仪式出现,比如前述的开光、嫁娶等等仪式,都是按照屯堡族群数百年约定俗成的规矩进行的。可以这样说,屯堡仪式是由以家庭、家族为单位的“私”的仪式和以社群组织、村落、村际为单位的“公”的仪式两部分组成。公、私仪式共同形成了屯堡人的文化认同、社会认同。“私”的仪式反映了村民的祖先崇拜和对人的生命历程节点上的重视、转换,它是承接过去、维系现在、指向未来的文化纽带。但是“私”的仪式的一整套规范和程序其实也是村落社区和族群社会的文化安排,谁人也不可破坏,当然也不能自立一套系统。“公”的仪式是由村落社群组织按照族群传统举行的仪式活动,它反映了族群建构的历史传统、村落社会运作的结构特征以及规范与价值、逻辑与秩序,反映了“国家的在场”一直是屯堡仪式和民间社会建构的基本动力。其中有些仪式来自民间信仰,有些仪式源于“国家的在场”的族群历史传统,但在屯堡地区“唯忠为大”的价值取向说明了“国家(王朝)”高于其他力量。民间信仰的传统和国家建构的传统,汇成了屯堡仪式不断延续的传统。
三、“时间自觉”:屯堡文化传承的一种机理
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就提出了“文化自觉”的理论,并且对“文化自觉”给出了一个为大家所知的定义:其大意就是要对自己的文化有“自知之明”,以获得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4]他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概括作为文化自觉理论的最高境界。
我们看到,民国建立以来“废旧历”,“立正朔”,“行公历”,一方面体现告别过去专制政体,确立民国政权的正统性,另一方面更是为了融入世界体系和现代文明,借此西方工业社会的公历制度、星期制度、时钟制度等时间制度进入中国,也对屯堡地区有所影响。但屯堡人在面对官家、在与外部社会打交道时采用的是公历的时间制度,而在农业生产、民俗仪式上仍遵循农历的旧规,实际上实行的是以农历为主、公历为辅的社会时间编排方式。如此,既应对了外部的体制性需求,又将大量的农业生产经验和民俗仪式传续下来。这是一种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是一种应对时代变迁的文化自觉,可以将其称为传统时间的文化自觉,简称“时间自觉”,是“文化自觉”概念之下的下位概念。我们认为,屯堡文化的传承与屯堡人对农历的时间自觉有着重要的关联。通过屯堡的案例可以看到,不同的时间制度对应的是不同的生产方式、文明形态及其仪式体系,这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来施行。
在此我们略微给“时间自觉”的含义做个界定:身处农耕状态的屯堡人,不仅在过去,而且在近现代的中国社会转型中,自觉地以农历这一传统时间制度为文化指令,安排农业生产和传承着诸多传统文化,农历成为屯堡社会建构的重要机制。在屯堡的地理空间里,长期匹配的时间制度与生产制度、仪式制度相互作用,共同建构了具有“大明遗风、江淮古韵”的汉民族亚族群社会。
注 释:
①屯堡习俗:从小留起长发的男孩,当作女孩来抚养,当长到一定年纪时,就要有“剃头”仪式,使其完成“性别”的角色转换,在社会中成为一个真正的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