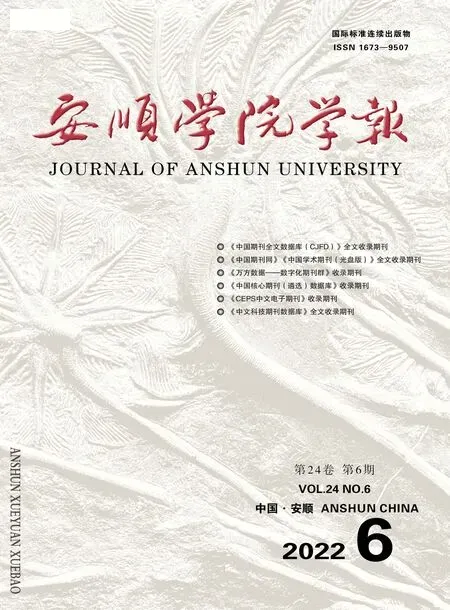食物、仪式与意义
——基于献祭研究的西方人类学理论解读
陈发政
(贵州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安顺学院政法学院,贵州 安顺 561000)
“献祭”是人类生活的一个重要文化事实,无论在人类发展的早期社会还是现代社会,它都具有广大的生存空间。西方文化学者最早对献祭进行专门研究,林林总总出现了许多研究成果,其中部分已成为后人研究献祭文化的学习典范或理论来源。显著地,献祭就是借助食物的符号作用呈现人们精神张力而建构神性时空的仪式,在它的核心环节中食物被作为沟通人神的重要媒介,进而不断幻化成宗教性的物品。因此,献祭的牺牲、饮食等祭品及其仪式过程成为阐释文化现象的关键。最早给“献祭”下定义的是莫斯、于贝尔,他们认为“献祭是一种宗教行动,当有德之人完成了圣化牺牲的行动或与他相关的某些目标的圣化行动时,他的状况会因此得到改变。”[1]82献祭研究在西方一是受到基督教自古有向神灵献祭的仪式传统的启发,遂成为西方文化学者研究宗教生活和神灵信仰不可回避的内容受到关注;二是随着西方资本市场在海外殖民地的扩张,人类学研究取向的兴起,世界各地的巫术、宗教等信仰文化的事实不断进入人们的研究视野,献祭因而成为文化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结合已有的“献祭”研究,本文选取数位有代表性的西方著名学者及其著作,基于各自的研究取向将他们的献祭研究划分为三个研究层面:第一,早期的人类学家们关于献祭的探讨,他们大多从献祭行为上寻求文化起源的根据及意义,其中产生两个被学界所公认的“献祭”观点:一是“献礼”,二是“共食”。第二,从献祭仪式的行为过程出发,分析现象背后所隐藏的结构特点和象征意味,试图挖掘献祭的功能和性质。第三,把献祭当作宗教事实,探讨它所要呈现的人的意义,乃至形而上的思考。
一、人类早期信仰体系下的“献祭”探源
可以讲,人类学的研究伴随着献祭而开始,无论是早先的摇椅人类学家还是后期有着丰富田野经验的人类学家,他们对原始文化的发问都回避不了有关原始部落民族的信仰和仪式,其间献祭是直接可观的表现形式。它不光直指着原始人“万物有灵”的信仰观念,也充分彰显了族群的生活方式,献祭作为沟通人神的圣俗观念进而启蒙了文化的研究。因此,从献祭的文化形式探索献祭的起源与其他文化间的关系,乃至考察原始初民的生命张力等是人类学进行文化研究的传统话题,包括爱德华·泰勒、罗伯逊·史密斯、J.G.弗雷泽及其后期异军突起的人类学家皆有涉足。他们的研究有着一个共同的前提,那就是人类早期先民有广泛的巫术活动和浓郁的原始宗教信仰。
最早对献祭进行记述并解释的是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受到当时持有进化论观点的巴斯蒂安、斯宾塞和达尔文等人影响,泰勒把进化论思想投放到人类的文化视野中来考察,在其著作《原始文化》中比较世界各地不同文明和种族间的文化特点,提出“万物有灵”的论点。他认为原初民族普遍具有灵魂信仰的文化特征,他们通过献祭以建构起人与神灵间的关系,因此,在泰勒看来,献祭形式起源于早期人类向超自然力量的献礼,这是原始人讨好外在于人的那些神力的唯一方式。当原始人越来越崇拜这些超自然神力并把它们推向人所无法企及的极高地位,为得到神灵的眷顾,采取献祭的形式不断向神灵赠送礼物,这种持续性的原始献祭方式在传承过程中凝练下来而成为一种庄重的仪式。在这里,泰勒把献祭看成是赠礼,礼物在于奉养神明,它是一种无需回报的单方面贡献和放弃的信仰行为,其源于人类对超自然力量的崇敬与恐惧。泰勒在描述献祭的内容时,他的关注点主要放在献祭的食物上,他说:“ 在历史的一切阶段上,从低级到高级,一般祭品数量中的十分之九或者甚至更多是食物祭品和圣宴”[2]825。
如果说泰勒对献祭的研究起了一个头,那么罗伯逊·史密斯则确想对献祭作出合理的解释。他在《闪族的宗教》(The Religion of the Semites: The Fundamental Institutions)一书中提出与泰勒不一样的观点,通过分析文献记录中关于闪族人(Semites)的献祭仪式,认为献祭最古老的形态不是 “礼物 ”,而是 “飨食 ”(communion)。史密斯关于献祭的理解受到当时兴起的有关图腾制度的影响,他从图腾崇拜中看到了献祭的起源,因为“在图腾制度中,图腾或神明是与它的皈依者密切相关的,他们有着同样的血和肉;仪式的目的是要维持和保障赋予它们生命的共同生活和将它们维系在一起的社会。如果有必要的话,它就会重建他们的统一性。‘血约’和‘飨食’就是想达到这个结果的最简单的手段。”[1]174那么,也就是说最早的献祭是在吃下图腾动物,把代表着祖先或是神灵的图腾作为食物消耗在身体里,从而实现自己与图腾、祖先的同化。这种消费图腾动物的部族共食行为,其目的也是为了达到群体内部的结盟,建立“祭祀共同体”(sacrificing community)[3]。事实上,“史密斯想强调的是献祭的集体性,仪式性和同属性——对原始部落的人来说,他们的家人,个人的神灵,还有图腾动物,都属于‘同一库存’(one stock),没有等级之分,也没有一方要去讨好另一方的利益企图,他们寻找的,是人和人之间,人和神性之间身体上的‘亲属’关系(kinship)。”[4]24
虽然罗伯逊·史密斯把献祭看成是起源于族群内部对图腾动物的共食,然而他也强调飨食献祭牺牲的行为只能出现在对神明的祭祀过程中,向神明献祭的形式逐渐发展为宗教仪式,当然,史密斯阐发献祭的功能并不在神学,但作为宗教神学早期的雏形,他绕不开神明献祭仪式的话题。关于神明献祭的宗教特征阐述在史密斯那里只是初步的,弗雷泽按照史密斯的思路将献祭神学向纵深推进。弗雷泽在《金枝》中试图探索一条不同于泰勒和史密斯的研究路径,提出“巫术——宗教——科学”三者具有相同理路的逻辑公式,他想撇清巫术与宗教之间的关系,但原始宗教起源于巫术的客观事实使他的努力显得有些徒劳。弗雷泽关于献祭的描述潜存于《金枝》的各个章节中,无论是以“王子”向神灵献祭的人祭还是“神体圣餐”或是“杀死神性动物”的“吃神肉”,皆凸显了献祭是建立在人与神灵的互动,以献祭作为行动方式与神灵取得联系,这是弗雷泽关于“交感巫术”理论的实际应用,他说:“把神当圣餐吃,或是吃代表神的人或动物,或是吃人形或动物形的面包。从原始的观点看,这样吃神的躯体的理由是相当简单的。野蛮人大都认为吃一个动物或一个人的肉,他就不仅获得了该动物或人的体质特性,而且获得了动物或人的道德和智力的特性。”[5]451事实上,关于献祭的研究在弗雷泽汇编的《<旧约>中的民俗》一书中有具体的阐述,通过对世界各民族有关宗教仪式的比对,他得出各地献祭仪式有共通之处,表现在献祭牺牲类型、献祭食物种类、献祭对象及献祭仪式的形式等方面。
沿着史密斯等人早期关于献祭与图腾信仰之间关系的研究维度,许多学者从各自理论之一隅展开深入探讨,如涂尔干在其《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以澳洲中部部落的“因提丘玛仪典”为例,将献祭仪式分为“朝觐圣地”和“图腾植物或动物仪式性享用”两个阶段,其目的在于证明社会事实所潜存的集体性特征[6]。弗洛伊德在《图腾与禁忌》中也从人类文化心理发展的脉络去勾勒图腾献祭的内涵[7]。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在他的系列《神话学》著作中采用二元结构方式解析澳洲土著的图腾与食物献祭之间的文化关系等等[8]。当然,基于“献祭”在人类学早期关于原始文化研究中的地位,许多流派的核心人物在其著述中也多有涉及,如美国历史特殊论的首倡者博厄斯,认为人类早期艺术源于原始人的信仰形式,并间接地介绍了有关献祭的内容[9];功能学派的拉德克里夫·布朗[10]、马林诺夫斯基[11]都有对文化实地考察的经历,他们的著作中对献祭的描述始于解释文化的整体性结构与功能;乃至于“献祭”在文化唯物主义的哈里斯和文化生态主义的斯图尔德等人那里也都有相关的论述,尤其是拉帕波特在《献给祖先的猪》一书中将猪作为仪式中的献祭牺牲宰杀看成是维系当地生态系统平衡的有效途径,同时将猪祭看成是人祭的替代[12]。
二、献祭图式潜存的性质与功能
对献祭研究颇深的莫过于法国的莫斯、于贝尔,他们摒除泰勒、史密斯、弗雷泽等人坐在摇椅上翻阅各种文献资料而研究献祭的缺陷,认为仅凭过去的文献资料去探讨献祭的起源与历史问题,那是本末倒置、徒劳无功的,至少价值不大,因为文献中记录的献祭内容受到记录者在文化认知、语言背景、观察角度和主体理解等因素的影响而无法准确反映其实际,容易犯以偏概全的错误。因而他对自己的研究界定为:“我们在这里并不建议追溯献祭的历史和发生,而如果我们说到优先性,我们是在一种逻辑的意义上而不是在历史的意义上来使用的。”[1]178鉴于莫斯对“献祭”的定义、仪式“图式”及所传达的一般与特殊功能的学理剖析,意在获取献祭背后的逻辑及旨趣。然而,由于献祭现象的纷繁复杂,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在献祭仪式中预设的文化需求不一,加之无法穷尽的献祭类型,要找到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献祭逻辑是有困难的。莫斯举证农业献祭的例子以说明要获得献祭的普泛解释存在困难,也即是源于人们期待献祭在形式和内涵上的多变性,他无法全观或穷尽农业献祭的类型,即使同一献祭形式却表达着不同的目的,他说:“这是我们观察最细致的献祭,它们的复杂程度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因为我们不敢说用区区几页文字就可以提出一个农业献祭的一般理论。我们无法预知所有明显的例外,我们也无法破译纷繁芜杂的历史发展过程。”[1]219正因如此,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借鉴《圣经·利未记》中关于献祭类型的描述把献祭分为礼物献祭、食物献祭和救赎献祭,莫斯认识到这样的分类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因为在献祭仪式中人们并非仅仅表达一个目的。
在实际的献祭中的确因具体目的的不同而形式各样,但莫斯认为献祭无外乎就是在通过牺牲的媒介作用实现人神的沟通,而这种建立在牺牲物上的祭主与神灵的沟通仪式实质上就是操演“神圣化”和“去神圣化”的神圣与凡俗不断转换的过程,这样的转换呈现为抛物线的发展趋势,包括祭主、祭师、牺牲和神明等都随曲线变化,其中牺牲的转换程度最高。莫斯还借用“洁净”与“不洁”去解析“神圣化”和“去神圣化”的关系,他认为人都是凡俗的,然而都在极力地崇拜和瞻仰神圣,神力是洁净的但也预示着某种危险,人们总会避开直接接触神明的锋芒,献祭中牺牲的作用因此变得重要。莫斯强调人对神性的追逐也源于人们对生命的向往及对死亡的无法把捉和恐惧。当然,莫斯的献祭研究仍脱离不掉年鉴学派惯有的研究方法,他把献祭看成是一种社会事实,其社会实体如何表征出应有的社会功能,在这一原则下满怀宗教情愫的个体意识必须服从于社会的集体力量,只有在由神明共同体一致遵循的社会准则下才有献祭中个体表达的价值与意义,如契约、救赎、惩罚、礼物、舍弃以及灵魂和不朽。因此,莫斯区别于以往的学者,其献祭研究并不局限在宗教文化视域,而是把献祭带到社会学的分析框架和范畴。
利奇在《文化与交流》中用一章节对献祭进行描述,若要深刻了解其献祭研究的内涵,须先了解他的理论观点。利奇的理论来源于两条线索,一条是早期师从马林诺夫斯基等人所学的功能主义,另一条是其继承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然而他并不囿于此二种理论,而是假借道格拉斯、特纳等人的象征范式,将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融入文化的象征研究,进而试图寻找文化象征背后的结构逻辑,这种研究方法在20世纪70年代可算是象征研究的新尝试。利奇认为人们生活中的文化事象不同程度地表现了文化的潜在语法和规则,透露出文化特征,进而形成两者间的结构性关系。二元结构集中展示为物质现象的世界和精神观念的世界,并由象征的方式将二者联系起来。因此,虽然人们习惯于将“二元编码”的思维方式运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但也极力寻求勾连二元对立结构的“物象”。物象既可以是天然的,也可以是人为的,依据此理物象可分为“换喻的线性序列”和“隐喻的聚合联想”两种象征表达方式。所以,将象征方式与观念、物象一道,进而构成类似于列维-斯特劳斯的“烹饪三角”。利奇从《圣经·利未记》有关献祭的内容出发,结合结构象征的分析方法,将献祭的空间划分为二元对立的结构模式,即野生自然/营外/世俗地带/此一世界——驯化文化/营内/神圣地带/彼一世界,在对立的两者间又划出“中间地带”,形成献祭的三角空间关系。另外,他还将献祭的对象间关系分为“捐献者——献祭动物——神”的三角结构类型,其中“供祭动物或物体总是祭品捐献者的一种换喻符号。通过安排某个阈限牧师,使之在阈限区域施行献祭,捐献者得以在神之世界和人之世界二者间架设一座桥梁,跨越它,神的潜势方可以(朝向自己)流动。”[5]451按他的说法,献祭牺牲是存在于捐献者和神之间的符号实体,牺牲不仅仅象征着受难者集体,也象征着带有半神圣性质的上帝使者——牧师。正是基于这一理解,利奇才会认为作为人神一体的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是基督教献祭的早期形式的典型,而后使用羔羊献祭只不过是一种替代性象征,包括给受难者食用的面包和红酒也象征着基督的“肉体”和“鲜血”。通过系列分析后,利奇最终发现在献祭上表现为一种相同的宗教情怀,它是构成献祭仪式岿然不变的潜在要素。从整体来看,献祭只不过是利奇借以分析象征结构的一个常见的文化事象,献祭中的每一个“物象”都具有一定的象征意味,然则它无外乎重在表现二元结构之间转换或隐喻的关系。因此说利奇既试图呈现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象征逻辑,也旨在给人演绎一套关于文化研究的象征分析方法。
相似于莫斯、于贝尔把献祭中的牺牲物当作沟通献祭者与神明之间的媒介,玛格丽特·维萨(Margaret Visser)认为“祭祀被用在仪式的开始阶段,标志着死亡是每一个新生命与生俱来的东西,而那只死掉的动物可以起到调停的作用,它如同一种连字符,一端连接着分离,一端连接着团聚。”[13]30当然,维萨在此认为献祭者所建立的两者并非莫斯指的献祭者与神明的关系,而是人的生与死之间的联系。一方面,他认为死亡伴随着出生而来,献祭与死亡有关系,人们通过宰杀动物献祭的方式,将动物所带来的变化——死亡暗指的结局,如敌意的终止、背叛的结束或某种初具规模的东西的完结,以告慰心灵。另一方面,牺牲者的意义在于人们“献祭一只动物,意味着有意识地加入宇宙的运动当中,让生命通过死亡进入另一个轮回。那只死掉的动物不仅被那些人类,还被某些看不见的超自然力量分享了,它的一部分肉会被摆到一边献给诸神。”[13]29在这里,维萨所要强调的是献祭的功用,作为死亡仪式,它建立了生死之间联系,抚慰人们对死亡恐惧的心理。在他看来,向神灵献祭是人们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的饮食行为,宰杀动物既是人饥饿的生理需求,也满足向神灵献礼的心理张力,吸引人们的注意力进而参与其中,实现社会交往的目的。
探讨献祭的起源时,维萨认为用动物进行献祭是人祭的替换,他说,“关于祭祀的神话通常告诉我们说,那只动物之所以被杀并被吃掉,不过是代替了早期的祭祀品——人类的位置。”[13]30他提出这样一种独特的观点与他在介绍献祭这部分内容之前所描述世界各地曾出现的“食人俗”现象有关,其中大多数部落社会中的食人俗并非把人肉当作食物,而是在战争中把捕获的俘虏用作献祭之物或是进行一种“暴力比拼”(一种部落间战争所出现对俘虏杀戮的比拼)。维萨谈到献祭中杀掉动物是一种非经济行为,“献祭”的含义即有“放弃什么东西”,在原初社会杀掉作为生活资料的动物是极不理智的,但对于那些献祭者来说,“在提供祭品并吃掉它们之时,想到的只是慷慨大方,并不是精打细算”。可以看出,在献祭耗费这一问题上,维萨持赞同态度,虽然违背了现代社会的经济原则,但献祭产生的社会文化意义远远大于杀掉动物所带来的经济损失,这种观点与下文巴塔耶的观点也有相似处。维萨也分析了献祭中的饮食象征,他列举了基督教做“弥撒”的仪式过程,基督徒在“弥撒”中进食作为献祭圣餐的面包和葡萄酒,它们象征着耶稣的肉和血液,因此耶稣不光进入教徒的思想里也进入到他们的身体里,于是“人们围坐在餐桌前,吃着上帝的圣体,不需要杀戮动物,不需要新的死亡,也不需要任何桥梁:上帝直接走进来了。”[13]33在这里,杀戮的血腥和死亡的恐惧不再是那样的直接与显露,而是献祭的另一种隐喻。
三、圣俗转换的“形上”考量
米尔恰·伊利亚德在他的经典著述《神圣与世俗》中对献祭有过一番论述,虽然篇幅不长,却把产生献祭的根源与其关于神圣与世俗的基本观点联系起来。纵使“神圣”和“世俗”是人类两种对立的生命状态,然而“神圣”却未曾在人类发展历程中缺席,尤其“对于早期人类而言,神圣就是力量,而且归根到底,神圣就是现实。这种神圣被赋予现实的存在之中,神圣的力量意味着现实,同时也意味着不朽,意味着灵验。”[14]4伊氏还表明,狂热的宗教徒对神明的膜拜并非局限于精神时空内,神灵通过“显圣物”昭明在他们生活中的实体,如房屋、石头和树等,当然也还有献祭仪式中的牺牲。很明显,“显圣物”身上渗透着“神圣”与“世俗”二元属性,它们“正是借助于神圣的表征,任何物体都能够成为某种‘别的东西’。但是在本质上仍然是其自身,因为它仍然属于它所属的那个宇宙的时空之中”[14]3。事实上, “显圣物”的存在除了沟通人神,建立世俗与神圣的关系外,伊氏认为这更是一种模仿,是人们用周遭世界的事物去模仿天神在元初时期创造世界的场景,呈现宇宙生成的意义。因而献祭与宇宙生成是相互依存的,“对原始生物的杀戮、用它的质料所创造出的并不仅仅是宇宙,而且还有农作物、人类不同的种族或不同的社会阶层,献祭牺牲也正是基于这种宇宙生成的神话模式而进行的。”[14]25伊氏的献祭描述是有关“神圣空间与世界的神秘化”内容的一个例证,他认为宇宙诸神创造世界是通过屠杀和毁灭海怪或者最原初的生物,并用他们的身体生成世界万物,因此宇宙的诞生充满着血腥。献祭便模仿这种血腥方式,只为重塑诸神创造世界的现实,让生命获得新生。在许多早期农业社会中存在献祭仪式的食人或以人为牺牲现象正是出于模仿天神的血腥杀戮,“农作物并不是由自然界所给予的,它是杀戮的产物。因为,它在时间的诞生之初,被创造出来时就是这个样子:猎取敌人的首级,以人作为牺牲献祭和人类相食,这些都被人类所接受以便确保植物的生命。”[14]54因此,依其观点可以得出献祭起源于人模仿神明。然而,模仿神明终究并不是目的,模仿的目的是让生命存在于一个“强壮、清新和纯净的世界”,如果说献祭是仪式中的一种模仿活动,不如说通过献祭这种模仿的方式,“把自己置于与诸神的亲密接触之中,也即是置自己于真实的和有意义的生存之中。”[14]118可以看出,“神圣”与“世俗”是伊利亚德在生命体系中力争表现的二元结构关系,通过象征的手段说明从世俗到神圣的“增圣化”和从神圣到世俗的“去圣化”的转换关系及基本逻辑,旨在表达神性世界对人与生命的意义。
与其他人研究献祭的思路不同,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从文化哲学的角度去考察献祭的意义。在卡西尔三卷本的《符号形式的哲学》第二卷《神话思维》中,他从神话思维起题引出“献祭”的内容。其间,卡西尔以“献祭”为线索,阐述它如何构建出人与神之间的问题,他借鉴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的观点,把后者关于“正题——反题——合题” 的辩证方法运用于献祭的研究。一方面,基于宗教思维的特征,献祭让人们有机会接触神明并与之建立一种互惠关系或共同体的关系,他们相互依存,即人依赖于神,神也必然依赖于人。另一方面,人神毕竟不是同一时空中的现实物,人的宗教行为扩大了两者间的张力和鸿沟。正如他所说,献祭“并没有提供一条通道以便从预先规定并严格限定的自我领域达到神的领域;相反,它们确定了这两个领域,并在两者之间逐步划出新的界线。”[15]251最后,两者间存在的张力和鸿沟不但没有被献祭的过程进一步拉大,相反却积极地将两者相统一,也即“人变成神和神变成人”。这种最终建立起来的人神统合关系,如同卡西尔借用鲁米的话,“就我们而言,你自己和我自己并不存在。我并非你,你亦非我,你我都是如此。此刻我是我也是你,此刻你是你也是我。”[15]253整个来看,卡西尔的献祭研究终究脱不掉符号哲学的基本观点,献祭的符号性质仍然鲜明,如同语言、数学、艺术等,它旨在人与神区隔化的鸿沟上铸造一座桥梁,然而这座桥梁并非只为起到到简单的沟通,因为献祭“以前表现为纯粹物质的或纯粹观点的中介,现在已经提升为纯粹的联系,在这种联系中第一次确定了神和人的特殊的意义。”[15]251按照卡西尔的观点,人们在不断认识和建构神性的世界或者神话的过程,实质上是在不断地认识自我,实现自身的过程。诚如以献祭等方式来联系神明,献祭也因此成为实现自我的直接性,它是人完成自己的外在途径,因此他说:“神祗不断增长的独立性是人发现他自己的一个确定的中心、一个意愿的统觉的条件,而这种条件和人感觉趋向的分散与差异形成对照”[15]244,正是这一人神间差异所形成的“鸿沟”才使人们不断寻找超越它的方法。
美国当代人类学家P·R·桑迪(Peggy Reeves Sanday)在其名著《神圣的饥饿:作为文化系统的食人俗》中列举了15个案例以分析食人俗的文化象征意义。他从食人俗产生的根源着手探索现象背后的文化理性,并因此将食人俗分为礼仪性食人俗、饥馑性食人俗、品味性食人俗和复仇性食人俗。他认为解释食人俗固然必须基于唯物观点的饥饿实证,但仅从饥饿、饥荒或蛋白质匮乏来解释是不够的,至少是不充分的,因为世界各地的确普遍存在着因饥饿而食人的现象发生,但也存在大量宁可饿死也不食人的现象。那么,食人俗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并延续,唯一靠得住的解释只能从文化持有者的神话或宗教热情中去获取。把人作为牺牲者向神灵献祭进而实现沟通神灵或取悦超自然力量的食人文化,其间也形塑了族群内部的本体论和宇宙观。从桑迪关于以人作为牺牲的献祭文化中可以了解到,他认同食人源于人的生物性饥饿的特点,但更看重食人是为解决人的精神性“饥饿”,它既能在仪式中获得欲望的满足感,又能在失去亲人后于情感上得到抚慰。总体来看,桑迪的献祭理论是综合性的,他所认识的食人俗是一个立体结构,书中无不透露出二元辩证的分析方法,包括神圣与世俗、物质与精神、个体与社会、自我与他者、男人与女人等等,他希冀照顾到全体,呈现一个饱满的食人俗文化特征,“为理解某种强有力的人类形象的逻辑提供一面透镜”[16]7。
谈到献祭,不得不提及法国思想家巴塔耶的观点,他曾以牺牲或献祭(sacrifice)为题撰写过两篇短文。虽然文章并非全然在探讨献祭的具体内容,然而却通过对献祭的形式及其在社会中的文化作用的描述来阐释他的神学思想。巴塔耶在思考神圣与世俗之间的关系时常常陷入思想的矛盾当中,一方面“他要让一个幻想的‘我’脱离实存的我,向神性的方向靠近,但是他同时又拒绝神性的客体化,拒绝将它与宗教上存在过的任何一个神灵认同起来。”[4]他既看到把神性客体化为“上帝”的虚无,也认识到物质世界对人的束缚而造就了孤独个体的凌空,希望在同质世界与异质世界间寻求一条生存的窄缝,或者说在理性与感性之间寻找一条存在意义的出路,这样思考的结果最终是“惨败”(catastrophe)。在他看来,“惨败”是将两者进行综合的方式,然而导致“惨败”的原因他认为就是死亡,死亡让人瞻望“燃烧的黑夜地平线”,让人过渡到时间的终结。在这一思想架构下,作为死亡的仪式,巴塔耶不同意泰勒等人将献祭看成是人向神灵的赠礼,也区别于莫斯、于贝尔将研究献祭的视角投放在献祭者的特点,去关注牺牲者暗含主体体验“去圣化”的意义。他批判基督教中关于献祭的功利性认识,提倡献祭的意义应恢复到原始状态中对神性的“无意识”表达。他认为献祭是“神灵”、畜生和人的一次集体混合,并提出“献祭就是消耗”的理论用以解构资本社会中观看世界的经济本能,它符合巴塔耶一贯以试图“逃离”物质世界的孤独个体“凌空”的思想。
结 语
诚然,献祭是人类发展史上一项重要的文化事实,它使人们从荒野生存中演化出来,建筑了安顿心灵的精神家园,通过这一古老的文化传统衍生出神秘的巫术—宗教意识,从而实现了建构人与自然、与自己、与他者之间和谐关系的生命意义与价值。西方社会不仅有悠久的献祭文化传统,从古希腊人的献祭诸神到基督教徒以面包和葡萄酒隐喻耶稣的血肉向上帝献祭,绵延千年。同时西方学者也最早致力于献祭的研究,乃至产生了纷繁复杂的理论体系,概括起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由献祭的文化现象归纳出的理论,包括泰勒的“赠礼说”、史密斯的“共食说”、弗雷泽的“交往说”和伊利亚德的“模仿说”等;其二,用献祭文化现象来演绎的理论,重在说明或例证某一理论的有效性,如莫斯的“社会功能”、利奇的“文化结构”、卡西尔的“符号说”、巴塔耶的“死亡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