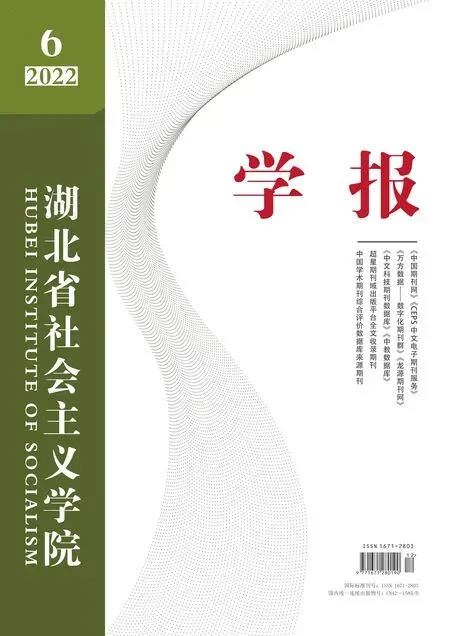文明史观视阈下新型政党制度的历史形成、当代发展与未来趋势
陈 红
(湖北科技学院,湖北 咸宁 437100)
一、历史形成决定新型政党制度必然成为政治文明新创造
新型政党制度的历史形成根源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贯穿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全过程,根植于传统文化近代化转型,这一历史逻辑决定新型政党制度必然成为政治文明新创造。
(一)历史形成根源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新型政党制度形成的根本前提。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型政党制度。近代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亟需产生新的领导阶级和政党组织。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1],这“是近代中国革命历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2](P74),“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3](P15)。从此,中国人民反帝反封斗争有了坚强政党作为领导核心,为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准备了重要领导力量。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前锋军”[4](P25),是依照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它的第一个纲领主张“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强调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4](P5)。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政党性质、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准备。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打下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共产党宣言》称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5](P41)。“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人民立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力量源泉是人民群众,这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1]中国共产党争取民族独立、国家解放、人民幸福,高度契合中国近代历史使命和人民愿望,使越来越多的进步力量向中国共产党靠拢聚集。民主党派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主张民族独立与政治民主,“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都是在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各政党的共同目标”[6]。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创立的最关键因素。[7]“中国共产党不是中国传统政治的延续,而是在世界政党潮流中产生”[8]的新事物,是中国近代政治文明新创造。
(二)历史形成贯穿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全过程
20世纪20年代,中华民族逐渐沉沦但未完全沦为殖民地,关键是“新的阶级、新的政党、新的经济力量及人民群众的普遍觉醒这样的上升因素在起作用”[9](P367)。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明确表示,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不与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4](P9),坚决与非马克思主义政党划清界限。次年4月,陈独秀对共产党及青年团加入国民党果断表示“绝对不赞成,在事实上亦已无加入之可能”[4](P15)。但基于革命实际,两月后他提出“无产阶级在目前最切要的工作,还应该联络民主派共同对封建式的军阀革命”[4](P25),更新了对政党关系的认知。
1923年党的三大通过“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党员应加入国民党”[4](P116)的决议。国共合作革命斗争实践使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掌握统一战线领导权和开展武装斗争对于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重要性,这为此后的政党合作及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的发展积累了经验教训。中国共产党再次与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划清界限,表示“必须克服‘机会主义’的倾向,进行彻底的阶级斗争”[10](P359)。1928年,党的六大制定工农民主统一战线策略,使这一时期的统一战线成为“反封建压迫、反国民党统治的工农民主的民族统一战线”[11](P207)。
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9年,毛泽东深刻总结建党18年来的历史经验时指出:“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12](P605-606)“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三个主要法宝。”[12](P606)统一战线理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重要内容。1940年,中国共产党提出抗日根据地“三三制”政权建设思想,“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13](P170)。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毛泽东特别强调:“‘三三制’政权中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无产阶级和贫农;左派分子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小资产阶级;中间分子及其他分子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12](P750)各根据地先后通过民主选举建立临时参议会和政府机关。“三三制”为党外人士参与政权并占有一定比例提供了制度保障,是新型政党制度的历史雏形。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延续“三三制”政权建设思想,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时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蒋介石派大批特务监视、恐吓、逮捕、绑架民主党派成员和民主人士。中国共产党主动伸出援手,协助民主党派部分领导人转移。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认清国民党的反动本质,主动摒弃中间路线思想,放弃“第三条道路”,支持中国共产党,大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拥护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积极投身爱国民主运动。1948年,毛泽东提出“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14](P1256)。这年5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15](P283-284)。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海外华侨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热烈响应,主动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新型政党制度的确立奠定基础。
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通过,各民主党派参加人民政府,支持社会主义事业,继续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新型政党制度正式形成。
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在政治制度上进行的伟大创造,是“做成”[16]的,是政治选择的结果,也是共同创造的政治文明新成果。
(三)历史形成根植于传统文化近代化转型
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了中国近代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任务。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解决了中国走什么路、建设什么样国家的问题。这一历史进程形成的新型政党制度与我国文化传统密不可分。它是在充分吸收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因子养分后,从中国土壤里生长出来的,是“长成”[16]的。它所涵养、积淀的特定文化内涵,蕴含着优秀传统文化近代化转型中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崇尚和谐是传统文化的价值追求。在新型政党制度中,多党合作有别于一党专政和轮流执政;政治协商非政治竞争和政治对立;有执政党与参政党之分,无执政党与在野党之别。在传统和谐文化的影响下,政党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在相互关切、包容、监督中实现动态的、有韧性的长期和谐。
求变是传统文化的价值追求。中国共产党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新型政党制度是顺应中国社会不断变化发展的实际求变应变的产物,不是古代传统政治制度的翻版延伸或西方政党制度的照搬照抄。
实践至上是传统文化的价值追求。“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止矣”“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等强调知行统一、以行为重。新型政党制度的历史形成蕴含着“理论—实践—理论创新—新的实践”的逻辑脉络。
二、当代发展表明新型政党制度必然实现政治文明新发展
新型政党制度的当代发展取决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实现了理论创新与实践发展的辩证统一,推动参政党自身建设与时俱进,这一现实逻辑铸就了新型政党制度必然实现政治文明新发展。
(一)当代发展取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
1949年、1954年、1956年三次有关民主党派的存废争议,中国共产党对保留民主党派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开国大典后,九三学社、农工民主党、民主促进会纷纷拟起草解散宣言。1949年11月22日上午,周恩来邀请章伯钧、郭则成、彭泽民、季方座谈了解情况,就民主党派前途、地位、作用交换意见。次年2月,毛泽东出访苏联回国后,对救国会解散惋惜不已,称其为进步团体应当保留,并邀请民主党派领导人座谈,明确指示民主党派应继续存在和发展,民主党派得以保留。1954年9月,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关于是否保留政协和民主党派的争议再起,党和国家领导人出面做工作。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确立生产资料公有制,民族资产阶级退出历史舞台,有关民主党派存废问题的争议更甚。中共中央及时召开全国统战部长会议,专门制定《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印发《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二年统战工作的方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我们有意识地保留下民主党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17](P34-35)民主党派存废争议至此平息。正确处理党际关系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在党的八大上正式通过。
多党合作制度在“文革”期间遭破坏,但仍保持其基本原则和总体格局。1966年8月底,周恩来指示中央统战部负责人:“统战部对统战政策不要动摇,不要撒手不管,统战工作必须坚持下去。”[18](P55)同年国庆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对李宗仁说:“政协还是要的,民主党派还是要的。”[19](P2)周恩来多次向有关部门提出:“要把已下放劳动的民主党派人士中的中央委员以上人员,从干校抽调回来。”[18](P357)1971年,毛泽东视察南方时再次表示要保留民主党派,指出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经受严峻政治考验,大多坚守热爱祖国、拥护共产党领导、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1975年,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积极参与筹备四届全国人大会议,宋庆龄、郭沫若、周建人等多位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会上被选举为副委员长,这次会议“体现了多党合作的原则”[20](P220)。
(二)当代发展实现了理论创新与实践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多党合作制度迎来新的发展。党的十二大提出多党合作“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党的十三大确定“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1989年,中共中央出台《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1993年,全国人大八届一次会议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21](P207-208)写进宪法。1997年,党的十五大指出,坚持和完善多党合作制度是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的重大任务。中国共产党持续深化对新型政党制度的认识,不断完善新型政党制度,推进新型政党制度科学化、程序化、规范化建设。
新时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不断推进新型政党制度理论创新、政策创新、实践创新。2013年,明确民主党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2018年,指出多党合作制度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22](P241)。这些新论述从多层面拓展和丰富了新型政党制度的内涵。并且,中共中央、中共中央统战部出台一系列重要文件,加强新型政党制度建设。
新型政党制度理论创新为中国共产党深化多党合作实践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在多党合作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
理论创新与实践发展使新型政党制度在当代政治实践中大放异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民主党派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历者、实践者、维护者、捍卫者。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为推进国家各项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6]尤其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他们“第一时间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号召,与中国共产党想在一起、站在一起、干在一起,凝聚起同心战‘疫’强大力量,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在关键时刻的责任担当”[6]。各方力量竭尽所能为抗疫作贡献,充分彰显“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有利于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23]的优势。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还在国家政权中团结合作,共同推动国家政权建设,“实现了对西方政党理论话语体系的创造性突破”[24]。
(三)当代发展推动了参政党自身建设的与时俱进
参政党自身建设是新型政党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各民主党派的自身建设。
新时代,民主党派的根本性质、功能属性、价值定位更加清晰明确。民主党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须有着与此相适应的标准和要求,对参政党能力素质的要求也更高,加强参政党自身建设刻不容缓。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民主党派加强自身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要求民主党派加强思想、组织、制度特别是领导班子建设,建立健全民主集中制、民主生活会制度以及各项议事决策制度,增进班子成员团结,提高各级领导班子成员的政治把握能力、参政议政能力、组织领导能力、合作共事能力、解决自身问题能力。他要求新时代多党合作要有新气象、思想共识要有新提高、履职尽责要有新作为、参政党要有新面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要当好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增强责任担当,共同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民主党派以执政党为师,以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对标参政党建设要求,与时俱进推进自身建设。
三、未来趋势昭示新型政党制度必然达到政治文明新高度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并不是一个终极的概念,而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发展的过程。”[16]它必将持续推进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必将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贡献更大力量,必将给人类政治文明带来深远影响。
(一)新型政党制度必将持续推进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
新型政党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中国化的宝贵结晶,其生成发展离不开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25](P75)“党是领导一切的,是最高的政治力量。”[26](P68)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进程的演进及社会主要矛盾、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中国共产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肩负的时代使命也会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创造性地领悟、调适、完善、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它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借鉴、吸收、运用,既遵循马克思主义之根本,又结合中国社会实际、适应时代发展要求。新型政党制度作为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将长期存在和持续发展。
伴随传统文化现代化转型中持续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新型政党制度的文化内蕴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同时,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也会以新型政党制度为载体,更好完成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使命。
当代中国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模板,不是其他国际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将面临新任务、新目标、新要求。为更好适应和满足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和要求,新型政党制度必须与时俱进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二)新型政党制度必将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贡献更大力量
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力量和制度支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把中国自己的事办好。新型政党制度之“新”,理论逻辑源于其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中国化,实践逻辑在于其制度效能特有的优越性。它能真实代表并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规避旧式政党制度只代表少数人利益的弊端;能紧密团结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为共同目标奋斗,有效避免轮流坐庄或监督缺失而导致的恶性竞争;能以制度化流程统筹各方面意见和建议,实现决策的科学性和公平性;能统筹兼顾各方利益与协调各方关系、促进决策施策科学性、保障国家治理有效性。新型政党制度的创新发展为世界创造了一种崭新的政党政治模式。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党人始终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5]“中国共产党是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实现中华民族崛起的‘世界上最强大的政党’。”[27](P177)中国共产党是“具有百年奋斗历史的政党必定是面对百年激荡、走过无数激流险滩、历经过重大考验的政党”[6],“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党”[28](P436)。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为世界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与世界人民携手创造人类文明新成就。
(三)新型政党制度必将给人类政治文明带来深远影响
毛泽东曾指出:“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29](P574)新型政党制度“以合作、参与、协商为基本精神,以团结、民主、和谐为本质属性,具有政治参与、利益表达、社会整合、民主监督和维护稳定的重要功能,实现了执政与参政、领导与合作、协商与监督的有机统一”[30]。“新型政党制度框架下的协商民主实践有效回应了政治参与压力和群众利益多元化对社会稳定和政治秩序带来的挑战,为中国共产党生成和维持执政韧性创造了必要条件。”[31]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型政党制度必然焕发出更强大的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
相比之下,西方政党本质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工具,只代表特定的党派、区域和集团利益。各政党视国家政权为竞相争夺的“猎物”,通过多党竞争实现轮流执政或延续执政来平衡利益冲突及党派矛盾,政党关系扭曲紧张,政党制度暴露诸多严重问题,政党主要精力用于筹集选票和拉拢选民而疏于国家整体战略规划和长期政治建设,这不利于国家、社会的整体和长远利益。西方政党整合社会力量的功能渐趋薄弱,社会撕裂顿显,出现“各国传统政党衰落并不断分化,宗教性政党和极右政党等的新类型政党异军突起”[16]乱象。西方政党制度的现实窘境及所呈现的“西方之乱”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创新发展及所彰显的“中国之治”形成鲜明对比。新型政党制度“实现了对西方政党理论话语体系的创造性突破”[24],必然给人类政治文明带来更深的影响。
新型政党制度的创建是政治实践的有益成果,是政治文明的集中体现。文明史观视阈下新型政党制度的历史形成、当代发展、未来趋势已深刻诠释新型政党制度的历史必然性、伟大创造性、巨大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6]透过历史、驻足当代、展望未来,新型政党制度必将达到政治文明新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