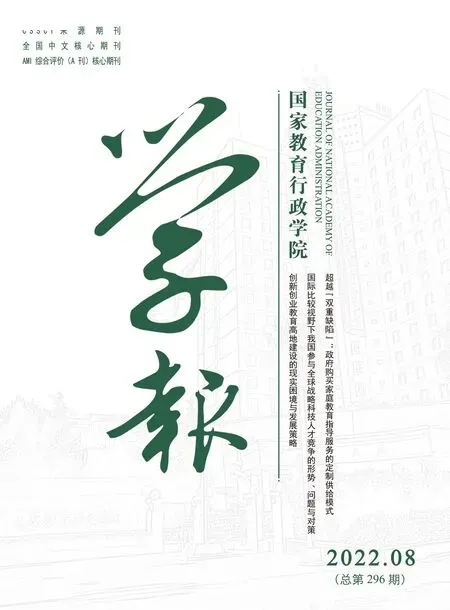自然与文化的融合
——论《自然文化概论》的文化价值
王 昉
马俊杰、程捷主编的《自然文化概论》是国内首部自然文化通识教育教材。该书在新的时代历史语境下,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重新廓清了自然与文化的辩证关系,定义了自然文化概念的内涵外延,以深度专业融合的方式系统阐释了山岳文化、高原文化、江河文化等自然文化形态。在人与自然关系发生转折的历史阶段,《自然文化概论》的问世无疑具有筚路蓝缕之功。但是,这本书的真正意义不仅仅在于学科建设本身,还在于更高层级的两个融合。第一,文化观的融合。该书在文化层面融合了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第二,思维融合。在思维范式上,该书融汇了诗性思维与科学思维。《自然文化概论》在这两个维度上的深度统一与融合真正体现了当代中国文化综合发展的新趋向、新高度。这本教材在新时代语境下的文化实践意义更是不可低估。
自然与文化两个范畴在西方文化史的主流中往往处在一种矛盾对立的关系中。自然与文化的对立早在《圣经》中就有所体现。18 世纪之前,由于生产力低下,西方文化普遍将自然看作需要克服与制宰的他者,“危险和毁灭就潜伏在文明的围墙之外”,这在大量的西方文献中都有体现。正如美国学者海德(Thomas Heyd)在《自然、文化和自然遗产:走向自然之文化》中所说:“从历史角度看,自然被认为是危险的、可剥削的,以及对人类来说本质上是下等的。”至18 世纪的浪漫主义运动,西方文化发起对现代性的历史反思,才开始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正如魏乐博(Robert P.Weller)所指出:“18 世纪——从启蒙运动到浪漫主义——在‘自然’ 的义项进化中尤为重要,自然和文化之间的对立在这一时期之初发展得非常迅猛……”至工业革命的到来,科学技术迅猛发展。19 世纪末20 世纪初,西方文化彻底将人之存在凌驾于自然之上。与此同时,浪漫主义运动以来始发的对科学文化的反思则成为细支末流,无力对峙科学理性的文化统合。直至马克思主义产生,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关联性又得到了辩证统一。佩珀(David Pepper)认为,马克思的自然的概念把自然设想为是一种社会范畴,即重新塑造和重新解释成人类社会。
人与自然的对立,质言之,就是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对立。科学文化的认知方式是将自然设定为认知与改造的对象,将人与自然放置于二元对立之中,科学认知与自然之间是一种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科学方法有两个特点,一是可实证的,其方法是科学实验与逻辑证明;二是可证伪的。科学认知的特点也决定了科学文化的局限性及对自然认知的局限性。从科学认知的方式可以看到,科学对自然的认识是客观的理性判断,不包含价值判断。这就直接导致了科学文化的极端功利性。在西方,科学观一度规约着历史观。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对西方历史观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历史进化论成为西方文化的主流历史意识,而欧洲中心论者又将这种历史意识传播至世界的各个角落,推进着全球的现代化进程。在现代性的冲击下,中国隔断了传统人文文化的价值反思系统,历史进化的现代观念成为中国人的共同意识。正如高瑞泉指出,19 世纪末20 世纪初,中国思想界的一大转变,乃是大批知识分子先后接受了进化论,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传统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世界图景和历史循环论。
历史进化论是线性的,由科学思维主导的缺乏反思维度的历史观带有明显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历史主体意识。这种价值观必然会导致“物我对立”的人与自然的对立观念。正如费孝通所说,我们的生活日益现代化,这种基本上物我对立的意识也越来越浓。在这种倾向下,我们的人文世界被理解为人改造自然世界的成就,这样不但把人文世界和自然世界相对立,而且把生物的人也和自然界对立了起来。质言之,历史进化观将人的主体功能无限度放大,认为单凭借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必然能创造出更为进步的历史阶段,传统文化必然被视为落后文化从而被新文化代替,自然宇宙必然成为人类征服改造的对象。19 世纪末20 世纪初,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的价值理性被置换为“天人分离”的科学理论性。
科学文化“人天分离”的思潮,在五四时期传入中国。由于当时中国文化界对西方科学理性的绝对推崇,科学文化遂深刻影响到了中国历史的现代转型。五四时期,文化界彻底否定了以人文文化为内核的传统文化,并置换以西方的启蒙思想,直至今日,这种科学理性至上的文化观念可谓深入人心。正如费孝通所说,接受西方文化的浪潮,拜德、赛两先生为师,是“五四”以后中国文化变动在历史上的主要方向,也是不容我们否定的历史事实。当前提出的“现代化”基本上是这个历史潮流的继续。20 世纪以降,在西方科学文化大行其道之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的自然人文文化观一直受到压抑隔断。而时至当下,在国际上,生态文化日渐兴盛;在中国,经济的崛起也催生了传统文化的觉醒与再造之势。西方科学文化与中国传统人文文化融合的历史契机已然来临,而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也将得到新的审视。正如胡帆等人指出:“……科学理性的弘扬正好弥补了人文文化对自然研究的不足和缺陷,也显示了人类改造自然的伟大力量;人文文化则展示了人性的尊严和价值,同时也是对科学理性文化的必要补充和引导。这就使得人文文化必然与科学文化走向融合。”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的融合是时代之需,也是历史之必然。
在此时代背景之下,《自然文化概论》体现了自然与文化的真正融合,即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交融重铸。在该书第一章 “自然与文化”中,首先阐释了“文化”与“自然”这两个“既对应又对立的概念……合二为一,称之为‘自然文化’”时,如何能产生新的内涵,实现“本质上的对立统一”。在其后,该书在分章介绍山岳文化、高原文化、江河文化等不同自然文化形态时,则从科学文化、人文文化、传统文化、现代文化的综合视域来阐释对象。例如,第三章 “山岳文化”的第一节“山岳的形成”中,主要是以纯粹的科学理性来论述山岳的形成及其特点,而在第一个分题“山岳形成的地质背景”中,该书则大量引用了《诗经·小雅·天保》《说文解字》《尚书·尧典》等隶属人文文化范畴的传统文献,在介绍科学知识理念的同时引入人文性论证。该章第二节“山岳景观美学”与第三节“山岳文化的类型及特征”则纯粹从文学艺术等人文审美范畴观照对象;第四节“山岳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则从考古学、历史学、哲学、文学以及政治学等多维度多视角综合论证山岳文化的生成发展与价值意义。该书的每一章节对每种自然文化形态的研究阐释,都将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紧密融合。这种融合充分弥合“自然”与“文化”的历史裂隙,从而具体阐释了新的综合性的“自然文化”观。这种自然文化观体现了自然与文化的辩证统一,正如王钟陵指出,自然决不仅仅是一种外部环境,地理条件也决非只是一种外因,它们必然向着社会的内部转化,正是这种转化,使特定人群和特定的自然环境谐协在一起,从而形成特定的文化丛。而该教材的思路就是重点阐释自然外因是如何转化为特定内因从而形成特定文化,在本质上揭示了自然文化的生成。
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融合又体现了两种不同思维范式的交融,即科学思维与诗性思维的结合,而这种思维上的变革更具革命性与划时代意义。诗性思维是意大利哲学家维柯(Giovanni Battista Vico)在其名作《关于各民族的共同性的新科学的一些原则》中命名的思维范式。维柯认为,人类童年时期“不能形成关于事物的理智的类概念,于是就需要创造诗性的符号;那就是想象的类概念或普遍物……”。维柯所指涉的想象的类概念,是指区别于逻辑思维的类似想象的直感、悟性、创造等综合性认知能力,这种认知能力没有逻辑推演的时间过程,而是以诗性的方式直接通达事物的本质,类似于胡塞尔(Edmund Husserl)提出的本质直观、佛教的当下直觉以及传统文化中的顿悟。这种思维方式创生了人文文化,而科学理性则创生了科学文化。因此,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融合实际上也体现了两种思维范式的融合。在西方,科学思维一直是主导性思维范式,于五四时期传入中国。中国社会在全盘西化的极端历史背景下,割裂了科学思维与诗性思维,将两者绝对对立,从而造成了文化的分野与阻断。其实,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范式在本质上就是科学思维与人文思维的结合,是一种球形思维。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周易》。《周易》以数呈象,就是在数理逻辑的基础上发展出人文思想。《自然文化概论》弘扬了传统文化中以数呈象的思维模式,在观照对象的时候,以地质、地理、物理等严谨的数理形式规定了对象的物质基础,进一步阐明物质怎样影响了文化的生成。例如在第四章 “高原文化”中,该书首先对高原的海拔、面积、特征列出精准的数据表格,其后以此为基础论述了高原民族、民俗文化的形成,两者相辅相成、互为因果。
由于该教材将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科学理性与诗性思维融合,呈现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合体思维,真正迎合了大时代的需要,在当下中国顶层设计的引领下,迈出了新时代文化融合的扎实步伐,其文化实践的历史意义不可低估。中西方文化史中对科学技术反思的影响范围往往仅存在于文化层面,并未进入政策层面和教育系统进而推进文化实践。对两种文化的反思与融合必然要推进到政教系统的文化实践层面,才能因“政教”而“风俗”再至民族文化心理,因此,实践性是文化传播的重要环节。正如洪晓楠指出:“我们追求科学与人文的……它们的关系正是辩证法所揭示的 ‘对立统一’,是二者保持独立的基础上的统一。”一个多世纪以来,由于历史语境的限制与历史变革的拘囿,中国社会在政策引导层面一直以科学文化与线性的进化历史观为主导,我们的教育系统也是贯彻以此为主导的教育理念。正如魏乐博指出,科学文化披着在五四运动期间被无比理想化的“赛先生”的外衣,在20 世纪20 年代建立了凌驾于其他外国思潮和更加有机的中国式观念之上的近乎支配性的权力,科学观完全掌控了教育系统和政策的建立过程。20世纪50 年代,我们的大学教育建制完全模仿苏联模式,文理严格分野。理工科的课程设置,除了基础性的大学语文、思政教育,完全没有人文文化的熏陶与诗性思维的训练,主要以科学思维为主导。而文史学科设置也阻断了传统文化中某些诗性思维的特质。因此,在我们现行的大学教育中,存在的是将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科学思维与诗性思维、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传统思维与现代思维隔绝的教育模式,这无疑是阻碍文化融合的一大弊端。其实,中国传统文化因为奉行一种具有反思维度的价值理性,一直强调教育的文理结合,注重思维的多向度发展与灵活实践,例如孔子设置的课程“六艺”就包含了“礼、乐、射、御、书、数”,将数理与人文结合,而且这种修养是终身性的,并不似我们当下的教育,到了大学教育就要严格分化文理。儒家也特别重视政教系统的文化传播,因此,儒家知识分子强调“出将入相”“达则兼济天下”的积极入世,从而能推行儒教化成天下。
文化理念只有进入文化实践层面才更具历史效应。其要进入文化实践,就必然要首先在思维方式上进行变革,而这个变革最终将依赖教育的变革,教育的变革又首先体现于教材的革新。在这个意义上,《自然文化概论》不仅真正做到了在工具理性中引入价值理性,而且是在理工学科严谨的科学思维体系之中引入人文文化的价值参考,实属难得。其对当下教育体系必然产生深远的影响,对改变近代以降中国人的思维惯性有着重要的引导价值和文化实践价值,思维的转化必然也会带来文化的重铸。
科学文化曾经一度成为文化霸权,科学思维深刻影响了我们民族的思维方式。当今,全球性的环境与文化危机,使得人们继浪漫主义运动之后又开始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根本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所倡导的生态文明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正是在主导思想中重树了人文文化与诗性思维的价值地位,将人文与科学的融合真正落实在文化实践之中。《自然文化概论》的出版引风气之先,正是当前时代文化融合实践的重要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