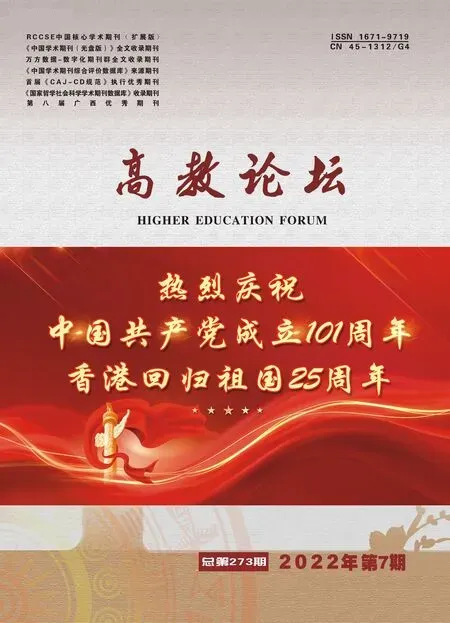“结构—行动”:探寻大学治理的新视角
张文江
(南京大学 党委宣传部,江苏 南京 210023)
一、问题的提出
以多元共治建构的大学治理模式,长期以来延续了结构主义的思路。其特点是把研究对象作为一个整体,重在强调各要素之间相互协作并在结构内部实现共治。具体而言,政府、市场、社会是大学外部治理主体,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民主监督权力是大学内部治理力量,在各自治理结构中发挥作用,以求实现大学善治。这种多元共治的理想模式有其历史贡献,也有其不足。近年来,学者们从大学治理需要内外部动态调适、需要从治理主体转向治理规则、需要与大学制度相融通、需要考虑方法论取向转变等角度进行了思考。如:常亮认为,“现有研究在有意无意间忽视大学内外部治理间的动态调适,未能构建大学治理内外部间的有效联系、双向互动、正向溢出机制”[1];李立国提出,“由探讨‘谁在治理’转向研究‘如何治理’‘怎样治理’,由探讨从主体为中心的‘表层结构’转向实践为中心的‘深层结构’,揭示大学治理的系统性、复杂性、多维性”[2],“大学治理的制度逻辑的关键在于通过融通‘大学之制’与‘大学之治’,使得大学制度通过体制机制建设转化为治理体系,并使得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3];张衡认为,“行动主义治理,突出强调行动者的能动性、创造性,为走出结构约制、制度宰制的重重包围提供了可能”[4],等等。这些研究让治理调适、治理实践、治理效能、治理行动等逐步成为大学治理关注重点,对于拓展多元共治的大学治理研究视野甚或探寻大学治理新视角大有裨益。
理论的发展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帕森斯(T.Parsons)的结构功能主义是与二战后重建秩序的时代之需相契合的,他认为任何系统都有适应、目标达成、整合、模式维持四大功能,当有新的变量产生时,又会形成新的均衡。这一理论在美国社会学界占主导地位长达三十年之久,直到达伦多夫(R.Dahrendorf)和科塞(L.Coser)创立冲突理论。此后,随着对人本研究的复归,霍曼斯(G.Homans)和布劳(P.Blau)提出社会交换理论,吉登斯(A.Habermans)提出结构化理论,布尔迪厄(P.Bourdieu)提出实践理论,等等。其间值得一提的是,亚历山大(J.Alexander)在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基础上提出新功能主义,强调了能动性在结构中的作用;格兰诺维特(M.Granovetter)在新经济社会学研究中,对经济行动嵌入社会结构作了着重强调,等等。现有研究对结构与行动的内在关系进行了着重分析,并认为:行动不是外在于结构,而是内嵌于结构;结构制约着行动,行动又改变着结构。这些真知灼见为从“结构—行动”视角研究社会事实提供了理论依据。
从外部、内部结构探讨大学治理的思路,虽然很难严格用哪种理论去框定,但究其理论渊源都与结构功能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与大学外部治理体系对应的是政府、市场和社会,与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对应的是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和民主监督权力,这三大主体和四大权力分别发挥着相应功能,形成了大学外部、内部治理的理想结构,以致于在近些年大学治理研究中,学者们对大学外部治理体系、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倾注了诸多热情。所不同的是,政府、市场、社会与大学是四个相对独立的组织,因而在大学外部治理研究中常冠之以“体系”;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民主监督权力是大学内部存在的四种权力,这使得大学内部治理研究可以形成闭环,故而被称之为“结构”。尽管各有侧重,但是其指向有异曲同工之妙。毫无疑问,既有的大学治理研究对于推动大学走向善治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有学者提出“从形式有效和实质有效两个维度考察我国大学治理的有效性”[5],“中国的大学治理要从‘求变’到‘求治’,从治理变革走向治理建设,从治理体系转向治理能力,从治理目标转向治理效能,实现从大学治理的‘实然’现状走向‘应然’改革”[6]。还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在‘权力下放’与‘自治能力’不够、‘自律意识’不强并存的情况下,多元共治的分权结构,甚或可能导致高校治理失灵”[4]。如何更好地形成切实有效的大学治理视角,这已成为摆在研究者们面前的新课题。其中最难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审视治理结构,在原来的结构分析框架基础上,根据大学特质和治理需要,让大学治理实效性得以凸显。为此,本文试图用结构与行动相贯通的视角作一尝试性分析。
二、大学治理何以秉持“结构—行动”视角
秉持“结构—行动”,是大学治理拓展多元共治的现实需要,也是探寻大学治理新视角的有益尝试。
多元共治的理想模型为从“结构—行动”视角研究大学治理提供了重要参考。大学治理的核心指向是实现大学善治,让大学成为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同时为世界大学发展作出应有贡献。自“985工程”提出以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成为引领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课题,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命题,一流的大学需要一流的治理就是其中之一。围绕这一命题,学者们进行了诸多探索。在其他学科广泛引用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与文森特·奥斯特罗姆(Vincent Ostrom)夫妇创立的多中心治理理论时,研究者们也将这一理论引入到了高等教育领域。用多元共治研究大学治理的思路受到了诸多青睐,一时间,多元共治几乎成为大学治理的代名词,似乎这才是大学治理应有思路。当然,也有学者对这一理论是否有效提出质疑,认为如同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存在一样,多中心治理理论也存在失灵可能,该理论模型“可能在特定的情况下是有效的,但是未必一定能够提供理想的政策选择方案”[7]。尽管在现实中还存在诸多不足,但这一理论模型对推动大学治理研究具有毋庸置疑的借鉴意义,特别是对大学内部、外部治理结构的区分,开启了从多个角度分析大学治理影响因素的有关研究,让从“结构—行动”视角研究大学治理有了现实参考。可以说,“结构—行动”视角是对现有研究的进一步审视和拓展,特别是对结构、行动以及结构与行动内在关系的关注,一定程度上可以弱化甚至避免多中心治理理论可能带来的失灵。
多元共治的行动规则为从“结构—行动”视角研究大学治理提供了诸多启迪。多元共治其核心内涵是多主体、多中心协作共治。在这个框架中,治理主体犹如分布在圆周上的重要节点,治理对象犹如圆心,双方形成多个治理主体指向治理对象的理想结构。协作共治是这个理想结构中的行动规则。与倡导治理规则应如何发挥作用相比,多中心治理理论更强调多元主体的自发参与。在该理论看来,可以自发地形成政府之外的多个其他类型的治理主体。该理论被引入我国,特别是大学治理领域后,虽然拓宽了研究思路,但也带来一些问题。如:在大学外部治理中,政府应如何变管制为服务尚不明确,市场、社会应如何参与治理也缺乏明确阐释;在大学内部治理中,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民主监督权力应如何协同发力尚停留在模型建构层面。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协作共治的确不易,而这恰恰为“结构—行动”视角更好发挥作用提供了重要启迪。就大学内部、外部治理结构来说,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民主监督权力都有其发力重点,政府、市场、社会也各有其行动逻辑,要把它们有机整合到多元共治的框架结构之中,至少需要两个前提:一是根据治理目标,制定具有共性特质的行动规则;二是根据各自逻辑,制定适合自己的行动细则。不仅如此,如何认识大学结构、如何激活并规范大学治理行动、如何促使结构与行动良性互动等所有这些问题,都是“结构—行动”视角要重点关注并解决的重要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是“结构—行动”视角对多元共治的不断拓展。
在“结构—行动”视角中,结构是行动的结构,行动是结构的行动,二者不可分割,更不可缺失。换言之,没有行动的结构是个空壳子,没有结构的行动是个四不像。对于结构和行动的架通,理论界已有多方努力,并形成诸多成果。就结构二重性来说,吉登斯认为,结构是由规则和资源建构的;规则是用来规范向时空延伸的例行化和区域化行动的连续形式;资源包括控制物质对象的配置性资源和控制人的权威性资源;结构二重性简言之就是结构对行动有制约作用,行动又改变着结构。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为大学治理探寻新路向提供了借鉴。总体来说,大学治理是个兼具结构和行动二重属性的研究领域,既要从纵向的时间坐标轴审视大学治理,也要从横向的空间坐标轴看待大学治理;既要考虑与大学治理相关的资源,也要考虑与资源运用相匹配的规则;既要从静态角度研究大学治理结构,也要从动态角度研究大学治理行动。
三、“结构—行动”视角下的大学治理
秉持“结构—行动”视角,就是要在时空坐标上把握大学治理的实然状态,在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相结合中把握大学治理应有效能,在结构和行动良性互动中把握大学治理既定目标。
在时空坐标上把握大学治理。大学是时空的产物,既有时间序列的移动痕迹,也有空间状态的驻留。只有从时空两个方面思考大学治理,才能把握大学所处的坐标。从时间上讲,大学是文化传承中的一个标志,代表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度代代相传的文脉特质和文化基因;从空间上讲,大学是世界文化交融中的一个缩影,代表着此时的世界文化的共性特征和所在国家的文化特性。从时空坐标把握大学治理,就是要在大学治理的设计和推进中,既看到大学的过去,也要看到大学的现在,更要预测大学的未来。随着大学日益走向社会中心,大学不再是抽象化的师生共同体概念,而是涵盖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国际交流合作诸多内涵的巨型社会组织。站在时空坐标上研究大学治理,就是要让大学职能成为构建大学治理结构的重要参考,即让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国际交流合作职能成为大学治理的目标所指,让这五项职能充分发挥作用成为大学善治的目标所在。
在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相结合中把握大学治理。配置性资源是可以控制物质对象的物化资源,如经济、法律等相关制度。权威性资源是与人伴随的资源,如威望、魅力等个人影响力。在大学治理中,既需要代表正式组织和正式制度的配置性资源,也需要与个性特征、行动情境、规则惯习等相吻合的权威性资源。就配置性资源来说,多元共治所提到的政府、市场、社会都是外在于大学,且有正式制度约制的正式组织,都可作为与大学治理相关的配置性资源。不仅如此,与大学内部治理相关的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民主监督权力也有配置性资源属性,也可根据需要整合到大学治理框架之中。就权威性资源来说,大学书记、校长及其战略眼光、社会影响、领导艺术、处事风格等个人影响力以及对大学治理可能产生重要影响的校内外人士,都可作为与大学治理相关的权威性资源。在把握资源的同时,还要建立起与资源运用相匹配的规则体系。“当规则逐渐产生并被整个共同体所了解时,规则会被自发地执行并被模仿”[8]。规则的建立,让行为有了可预见性和可模仿性,让资源的运用有了相应的约束力甚至内动力。对于配置性资源,要充分发挥制度信任作用,让正式的组织行动可预见。对于权威性资源,要充分发挥人际信任作用,让复杂的人际交往过程更易理解和更可预见。当然,“大学是一个独特的学术性组织,它有其独特的价值追求,有其独特的运行规则”[9],这就要求建立规则体系时必须坚持学术导向,只有这样,才能让大学与其他类型组织相区别,也才能更好发挥大学治理效能。
在结构和行动良性互动中把握大学治理。“大学治理不能光在静态的结构上做文章”“善治见于行动”[10],把结构和行动架通起来是大学治理取得实效的内在需要。大学治理结构不是资源和规则的堆砌,而是资源和规则的运用。其间发挥作用的就是行动者,既包括组织,也包括个人。此处的组织既指正式组织,也指非正式组织;个人既指大学书记、校长,也指对大学治理可能产生重要影响的校内外人士,其中就包括“组成大学的三个群体——教师、职员以及学生”[11],他们具有高度一致的目标,是大学治理的坚定践行者。在“结构—行动”视角中,结构不再是框架性的存在,而是既约制行动,又因行动而动态调整。促使结构具备静态属性和动态属性的动力源在于行动者及其行动规则。单纯的组织或者单纯的个人,都不可能实现结构与行动的良性互动,因为组织是个人的组织,个人是组织的个人,只有把组织与个人在行动目标、行动情境、行动规范上相对统一起来,才可能在结构形成和变迁中发挥正向作用。同样的道理,单纯的治理规则或者单纯的学术行动,都不可能实现治理规则与学术行动的有机结合和同频共振,只有将二者统一到大学治理目标、治理效能的框架下,才能为二者的契合提供内动力,也才能让大学治理朝着善治目标阔步前行。
四、结语
以多元共治建构的大学治理模型拓宽了我国大学治理研究思路,有其历史贡献,但随着发展逐步显现出不足。在推动大学治理走向善治的过程中,有必要立足多元共治的现实需要,客观分析现有大学内、外部治理诸多影响因素及其在协作共治中所面临的具体问题,进一步明确大学治理秉持“结构—行动”视角的内在需要及其可能性,逐步聚焦治理行动与治理结构适切这个大学治理的关键话题。在“结构—行动”视角中,结构可以约制行动,行动可以改变结构,在二者的能动作用下,大学治理结构在与内部、外部环境的适应中保持应有的动态特性。其中,时空坐标为适时调整大学治理起到了把舵作用;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的结合以及制度信任和人际信任的结合,让大学治理效能发挥成为可能;集体与个人二者在行动目标、行动情境、行动规范上的相对统一,让大学治理处于良性的动态调适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