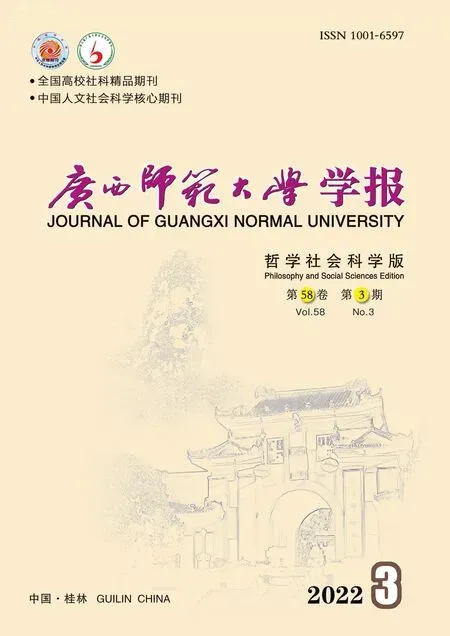赛璐珞、影像共同体与数字化
——从《一秒钟》到数字时代的影像
蓝 江
(南京大学 哲学系,江苏 南京 210093)
2020年底上映张艺谋导演的新片《一秒钟》用了十分古典的方式,让我们重新回忆了那段曾经沧桑的岁月。一望无际的黄沙、矗立在公路边的小镇、方砖砌成的礼堂、风俗淳朴的民众,与那张镶着黑边的白色荧幕一起构成了张艺谋导演为我们呈现出来的一个20世纪60年代中国西部的世界。或许,这部电影的主角并不是打了人,从劳改农场逃出来,拼了老命就为了看女儿一秒钟影片的张九声;也不是为了盗取电影胶片来赔偿被弟弟烧坏了人家用电影胶片制作成灯罩的刘闺女;也不是在二分场里因为放映电影拥有着崇高地位,总是试图用尽各种方法来保住自己电影放映员地位的范电影。其实,《一秒钟》试图通过被电影重构出来的那个时代的三个小人物的故事,来展现一个特殊的主角:电影本身。换言之,《一秒钟》是一部关于电影的电影,它本身制造了一个时代,一个以赛璐珞胶片电影为中心地位的时代,在那个叫做二分场的地方,电影成为了一种圣物,而放电影和看电影也随之变成了一种仪式,这种看电影的仪式,经过导演的塑造,变成了一种以电影为中心的社会关系格局,而《一秒钟》中的那两卷电影胶片自然也成为了勾连起整个电影故事脉络以及三个彼此看起来无关人物之间的关系,甚至直接构建了整个位于中国西北一隅的小镇上的社会关系网络。在这个意义上,电影(包括具体的电影胶片和范电影所在的剧场,甚至包含了抽象的电影观念)构成了《一秒钟》整个逻辑框架的中心,它就是《一秒钟》的真正主角。
倘若从这个角度深思下去,不难发现,张艺谋导演通过《一秒钟》复活一个以电影为中心的时代,并不是为了缅怀一段业已逝去的岁月,一个让电影如此神圣的时代,更不是对那个时代的种种现象的挞伐,而是一种埋葬。就像最后被埋入黄沙里面的那一秒钟张九声女儿的胶片一样,曾经的赛璐珞电影业已在今天的数字化时代被埋葬。今天的时代,俨然已经是数字媒体为王的时代,人们当然还可以到电影院里去看和范电影在礼堂里投影在屏幕上的一样的电影,但更经常的是,我们可以在自己家的手机和电脑上看电影,甚至可以在地铁和公交上看电影。原来一部电影胶片的拷贝需要从一个地方护送到另一个地方,就像《一秒钟》的杨河所做的工作一样,但今天的一份拷贝仅仅只是电脑上的一个复制加粘贴的操作。在进入到5G和万物互联时代之后,一部时长一个多小时的高清电影,在网络上下载可能真的只需要一秒钟。试问,在这样的时代里,我们为什么还需要怀念那个曾经的赛璐珞胶片的时代?尽管我们今天仍然可以在电影博物馆里保存着经典的赛璐珞胶片,但是,那些曾经以这样的方式看电影的人和空间或许很难再被复制出来了。或者可以这样说,《一秒钟》在根本上就是一部埋葬电影的电影,在《一秒钟》的最后,包含张九声女儿一秒钟的胶片还在,只是被埋入了滚滚黄沙之中,我们今天何尝不是如此呢?很多经典影片的赛璐珞胶片还在,但是已经淹没在更个性化和细分化的数字媒体当中,它们当然可以通过数字复刻的方式再现在人们的电脑和手机屏幕上,但那个原本的胶片放映的体验却永远地埋葬了。因此,在表面上,《一秒钟》似乎在为生活在21世纪的中国的人们讲诉曾经的往事,但更根本的是,《一秒钟》向今天的人们提出了一个震耳发聩的课题:萦绕在电影周围的神圣化光环退却之后,电影影像还能为我们的生活世界做些什么?
一
在整个《一秒钟》电影中,或许,在一些观众心目中,影片临近结尾处,张译饰演的张九声最后在面对被保卫科干部扔进黄沙里的女儿的胶片嘶吼的镜头是整个片子最富有情感张力的片段。但对我来说,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却是当范电影的傻儿子赶着驴车驮着第22号《新闻简报》,而那一卷胶片已经变成了范电影口中的“一堆烂肠子”。随后的一系列镜头,对于当今处于数字时代的人们来说,已经变得有些匪夷所思了,为了这堆“烂肠子”,范电影几乎动员了整个二分场的力量,不管男女老幼,为了看上这么一场电影,都主动听从范电影的安排。二分场的女人们回家找了好的花布,缝合起来,将已经变成“烂肠子”的胶片放在了这块巨大的花布上,众人小心翼翼地托举着花布,一步步地将大街上沾满灰尘和砂砾的胶片送进了放映电影的礼堂。在这里,导演给出了从空中俯拍的镜头,这似乎是从一个神圣的视角向下看到了一种胶片相对于二分场群众的一种权力关系,花布下的每一个人,都努力维持着位于她们上方的电影的神圣性,那堆被搅成“烂肠子”的赛璐珞胶片,在今天看起来就如同垃圾一般,但在那块神圣的花布上,那就是一种象征,一种代表着二分场所有人精神生活的象征。正如范电影所说,“看一次电影,跟过年一样”。
在二分场的群众热火朝天地将电影胶片送进礼堂之后,便进入到了清洗过程,和找花布的过程一样,二分场的老少爷们在街道上开了火,并按照范电影的说法,制作了蒸馏水,用这些被视为最纯净的水,来清洗这些被神圣化的胶片。我们注意到,范电影要求的不是普通的开水,而是经过蒸馏提纯的蒸馏水,相对于开水,制作蒸馏水需要更复杂的工具。或许,张艺谋导演试图通过这个制作蒸馏水的过程,试图表达出一种象征性意义,即蒸馏水代表着纯洁无瑕,那么,即便在那个时代里,被蒸馏水清洁的对象也一定是纯洁无瑕的,换言之,当范电影提出用蒸馏水来清洗电影胶片的时候,或许已经不再纯粹从技术性的原理来理解蒸馏水与电影胶片的关系,蒸馏水的纯洁与胶片的神圣性建立了一种语义学的关系,即无论时代如何风云变幻,那些神奇的电影胶片,即便被卷成了一团,沾染了尘土,它依然是最神圣无瑕的存在物,也只有这种最纯洁无瑕的存在物,才能有效地将二分场群众上下一心地统一起来。在具体擦拭环节中,范电影像刚刚提出烧制蒸馏水的方式一样,对参与擦拭胶片的动作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在看到一些毛手毛脚的老爷们干不好这个活的时候,他生气地将所有的男人都赶下台去,只留下了那些干活细致的妇女用她们纤柔的巧手,一点点地拭去胶片上沾染的泥土和尘埃,让胶片重现清澈透亮的原貌。
此后,导演不停地用镜头切换表现了在后台上细心擦拭着胶片的人们,甚至有时候给出一个特写,看出某个人面对胶片的那种眼神,不是一种主体面对着客体带着认识论权力的凌厉目光,而是一种崇拜,如同信徒在神灵面前的眼神一般。对经过蒸馏水擦拭过的胶片,电影给出了一个中景,让观众的目光停留在两行挂着电影胶片的平行的绳子中间,光线从正前方的窗户照进来,让被清洗过的胶片在光线的反射下熠熠生辉。而略透着明亮光线的电影胶片轻微地摇曳着,似乎在面对着映射过来的光线做着它们最自然的反应。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隐喻,我们知道,电影胶片最终是透过光线将影像投影在荧幕之上,在这个意义上,电影胶片不仅仅意味着纯洁无瑕,也意味着它们在从沾染泥灰的不透明状态向被擦拭之后的透明状态的转变过程中,在重新可以被光线透过的那一刻,胶片重新获得了生命,在光线的洗礼下重新焕发出活力。这一组镜头,与其说是在为今天的人们重现出上个世纪赛璐珞胶片时代如何清洗胶片的技术性常识,不如说张艺谋导演用光与胶片之间的映射关系,谱写出胶片电影时代的诗学,电影需要胶片,因为胶片是电影的身体,电影也需要光,因为只有光才能赋予胶片灵魂。当然,在光和胶片之间,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元素,就是那些介入其中的人,只有人的目光,人的凝视,正像电影中给出的特写镜头一样,让光与胶片的关系发生了关联,让光的能量真正注入到那些物质性的胶片当中,那么,人的目光构成了光和胶片辩证关系的催化剂,让胶片可以在人的目光之前道成肉身,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电影。这是一种三位一体的诗学,它构筑了光—胶片—人的目光之间的循环,而这种循环才是胶片时代电影的意义所在。
终于到了电影的放映环节,事实上,当范电影每一次从后台走出来,告诉清洗胶片的进展时,礼堂下面都会响起雷鼓动山川般的掌声。当夜幕降临,礼堂内的光线都熄灭之后,从正对着屏幕的窗口中投射出来一束白光,洒在那洁白的幕布上。整个礼堂顿时喧嚣起来,在那一刻,礼堂里的男女老少似乎从日常生活的节奏中剥离开来,他们找到了另一种自我;在白色光束的指引下,他们的身体似乎在那被白色灯光映射的幕布上找到了最好的出口。他们大声嘶吼着,将埋藏在心里的压抑和兴奋都发泄出来;他们伸出手来,触摸着在礼堂空间里那道唯一的光;他们身体的任何部位出现在白光经过的地方,都会被直接映射在幕布上,看到了自己的行为得到了回应,人们更加兴奋,不顾一切地将自己映射在幕布上,仿佛在刹那间,自己在荧幕上的映射成为了他们逃逸整个日常生活空间的出口,有人甚至搬来了自行车和其他日用品,用自己的身体和物件在幕布上绘制着属于他们自己的艺术画作。这是今天的电影院里无法再享有的艺术和快感,因为在今天的人们看来,走进电影院等待着电影的开场就是一种日常的程序,进入影院与电影的放映是直接连接在一起的,中间没有太多的间隙。而在上个世纪有过类似观影经历的人们都知道,在那个时代,观众入场坐好和放映正片之间有一个巨大的时间空隙,而在这个空隙中实现一种观众的狂欢化,成为那个时代观影经验不可磨灭的记忆;导演足足给出了几分钟的时间,让礼堂内的人们竭尽全力去展现出自己,也让今天的人们通过我们眼前的这块屏幕体会了那个时代的观影愉悦。让我们知道,在那样的体验中,看电影不是一种静态的观众和影片的二元关系,而是一种参与性的活动,每一个人都试图通过自己的身体和手中的物件来为这场放映留下自己的痕迹,而他们的身体运动也与电影的活动有效地衔接在一起。或许,我们可以从这个侧面重新理解范电影的那句话,放映电影就“跟过年一样”,它具有特殊的快感和意义。而今天电影院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恰恰是观众面对荧幕的冷静,人们的观影体验不再是狄奥尼索斯式的狂欢,而是阿波罗式的常规化轨迹,这种仪式化的狂欢快感的消失,也意味着一个时代的逝去。
二
在放映正片《英雄儿女》的时候,导演给出了一段运动—影像的长镜头。镜头从荧幕前最正常的观影位置开始运动,这个起点是我们今天在电影院里被视为最佳观影位置的地方。通过这个方式,电影形成了两个视角的重合:一个角度是我们今天在电影院里观看《一秒钟》这部电影的角度,另一个角度是坐在二分场的礼堂里从最佳观影位置出发观看《英雄儿女》的角度。这种错位造成的感觉是,我们在此处看的《一秒钟》,实际上也正在观看着影片之中的《英雄儿女》,我们同时成为了两部电影的观众,但是这两个视角并不是完全重合的,因为我们看到的《一秒钟》是宽荧幕电影,而《英雄儿女》是窄荧幕电影,那么《英雄儿女》的两侧实际上是露出来的;而在张艺谋的再现下,一些观众实际上是站在二分场礼堂中央舞台的两侧来看《英雄儿女》的,在那一刻,似乎这些站在两侧看《英雄儿女》的观众,也仿佛出现在我们的荧幕两侧,和我们一起看着《英雄儿女》。借助这种视角的重合,我们和二分场的人们一起参与了一场观影行动,现实中的我们似乎与电影中的观众叠加在一起,构成了一种画面里和画面外的共同体验。倏然间,我们仿佛通过这种共同体验穿越了时空,和那个时代的人们一起感受了那个世界,一起体会了赛璐珞胶片时代的特定感受。为了增强这种感受的现实感,导演还特意增加了一个烧胶片的插曲,烧胶片是赛璐珞胶片时代特有的产物,一旦烧片,放映员在放映室里就会一阵忙乱,将烧掉的影片剪掉,将前后两个部分重新接在一起,继续放映。估计有不少观众在看到眼前电影中烧胶片的那一刻,都有一种时代的穿越感,一个胶片时代的事故,在张艺谋的电影里突然变成了一种浓浓的乡愁。
随后,电影的镜头发生了运动,通过镜头的运动,为今天的观众展现了赛璐珞胶片时代特有的观影仪式感,在礼堂里,不仅仅在中心场地上挤满了各色各样的人,礼堂的窗户和门口,以及中心舞台的两侧都挤满了人。镜头做了一个弧形运动,从中心场地运动到侧面,再从侧面运动到荧幕的后方,我们看到,原先用来清洗和擦拭胶片的后台,此时此刻也坐着满满当当的人;一个中景镜头告诉我们,这些观影的观众,即便处在观看视角很不好的侧面和后方,他们都带着欣喜和愉悦,欣赏着荧幕上的运动—影像。在我们今天的观影体验中,无论是在电影院,还是在家里,我们都会选择最好的观看角度。但是,那个时代不一样,如果能具有最佳的位置当然是最好的(范电影似乎正是通过帮人保留好座位获得了某种特殊地位,譬如多加一勺油辣子,媳妇们会让范电影的口袋里塞瓜子花生,等等),但倘若没有最好的位置,大家也毫无怨言,尽可能选择能看到荧幕的角度去观看,即便这个角度(比如荧幕的侧面)实际上看不到太多东西。从这个细节中我们似乎看到,在那个时代,看到电影的内容并不那么重要,与看到具体的人物和画面比起来,人们更关心的是看得到荧幕。也就是说,当电影从《南征北战》换成《英雄儿女》似乎并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在每个月的那天晚上能看得到电影,同样,至于荧幕上放的是《新闻简报》还是《英雄儿女》也不是那么重要,因为正如范电影所说,即便是《新闻简报》连续放映一晚上,二分场的观众也会跟着看一晚上。于是,相对于彻底理解电影的叙事和内容而言,人们更关心的是看到影像本身,至于情节,显然被置于次要地位。人们更希望的是,通过自己的身体性参与,加入到二分场的一月一度的狂欢当中,电影就是这个狂欢的媒介,通过电影的放映,整个二分场的世界被组织起来,形成了一个共同体,放映电影成为了那个时代二分场的固定的仪式。而通过这个仪式,人们被整体动员起来,在那一刻,日常生活的张家长李家短都被悬置了,人们尽情参与在白色光线照射下的狂欢,电影成为了这个巨大的狂欢派对中的物神,在电影凝聚的力量下,二分场成为一个被电影塑造出来的共同体。正如法国思想家维希留曾这样描写道:“当电影放映厅陷入人造的黑暗中,它自身的轮廓和坐在大厅中的人们便悄然消失。遮挡荧幕的幕布升起,就重现出涅普斯的原始仪式。”[1]45
如果说古希腊戏剧是实现城邦共同体政治教育的仪式,那么在张艺谋的《一秒钟》中,电影也成为这种凝聚人民群众的仪式,在这里,电影不仅仅是艺术性的,更是政治性的。在古希腊传统中,戏剧和仪式从来不是独立的艺术形成,参与仪式和观看戏剧,本身就是让城邦成为城邦,让诸众成为公民的过程。正如尼古拉斯·赫隆(Nicholas Heron)指出:“仪式体系成为古希腊城邦行政治理体系的一部分,而这种体系也贯穿了整个希腊化和古罗马时期,并在托勒密时期的埃及达到巅峰,托勒密的埃及会一次性要求几乎全体人民都参与到仪式中来。”[2]4如果从赫隆的角度来看,我们便可以理解,在《一秒钟》所设定的时间和空间里,看电影早就不是一种纯粹的艺术和娱乐形式,而是一种仪式,一种政治仪式。在这种仪式化的狂欢中,人们的身体性的参与和聚集,形成了一个悬置日常生活和区分的共同体,在电影荧幕前,日常生活的身份都悬置了,那里只有观众。这种悬置的最极端情况,就是当保卫科的崔干事在抓住并绑好了张九声之后,在礼堂里一起重看了《英雄儿女》,一个不经意的镜头显示:被绑在地上的张九声和作为政治符号的崔干事一起流下了泪水。只有在看电影的过程中,崔干事才不再是崔干事,他会与寻常人一样流下泪水,而张九声也忘却了自己的身份,和抓住自己的保卫科成员们一样地看着荧幕上的影像。在这样的环境下,《新闻简报》加上正片放映的模式才能起到最佳的政治教育的效果,在《一秒钟》的小空间里,荧幕上的影响能够将二分场统一为一个整体,在整个国家层面,放电影和看电影的仪式也将中国建构为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的中国。
三
然而,事情总有一个例外。这个例外是,本来准备看完一秒钟镜头就走的张九声折返回来,向范电影说:“一秒钟太短,不够看!”从情感上,张九声的要求是能得到观众的同情与理解的。不过,真正例外的不是张九声的要求,而是范电影的回应,范电影不仅答应了要求,而且用自己的独门绝技完成了一个大循环,反复在荧幕上播放着张九声女儿的一秒钟影像。而完成这个大循环操作之后,作为放映员的范电影有些自鸣得意,并号称整个农场只有他会这个绝活。怎么理解这个特殊的设定?既然在《一秒钟》设定的时空中,电影成为了二分场这个小镇上的物神,所有的人的关系都几乎围绕着放映电影的结构组织起来,那么,在电影背后有一只操作性的手,在放映机背后控制着整个播放仪式的进行。当然,在一般情况下,放映员并不能成为一个主体,他的存在仅仅实现了电影放映机的自主运动,他偶尔只会在换片或烧片的情况下出场,履行他们的职能。不过,《一秒钟》里的范电影并不仅仅只有这个功能,他有改变电影播放结构的能力。一方面,他具有能力决定先放《英雄儿女》,后放《新闻简报》,但更重要的能力是,他能做出剪辑,完成一个原本胶片中不存在的电影运动,这个运动就是他所谓的大循环。在《一秒钟》中,导演十分细致地为我们展现了范电影如何炉火纯青地实现了他特有的剪辑能力,然而,恰恰是范电影的这个能力,让他获得了一个超越于普通电影放映员之上的地位。正如德勒兹曾强调说:“剪辑就是创作(composition),是运动—影像的装置(agencement),让它成为时间的间接影像。”[3]47简言之,从德勒兹电影理论的角度来看,一旦范电影完成了大循环的剪辑,他实际上完成了一个新的电影影像,尽管这个电影影像是专门为张九声生产的。不过,正是因为他的这种随意剪辑的能力,让他成为了电影放映之上的主体(subject),而不是一个代理人(agent)。于是,范电影深刻理解了这种权力带来的一种潜移默化的优势,他所感到欣喜的不仅仅是为几个人提供几个前排座位的权力,也不是多加一勺油辣子的好处,而是一种凌驾在电影之上的权力,一种可以通过自己的剪辑手段,来决定电影的创作权力。这是一种生成电影的权力,也是生成共同体的权力,这种权力不能简单还原为体制内职位的好处,而是他在隐隐中看到了他不仅决定了礼堂之内的电影放映,也决定了二分场这个政治共同体的构建,而他无疑将自己放在了这个共同体的主体位置上。因此,一旦这个职位遭到威胁,一旦诸如杨河之类的人物试图来挑战他的地位时,他才会不惜做出违反良心的行为来保住这个共同体隐形掌控者的虚幻地位。
然而,《一秒钟》的世界最终在张九声女儿的电影胶片永埋黄沙之中结尾,似乎在张艺谋导演看来,这隐喻着那个曾经的胶片电影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在那一刹那,我们仿佛迅速地被画面冲击回到现实,我们突然明白,张九声最后的遗憾,最终不再是数字媒体时代的问题,因为今天的一秒钟的画面,就是24帧画面组成的文件,只要我们鼠标轻轻地一点击,或者我们的手指轻轻触摸屏幕,就可以轻松地制作一个副本。而范电影的绝技也不再是什么绝技,在电影剪辑方面,很多普通用户已经能使用PR、Vegas、Edius等软件实现比他更为炫酷的操作,让电影可以随时被编辑创造,不断生成出新的版本。问题在于,在这样一个数字化技术成为主流,5G通信和万物互联技术让我们观影体验日新月异的时代里,我们是否还能期望电影的影像拥有一种强大的政治动员力,让人们在看电影的名义下被整合起来成为一种巨大的力量(就如同《一秒钟》的范电影对整个二分场的动员一样)?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尽管在一些学者看来数字化技术并没有真正改变电影的本质,如罗多维奇(D. N. Rodowick)曾认为,“毫无疑问,电影艺术通过数字过程的整合不断地更新和重塑自己,同时某种电影的理念也被融合到互动媒体的发展之中。在这里,类似的艺术并没有被数字技术所取代,而电影的理念仍然会在新媒体中持续存在,成为视觉参与和观众想象的主流文化和审美模式”[4]97。然而, 在十多年之后,数字媒体的发展显然超出了罗多维奇的想象力,所以,在新近的后电影和数字电影研究中,人们不仅看到了数字媒体和互联网互动媒体正在重新定义着影像的可能性,比如网飞(Netflix)公司的作品《黑镜:潘达斯奈基》(BlackMirror:Bandersnatch,2018)实际上需要观众参与影片中的互动,像游戏一样选择选项,从而改变电影的结局。而这种多线程的电影观看,不再是将影像的内容局限在一两个小时的内容中,因为这种互动性的电影模式,看完全片并没有实质性的意义,而更有意思的地方在于观众的不同选项导致了什么样的组合,从而生成了一种新的电影。换言之,原来专属于具有某种特殊技能的放映员的权力,已经从放映室走向了每一个屏幕面前,而每一个观众都可以在自己的选择中实现对影片的重新组合和剪辑,去让潜在的可能性得以实在化。
《一秒钟》是一个不错的尝试,张艺谋导演试图在数字化媒体时代去回顾一个业已淹没在历史黄沙中的观影方式,即在类似于二分场礼堂空间中用电影放映机来放映赛璐珞电影的方式,那里有一种观影的共同体,人们在观影中被整合为一个光学技术装置下的整体。然而,无论如何帮助今天的观众去体验这种经验,张艺谋导演也十分清楚,那个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正如美国电影研究学者罗格·F.库克(Roger F. Cook)指出:“就是说,正如胶片电影让20世纪中早期的城市居民的神经中枢网络去适应了一种更快速、更高度机械化的现代文化一样,那么今天的数字电影影像也让我们进一步适应了一种新的文化环境,即我们生活于其中并在很大程度上被数字技术所中介的环境。”[5]182库克的说法没有错,今天我们的感觉神经中枢系统已经被更为弥散的数字化技术和媒体所中介,正是这种中介,让今天的人们已经很难再体会到赛璐珞胶片时代的共情,以及在电影放映中形成的共同体。与之前的共情性的感觉相比,今天的数字化媒体让我们更集中于个人化的观影体验,更数字化的拟真感,以及更炫酷的影像效果。在这种观影效果下,我们的感觉神经中枢已经被连根拔起,变得与周围的世界相分离,这样,今天的影像不再是构建共情的影像共同体,而是转向了被数字技术介入的个体,数字化技术不断对我们的观影体验进行数字化图绘(digital profiling),让我们找到让自己更惬意的影像和观影感受,也意味着数字化的媒体在生成着我们的感觉中枢,它们会比我们自己更了解我们自己,让我们日益沉浸在这种体验之中,让我们身体和神经中枢同时成为巨大的算法机器和大数据结构所俘获的生命。
被黄沙埋葬的赛璐珞,意味着胶片电影时代的逝去,也意味着曾经的电影架构的共同体的解体。数字化时代的《一秒钟》成为了埋葬赛璐珞时代的电影,因为我们今天也在自己的数字环境里欣赏着这部影片。或许,《一秒钟》更像是沙漠中的一阵狂风,它曾吹起了覆在胶片上的沙尘,让胶片露出了一点点痕迹,然后再次被新的黄沙掩埋,让它继续沉浸在无尽的沙漠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