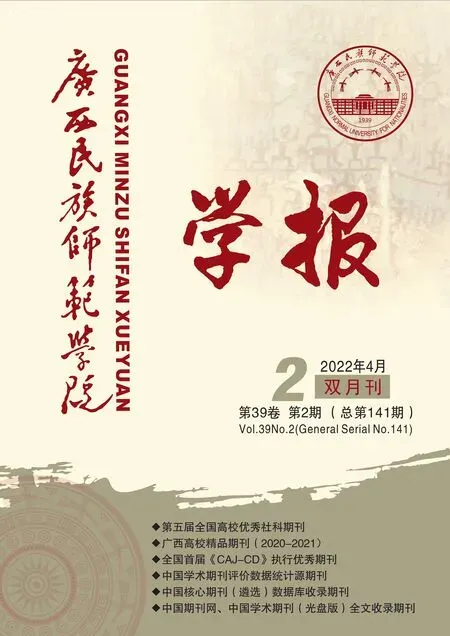广西河池市东兰县花香乡乌洋神戏唱本探析
杨绍玉
(南宁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1)
一、研究背景
乌洋神戏是源于汉代的戏种,800 多年前由四川遂宁传入广西东兰,扎根花香乡永安村。乌洋神戏是当地民众在还愿、祈祷等活动中所表演的戏种,故也称汉戏、还愿戏、发财戏等[1]。乌洋神戏作为广西东兰地区一种独具特色的戏种,已列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七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广西河池市东兰县花香乡的乌洋神戏属于阳戏,阳戏的研究成果众多。吴电雷认为阳戏从属于傩戏,或者说是傩戏的一个品种,是傩戏系统中戏剧表演因素更趋完备的剧种[2]。吴电雷还对西南地区的阳戏进行了系统研究,在分析各种阳戏形态的基础上,发掘了中国西南地区阳戏的共性和内在联系[3]。聂森对黔北地区颇具地方特色的民间祭祀仪式表演活动——舞阳神戏进行了研究,表演活动中演员脸上涂抹着的脸谱具有独特魅力,备受人们关注[4]。金德谷认为阳戏是傩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全称是舞阳神戏,简称阳戏,是祭祀仪式中进行的若干戏剧性表演[5]。胡天成将重庆阳戏和福泉阳戏进行比较研究,认为阳戏对传统戏剧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6]。乌洋神戏由四川传入广西,在广西河池市东兰县的传承过程中,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原本的内容和形式,东兰县花香乡的乌洋神戏曲目唱本与西南其他地方的阳戏唱本有诸多相似之处,但其在语言和所敬奉的神祇等多个方面融入了广西当地民族文化和地方特色,从而造就了东兰县花香乡乌洋神戏的独特性。笔者通过对东兰县花香乡乌洋神戏唱本的搜集、整理与研究,试图从唱本的内容、文化内涵、艺术特色以及唱本的功能、价值等方面进行探讨,助力乌洋神戏活态传承与保护。
二、乌洋神戏唱本的内容
阳戏在广西东兰县的流传过程中演变成乌洋神戏,乌洋神戏唱本的内容涉及广泛,但基本都是围绕“神灵叙事”展开,既有神话传说和传奇故事,也有民间世俗故事。总体而言,乌洋神戏的唱本内容分为三大类。
(一)请神酬神类
乌洋神戏的表演,始终围绕着“请神—酬神—驱鬼—送神”的主题来展开,并穿插一些其他类型的剧目来充实整个表演,体现出乌洋神戏作为仪式性戏剧既娱神又娱人的特征。乌洋神戏演出的主调是唱诵各位神灵,通过献牲和各种演戏献媚神灵,以期得到神灵的庇护。在表演《开坛》剧目前,要将请神仪式中用的铜锣、铰钵、木鱼、笛子等东西准备齐全,表现出当地民众请神的真诚情感和虔诚信仰。在表演《上捧香童子》剧目中,师傅敲锣打鼓,从川主、土主和药王开始请神,师傅在吟诵的同时烧香作揖,按照所敬奉的神灵依次请神,表示对神灵的尊敬。在《上头请》《上领牲》《二奏土地》《回熟》等剧目中,一次又一次地邀请和安顿各位神灵,重复唱演唱词,但是并未让听众觉得冗杂,体现民众祈求诸神帮助的虔诚期望。
在当地民众的传统观念中,通过表演乌洋神戏来请神酬神,是为了让神灵保自家平安、驱邪除恶。民众在神灵面前许下愿望,并许诺愿望成真后,就宴请各位神灵,以感谢他们的帮助,这体现出当地民间信仰功利性的特点。
(二)神话故事类
乌洋神戏中的神话故事戏,是仪式表演的主要内容,包括两方面的主题:一是神祇的身世经历和降临神坛的行程见闻,二是娱人娱神的传说故事。
在《上领牲二郎》剧目中有这样一段唱词:
别人胚胎十个月,我娘胚胎三年六个月。选得好年无好月,选得好日无好时。选得甲寅年六月二十四,子时生下小官员。家公取名叫川宝,家婆取名叫川针。只有我母多灵利,取名灌洲李二郎。①
这段唱本指出了二郎神的身世经历。二郎的父亲和母亲是仙凡配,其父为李坤王,其母是云台公主。云台公主在孕育二郎神时便显现不凡之处,凡人怀胎十月,而二郎却经三年零六个月才降世。蜀地水患,蜀太守李冰治水,民间认为是恶龙作怪才引发水患,李二郎在灌洲斩蛟龙,协助其父治水,百姓祀为二郎神。在乌洋神戏中,李二郎的形象源于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二郎神杨戬,东兰县当地民众在杨戬形象的基础上塑造了一个可以驱除一切冥界妖魔鬼怪、排解万般凶险的巨神形象。融合了多位神话人物特征的李二郎,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箭垛式人物形象。
在《上灵官》剧目中,提到了忠孝两全的潘角、舍身替死的李夫人、行善积德的黄真、敬老爱老的安安等人物,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孝文化。在乌洋神戏唱本中,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唤起民众内心的共情,折射仁、义、礼、智、信、忠、孝、节、义等伦理道德光环。如肖氏女和蔡伯喈的人物形象就生动地阐释了中华传统孝道,弘扬了至善至孝的优秀传统文化。
剧目《范郎》则以《孟姜女哭长城》中的范杞梁为原型,塑造了一个忠孝的范郎形象。“鼓打咚咚不要忙,听唱神州范杞郎。范郎死在沙场内,哭断长城是孟姜……”既写出了范郎被抓去服劳役的故事,同时也引出了孟姜女哭长城这一人们耳熟能详的传说故事。
(三)世俗生活类
世俗生活类的剧目主要是表现当地民众的生活状态,唱词中不仅包含当地民众对生活的理性思辨,还折射出中华农耕文化所浸染的永安村集体历史生活记忆。在众多世俗生活类唱本中,表达对美好爱情和婚姻生活的向往是最常见且深受当地民众喜爱的剧目主题。在《上张陀子》剧目中,年纪大且智力有问题的张陀子娶了一个年纪较小的妇女为妻,打工回来的表弟何小二向张陀子借妻回家。张陀子的妻子随何小二回家后再也不愿回到张陀子身边,张陀子将此事告到青天老爷那,青天老爷让他另讨一个妻子。这个剧目揭示了古代社会中不幸的婚姻现象,反映出古代社会伦理的价值取向。在《开财门》剧目中,通过男女情歌对唱,表现男女婚恋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转向自由婚恋的社会现象,体现了民众对自由恋爱的歌颂。在《上二请》剧目中,有这样的唱词内容:
头上搭张乌油帕,八幅罗裙紧缠身(哟依哟呀)。
四更鸡儿叫哀哀,女在娘房巧穿鞋(哟依哟呀)。
七尺白绫脚上绞,三寸花鞋脚下蹬(哟依哟呀)。
这几句唱词勾勒出了当时东兰县妇女的传统着装打扮,妇女头上包着乌油帕,穿着八幅罗裙,脚上着有七尺白绫和三寸花鞋。八幅罗裙是土家族的代表性服饰,可见当时各民族间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七尺白绫和三寸花鞋则体现了当地妇女尚存的裹小脚风俗。透过乌洋神戏的唱词,可以了解不同民族的民风民俗,可见东兰县当地民众对不同民族文化的接纳与包容。
三、乌洋神戏唱本的文化阐释与艺术特色
乌洋神戏的唱本由广大人民群众谱写,内容包含神话、传说、故事、民歌等,有古老、浓厚的民间文化气息,是民间文化的宝库。这些唱本在文化阐释、艺术特色方面具有多元化的特点。
(一)文化阐释
1.文化共生
乌洋神戏源于四川,作为外来文化在东兰县落地生根。在其传承过程中融汇了当地的民族文化特色,这在神灵崇拜和语言艺术等方面尤为突出。在乌洋神戏的神灵系谱中,充分体现了川蜀文化与广西文化共生的特点。川主、土主、药王合称为三圣,是乌洋神戏中所供奉的主要职能神。川主居于首位,指四川之主。乌洋神戏的唱词中除了川主等主要的职能神,也有许多当地民众信奉的地方神灵,比如“奉请看祭神王老祖、国王父母、部下随行土地,广西所属大殿大圣公婆、二殿二圣公婆、三殿三圣公婆,千和万何,合志梅花小姐、梅花小娘一路行……奉请广西德道三界公爷、社王天子、莫叶大王、峰师老爷、黑杂太子、飞山公主、广会猴王一路行……”这部分唱词中就包含了许多如社王天子、莫叶大王、峰师老爷等当地民间信奉的神灵,展现了不同文化在传播交流过程中的共生现象。
在语言艺术方面,乌洋神戏的表演使用的是当地方言——桂柳话。在桂柳话中,尾词“子”的使用很多,所以,乌洋神戏唱本里尾词“子”也大量存在。在《范郎》剧目中,就有大段包含尾词“子”的唱词,如“……右脚穿的是鞋子,走到一个坳头子,碰着他的大舅子,背上背的是背兜子,里面装的是荞子……”唱词中尾词“子”的应用,不仅符合当地人的用语习惯,而且丰富了唱词的韵律,使韵调更加生动欢快,缓解了酬神仪式中的神圣感,体现出村落语境中民族文化的交融。
总之,乌洋神戏以一种开放的姿态,不断融入地方的民俗和语言文化,文化共生是乌洋神戏得以扎根东兰文化土壤的根源。
2.儒释道文化的融合
乌洋神戏唱本中也包含着儒释道文化。儒家文化在乌洋神戏中主要体现为对“真善美”和“孝”文化的宣扬,通过一个个剧目的表演,对民众起到教化的作用。例如在《上灵官》剧目中,安安、潘角、黄真、目莲等人物,树立了“真善美”的典范,通过“羊有跪乳来报母,鸦有反哺报双亲”等唱词,告诫民众行孝的重要性。在《上白猿猴》剧目中,李二郎不畏艰险去桃山救母,将母亲救回后又为西川百姓制伏孽龙,生动形象地塑造了一个忠孝两全的人物形象。
佛教对乌洋神戏唱本的影响表现在供奉的观音等神祇及唱词中对佛家因果报应等观念的阐释。在表演《上头请》《上二请》《回熟》等剧目时,待所请神祇安座后,师傅便要念诵佛家《心经》全文,可见《心经》在乌洋神戏中的重要地位。
道教的鬼神崇拜与乌洋神戏也有联系。在乌洋神戏中,驱鬼逐疫以请神护法为前提,在开坛、请神、酬神、送神等行法事的过程中,须由师傅请三圣、诸路神仙和各家师主、师爷降临,进而才能行禳病、打鬼、消灾、还愿的仪式,这些请神酬神的仪式过程与道教的鬼神崇拜有很大的相似之处。
融合儒释道文化的乌洋神戏,满足了当地群众的需求,也获得了当地民众的认同,为乌洋神戏的发展奠定了群众基础。
3.丰富多彩的乡土内容
乌洋神戏的生长土壤在民间,民情风俗是其发展的养料。乌洋神戏中的乡土内容主要体现在文本中按需填补的信息、唱念时重复的词句和抄本中音同形异的字词等。
在乌洋神戏唱词中,一些涉及师傅姓名、愿主姓名、居住地址的信息,常用“Δ”表示,演出时根据具体时间和地点随机应变。如《上头请》剧目中的唱词:“中华人民共和国广西壮族自治区Δ 县Δ 乡Δ 村Δ 屯,土地祈下,居住奉神圣设供焚香,酬恩了愿迎祥信士。。。,缘人Δ 氏人等,右既合家卷等,即日投呈皈依莲座,上言伏以。”其中的“。。。”代表一家之主的名字,“Δ”则指地点或姓氏,根据展演地点及人物的不同进行应变的唱词,更加贴近民众的生活。有了这些地名和住宅的位置,可以拉近神界和人世的距离,更能让人产生崇拜敬仰之情。
在乌洋神戏的手抄本中,存在着一些常见的特殊标识性符号,这些符号重复出现在唱本中。例如有些唱段、唱词和易记的部分,抄录者就会用艺人熟知的符号来标识,表示字的重复。在《上捧香童子》唱本中就有“香烟渺∽透神门,贯洲迎请川王神”。使用“∽”这一符号,可以减少抄写者的工作量,减轻演唱者的记忆负担。
字词的音同形异是乌洋神戏乡土性的另一特点。乌洋神戏传播方式主要是口耳相传,口耳相传的不稳定性会造成一些同音不同字的异变现象,这是民间口头文化向书面文化转变的过程中常见的现象。乌洋神戏唱本由民间艺人所作,所以唱本也融入了很多与民众自身生活密切相关的乡土内容,以此引发民众的情感共鸣,让观众迅速融入乌洋神戏的表演氛围中。
(二)艺术特色
1.表述语言的乡土化
黑格尔认为,语言是可以传达精神的媒介,它是不占有空间的物质,和雕刻艺术中所使用的木、石等感性材料不同[7]。语言在民间口头艺术表现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乌洋神戏唱本里有许多通俗质朴的口语,既浅显易懂又形象生动。乌洋神戏是用桂柳话演唱的,语言通俗但不是“大白话”,它们大多经过传承人加工,语言简洁凝练。在《范郎》中,谜语的巧妙运用,凸显了范郎广博的知识面,也从侧面反映了农村妇女善于运用谜语的方式将生活中的事物巧妙地表现出来。
乌洋神戏唱本中还运用了十字调的艺术化表达方式,十字调不以字数而论,而是以词句中从一到十的应用来命名为“正十字”和“倒十字”[8]。如《上太子》里的唱词:
一字原来一条枪,二字原来二条龙。
三字原来不满街,四字原来不留门。
五字原来盘脚座,六字原来两脚蹬。
七字原来左脚钩,八字原来两边丢。
九字原来像把弓,十字原来线穿针。
这里就唱了4 次十字调,前3 次是以“正十字”的方式演唱,第4 次是以“倒十字”的方式演唱,这就使得剧目内容跌宕起伏,更具美感。
乌洋神戏属民众艺术,语言表达缺少文采而显得口语化,它不具文采却内容丰富,反映着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富有乡土气息的方言文化和独特的民族文化是其魅力所在。
2.人物塑造的生动化
欧洲传统戏剧贯以“情节”为第一性,而中国戏曲不论是文学的还是舞台的,却贯以“人物”为第一性[9]。乌洋神戏剧目的表演就贯以突出神或人物形象。乌洋神戏唱本中的形象大多是各类神祇、祖师等,既有佛教神灵,也有广西本土神祇,还有一些百姓形象。
《上捧香童子》《上城隍》《上张陀子》《上药王》《上太子》《上老王》《上青衣童子》《上报马郎君》《上领牲二郎》《上白猿猴》《上催愿》《上白旗小将》《上灵官》《延麽夫人》《开盘小鬼》《目莲和尚》《钟馗》《上范郎》《伯公伯婆》《老曹判子》等乌洋神戏唱本剧目,都是通过剧情的展演来塑造人物。如《上领牲二郎》剧目便是围绕李二郎展开叙事。剧目中的李二郎身着缎子黄服饰,携有金弓、金盆等物件,运用夸张的叙述手法对李二郎的衣着、配饰等进行描写,塑造了家世显赫、身具神力的人物形象,表现了当地民众对富裕生活的向往与追求。人物刻画生动形象,彰显了乌洋神戏艺人解读生活的艺术表现力。
3.叙述方式的灵活化
乌洋神戏唱本在人物叙述方式上主要表现出叙事体为主、代言体为辅的特点。叙事体,主要是用第三人称的口吻进行故事说唱,用来介绍人物、叙述故事情节。如《开坛》《上捧香童子》《上头请》《回熟》《二奏土地》《送神》等剧目就是以叙事体进行展演。代言体是指戏剧文学演绎的一种体裁,是相对叙事体而言的,指一个或几个艺人相互配合,或说或唱进行表演,主要表演者同时承担说唱的任务,即作为第三者叙述故事情节、描绘人物形象,构建故事脉络,自己或者其他艺人代言作品中人物语言,用人物声口来演说角色[10]。如《开财门》《上城隍》《上张陀子》《上老王》等剧目就是以代言体对唱本进行叙述。在乌洋神戏的表演中,师傅多以第三人称开始赞唱所请之神,在叙述神的经历或遭遇时,则以神的身份进行表演或对白,在剧情结束之后,恢复第三人称的身份。
在《上药王一宗》这一剧目中,师傅开始是以第三人称的说唱进入叙事,在介绍药王的身世和经历时,转变为第一人称,以药王的身份进行自述。这样的叙述模式在唱本中多次出现,师傅身份的转换也使表演更灵活多变。因此,艺人就像一个说唱表演者,既要向观众唱神的故事,必要时又要进入故事里,变成故事中的角色进行自述,唱完了角色的故事后,再以说唱者的身份往下叙述[11]。表演过程中,有时因剧情的需要,也有一人饰多角的情况。师傅在时进时出中,完成了人物刻画、故事叙述、请神酬神的任务。
四、唱本的价值
乌洋神戏除了满足民众的基本诉求,还具有多方面的价值。
(一)文化价值
乌洋神戏的演出场所一般是在民众家中,师傅通过仪式表演取悦神灵,祈求主家人丁兴旺、出入平安、身体健康,表达民众的生活愿景。一些表现扬善惩恶、规正风俗、德教化民主题的剧目,则反映了当地人尊师重道、忠孝伦理等观念,有助于塑造和丰富民众的价值观。乌洋神戏唱本中还蕴含了很多农业生产知识和社会生活基本常识,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从事生活、生产活动。乌洋神戏既娱神又娱人,在当地民众生活中,乌洋神戏的演出是人们一年之中难得的消遣活动,师傅们的表演也成为当地民众生活的调味剂。
(二)文学价值
乌洋神戏唱本作为广大民众共同谱写的艺术文本,体现出独特的朴素之美,是广西民间文学艺术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简朴浅显的语言,娓娓道出现实生活,通过仪式展演高大的神灵形象。乌洋神戏唱本通常以质朴的语言阐述故事的情节,在基本情节单元的基础上,师傅依据具体的演述场景重构故事,将唱本中的内容活灵活现地展演出来,这便是民间文艺的独特魅力。从广大人民群众中来,再到人民群众中去,乌洋神戏唱本蕴含着广大民众的集体艺术巧思,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三)研究价值
从民俗学的角度来看,乌洋神戏唱本中蕴含着人民群众的物质精神生活和风俗礼仪等多方面的内容,仅从戏曲本身来看,唱本中的神祇、祭祀行为以及神灵体系等是民俗学研究的对象。从语言学的角度看,乌洋神戏唱本是用口头语言进行创作,包含了东兰县丰富的语音、词汇和语法内容,是语言学的研究资料。
结 语
综上所述,乌洋神戏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有着独特的内在生命力,在当地民众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随着社会和文化的不断发展,乌洋神戏生存的土壤以及传承的空间逐渐被压缩,对乌洋神戏唱本的整理和研究迫在眉睫。作为地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乌洋神戏急需社会的关注与保护。本文通过对唱本的研究,希望能使大家对乌洋神戏多一些了解,为乌洋神戏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思考。
注释:
①文中引用的唱本内容均源于广西河池市东兰县花香乡乌洋神戏传承人刘顺海所存手抄本《乌洋神戏全集》。本文得到刘顺海的大力支持,他为本文提供了唱本内容,并对笔者的疑惑作了详尽的解答,在此也对其表示深切的感谢。